我的朋友李章
2022-10-11文字孙国忠
文字_孙国忠
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谈谈李章,但直到今日才动笔。感谢《音乐爱好者》的“音乐与阅读”栏目,让我有机会用随笔的文体漫谈音乐书籍和与“音乐阅读”相关的书人书事。音乐书籍浩如烟海,我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介绍与评说,一方面是我认为这些书的内容有意思,值得分享;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书给予我美好的回忆,看到它们就让我想起先前的读书情境和因书结缘的师友。对一个爱书人来讲,每本认真读过并乐意收藏的书都是有故事的,书本内外的人与事在很大程度上丰润了文本阅读的文字记忆,形成书籍认知和阅读体验特有的个体化情感积淀。

01 李章(左)与朱践耳(中)、戴鹏海(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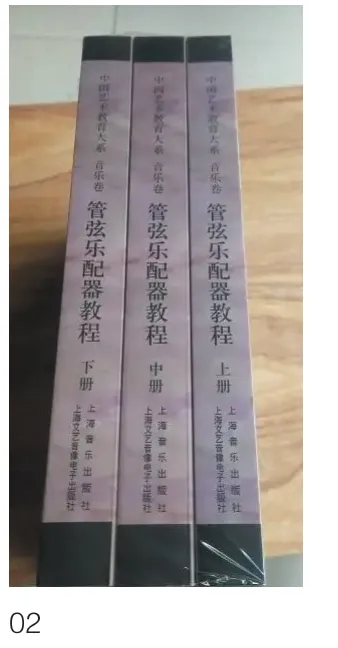
02 《管弦乐配器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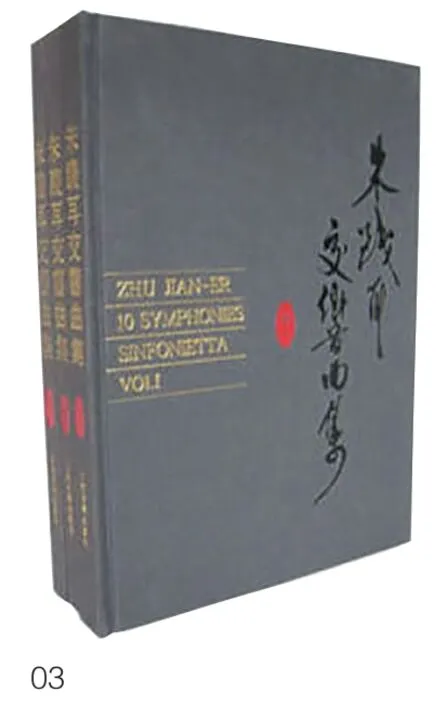
03 《朱践耳交响曲集》
想写李章,当然与音乐和书有关。李章并非名人,退休之前他只是上海音乐出版社的一名资深编辑,编过十余年的《音乐爱好者》杂志,作为责任编辑还编过一些乐谱和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朱践耳交响曲集》《管弦乐配器教程》和《辛丰年音乐笔记》。我有多位在出版社做编辑的朋友,对他们的工作我充满敬意。编辑是为人做嫁衣的职业,每一本好书和每一篇好文章的问世都离不开编辑的辛勤工作。进而言之,如果你与一位好编辑成了朋友,你会深深体会到:优秀的出版物不仅承载了作者的思想和创造力,还包含了编辑的学养和智识。李章就是这么一位富于学养和智识的好编辑。
第一次与李章见面是1990年初夏,地点在上海艺术剧场(现已恢复原名“兰心大剧院”)。我已忘了去看什么演出,但清楚地记得与李章初次见面的场景。那时李章刚开始编《音乐爱好者》,沈庭康兄介绍我们认识,简单交谈之后,李章就热情约稿。得知我即将赴美国留学,他希望我以后能为《音乐爱好者》写一些介绍国外乐坛动态和音乐人物的文章。我一口答应下来,感谢之外还表示会努力写作。这么爽快地答应李章的约稿,是因为我被他的诚恳打动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待人诚恳的人,所以我很乐意结识同样诚恳的人。如果相识后能成为朋友,那当然更好。李章相貌端正,举止大方,有一种正气的亲和力,这自然增强了我对他的好感和信任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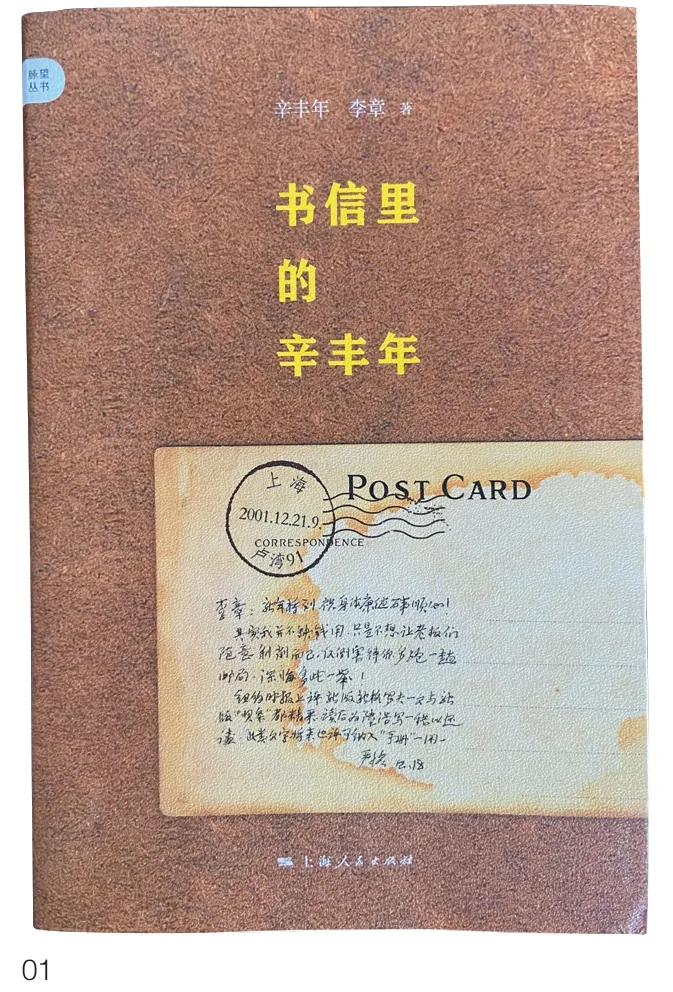
01 《书信里的辛丰年》

02 《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
我到美国读书后因忙于博士学业,只为李章写了几篇文章,真是愧对他的热情约稿。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有了通信联系,渐渐熟悉起来并成了朋友。李章对音乐的热爱、对办刊与组稿的投入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他对朋友的真诚和热情让我特别感动。1994年暑假我从美国回上海度假,回国前就与李章约好要去看望他。那是个炎热的下午,我按约定时间前往李章家。让我想不到的是,李章担心我找不到家门,竟顶着大太阳提前来到路口等我,由此可见他待人的真情和实在。那天我与李章一直从下午聊到晚上,他太太王安忆也在家,晚饭就在李章家吃的。具体聊什么我已记不清了,话题肯定都与音乐和艺术有关。临走前李章还送了我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库尔特·布劳考普夫的《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这本音乐学名著我保留至今。
2000年我回国后重回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与李章时有联系,这种联系依然以工作为主。我们也经常在听音乐会和看歌剧时见面,开演前或中场休息时的交谈虽然时间不长,但聊得很开心,彼此舒服。我们都是真正的乐迷,到音乐厅和大剧院现场欣赏音乐会和歌剧演出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新世纪伊始,上海音乐出版社就接到一个大项目:编辑、出版《朱践耳交响曲集》。朱践耳的十部交响曲堪称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座丰碑。朱践耳先生的音乐不但展示了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和艺术情怀,而且呈现出蕴含深意的历史审思。正是这种具有反思意识和人文精神的音乐创作,使得朱践耳的交响曲在震动中国乐坛的同时,也引起了知识界和爱乐人的很大关注。这套三卷本作品曲集的出版是一项大工程,因为这是中国音乐作品出版史上第一次用“手稿版”的样式印制一位作曲家的“交响曲集”,而李章正是这项大工程的责任编辑之一。毫无疑问,李章是《朱践耳交响曲集》最合适的编辑人选。他早年曾在地区文工团担任过作曲与指挥,先前的音乐创作和指挥乐队演奏的经验是一种很好的艺术积累,有助于他研读、校阅朱践耳先生的交响曲总谱手稿。不过,我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李章对朱践耳先生的崇敬和对其作品的热爱,再加上他极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据我所知,朱践耳先生和夫人舒群老师是非常信任李章的。我能够想象朱践耳先生与李章一起讨论谱面上的各种技术问题和商量曲集编订、出版事宜时的愉快心情。这套手稿版的《朱践耳交响曲集》能够顺利出版并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作为责任编辑的李章有着汗马功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作曲理论“四大件”中的和声、复调、曲式(或称“曲式与作品分析”)的专著出版了不少,独缺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分量的管弦乐配器著作。因此,纳入国家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建设项目和“中国艺术教育大系·音乐卷”的《管弦乐配器教程》就成了中国音乐界和高等音乐院校师生们翘首以盼的书。人们热切期盼这部配器专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的作者是杨立青教援——当代中国管弦乐配器研究的“首席专家”。杨立青先生是杰出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多年精研管弦乐配器,他在这一专业领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建树建立在他对中外管弦乐作品的大量音乐文本细读与分析的基础之上。倾注了杨立青先生多年心血的三卷本《管弦乐配器教程》既是高规格的教科书,又是一部独具品格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可谓是中国音乐界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彭志敏教授对此书的评价很到位:“通观全书,可谓理论与经验交融,智慧与灵性贯通,剖析与点评同步,讲授与练习齐备,乐谱与音响配套;有继往,有开来,有集成,有创新,有明道,有觉悟。”
在我看来,除了必须掌握管弦乐配器技术的专业作曲家之外,真正心仪交响乐并有总谱阅读能力的人(无论是音乐学者还是高水平的爱乐人)都会对交响乐作品的管弦乐配器感兴趣。在这种形式的音乐创作中,作曲家的乐思、和声、织体与结构最终都体现于管弦乐的音响建构中,而细读总谱了解乐曲的管弦乐配器是深入理解交响乐作品之音乐形态特征最重要的环节及路径。李章挚爱音乐,又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做这部管弦乐配器专著的责任编辑,能够亲自编辑这部专业性很强的著作对他来讲是一次再度研修管弦乐配器的好机会。然而,身为责任编辑的李章也有苦恼,因为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杨立青先生公务繁忙,迟迟不能交稿。当时我很关心这部著作的出版,每次见到李章都会询问此书的进展,他都是微笑地回答:“还在等待书稿。”这部《管弦乐配器教程》从纳入选题到最终出版(2012年),时间跨度超过十年,李章可谓“苦苦等待”,全力相助,这种执着的编辑态度和工作热情显然渗透着他对管弦乐写作之理论与实践的钟爱。
《朱践耳交响曲集》与《管弦乐配器教程》这两套大著的编辑与出版足以证明李章作为音乐编辑的优秀。除了这两项专业性很强的音乐与音乐理论出版的耀眼成果,李章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他执事《音乐爱好者》的十余年里,拓展了这本音乐杂志的“疆土”,开阔了爱乐言说的人文视界和艺术论域。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于李章的盛情邀约,辛丰年先生才能心情舒畅地为《音乐爱好者》撰写众多谈音论乐的文章,让广大读者体会音乐艺术的别样滋味和趣味,也使音乐界的“学院派”感觉到“爱乐”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与爱乐人群体之艺术能量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讲,没有李章的盛情邀约和对辛丰年的关爱与帮助,这位在三线城市隐居的老人不可能有如此高涨的写作热情并贡献这么多独具特色的爱乐文字。上海音乐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了六卷本的《辛丰年音乐文集》,其中大量文章都是先前在《音乐爱好者》上发表过的。

《辛丰年音乐文集》
关于李章这方面的工作和功劳,可仔细阅读《书信里的辛丰年》,这是辛丰年与李章的“两地书”,记录了他们二十多年的交往——从最初的作者和编辑关系发展到挚友,维系这对忘年交深厚友谊的是他们的爱乐真情和做人的纯粹。2015年李章赠我此书,我读后深受感动,它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李章的为人、修养和品格。李章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他对辛丰年先生的尊敬、关爱和用心尽力的帮助令人动容。1991年3月,李章第一次去南通拜望辛丰年,他这样回忆道:“辛丰年焕然一身新军装,早早地等在我入住的有斐饭店门前,濠河在他身后流淌,这画面庄严郑重,令我肃然。我深知这是对《音乐爱好者》的看重。这种态度,似老一辈人才会有。”2013年辛丰年去世,李章和同事樊愉赶往南通参加先生的追悼会。李章一身黑色正装,这让樊愉和前来迎接的好友吴维忠都感到惊讶,他们从未见过李章这般穿着。李章写道:“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是还先生的一份情义,这情义欠得太久,整整二十二年!我与辛丰年第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贝面,就像奏鸣曲式的两端,呈示与再现;着装是主题,我来完成‘仪式’的再现。”
读此书我才得知,李章于1997年3月27日写给辛丰年的信中还提到了我,这让我感到亲切。当时辛丰年很想读保罗·亨利·朗的英文名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李章正为他想办法借书,并已为老先生复印了若干章节。信中李章这样对辛丰年说:“正好新一期《爱乐》孙国忠的文章也提到了这本书。这几十年就没有书能够超过它。好像孙国忠的意思他也有这书,正好他即将学成回国,我和他也很熟,到时候再问他借。您先用复印件解解渴吧。”看到这里我真是感慨,如果早知道就好了,我肯定会去买一本《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尽快托人带回国内赠送给辛丰年先生。
屈指一算,我与李章认识已有三十多年。李章一贯低调,退休后更是很少露面,我也没有主动约过他,上一次见面好像还是疫情前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看演出时的不期而遇。除上文提到的多年前去他家拜访并被留饭,我们再没有另一次的共进午餐或晚餐,用“君子之交淡如水”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适的。我很欣慰有李章这样的好朋友,很看重与他的交往和友情,写这篇文章就是想表达一下这样的心意。希望哪天再去听音乐会时又能见到李章,随便聊上几句也是愉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