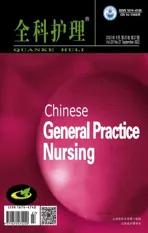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2-09-26刘倩倩
刘倩倩,徐 姗,高 伟,史 可
产褥期是指从胎盘娩出至产妇全身各器官除乳腺外恢复或接近正常未孕状态所需的一段时期,一般为6周[1]。该期是产妇分娩后身心恢复的关键时期。初产妇由于无生育经验且需在产后面对繁重的育儿任务,亟需来自家庭的帮助与鼓励,而配偶作为伴侣是家庭支持的重要来源。育儿参与是指通过参与婴儿的日常生活照顾、互动沟通和关怀陪伴,满足婴儿身体、情绪、心理等方面的需求[2]。有研究显示,配偶参与婴儿的照护活动能够增进夫妻亲密关系,减轻父亲压力、焦虑,对婴儿智力发育、性格培养以及平等的性别角色意识均具有良好的影响[3-5]。西方学界关于配偶育儿参与的研究已有40多年,相关的理论与成果已趋于成熟[2]。而我国对于配偶育儿参与的关注较晚,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及心理学,研究内容主要是探讨配偶在子女幼儿期、学龄前期或学龄期中的亲职参与情况[6-8],而从临床医学视角对产褥期初产妇配偶的育儿参与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从临床医学视角出发,通过对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现状进行调查并分析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针对性的临床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1年9月—2021年11月济南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陪同产后复查的初产妇配偶为研究对象。要求产妇:单胎妊娠;分娩后6~8周。要求初产妇配偶:意识清楚,无认知障碍,能独立完成调查;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有严重产科合并症或并发症产妇的配偶;婴儿因各种原因不在身边者。横断面调查样本量至少为自变量的5~10倍[9],本研究中共包括23个变量,故样本量至少达到115~230人。考虑到15%的无效问卷,本研究应收回问卷132~265份。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研究目的和内容自行设计,包含一般人口学资料及产科相关资料。其中,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居住地;产科相关资料包括是否计划中怀孕、分娩方式、期待婴儿性别、有无陪产假。
1.2.2 父亲育儿参与量表(Father Caretaking Inventory,FCI) 该量表由Nugent[10]编制,孙洁等[11]汉化,用于评估配偶育儿参与程度。共包括陪伴睡眠(2个条目)、护理身体(3个条目)、哼唱儿歌(1个条目)、陪伴玩耍(1个条目)、喂养(1个条目)和安抚(2个条目)6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法评分,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5分,总分10~50分,分值越高表示其育儿参与程度越高。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1.2.3 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C-PSOC) 该量表由杨晓等[12]汉化用于评估产妇配偶的育儿胜任感。包括育儿自我效能和育儿满意度2个维度,17个条目。采用6级评分法评分,绝对不同意、不同意、少许不同意、少许同意、同意、绝对同意分别计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其中条目2~条目5、条目8、条目9、条目12、条目14、条目16 采用反向计分,总分17~102分,分值越高说明育儿胜任感越好。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采用肖水源[13]编制的量表评估配偶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10个条目,条目1~5、条目8~10每个条目按1~4分评分,条目6、条目7若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若从“9个问题”中选择选几个计几分,总分为各条目的总和。分值越高说明配偶获得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9。
1.2.5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在配偶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由研究者本人统一发放纸质问卷,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68份,有效回收率为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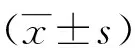
2 结果
2.1 孕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得分情况 本研究中孕产妇配偶FCI得分为(30.66±8.29)分,各条目均分为(3.07±0.83)分。各维度得分见表1。

表1 初产妇配偶FCI得分情况(n=268) 单位:分
2.2 影响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单因素分析 268名初产妇配偶年龄22~36(28.80±5.21)岁。结果显示,初产妇配偶年龄、文化程度、有无陪产假及孕产妇分娩方式与配偶育儿参与有关(P<0.05)。详见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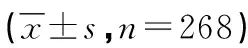
表2 影响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单因素分析 单位:分
2.3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育儿胜任感和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初产妇配偶FCI得分为(30.66±8.29)分、C-PSOC得分为(73.33±11.41)分、SSRS得分为(41.47±7.39)分,在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中,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得分最低,为(7.94±2.02)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初产妇配偶FCI得分与C-PSOC得分呈正相关(r=0.360,P<0.05);初产妇配偶FCI得分与SSRS得分呈正相关(r=0.318,P<0.05)。
2.4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以初产妇配偶FCI得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3。结果显示初产妇配偶年龄、文化程度、育儿胜任感及社会支持4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可解释配偶育儿参与变异的32.7%,见表4。

表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4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产妇配偶FCI得分为(30.66±8.29)分,条目均分为(3.07±0.83)分,处于中等水平。由于测量配偶育儿参与的工具、时间范围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略有差异。陈荣等[14]采用中文版育儿联盟量表对产褥期初产妇配偶的育儿参与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孙洁等[11]采用FCI测量3个月月龄内婴儿父亲的育儿参与,结果显示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处于偏低水平。提示初产妇配偶的育儿参与度仍需提高。医务人员应关注影响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因素,通过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方案和应对措施,促进其育儿参与。
3.2 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影响因素分析
3.2.1 年龄 本研究发现,年龄是配偶育儿参与的影响因素,越年轻的配偶育儿参与度越高,这与傅冰燕[2]的研究相一致。本研究中年龄22~30岁的配偶FCI得分高于年龄≥31岁的配偶。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由于年轻的配偶对初次进入父亲角色感到兴奋,为新生命的到来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另外,年轻的配偶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能以一种平等性别角色态度履行父亲职责。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年轻的配偶家庭压力及职业压力相对较小,而年龄较大且事业处于上升期的配偶不得不分出更多的精力在工作上。建议医务人员要更关注年龄≥31岁的配偶,教育并鼓励他们更多地承担育儿职责。
3.2.2 文化程度 本研究发现,配偶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参与育儿度越高,与古艳芳[15]的研究相一致。一方面可能由于文化程度高的配偶,自学能力强,能够利用现有资源快速掌握婴儿护理的相关知识及技能,而知识及技能水平的提高将促进育儿参与的实现[16];另一方面文化程度高的配偶,对父亲角色意义有更积极的认同,重视对孩子的陪伴与交流,并内化为行为,具体体现在有较高的育儿参与。因此,医务人员在进行健康宣教时应将文化程度较低的配偶作为重点的干预人群,在提高育儿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还需重视参与意识的培养与提升。
3.2.3 育儿胜任感 本研究发现,配偶的育儿胜任感越好,其育儿参与度越高,这与Shorey等[17-18]的研究相一致。有研究表明,当父母认为自己有能力照顾婴儿时,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不仅能对其心理状态产生积极影响,还能对家庭氛围及婴儿的健康成长产生积极效应[19]。本研究中部分初产妇配偶因缺乏照护婴儿的知识和经验,信心不足,导致育儿胜任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建议医务人员可采取线上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孕妇课堂、手机APP或微信公众号等多元化方式向配偶提供育儿信息及技能的指导,提高配偶的育儿知识水平,提升其育儿信心及育儿胜任感,以促进其育儿参与。
3.2.4 社会支持 本研究发现,配偶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育儿参与度越高,这与李敏谊等[20]的观点相一致。社会支持水平高意味着婴儿父亲从医务人员、朋友、家人等处获得的关心、帮助多,积累的经验多,就越能提升他们照顾婴儿时的能力和信心,从而促进其育儿参与[21]。本研究社会支持的3个维度中,对支持的利用度维度得分最低,可能由于配偶受男性独立性格的传统观念影响,在育儿参与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积极向外界寻求帮助,而是自己设法解决,导致对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度低[22]。建议医务人员可提供针对配偶的育儿教育资源,对其实施延续性护理,如建立微信群、QQ群,当碰到育儿问题时鼓励配偶主动向支持资源寻求帮助,帮助其克服育儿过程中的困难及挑战。
4 小结
本研究对产褥期初产妇配偶育儿参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示配偶的育儿参与处于中等水平,与配偶的年龄、文化程度、育儿胜任感及社会支持等因素有关。医务人员可据此为参考,针对影响因素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以提高配偶的育儿参与度。但受人力、物力所限,本研究仅采用量性研究的方法收集了济南市1所三级甲等医院的资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倚,表现为研究地区为城市,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研究对象整体文化程度较高,可能会对分析结果造成局限。未来可在农村、低学历的人群中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也可考虑结合质性访谈,更加深入全面了解影响配偶育儿参与的因素,为提高其育儿参与度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