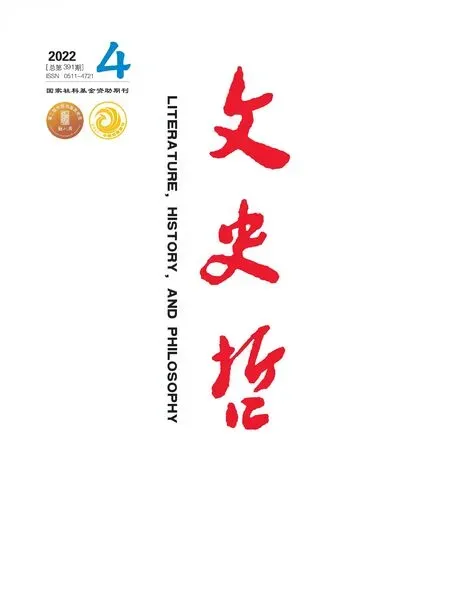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中的史诗
——以屈原和《离骚》为例
2022-08-10柯马丁姚竹铭顾一心郭西安
柯马丁 撰 姚竹铭 顾一心 译 郭西安 校
一、引言:“文化记忆”与早期中国文学
“文化记忆”是一种与历史实证主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它所阐明的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下,意义和身份被社会性、制度性以及物质性元素所构建的过程和实践,它所尝试解释的是各个社会如何通过探究其奠基性叙述、神话信仰以及文化流程来理解它们自己。这一理论业已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共有的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概念,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学界。这一概念首先由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古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于1988年提出,后在其1992年出版的《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ä:,äü)一书中得以成熟发展。阿斯曼随后的英语著作及其相关主题研究的译作更进一步提升了该理论的知名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的英语及文学研究教授阿莱德·阿斯曼(Aleida Assmann)也着手出版了她关于“文化记忆”的大量研究。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集中于古代,尤其是古埃及、以色列和希腊,与之相较,阿莱德·阿斯曼的视野则一路拓展到了20世纪,且更为关心更宽泛的概念性问题。
很可能是因为两位阿斯曼教授的核心研究直到其德语原著出版多年后才进入英语世界,“文化记忆”这个概念为中国文学研究所注意也相对缓慢。诚然,更早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已有个别作品对中国文学中追忆的实践有过反思,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以及傅汉思(Hans Frankel)的论文《唐诗中对于过往的冥思》(“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in T’ang Poetry”)。二者的出现皆先于“文化记忆”这一概念,且二者的研究重心皆为中国中古时期的文学,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近年所发表的一篇论文也是如此。这一中国文学的研究分支也应该能够继续引发更为深入的以“文化记忆”为指导框架的研究。
对过去的挪用是一种社会实践,运用“文化记忆”这一理论方法有助于阐明其一系列的具体特征。“文化记忆”这个视角总的来说是属于“记忆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而后者始于古罗马时人们对记忆术(,亦作)的钻研,亦即,将记忆作为一种技术性学科(mnemonics)。记忆术的提出是受关于古希腊诗人,凯奥斯岛的西莫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 约前557-前467)之故事的启发。据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所述,西莫尼德斯即兴创造了一种记忆技巧,精确回忆起一次宴会上所有与会者在会场坍塌前的座位安排。他的还原使得每一个死者得以被准确指认,从而恰当落葬。自亚里士多德的《论记忆与回忆》()起,包括无名氏的《致赫伦尼乌斯的修辞学》(, 约作于前80年)、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以及昆提良(Quintillian)的《演说家的培养》()在内的三部作品都一致将记忆视为一种服务于公共演讲的修辞技巧,尤其是根据“处所”(希腊语 topoi;拉丁语 loci)从思维层面来给想法和表达“定位”的技巧。正如耶茨(Frances Amelia Yates)和卡鲁瑟(Mary Carruthers)两位学者所述,诸多中古及近代的著作都陆续对这些早期的论述进行了拓展。在文学研究领域,丽奈特·拉赫曼(Renate Lachmann)在使记忆理念延伸至互文性的阐释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程度有别,“记忆”如今也见于早期中国的学术研究中。
本文的目的并非对笼统意义上的“记忆”或特定意义上的“文化记忆”有关的个别汉学研究进行评估,而是通过清楚地勾勒两位阿斯曼教授所定义的“文化记忆”究竟为何物,以期至少提供一些导引,从而反对就此概念所做的某些肤浅征用。我不可能对两位阿斯曼著作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讨论,那样只会得出一幅博尔赫斯式世界地图般的产物。我将仅针对他们的核心理论假设做出总结。
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将“文化记忆”的概念引入对中国的原型诗人屈原(传统上认为其生卒年为前340-前278年)以及“他的”《离骚》的重新思考中。具体而言,我将试图展示,只有具备了被恰当定义后的“文化记忆”的意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围绕着屈原人物形象和诗歌而展开的诸多文本。早期中国文学本身即富有个性特征,尤其能使“文化记忆”的内涵得以明显丰富,以此为背景,我将从我个人对早期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出发,通过检视“文本素材库”(textual repertoire)与“合成文本”(composite text)两类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进一步拓展两位阿斯曼的概念。由此,我认为汉代的屈原形象并非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非指向所谓“他的”作品的作者,而是一种合成文本的形构,其间铭刻了汉代“文化记忆”充满变迁的理念。这一构想()源自一系列的追忆,内容涵括以下诸方面:楚国旧贵族阶层的典范构想;对楚亡于秦的预见,同时伴随后来秦朝瓦解的必然性;楚国的宗教、历史和神话传统;具象化的君臣关系模式;楚国的文学遗产;诗性英雄向英雄诗人的转化;以及经由刘安(前179-前122)、司马迁(约前145-前85)和刘向(前77-前6)而逐渐形成的作者身份的理想,等等。
二、什么是“文化记忆”?
所有把“文化记忆”视为一种“社会”或“集体”的记忆模式的讨论都可回溯至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以下著作:出版于1925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é),出版于1942年的《圣地福音书的传奇地貌:一项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éÉ: éé),以及出版于1950年的身后著作《论集体记忆》(é)。哈布瓦赫出生于法国兰斯,曾在巴黎和哥廷根接受教育,最后于1945年3月16日在德国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离世。他绝大多数的家族成员也惨遭纳粹成员谋杀。哈布瓦赫于是乎就构成了战后记忆研究第一次浪潮所回应的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即纳粹大屠杀。战后记忆研究的第二次浪潮于20世纪90年代继苏联解体之后兴起。在这两次浪潮中,关于过去的宏观集体叙述轰然坍塌,而通往受压迫身份和政府控制档案馆的大门则被开启。哈布瓦赫指出:“任何脱离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用来决定和提取他们回忆的框架的记忆是不可能的。”受此洞见的启发,集体记忆的研究在下列众多学科中得以发展(排列不分次序):历史学、艺术史、文学、语言学、哲学、所有的区域研究(包括汉学)、社会学、媒体研究、人类学、建筑学、宗教学、圣经研究、政治科学、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等等。
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尤其激发了两个特别重要的讨论:一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可能存在的契合性,二是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如果所有人类记忆都植根于神经系统,并因此而在根本定义上就是个人化的,如何会有“社会”或“集体”记忆这一类的存在?相对于“历史”而言的“记忆”作为一种关于过去的方法,有多大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用途,尤其当我们把记忆的流程与历史编纂学的流程相对照的时候?作为这样一种双重构建的“集体记忆”——首先是一种过去在被认知之前所通过的心理过滤机制,其次是对这种可能完全不存在于个体人类心智之外的过滤的抽象化——的真值(truth value)又是什么?根据阿斯特里德·厄尔(Astrid Erll)的说法:“我们对‘记忆’之于‘历史’的关系的实际性质存在相当大的困惑。‘文化记忆’不是历史的他者(Other),也不是个人记忆的对立面。相反,它是这种多元文化现象得以发生的情境的总和。”他还补充道:
尽管术语具有不可避免的异质性,(有意识的)记忆具有两种普遍得到认可的核心特征:其与当下的关系以及其构建性的本质。记忆并非过往感知的客观成像,更不是一种过往事实的客观成像。记忆是一种主观的、具有高度选择性的重构,并由提取记忆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记忆是一种将发生于当下的所有可见数据进行拼凑的一种活动。根据当下状况的变化,每一个过去的版本也会随着每次回忆而改变。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谁也不是过去的镜像反射,而是身处当下、进行记忆活动的个人或群体之各项需求和兴趣的一种表达指征。其结果是:记忆研究的兴趣并非指向记忆中的过去之形,而是指向记忆活动所发生的具体当下。
由此,记忆研究不去尝试重构或具象化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寻求这些事件为了某个群体当下的目的和兴趣而被唤起时所处的状况与所历的过程。这个有关如何看待过去的根本性重新定位与“历史”和“传统”都有所分歧:与历史的区别在于它的兴趣并非落足于过去本身,而是对过去持续且回溯性的形构;与传统的不同在于它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保守的,正因为对不断演变的当下有所反馈,它是动态的与创新的。
举一个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例子:2021年6月17日,六月节(即6月19日)被指定为纪念美国废除奴隶制的联邦法定节日。这是自1983年宣布成立马丁·路德·金日以来第一个新定的联邦节日。1865年6月19日发生于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市(Galveston)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任何改变;有所改变的,是一个试图从当下出发且着眼于未来而重新定义其政治认同的国家,它如何从现在开始通过每年对6月19日的庆祝和更新来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集体性的纪念。请注意这里的几个关键词:集体纪念、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当下与将来、庆祝以及更新。这些词都是“文化记忆”的特征,也是其区别于“历史”之处。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而言,重要的是在什么状况下、以何种目标、通过哪些流程来把某些发生于1865年的历史事件重新铭刻进这个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中。
故而,任何社会在任何历史时刻的“文化记忆”都不是一种固定的存在,无论存储和维护其持久性的物质载体与符号为何,建筑铭刻也好,雕塑也罢,或者其他各类纪念碑,都不影响这一特征。它是一种持续的、永远都在演化的更新行为,这种更新包含了抹除与纪念两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某些地方或者群体的“文化记忆”可能看似已确定无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失去稳定性,或被重建,或被消除。这个过程永远都是充满争议的。所谓“历史”之争根本不是关乎“历史”,而是关乎记住些什么,以及怎么记住。这在一些存在不同群体争相推举不同记忆的社会尤其明显,比如,他们会针对过去讲不同的故事,或以不同的方式讲过去的故事,近期刊载于《纽约时报》的1619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了进一步界定“文化记忆”,两位阿斯曼教授将其与“交流性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区别如下:“文化记忆”可以回溯至数千年以前,而“交流性记忆”只存在于三到四代人之间,通常不会超过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模型下,“交流性记忆”包含了“个人传记框架下的历史经历”;它是 “非正式的、不拘于形的”;它“由互动所生”,与“鲜活有机的记忆、经验和传闻”相关联,且被“记忆群体中的当代见证者们”以并不特定的方式来承载和传递。相较而言,“文化记忆”由“关于起源的神话历史”和“一个发生在绝对的过去中的事件”所构成;它“有组织性且极度正式”,并在“仪式性沟通”和“节日”中成型;它的表达是“通过文字、图像、舞蹈等媒介而固定下来的客观外化物,以及传统象征符号的分类与展演”,且依赖于“专职的传统承载者”。这个定义下的“文化记忆”有几个关键概念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阿斯曼对于“神话”(myth)一词的使用值得特别注意:
神话也是记忆的投影(figures of memory),任何神话和历史之间的区别在此都被消除了。对文化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客观历史而是记忆中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记忆将客观历史转化成了记忆中的历史,并由此而将其变成神话。神话是一种为了从其起源的角度来阐明当下而讲述的奠基性的历史(foundational history)。譬如说,无论其历史准确性如何,《出埃及记》都是奠定了以色列民族根基的神话;它因此在逾越节受到庆祝,也因此而成为以色列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通过记忆,历史成了神话。这并不会把历史变得不真实,相反,从历史由此成为一种持久的、具有规范性和塑造性的力量这一意义上来说,这才是历史变得真实的缘由。
其次,“文化记忆”依凭仪式性时间结构下的重复记忆活动:
我们通常承认,诗性的形式具有一种获取知识进而对之进行统一化的记忆术式的诉求(mnemotechnical aim)。同样为人熟知的是以下事实:这种知识通常通过多媒体形式呈现出来,而处在这个过程中的语言文本是与声音、身体、无声模拟、姿态、舞蹈、节奏以及仪式活动等诸多因素无法分割的。通过有规律的重复,节日和仪式保证了赋予一个群体之身份认同的知识得以交流和延续。仪式重复还从时间和空间上巩固了这个群体的一致性。
如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所指出过的:
仪式具有赋予那些表演它的人以价值和意义的能力。所有的仪式都是重复性的,而重复自动意味着对过去的延续。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中国古代祖先祭祀这种特定的现象:它定期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举行,这个空间按照世代顺序来安排祖先的先后,并把最遥远的创始祖先放置在最中心的位置;这就不仅将处于当下的主要子孙表现为其最近祖先的孝后,更通过对孝行的表演,将他们表现为终将被自己的后代以同样的孝行纪念的未来祖先的模范;其相关诗歌和铭文中的语言也是高度程式化的,处于一个严格限制且重复、且被富有节奏地表演出来的词汇范围之内。根据韦德·惠洛克(Wade T. Wheelock)的说法,仪式性演说具有如下特征:
通常来说它是一个固定且被熟知的文本,这个文本随着每次表演被逐字重复。对于这个祝祷文的语言经常指涉的直接仪式环境而言,其构成元素通常来说也是标准化了的,且因此被所有参与者熟知,不需要任何语言形式的解释。因此,从普通对话原则的视角来看,就仪式而做的每一次表达其实乃是一种冗余。
最为重要的是,青铜器铭文所承载的祖先祭祀的三重结构所关心的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如下列出自《礼记》的段落所言:
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
在这里,记忆和“被记住的记忆者”(“the rememberer remembered”)这两个喻体都尤其与书写行为关联在一起。对阿莱德以及扬·阿斯曼而言,这正是“文化记忆”的一个核心特征,且与作为经典(canon)的文本有关。显然,这个理念引人入胜,因为它不仅涉及记忆被铭写而获有的持久性,还关乎记忆如何从人类心智外化为一种“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的书面化“存储”(storage)或“档案”(archive),可供长期调用。同样明确的是,书写早在西周时期就以这种方式被使用,史墙盘铭文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另外,如我们经常提及的那样,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已是第二手材料,其原始文献书于竹帛且被存储在西周宫廷档案之中。最后,我们也可以把五经的形成视为一种“文化记忆”的特定实现,它们得到早期帝制中国及其太学和图书馆机构的审定、形塑及维护。
同时,作为书面档案的补充,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历史悠久的口头档案。无论是早期的荷马史诗,还是程度更甚的例子,即远为庞大和悠久的吠陀文学资源库,都是某种被植入且不断再现于节日和吟诵的正式结构之中的档案库存。同样,《诗经》里的仪式颂歌也反复表达出这样一个事实,是仪式实践本身,而不仅是一套特定的文本,表现了对远古的延续。这种延续通常以设问的形式出现,并由对过去实践的演颂作答:
自昔何为。
诞我祀如何。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文化记忆”并不传递新的信息;它重复所有人已知的内容,如阿莱达所言,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召回一段遥远的“绝对意义上的过去”,而是为了将这个过去重新呈现为当下这个时刻。正是经由这种形式化的仪式性姿态,处于当下的群体才能确认自己的社会、宗教、政治或文化身份:
由此,“被记忆的过去”不能等同于对过去的一种客观、超离式的研究,后者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而前者总是与投射出的身份、对现在的解释以及对确证的需求混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记忆研究会把我们引向政治动机以及民族身份形成的纵深之处,我们所拥有的是助力于创造身份、历史和群体的一切原始材料。对民族记忆的研究与对记忆术或记忆艺术及能力的研究是大为不同的:前者把记忆作为一种能够驱动行为和自我阐释的动态力量来处理,这种力量是法国人所谓的“构想”(imaginaire)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这种想象形式低估为一种单纯的虚构,因为这种虚构抑或说创造实际构成了所有文化建构的基础。
抽象的、普遍化了的“历史”在被转化为共有的知识和集体的参与时就变成了一种再度具象化了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会被重新形构为一种特定的、充满感情的“我们的历史”,且被吸收为集体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文化记忆”的定义具有如下要件:(1)它指向奠基性的叙述以及蕴藏其中的神话式真理;(2)它通过刻意的记忆与忘却行为有选择性地从当前的视角来重构过去;(3)它是集体性的,且植根于社会互动;(4)它由权力的制度性结构塑造和维护;(5)它定义、稳定及持存被社会力量所调和后的身份认同;(6)它不断实现于文本和仪式的重复之中;(7)它动态地回应当下的需要;(8)它具有规范性、约束性、强制性和经典性;(9)它保存于持久性媒介,尤其但不仅仅是书写之中。
要让“文化记忆”理论对具体分析切实有阐释力,我们必须考虑到以上各点的具体含义。作为理论的“文化记忆”,其特有力量来自它后结构主义式的潜力:“文化记忆”要求我们从某些方面将过去视为基于当下目的的重构,也要求我们去揭示这种重构对某个群体的身份创建需求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就其核心而言,“文化记忆”是一种与历史实证主义冲动(impulses of historical positivism)所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它所阐明的,是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下,意义和身份被社会性、制度性以及物质性元素所构建的过程和实践,它所尝试解释的,是各个社会如何通过探究其奠基性叙述、神话信仰以及文化流程来理解它们自己。
三、“屈原史诗”
在始自汉代早期的历史观念中,屈原是早期中国最重要的诗人,而《离骚》也是古代中国最宏丽的诗作。然而,屈原远不只是以一个原型诗人的形象被纪念至今;更为重要的是屈原形象所象征的一整套身份认同生成的范式,维系了无数中国知识人的理想和志向,首要的是他作为一位高尚而忠诚的贵族政治顾问而终遭流放乃至自尽的人物形象。在后文中,在我早先关于屈原人物形象、作者身份以及《离骚》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我将从“史诗叙事”(epic narrative)的视角进一步扩展之前的分析。就分析屈原这一案例而言,这一长诗并不是一首单一的诗作,而是一系列诗歌和散文形式的文本的聚合,其中包括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屈原、《离骚》,以及其他或被收入《楚辞》或未被收入其中的相关文本。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史诗的一个标准定义:
一首史诗即是一篇关于英雄行为的长篇叙事诗。称其为“叙事”是因为它在讲一个故事;称其为“诗”是因为它以韵文而非散文写成;称其为“英雄行为”是因为,尽管会被各大史诗诗人重新诠释,但从广义上来说,它讲述了对该英雄所属群体具有重要意味的一系列英雄行为。史诗的情节通常围绕一个人或一个英雄的所作所为展开,这个英雄虽为凡人却出奇的强壮、智慧或勇敢,且经常受助或受制于诸神。史诗的背景被设置在一个遥远或传奇的过去,而那个过去是一个远比当下更为英雄主义的时代。史诗的风格是崇高的且高度修辞性的。
从欧洲视角来看,一首史诗被认作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但这没有理由构成史诗的唯一定义。关键不在于单一的长文本,而在于这个单一长文本之所以构成一首史诗的理由:它是叙事性的和诗性的,且只围绕一个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能力范围都远超其他凡人的单一主角的英雄行为展开。
作为一种分布于多种文献资源的文本,屈原故事可以视为一种独特的史诗。如果我们将屈原与另一个著名人物伍子胥(前484年去世)相比较,后者也是孤独的英雄形象,且在早期中国更为著名。伍子胥的故事丰富而充满历史细节,在先秦文本中已然广泛存在;但屈原的故事并不见于先秦文本。另一方面,在先秦或汉代,伍子胥的功绩从未以诗歌来讲述,更不用提冠伍子胥之名的伪自传体诗歌了:伍子胥仅仅存在于故事和轶事之中。屈原的情况则相反,他之独一无二,不仅是呈现为第一个中国伟大的诗人,而且围绕其典范式的经历汇集而成了一整个文集,还有更宏阔的相关知识传统,无论是书写的还是口传的,明显沿袭并超越了这一文集之所选所集而流传下来。屈原在汉之前的文本传统是籍籍无名的,而当屈原作为一个英雄诗人和被谤辅臣的模范性形象浮现之时,汉代以及之后的文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屈原在大量楚国甚至西汉楚地的文献中是缺席的,这进一步证实了是西汉学者全然建构了“屈原史诗”,他们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人的镜照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位先人去今足够久远,他不为人知,只能在文化记忆中被创造,只能被赋予理想的而非现实的英雄力量,他经历的英勇挫败不是可怜的,而是悲剧性的,也是超越性的。
比照上述史诗的定义,我们来看下《离骚》开篇的三节:下列这几个章节明确地将主角展现(stage)为某个具有神圣血缘的神话人物形象,他在某一吉日神性地“降”于凡间,并以一种强烈的个人化口吻自我介绍:
1.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2.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3.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这里由七个第一人称代词所共同指涉的“我”是一个记忆中的英雄,没有哪一个古代中国的诗人可以把自己称作诸神的后裔。这种角色模拟的表演性本质是在语言层面上被标记的:如一般表演性语境中的指示性表达那样,“此内美”只能被理解为戏剧舞台上面对观众时的一个实际动作,主人公的“内美”如果不通过他华丽的外表呈现出来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意味着《离骚》整首诗歌都是一个为了公共表演而作的文本,而是说它包含了表演性文本的元素,就如它也同样包含了其他文本材料的元素一般。
在我的分析中,《离骚》应当被视为一个模块化断章的集合,而不是一篇单一的诗作。它是一个不同种类和不同来源的表达的集合。这一分析围绕四项要点而展开:一、《离骚》中不同类型的话语、词汇和诗体风格;二、《离骚》中某些与周边文本并置而通常没有过渡衔接的文本模块;三、《离骚》内部的互文及重复元素;四、《离骚》与《楚辞》文集较早文本层中某些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就此,我把宽泛意义上的“屈原史诗”和《离骚》这一具体存在都视作一种“文化记忆”的体现,其形式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无作者的话语,它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成型,固化为《楚辞》的各个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称之为《离骚》《九歌》《九章》《九辩》等相互独立的文本实体。这一“屈原史诗”的文本既由多种材料组合(composed)为一,又在若干文本化的实现之中分散(distributed),由此,它是一个“文化记忆”的绝佳所在。我们在传世文集中所看到的只是这个文本被经典化之后的版本,它的最终成型既归功于包括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32-92)、王逸(89-158)和洪兴祖(1090-1155)在内的诸多评注者所做出的相继努力和决定,也离不开贾谊(前200-前169)、王褒(约前84-前53)、扬雄(前53-18年)及其他人的诗学回应与隐性诠释。
四、屈原之传
在西汉的观念中,屈原故事直接与东方旧邦楚国为秦所灭(前223年,即秦建立大一统帝国的两年前)的史事联系在一起。值楚国倾覆之际,屈原早已离世(其在传统上被确认的生卒年代并无根据),但依据《史记》,他在生前曾警示楚怀王(前328-前299年在位):“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也。”这一措辞在《史记》和其他文献中被归于诸多先秦历史人物之口,但在屈原的传记中则仅系于屈原一人。乃后,他被表现为预示楚国覆灭的唯一先知:继屈原之死,“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在司马迁以前,屈原势必已经成为先楚旧地具有重要意义的神话虚构性人物,楚地而今是刘安统治之下的西汉封国,其都城寿春正是楚国最后的都城。
也许正是在刘安的宫廷里,最初的《楚辞》得以汇编,屈原的人物形象得以确立。然而,屈原并不仅仅作为预示楚国覆灭的先知而存在;他对于秦之为“虎狼之国”的评判同样预示了秦最终覆灭的缘由:它将被新的王朝即刘氏的汉家所取代,后者正是崛起于先楚的旧地。这直接导向了屈原之所以代表汉代意识的第二点。在源于寿春的西汉视角中,屈原作为具有旧邦楚国三支王室血统之一的传人,其于汉代的身份是一位祖先。存续于旧都的楚国文化和历史,如今已成为汉家本身的文化和历史。“屈原史诗”提供了这样一种视野,它既包含了原先的楚国贵族文化,这一文化如今随着刘安及其宫廷而存续,又容纳了楚国的历史、神话和宗教,而这些元素分布在《楚辞》选集的不同部分之中。
屈原人物形象与汉代早期的思想政治需求相印证的第三点,在于它示范和体现了君臣之间的论辩:处于这一论辩中心的,是致力于美好统治的忠直顾问形象,这符合汉代知识人的自我旨趣,同时还有他们对不公正惩罚的抗议,如同贾谊和司马迁所遭受的那样。与屈原类似,贾谊最终被放逐于充满瘴气的南方;司马迁则避免了屈原式的自杀命运,而选择了承受宫刑,当时刘安已被迫自杀。由此,在《史记》他们的合传中,屈原和贾谊互为镜像并解释了彼此,但明显这是出于他们的汉代立传者所想象的贾谊视角。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屈原其人与汉代政治和文化想象之间的呼应在于他作为首位英雄诗人的形象。过去约二十年以来,西方汉学界已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在前帝国时期,这类个人作者的形象痕迹寥寥,这一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汉代前期经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等人之手建构出的产物。对个人作者这一新意识的激切表达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中,史家将自身呈现为首席读者和一位新的作者,他也把作者形象赋予一群他想象为其思想和道德先驱的过往先人,首当其冲者即为孔子和屈原。在《史记》中仅有两次,史家声称自己通过阅读想见文本作者之为人: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如我早先所评论的:
对于司马氏这位最杰出的读者和传记作家而言,正是文本将我们带向了作者其人的真实本质,于此,作者被最终认识和理解。在此意义上,作者取依附于读者:是后者在当下想象着前者,也是后者将文本连同其中的作者打捞出来。毫无疑问,正是以这种方式,司马迁不仅纪念了屈原和孔子,也将自身想象为另一位宿命化的作者——他所希求的,是自身的余晖能存在于未来读者的意识中。杜甫之情形亦然。与古代的史家一样,这位唐代诗人寻求创造关于他自身的未来记忆。屈原乃至孔子,司马迁乃至杜甫,浑然一人:他是身无权力的高贵者,志向高洁的个人,唯求德性的卓越而已;他创造了文本的遗产,于当世无人问津,仅俟来者。
概言之,在西汉的构想中,屈原其人作为一个“文化记忆”形象,被赋予了一系列对当时的写作者而言极为重要的观念。这一群星闪耀所共同映照出的形象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这一人物形象连同所谓的“屈原史诗”是如何产生的呢?《离骚》本身并不支持传记式的读法;它关于历史意义上的屈原毫无片语谈及。对它进行传记式(或自传式)阅读完全依赖于从多种其他文献中收集的外部材料:《史记》中的屈原传记,《楚辞》选集中的两篇短章(《卜居》和《渔父》)——这两首诗皆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谈及屈原,却被认为系屈原本人所作,《楚辞》文集以内和以外的其他汉代诗歌,以及多种汉代的评论和全篇的注解,最完整者即王逸的《楚辞章句》,今存于《楚辞补注》。人们无法从《离骚》本身重构屈原其人,事实上,如果不是由于各种外部材料将屈原其人与这一文本相系,没有人能够将该诗与屈原其人关联起来。
追问《史记》中的屈原传记是否确为司马迁本人的作品是徒劳无功的。这一文本是由多种资料组构而成,编连颇显粗陋,缺少连贯性,它甚至在传主本人的名字上都显出不一致:在指涉《怀沙》作者时为屈原,在指涉《离骚》作者时为屈平。此外,《离骚》是作于作者遭到放逐之前,还是作为对放逐的回应,文本对此的记载也不一致。“屈原”和“屈平”也许的确指向同一个历史人物,但传记本身并未将二者合而为一,同时请注意,二名均未在《离骚》中被提及。作为一批不同资料的编集产物,这篇传记向我们敞开了一个窗口,透露了早期屈原传说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并折射出不同的神话叙事和诗歌表演传统。它揭示出,围绕屈原这个人物存在着多种平行版本的文学材料,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被推尊为源头,也不能被降格为衍生之物。由此,当我们发现《离骚》和贾谊的《吊屈原赋》之间,《惜誓》(同样被归为贾谊之作)、《吊屈原赋》以及其他《楚辞》选集中的篇章之间,都存在着直接的平行文本时,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一名作者摘引另一作者作品”这一意义上的“引用”(quotation)行为。这种看法假设了早期文本的确定性,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假设。相反,上述现象意味着在汉代人的构想中,存在着某种共享的表达集合体。
尽管在前帝国时期,屈原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已经存在,且其故事被传诵于楚地,但直至西汉,我们才得以看到他的复合形象的全貌。正如《史记》屈原传记的不同部分所显示的,一位与君王相抗的政治英雄,受到统治者不公待遇的辅臣,某种处在崩溃边缘的社会秩序中的贵族代表,以及在诗歌中哀叹其命运的自传性诗人。以下这段关于《离骚》之所作的评述尤具启发意义: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处于这段引文中间的四行韵句遵循着相同的句法和韵律结构,总体上是一个来源未知的诗化片段。这一语篇几乎不可能是史家本人所原创的,而当来自某一更长篇幅的、也许被理解为自传性的诗歌材料,即以屈原名义发出的自我声音。这也构成了“屈原诗歌”也存在于已知选集之外的证据,它们也许曾以较小的单元形式流传,且可被拼合在其他文本之中,譬如现在讨论的《史记》之例,就属于被嵌入于传记里的散文式叙述。在这样的拼合里,主体和客体的形象,主人公和自传性的诗人,彼此可以轻易切换,正如在《九章》《卜居》和《渔父》中那些模棱两可于传记和自传之间的诗句一样。
这种模糊性在《史记》传记中还出现过另一次。对话性的篇章《渔父》,在《楚辞》选集中被收入且归属于屈原本人,在《史记》中则并非如是,而是显示为传记性叙述的一部分:一位渔父责疑屈原,认为其固执和忧郁是由于无法适应变化的环境。同样,此处风格化的对话不太可能是传记作者本人的创造,更有可能是移用自某处更早的文学版本。同时,与《楚辞》选集相比,《史记》的版本并未包括《渔父》的全文。在《史记》中没有《楚辞》选集里平行文本结尾处渔父的短歌,而这一短歌又出现在《孟子·离娄上》且与屈原(或渔父)毫无关系。也许是《史记》的作者去除了这首短歌;也许他并不知道它。无论是哪种情形,在传记之中,短歌的缺失更有益于故事的讲述。传记给予了屈原最后的陈辞机会,此时,他既是英雄也是诗人,他的陈辞也显得高度情感化与个人化:
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这一陈辞之后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乃作怀沙之赋。”而在《怀沙》文本之后,史家仅余最后一事可陈:“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正是这一时刻,屈原作为诗性的英雄以及英雄化的诗人的双重性质发生了分裂,换句话说也是文本中的形象和文本的作者分离之时:作为英雄角色的屈原,一个古代贵族的孤独形象,正决绝地步入生命的终点;作为诗人的屈原,并不可能恰在此刻即兴“作”出高度精美的诗篇,且这一作品不可能在此刻之后被保存下来——然而,他的诗作在其自杀之后却得以保存。作为英雄角色的屈原,在面对其命运而自沉汨罗之际是独自一人,伴随着作为自身传奇中心主题的孤独感,而作为诗人的屈原,在自沉前回应命运而创作并演诵《怀沙》之时,却并非独自一人。而在汉代的“屈原史诗”中,这一矛盾无关紧要:诗人和英雄可以轻易地交换位置。
近一个世纪之后,扬雄在其《反骚》中质疑了屈原的抉择:他认为屈原没有理由在遭到谗言和放逐后就自沉,而本可以没世隐居或是离开楚国。但扬雄想象的是前帝国时期的屈原形象,这个人可以有其他选择。不同的是,司马迁则完全是在帝制国家的情形中来想象屈原形象的,而这正是司马氏自己的情形:面对唯一的国君,除了死亡之外别无他途可遁。司马迁在其屈原想象中所投射的,是一位帝国时期士大夫的困境和声音:这一声音在帝国以前并未出现,但在汉代“文化记忆”中具有了显著的意义。
五、素材库和作者
我在近年来发展了一种“素材库与合成文本”(repertoires and composite texts)的理论模型用以分析《诗经》的诗篇,并不将之视为各自独立的诗歌系列,而是从“素材库”中缀合而成的选集:那些丛聚的诗篇彼此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质上是化身于诸多变体中的同一首诗。这一模型淡化了独立作者的概念,而是假设存在着某些与特定成套的诗歌表达联系在一起的诗歌主题,它们可以被灵活地实现于不断更新的或书写或口头的变体之中。这样一种诗歌概念在个别文本的层面上是不稳定的,但它在素材库的层面上,抑或是这些个别文本所取材自的材料集合体的意义上,则大体是稳定的。结果是,随着文本材料以模块化的形式流动,形成了诸多彼此相似但不一致的相互关联的诗歌。
这样一种关于古代诗歌创编的模型并非罕事。在中世纪欧洲的诗学传统中,这一存在于诗歌层面的不稳定性在保罗·祖姆托(Paul Zumthor)的术语中被称为,而在伯纳德·瑟奎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的术语中则被称为,两者分别对应口头和书写的创编不稳定性。重要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作为一种控制性因素的“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来作用于文本的解释以及稳定性。对于从“诗歌材料”(poetic material)和“素材库”中以不断更新的具体实现形式而产生的诗歌来说,任何一种回溯性地“重构”或是“发现”一位特定作者或是历史上特定创作时刻的努力,都是在概念上被误导的,也是具有人为局限性的。宇文所安在以这两个术语来概念化中古早期中国诗歌的互文性时,还提出了“同一之诗”(one poetry)的说法,即一种文本库,其中的单个文本仅仅是“有可能被创编出的许多潜在诗歌中的一种单个的实现形式”,它属于“一个单一的连续体,而不是一个包含着或被经典化或被忽视的文本的集合。它自有其重复出现的主题,相对稳定的段落和句法,以及生成的程序”。
在重新思考存于多种文类的中国古代诗歌的性质时,采用这一变化有度的诗歌流动性的解释模型是卓有成效的。它将我们从有着极为明显虚构性的作者归属中解放出来;它也免除了去创制年表、等级序列和线性直接引用关系的必要;它解释了密集的互文联系以及模件化的文本“建筑模块”(building blocks)如何在早期中国书写中轻易移动于不同的文本实例之间;它还将诗歌文本置于诗歌流通、表演和变异的社会实践语境之中。最后,同时也是与当前的分析相关的,我们看到“屈原史诗”中这种诗歌表达的分散性质,与“文化记忆”的集体性维度互相印证:西汉意义上的屈原不是某个具体文本建构的结果,而是对某些被共享的当代意识的回应。
不过,有必要在早期中国语境中对这一“文本间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作更具体的说明。杜恒已将《楚辞》中一批较早的互相联系的核心文本群与一些较晚的模拟篇章区分开来,这一做法某种程度跟从了霍克斯(David Hawkes)及其他一些前人学者。在杜恒的解读中,后者以诗篇形式被分散,并承担了副文本的功能(paratextual function)。这尤其体现在《卜居》和《渔父》,两者都命名和定义了屈原的人物形象,标记了他的死亡,并由此完成了对归于他名下的一组经典的闭合。正是在这一文本闭合完成之后,所有接受、引用、注解或是拟作才得以可能。至少在某些较早的《楚辞》选集版本中,《离骚》被视为屈原的唯一作品,一部被“传”所附丽的“经”;作为这种早期理解的遗留,“离骚经”这一标题在东汉的王逸注解中存续,但其具体含义已不为人所知。尽管千年以来的大部分学者仍然接受屈原之于《离骚》的作者身份,从而将此文本作为一首单一独立的诗歌,我本人的分析却将引向一种更颠覆传统的对于楚辞之“核心”的后结构主义式解读,茱莉亚·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和丽奈特·拉赫曼共同构成了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谱系,而他们均可上溯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我的解读模式将表明,“屈原史诗”的形成乃是出于一种合成文本、文本素材库和“文化记忆”之间的互文性,这种互文性在《离骚》和其他文本之间,以及《离骚》自身之中都发挥着效用。
事实上,正是王逸本人开创了这一理解的先河。关于《九章》(包括《怀沙》),他指出在屈原死后,“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类似的,关于《天问》:“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关于《渔父》,王逸则是提出:“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对于王逸来说,《九章》的诗篇产生于屈原的自杀并不可信;《渔父》涉及屈原的视角是第三人称的;而《天问》则因次序过于散乱而不可能出自屈原本人的最终创编。此外,关于《九歌》,王逸更多地将屈原视为编辑者而非原创性的作者:因他在流放之际所遇的南方的宗教歌诗形式“鄙陋”,屈原遂重构了它们,以表达其自身的反抗和规谏。基于此,“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在此意义上,作者身份是公共的、合成的,被分散在收集者、编辑者、校订者和评注者的诸种角色之中。在刘安、刘向和王逸等人相继参与重新整理《楚辞》以及与之伴随的屈原传说时,他们并非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对这一选集作出诗学贡献的过程里,他们依然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创造了以屈原为精神先驱的单一化作者模型。这一新的作者形象变得可见很可能首先得益于刘安的实践,西汉作家作出了明确的回应:这些回应包括了刘安及其《离骚传》(或《离骚赋》),司马迁(或是其他人)及其《史记》的屈原传记,尤其是刘向及其《九叹》,《九叹》中第一次提到了《九章》之名,并将其系为屈原之作。《九叹》正是依照《九章》的风格写就的,这种模拟体现在如开端和结语这样的结构性设置中,还体现于它同样在第三人称视角叙述和第一人称视角拟代屈原这两种模式之间自由切换。《九叹》之中的渊博学识反映了刘向在宫廷中所任的职分地位:他整理了秘府图书,并创造了关于知识遗产、思想与文学史的新系统。事实上,在《九叹》中的刘向声音里,将屈原这一人物形象定义为《九章》作者的信号之频繁可谓前所未有。刘向笔下的屈原,是刘向自身形象中的屈原;而刘向自身的声音,则是通过定义屈原的声音而建立起来的。
故此,我提议将《楚辞》划分为三个文本层:其中最古的文本层显示出文本重叠的多种例证(尤其是《离骚》《九歌》《九章》《九辩》);一个稍晚的文本层则明确指涉这些较早的文本(在《九叹》里尤其明显);而第三个文本层所包含的文本则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以上两个或早或晚的文本层之外(譬如一批召唤式的诗歌,《卜居》和《渔父》,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天问》),它们在某个时间点上被加入选集之中。将较早的文本层与较晚文本层区分开的,是前者之中程度远甚于后者的互文流动性,这些互文文本产生自素材库,它们之间平行而无层级之分。这种流动性发生在诗歌被经典化为各自独立的篇目之前。也就是说,这两个分属早、晚的文本层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本生成模式:一种是模块式的且不强调作者,另一种则出于对前者的回应而被自觉地作者化,从而更加受控制、不重复且自足自洽。举例来说,《九歌》诸篇彼此之间分享词句的频率颇为可观,而附于《楚辞》最末的王逸的《九思》中则全然无此现象。
《九歌》《九章》和《九辩》本身就是不同的素材库的选集化呈现。尽管这些文本系列中的一小部分独立于整体之外,其他成组集的部分却可能反映了它们起初的彼此互渗(试考虑《湘君》和《湘夫人》)。这种流动性的表现尤其可见于《九辩》,其中的各个诗章甚至没有被分别标以题目。但是,仅仅通过诗歌之间共享了某些理念和表达,是不足以说明素材库模型的有效性的,这些诗歌同样必须能与来自其他素材库的诗歌区别开来——正如《九歌》和《九章》之间的诗歌就判然相别那样。
然而,只有一篇合成文本最终将这些彼此分别的素材库以独立诗篇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也正是因此,该诗显示出声音、视角和词汇上的内在多样性,也表现出断裂、重复和突兀的不连续性:这首诗即是《离骚》。
六、作为诗歌互文的“屈原史诗”
每一种西汉乃至更晚的资料都将《离骚》置于《楚辞》的卷首,作为其毋庸置疑的源头和主文本。但是,这样一首长达373句的诗篇何以横空出世?它如何一代代地流传,尤其是如何经历公元前三世纪的乱世而进入汉代的?
最晚从南宋开始,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离骚》中不连续、非线性以及互相独立的诗章结构。事实上,尤其是当文本在繁多的重复之中回旋式地前进之时,一位读者可以随意移动其中某些章节而不对其理解产生多大影响。将这一文本划分为不同部分的诸多尝试全都无法成为最终的结论,无论是划分成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八个、十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或是十六个部分,这种莫衷一是乃源自同一个原因:在意识到文本的断裂和重复时,学者们依然将《离骚》解读为单一作者的单一诗作,其中包含着单一的声音和单一的意义。
然而,与其本身的重复模式相伴,《离骚》中的这些个别章节显示出与《楚辞》中的其他文本之间非常具体的互文联系,尤其是和《九歌》《九章》和《九辩》(甚至《天问》),这些文本包含了各自的主题、语言模式和词汇,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诗歌声音、言说视角和意象类型上的不和谐效应。因此,我提议将《离骚》本身既不视作单一诗人的创作,也不视作单一诗篇,它是“屈原史诗”的不同元素的选集,正如《史记》的屈原传记是彼此相异且颇不协调的资料的选集一样。按照这一读法,《离骚》并不早于《九歌》《九章》或《天问》之诗,屈原不是其故事的作者而是其故事的主角,有关屈原的故事已然在一系列不同的资料中被讲述。《离骚》作为正典化的“经”,并不在于它是这一故事的最初表达,而在于它是充满雄心的综合(summa);其余作品是相对第二位的,并不在于它们是继《离骚》之后而产生,而在于它们局限在特定的内容和诗歌库存里。这一读法并不主张某种关于《九歌》《九章》《九辩》或《天问》等传世文本之于《离骚》的年代学谱系。我想提出的是:这些文本所属的不同诗歌库存以及词汇集合存在于它们被分别整理进入《楚辞》之前,早于包括《离骚》在内的所有编选版本;它们共同代表了关于楚的“文化记忆”里那些与汉代作者们有关的特定方面:它的古代宗教性活动(《九歌》),历史和神话(《天问》),以及正直辅臣的悲叹(《九章》和《九辩》),后者自贾谊开始以屈原的形象而被确认。
文本整合与汇编的过程也许是经由刘安本人及其宫中的学者完成的,也可能是刘向所成。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离骚》和《九章》仍然保留着很强的表演元素,这一点从《离骚》最初的三节诗章对主人公的呈现开始贯穿始终。在最终的文本化定型之前,屈原故事必然已在时光中以口头和书写的形式被讲述和重述、表演和重演、创编与重编。这不仅体现在文本中的表演性元素、重复和断裂,也体现于如下事实:《离骚》中的某些章节,由于文本本身完全缺乏语境,实际上是无法被理解的,这一脱落的语境必然曾经存在于某种更早的版本中,或是曾被情境化地提供,也就是说,这种语境是外在于《离骚》文本的。尽管篇幅较长,《离骚》并非一篇自足自洽的文本。
“屈原史诗”文本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如前文已论及的,在《渔父》和《史记》屈原传记以及后者中的诗化片段之间的重叠,在《离骚》内部和《离骚》与其他诗篇之间的大量的文本共享,以及《离骚》本身之外的文本之间的共享。这里仅举最后一种情况中的一例,即《九章》中的《哀郢》在终篇之“乱”以前的最后十句。这一文本与《离骚》之间毫无重叠,同样的十句同时还出现在《九辩》后半部分的篇章里,尽管是离散分布于四段诗篇之中,《九辩》与《离骚》还共享诸多其他诗句。某些学者简单地接受传统的观点,认为《哀郢》由屈原写下在前而《九辩》由宋玉写下在后,由此来解释这种文本共享现象,但是,这隐含了两点假设:一是《哀郢》在相对早期的书写稳定性和经典性,二是某种从这一稳定文本那里“引用”的实践,然而几乎没有更多证据可以支持这两点假设。另一种至少可能的解释是,《哀郢》形式紧凑的结尾是在某个时间点上被附于文本的,它是从别处散见的句子中被汇编在一起的。又或者,《哀郢》和《九辩》都取资于某一被共享的材料集合,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了它。在这一语境中,冈村繁的假说就显得十分有趣了,他将《楚辞》早期文本层中整句的平行互见归因于背诵过程中对韵律稳定性的需求。冈村氏列出了《九章》《九辩》和《离骚》之间的此类平行文本,以及《离骚》本身内部或完全或部分重复的十四行诗句(散见于全诗的十二个诗章)。
试考虑以下两节诗章:
47.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87.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翱之翼翼。
“苍梧/县圃”和“天津/西极”这两组地名彼此完全是可互换的,两者分别以转喻和抽象的形式指代东方和西方。这一“朝—夕”结构同样见于第4和第17章:
4.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这里,类型化的地名“阰/洲”指代了山和水在宇宙论意义上的对立,而“木兰”和“宿莽”/“秋菊”之间的两度对照则表示了东方和西方的对立。以上四节诗章都构造了世界各地理尽头之间的对立,但从没有描述在它们之间的游历。所有行动都被定格在地名之中,既无目的也无过程。第4和第17章共同哀叹了时间的流逝,但后者并未提供任何比前者更多的内容。第57章同样包含了“朝—夕”的表达程式,但是顺序相反。这一诗章显示了同样的宇宙论意义上的对立以及无目的性的动作,在这里,动作的主体应该是一位难以捉摸的女神:
57.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
第4、17、47和87章可以轻易地变换位置而对全诗不产生任何影响;而第57章则来自一段唐突而暧昧的对某女性形象的寻求。然而,除了《离骚》内部的重复性模式之外,对缥缈女神的寻求与“朝—夕”这一表达程式的结合同样还出现在《九歌》的《湘君》和《湘夫人》里,同样重复出现的还有大量的植物意象。《九歌》诸诗在意象和内容上很大程度上是连贯一致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独一而自洽的表达集合;然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离骚》部分篇章里的语言不论在展开还是终止时均显得突兀而缺乏叙述语境,正如其他的语义元素一样。这造成了一种的不连续感。
在《离骚》中,这样一些特定的语义元素高度集中于某些部分而几乎不见于别处:在第37-41以及第72-74章,对古代先王的罗列成组集中地出现,使人联想到《天问》;神话性的地名出现在第47-49、54-55、57、59以及86-89章;植物意象尽管偶尔分散独立地出现,但集中在第3-4、13、17-18、68-70以及76-81章。当它们以间隔随机的重复形式重现时,它们被成组连缀在一起,构成了《离骚》内部可辨识的文本单元;更说明问题的是,这些单元之间甚至不相重叠而是看上去相互排斥,从而揭示了《离骚》作为一个整体的合成性。
之前已论及的第17章,更进一步地与我们所讨论的《离骚》中这两种相互区别的结构特征有关。首先,试考虑以下四个诗章:
14.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29.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是什么令这四个诗章在结构上一致从而可以自由互换?每一个诗章的前两句都提供了关于植物的描写,或某种施于其上的无目的性的动作;每一个诗章里,继之而来的两句都没有任何描写而纯粹是关于情感冲突的表达,且每次都伴随着“虽”或“苟”。此外需注意到字词层面的平行,即并见于第14和17章的“何伤”,以及第17章的“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与第29章的“苟余情其信芳”。如果描写性的植物意象使人回想起《九歌》,那么,对情感的表达通过修辞性问句,诸如“伤”“信”“心”“情”等词语,以及对第一人称代词(尤其是情感性的“余”)的密集使用而被戏剧化,则使人联想到了《九章》的声音。在以上每个诗章中,这些程式之间的顺序都是一致的,且每一次都是后两句中的《九章》式的悲叹形象支配了对前文植物意象的解释。描写性的两句也许是过去时,而情感性的两句则属于现在时。
在这一合成的结构里,第14和29章之间看不到任何推进;我们拥有的仅仅是相同主题的不同变体,甚至这种变体是可以更进一步地衍生而不造成任何影响的。然而,刚刚我们识别出的这一结构为文本的前三分之一所专有(它仅以相反顺序再次出现在第77和81章);在这之后,是其他的重复结构在主导。
第14章和第17章通过下述它们各自相邻的诗章而被进一步联系在一起:
13.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18.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
无论这两个诗章意在表示什么,它们与方才讨论的数章之间的区别是它们两者都完全集中于描写施于植物的无目的性的动作。在整首《离骚》中,没有其他诗章如此;在它们突兀、随机而孤立地出现之前,读者并未获得任何铺垫。不过需要注意到它们与第14章和第17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第13章在第14章之前,如此可解释何以植物的意象延续到后面的两句,但在第17章和第18章之间则没有这种逻辑关系。无论哪种,主人公都延续着他在此前某一时间点所曾做过之事。
存在大量其他的文本细节可以阐明《离骚》的合成性、重复性和非线性特质。这是一件包罗着源自《楚辞》选集其他部分不同话语的不同元素的繁复拼缀之物。在汉代的某个时期,这些不同话语被分别归置于相对连贯而自洽的若干文本系列之中,而《离骚》的多义性和其声音的多元性则源自这些话语在一个单独文本中的结合。还有以下话题是必须更多加以讨论的:
(一)《离骚》《九章》和《九辩》之间众多的平行文本。
(二)《九歌》和《离骚》之间(以及在《九章》和《九辩》之间偶尔出现)的平行文本。
(三)《离骚》内部成系列的相同措辞。
(四)大量第一人称代词(“余”“吾”)高度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它们在不同类别篇章里的区别用法:在表哀叹之情的篇章里大部分为“余”,在含有命令式权威语气的篇章里大部分为“吾”,如“吾令”(仅仅出现在第48、51、52、56、60章)。
(五)情动表达的成组集中出现,尤其是“恐”(第4、5、9、61、63、75-76章),“伤”(第14、17章),“哀”(第14、20、45、54章),强化语气的“信”(第17、29、58、65章),以及名词“心”(第15、16、21-22、26、32、36、61、70、85章)和“情”(第10、17、29、35、64、73章)——所有这些字词都显著集中在全诗的前三分之一,同时也高频率地出现于《九章》,而在《九歌》中痕迹寥寥。
(六)用于进一步强化感情的诸如“何”“虽”“苟”等句式结构。
(七)难以统一化解释的《离骚》中变换的声音、视角和性别。
举例而言,互文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第10-12章中得以完全的展示:
10.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11.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12.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搁置文意解释层面的疑问(“‘灵修’所指何人?”),我关注的焦点在于互文性。“察余之中情兮”(第10章第3句)在第35章重现,同时还在《九章》的《惜诵》里出现(在该处,它还与某一平行于《离骚》第24章的诗句相连)。“指九天以为正”(第11章第3句)在《惜诵》中重现为“指苍天以为正”。第11章的第5、6句呈现了一个问题:它们被添加在四句一章的惯有结构之后,这在全诗是绝无仅有的,但没有王逸的注解;洪兴祖由此设想这两句是稍晚时才被孱入文本的,但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试将此两句与《九章·抽思》篇中的以下段落相比较:
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很明显,我们正在阅读的是同一段的两个不同版本,即使两者间存在微观的变化和不同的句序。没有什么能令我们赋予《离骚》中的版本更多权威;相反,我们应该质疑《离骚》中额外出现的两行的初始样貌。我们无法断定这两行诗句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本的,也许它们在某个王逸所未见的汉代版本里已经存在了。与其付出徒劳的努力去确认这些篇章之间“抄本/副本”(copy)和“原本”(original)的等级关系,我建议我们首先承认,《离骚》和《九章》中的诗句可以多么轻易地集聚成丛和更换位置,也许从它们最初共同取材于同一个“屈原史诗”的素材库之时起,这些诗句就确已如此运作着。
七、结 论
《离骚》本身的内在复杂性,以及它与其他有关屈原的早期文本之间的联系,是令人惊异且无法被消解的,众多不同解释的存在即表明了这一点。这给予了我们若干种选择。其中最不可信的一种,即简单地提取《离骚》中所散布的多个文本层中的一个,并以之统摄其他所有的文本层,将文本化约至单一意义和意图的层面。这种选择所牺牲的恰恰是《离骚》文本的多义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来自其中多重的、互不兼容的但又各自迷人的维度,它们将《离骚》与所有其他早期中国诗歌区别开来。不幸的是,传统的解释采用的正是这种最不可信的选择,在此解释中,《离骚》的意义仅止步于被当作另一个更加混乱无序版本的《九章》。一种更好的选择则是辨识和珍视屈原故事被想象和讲述的多种方式。这些想象和讲述也许从战国晚期开始,而盛行于汉代早期。在该时期,屈原故事回应了一系列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
从汉代早期到刘向发生变化的恰恰是这类需求,在王逸的时代变得更加强烈。在当时的各个阶段,他们迫切需要去想象一个意味深长、关乎身份认同生成的过去。刘安的屈原所应和的是寿春一带乡愁式的关于楚国的构想;刘向的屈原则应和了帝国时期的士大夫身份认同,以及一种新的古典主义,此间,作为遭厄作者和皇室辅臣的屈原被赋予了一席之地,但不再有更多空间留给看似光怪陆离的楚国宗教、神话和情欲想象。基于“屈原史诗”的“文化记忆”已经变化,以迎合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