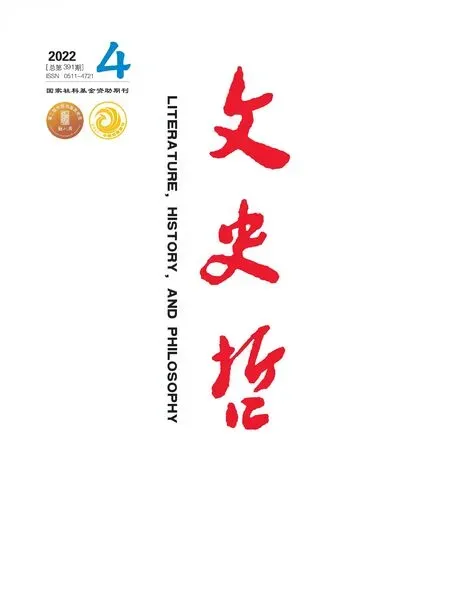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
——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2022-11-08崔罡
崔 罡
近年来的儒学界确实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态势,但同时亦蕴藏着分歧层出不穷的局面。正如黄玉顺指出的:“如今的儒学,既有原教旨主义的儒学,又有自由主义的儒学,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儒学已经分裂了。这种分裂并非古代那种‘儒分为八’的分裂,而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的分裂。今日儒学唯一的‘共识’,就是大家都自称为‘儒家’。”
此种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儒家哲学”观念本身进行反思。道理显而易见,根据现代学术的基本规则,倘若儒家哲学真如学者所以为的那样具有内在系统性,分裂的状况便必然是由基础概念的分歧导致。但是,只要稍加推敲,我们就极容易提出一个基础性疑问:“儒家”与“哲学”是怎样实现兼容的?“儒家哲学”这个概念又是如何吊诡地成了现代儒学的核心语词?
本文试图阐明如下真相:“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也就是说,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是种种彼此冲突的立场之表达,根本不能也不应被视为某种自洽的哲学。最后,本文还将尝试性地提出,儒家哲学应是一种不同于欧洲理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儒家情感主义。这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儒家与哲学: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
综观先秦至汉初所有学术史文献,如《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韩非子·显学》《庄子·天下》《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等,没有任何一例在学派的意义上使用“儒家”概念。“家”被赋予“学派”的含义最早见于《庄子·天下》,文中提到“百家之学”“百家众技”“百家往而不返”,凡此三例。尽管《天下篇》“在‘家’的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但全文仍然是以松散的学术史观来讨论“道术为天下裂”的学术态势。先秦有儒者、儒士、儒生等用例,但前述文本至少表明,在中华帝制时代之前,“儒家”观念与此后习以为常的理解绝不相同。
在严格区分“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各家意义上使用的“儒家”,真正成型于《论六家要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这段话严格符合“属加种差”的概念定义原则。在司马谈看来,天下所有的思想归根结底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即如何治理天下(此其“属”),在此前提下,根据其立场和观点的不同(此其“种差”),天下学术被分为了六家,而儒家是其中之一。学术是否真的只是围绕此唯一问题展开,不是本文要讨论的。关于《论六家要旨》的历史事实是:其一,它是典型的中华帝制前期生活方式的显现,是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完成之后“大一统”现实诉求的反映;其二,它被保留并整合为“诸子出于王官论”,并随着从《汉志》系统到《隋志》系统的更新换代,成了漫长的中华帝制时代“天经地义”的观念。也就是说,“儒家”首先对应的是经(六艺)子(诸子)之分,它属于子学;在子学中,它又对应“道家”“墨家”各派。“儒家”概念在中华帝制时代保持了基本的一致,它的背后是一整套彼时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系统。质言之,“儒家”是前现代话语。
汉语学界使用的“哲学”是舶来词。在西方语境下,它至少具有三个不同的含义:philosophy,这是爱智慧的行动;metaphysics,形而上学,这是爱智慧的产物;knowledge of metaphysics,这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知识,亦即哲学专家处理的知识领域。哲学在西方传统中的语义变迁非本文所能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之后,学者已经习惯性地、不加区别地使用这三层含义。
“哲学”概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时,时人承接了彼时西方流行的哲学观,普遍将“哲学”理解为“统合之学”,也就是metaphysics。例如,发表于1901年的一篇文章认为:“上下古今纵横,宇宙自洪荒最初之点迄世界大同之场,其所以纲维人类主宰事物而有莫大之势用者,学术也。然事物有万变而学术亦有万端,于纷歧复杂之中而有一至理贯彻之、综合之,使无不明之事物、无不达之知识者,惟哲学。”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人们既亦将哲学视为知识门类之一。王国维在1904年即讨论过戴震与阮元的哲学。程树德称荀子为“哲学大家”。更早的例子是1898年译介的日本学者大桥铁太郎的周敦颐张载哲学。直到科玄论战,学者们依然不加区分地使用“哲学”和“玄学”,并习惯性地用metaphysics补充标注。
“哲学”概念开始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被大量使用是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且其使用量呈爆发式增长趋势。彼时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时期,也是救亡图存三阶段论的成型时期,还是中国现代学科的初建时期。“哲学”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初就被视为一整套近代以来西方世界观和价值系统的象征。这不仅是教育系统的转变、知识系统的转变,更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动、社会秩序的崩溃和重建。这个转变,通常被视为晚清现代化的重要现象之一。这清楚地表明,“哲学”在进入汉语学界之初就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质言之,哲学是现代话语。
因此,严格来讲,“儒家”和“哲学”是基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彼此错位的概念——前者是前现代的,后者是现代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现代化就要反传统(因为现代与传统互释),反传统就是反儒家(经学也被视为儒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持有儒家立场的学者都会被理所当然地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不论国人对自己的传统还有多少香火情分,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对儒学陌生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哲学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大量严肃地专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平时可以和儒家形同陌路,但一旦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与儒学遭遇,就会迅速爆发激烈的争论。最近的例子是关于“父子互隐”的大争鸣。
但“儒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界的最核心话语之一,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假思索的判断是,儒学发生了现代转型。这自然没错,同时亦表明,只要不否认“哲学”的现代性意涵,那么,就必然是儒家“被哲学化”了。不过,事实绝非如此简单。
二、“儒家哲学”与歧进的路向
“儒家哲学”最早被使用应该是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即如《礼记》中许多儒书,只有几篇可以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不过全书也仅此一例。这个概念被正式用作著作题名是1922年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1926年,梁启超在题为《儒家哲学》的讲座中表示:“‘儒家哲学’四字大家都用惯了。”由此可见,“儒家哲学”已成为学术讨论中的常用词。
那么,“儒家哲学”是在什么意义上被使用的呢?
根据陈来先生的观点,“儒家哲学”有两个大的分别:“一是指对传统儒学的学术研究,即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清理儒学概念的意义及演变,研究儒学在不同时代与社会、制度的联系,澄清儒学的思想特质和价值方向等等;一是指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即20世纪面对时代、社会的变化、调整和挑战,发展出符合时代处境的儒家思想的新的开展,开展出新的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新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以及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境况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的哲学。”要言之,儒家哲学不外乎两类形态,一是知识化了的儒学,也就是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标准将传统儒学分解和重组;一是资源化了的儒学,也就是批判继承儒学思想资源,回应当下的问题。
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将“儒家哲学”分为三类:一是“儒学中的哲学”,一是“儒家化的哲学”,一是“儒家式的哲学”。
所谓“儒学中的哲学”指的是,按照西方哲学的分类体系,将儒学中与之符合或类似的内容单列出来,纳入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中。其下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以西律中”;第二类是以郭沫若、蔡尚思等为代表的“以马律中”。从数量上来讲,这种用法是此后各种儒家哲学研究的典型范式,其价值或如蔡元培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由此带来的争论是,儒家是否有形而上学(metaphysics)?
所谓“儒家化的哲学”指的是,运用儒学的思想资料,积极建构儒家的哲学体系,但参照的仍然是西方哲学的标准。贺麟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盖五花八门的思想,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文化,漫无标准地输入到中国,各自寻找其倾销场,各自施展其征服力,假使我们不归本于儒家思想,而加以陶熔统贯,如何能对治这些分歧庞杂的思想,而达到殊途同归、共同合作以担负建设新国家新文化的责任呢?”由此带来的争论是,中国哲学是否合法,或中国哲学的失语症问题。
所谓“儒家式的哲学”指的是,持有儒家的立场、建构儒家式的哲学体系。其下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样态说,代表观点见于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所谓哲学就是有系统的思想,首尾衔贯成一家言的。”在梁先生看来,哲学乃是思想,而思想即是文化。“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一类是人生哲学说,代表观点见于梁启超。他认为儒家哲学的范围要远远大于西方哲学的范围,是不能简单地采用现代哲学来对其解释的,因为“我们所谓哲,即圣哲之哲,表示人格极其高尚,不是欧洲所谓Philosophy范围那样窄”。此一类的前提是对哲学另做解读,但其所持是否如论者以为的儒家立场,则存争议。
无论二分抑或三分,都未根本性地扭转话语自身的错位性。知识化的儒学不可避免地被现代学术分解,至少被分到了历史学和哲学两个一级学科门类之下。那也就意味着儒学不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独立性,且其哲学品质总体上不被高度认可。
资源化的儒学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转型后的哲学形态。如此一来,被冠以“现代儒学”之名的种种儒学的提倡者们,一直以超乎寻常的热情积极参与新潮的、时尚的、通常是西方学者率先发起的话题。请注意,这意味着“现代性”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很容易令非儒家学者诟病的是,凡是有一种西方的哲学流派,就几乎会有一种与其对应的儒家哲学,诸如康德式的儒家、黑格尔式的儒家、现象学式的儒家、诠释学式的儒家等等。扩而言之,现代思想中但凡有一种主义,就会有该种主义的儒家。所谓“主义”指的无非是就公共生活“所具有的信仰和行动”。这显然意味着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本来、应当是分明的。“主义”的背后,是关于现代性诸问题的立场对立,且这些对立是实然的,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流血冲突。儒家哲学居然能够逍遥乎其中,这简直太荒诞了。
在“主义”的意义上,中华帝制时代的儒家确实可被理解为“某种主义”。但问题在于,面对当下的状况,儒家究竟算何种主义?倘若存在儒家主义,那么,它是什么?它又如何与其他种种立场相区分?倘若不存在儒家主义,儒家是否就必然消融在各种现代性的主义之内,而仅仅是思想资料和话语工具?如此它又凭什么获得自身的独立性?
总之,当下的儒家哲学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存在:它似乎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安身。歧进的路向背后是错位的话语,换言之,当下的状况是由“儒家哲学”观念本身混乱引发的。既然如此,只要不对儒学进行全盘否定,就应从根本上阐明“儒家哲学”的现代意涵。
三、情感主义:儒家哲学的现代意涵
“儒家”作为一个偏正语词,“儒”是种,而“家”是属,这样就必然存在与“儒家”并列的别家。孟子“拒杨墨”,杨、墨即与儒家并列;司马谈分六家,其余五家即与儒家并列;宋明“辟佛老”,佛、老即与儒家并列。无须赘言,这些并列方式、理论对手、问题指向,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例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佛学资源,这在宋明理学家看来是犯了大忌的,却丝毫无损梁、熊二先生在现代新儒家中的开山地位。寻求“儒家哲学”的现代意涵,即要明确它在现代哲学中的并立之学。
“儒家哲学”首先是哲学,这是其“属”,它与其他哲学的差异即是其“种差”。“现代哲学”作为学术分工之一种,即是对现代性诸问题的一般性、根本性阐明。考虑到20世纪以来鲜明的“去形而上学”倾向,考虑到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此前原本下辖于哲学学科诸问题的分有(此种分有乃人类学术史的常态),哲学愈发地表现为对诸学科形而上学承诺的审慎反思,亦即,它愈发地表现为某种思维方式。
那么,什么是思维方式呢?蒙培元先生对此进行了界说。在他看来,首先,思维方式是广义的认知,也就是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安置生活的致思进路。其次,思维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客体的对象性认识”或“自觉的理性认识”,即理性主义(rationalism)思维方式;另一类则是“主体论的存在认知和评价认知”或“非自觉的非理性认识”,即情感主义(emotionism)思维方式。
纵观人类历史,自轴心期以来,在安置公共生活问题上,主流的、基本的思维方式都是理性主义的。无论这里的理性指代的是自然哲学的自然规律,还是先验哲学的义务论,或是宗教哲学的神命论,其本质是完全相同的。它在欧洲中世纪表现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卓越工作;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则表现为汉唐儒学的“天”或宋明儒学的“天理”观念。此种历史事实有其正当性。因为情感一定是个体的情感,而公共生活又必然是非个体的。个人情感的反复无常自然会成为公共生活中嘈杂的声音、不协调的旋律、令人厌烦的扰乱者。因此,在哲学史上,对情感的基本态度要么是道德哲学式的“给这些放纵无度的渴望套上辔头”,要么是政治哲学式的“可以怎样被塑造和被影响,来促进我们的正义目的”,也即传统儒学的“发而皆中节”的伦理要求。
在理性主义的原则之下,人类打造出了高度组织化、高度模式化的现代社会。在此社会中,“作为自然或历史发展的法则的近代形式的普遍法,成为运作的原理,不断保证人为的实定法的规则和规范体系的有效性”。此种思维方式潜藏着巨大的危机,19世纪人文主义的先驱者们对此早已发出了警告。但这些“不合时宜”的谏言被淹没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理性主义狂热之中。
因此,现代性诸问题带来的真正焦虑在于:我们已然无法确信现代性是否会必然带来美好生活。于是,对理性主义的警醒就成了20世纪哲学的重要倾向。再进一步的追问是:公共生活一定是理性的,但安置公共生活的思维方式就只能是理性主义的吗?
谈到理性,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亚里士多德的著名格言:“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也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最核心的价值之一。“理性”用拉丁文来表述是“rationale”,而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那里的表述则是“logon”,直译为“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里显然存在着ratio与logos之间的差异。“古希腊语中,logos具有言语和理性的双重意义,表达这种保证对话能力与思维能力的统一性的用词,后来就变成了ratio。从政治的观点来看,两者是不同的。后者先是在理性的个体内存在,与个人有关系,以后,成为个人向他者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使用的言语。但是,前者根本上与他者有着联系,因此其本性是政治的。”从汉语的表达习惯来讲,logos既是指“说道”,也就是人类运用连贯的思想和表达能力对存在者的言说,通常被理解为人性天赋的理性能力;还表示“道说”,也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的自我显现,通常被理解为客观的规律、规则。

儒家情感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彻底的“由情及理”的思维方式。蒙培元指出,“将情感作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来对待,是儒家哲学特有的”。“这里所说的‘哲学问题’,不是指哲学中的某一个问题,或哲学中的一个分支(比如美学和伦理学),而是指哲学的核心问题,或整个的哲学问题。”
蒙培元的工作是对先秦儒学,尤其是孔子儒学的重新发现与复归。在孔子那里,有一个更为源初的“情—理—情”结构。《论语·泰伯》记载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这个框架性结构中,“《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志”即是情感的意向性,而“和”则是情感的满足。这就是说,问题生发于情感,其最终的归宿也是情感。在发生与归宿之间,则是“理”的环节,是诉诸公共性、连贯性的能力,落实来讲,可以是礼乐制度、礼乐文化,抽象地说,则是一般性的理性原则。

情感主义则不然,其基本的判断是因为有如此这般的情感样态,故而人被视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质言之,不是理性驾驭了情感,而是情感生成了理性,理性是且只是情感的工具。
再次申明,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都是用以应对如何安置公共生活的思维方式。既然公共生活必然是理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看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由此可以导出一些情感主义的基础性立场:其一,安置公共生活的方式不是来自某种形而上学设定,而是来自个体情感的诉求,来自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以及公共善(public good)的约定。其哲学化表达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与回答。其二,倘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生活是实然的,那意味着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观之间的沟通乃不争的实情。纷争不断不是因为彼此天然的隔阂,恰恰相反,而是彼此沟通不足所致。讨论至此,儒家哲学的现代意涵已然呼之欲出。作为现代哲学的形态,儒家哲学不同于任何哲学的根本性特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