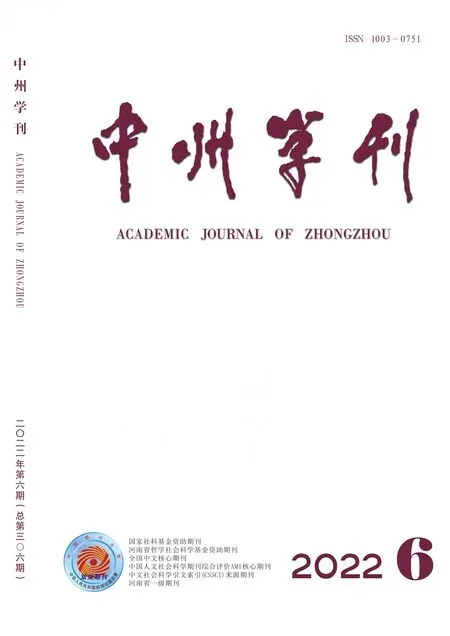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
2022-07-22焦艳红
焦 艳 红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10个条文使用了“相应的责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相应的责任”具有何种含义和性质?对此,理论上存在诸多解释,特别是对数人侵权责任规范中“相应的责任”的含义,观点尤为不一。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是一种新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具有与传统责任形态不同的特点;也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并非一种新的责任形态,应将其解读为某种传统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还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表达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责任形态,应根据其所处法条的位置及不同的语境,确定其具体属于何种责任形态。理论上存在争议,必然影响到司法裁判难以统一,导致类似案件出现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的结果。因此,从理论上、立法上对“相应的责任”的含义和性质进行探讨,进而对相关规定作出正确的解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相应的责任”及其解读困境之由来考察
科学地界定一个法律概念的含义,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运用历史法学的方法,探讨该概念产生的历史缘由,再基于其产生缘由和目的,确定其基本含义;二是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将该概念与相关概念及其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再基于各概念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界定该概念的确切含义。由此,探究“相应的责任”的真正含义,首先应考察该概念的由来及其发展沿革。
“相应的责任”作为对法律效果的一种表述,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早已有之。我国原《民法通则》第61条首次使用了“相应的责任”,用以表达民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均有过错时应各自承担的责任;此后,我国原《担保法》、原《合同法》中相继出现了多处“相应的责任”。原《担保法》中“相应的责任”并未超出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所规范的对象和范围,仅表明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的情况下债务人、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有过错时应各自承担的责任。原《合同法》中“相应的责任”既表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双方均有过错时应各自承担的责任,又表达双方违约时应各自承担的责任。可见,在原《侵权责任法》之前,我国立法中“相应的责任”表达的只是一种民事责任划分、承担方式。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并不存在争议。


“相应的责任”在原《民法通则》中产生以来,含义、语境和适用范围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担保法》《合同法》虽然扩大了“相应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的基本含义,仍然是对合同无效、被撤销后或双方违约时各自根据过错大小或违约情况承担份额责任的一种描述。此时,“相应的责任”并不具有责任形态的含义和性质。“相应的责任”被引入原《侵权责任法》后,所表达的法律效果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关条款的规范内容明显突破了原《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中“相应的责任”的含义、语境和范畴。《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与“相应的责任”有关的条款数量剧增,适用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双方存在混合过错时各自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责任;二是数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时各自根据其过错或原因力大小对受害人承担责任;三是数人侵权情形下除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外,其他责任主体也应承担责任。第一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清晰,属于民事责任划分和承担的一种方式,并非一种责任形态;第二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也比较明确,责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第三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复杂,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极大争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通过以上对“相应的责任”发展沿革历史的考察,笔者发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虽然改变了“相应的责任”所处的语境,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其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的基本含义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质言之,“相应的责任”仍然是一种根据行为人的过错或原因力确定责任的一种责任划分方式,并非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值得研究的主要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第三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其与前两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含义可以直接体现为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前者因处于特殊的数人侵权规范中而应根据数人侵权的不同情形确定责任人应如何根据过错承担责任;后者可以根据所处条文的规定予以直接适用,前者的规范含义须结合所处条款对应的另一个数人侵权责任条款才能最终确定。本文重点研究前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7个特别条款中“相应的责任”的责任形态,对此必须借助于对相关的数人侵权责任条款的分析。
二、“相应的责任”之含义厘清
科学界定“相应的责任”的含义,既需要从性质和内容上辨析其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也需要从词语和文义上探析其确切法律内涵。
(一)“相应的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形态



最后,“相应的责任”可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可能是一种单独责任。比如,我国《民法典》第1193条规定的定作人的责任包括两种情形:承揽人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情形;承揽人造成自己损害的情形。在第二种情形下,定作人对承揽人的损害承担责任,其承担的实际上是单独责任。既然“相应的责任”有可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有可能是一种单独责任,怎么能将其解释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呢?
(二)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不宜作一体化解读
“相应的责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如果是一种共同责任,对其责任形态就应进行一体化解读,否则违背概念的统一性规则。笔者认为,从规范体系考察,不宜将“相应的责任”统一解释为同一种责任形态。
首先,“相应的责任”不可能被统一解释为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因为这两种责任形态通常被明确规定在有关条文中,立法者若有将“相应的责任”作为这两种责任形态之一的意图,完全可以直接在有关条文中予以规定,无须将原来的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修改为“相应的责任”。

最后,将“相应的责任”统一理解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缺乏规范评价上的统一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可称为法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文,其内容均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都使用了“可以向……请求赔偿,也可以向……请求赔偿”的表述;二是都存在终局责任人,非终局责任人只承担垫付责任,其本身并无过错且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追偿。但是,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行为人本身均具有过错,相关法条的内容中是否存在终局责任人、谁是终局责任人均具有不确定性。
(三)不宜将具体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

(四)“相应的责任”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性、转致性法律概念
根据上文分析,“相应的责任”本身不具有确切含义,既不是一种新的独立的共同责任形态,也不是一种具体责任形态,甚至在同一条文中也难以固化解读为同一种共同责任形态。那么,作为《民法典》中统一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其含义究竟如何?对此,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


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具体条款解读
通过对“相应的责任”的立法缘由和规范含义进行考察,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相应的责任”除明确指向单独责任的以外,在侵权法视域下实际上属于转致性规范。因此,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7个有争议的“相应的责任”条款进行理论阐释,应当按照前述解读规则,采用体系化分析方法。
(一)对《民法典》第1193条的解读

(二)对《民法典》第1209条、第1212条的解读
《民法典》第1209条、第1212条是关于责任主体分离的情形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对于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两者的主观状态不同,不宜对其责任形态作固化解释,而应考察案件事实能被何种数人侵权责任规范所涵摄,据此确定责任形态。在机动车租赁、借用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对安全适驾状况负有相同的注意义务,若明知存在不适驾的情况,可推定其对致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有意思联络,从而构成共同过失,应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并非明知而是因过失而不知道使用人存在不适驾的情况或者机动车存在缺陷,则其与使用人乃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应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承担按份责任。此外,在《民法典》第1212条规范的未经允许驾驶车辆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可能就不适驾的情况相互明知或者就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进行沟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主要表现为未对机动车妥善保管或管理,其过错行为与机动车使用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的发生,因而也应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的规定承担按份责任。
(三)对《民法典》第1256条的解读

(四)对《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的解读
对于未尽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承担的“相应的责任”,笔者认为,将其解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具有合理性。从体系上看,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解释为典型的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民法典》第1169条第1款、第2款应是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系,前者规定教唆、帮助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后者规范的是特别情形且对责任承担方式的表述与前者不同,不宜将其解释为连带责任。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补充责任应符合《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的构成要件,但监护人并不是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适用该条款的可能性,将其承担的责任解释为补充责任不具有合理性。从立法目的看,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解释为按份责任。按份责任意味着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规定监护人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立法本意应是减轻监护人的责任而非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按份责任,会削弱对受害人的保护,因而并不妥当。
从理论基础的成熟度来看,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比解释为单向连带责任更具有合理性。因为监护人与教唆人、帮助人之间并无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无法依据数人侵权的法律规定予以解读。鉴于前述单向连带责任的概念存在歧义,以及监护人有承担全部责任的可能性,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对此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进行解读更具有合理性。其一,《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的文义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构成条件。立法规定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都应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前者是因被视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后者则是因未尽到监护职责,法律未对两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其二,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通常情况下,教唆、帮助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在主观上是过失。监护人在极端不负责任的情况下,如被多次告知有不良或不法行为却仍对被监护人不加管教,构成重大过失。此时,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之间的主观过错程度差别极小,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在两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外部责任关系而言,实践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如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差别、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辨识能力的差别以及监护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差别,认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范围。就责任主体的内部关系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的规定,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之间互有追偿权。至于追偿权是否成立,可由法官酌情裁量。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内部法律效果不确定的法理。
(五)对《民法典》第1189条的解读

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通常并无共同实施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因而不能依据数人侵权的一般规定对《民法典》第1189条进行解读。在委托监护的情况下,监护人基于监护关系承担替代责任,受托人因未尽约定监护职责而承担过错责任。产生这两种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产生条件。就外部关系而言,受害人可以请求监护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受托人承担责任。就内部关系而言,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监护人承担责任后可依照《民法典》第929条的规定,以委托人的身份向有过错的受托人请求赔偿损失。因为受托人是受托履行监护职责且承担过错责任,所以不存在受托人向监护人追偿的可能性。
(六)对《民法典》第1191条第2款的解读


四、结语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7个条款中规定的“相应的责任”,并不是某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不宜将其一体化解释为某种既有的责任形态,或者将某一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当“相应的责任”条款规范的情形属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范畴时,“相应的责任”具有转致性概念的性质,对其解读应结合其他关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规定或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找到能够发挥法律效果形成功能的规范。随着《民法典》的施行,理论界和实务界应逐步深化对其中“相应的责任”条款的研讨,形成更多理论共识,积累更多实务经验,在理论与实务、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有更深沟通的基础上,尽量消弭对此类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尽量消除同案不同判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