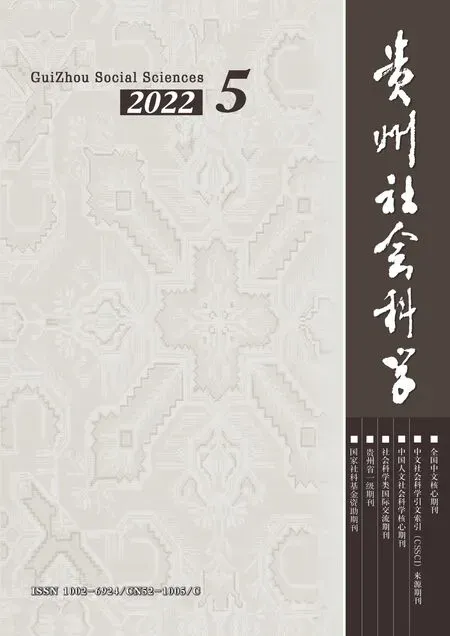《管子》“煮海为盐”神话历史谫论
2022-07-20孙凤娟
孙凤娟
(江苏大学,江苏 镇江 212013)
盐自古及今都在人类日常饮食中占据着关键性位置,正所谓“夫盐,食肴之将”(《汉书·食货志》),“国无盐则肿,守圉之国,用盐独甚”(《管子·轻重甲》)。与此同时,海盐生产也始终是中国盐业生产的主项,比重占据整个盐产量的80%—85%,接下来是山西解州盐湖所产之盐(10%—15%)以及四川、云南的井盐(5%)。[1]20通过爬梳传世经典文献可知,关于盐的史料记载整体而言相对匮乏,这虽为《管子》煮海为盐问题提供了阐释空间,但研究者囿于研究路径择选偏误等因素,致使考释无法得其要领,或语焉不详,甚或臆说歧出。文学人类学力倡四重证据法,解决了经典要籍中诸多难解乃至无解的哑谜疑案,为考释《管子》煮海为盐的神话历史问题另辟出一条择选路径。
一、《管子》“煮海为盐”的神话学发生背景
早期经典《世本·作》所记录的“夙沙作煮海”,是目前已知关于夙沙氏煮海为盐神话最早的史料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盐业史的开端。而自两汉至明清的经典文本对此所载,也基本上承袭《世本》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古者夙沙初作鬻海盐”,“鬻”意即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涑水》引吕忱曰“夙沙初作煮海盐,河东盐池谓之盐”;而北宋官修韵书《广韵》曰“古者宿沙初作煮海为盐”,“宿”与“夙”通;明人彭大翼则谓“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红、白、黑、紫五样”(《山堂肆考·羽集》)。所有这些描述都共同诠释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传说时代的夙(宿)沙是第一次煮海为盐的实践者。
当然,被崇奉为“盐宗”的夙沙氏身份问题也曾饱受争议。《吕氏春秋·用民》云:“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2]《淮南子·道应训》云:“昔夏、商之臣,反雠桀、纣而臣汤、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此世之所明知也。”[3]《太平御览·饮食部》引《鲁连子》云:“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溃沙,虽十宿不能得也。”[4]研究者基于历代注释家的注解,通过这些被称作“神农诸侯”或者“黄帝臣”的夙沙之民,普遍认可夙沙为炎帝、黄帝时代的上古部落,而非专指特定的人物个体。由此将齐国人鲁仲连笔下的宿沙瞿子,视为夙沙部落中最“善煮盐”的盐工,显然更能成立。
古籍文献资料显示,中国古代海盐生产的发生地越来越明确指向渤海南岸地区,更准确地讲,位于管仲就任上卿的齐国境内,这与夙沙部落“齐滨海”的地望近乎一致。《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5]147-148邵望平等学者根据考古学证据,认为《禹贡》所述九州风物与夏商周三代考古所揭示的史实相符,故而其中所载青州盐贡之说亦当是事实。因此,至迟在商周时期,九州之一的青州已经成为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不仅如此,擅长煮海为盐的部分夙沙后人很可能已经参与到了国家政权之中,《左传》中曾屡次提及的齐灵公寺人及少傅夙沙卫就说明了这一点,炎黄时代的夙沙部落也得以在今天山东寿光北部沿海地带繁衍生息。
“夙沙煮海”神话的产生与流传,奠定了《管子》煮海为盐的特定神话学发生背景,这在王仁湘收录的流行于寿光沿海地区的传说故事中有所反映:“夙沙部落的部落首领夙沙氏,聪明能干,膂力过人,善使绳网,每次外出打猎,都能捕获很多的猎物。有一次夙沙氏在海边煮鱼吃,他提着陶釜从海里打了水放在火上煮,突然一头大野猪从眼前飞奔而过,夙沙氏追猎野猪回来,釜里的水已经熬干,釜底留下了一层白花花的细末,他第一次尝到了又咸又鲜的滋味,这美味就是盐。夙沙氏尝试着再用陶釜煮海水,得到更多的盐,从此煮海就成了他和他的部落新的营生。”[6]
上古时代,以夙沙氏为代表的初民对于偶然得到的盐充满敬畏。初民赋予盐一种超自然的神性与灵性,并逐渐建构起一种神圣性的神话想象景观。这在今天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部分原始部落中仍然能够觅得踪迹。比如,在大洋洲新几内亚的巴鲁亚(Baruya)部落中,原住民通过焚烧“盐草”植物,进而从灰烬中提取盐分制成盐棒,巴鲁亚人借助于这种特有产品与周边部落长期进行着“不等价交换”,他们甚至能够用一根盐棒换取六个树皮布斗篷。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将其归因于“双重缺乏”的巴鲁亚垄断,即“产品缺乏”和“知识缺乏”。[1]68事实上,这种所谓“双重缺乏”源自巴鲁亚人独占着令其他部落极度羡慕的“神奇知识”,他们相信唯有巴鲁亚人才拥有上天赋予的从“盐草”植物中提取结晶盐的神秘能力。英国心理学家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指出:“古往今来,盐一直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这种意义远远超过了它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荷马把盐称为‘神赐之物’,柏拉图把盐描述为对诸神来说极为宝贵的东西。我们如今注意到它在宗教仪式、缔结盟约和行使咒语时的重要性。而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情况应当一直如此,这表明它是人类的普遍性,而不是什么地域性的习俗、环境或者概念。”[7]
由此推知,在夙沙最初煮海的神话想象大背景下,初民对于充斥着神秘色彩的盐所怀有的虔诚敬畏之心,在很大程度上助推夙沙部落终将煮海为盐作为“新的营生”。而古时,被奉为神物的盐还常与“玉帛二精”同出于祭祀水神等神圣礼仪之中,据《后汉书·祭祀志上》载李贤注引“汉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马珪璧各一,衣以缯缇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盐一升。”[8]虽然盐在汉祀令中用量仅为一升,但是重要性却不言而喻,而且也只有祭祀黄河水神时才会使用,其他川水之神是无此待遇的,这些显然与巴鲁亚人掌握盐棒的制作技巧、荷马将盐视作“神赐之物”一样,都能够反映出相同的神圣信仰与观念。
在“夙沙煮海”神话中,盐作为一种兼具稀缺性与神圣性的新物质真正融入进来,充当起神圣进行自我表征的“显圣物”角色,为整个煮海为盐叙事重铸了圣化符号意义。赵世瑜指出,“无论是历史还是传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9],这样的出发点无疑非常中肯,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皆可被视为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因此,在具体阐释《管子》煮海为盐的神话历史时,不应将神话与历史人为对立起来,而是应该透过代表着人类文化基因的神话,最大限度还原文献记载遮蔽下的历史真实信息,进而使重新解构历史撰写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二、“盐”“卤”同质:出土文字中的圣物与信仰
如果说《世本》诸典籍所载笼统或者拟测之辞偏多的话,那么《管子》一书则真正做到了“渠展”“北海”等地理名称记载的具体化:“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管子·地数》),“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管子·轻重甲》)等,这显然是对煮盐地域的进一步明确化。然而,在《地数》《轻重乙》《轻重丁》诸篇中多次出现的“煮泲水为盐”之“泲水”却迟迟未能明确其“地望”所指,原因恰恰就在于受传统思维所囿,部分学者盲目而偏执地欲给“泲水”找到一个合理定位。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泲水”并非地名实指,清儒于鬯曾言:“泲盖谓盐之质。盐者,已煮之泲。泲者,未煮之盐。海水之可以煮为盐者,正以其水中有此泲耳,故曰‘煮泲水为盐’。”[10]惜其观点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马非百据于鬯之说,得出“泲水云者,当即今之所谓卤水”[11]的结论,自此以后,“泲水”即“卤水”的观点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可。“海出泲无止”,“煮海为盐”很大程度上应是先将海水浓缩成卤水,抑或从海水中淋出卤水,再将其煮而成盐的,这可通过山东寿光大荒北央商周遗址所发现的用于挖取地下卤水的卤水沟进行印证。当然,此类现象在渤海南岸地区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中同样并不鲜见。


需特别注意的是,齐国“亡盐戈”铭文之“盐”,上部为“滷”。《尔雅·释言》云:“滷,苦也。”邢昺疏曰:“云‘滷,苦地也’者,谓斥滷可煮盐者。”[5]2581而“斥”与西方鹹地所生之“卤”不同,普遍指称东方海水浸蚀之地所产的不湅之盐。《管子·地员》载:“凫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状,甚鹹以苦,其物为下。”[16]1142郭沫若《管子集校》指出“汪继培云:此即《周礼》所谓‘鹹潟用貆’者也。《禹贡》‘海滨广斥’,康成《注》‘斥谓地鹹卤’,《说文》‘卤,西方鹹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斥’、‘桀’音亦相近。”[17]齐国五桀之地居滨海,深受海水浸蚀影响,遍布斥卤,土质最差,故“五桀”意即“五斥”,汪氏所言甚是。此外,结合冯时借助青铜铭文所载伯懋父率军征伐东夷,一直攻打到海滨的背景来推断,“五桀”当为西周早期古土田之制中的滨海斥卤之地。
商周以前,“斥”“卤”虽有分布地域的东西之别,但本质上并无二致,在初民的观念中,二者皆可与“食肴之将”的“盐”划等号。殷商时期,统治者有用盐卤祭祀的传统,盐卤也因而具有了飨神祀祖的特殊属性,被初民视为“圣物”,这与《周礼·天官》所载“祭祀,共其苦盐、散盐”的古礼制是一致的。此外,赵平安根据马王堆一号汉墓103、104遣策上的“盐一资”记载,以及同墓所出印文陶罐中的“盐一资”竹牌,认为盐也作为随葬物品使用。[18]
因此,“夙沙煮海”神话最初讲述的或许是作为英雄王者的夙沙氏受命于天的传奇故事,而在后来华夏文明的不断形成过程中,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对盐这一“圣物”进一步从“神话化”转向“神圣化”。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竹简帛书中对于煮海为盐的明确记载,更是将初民信仰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盔形器:物的在场与叙事
“夙沙煮海”虽系神话传说,但其反映出的历史却并不虚无,进一步讲,煮海为盐所体现出的隐喻持久性与文化穿透力,对今天整个山东北部沿海地区依然影响深远。盐作为一种在遇水和高温环境下极易溶解流失的物质,性质极不稳定,今人是无法直接获取古代盐实物的。但是,近些年的盐业考古新发现,却为重新探讨煮海为盐问题提供了说服力强大的实物证据支撑,这便是在以渤海南岸为代表的鲁北沿海地带广泛分布且数量众多的盔形器。
盔形器,是具有浓郁山东地方特色的一种常见陶器,多为泥质或夹砂灰褐陶,直口,筒形腹,壁厚,圜底或尖底,器身饰绳纹。通行于商周时期,普遍被视作煮盐器皿,是海盐生产的专用工具。根据调查统计,鲁北地区目前出土盔形器的遗址超过70处,这些盔形器“集中分布于渤海湾沿岸地区,与地下卤水的分布带恰切相吻合……由内陆居民制造并运输到制盐遗址,结果盐和海产品又被带回至内陆地区”[19],这已经在山东沿海地区的盐业考古遗址中被大量证据所证实。然而,鉴于博兴、章丘、邹平、桓台、临淄、青州等地的盔形器多出于水井之中的事实,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鲁北内陆平原地区盔形器中,不排除有一部分充当汲水器的可能性。但沿海地区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圜底或尖底盔形器,其功用为煮盐无疑,这与至迟在商代晚期鲁北渤海沿岸地带已然成为重要产盐区的历史甚为相符,两周尤其是战国时期,海盐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管子·匡君小匡》所载“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几而不正,壥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宽焉”[16]439-440,足以为证。
在考古学上,盔形器无疑已被视作用于海盐贸易与分配的标准量器,但若被认定为煮海为盐的生产工具,仍需提供更具实证性的科学依据,这不是由器物型式决定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器内残留物是否具备盐的属性。燕生东指出,盐业遗址内出土的器物中95%以上为盔形器,而90%左右的盔形器腹部内壁都存有白色垢状物,双王城014B遗址灶室内出土了成堆的白色和黄白色块状物,其特点是内部呈颗粒状、空隙大、结构松散、重量轻,同时在生产垃圾内还发现了成片的白色粉状物。[20]105后经X射线衍射(XRD)分析等科学方法鉴定,表明双王城遗址内所发现的大量白色物质为碳酸盐,而这些物质正是在煮盐过程中形成的。这就证明与双王城遗址一致,大荒北央遗址所见白色垢状凝结物同样非盔形器在埋藏过程中受浸染所致,而是属于自身所有,由此观之,鲁北沿海地区考古出土的盔形器当为煮海为盐的专属工具。
笔者通过主要盐业考古遗址内遗迹与遗物分析,再综合考量各家观点,认为燕生东对于盔形器煮海为盐流程的复原描述可信度更高:“制盐原料为浓度较高的地下卤水而非海水。从坑井内取出卤水后经卤水沟流入沉淀池过滤、沉淀,卤水在此得到初步蒸发,再流入蒸发池内风吹日晒,形成高浓度的卤水,在这个过程中,部分碳酸镁钙析出,卤水还得到了纯化。盐工把制好的卤水放入盐灶两侧的储卤坑。在椭圆形和长方(条)形灶室上搭设网状架子,网口内铺垫草拌泥,其上置放盔形器。在工作间内点火,往盔形器内添加卤水,卤水通过加热蒸发后,不断向盔形器内添加卤水。煮盐过程中还要撇去漂浮着的碳酸钙、硫酸钙、碳酸镁钾等杂质。盐块满至盔形器口沿时,停火。待盐块冷却后,打碎盔形器,取出盐块。最后把生产垃圾(盔形器、烧土、草木灰)倾倒在一侧。”[20]105
通过对盔形器的分型定式,结合其由圜底向尖底的形制演变序列不难推知,其祖型应为史前文化中的圜底器。相传炎帝发明陶器,所以在炎黄时代,夙沙部落用圜底器煮海为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从人类学提供的民族志资料审视,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圜底器进行煮盐生产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诸如非洲尼日尔共和国芒加(Manga)地区发现的圜底盆、德国萨勒河(Saale River)畔出土的史前圜底器、墨西哥特斯科科湖(Lake Texcoco)区域居民使用的圜底罐等,这些圜底器在承接卤水进而熬制盐饼方面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更为有趣的是,考古学家在中美洲国家伯利兹(Belize)的古典期玛雅文化盐业遗址中,出土了包括圜底罐、隔垫和柱形支座等在内的整套陶器组合,并且这些圜底罐的使用也是一次性的。[21]国外学者由此推断出该遗址与中国山东北部沿海地区使用盔形器煮海为盐近乎一致的操作流程。
结合山东北部盐业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对出土盔形器进行综合考证分析,不仅将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地望推定到广饶至寿光古海岸附近,甚至将范围进一步缩至双王城一带,与此同时,还为后世文献中煮海为盐工艺流程的文字以及图像描述提供参考与借鉴。元代陈椿著有《熬波图》一书,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对煮海为盐设备和工艺流程予以系统描绘的专著,虽然此时盔形器已不再作为煮盐设备使用,但鲁北沿海地区发掘出土的盔形器却为书中所绘流程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盔形器的不断面世,也对诸如北宋唐慎微所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直接将海水导引至锅中熬煮的合理性,留足了质疑空间。
陈来指出:“在早期文化发展时代,人们认为火、工具、医药、文字的发明不是靠人的力量和智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神灵赐给人们的赠品。文明被看作从神灵手中接受来的东西,而不是人所创造的产物。”[22]通过前述古籍文献与出土文字可知,盐同样可被视作“神灵赐给人们的赠品”,作为煮盐“工具”的盔形器在被创制之初,或许也曾被视为神赐赠品,只是它随着功用在后世逐渐发生从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原初意义得以被重铸,与初民所赋予的符号意义相脱离。但毋庸置疑,考古发现的盔形器足以彰显物的叙事所特有的证明优势,实现着夙沙煮海神话与客观历史之间的有效对接,使文字记载终得印证。
四、咸与权:盐在齐国历史中的地位
近年来,文学人类学愈发重视物质文化研究,尤为重视物所承载的原初编码意义,因受神话思维主宰,这种文化编码得以将初民观念中的文化想象与神话叙事彰显出来。事实上,初民同样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之中,其生产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表达等都会受到所处时代物质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深刻反映出自身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信仰。自上古经殷商至春秋战国时代,煮海之盐对人们行为及观念的诠释效力尤为明显,丰富的海盐资源与《管子》中首创的食盐专营制度,更是助推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盐在整个齐国历史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山东北部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有海盐生产传统,资源充裕,工具先进,工艺成熟。事实上,商人东扩的目的之一就是获取丰富的海盐资源,同时掌管古济水、泗水等重要的交通运输路线,这从济南大辛庄、滕州前掌大等遗址发掘位置以及出土文物都能够得到证实,如此便可将鲁北、鲁东南地区的海盐等自然资源经此运达商王朝统治区。西周时期,海盐资源以及交通线路对于中原地带周王室的供给作用,同样不言而喻。但到春秋之时,随着周王室渐衰,以齐国为代表的各诸侯国虽然也向周天子象征性献贡,但是将绝大部分资源据为己有已成既定事实。为了更好地管理海盐资源,为齐桓公称霸进行经济蓄力,《管子》针对性地提出“官山海”“正盐筴”的盐政主张,意在通过食盐专营实现富国安邦之治。《管子·海王》对此记载甚为明确: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筴。”桓公曰:“何谓正盐筴?”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今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筴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筴,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16]1246
对此,曾仰丰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管子之意,以盐为人民日用所必需,若明令征税,则人民鲜有不疾首蹙额呼号相告、以图抵抗者,不如寓租税于专卖之中,使人民于不知不觉之间,无从逃脱,则盐利收入,其数必钜,公家可不必另筹税源,而国用已足,此乃专卖制之优点,故《海王》一篇,实为千古言盐政之祖。”[23]事实上,盐政推行目的在于巩固统治阶层的特权,盐所负载的物质文化意义理应服务于政治象征内涵的表达,这种特殊物质体现出的高度特权性源于自身具有的稀缺性、神秘性与不可或缺性,只是此时的稀缺性与“夙沙煮海”神话发生时代不同,乃食盐专营的盐政所致。
商周时期,盐作为“国之大宝”而倍受统治者重视,统治阶级上层掌有盐业大权,并为此专设司盐之官。殷商王室已经设有“卤小臣”之职来掌盐卤之事,而《周礼·天官·盐人》亦有“盐人掌盐之政令,以供百事之盐”的确切记载,只是“卤小臣”与“盐人”尚存区别。但根据甲金文的具体记载可知,商周王室的用盐主要集中在祭祀、赏赐、朝宗与易物四个方面:“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主要是王室献祭祖先,以庇佑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利好之需;统治者将盐赏赐臣下,有助于维系君臣关系;盐卤被视为奇珍之物,也会作为宗族内部朝问觐见的致送之礼;盐因自身的特殊性,有时还具备一般等价物功能,进而被统治阶级用来交换其他物品,春秋时期的晋姜鼎铭文就曾记载统治阶级用盐换取铜料之事。但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商周贵族统治阶级的用盐行为,盐在此时是奢侈品,具有无可比拟的象征价值。
到了齐桓公时代,虽然盐依然能够体现出豪绅权贵们的社会地位,但即便开始实行食盐专营制度,此时的盐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必需品,变得更易接受、更家常化,他们将盐的用途进一步丰富并进行重新分化,进而融入新的语境之中。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W. Mintz)指出:“在复杂的等级社会中,‘文化’从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体系。它的突出特征是,在不同的层级有行为和态度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观念、实物和信条的使用、运作及变化的区别性方式表达并反映出来。文化‘资料’,包括物质实体、描绘它们的词汇以及行为和思考的方式,能向上或向下运动,从贵族到平民,或相反。但一旦发生,它们的意义不是毫无变化的。认为这样的扩散向上与向下同样容易,或者频繁,是天真的想法。财富、威信、权力和势力肯定影响到扩散发生的方式。”[24]
可见,不同等级社会中的“文化”差异需要借助观念表达、物质使用等方式表达出来,物质实体与行为方式等文化“资料”的扩散,同样会促使其意义发生变化。毋庸置疑,随着齐国经济实力愈加强劲,盐自上而下、自内而外不断扩散转移开来,其象征价值随着产量增多而渐趋衰落乃至穷尽,已然失去了自身区别标示使用者特殊地位的力量,成为一种有别于殷商与西周之盐的“新物质”,不可避免地更改原有意义或者产生新意义,功能属性也更趋简单与泛化。但不可否认,统治阶层的财富、威信、权力和势力定然影响到了盐扩散发生的方式,其作为利润来源的潜力却是日益上升,从最初的上层奢侈品逐渐演变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这就为齐国称霸天下提供了最现实的经济驱动力。
目前的盐业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足以表明,东周时期是莱州湾沿岸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继殷墟至西周早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管仲相齐,大力推行盐业政策,通过轻重之术进行国家干预,在国内利用“正盐筴”获取大量盐业税收收入,此外,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使这些国家在海盐消费上不得不对齐国形成依赖。齐国正是凭借着内外兼举的盐政管理策略,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特殊咸味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国家财富积聚,国力提升。
五、小结:神话观念驱动行为动机
神话中存在真实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吗?从国内文学人类学所倡“神话历史”视角分析,这或许不再是一个关涉“神话/历史”二元对立的问题,以往普遍被认为具有虚构属性的神话传说故事,如今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与遗物,已经被证明或者至少部分被证明是可信的,毕竟它们极有可能承载着远古时期的原初文化记忆。神话观念驱动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且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驱动作用,当然,神话观念驱动论这一理论命题,重在强调观念史、思想史与文化史开展贯通式研究的一种整合性视野。目前,比较神话学与考古学、物质文化研究的日益结合,实现着向“神话历史”研究范式转型的诉求,如同伦福儒(Colin Renfrew)强调的那般,新的物质性逐渐使得新的社会互动成为一种可能:“在人类社会中,有形物质如何能够呈现意义而产生新的制度事实;人类创造了物质符号,于是形成可感知的现实……物质和财货是如何呈现价值与意义,之所以如此,是透过人类这种赋予无生命物质意义的特殊习性,因而使这些事物成为象征符号,但是它们不只是象征符号,实际上还能将财富具体化,而且能授予人类权力。”[25]
史前期的盐因在色、形、味等方面呈现出神秘性,被初民视为能够进行自我表征的“显圣物”,正是虔诚的信仰观念与盐这种神圣物质的交互作用,才成为催生后世文明的驱动力。考古出土的文字与文物材料,已经用阐释效力充足的证据,证实商周时期煮海为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夙沙煮海”神话所反映的历史不虚。《管子》中推行食盐专营的经济策略,与周边国家进行盐业往来,大规模的煮海为盐行为得以发生,这当然离不开文化观念的支配作用,或可认为“夙沙煮海”神话与《管子》所载“煮海为盐”所体现的正是源与流的关系。
正如叶舒宪指出,人类最初建构宇宙观的行为,来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26]神话是初民智慧的表述,能够最充分地保留着远古时代的信仰观念。自古及今的每一个文明时期,都有其自身所信奉的神话体系。人是文化性动物,必然深受自身文化观念的影响,今人没有办法直接去碰触或者体认初民所构拟出的神话故事,但是却能够间接获取他们早期活动留下的某些极有价值的物质痕迹。借助这些无文字记载的物与图像,研究者们或可更多地求解神话观念支配与叙事表达的规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