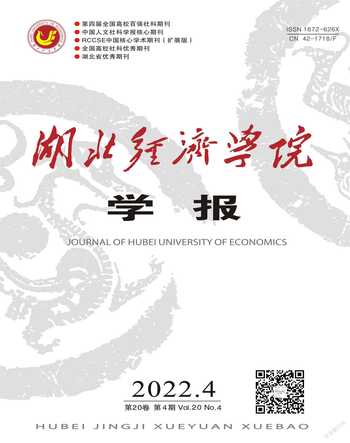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重新探究:基于自然禀赋视角
2022-07-18吴亮
吴亮
摘要: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贫困,以现实的人与社会矛盾为基点去剖析贫困问题,最终形成系统性的反贫困思想。在马克思的视野下,现实的人本身和周围自然禀赋的差异在社会制度的作用下,将影响主体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贫富的两级化。因此,在反贫困斗争中,除了制度因素外,还应顺应人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自然这两条逻辑主线,坚持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两个基本原则,最终实现主体平等自由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贫困;自然禀赋;制度
中图分类号:F091.91;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22)04-0041-08
一、引言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作为中国脱贫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至今,关于馬克思反贫困思想研究的成文性文献资料共计200余篇,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探讨。王浩斌和李勇(2021)从人学的角度去刻画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的相对贫困问题[1]。但马克思贫困化问题的“有时现象派”代表人物蒋学模(1979)认为马克思反贫困思想是一个严密的整体,自然要分析无产阶级贫困的各种形式,包括绝对与相对[2]。郑继承(2021)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贫困问题不应区分绝对与相对,生产总量的提高减少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问题凸显,但工人阶级状况持续恶化又内涵着绝对[3]。
二是对无产阶级贫困制度性因素的探究。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因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被迫出卖劳动力,与资产阶级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雇佣关系,在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规律的支配下,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产阶级攫取,其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4]。此外,资产阶级的逐利性使其提高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造成相对过剩的人口。对资本积累的渴望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平稳性,将更多人抛向贫困的窘境[5]。
三是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尤其是其思想的中国化方面。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理论指南,与我国不同时期反贫困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反贫困理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认为消除贫困必须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一化三改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从思想层面革新“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论断;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从思想上淡化“贫穷意志”,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并最终形成了以人为中心、以精准扶贫为路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6~7]。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虽然在研究目的、结构和范式上存在差异,但研究内容均侧重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的制度因素,即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导致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诚然,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的内生性是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若将贫困仅理解为制度因素,易造成对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理解的片面性。因为马克思也注意到人自然禀赋的差异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化,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及“个人的肉体组织”[8]519的先天差异,以及水源、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的“自然的效用”[9]728对个人和社会福祉的重要作用,而现有的文献资料尚未对此有成文性的论著。基于此,本文试图基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自然禀赋的视角,剖析自然禀赋致贫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以期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
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丰裕只能消除因物质匮乏而产生的绝对贫困,而缓解相对贫困将是复杂而艰巨的长期任务。处于后减贫时代的中国,治贫的重心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移。这种转向,背后不仅体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发展、社会公平、绿水青山的美好向往。当此之时,从自然禀赋的视角重温和探讨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二、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的贫困
马克思虽然认可主体自然禀赋差异而导致不平等的客观事实,但在其经典论著中并没有形成自然禀赋的系统性理论,其相关理论思想只能从贯穿其著作始终的“自然条件”“自然分工”“先天能力”“天然优势”等词探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进一步将自然条件细分为人本身的自然和人周围的自然。这两种自然的不同,导致主体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基本生存空间、基本发展状态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主体贫富的两级化。
(一)人本身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的贫困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的天赋才能、生理特征、血缘关系的差异导致个体通过自己的肉体组织及其与自然的关系创造出的物质生活条件存在差异,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着肉体组织发展的状况。在天赋才能方面,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及“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发性等等”会自然或自发地形成社会分工[8]534。对于这种个体天赋的不平等造成的工作能力的不平等,马克思称之为“天然特权”[10]435。这种天然特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天赋不同的个体从事的职业各异,而这种分工引发的生产和交换与人类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得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的物质的联系,这些物质的“纠缠”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8]533。换言之,天赋差异会导致个体社会分工的不同,进而导致所得的不均。
在生理特征方面,性别是现实个体最直观存在的客观差异,在父权制社会似乎带着“原罪性”。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从私有制、家庭内部分工、社会生产等方面阐述父系社会女性被禁锢、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在蛮荒和英雄时代,女性之于男性“不过是他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11]75,甚至被当作“商品”随意送出。女性被迫成为男子的附庸,处于半囚禁状态。即使在文明的大工业时代,个体家庭的维系还是“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11]78。马克思将这种家庭内部以生理为标准划分的“两性自然分工”,讽刺为资本家对无产者的残酷剥削:身为男性的资本家从事着有偿的社会性服务,而身为女性的无产者被迫从事无偿的家庭性工作[11]87,187。即使女性外出从事社会性服务,也因为性别差异报酬更低。以煤矿厂为例,女性每日报酬比同工种的男性少5/13~8/13。正是这种阶级压迫并性别压迫,才会导致富饶的英格兰农业地区,缺乏营养的往往是妇女,因为男人要外出从事社会性服务而具有享用食物的优先权[12]755。此外,儿童手指纤细、身躯瘦小的生理特征也被利用得淋漓尽致。细巧的织物需要儿童灵巧的的手指,儿童如牛羊一样被杀戮。房顶的烟囱正好容纳瘦小的身躯,儿童被父母贩卖成为“肉体烟囱清洁工”[12]457。托·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曾说:“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对他能力使用的报酬”[12]198。但是,除了因天赋导致的能力差异外,性别和年龄也成为制约肉体组织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父权制下,这种天然的生理特征差异成为男性剥削妇女儿童的帮凶。
在血缘关系方面,其作为人类最初始和最本源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家庭关系、种族关系等,这些血缘关系的存在客观上造成了个体发展的异质。在家庭关系方面,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虽然认可霍布斯有关人的价值的论述,但也不禁发问:为什么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些人是天生的买者,而有些人是天生的卖者?除了后天机遇外,预先积累最为关键。以亲缘关系紧密结合的世袭社会,必然会导致“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11]336。资本家依靠世代沿袭所获得的财富,在制度的扶持下,获得各种垄断的特权。印度的种姓制度最为典型,以种姓为标准的职业世袭分工造成低种姓的贫困代际传承。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业的排他性使得技艺只在家庭内部传承,先天因传承而获得优势的群体,利用特权阻碍弱势群体后天习得技能的权利。为了维护世袭的权利,“给予人们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13]377。马克思用“地道的俄国手段”讽刺德国特权阶级用卑劣的手段扼制底层青年发展,使高等教育变成上层社会的专享[14]409。穷人甚至被唐森批评是“轻率的”,就应该陷入永久性贫困,就应该从事低贱、肮脏的工作,谁让他们“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12]745。这种因贫富和特权的世代传承而引起的分工,通过制度的强化代代传承。
在种族关系方面,马克思主要聚焦以下三点:其一,以亲缘或其他关系形成的社会群体存在相同的特质,比如,西徐亚人是“擅射的”[8]765,施特劳宾人是“愚昧的”[14]715,中国人似乎具有多面性,被称为“节俭的”“勤劳的”[13]674,甚至是“可憎的”[14]636。这种种族的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裹挟着个体肉体组织与种族同步发展。马克思指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与劳动生产率相联系[12]586,如英国人生产棉花的劳动产出率高于印度人数倍。其二,不同种族之间特质各异,因而面临困境时采取的策略不一。如同样面对英国的侵略,波斯和中国采取了不同的抵抗策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13]622。其三,种族与杀戮和剥削关联。资本家出于利益目的而进行的探索和开发,导致美洲土著被剿灭,东印度的居民被殖民被掠夺,非洲成为北美黑人奴隶的货源地。而这种剥削和掠夺,却被殖民者包装成“德政”和“仁善”。殖民者的强势地位为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和本国经济的发展,但给被殖民国家带来了无尽的穷困和杀戮。
(二)人周围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的贫困
在马克思看来,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和其他资料的自然富源作为“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直接影响了劳动者获取劳动资料的的成本[12]586。首先,关于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马克思谈论最多的是土壤的肥力,将其分为自然肥力、人工肥力和经济肥力。自然肥力是指表层土壤所含植物的养分。肥力作为土地的客观属性,其天然养分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土地的产出和改造成本。马克思认为土地最初以食物形态供给人类生活资料,其多寡完全依赖于土壤的自然肥力[12]208。但是自然肥力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随着农业技术和化学水平的发展,对土壤进行改造会使肥力发生动态变化。这种人为的“处理”,马克思称之为人工肥力。可以看出,人工肥力以自然肥力为基础,是在自然肥力上的后天改造。在产出同样的前提下,不同土壤的改造成本不一样,如肥沃的潘帕斯草原无需过多改造,而贫瘠的密歇根州则需较大的后天投入。自然肥力和人工肥力在同一块土地融合,会形成经济肥力。马克思指出,“从经济肥力的角度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和土地的化学结构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也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9]734。这种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异,不仅导致土地耕作者投入产出的差异,在经济上也导致级差地租的出现。
其次,关于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马克思对此主要谈及自然力。这里的自然力指界定自然界的自然力,即马克思所说的单纯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15]279,以及人化自然力,如煤矿、金属等。自然力和人都是劳动生产的第一要素,人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作用于外界,会形成“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单纯自然力是可再生资源,是一国或地区内在作为自然生产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在各国文明发展的初期起着关键性作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单纯自然力的差异,决定了使用该自然力作用于生产力发展的异质。如英国因水力资源丰富而广泛使用水车,荷兰地势平坦低洼只能借助风力。人化自然力是不可再生资源,是“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16],它的开发和使用对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然,人化自然力具有异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人化自然力不同。人化自然力也有其自然阈值,一旦突破该阈值就会成为反噬的力量,破坏生产的自然条件,造成环境危机。同时,人化自然力的可被掠夺性,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化自然力的质和量具有可变性。具体如何变化,取决于该主体在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处于压迫地位的主体,借助科技的力量,可使被压迫地位的主体陷入贫困。
最后,关于其他资料的自然富源,指既非生活资料也非劳动资料,但也是人周围存在的客观自然,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等。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其在空间上与其外部的自然、经济、政治等客观事物相结合的点。有利的结合即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助于主体的发展。如马克思在《俄国对话贸易》中,用地缘优势解释恰克图为何能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如何从普通要塞发展成大都市。一国或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往往也决定了该国或该地区职能的特殊性和规模性。农业国家如埃及、印度是两河流域途经地,利用河水来润泽沃土肥田;商贸港口城市如利物浦、布里斯托、伦敦临江临海,几乎垄断了英国的海上贸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财富的无限制贪求,破坏了自然力的内生循环系统,造成生态失衡。外部环境的失衡变化,危害生命生存和发展。如浑浊的空气助长了肺病的发展,污染的水源成為病毒的培养皿。这种生态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蔓延,造成了肉体组织的虚弱无力、身材瘦小,进而制约了个体与物质产生联系的程度,最终造成居于污浊环境下个体的疾病与贫困。
三、自然禀赋与制度的互动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本质,是以现实的人为研究主体,以社会制度为承载客体,其中现实的人的自然禀赋与制度的互动是其反贫困思想的逻辑要点。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导致财富马太效应的基础上,马克思追根溯源,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剖析从蒙昧到文明时期现实的人的自然禀赋在制度要素的作用下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指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完全消除因自然禀赋导致的现实的人产生的贫富两极化现象。
(一)人本身的自然禀赋与制度的互动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现实的历史,其发展方向、发展空间、发展程度从根本上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直接上则取决于人过往交互活动的现存产物,即社会制度。在制度的作用下,天赋才能、生理特征和血缘关系等人本身的自然禀赋对肉体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力各异。首先,天赋才能方面。在制度要素的作用下,天赋才能对个体发展的效用呈Ω型。在原始社会低级和中级阶段,在“最具天赋的人”的带领下,生产和分配归集体统管统分,天赋才能的个体差异对肉体的发展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效用。在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出现,进而导致如果占有的生产资料越多,则占有的剩余产品也就越多。于是,社会制度逐渐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而那批原始社会内部“最具天赋的人”,通过“天赋”的积累在“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原始形态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中占据优势”[1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中,马克思指出在狭隘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财富是人对自然力(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15]137。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话;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15]137。人与人自身异化,人被当作活的劳动器官,个人智力、体力等天赋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影响工人的分工等级。但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肌肉使用已成为偶然”[12]432,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也从主导沦为从属。这种转变,使得天赋才能对个体发展几乎再没有任何促进效用。马克思在《分工和机器》中也曾用家犬和猎犬之间天赋的差异明喻天赋才能对个体发展效用的微小。而这种微小被“烫平”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天赋才能的差距必被后天全面自由的发展所弥补。
其次,在生理特征方面,制度的变迁似乎削弱了性别这种最为直观的生理差异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在原始社会,用性别来对标权利和义务是荒谬的,性别只是一个符号,“男女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11]178,共享所有的财产和平等的权利。但是,这种平等的特权随着新财富的出现而被破坏。由于男子活动的领域正是野蛮时代财富增长的风口,而妇女的家务性劳动与之相较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11]181。物质决定意识,这种男女财富的分配决定了家庭内部的分工,也决定了男性的统治地位。这种统治,“由于母权制的颠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15]137。即使在“肌肉使用已成为偶然”的资本主义社会[12]432,女性也只被当作剥削的对象、男子廉价的劳动替代品。即使法律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12]87。那么女性又该如何摆脱性别的局限?马克思指出女性只有回归人的本质,回归公共事务,才能摆脱性别、自然、社会对其的约束,获得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这些只有在“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属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也必将实现[11]88。
最后,在社会制度的作用下,血缘的亲疏程度和影响力呈下降趋势。在家庭血缘方面,马克思描述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家庭[8]532,其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是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在原始社会,家庭关系与群婚制结合构成了共产制的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两种形式。在血缘家庭里,近亲繁殖影响了人类智力和体力的发展。而在普那路亚家庭里,母亲、姐妹、子女等称呼并非单纯的荣誉符号,而是确定的成员归属和郑重的相互义务。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体家庭有能力立足社会,进而从共产制家庭中分离出来,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单位的核心,婚姻家庭制度也向专偶制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家庭以家族为本位,由夫权统治,个人的身份属性和发展空间取决于父亲。如印度的首陀罗只能从事苦力劳动,而婆罗门则处于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对家庭的依附关系较之前大为削弱,个人的独立性增强,但是家庭关系却增添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性质,家庭的温情也被冷冰冰的金钱替代。马克思认为,专偶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男性要将其财富传承给后代,而无论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无法改变财富的代际传承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财富绝大部分归社会所有,专偶制存在的经济因素才能消失,个体的发展才不会受制于家庭。
在种族血缘方面,随着制度的更迭、生产力的发展,种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加深,各种族之间的特质逐渐淡化,呈现同化的现象。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市民社会不断创造具有“犹太精神”的利己主义者,热忱和友善的种族之气逐渐消散。在社会制度这个主动轮的驱使下,美洲的土著被剿灭、被奴役,非洲成为黑奴合规的货源地,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公民成为劣等公民。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田园诗般的发家过程,导致了基于肤色、血统及其他外形特征的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一经出现,就会不断地自我包装,以证明其掠夺、剥削的正当性。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鼓吹的“自由贸易至上”,其实质是在商业上对其他种族的奴役和剥削,是白人至上的特权主义。这种虚伪的自由造就的种族不平等,其实质是财富阶级的不平等。只要社会成员仍按照占有财富的多寡被划分成不同的阶级,那么种族歧视存在的制度空间就会继续存在。
(二)人周围的自然禀赋与制度的互动在马克思看来,人周围的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与人的有机身体的特定关系受当前社会制度制约,不同的社会制度导致人周围的自然对人的发展效用也不同。在生活资料方面,人存在状态的历史变化导致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对个体发展效用呈弱化的趋势。在原始社会,人与周围自然的关系基本围绕着生存需要。人主要依靠周围的自然进行采集、打猎、耕种等生产活动,与周围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依赖的,对自然怀有崇拜的情感。自然被当作一种神秘而无法征服的异己力量,其生活资料自然富源的程度直接决定人从无机身体中获得生存所需产品量的多寡,间接影响个体的良性发展。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农耕和畜牧替代了纯粹依靠自然供给的生活方式,人初步形成了对自然改造的能力,但这一能力有限,自然仍处于主宰地位,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对人的发展仍具有重要作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对自然的依赖逐渐转变为对物的依赖,生活资料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也逐渐让渡给劳动资料。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生活資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劳动资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586。在这一阶段,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广泛应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程度可被人为改造,无法对个体发展形成有效制约。
在劳动资料方面,社会制度对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的效用与生活资料相异。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劳动资料对人有机组织的发展几乎不起作用。尽管这一时期人们基本都居住在水源附近,但水更多作为生活资料而非劳动资料。在农耕文明时期,工具的使用大大增强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自然力逐步成为生产的力量。随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由从属变成主导,人驱使自然力作用于生产,创造出各种满足自身精神和物质需要的使用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与周围的自然条件相关。但自然力具有地域性差异,“这些自然条件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其他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9]726。在制度和科技的推动下,这些自然力的差异决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空间和可能性大小。自然力尤其是人化自然力具有双重阈值,一重是其不可再生性带来的藏量的天然阈值;另一重是基于生态代谢效率的生态阈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逐利性必然会促使其极大限度地使用这种社会生产力。如马克思所言:“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过去哪一个世纪预料到在社会劳动力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3]36但这种发展不具备可持续性,突破自然底线的人类计划,都只会带来灾难[18]。人与自然力异化所呈现的残酷现实,一方面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暗示更高级社会制度的到来。
在其他资料方面,地理条件在制度要素的作用下,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力逐渐弱化。随着生产力发展,交通愈加便利,在经济上减轻了人类流动的费用,在制度上解除了人类流动的限制,人类的发展无需受制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在生态环境方面,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人类不合理的活动也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所以破坏性较小,在生态代谢链可承受范围内,且人们居住相对分散,破坏呈区域性、局部性特点。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的破坏突破了生态代谢效率的生态阈值,造成生态代谢链的断裂,导致生态失衡呈全球化发展态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极大的篇幅描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广泛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这些问题内在看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外在看是人與周围自然的对立,直接影响人有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路径必然是人与周围自然关系的正确定位。自然被神话,不利于发展;人被神话,带来灾难。人只有融入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对立才能真正消除。在马克思看来,金钱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倾向于破坏和贬低自然,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才能促使人与周围自然内在和外在的有效融合。
四、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对我国后扶贫时代的意义根据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自然禀赋的差异在制度要素的作用下对个体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为人全面自由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其实现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基础上,只能在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发展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19]。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全面解决了“吃饭权”的问题,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向,贫困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扶贫不能只停留在物质上,更应该关注人本身自我发展的意愿和能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一)人本身的自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批判人利用天然差异形成的累积在旧制度的作用下,导致人发展的片面性,在物质方面表现为贫富的两极化,在精神方面表现为侵吞人个性的自由发展。这种不均等、畸形的发展状态,只有通过建立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根除。可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包含了物质和制度两个基础前提,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首先,缺乏物质的制度,人的全面发展都是设想。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实行公有制,自然禀赋不会造成个体发展的差异,但两种社会人的发展却存在巨大的鸿沟,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不同导致两者物质基础的差异。物质是社会生产力的现实产物,为人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其次,缺乏制度的物质,人的自由发展受局限。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对增长虽给予人更多的自由,但并没有消除劳动者被奴役、被禁锢的状况。个体的自由被披上“竞争”的外衣,在社会制度的演化下呈两极化发展。最后,制度与财富的关系。制度作为人现实的制约,决定人发展的空间;财富作为历史的沉淀,决定人发展的程度。只有制度和财富协同发展,人才能获得全面的自由。马克思指出,只有在财富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由社会共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回到其价值归宿,才能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10]436。
在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变得复杂多样,获取生活资料的绝对贫困形态已经全面消除,现在更多的是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诸多限制,如“权利贫困”“教育机会贫困”“性别贫困”等,这导致扶贫策略有所差异。针对个体自然禀赋导致的贫困,治贫策略主要表现为:在天赋方面,教育是最好的弥合剂,国家应从制度上确保教育机会均等,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在生理特征方面,消除封建思想余毒,确立机会均等的基本原则,构建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家务劳动工资化的“家庭经济”理念,让社会认可并承担女性的家庭服务性劳动;在血缘方面,利用税收制度调控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削弱财富代际传承的效用,在法律上废除种族歧视,在思想上尊重种族文化,实现种族协同发展。此外,在物质积累的过程中,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形成的垄断成为社会异己的力量,阻滞生产力发展和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反贫困表现为: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控制和盘活现有资本,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发展回归其本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积累物质基础,同时利用宏观手段统筹调控,提供系统性、多元性、异质性、工程型的治贫手段,激活人本身蕴藏的潜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人周围的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马克思驳斥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基本关系,强调两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和谐共生关系。但在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作用下,人被神话,自然成了资本造富的工具,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破坏了人与自然良性循环生态代谢链,导致森林沙漠化、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问题凸显,威胁人与自然健康、可持续发展。要解决人与自然这些异化问题,应始终坚定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具体可以从以下四点入手:第一,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自然主义的回归;第二,合理利用科学技术,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促进人内在本质从物性到人性的回归,从追求物质转变为追求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第四,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确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共生关系。
为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早期我国曾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策略。但时至今日,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生态失衡现象日益凸显,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构建“美丽中国”的生态蓝图。在充分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人与周围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人与自然平等、休戚相关的共生意识,同时积极应对现有和未知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次,正确处理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科学技术从中协调,促进资源的生态循环,将原本的废弃物“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9]94;再次,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绿色消费、理性消费,避免无节制消费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最后,在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下,坚持“绿色、共享、协调”的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之路。
总之,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人本身、人周围自然的理论,为我国在脱贫攻坚中促进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以及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人本身自然差异的消除,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人共享发展成果,不仅为共产主义的实现积累人才的基础,也为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提供社会基礎;另一方面,人周围自然差异的根除,体现了人与周围自然和谐发展的共生关系,有助于缓解生态失衡现象,实现人们对绿水青山的美好向往。
参考文献:
[1] 王浩斌,李勇.相对贫困的马克思人学阐释及其三重维度[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1(6):20-25.
[2] 蒋学模.再谈无产阶级绝对贫穷化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2):89-94.
[3] 郑继承.相对贫困的经济学辨析与中国之治[J].社会科学文摘,2021(9):52-54.
[4] 孙咏梅.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及其对中国减贫脱贫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87-95.
[5] 杜利娜.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8):31-40+159.
[6] 魏枫,周灵丽,完颜含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理论研究[J].理论探讨,2021(5):20-26.
[7] 任东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基本经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2):81-88.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91.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19]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359.
(责任编辑:彭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