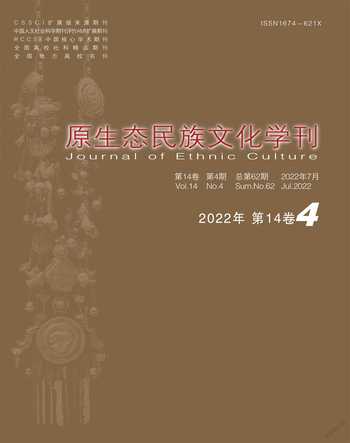创伤与信息创伤:医学人类学视域下的仪式治疗新解
2022-07-15麻勇恒张严艳
麻勇恒 张严艳
摘 要:从医学人类学的视域,对信息创伤与信息疗法的学理基础展开解读以揭示仪式治疗的科学依据。认为人类大脑的功能属性决定了对其可能造成创伤的外部因素构成中,除了病毒及物理破坏力之外,不良信息也将成为导致大脑受创的重要因素;当高强度不良信息的突然输入对大脑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脉冲式撞击时,就形成信息创伤。仪式,正是强大信息流得以产生的文化场景。因而仪式治疗本质是信息疗法。鉴于不同主体对同一信息的感知(应)不同,决定了相同的仪式实践模式,对不同患者可能产生不同的信息治疗效果。
关键词:医学人类学;信息创伤;信息疗法;仪式治疗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4 - 0129 - 11
一、问题的提出
苗族信仰万类有命[1],万命有魂。在此认知框架下,苗族先民以为谷物如同人类一样也是具有灵魂的。即,视谷物为具有生命灵性的对象存在,因而形成了关于针对谷神的特定祭祀仪式,苗语称之为“辽侬”。1千百年来,苗族先民认为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六畜不旺都是谷神不保佑或“谷魂”离散所致。为了使家人渡过生活难关,事主之家往往请“巴狄熊”(bad deib xiongb)择吉日来家中设坛,摆上酒、肉、米饭,献上香蜡纸钱,祭祀谷神、请回“谷魂”。“巴狄熊”操办祭祖仪式,念诵神辞,敬请各路谷神光临,祈求谷神做主,请他们将献上的酒肉吃完,把纸钱带回去,并求他们保佑事主之家年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2]。这一文化实践的存在及其操办表明,在苗族先民关于对生命的认知中,不仅是人类或动物有灵魂,植物(如稻谷、小米、高粱)都具有灵魂。“辽侬”这一堂法事,作为对谷物生病而进行仪式治疗的实施,也是人类早期实施信息疗法的一种场景呈现。类似的习俗,在苗族之外的族群生活中也普遍存在。例如,“在摩鹿加群岛,当丁香树开花的时候,人们像对待孕妇一样对待它们,不许在它们附近吵嚷,夜晚经过时不许携带火光,任何人不许戴着帽子走近它们,在丁香树前必须脱帽致敬。这一切必须遵守,否则丁香树就会受惊,不结果实,或果实过早掉落,好像妇女怀孕期间受惊早产一样。同样,在东方,对待生长中的稻秧,也像对待生孩子的妇女一样精心照顾。在安汶岛,当稻秧开花的时候,人们说稻秧怀孕了,不许在附近放枪或做出其他闹声,恐怕稻秧受了惊扰,就要小产,只剩下草而不长谷粒”[3]。这说明,诸多民族文化认知中都意识到人类活动作为一种信息对动植物生命秩序产生影响,并尽量规避这种不利影响的发生。这也就使得作为文化实践的仪式治疗,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民族社会中都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与应用场域。
即使到了科学发达的当今社会,乡村社会的人们也通常认为一个人要遭遇不测或厄运之前,都会出现一些不吉的征兆或“异象”[4]。這些征兆往往以某种“奇怪事件”1的发生来呈现。例如,邻居家的一位小女孩在生病死亡之前,有一段时间仿佛总是听到她家房子里传来阵阵哭声,而且就在她将死的那天晚上,还清晰地告诉她的父亲:“有人来等我了,我要跟她们走了…… ”说着说着,就咽了气。对于这样的事,人们都说是有鬼来接她走。可是,用实证科学去解释却找不到合理性。其实,在乡村生活会遇到许多难以用科学解释的现象。再如,一个小瓜刚开蒂生长时,不容许人用手指去指它。如果用手去指它,它就会如同小孩夭折那样凋谢。所以,小时候父母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用手指去指刚开蒂的小瓜,因为它很脆弱,会死掉。那么,为什么用手指一下小瓜就会导致它的凋谢?这一动作对小瓜产生的伤害是什么?同理,一些小孩受惊骇而不明不白地生病,所受到的创伤又是什么?出于对这种奇特生命现象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信息创伤”与“信息治疗”[5]两个概念的分析,并在医学人类学框架下解读发生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奇象与民间仪式治疗实践。进而言之,通过田野调查中获取的个案描述与分析,对信息创伤与信息治疗的概念进行医学人类学注解,以作为理解信息对生命秩序产生扰动或修复的学理基础,为仪式治疗及其有效性提供新的理论逻辑。
二、作为信息编码存在的人类文化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类自诞生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意味着,人类对疾病展开的治疗实践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实践。因为“文化本质上属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发展”[6]。文化作为一套信息系统的存在,业已成为人类学界的共识。但这一共识的形成,却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发展的结果。在人类学早期的理论探索中,关于文化的理解有若干种,若按照克鲁伯(A.Kroeber)1958年在《文化概念》一文中的归纳,当时文化的定义多达160多种。这是因为,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和人类学大师都有对文化的一番理论。经典进化论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 - 1917)对文化的定义中指出,所谓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7]。泰勒试图从“复合论”的视角理解文化,并将文化理解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出于对经典进化论的修正与超越,新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1900 - 1975)在其《文化的科学》一书中指出:“工具×符号=文化。”[8]此时,怀特已从符号及工具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在不断趋近文化作为信息系统这一本质属性的理解。而法国社会思想家莫兰(Edgar Morin)则曾经清晰地认为:“文化作为再生系统,构成了准文化编码,亦即一种生物的遗传编码的社会学对等物。文化编码维持着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和同一性,保障着它的自我延续和不变的再生,保护它抗拒不确定性、随机事件、混乱、无序。”[9]即文化在功能上是维系秩序,确保社会系统的稳定与完整。道格拉斯·C.诺思等人认为:“人类文化是通过教育传递的共同信息(common information),不论是正式的,课堂意义上的,还是非正式的,家长或其他人教给孩子社会规范意义上的。”[10]也就是说,文化是作为一套社会共享的信息而存在的,也是“告知、训规和指导人们如何进行社会博弈的信息体系,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与延续的信息系统”[11]。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 - 1979)认为,“文化作为价值、标准和符号系统是充分解决秩序这一问题的中心因素,因为它提供了价值、可共享的关于在社会中什么是可欲求的观念(也许是像物质财富、个体自由和社会公正那样的价值)以及标准、获得这些事物(如诚实努力是通向成功之路的观念)的可接受的途径。文化也提供语言及其他对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符号系统”[12]。帕森斯也意识到文化作为信息的功能,是为社会秩序的维系提供依据与路径选择。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1920 - 1983)在对仪式与序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支配性的象征符号,通过这套支配性的象征符号将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与强烈的情感刺激紧密相连。”[13]158特纳的研究表明,文化作为一套象征符号体系以一种无形的方式,参与了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建构、维系与修复过程。
当然,对文化作为一套信息编码的理论认知,不仅是国外人类学研究的共识,也是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共识。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曾指出,文化是“某个人类社群用来整合该社群的一套特有的人为信息系统。文化具有综合利用生命信息和自然信息的功能,从而使相关社群获得有效利用无机和有机资源,谋求自身生存与稳态延续的能力”[14]。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在系统总结前人关于文化理解的基础上,也从信息角度对文化做出新的定义,认为“文化是人类遵照其相应的自组织规律对人类及其全部生活事物的各种联系,运用信息进行秩序创造并共享其意义的具有动态再生产性的编码系统”[15]。前人研究对文化作为一套信息体系存在的认知,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些已有的理论探究表明,文化具有信息的属性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实现包括生命秩序在内的各种秩序的维系、修复与重建。文化强大的“致序”功能,其实早已为各个人类群体所悉知并加以应用。仪式治疗的久远性与广泛性及其医疗实践的有效性表明,仪式实践过程所产生的强大信息流对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产生的秩序修复过程,这才是仪式治疗得以有效的学理基础。
三、医学人类学视域下的创伤与信息创伤
从广义上的创伤来看,创伤就其发生机制而言大致可分为3类。其一是物质创伤,例如,因吞食有毒有害物质而导致的病变与机体损伤;其二是能量创伤,如因生命机体过度受冷或受热而导致的病变与损伤;其三是信息创伤,如因受惊吓而导致的机体病变与功能失常。然而在医学的意义上,“创伤(trauma)是由多种机械因素引起人体组织或器官的破坏,是临床常见的导致急危重病情的原因。创伤患者局部表现为伤区疼痛、肿胀、压痛,骨折脱位时伴畸形和功能障碍,严重创伤时还可能出现致命的大出血、休克、窒息和意识障碍,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16 - 17]。医学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创伤,更多属于物质与能量创伤范畴。也就是说,医学理解的创伤通常是指因外力作用下对人的身体器官或组织产生的结构性破坏。这种伤害,可以从外形的改变或组织结构的损坏来呈现,属于物质创伤与能量创伤的范畴。例如,子弹穿过人体某个部位产生的破坏,细菌或病毒对人体器官与组织的侵蚀而产生的组织坏死等,均属于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创伤范畴。这些创伤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产生的伤害与组织破坏是可以肉眼观察到的,这类可以肉眼观察到的创伤,可称为实体创伤或物理创伤。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是肉眼观察不到的创伤,如一个小瓜被手指而最终凋谢夭折,一个人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而产生的心理防线崩溃,使得机体迅速发生器官代谢故障与衰竭的创伤,则是与物理创伤在作用机制上不同的创伤形式,本文把这类创伤称之为“信息创伤”。信息创伤的特点就是具有隐蔽性,即受创伤的状态是肉眼观察不到的,但可从随后的机体代谢反应中感知到这种伤害的不可忽视性。简而言之,基于信息感知或感应而产生的对原有生命秩序产生扰动,进而让生命秩序偏离常态的创伤就是信息创伤。这种创伤,在一些书籍或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中常称为“心理创伤”。受过心理创伤的人,容易产生精神抑郁,而“精神抑郁等消极情绪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会引起植物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18]。但“心理创伤”的解释不能理解植物生命体受信息干扰而产生的生命秩序失稳与偏离问题。因为植物的“心”是没有思考力的对象,即植物的“心”是不能作为信息处理的器官,而只有人的大脑才具有接收、加工处理并发送复杂信息的功能。因而可以认为,信息创伤的作用机制在于某个信息的突然输入对生命有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脉冲式撞击的缘故。因为“中枢神经系统主要是处理来自外部环境的资讯,并将其分类、传达‘指示’到某一部位。它的工作是综合和双向交流的,不断来回反馈”[19]12。当患者收到的信息震撼力超过其承受范围时,信息就变成了对其中枢神经系统的扰动,进而形成“信息创伤”。或许正是信息创伤的存在,医院一般都有让家属对患者保密病情真相的规定。如某某老人到医院检查出了绝病,职业规范要求医生只能将此情况悄悄告知患者的家属,并隐晦地表达老人的病情无解的事实,同时劝告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安排后事的准备。医生不能把绝症患者的病情真相告诉患者本人的原因,就是深知不好的信息对病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创伤,击溃病人的精神与心理防線,导致快速死亡。实践证明,一旦病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创,那么这个病人机体代谢功能就会迅速紊乱,进而导致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走向生命的终结。
无论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不得不承认,“人是宇宙万物进化的结果,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妙绝伦的化工厂,或者说它是目前地球上最复杂、最精密和最准确的生物机器”[19]4。而人脑是对信息加工处理,进而对人体器官发出指令以维系机体正常运作的特殊高精密装置。事实上,正是“人类在大脑进化上所取得的成功,支持了人类具有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人类对符号的使用实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符号化。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处理信息的能力,确保人类的生产、生活经验能通过文化编码的形式嵌入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以此实现知识的积累与经验的传承以及智慧的提升。可以说,人类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人脑进化、智力提升的结果”[20]。人脑的功能属性定位决定了对其可以产生创伤的外部因素构成中,除了病毒及物理破坏力之外,不良信息也将成为导致大脑受创的重要因素。这如同电器可以被高电压电流所损坏那样,“处理信息的机器——大脑”,也必将可能遭遇不良信息的干扰而受创。例如,当小孩突然看到恐怖场景(画面),或突然听到一声恐怖的叫声,往往会因此受到惊吓而生病。这种病,用西医的检测手段是不太容易检测出来的。但是,小孩会因为这样的刺激而因此茶饭不思、食欲不振,若久治不愈则可能如同一株慢慢枯萎的小草,一天一天地加重病情,最终衰竭而亡。因惊吓而生病,本质上是因中枢神经系统受创而发出紊乱指令,导致各个器官无法正常完成生理功能代谢所致。人体中的所有器官的正常工作,都需要在中枢神经系统正常指令派发的前提下完成。在发病初期,即中枢神经系统受创还没有导致整个身体器官功能紊乱的“躯体化”症状出现之前,用药物治疗往往是无效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信息创伤导致的病可用信息疗治救治,并且效果奇特,这一实践,在民间有着广泛的认同基础。苗族民间社会中的巫医治疗,就是苗族传统治病方法中专治信息创伤的一种文化实践。对于因受惊骇而致病,苗族民间巫医的判定是“落魂”(丢魂)所致,针对性的信息治疗安排就喊魂、赎魂、招魂或抢魂。这套仪式操办时所形成的强大信息流,可以对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信息修复,进而达到治疗的效果。需要强调的是,对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信息创伤的治疗一定要及时。这样的经验,在世界范围内许多民族的文化习俗中都有所体现,例如,“很多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人种都认为患苏斯托(susto)的人是受到了惊吓而丢了魂,这些人一般都会食欲不振、浑身乏力,他们情绪低落,焦灼不安,心情抑郁,离群索居,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要想病好就必须让他们的灵魂归位”[21]。若拖久不治,因中枢神经系统受创而形成的器官代谢功能紊乱已经严重地躯体化呈现,那时采用信息治疗的手段效果就不佳了。因此,因惊吓而生的病一定要及时治好,否则易拖成大病或不治之病。原因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受信息创伤,就会发送错误指令让器官工作发生紊乱,引起严重后果。若是导致内分泌系统工作发生紊乱,不能迅速治愈则可能导致精神病、糖尿病等。朋友的儿子就是因受惊吓久未治愈而最终演化成了糖尿病,最后因没钱治疗而亡。信息创伤的根源,在于人们受到不良信息(如流言蜚语、诽谤、生活压力等)的刺激。在信息社会,各类不良信息对中枢神经系统形成的无影伤害,可衍生出一些意料不到的现代性疑难杂症。
四、信息可被不同主体所感知(应),并可形成创伤记忆
以下3例发生在乡村社会中的神奇事件,以个案的形式呈现给读者。
个案1:魂归故里唤开门
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邻居的一位叫档·佧的家族长辈死了。档·佧生前养育三男二女,小儿子名叫金章,只比我大1岁,按照辈分我应该称他为小叔,但在小时候我俩是最好的玩伴,彼此间只称呼名字,没有辈分之称的俗套。在档·佧死前一个月,在他家里发生一件怪事:2条硕大的乌梢蛇爬到他家正屋的房梁上“缠绕结对”。这情景被来他家玩的村里人发现并打死丢到小河边。然而,没过一周档·佧就突然生病了,起初病症表现为痛肚子,随后痛得受不了在地上打滚,当天下午档·佧就被担架抬去县医院住院,金章的两个哥哥也随同母亲到医院,金章和他的姐姐老梅、妹妹东治守家。因晚上害怕,金章叫我陪他守家。大概凌晨4点左右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老梅,开门!”声音有点急促,还拌有推门的响声。结果,老梅去开门,什么也没有。当时觉得有点奇怪,百思不得其解。但没料到的是,天大亮就有人带信回来说档·佧死了,死亡时间正是凌晨4点半。九点左右,檔·佧的尸体被抬了回来。
借用信息感应的解释,一定是死者临死前想到回家。苗族村寨里的多数老人,都害怕死在医院,因为在苗族的丧葬习俗中,这样的死亡属于不吉利。所以,档·佧老人能以“魂归故里”的方式表达他死亡前的意愿,并给家里的孩子提前报信以便做好迎接的准备。
个案2:牛群惊骇不敢前行
金峰·佧在8岁时,她的母亲因患心脏病死在医院。他的母亲叫群川·颧,生前是一位长得标致且心灵手巧的女人,做的绣花鞋是村里最有名的。由于死在医院,而且死时才32岁,英年早逝给村里弥漫着阴森的气氛。葬礼操办完毕后的第三天早上,村里的牛群在经过她家左侧的村道时,突然不敢向前走,甚至还急忙倒退,仿佛是被什么吓住而不敢向前迈进一样。赶牛的人深感怪异,甚至有一丝恐惧,不知如何是好。幸好村里一位叫龙昌贵的老木匠懂些驱邪的法术,正好也路过那里,见此情状便立即施法并破口大骂,扬着锄头柄象征性地击打路基几下后,牛群才敢往前走,但仍小心翼翼。经此事后,晚上路过那里时人们都有心理发怵的感觉,大约3年后这种感觉才慢慢消失。
这一怪异的场景亲眼所见。这一案例表明,同一信息可被不同主体所感知。换言之,对于人类看不见或听不见的场景信息,其他动物或许可以听见或看见。因此,在一些自然灾难(如地震)发生之前,往往会出现“动物搬家”等异象,这其实是如同本案例中牛群表现出来的怪异行为那样,是动物感知到人类无法感知的恐怖信息而作出本能躲避的行为表达。
个案3:吃漆虫中毒形成创伤记忆
2021年7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教授石德富先生来到凯里做中部方言苗语调查,其间与他交流有关信息创伤与信息治疗的学术构想时,他告诉我一个在他小时候看到的,发生在他家乡湾水镇鱼良村的“吃漆虫中毒形成创伤记忆”的个案。
鱼良村有一位叫SKW的村民在年轻时特别胆大,可以说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人们说什么不能做他就敢去做;说什么不能吃他就敢去吃。他听老家人家说漆树虫(以下简称“漆虫”)不能吃,但他就去找漆虫吃。他劈开一株枯干了的老漆树,把里面的“漆虫”捉出来烧着吃。结果很快就中漆毒而全身肿胀。若仅是身体的某个部位感染漆毒而浮肿,通常可用生(没有煮过的)酸汤或韭菜叶捣烂成汁擦洗患处,几天便可让肿胀症状消退。然而,SKW的这次中毒不是一般的皮外中毒,而是由体内中毒向外扩散。病情非常严重,日常的治疗方式已经无济于事。最后,村里老人想到公鸡吃百虫,就用公鸡的骨肉捣烂拌韭菜敷裹其全身,结果有奇效,花了半年的时间治好了他的病。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只要在SKW面前提及“漆”字,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他的全身就会重新诱发浮肿。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才完全消除。
这个例子表明,这次“吃漆虫中毒事件”已经在患者SKW的躯体里面形成创伤记忆。这种滞留在机体里面的创伤记忆一旦受到激发又引发机体的病变反应。
发生在乡村生活场景中类似的个案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这些听着有点不可思议的故事,不是杜撰,而是发生在乡村社会生活场景中的真实事件。表明了信息对人或动物的作用是存在的。换言之,动物可以感知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信息。1当信息以某种悲伤的事件抑或恐怖的事件呈现时,那么信息就可能对人或动物产生恐骇效应,进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应都属于信息创伤的具象表达。
五、以巫治病:信息治疗的实践应用
以巫治病,自巫术产生以来就一直在实践着。事实上,在巫术的社会功能之中,医疗为其大宗[22]。何休在注解《公羊传》中也指出:“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也。”[23]尽管巫作为仪式具有治疗功能,但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常侧重于从人类生活及社会秩序转换的角度来展开。例如,特纳(Victor Turner,1920 - 1983)在对仪式的分析中认为,仪式在结构上分为阀限、共融、分离等阶段,他将仪式的功能定位于对场景中的主体社会角色的转换,或对一种社会秩序过渡的接纳。特纳的研究认为,仪式治疗所治疗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群体,所以仪式治疗的功效在于提升社会团结、解除人际关系的紧张,为仪式中的实践群体“提供了一套关于疾病和死亡的解释”[13]158。早期许多研究就是跟从这一解释,将仪式治疗患者的病因归因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仪式治疗重塑人与人、人与家庭甚至是与社会的关系,具有有效性[24]53 - 58。若从医学人类学的意义上进行界定,仪式治疗是持续强烈的“信息流”[25]生产的过程。在治疗时,它以让患者看到、听到的方式作用于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促进神经系统的结构修复,最终复原神经系统的秩序结构,进而恢复中枢神经系统对人体脏器的正常指令派发,从而对生命秩序的正常维系提供强大的中枢调控。
在疾病的诊断方面,西医关注的是生物身体,而非西方医学除了诊断病理本身,还会在“社会身体”方面寻找病因,比如家庭或社会成员,甚至将病因归咎于超自然力量的愤怒,故而在家庭或者社区范围内举办驱邪仪式,或者在公开的文化仪式中安排治疗环节(比如中国的迎神赛会),以图恢复正常的社会关系或平息神灵的怨怒[26]。因此,当病者的致病缘由无法通过现代西医的医疗设备探知时,苗族民间社会中的乡民就会自然地想到巫医。因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巫医是同源同宗。正如李今庸对巫医关系进行界定时所指出那样:“巫之为人治病,由来已久,……医在战国以前,被操之于巫觋之手,巫、医不分,巫就是医,医就是巫,故‘医’字从‘巫’而作‘毉’,又恒以巫医为称。”[27]51加上在仪式场景中,通过“巫师向鬼神祝祷,并对病人施以催眠、暗示和激发等手段,使病从相信自己的病是由特定的鬼神作祟,在巫师象征性地祈求某神的原谅或驱使某鬼神遁逃的过程中,病人的内在防御机能例被充分地诱发出来,这就是《素问》所谓‘移精变气’,与此同时,因生病而产生的忧郁、恐惧心理也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排解。对于心理障碍性疾病和一些小病症,巫术疗法往往比较灵验”[27]53。正因如此,巫醫在民间社会中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的存在基础如此深厚自有其复杂的历史根源,因而不宜粗暴地认为那是“迷信”。一旦承认人类的生命构成是灵魂与肉体的合一,那么,巫医实践本质上就是对灵魂的呵护与救治。巫作为一套复杂的仪式结构,在展开对生命灵魂救治的实践中实则是以一种强大而持续的信息流作用于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在场人的中枢神经,让每一位在场者有一种震撼感。这种在场者所感知的震撼感,本质上是信息流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作用的结果。从生命科学的层面理解,物质、能量与信息精密配置与相互作用,是生命诞生并得以正常维系的前提。这就意味着构成生命的物质结构破坏,就会导致生命秩序出现偏离甚至秩序的崩溃(死亡)。而信息在参与生命体正常运转的过程中,是以各种指令派发的形式来调节物质、能量的消耗、流动与储存。换言之,以非正常指令派发的不良信息加载,则可能导致生命有机体运作的紊乱。这就容易理解,信息创伤导致机体生病的科学原理。对于因信息创伤而生的病,则需要通过信息治疗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也是一种“对症下药”,而不是所谓的“迷信”。通过物质补给与能量输入都不能见效的情况下,以仪式的方式而展开的巫医治疗就派上用场,并且这种治疗实践的展开不仅仅是对于人,也可用于对动植物的生命秩序的修复与救治,通常都能产生奇特的疗效。
文学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古歌的唱颂也具有奇特的疗效,并用于实际的治疗实践中。因为古歌的吟唱也是在特定的仪式场景中完成的,同样可以产生强大的信息流。同理,现代医院中兴起“音乐治疗”也属于仪式治疗或信息疗法的范畴。“音乐治疗是一个系统的干预过程,以心理治疗、医疗的理论方法为基础,运用音乐特有的生理、心理效应,在音乐治疗师引导下通过各种音乐行为,经历音乐体验达到清除心理障碍,恢复或增进身体健康的目的”[28]。此外,还有“艺术治疗”[29]等。如果将仪式治疗理解为“治疗师通过与咨询者建立咨询关系,运用音乐、舞蹈、戏剧、冥想、祈祷、魔咒、符文等仪式和符号,解除咨询者生理或心理痛苦,或社会适应不良的过程”[24]53 - 58。那么,无论是音乐治疗抑或是艺术治疗,本质上都是信息疗法或仪式治疗的具象形式。以巫治病之所以可以产生奇特的疗效,根源于这一实践仪式能产生强大而持续的信息流作用于患者,进而在对场人有震撼的同时也对患者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积极的修复作用。
在人类社会里,应该说,信息与物质、能量一样有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所有的知识,还包括通过五官感觉到的一切。例如,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报纸上的新闻、市场行情、天气预报以至一幅画、一张照片,都属于信息的范畴[30]。自人类产生以来,就一直生活在信息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信息创伤常常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并不断地对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作用。人类在实践中已经发现这种创伤,并通过仪式(信息)治疗以实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秩序修复或救治。正因为信息创伤的存在,出于对患者的关爱而不会将其病危的消息告诉他本人;同理,作为对亲人的关爱,人们也往往不会把不好的消息告诉家人。即使在外生活得不那么理想,也不会告诉家人说自己在外的真实情况。正是信息创伤的存在,极度恐怖的消息是不容许随意传播,因为这类信息的传播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可能会导致个人生命秩序的迅速紊乱,甚至传导社会秩序的崩溃失控。
六、余论
文化具有信息的属性,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参与包括生命秩序在内的各种秩序的维系、修复与重建。因此,从医学人类学视域来理解,小瓜被人手指就可能凋枯的原因在于,人有意识发出的信息对脆弱的小瓜的生命秩序产生了扰动,导致它代谢紊乱所致。同理,受惊骇致病的小孩常常可通过操办“祛骇仪式”而康复,则说明“在仪式行为语境中,整个社会的兴奋情绪和直接的生理刺激,如音乐、歌唱、舞蹈、美酒、香烛以及各种古怪的服装样式和仪式象征符号一道”[13]29汇聚成强大的信息流,仪式治疗通过产生强大而持续的信息流,可能对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创伤的修复是有效的。此外,本个案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还表明以下事实的存在。
首先,人在遭遇厄运或不幸之前总会出现一些征兆头或“异象”。对于这类异象的民间理解,则自有民间的理论概括。然而,民间的解释往往与科学理解性的解释不兼容。在科学的强势压制下,民间的解读成了“迷信”解读。
其次,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具有感知信息并做出反应的自发机制。只不过,因观察的疏漏让一些有趣的现象没有引起科学研究的重视,加上现代人对科学的过度相信,从而完全否定了民间的文化解释合理性,因而民间的文化解释总是处于与主流的科学解释不相容的框架之中。
其三,不同主体对同一信息的感知强度是有差异的。因此,小孩可以感知成人感知不到的信息;同理,动物也能感知人类所不能感知的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应急反应。
其四,当信息创伤在大脑形成记忆后一旦受到相关的信息激发,那么,机体曾经遭遇的创伤症状可能会自发地再次显现。
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创伤与信息治疗的提出,是试图从医学人类学的学理框架理解苗族民间医疗(治)实践,尤其是“以巫治病”的文化实践逻辑,并非出于标新立异。尽管学术界已有“仪式治疗”“心理治疗”等理论解读模式,并且在内涵上与本文提出的“信息治疗”与仪式治疗大致相同,或者说“信息治疗”是仪式治疗的“另类理解”;但信息创伤与心理创伤尽管有内涵相叠的成分,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在医学人类学语境下使用信息创伤的概念,能解释的生命现象范围更为广泛,可以解读植物,动物与人类生命秩序受信息扰动的问题。如果人类学与信息科学的研究可以联姻的话,那么,信息创伤在未来将是可以量化检测的。相对而言,心理创伤所能解读的现象仅限于人类自身,即人类心理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信息创伤、信息治疗的提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一组概念不仅可以解读乡村社会中的一些奇特的生命异象,还能将原以为是迷信的“仪式治疗”纳入信息科学的研究视野,这为信息科学与人类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1] 麻勇恒.敬畏:苗族神判中的生命伦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216.
[2] 吴琳.祭农神[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9:5.
[3] J.G.弗雷泽.金枝(上册)[M].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97.
[4] 王 倩.感生、异相与异象:“天命”神话建构王权叙事的路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1):45 - 54.
[5] 梁昌林,兰小筠.信息治疗研究综述[J].医学信息杂志,2017(2):48 - 51.
[6] 韩民青.论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J].云南社会科学,2011(3):86.
[7] 愛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大学出版社,2005:1.
[8] 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M].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40.
[9] 莫兰.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9.
[10]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M].机行,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35 - 36.
[11]罗康隆.论文化与其生态系统的制衡关系[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 (1):18 - 25.
[12]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斯考特·麦克拉肯,迈尔斯·奥格伯恩格瑞葛·斯密斯.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7.
[13]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4]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9.
[15]张小军.人类学研究的“文化范式”——“波粒二象性”视野中的文化与社会[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6 - 67.
[16]李兵,乔鹏,武宏杰.创伤性颅脑损伤术后凝血功能障碍与疾病严重程度和肝功能的关系[J].创伤外科杂志,2020(6):47 - 450.
[17]张璐平,刘励军,朱涛,等.严重创伤患者发生纤溶亢进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J].中华创伤杂志,2020(8):720 - 725.
[18]罗烈文.小健康 大智慧[M].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244.
[19]廖晓华,田洪均,刘丽.健康的真相——人体的危机与出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0]麻勇恒.作为社会性遗传信息系统的进化机制——基于“文化能量说”的启示[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68 - 72.
[21]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家怎么看[M].禾木,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4.
[22]惠冬.宋代巫医治理的区域特征及其生存实态[J].中华文化研究,2020(6):43 - 50.
[23]詹鄞鑫.心灵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4.
[24]周小昱,余建华.仪式治疗的国外研究述评[J].医学与哲学,2019(4)53 - 58.
[25]李 娜,娄永强.从条件句悖论看信息流理论的哲学基础[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74 - 80.
[26]范长风.安多藏区曼巴扎仓的医学民族志[J].民俗研究,2019(1):136 - 143.
[27]李今庸.古医书研究[M].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2003.
[28]朱婷,何凌.音乐治疗对身体机理反应及自动疗效评估[J].科技视界,2020(36):63 - 66.
[29]李世武.巫医的艺术治疗:幻觉问题[J].广西民族研究,2015(5):59 - 65.
[30]冯端,冯少彤.溯源探幽:熵的世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94.
[责任编辑:吴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