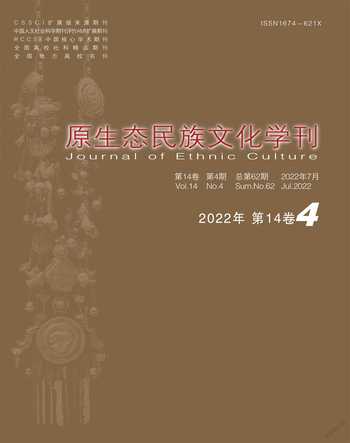暴君·神祇·祖先
2022-07-15杨文辉
杨文辉
摘 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不可避免地受到史籍书写者的立场与情感倾向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因而不同时代、不同取向会导致对同一人物的褒贬大相径庭。大义宁国国王杨干贞的形象,呈现出暴君、神祇(本主)与英雄祖先的不同面相,究其原因,暴君的定型最初是由于相关材料的书写有着大理国段氏集团强烈的意识形态建构的诉求,历经后世对段氏政权怀着“故国之思”的知识精英的书写后逐渐尘埃落定,而被树为神祇(本主)则源于杨氏起兵之地的下属民众及桑梓百姓的集体记忆,英雄祖先的形象出自自称杨干贞后裔的杨氏族人的书写与表述。后二者中都隐含着基于现实社会情境的利益博弈的考量。但不同的形象建构处于“各自表述”的状态,反映出精英的文字书写与民众精神世界诉求“并行不悖”的文化生态。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大理国;杨干贞;民间传说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4 - 0098 - 11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人(包括群体与个体)的行为构成了历史事实与历史材料的基本内容。对相关群体与个体的行为、思想的研究则是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从对历史活动中个体的关注而言,由于记录材料的限制等原因,能进入史家视野的个体注定是少数,即便是曾经在史料中留下痕迹的个体,因后世史家所处环境的制约与学术旨趣的差异,也会经历沉浮隐晦。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反映的是史家的心境与价值观,也正是从这一意义而言,每一代人都在重新解读历史,解读的过程也就是重塑的过程。历史人类学所主张的学术理念之一“过去如何在现在被创造出来”[1],或可简称为“现在如何造成过去”,便是对此种情形的精当表述。近年来个人生命史的讨论方兴未艾,与历史人类学这种学术理念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关联。简言之,对历史上特定个体的认知与评价,往往取决于史家(评论者)所处现实情境的需要与制约,而不一定完全合乎历史人物的实际情形。以笔者有限的史学素养与认知而言,对于史料记载较为有限的历史人物,似乎更容易发生评价的分歧与争执,不同的研究者依据相同的文字记录,可以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显然,研究者的观念与立场差异决定了这种分歧的发生。
本文试以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上一个不太起眼的历史人物杨干贞1为个案,讨论其形象与评价的多重面相,阐述差距甚大的几种认知定位产生的根源,简要分析此种社会事实背后蕴含的实质或“本相”,揭示文化资源在区域利益博弈格局中的地位与功能。
二、暴君是如何炼成的:地方史籍记录中的杨干贞形象
杨干贞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因为其建立的大义宁国前后存在时间不足9年,就被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取代,从此云贵高原进入一个相对承平发展的历史时期,前后延续300余年的大理国,完成并稳定了西南边疆的局部统一,为元代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就是说,杨干贞恰好是云贵高原从南诏国到大理国之间动荡局面的重要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处于由“乱”到“治”的历史关节点的政治人物,作为乱世终结者段思平的政治对手,谓之云南高原的乱世枭雄,可谓是恰如其分的。
关于杨干贞,治南诏大理史的学者专门论及者不多,在地方史、民族史相关著述中述及时也往往是一笔带过,一来因为杨干贞和此前的郑隆亶、赵善政一样,只是南诏国和大理国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二来更主要的是,其在位时间甚短,相关记载极少,从目前可见的材料,基本可以断定出自当时的文献基本缺失,后世研究者所能见到的记载均产生于元代及以后。
在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中,杨干贞的定位是简单而清晰的:乱世中以军队为依托崛起,执掌权柄而不能长治久安,又被后来者推翻;施政苛暴,是一个“暴君”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形象定位一直延续、影响到了今天的主流表述。如在《白族简史》中有两处提到杨干贞。
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权臣剑川节度使杨干贞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杀死第三王郑隆亶,灭了“大长和国”,扶持清平官赵善政,建立了“大天兴国”。十月后,杨干贞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改称“大义宁国”。杨氏统治云南时期,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和压榨,史称其“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广大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这时,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乘时而起,联合了奴隶、农民的起義队伍和各部落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大义宁国”政权,摧毁了奴隶占有制,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制政权。
……段思平乘时而起,他联合了广大人民的起义力量,推翻了杨氏“大义宁”政权。……当“杨氏政乱”,他图谋在大理一带进行起义活动的时候,遭到杨干贞的缉拿,得到牧民和农民的掩护。……于后晋天福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公元937年2月4日)举行起义,破下关,执杨干贞,灭了“大义宁”,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封建制政权[2]2。
作为现代研究的有着官方背景的著作之一,《白族简史》也具备同类成果同样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各界民众中具有超越一般学术著作的影响力,《白族简史》采纳了后世文献中的“贪虐无道,中外咸怨”1这种说法,这样的定性也强化了杨干贞“无道暴君”的现代形象。而以社会发展史的阶段论将大理国定位为“先进”的封建制,使得杨氏政权的被推翻具备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并在表述上将反对力量称为“奴隶、农民的起义队伍”,是极为正面的肯定,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中,“起义”一直具有足够的正义性,由此,杨氏政权在并无更多实证材料支撑的情况下被定性为“反动”,也就具有了不须多费唇舌的“正当性”。但这样一种仅仅依据出于后世的寥寥无几的文献作出的定性表述,却又难以避免地落入了成王败寇的窠臼。
但细检史料,发现杨干贞“暴君”形象的定位,所有的文献依据均源于《滇载记》《南诏野史》等几种地方史籍中大体相同的简要记述,即被称为“白古通”系的地方史料。2这些史料中的表述,又以《南诏野史》的表述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清代胡蔚增订的《南诏野史》,一是文字上较为详细;二是此后的史籍如《滇云历年传》等无论从详细程度还是史实记载方面均未超出胡本《南诏野史》的范围。因《南诏野史》有几种不同版本传世,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将几种本子的记载都引述如下。
(倪本)《南诏野史》大义宁国条说:
杨干贞,唐明宗天成四年篡赵氏自立,国号大义宁,改元先圣,又改大明,伪号肃恭皇帝。干贞和村人,母名弥灵,有美色,封民宣武王私之,有孕。后适渔人杨氏,生干真。父捕鱼,真在船头,见水中有人龙衣冠冕凤鸟白光之像,呼父视之,见是儿影,大喜。后遂灭赵、郑而自立。贪虐聚怨,通海节度段思平攻之,干真兄弟五人拒之,不克,真出奔,国亡。
(胡本)《南诏野史》关于杨干贞的记载:
杨干贞于后唐明宗己丑天成四年夺大天兴国赵善政之位,改国号曰大义宁国,建元兴圣,又改元大明。干贞萂村人。母名弥录,有美色,蒙隆舜私焉。有孕,适渔人杨氏,生干贞,后又生诏。其父捕鱼,贞立船头,见水中有人龙衣冠冕,左右有凤鸟,白光拥护,乃呼其父视之。父见是贞之影,大奇之。长仕郑氏,官至东川节度使。至是夺善政位而自立。贞在位,贪暴特甚,中外咸怨。后晋高祖丁酉天复二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讨之。贞遣弟杨诏等五人出拒。诏兵败,干贞出奔。思平遂得位,寻赦其罪,废为僧。计贞在位八年。
(胡本)《南诏野史》大天兴国条说:
明宗己丑天成四年,善政待干贞,恩礼浸衰,凡干贞所有请乞,辄不许。干贞恃功怨望,遂赂结诸臣,废善政而自立。善政在位仅十月。
(王本)《南诏野史》“肃恭皇帝杨干真”说:
杨干贞,唐明宗天成四年篡赵氏自立,国号大义宁,改元光圣,伪号肃恭皇帝。干贞和村人,母名弥录,有美色,封民宣武王私之,有孕。后适渔人杨氏,生干真。父捕鱼,干贞在船头,见水中有人龙兖冕旒,彩凤白光绕之。呼父视之,见是儿影,大喜。后遂灭赵善政而自立。长兴二年辛卯,改元大明,干真贪虐,中外咸怨。通海节度段思平讨之,干真命弟五人拒之,不克,真出奔义督,在位八年,国亡[3]。
细读上引史料,不难发现,杨干贞形象的定位主要源于以下这几句被后来的地方史籍广为征引的记录:
“灭赵、郑而自立,贪虐聚怨。”(倪本)
“干真贪虐,中外咸怨。”(王本)
“贞在位,贪暴特甚,中外咸怨。”(胡本)
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有关杨干贞治国无方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字表述,也是构成其暴君形象的主要文字依据。
此外,在明清时期成书的几种史籍中也都对杨干贞及其建立的大义宁国有简略记载。
《南诏源流纪要》载:“(郑)仁旻继袭,为权臣剑川节度杨干贞所杀。立侍中赵善政,国号兴源,甫十月,干贞又夺之而代立,国号义宁。晋天福间,段思平以通海节度讨杨干贞,废为僧。”[4]
《滇载记》载:“杨氏名干真,既夺赵氏而有蒙国,改国号曰大义宁,改元曰尊圣。贪虐无道,中外咸怨。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兴师问罪,干真不能御,走死。杨氏立仅二年。”[5]
《滇考》载:“杨干贞,和村人,本渔家,母弥录有殊色,蒙隆舜私之,而生干贞。……杨干贞既弑隆亶,恐下不服,乃推善政立之,使尽诛郑氏子孙。……仅十月,干贞又夺之而自立,改国号大义宁,改元光圣,寻又改大明。在位贪虐,中外咸怨,不二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讨之,干贞不能御,出走永昌,自缢死。”[6]
《滇云历年传》载:“(天成)四年,杨干贞自立,改国号曰大义宁,改元光圣,又改兴圣。长兴元年,杨干贞改元大明。五代晋高祖天福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讨杨干贞。干贞败走永昌,自缢死。”[7]
从上引史料可见,《滇载记》和《滇考》对杨干贞的评价有着较强的立场倾向,即被广为征引的“贪虐无道,中外咸怨”,与诸本《南诏野史》的表述如出一辙。而《南诏源流纪要》与相对成书较晚的《滇云历年传》则没有类似的语句,用语较为平实,更近于客观叙述史事的书写。这种情况在成书相对较早的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体现得同样明显,从李京的记录中看不出多少有价值判断倾向的褒贬。
善政立,国号兴元,改元应天。历二年,剑川节度杨干真杀之。
干真国号义宁。改元曰光圣,曰皇兴,曰大明,曰鼎新,曰建国。凡九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之,时晋天福二年也[8]。
虽然记录极为简略,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得以推断,在相对时代较早的元代,对杨干贞的评价并未像后来一样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这种倾向,在出自云南本土文人杨士云笔下的《郡大记》中也有同样的体现。
天复二年,南诏清平官郑买嗣夺蒙氏而灭之,僭号大长和国。
明宗天成元年,东川节度使杨干贞弑郑隆,立侍中赵善政。
三年,赵善政僭号大天兴国。干贞废之,自立,僭号大义宁国。
后晋天福元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讨杨干贞。干贞走死。
二年,段思平自立,僭号大理国,居羊苴咩城[9]。
不难发现,在成书于明代嘉靖初年的杨士云《郡大记》中,将郑、赵、杨、段的更替均称为“僭号”,从4个政权更替的表述来看,作者显然亦并不认为郑氏、赵氏、段氏比杨氏有着更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杨士云眼中,每一姓取代前朝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改朝换代而已,只是作为地方政权,相關国号在身为大明王朝子民的杨士云看来自然是“僭号”了。
从文献源流而言,《南诏野史》成书已是明代万历(1573-1620年)年间,方国瑜先生考订倪辂成书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或稍后[10],1距杨干贞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650多年。胡蔚增订刻本则已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尽管《南诏野史》有关南诏、大理世系更替及年号等的记载被公认是可信的,但在有关杨干贞“暴君”形象的书写上,却实在难以发现《白古通》系史籍之外的材料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此前就有。成书时间早于《南诏野史》的几种史籍,并无特别的记载对其施政举措及个人形象予以评价。
因为《南诏野史》的成书年代较晚,讨论就势必涉及一个其书材料来源的问题,方国瑜先生曾要言不烦地指出包括《南诏野史》在内的云南地方史籍的源流。
云南地方史之书,大理段氏时,编成《白古通纪》,出自所谓释儒之手,略纪统治家族世系、名号、年代,杂以神话传说。元以来已有转为汉文之本,且参录史籍记载。各家依之,编录成书,而取舍不同。明中叶以来,有张云汉、蒋彬、顾应祥、倪辂诸人,各有所得,亦各有别载而成书。倪辂集为《南诏野史》,取材较备,多有传抄之本。抄者又作删润、增补,先后有阮元声、胡蔚、王崧诸人锓板,尤以胡蔚刻本最通行,影响亦大[10]383。
方国瑜先生的这一观点,后来经侯冲先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在《白族心史》一书中有详尽、细致的讨论[11]。作为云南地方史籍之源的《白古通记》,后虽散佚,其影响却极为深远。经王叔武先生辑佚,部分文字重新成为可供研究者讨论的材料。如:(郑隆亶)“为其臣杨干贞所弑”。又说:“杨干贞杀郑隆亶,而推其党赵善政立之,国号大天兴。仅十月,杨干贞自取之,国号大义宁。于是段思平起兵讨平之。赵氏、杨氏得国共九年。” [12]
从王叔武先生的辑佚文字看,《白古通记》中对杨干贞的记载也并没有称其“贪虐聚怨,中外咸怨”之类的评价。但其书写的笔法却可提示一点讨论展开的线索。可以看到,在被学界公认为地方史籍之源的《白古通记》中,虽然尚无“贪虐聚怨”等极其强烈的评判用语,但笔法当中已经明显体现了对杨氏极为不利的道德评判。如述及杨杀郑隆亶时用“弑”,段氏起兵反杨氏则用“讨平之”,其视杨氏为逆臣贼子、暴君的立场已经非常明显。历经《南诏野史》等史籍的渲染,到了清代主要依据《白古通记》成书的《僰古通纪浅述》中,关于杨干贞的记载便有如下表述。
杨干真乃和村人,……后遂灭郑、赵而自立。后唐天成四年六月篡赵,改元光圣。辛卯,改大明。干真为帝贪虐,中外咸怨,通海节度段思平攻之。干真命弟五人拒之,不克。干真出奔义督。在位八年而国亡[13]。
关于《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由于原书已佚,目前亦存在不同看法。方国瑜先生说:“《白古通》之著作年代,从其内容观之,称引《白古通》者,止于大理段氏之灭亡。”[10]109则其成书年代最早亦当在元初。王叔武先生据万历《云南通志·羁縻志》所引“世祖斩高祥于五华楼下”一语推断“是书之成不能早于元初”,与方国瑜先生所见一致[12]60。侯冲先生则从《白古通记》被征引情况及成书背景的详细考说,认为《白古通记》为洪武至永乐年间著述,“成书时间为洪武十七年至永乐十四年(1384 - 1416年)”[11]41。且此书是为了“强调夷夏之辨,重在建立道统、重气节和‘虑身没而心不见知于后世’”的“白族心史”,是明代大理段氏遗民抒发“故国之思”的产物,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白古通记》不能算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书,其中不少内容都是明初才编撰出来的,不能视为信史”[11]86。尽管对《白古通记》具体的成书年代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其作为《南诏野史》编纂的主要依据与材料来源这一点上,诸家之说是高度一致的。
显然,即使是现存的史料中,如果细细加以梳理的话,对杨干贞的评价亦有2种倾向:一是“白古通”系以诸本《南诏野史》为代表的史料,通过书写将其定位为一个弑君逆臣、一个贪虐聚怨的暴君;二是李京《云南志略》为代表的史料,将其作为乱世中的过渡人物看待,与郑氏、赵氏、段氏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后一种看法显然在对杨干贞的研究与讨论中并不占主流,这可能也是前文所引像《白族简史》这样的论著采信前一种观点的原因。于是,经由与后世历史文献的描述与现代知识人的重新建构,杨干贞的“暴君”形象逐渐得以定型并成为主导公众认知的表述。
三、田野材料的表述:圣明天子及英雄祖先
与文献记录及被现代研究者多数采信的“暴君”形象相对立的是,杨干贞在民间传说及白族民俗的表述中却是另外一种形象,他不仅不是暴君,而且是一个有着神异行迹的英雄,是年年月月有香火供奉的本主;对洱海区域的部分杨姓居民而言,还是祖源记忆中的荣耀祖先。这种形象与上文所述的“暴君”,可谓有霄壤之别。
在流传于白族民间的杨干贞传说中,以下这则《杨干贞本主》较有代表性。
洱源县城南罗坪山麓有一座本主庙,庙内供奉着大义宁国皇帝杨干贞,封号“肃恭景帝”,旁为干贞妻,供台上还供奉着杨干贞的弟弟杨诏及夫人。每年正月十八日是本主的诞辰,神充、大埂、下营、河埂、马家营等五大村的男女老幼都要敲锣打鼓到本主庙将木雕像抬到平坝,搭棚供奉,并表演歌舞,打霸王鞭、唱戏,让本主老爷与全村老少共享欢乐。
传说南诏国时,宾川萂村一位姓杨的渔夫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杨干贞,老二叫杨诏。弟兄两个长得很结实,经常跟父亲出海打鱼。有一次,杨干贞随父到洱海中捕鱼,他站在船头,见水中有一个人,龙衣冠冕,左右有凤鸟白光拥护。干贞见了十分惊奇,急呼父亲到船头观看,他父亲到船头一看,水中的人影不是别人,正是杨干贞的像,心中暗暗高兴,后来杨干贞果真当了大义宁国的皇帝。
那时候,南诏的军事力量很强。兵曹长正在南诏境内的城邑中挑选能领兵作战的将领。选拔十分严格,要参加马军和步兵的比赛。由于杨干贞出身贫寒,经常出海捕鱼,是游泳的好手,平时又经常上山打猎、砍柴,练就一身好本领,除善于骑马射箭,急流中游泳捕鱼外,逢年过节还经常在村中比赛击剑刺杀,这为后来的带兵打仗奠定了基础。那時恰遇南诏兵曹长在羊苴咩城集中乡兵选拔带兵苴子,杨干贞在各项比赛上武艺高强,才貌惊人,获得第一名,被选为带兵苴子。兵曹长亲自给杨干贞戴上朱盔,身着象皮甲胄,持铜盾,显得很英武。他严格训练军队,苦练作战本领,每次率兵出征,他总是冲锋在前,拼死博斗,胜利回阵。杨干贞经过多次考验立了功受了奖,被提为“负排官”,专门护卫南诏王及大军将的安全,过了几年,杨干贞又被南诏王提拔为兵曹长。在历次的战役中,杨干贞战功显赫,又被南诏王任命为大军将。后唐天成三年(公元928年),杨干贞被任命为剑川节度使,手中握有重兵。他看到大长和国郑隆亶年仅十二岁,治国无方,沉醉于腐朽的宫廷生活,便起兵拥戴宁北(今洱源茈碧)清平官赵善政为国王,改号大天兴国。到天成四年(公元929年),杨干贞又将赵善政赶下台,自己当了骠信(白语:君王之意),改国号大义宁国。
那时节,神充、大埂、下营、河埂、马家营五村的牛羊牲畜,受到罗坪山下来的野兽伤害,但谁也没有制服野兽的办法。有一天晚上,五大村乡绅耆民梦见大义宁国皇帝杨干贞及弟杨诏指挥大队兵马,张弓搭箭在山坡上追逐下山食羊的野兽,使村里的牲畜得到保护。第二天,大家到田野干活,人人都说做的梦相同,只有杨干贞兄弟能带兵马降伏野兽,于是五大村人合力建一座本主庙,雕了杨干贞及夫人和他的弟弟杨诏及夫人的像。从此,杨干贞成了五村共同的本主神,永被供奉。(流传地区:洱源,搜集地点:洱源茈碧,搜集时间:1984年,搜集:田怀清)[14]
此外,在杨干贞的故里,即位居洱海东岸大理市海东镇的萂村,每年正月春节期间都要接本主杨干贞,也有村民习惯称之为“接天子”,其隆重程度,与其他白族村庄佛节时“恭迎圣驾”时的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毗邻的大理市挖色镇的沙漠庙,杨干贞也是高居神坛的本主神之一。关于洱海东岸的杨干贞信仰及其传说,王富先生曾做过整理。
大义宁国肃恭皇帝杨干贞,白族(公元929-937年在位),其父杨和丰,为南诏将,原籍萂村人。因群臣内讧,其父外逃。其母弥禄下阳人,怀干贞后到处流浪。生前其母至孟郡城神祠(今大城沙漠庙)为干贞父子祈祷,八月初十日(农历)晚生干贞于庙前大刺蓬中(此地在沙漠庙青龙过江桥南,昔为干贞天子庙址),取乳名为“起黑”(白语—刺生),后被神祠庙祝救于祠后岩洞中养育长大,该洞白语称为“捣括朵”(大官洞),庙后之山亦名大官山,(明碑曰王屋山)汉译“天子洞”。长大后过继与挖色村渔人杨氏夫妇为养子,取名杨干贞。
早年干贞与养父在洱海中捕鱼,养父见干贞身影在洱海中皇袍衣冠,前有双龙护卫,后有百鸟尾随。干贞是捉鱼能手,幼年在大成七星水塘(今大成水库前身有7个小水塘)和洱海中每天捕很多鱼,常常请小伙伴们做客,做出蒸、酥、拌等8碗鱼菜,白族中称为“务鳔”(鱼魁)。也能吃鱼,说他的食鱼量可达一筏(约15市斤)。尤以喜食弓鱼拌。如今其后裔八月初十日到沙漠庙做干贞生日时,仍用弓鱼拌这道白族名鱼饮食供祭,并还宴客哩。
杨干贞还能背住日月,让太阳和月亮不落,白语谓之“武尼武洼”(背日背月)。杨干贞在沙漠庙的塑像,白语称为“弓务信”(弓鱼星),连同他在挖色村的后裔人们都称“弓鱼星”,这是因为他当政时洱海弓鱼纷纷窜出山林间,逃避捕捉。渔人上书,干贞下旨命弓鱼回归洱海,规定弓鱼的活动范围,西岸至烧香路止,东岸至本川石马桥(凤尾箐口)止。其中本川有一对弓鱼(一公一母)不听旨教,违抗命令逃入山林,被干贞用弓箭射落在地,叫他们永远不得回归洱海,变成竹鼠,就地繁衍。如今本川凤尾箐间有一地名叫竹箐,竹鼠较多,相传便是这对弓鱼繁衍的子孙。如今杨干贞的塑像在大成沙漠庙系为皇袍衣冠,一手执大印,一手执弓鱼。
杨干贞幼年习武,后入孟郡神祠(今沙漠庙)学经书,后来从军,步步高升为剑川、东川等地节度使。他后来找到父亲,干贞有两个弟弟即杨名、杨诏,萂村留妹招婿赵姓,后裔多姓赵,仅有一户姓杨。杨干贞在萂村的后裔,白语称“括简”(官宅)。在宾川大营、瓦溪等地有皇庄至民国时收归国有。在本川有弓鱼沟和油鱼洞的捕鱼权归挖色后裔享受,至合作化后归入集体。
杨干贞在萂村和本川南山均有坟地,相传被废为僧充保山金鸡寺,死后遗体火化。又曰正当段思平起兵之日,他家中馬下双驹,本为喜事,然他去看时双驹则变为一对大蛤蟆,被蛤蟆吓死了。1
在田怀清先生整理的文本中,故事的最后一段专门解释了杨干贞及家人为何成为五大村本主,主要原因还在于为当地百姓和利益作出了贡献(驱逐野兽,保护畜牧业的生产安全)。故事解释了杨干贞何以能成为君主,关键还是在于天意,这使他异于常人的本领和才能亦蒙上神授的色彩,从整个故事情节来看,对杨干贞都是正面褒扬的,没有地方史志记载中那种负面的评价。可能因为是本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本主就是肯定表述者自身,否定本主也就是否定自己,故消极的评价不太可能出现。2这一点也符合集体记忆建构的常规逻辑。王富先生整理的文本则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对杨干贞形象的塑造也是最“光辉”的。上述两种文本的共同点均在于杨干贞完全是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与地方史籍记载的“暴君”形象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跻身于本主行列的杨干贞,更是庇佑一方子民福祉的神灵,杨干贞建立大义宁国的事迹,也是构建其光辉形象的原始素材,而完全与正义非正义之类的价值判断无涉。
另外一种可以作为佐证的材料是产生于民国年间的祥云县杨氏家族墓碑中对杨干贞与段思平的表述。
盖自杨姓启祖……从江南至云南落籍洱海。唐开元间蒙诏东川封侯职,继任节度使之职。回(疑当为“四”——引者)传杨干贞公,后晋灭郑,称大义宁国。天福之年丙申,南诏通海伪节度使段思平□干贞战镜州,是时干贞走,而段氏据其国,未几复将其子奴仍守镜州。……先后事实有宗谱可考,不胜枚举。……师范讲习所毕业姻侄张大英拜题并撰[15](按,录文无年月,但从行文用语来看,当撰于民国年间)。
令我们多少有些惊讶是碑文中的“南诏通海伪节度使段思平”和“段氏据其国”的表述,称段氏为篡位的逆臣贼子,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唯一见诸文字的对段思平的负面定位。尽管今天洱海区域的大多数家谱较为可靠的历史年代线索只能追溯到明代,此前往往无法认真考究,但在民间却是把家谱的说法当成完全可信的历史记载来看待的。即便如祥云杨氏墓碑这样书写于民国年间的碑碣,其影响依然不可小觑。很明显,碑文的立场是完全为杨氏先人评功摆好的,但即便是这样,对段思平的定位还是多少令人吃惊。1我们当然无须过多地纠结于碑文所述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但却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如果是段氏后裔或完全处于段氏立场的人来书写杨干贞,那杨的形象显得极为不堪也就在情理之中。
杨干贞本主的传说在洱海以北的洱源等地流传,根本原因当在于杨干贞起兵前为剑川节度使(部分史籍误为“东川”),这一带乃是杨氏集团的根据地。这既是杨能够起兵夺取王位的基础,也是其统治不能长久的根本原因之一。木芹先生说:杨干贞“身任剑川节度,当有一定实力,因其职为独镇一方,握有实力,然而有其弱点,即剑川节度在南诏前期为宁北节度,惟地多在吐蕃势力控制之下,异牟寻(贞元十年)破铁桥后,宁北节度移于剑川,故又称剑川节度,因此之故,一则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洱海以南之地;二则原来为三浪住地,吐蕃控制时期往往利用民族隔阂,即南诏蒙氏与三浪施、顺蛮之间的矛盾来要挟南诏,所以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这里的民族关系不很融洽,提出此一点是为了说明,这一区域不可能全力拥护杨干贞。”2木芹先生的论断,为我们今天认识杨干贞传说的分布格局与相关评价,提供了坚实的史学基础。
四、余论:成王败寇还是公道自在人心
在一般可见的集体记忆材料中,如果作一个简要的类型划分,大致可以分出3种:一是“圣明领袖 - 英雄祖先型”,这一类型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表述一般是积极、正面的,有助于激发自豪感与自信心的,祖先的荣耀与光环是后代子孙可资夸耀的文化资源;二是“苦难记忆型”,作为受害者的一种记忆,“我们”是无辜的,是被加害的弱势群体,我们过去的屈辱与苦难都是邪恶的敌对方所施加的,所以应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表述模式,曾经的黑暗和灾难应成为今天后人奋发向上的警世钟;三是“智慧传承型”,即其中隐含的情感倾向并不具备更多的泛政治化色彩,而着眼于过去的人事与社会变迁当中体现的高度的智慧,这当中当然也夹杂着阴谋与算计,有对立和协作,最终较为明晰的指向则往往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无常,白云苍狗,唯有真知与智慧与天地同辉。当然,这三者之间往往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融,上述划分主要着眼于其表述的侧重点,同时也是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杨干贞本主的传说及杨氏家族的祖源书写,显系第一种类型的表述。
有趣的是,有关杨干贞的不同表述中看到的既不完全是历史叙事中屡见不鲜的“成王败寇”,也不单纯是道德至上的“公道自在人心”,而是在逐渐官方化、正史化的主流表述(暴君)与口耳相传、四时献祭的英雄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各自表述”的格局,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双方都对彼此的存在采取了“视而不见”的立场。或许,正是这种立场导致的平衡,客观上为后世保存了相对丰富的材料,为时空远隔的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认识杨干贞的是非功过及其个人形象的塑造过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时至今日,环洱海区域各地理单元之间的人群之间的利益博弈,事实上也依然存在(尽管更多的情况下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种状况决定了人们对过去的表述还是会延续以往的模式,原有格局未从根本上被改变,与之相应的表述模式自然就有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于是,在洱海以西地域(段氏集团根基所在及王畿区域)如喜洲、湾桥等地的传说中,杨干贞继续充当“坏人”,是弑君者和治国无方的统治者形象。在洱海以东区域,杨干贞是为民众福祉作出了切实贡献的英雄,是“弓鱼星”,是其后裔杨姓渔民四时祭献的祖先,也是高居庙堂、护佑一方平安的本主神,口头传统表述中着力强调的是其神异勇武有别于常人的一面;在洱海以北的洱源、剑川等地,杨干贞的形象更近于常人,或者确切地说更近于常规意义上的本主神,与其他来源各异的本主神的形象无多大差别。
如果说历史人类学的要义之一是“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那么在杨干贞的个案中即较为鲜明地体现了不同区域的人群对历史的创造与运用,这一特征应该说从大理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各种表述之间的差异正体现了“被建构的历史”的一般特点,建构历史的背后是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的博弈。具体而言,杨干贞的污名化,在于段思平集团建立大理国之后要树正统,因为段氏政权是从杨氏手中夺来的,势必要从道义上有一套说辞,在意识形态上占领舆论阵地,把握舆论导向,使民心向着有利于段氏集团一方。尽管这些材料已散佚殆尽,但作为后来对段氏政权怀着“故国之思”的知识精英的基本书写依据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干贞最初的污名化,是段氏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政治需要;而这种污名化的“暴君”形象在几百年后的传世文獻中得以定型,则是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书写的结果。从今天可见的史籍来看,最有代表性的文献为《南诏野史》,其资料来源为已佚的《白古通记》,尽管对《白古通记》的成书时间尚有不同意见,但在《白古通记》当依据南诏大理旧籍编撰而成这一点上却并无争议。1也就是说,其主要内容乃至旨归均与南诏大理时期的记录有密切关联。而且,如果确如侯冲先生所见,《白古通记》乃是段氏统治下的故国遗民为了抒发、排遣“故国之思”而作,那么,其拥护、怀念段氏王朝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作为段氏对立面的政治集团——不论是作为段氏得国之前的杨氏集团还是彻底消灭段氏集团的朱明王朝——采取排斥、贬抑的书写方式也就在情理之中。但这种表述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群的认可,洱海以北的洱源等地,洱海以东的挖色等地的人群,在区域性的集体记忆中顽强地保存了一种不同于主流话语的表述。在这种“各自表述”的格局中,历史的真实已退居其次,基于集团利益或区域利益博弈的需要而做出适宜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策略和举措。
参考文献:
[1] 西佛曼,格里福.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 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25.
[2] 《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97 - 98,104 - 105.
[3] 木芹.南诏野史会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203 - 205.
[4] 蒋彬.南诏源流纪要[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 徐文德,木芹,纂录.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748.
[5] 杨慎.滇载记[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徐文德,木芹,纂录.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760.
[6] 冯甦.滇考[M]//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徐文德,木芹,纂录.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27.
[7] 倪蜕.滇云历年传[M].李埏,校点.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158 - 159.
[8] 李京.云南志略辑校[M]//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91.
[9] 杨士云.郡大记[M]//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17.
[10]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4:376.
[11]侯冲.白族心史——《白古通记》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12]佚名.白古通记[M]//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60.
[13]尤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96.
[14]杨义龙.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洱源卷[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61 - 62.
[15]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白族社会历史调查(四)[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254.
[责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