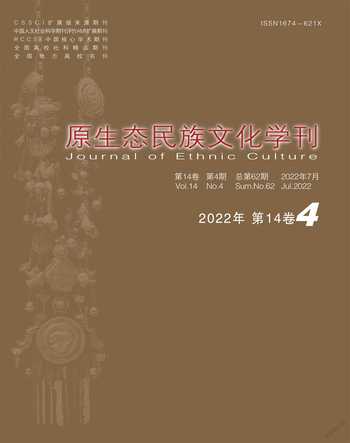个体生命叙事与多元文化杂糅
2022-07-15王彦芸
摘 要:位于南岭通道的都柳江自清代中期河流疏浚以来,成为人、物流转频繁的重要孔道,移民因盐、木贸易兴盛流入沿河重要商埠定居经商,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神灵信仰并建立庙宇。在人群流动交互的区域历史背景之下,本文以一个女性仪式专家的生命自述及仪式实践为例,探讨原本殊异的文化符号,如何与个体生命经验相结合,通过再诠释与再创造,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地方复合象征体系,进而思考多元人群互嵌地区文化碰撞的杂糅与交织。
关键词:都柳江;生命叙事;文化杂糅;多神崇拜;历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2)04 - 0109 - 10
一、引言
都柳江属珠江水系,发源于贵州省独山县,流经贵州三都县、榕江县、从江县,在广西三江老堡口河段与浔江会流注入融江。清代中央王朝设立“新疆六厅”,囊括今天的整个黔东南地区,而正是在苗疆地区治理的过程中,开始了都柳江航道的疏浚。疏浚完成后,河流的流动性使人与物沿河上下流通互通,首先来自下游溯江而上的闽粤籍商人因经营木材、粤盐贸易,在都柳江下游商镇码头地方逐渐定居,而两岸苗侗居民也因市场活动的兴起寻找生计,在上下游迁徙搬迁,并围绕商镇市场生存、定居,形成了至今所见闽粤“客家”在曾经兴盛的市镇与周边苗侗村寨互嵌居住的格局。本文所关注的位于都柳江下游的富禄乡,则是在此区域背景之下,作为都柳江下游重要的市场集镇,即使在水路通道已经没落的今天,富禄街道也依然保持着闽粤移民“商业街”的空间格局,而这一人群流动汇聚的历史,也在这里留下了多元文化景观。
河道产生的流动性不仅带来了人与物,也带来了不同历史叙事的碰撞以及不同感知、不同观念的流动[1]。今富禄上游1公里处的都柳江南岸,坐落着葛亮侗寨,它是最初富禄市场的中心所在,也是闽粤移民最早的定居地,也因此缘故,寨中至今仍保存着闽粤移民清代所修建的天后宫、关帝庙,这些庙宇虽几经破坏与重建,但与葛亮侗民后来在不同时间中所修建的孔明庙、孟获庙、“萨岁”,一同构成了该地庞杂多样的神圣空间。如今,这些原本意义分殊的庙宇和神灵符号,已在苗、侗、客人群互动、文化交汇的过程中逐渐互渗、交织,成为当地人所共同接纳的“多神崇拜体系”。本文希望讨论的,正是极具差异的文化如何经创造而杂糅整合的过程。上述不同文化观念的相互遭遇与叠加转换,不仅与整体性的区域政治经济过程相关联,同时也与地方人群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乃至极富能动性的个体之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民间信仰共存、混杂的多元形态在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中并不陌生,也是学者们借以讨论人群互动、文化碰撞和历史变迁的重要主题,其中从民族走廊着手,对跨民族互动中形成的地方民间信仰以及社会文化体系融合的研究成果尤为凸显[2],对都柳江所在“南岭走廊”地区民间信仰的关注,更是集中于信仰、仪式文化的多样性,讨论族群互动及跨文化交流中所形成的文化动态。1正因复合、混融的民间信仰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与过程性,学者们亦从时间的维度开展讨论,在历史人类学领域,从苗疆地带的民间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方理解、展演出发,关注信仰活动所反映的地域社会秩序及其变化,以及国家与地方透过民间信仰活动的上下整合过程。2上述研究的共识,在于强调多元民间信仰在一地的共存杂糅,需超越“地方”、在人与人、内与外以及多元政经力量的交互联结之上方能把握文化的复合性,探讨文化交错影响之下文化内部的多元性[3]。
然而流动性所带来的不同文化知识体系如何实现意义的重塑、共享?又如何在当地产生现实意义,被接纳、整合与实践?有学者从历史与神话角度出发,注意到民间信仰中意义如何通过与历史记忆结合从而在诸知识体系中具体改造、建构的过程[4];也有学者通过地方族群具体的合作结盟、竞争对抗过程中理解多元神灵体系的张力关系与“灵力”(apiritual power)的生产[5];而对于不同知识及表达体系互相遭遇的相关研究,值得关注的是Erick Mueggler在《纸路》[6]一书中,通过描述西方植物学家在中国西南雇佣当地人共同進行搜集、分类、整理地方植物的过程,试图讨论内在经验(experience)和抽象档案(archive)之间的关系,在西方植物学家深入边陲地带寻找超验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以及不同的地方合作者,其内在世界也沉浮于此,人与地、感官和情感、地方与帝国,实则彼此碰撞、交织和叠加,作者借以反思了现代西方主体和客体的割裂,并强调表述并不是客观事实的再现,“表达是鲜活的生命在不同力量、因素、互动和关系下在符号和话语层面留下的可供追查的痕迹” [7]。在这些关于文化交互的讨论中,即将个人经验和想象放置于中,同时也凸显了文化的历史化的命题。
这种经个人经验与想象跨越不同知识的讨论以及对表述中文化遭遇的重视,对思考葛亮多元庙宇复合意义的建构过程尤为关键,因为这些不同庙宇、神灵的日常诠释工作和仪式,均由当地一位75岁女性赖JQ操持,她是村中的仪式专家,其身份既是闽粤籍客家移民后代,又嫁与侗家作为侗家媳妇,她跨越不同族群的身份属性使她获得了在不同象征符号中穿梭、言说、转译、创造的权力,另外,作为仪式专家,赖JQ却并不依赖科仪文本的知识进行实践,她极富创造性地通过对自己生命经验的不断讲述,将葛亮不同庙宇空间中的神灵整合进个体生命故事之中,不仅赋予了自身身份的神圣性,也在生命故事的重复讲述中不断编织、生产诸神灵的关系意义。简美玲在苗族歌师研究中注意到具有仪式专家、苗人文化记录者和翻译者多重身份的歌师,在创作中结合自身个人生命史和苗人古歌文本进行知识生产和文化创造[8];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对口语文化神话与仪式的讨论中,意识到想象与“幻想”对于文化的可变性和创造性的重要作用,提出仪式与神话的执行者和传诵者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个性化处理,并按照自己的需求生产出来[9]。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从赖JQ的生命经验出发对都柳江下游多元崇拜的思考,一方面将聚焦于其自述中所镶嵌的区域社会历史框架,呈现主观创造、诠释背后的历史脉络与叙事基础;另一方面,则希望讨论文化的杂糅如何经由个人能动的创造与实践,在过去与当下的叠合中被生产和实现。
二、人的流动与诸庙修建
雍正八年(1730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鄂尔泰加强了都柳江流域古州地区的控制,同时组织地方上的土司率士兵多次疏浚对江道,航路的通达将这一地区与下游西江乃至珠江连接起来。如今的广西三江富禄,曾因极佳的水陆交通位置成为都柳江下游货物转运的重要商埠,两广米粮贸易的发展对富禄影响颇为明显,而木材贸易也随之兴起,两广、江浙等地木行木商陆续来到都柳江流域采购木材。另外,都柳江航道的开辟推动了粤盐在黔省的销运,闽粤籍商贩将海盐从广东先运至梧州、柳州等地,再通过都柳江航道分销沿岸及贵州腹地,而富禄则成为商人们进入苗疆地区的必经之地。
河网市场的形成也带来了商业移民的迁徙,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商人因贸易活动沿江上下流动,而其中又以广东、福建籍客商为众,随着富禄市场的逐渐兴盛繁荣和移民的代际更替,汇集富禄的移民人数渐增并最终定居下来,其中又以闽粤籍赖姓人数者为众,他们自称“客家”,从下游将粤盐运至富禄市场,再从富禄码头通过河流、陆路分销到周边村镇,随着资金积累,也同时在两岸高坡买下山林,将木材在河口扎排放运下游市场,因此,在富禄市场中占据中心的闽粤客商随着商埠的日趋发展,也逐渐具备了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地方兴办公共事务与筹建庙宇。道光年间,闽粤移民在最初集中定居的葛亮寨集资修建闽粤会馆,馆内供奉天后娘娘,亦称天后宫,这一商业移民会馆属性的天后宫信众不仅限于富禄一地的闽粤移民,也包括了都柳江主航道上下、支流各集镇中的闽粤籍商人,每逢三月廿三妈祖诞,富禄市场网络中的闽粤移民都会前往葛亮天后宫参加酬神仪式。在天后宫建成后第三年,同样由赖姓商家主导在天后宫旁修建了关帝庙,两座庙宇建成后均由闽粤籍的移民负责管理。
虽然闽粤移民是富禄市场中的主导,但在汇集葛亮的移民中,也包括从上游两岸到富禄市场寻找生计的苗侗人群,他们帮“老板”放排、撑船、做副食或肩挑背扛等,也有部分参与到盐木贸易之中,可以说葛亮寨就是由富禄市场吸引而来的不同移民所构成。大约光绪年间,富禄市场重心由南岸葛亮转移到江北岸的富禄码头,葛亮的移民商家也陆续搬离,并重新在富禄修建起“五省会馆”与三王庙,囊括闽、粤、湘、黔、桂,意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移民社会整合,大商家们也将酬神的重心放在了更多人群参与的“三月三”祭祀三王的节日上,这一仪式空间的转移,使得天后宫与关帝庙以及与之相关的“三月廿三”妈祖诞留在了葛亮,由葛亮侗民和极少数闽粤籍移民共同维持,这样一来,原来由闽粤移民筹集资金主导的“三月廿三”,转而由葛亮侗民主导,他们不再是酬神节日与活动中的旁观者,而是亲身参与者和主持者。
实际上,都柳江航道人与物的流动并非只限于清代,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以及抗战期间,其他通路入黔的物资运输受阻,因此珠江水系的航运更为繁忙,一度造就了都柳江上舟船拥挤的鼎盛时期,而移民也在不同的时间陆续流动、迁徙进入富禄、葛亮,在长时间的人、物流动中形成富禄当下之多样人群交织的格局。除了上述闽粤移民修建的庙宇以外,葛亮寨还有其他多处神圣空间,首先有侗寨之处就有萨坛,葛亮侗民在寨中安置萨岁,在集体活动中举行敬萨仪式,除此以外,在葛亮的侗族移民,根据“葛亮”地名,创造性地将区域内苗侗人群流传甚广的孔明传说与“村落历史”相结合,并透过孔明信仰的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的身份认同,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在一户侗族罗姓的主导下,修建起了葛亮寨孔明庙[10]。随着时代变迁,葛亮寨的神圣空间也在新近时间中变化、新增,2007年,位于都柳江下游里的同乐乡孟寨因寨中新公路的修建,不得不拆除本地“孟公庙”,孟公庙主祀神为孟获,传说孟寨当地的侗族居民在即将拆掉庙宇期间,在“梦”中得到孟获指引,孟获表示他愿意追溯孔明公,搬迁去葛亮,于是,孟寨人群将孟公移至葛亮,为其修建庙宇,与孔明庙并列。
根据上述葛亮庙宇兴建的背景讨论,我们亦可了解到富禄的人群构成、贸易往来以及都柳江河道流动性的历史,首先,最早闽粤籍移民在葛亮修建天后宮的主要考虑在于保护依赖水运行船的商家一切安全,关帝庙在于祈求生意的顺遂,而后,随着移民数量增多,以及移民身份的更加多元,为凝聚移民向心力,闽粤移民转而迁至富禄码头,祭祀五省会馆中的三王庙,而将天后、关帝、土地留在了葛亮。而在区域内流动至葛亮寻找生计定居的侗族移民,也在不同时期中带来了自己的信仰,修建庙宇和神圣空间。正是在这样的人、物、观念流动的历史过程中,在葛亮形成了诸神汇聚的多元文化景观,而这样的区域社会历史也成为了个体在叙述自身生命历程时的基本框架。直至今天,天后宫、关帝庙、孔明庙、孟公庙,以及侗族“萨岁”信仰之萨坛依然在葛亮交错共存,诸神灵仍持续受到当地人的供奉,而每逢葛亮三月廿三,人们会做3个花炮分别祭祀天后、关帝和孔明,并在当天的花炮游行中,前往上述不同的神圣空间进行祭拜,“抢”花炮节环节结束之后,夺得花炮的人家又将代表具体神灵的花炮搁置家中供奉直到次年三月廿三,由此可见,这些庙宇及其神祇仍然鲜活,持续在具体实践中不断产生贴合当下的意义。那么,这些在特定时间中因人的流动往来,具有不同意涵的庙宇,究竟如何整合成为葛亮侗寨人群所共同接纳的诸神?当地人如何再诠释、再创造多元象征符号以持续生产诸神在当下之新“灵力”,将是后文持续关注的问题。
三、个体生命叙事、梦境与意义再造
由上述历史过程可知,从层叠堆积的神祇符号,到在日常生活和节日中诸神共祀,必经对神灵及其意义的重新创造与诠释才可完成,然而民间信仰中象征意义再创造过程因关切到“灵力”的生产,需由特定人物与特别途径予以实现。在灵力生产的相关讨论中,纳日碧力戈曾注意到呼唤神名在仪式中生产灵力的作用[11];安琪关注到图像作为再生产灵力的重要机制[12];石汉则强调了神圣空间设置的首要性[13]。然而在葛亮,诸象征符号意义改造钩织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一个女性,她通过对自己生命故事的表述,将不同神灵编织其中,成为生命“灵力”经验的一部分,也在地方社会中再生产了诸神新的关系意义。
笔者与75岁的赖JQ初识于2011年的葛亮三月廿三,她的气质与村中大多数腼腆温婉的妇女截然不同,在花炮节中她不仅在公开场合极为活跃,也主导着每一个仪式流程,指导人们该做什么,要遵守什么禁忌,甚至在节日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村民们有任何与神灵有关的需求与疑惑都向她询问意见,虽然她的身份可以称作村中的仪式专家,但却又和一般意义上基于知识传承的仪式专家角色不同,她主要依靠与葛亮诸神沟通来为村民解决诉求,而她所具有的“力”则来自其表述的特殊生命经验,赖JQ曾多次在公共场合中或与笔者单独相处时,谈论自己的人生历程。赖JQ是如今葛亮寨中为数不多的赖姓之一,正是从福建到富禄经商的移民后代,她的父亲曾与弟兄三人离开福建到外地谋生,最初在都柳江下游融安经营些小营生,兄弟们则住在柳州,因听闻富禄商机多,其父便从融安前往葛亮寻找生计,逐渐与富禄赖姓商人们合伙参与了一些木头生意,因在融安、柳州还有些人情关系,所以常常放排去柳州再沿水路去广东贩卖,慢慢积累起资本发家,再回到葛亮置办土地,也正因如此,1949年后土改中其家被划成地主,生活变得艰难不易,7岁时父亲过世了,只有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她哥哥生活,艰难不易。虽说她是福建客家后代,原本客家与苗侗较少通婚,但也是因其家庭状况的衰落,她长大后还是嫁给了葛亮当地的一个侗族男性,变成了侗家媳妇,如今她的穿着打扮已和普通侗族妇女无异。上述关于生命历史的表述,是个体在区域社会历史脉络下的述说,她父亲迁徙、维生的经历以及早年生活境遇的转变使她的生命讲述承载了“苦难”的主题,同时,也正是因为她族群身份上的跨越与多重,一方面客家人后代身份使她具备了管理、沟通天后、关帝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客侗双重身份又使得当地侗族人群对她有一份亲近感,对她十分信任。
不过,赖JQ的人生故事讲述與富禄其他移民故事大为不同,不止限于上述现实层面的经历,而是将葛亮各种神灵,通过在梦境中的显现,与自身相关联。她如下表述。
我7岁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去世了,只得我妈带着我跟我哥。我7岁的时候其实已经死过一次了,死了7天,当时我妈带着我们还住在柳州,实在找不到土地可以埋,就把我放在家里。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进门就说他是来救一个人的,当时我哥哥也生着病,但还没有死,所以我妈以为他是来救我哥的,就带他去看我哥,但是那个老头说,我是来救那个已经死了的人的。然后看到我,掏出一些药,把我嘴撬开喂进去,我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说到这里,她指着她屋中一个太白金星的神像说:“你看,就是这个人救了我了,就长着长长的白胡子,这个人在我7岁、28岁,39岁在梦里面找过我3次。”说到这里,她突然变得非常感慨。
之前我的日子过得苦啊,我老公死得很早,只得一个儿崽(子),儿崽(子)结婚不多久才得一个女就死了,儿媳妇改了嫁,留一个孙女给我带着,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别人来收电费我也没钱交,我这辈子不怎么流眼泪的人啊,那年过年对着天嚎啕大哭。
但是39岁之后,太白金星就给我说,他要跟着我了,从那之后,太白金星每月十五都会来找我,他来我其实也有点害怕,所以每到十五,我就会把家里的灯都打开,太白金星有时一个人来,有时还带了好些随从和兵。他决定跟着我之后,我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我和那些地理先生不一样,我不做那些鬼的事情,我只是治病救人,如果人生病了去医院也总不见好,我就可以给他们一点“药”,这些药很灵。不光太白金星跟着我,有一天我做梦,梦见天后站在我的床跟前,她的眉心间长着如同硬币大小的红黑色圆点,天后从这次以后,也决定一直跟着我了。
在赖JQ的讲述中,葛亮的各种神灵都在梦中与她进行沟通,她的梦以及她的身体,成为汇聚诸神的重要场所,梦醒之后,她又将诸神的“意思”实践和表达,不断生产出现实意义与灵力。而这类关于梦的讲述,也是镶嵌在地方文化脉络之下的,在都柳江流域苗侗文化中,梦是一种获得现实启示的重要途径,也只有那些梦到过神祇,并在梦中与之交谈过的人,才能获得特殊身份或指导。对梦的关注在人类学领域并不陌生,人类学常借由“梦境”以及梦与现实的关联,尝试探讨个体如何构建意义和身份[14],或从心理层面出发讨论个体与文化的关系[15]。在这里,“梦”是赖JQ连接神圣和世俗的重要途径,与个人生命历程紧密结合的、极具主观性的梦境在这里成为知识生产与转换的中介,也是将多元文化体系创造性构织关联的关键环节。且这样的梦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在地方观念中,只有那些命运波折、家庭无后或没有丈夫的女人,才足够“洁净”,神灵才会到梦中来找,她的苦难命运和生命体验赋予了她特别的“力”,在葛亮,她常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因此,这些体验不仅限于她的个体记忆,也具有的某种公共属性,成为村中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家都称她很“灵”。
生命中的苦难、在梦中遭遇诸神,关于这一切在现实中的表述,为原本意义分殊的诸神创建了互动和关联的空间,虽然她的表述充满了晦涩,对诸神的描述经常混杂以至于使听者费解,比如她说天后其实姓赖,关帝其实是“天后公公”等,但正是这些晦涩、混沌却生动的讲述,诸神就像村中普通邻居那般栩栩如生,这些根植于个体经验的想象与表达,不仅杂糅、交织了葛亮的诸神意义,也超越了过去与现在、群体身份与自我,世俗与神圣之间的隔阂,成为了赖JQ与葛亮村民感知当下的途径。通过这种主观性、创造性的方式,赖JQ表达神意、甚至以一种看似极为随意的方式举行仪式,并告知人们诸神对世俗为人道德意义上的要求与好恶,逐渐形成了一套杂糅复合的地方象征知识,塑造着当地人头脑中的宇宙秩序以及日常行为规范准则。
四、纠缠的多元象征体系与清晰的秩序
葛亮本由不同人群带来的诸神灵,通过赖JQ的生命故事和梦境彼此关联,同时,村民也在她的主导下,通过日常以及节日中的仪式活动加以实践,真正在人们现实生活里产生意义,在诠释、认知与实践的相互映照中,形成葛亮以及周边村寨共同信奉的多元象征体系。
在葛亮,人们把所有的非人力量都称作“鬼”,而在此基础之上,则分为4个层次,分别为“神鬼”“仙鬼”“家中鬼”与“野鬼”。第一个层次,“神鬼”指的是那些有具体神圣空间的神祇,包括“萨神”“土地神”“关帝”“天后”“孔明”与“孟公”,他们无一例外都有具体供奉的庙宇。其中“萨神”是侗族传统民间信仰所供奉的女神,她安置在村落中一个特别的土堆中,并没有神像,人们在土堆上种上一株万年青,萨坛象征着村寨和集体,人们只在集体活动时会祭祀萨神,如特别的节日或与其他村寨赛芦笙、打篮球时会在清晨或离开村寨之前祭祀,萨神信仰的背后是传统侗族文化中对集体观念的强调,人们也常说“建寨先建萨”。同样具有村寨集体象征的,是土地神,土地庙位于村寨公共空间一棵大榕树下,除了节日时间以外较少祭拜。只有当涉及成人个体时,就会向“神鬼”祭祀,且对应的人群也各有不同,天后对应的是女性,特别是与生育相关的诉求会向天后娘娘举行仪式予以祈福;关帝与孔明则对应着男性,男人出外打工、做生意,就会祭祀祈求世俗世界的成功与顺利,在这里可以看到,孔明的象征意义并不十分清晰,当地人认为他对世俗世界的功能总是与关帝“差不多”。第二个层次是“仙鬼”,“仙鬼”是在赖JQ表述和梦境中出现的其他神祇,这些神祇在葛亮没有庙宇,因此赖JQ把他们安置在自己家屋中,摆放神像供奉之,而它们对应的,多数是与疾病相关的治疗仪式。第三个层次是“家中鬼”,所指的是一个家屋中已过世的成员,在葛亮,人们通常在厨房中而非堂屋中中供奉祖先,侗人认为祖先围绕在传统家屋中的火塘边,如今火塘在村中虽已被现代厨房器具所取代,但是人们仍然认为祖先依旧存在于日常烹饪的灶火旁,因此只能在灶火边供奉。而堂屋中供奉的只能是“神鬼”。第四个层次,则是“野鬼”,即非自然死亡并无后人祭祀的,被当地人称为“外面鬼”,在内与外的对照下,“外面鬼”意味着危险和帶来厄运,在节日时间中,人们除了在上述各个神圣空间中祭祀前三种类型的鬼以外,也会在家屋门外的空地上,点香给“外面鬼”,好让它们不会作祟。
这些在历史不同时间中汇聚葛亮的诸神,通过上述不同层面的禁忌与仪式,真正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意义,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能解读到闽粤移民天后、关帝神祇的传统含义,也能解读出侗族人群的“萨岁”信仰以及在更长的人群互动过程中出现在葛亮的鬼神观念,它们似如历史的层叠,但却不是简单堆砌,而是经由创造性的文化转译、改造,纠缠嵌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世界,在人们头脑中塑造新的宇宙秩序。虽然对这些神祇含义的言说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人们现实生活中确定的期许赋予了诸神各自清晰的位置,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是葛亮 “花炮节”,花炮节原是闽粤移民举行的妈祖诞,移民离开葛亮之后被当地侗人群延续和演绎,在这个参与人群和文化内涵极为复杂的节日之中,祭祀的顺序为“萨坛 - 土地 - 天后 - 关帝 - 孔明 - 孟公”,这一顺序既体现了诸神之间的序列,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符号出现在葛亮地方的历史顺序,从集体象征的萨与土地开始,人们祈祷保寨平安,随后将3座特别制作的花炮分别敬天后、关帝与孔明,天后与关帝是曾经闽粤移民举行妈祖诞祭祀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孔明庙修建之后,当地人特地为其增添了一枚花炮供奉,最后才对外来的孟公进行祭祀,在花炮节这一特殊时间中,葛亮人群将诸神汇聚、整合,又在仪式过程中再现历史和焕发当下的新意。当地人用一套世俗类比去表述诸神的关系。
萨坛呢,我们平时不怎么管,但是如果是关于寨上集体的事情,我们就得去拜,过年过节什么的,也会去敬她。打个比方说,她就好像是寨上的书记,但是具体的事情呢,还是要拜托其他的神灵,比如求子要拜天后,做生意和成功就要拜关公和孔明,他们就像寨上的部门主任,而更小一点事情,比如小娃崽生病不好什么的,就要去拜土地公和土地婆,他们就像办事员一样,负责更琐碎的事。孟获,我们葛亮屯的人其实不怎么拜,孟获虽然是独洞河边一个叫孟寨的那边的人过来修的,但是他们也很少来,我也很奇怪。按照我的想法,我觉得以后的花炮节应该弄4个花炮,拿一炮来放给孟获的。1
在这一通俗的理解中,我们既看到一种杂糅整合的神灵体系,也能看到诸神间依然保留了差异,并依据文化的远近和历史时间的远近形成了相互的等级。葛亮含义模糊与秩序清晰的多元崇拜,既是历史上人群间长期交互的结果,但同样重要的,也是如赖JQ般的个体,在地方文化逻辑之下能动的创造与重塑,将诸文化符号与现实联结。尽管人们对区域历史已经陌生,但是历史仍旧留在了个体生命历程之中,也留在了依然在当下焕发新意的文化符号之中,从这一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文化杂糅,既在历史中生成又与当下紧密关联,又是一种和个体休戚相关的,从地方文化内部不断产生文化动力的创造过程。
五、结语
由上文可知,富禄葛亮是随着都柳江河道疏浚、区域市场形成而逐渐兴盛的聚落,在人的流动下外来商业移民陆续进入这一苗疆地带,修建起作为精神寄托和社交场所的民间信仰庙宇,而后漫长时间中因移民构成逐渐复杂、市场中心和居住空间的变迁,多种神圣空间陆续出现在葛亮村寨中,在当下呈现出层叠的历史文化景观以及多元并立的信仰形态。正是在这个多样人群、文化交汇聚合的地点,我们得以讨论,这些从过去走来的彼此殊异的神灵,是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关联、产生意义?而依旧活跃在村寨现实生活之中?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关切到的正是多元文化杂糅的主题。本文以一个女性仪式专家的个人生命叙事作为讨论的开始,在她的生命故事中,既有镶嵌在区域客观历史脉络中的命运表述,又有根植于地方文化逻辑下的主观演绎,而她极为灵动的个性表达却模糊了客观与主观的界限,这些表述不仅再现了经验,也再造了经验。同时,葛亮诸象征符号,借由她在公开场合对苦难命运与梦的奇幻经历的表达,也在现实中得以复活。也许,赖JQ的叙述是充满了含糊、矛盾的,然而通过仪式的实践,结合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期许,原本混杂的要素被捏合成在当下有意义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个体经验和想象,正是异质性文化重新编织、复合、杂糅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同时,文化的杂糅也需借助象征符号,展开意义的建构、文化的实践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持续生成。
早期林哈德(Godfrey Lienhardt)在非洲丁卡人宗教研究中就认识到经验和神灵的关系,在面对丁卡人多样“神性”(divinity)时说道:“神性是多样的,因为人类的经验是多样的,如同这个世界是多样的;神性又是一体的,因为自我的多元经验可以被带入统一的关系中。神力彼此不同,因为人的经验彼此不同,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整体经验世界与自我之间也是如此不同。”[16]王铭铭在对溪村的研究中曾注意到,在地方象征与仪式中,起作用的不是显眼的表现形式,而是具有隐秘性的人物及他们相关的文化创造、表达与传递过程[17]。这些人类学曾提到的经验、个人能动性对于地方文化影响的重要性,在今天文化杂糅的讨论中也具有同等价值。在历史性与流动性的视野下,已不再将文化视作孤立、封闭,而是在历史中不断互动、生成,然而其生成的过程及其机制,又因其参与者、文化观念、历史情境的不同而不同,需要持续投入观察与理解的努力,同时,文化的杂糅并非仅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应当在历史与现实相遇的地方探讨其生机与活力。另外,虽然群体之互动、超越地方之外的政治经济联系是讨论文化碰撞、复合杂糅的前提,然而人的具体活动、整体之下的个体并非只是上述前提的承载者,正是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创造、从个体生命经验出发的转化与表述,生活其间的鲜活人群其内在世界也才不断投入,不仅将复数的文化关联,也使得意义得以缝合和纠缠,重塑观念与世俗的秩序。巴斯曾将“文化”理解为“一套人们赖以理解与应对他们自己及他们所处之地的观念”[18],也只有基于人之观念复杂性与地方动态性的相互关照之下,才能深入理解文化杂糅背后持续流变的、历史与意义不断随之展开的鲜活世界。
参考文献:
[1] 王健,陈兴春,黄雨霞.地方感知与历史叙事——以都柳江下游梅林村为例[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9(6):110 - 119.
[2] 王建新.包海波.民族走廊理论对宗教文化研究对学术启迪——整体观与区域实践[J].西北民族研究,2020(4):62 - 70.
[3] 王铭铭.文化复合性——西南的仪式、人物与交换[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4] 杨德爱.多元的层叠: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的现实建构[J].大理大学学报,2020(3):1 - 8.
[5] 罗景文.冲突、竞争与合作——南台湾神灵门斗法传说中的叙述结构、信仰关系与地方互动[J].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20(4):199 - 230.
[6] MUEGGLER E.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7] 李晋.纸·路·西方博物学家的中国之旅[J].读书,2018(8):71.
[8] 简美玲.苗人古歌的记音与翻译——歌师Sangt Jingb的手稿、知识与空间[J].民俗曲艺,2014(183):191 - 252.
[9] 杰克·古迪.神话、仪式与口述[M]. 李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0]王彦芸.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7):7 - 11.
[11]纳日碧力戈.名字与神灵[J].中国研究,2014(1):4 - 10,228.
[12]安琪.阿嵯耶观音图像与信仰:再谈南诏大理国的神话历史叙事[J].云南社会科学,2016(1):87 - 94,100.
[13]石汉,徐菡.民间儒教的窘境生成——论中国农村家屋的空间与道德中心[J].中国研究,2014(1):37 - 55,229.
[14]林淑蓉.从梦、仪式到神话展演:中国贵州侗人的自我意象与象征形构[J].台湾人类学刊,2012(2):101 - 137.
[15]HEIDI FUNG.When Culture Meets Psyche: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ualized Self through the Life and Dreams of an Elderly Taiwanese Woman[J].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2(1):149 - 175.
[16]LIENHARDT G.Divinity and Experience: the Religion of the Dinka[M].Oxford Uinversity Press, 1961:156
[17]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0:137.
[18]BARTH F. Cosmologies in the making: a gene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variation in inner New Guine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87.
[責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