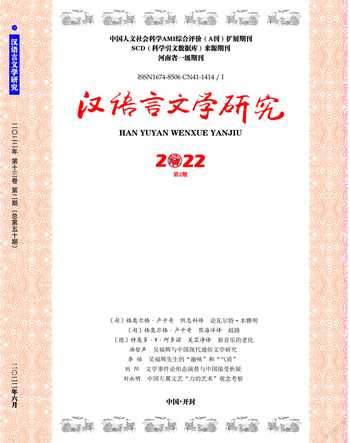辛弃疾《清平乐·村居》本义探微
2022-07-11郑慧霞
摘 要:《清平乐·村居》作于辛弃疾壮年落职后闲居上饶带湖期间,此词多被作为表现“农家乐”的农村词来看待,但这显然与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格格不入,以北复中原为志慨然南渡的英雄辛弃疾,自当驰骋沙场而今却只能“村居”做一闲人,怀失位之沉郁是必然的。词中“吴音”最为关键,点出词人是操北音而身居“吴音”区者,故相对操“吴音”者而言是以他者身份而存在的,由此则可判定作为“村居”书写者的词人和被书写者之间互为他者的人物关系。此关系的确立是理解该词情感基调最关键者,镜照出词人南渡初衷不得、却又不得不“乐”处当下即“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人生困境。
关键词:辛弃疾;带湖;《清平乐·村居》;吴音;北人情结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堪称宋词中和田园题材相关的典范之作,它的文字在轻灵跳脱中弥散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笔下的吴地田园和日常,是如此自然亲切、醇厚馨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首词化版的《桃花源记》。正是基于如此的文本呈现,我们可以理解在既有的研究中,此词何以被简单作为一首萧散自然的农村词来理解:“这首词通过一户农家生活的侧面,反映出当时江西上饶一带农村的和平宁静生活情景。……是一幅和平安定的欢乐场景。”①此词“带有乡村生活牧歌情调”②;“写农村生活的欢乐美好”③等。但“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④。还当考虑第三个着眼点即具体作品产生的整体文学场域。《清平乐·村居》作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至晚当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⑤因此,用以上观点解读此词者亦觉困惑,谓“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南宋,这样的‘农家乐’是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的本质的”⑥;“我们应看到这并不是‘国脉危如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严重的南宋农村的普遍现实”。⑦联系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对此词进行文本细读,可读出词人“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苍凉无奈:以北复中原为志慨然南渡的英雄辛弃疾,“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自当驰骋沙场而今却只能“村居”做一闲人,怀失位之沉郁是必然的。以此心态观照“村居”之景时心境如何,词中以“吴音”①进行了暗点,即点出词人是一个“外来者”即“北人”做了“江南游子”的自我身份体认。所以词中的“吴音”最为关键,镜照出词人南渡初衷不得、却又不得不“乐居”当下“村”中的人生困局。考察此词真实的情感,需把它置入带湖期间辛弃疾的创作场域中进行整体观照:因为单独拈出此词考察即就詞论词,视阈的有限正如在园林中透过一扇窗儿、一页门扉或者一丛花儿等去看外在的世界一样,所看到的是被一扇窗儿、一页门扉或者一丛花儿等限定或隔断的景观。框界中的景物相比于框界外的园林,毫无疑问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会导致片段性或局部性的误读、漏读和失读。这种片段阅读或局部阅读的效应,正如《红楼梦》中隔着“蔷薇花架”互看的宝玉和龄官:宝玉因不及看到事件的后续发展差点儿误判龄官的痴情为东施效颦;而龄官则因蔷薇花枝叶的遮挡竟把宝玉误认成一个“丫头”:
(宝玉)刚到了蔷薇花架……果然架下那边有人。如今五月之际,那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时,宝玉便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想毕,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致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写了,下大雨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②
不惮赘引上文,乃在于揭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果不考虑整体性的全域观照,一来宝玉会因仅截取场景之片段而误以为龄官画字是在东施效颦;二来宝玉因被花儿遮隐而被龄官局部误看成“姐姐”。宝玉和龄官的误读和互被误读,多多少少有点儿“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的意味。《清平乐·村居》长期以来被仅仅看成一首农村题材的词作,正当作如是观。所以考察这首词的情感倾向即《清平乐·村居》的本义,是需要把词作本身放置进整个“园林”即文本生成的历史场域进行整体观照的,如此方能还原出词作的彼时真义。辛弃疾同期所作《青玉案·元夕》③最为典型,如果考虑进“带湖”这个特定的文本生成场域,显然“嬉闹”“热闹”④的文本呈现场景,是为“别有寄托”⑤的局部场景呈现。赵仁珪先生谓“那人”,“一直是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站在一旁,冷眼地观看着这场人间的悲喜剧……正像梁令娴《艺蘅馆词选》所评:‘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⑥。正是把这首词置入文本生成场域解读出来的不易之论。
一、《清平乐·村居》中的“村景”书写
《清平乐·村居》毫无疑问是词人“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的心情呈现。它首先选取了一个限定性的静态视角,把视角限定在了“带湖的村居”:“村居”或为词人退隐处耳目可接之“村”,抑或是词人“闲”时游走置身其中之“村”。①如属前者则是词人司空见惯寻常“村居之景”;如属后者则是词人偶遇之村景,带有随意性和即时性特征,类似“记游”。当然,无论何种“村居之景”,都属“吴音”地域之景。因为是“村居”,“吴音”会更加醇厚也更难懂,“相对北方语言而言,吴语毕竟属不易听懂的南方方言。……郁达夫《出昱岭关,过三阳坑后,车道曲折,风景绝佳》诗有‘地传洙泗溪争出,俗近江淮语转蛮’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②。词人是操北音而身居“吴音”区者,故相对操“吴音”者而言是以他者身份而存在的,由此则可判定出作为“村居”书写者的词人和被书写者的“翁媪”“大儿”“中儿”“小儿”之间是互为他者的人物关系,这一点是以词人好似不经意间用到的一个“吴音”来作为明确标识的。③此关系的确立是理解该词中词人情感基调最为关键者,由此判定词人的视角是他者即作为一个旁观者去书写他者的日常村居生活——他者之于他者的关系,是“在一起”而又彼此疏离、“熟悉”却彼此陌生、生活在同一场域(时空)但彼此互不搭界的关系,故词中才会呈现“白发谁家翁媪”之平淡不经意且丝毫不须解答的语气。④不用“东家”“他家”“君家”⑤等具体标识语以确定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用有意无意的“谁家”来表示不确定亦无须确定的人物关系,这种心绪的书写与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中“人在何处”的表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漂泊无依与身在何处的情感体认在淡淡的似问非问、根本无须作答的疑问中表露无遗,不确定的语气表示出对当下的不确定;无须作答的语气显示出的是一种对当下无可无不可的不在意和漫无目的的浮泛。故由“谁家”判定出“村居之景”当是词人“逛逛”时偶遇之“景”,是属于“村居”时的“记游”遣怀类词作。⑥
“记游”题材中“村居”类作品,最经典的是陶渊明作于71岁前后的《桃花源记》,⑦“桃花源”是相对于其外部世界的一个封闭、独立、纯朴的理想之“村”,只不过“游”者是“武陵捕鱼人”,陶渊明用全知视角代为“记游”而已;“桃花源”亦“武陵捕鱼人”无意间的发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①。这点出“桃花源”不是“武陵人”自觉“寻”得的,而是“捕鱼”时“忽逢”的结果。故“桃花源”带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素,正是捕鱼人无目的与无指向性“逛逛”的产物,这亦可用作理解《清平乐·村居》中“村居”之“景”的出现。陶渊明把渔人“无意”间“发现”的“桃花源”记下来,就化渔人的“无意”为书写者的“有意”,即“记录”者是有某种意旨或情感需要表达或诉求的,这才是“记游”的目的所在,也是文本義所在。自然,“桃花源”只是存在于作者理想中的“太虚幻境”,类似于“记梦游”。同属陶渊明的作品,如果说《桃花源记》是理想中“村居”景象的“记录”,那么《归园田居》②则是“现实”中“村居”生活“真实”的呈现:其中场景有“草屋八九间”、有“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带月荷锄归”、有“道狭草木长”、有“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有“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有“稚子候檐隙”等诸多场景呈现。与《清平乐·村居》对读可以发现,辛词中景物并非完全出自词人眼见实景,而多出于心中臆想,类似于“桃花源”。之所以如此断言,在于陶渊明是作为辛弃疾带湖期间“借”以“湔洗”胸中块垒的精神导师而频频见于笔端者,如他在《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中明讲:“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既然带湖期间陶渊明于辛弃疾的生命存在如此重要,故辛彼时“学陶”倾向特别突出,词中涉及“陶”者共计92首,占辛词629首的1/7多;诗中涉及“陶”者共计19首,占辛诗1/8多。③综合考察带湖期间辛的“学陶”词,不难发现《清平乐·村居》中隐见着对“陶醉”的效仿——“醉里”是最明显的标识,如《念奴娇·赋雨岩》之“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生查子》“谁倾沧海珠”之“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等在在有“醉”。
“茅檐低小”,显然指“村”中“草屋”,更是辛弃疾意念中“学陶”的“身心归处”,所以会一再出现:《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有“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有“平章了,待十分佳处,著个茅亭”等。“茅檐”与“庐”“茅亭”“草屋”当同一意指;“溪上青青草”之“溪水”和“草”,在陶诗中是“清且浅”的“涧水”和田中“狭道”上的“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在陶诗中是“墟里人”,他们“时复”“批草来往”“但道桑麻长”;“醉里吴音”在陶诗中则是被化整为零具体真切地消解在“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中,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词只不过是浓缩版的陶诗而已。陶渊明是江州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市西)人④,九江在春秋时属吴之西境、楚之东境,因而有“吴头楚尾”⑤(辛弃疾词中亦如此称谓)之称,自然以“吴音”相互“道桑麻长”。辛弃疾作为一名操北音来旁听“吴音”者,自不如懂“吴音”的陶潜听“吴音”而知所谈内容即“桑麻”的具体真切,故辛对“吴音”“媚”的特点因陌生而感觉鲜明。辛词突出的是对“吴音”听觉的大致浮泛印象,陶诗则重在说话的具体真切内容。如此区别的原因是辛根本听不懂“吴语”故只能对“音”有个整体的印象而已。这也是陶诗中“我”与“人”可以有对话交流有情感互动而更显亲切自然醇厚之因,因为“我”是作为“村”景之一部分而存在,是与“村”景交融浑然为一体的。而辛弃疾则不能,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听去看,是外在于“村居”之景的一个他者,只能作看客来“闲看”“村景”,故“景”与词人之间没有互动,只有词人看“景”、听“景”和对“景”的感觉或想象,如此则词中之“景”与书写者之间是纯粹的客与主的关系,对“景”是客观地书写①:从“低小”“青青”等客观存在状态修饰词的运用即可看出词人情感是淡出而非融入的。他者的自我身份体认使得辛词中此类题材之作中均凸显着一个“我”,且“我”与“物”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隔阂,如《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中“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依然可以读出词中“我”横亘其间、不能浑然融“我”于“物”中。外在于“物”,以“我”役“物”,是辛词写景类词作中自我形象书写的显著特点。因此,辛词不能如陶渊明一样消泯物我内外之分而做到身心圆融无间、真正让身心安适地“归园田居”。当然,退居园田时陶渊明55岁且是主动归隐,此年作《归园田居》;②而辛弃疾则正当大有为之中年被动“村居”;故心态上陶平和而辛郁闷:平和则温煦自然,郁闷则块垒巉嵒——虽极力消泯却终有不平之气。块垒感来自人生处境的严重错位即自我身份体认与现实所赋予身份之间的巨大偏差,其《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曾托“雕弓”自喻:“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雕弓”“挂壁”非但“无用”,反有蛇影之嫌恶,这才是英雄辛弃疾对自我处境的一种悲剧性体认,也正是理解其写“村居”时心态的一把钥匙。
此心态下“游走”“村”中,自然是为消遣释闷,由此陶渊明及其诗文等构成了辛弃疾“村居”书写中隐约可见的一层意蕴背景:“大儿锄豆溪东”中“锄豆”场景,在陶诗中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儿正织鸡笼”之“鸡”,在陶诗中是“鸡鸣桑树巅”“双鸡招近局”;“亡赖”“卧剥莲蓬”之“小儿”,是陶诗中的“稚子”。“大儿”“中儿”“小儿”在陶渊明笔下,以“子侄辈”总称。在以上把辛词与陶诗对读后会发现:辛词中“景物”是借鉴、化用或者[檃] [急]栝陶诗相关题材所涉“景物”而成的结果,故是“记录”刹那间“心象”即心目中臆想“村居”图景的文字呈现,带有非常明显的自我告慰自我宽心自我和解的意味。或者可以直接说成是词人假装如陶渊明一样在“村居”以自欺欺人。如此断定的另一个依据是“大儿”“中儿”“小儿”的结构模式,不无借鉴乐府诗中频繁出现的“三妇艳”类书写模式。③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结论:辛弃疾“村居”仿效的是陶渊明的“园田居”;“村居”对“田园景观”的书写,又不无古乐府及南朝《三妇艳》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辛词从大的题材的选取、到具体的书写模式,都绝不是信手拈来眼前景的呈现(至多是由某点景物而勾起沉淀郁积于心的感、想或意念),是对其意念中“诗意栖居地”的书写:看似“实”写的“村”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意”中的存在而已。是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和“园田居”题材、意境和“景观”等相浑融叠加后的艺术呈现:“桃花源”中的“太虚幻境”和“园田居”的“日常生活”书写,故给人的艺术感觉是“真”的“闲适”;但却绝非生活中的真实:蛟龙只能作池中物——如果真能心平气和,则恐怕就不是辛弃疾了,也就不会有辛词了。充其量也只能是如吉光片羽一般稍纵即逝、转眼便消的“会心一笑”而已。如沧海一粟,我们不能因为漂着“一粟”而断定“沧海”可生“粟”,但“粟”确实存在于“沧海”中。辛弃疾情绪心境等变化,亦当作如是观。
二、《清平乐·村居》中的 “吴音”书写
《清平乐·村居》如此亦真亦幻、虚虚实实地呈现“村居”日常生活,著意当然在“归”字:不仅仅是为求得身“归”可力田,词人更在追求一种心“归”,即彻底忘掉“村”外世界的喧嚣纷扰,不再纠结于对既往自我“补天者”身份的定位与“整顿乾坤”使命的执着,当然不无对自己“犹欠封侯万里”深深的怅恨。①正视、接受、享受当下“力田者”身份一如陶渊明主动弃“樊笼”而“归反”自然,不再“以心为身役”而身心俱“闲”。如此,方是“归”的真境界,此当为词人出游“村”中且“如实记录”“村居之游”写出《清平乐·村居》之初衷。
“记游”类题材在辛词中有很多,词人有很多“记游”之作会谈到出游的缘起、目的和游途所见景物等,此类词有较固定的结构模式:“独处无聊”→出游“闲看”→倦怠→抒无聊之怀。这刚好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模式:出游本为散心释闷、而出游又往往增“情怀恶”而还。“恶情怀”为此圆形结构的衔接点:起端衔接着“无聊”出游;终端衔接着还归。很显然,《清平乐·村居》属于此类词作结构模式中的“出游‘闲看’” 阶段,故纯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和游赏者的视角来客观书写。其中的景和人,都是作为“静景”被书写的,此乃被大多读者以为词人闲适自得情怀的主要原因。
只有“醉里吴音相媚好”处于“动态”中,是词人综合听觉、视觉(“白发”)、嗅觉(酒味儿)甚至感觉(“相媚好”)而得到的一个“景点”。如无此句,整首词完全可作为一幅静态“村居图”来解读。②但“吴音”的出现,表明这确实是词人“村居”生活的“现实书写”而不是一幅写意画,只有真实“听到”“白发翁媪”的“声音”,才可作出“吴音”的判断——是吴人而非如己一样南渡的北人或者其他方言区的移居者。这一点特别地被提及,是词中之眼,毫无疑问是被“著意”凸显的一处“声景”。围绕此“声景”的,则是词中其他全部出于视觉的“静物”——即便有“声”亦无甚特异的泛泛写来:“溪水声”“锄豆声”“织鸡笼声”“剥莲蓬声”等,这些“声”是无南北即“吴音”北音之区分的。在这些无区分的“声景”中,更显出“吴音”的个别与真切,它的出现暗示出此词情感的沉郁,提醒着词人自我角色的体认和由此所带来的不快,从而带上了浓郁的辛弃疾个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弃疾是一个高明的词人,是真正着眼于日常生活书写的妙手:他抓住最能体现生活原汁原味儿的声景进行书写,借声景把时代、家国、悲欣等大题材与日常生活打并糅合,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写出南北天涯的故国之思与英雄失志只能做“闲人”的悲哀。而这悲哀却是分散化解在对“村居”之景淡淡的书写中,丝毫不被人察觉——虽然“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但“雨”“风”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此词中的“雨”“风”就集中体现在“吴音”上,它明确提醒着词人“江南游子”的身份。在辛弃疾之前,杜甫就已用方言婉述心曲了,如其《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前六句写“夜宴左氏庄”之“赏心乐事”,在“诗酒”欢景中,诗人“闻吴咏”而起“扁舟意”。洪业考此诗作于735年,时杜甫对前途正踌躇满志。③因为“苏州、杭州和附近州郡的吴方言与首都以及其他北方地区的方言有很大不同。因为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换句话说,能确切地了解并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所打动”④。洪业此段分析即着眼于吴方言陌生化的效应而对北人杜甫心绪的影响,因听懂了“吴咏”,会起范蠡之思。辛词中的书写亦是听“吴音”而起“意”,只不过是听不懂地道的吴地村言而无形中更“著意”于自己“客”的身份罢了。如非基于“听吴音”而“客意不忘”,此句完全可以化用陶渊明诗中“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句式进行转换——“醉里杂言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醉里桑麻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置换后毫无疑问艺术效果更佳,因为谈话内容具体而更显出村居人家日常生活的细节与亲切。但辛弃疾却用了浮泛化的“相媚好”来传达一种听觉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吴音”不是自己的乡土之音,客观上的陌生化和主观上的疏离感,使得词人不可能对“声音”进行具体化和细微化地书写。如此,则“吴音”是突兀地被矗立在“村居”这幅看起来颇为静谧闲适的写意画中,打破了“村居图”本该有的和谐与“土味儿”,从而成了窥知辛弃疾“北人”心态的一个窗口。
在陶渊明笔下,所“归园田”之“居”是具体而实在的,诗中所叙“归园田”后一系列活动与景物都是真实可感的。作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主动向田园回归追求身心与自然契合、诗意栖居于“草屋”者,陶渊明是第一人。①他笔下的“田园”景物、人、事等,是亲切自然的,与诗人无隔阂而浑融为一,即诗人自身亦是“田园”中“风景”;“田园”同时也成就了陶渊明,故渊明“和那片风景已经融为一体”。②当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渊明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的“故乡”印记,③故园所有的一切自然而然在眼中是亲切的、温煦的,作为诗人生命一部分的记忆又被唤醒、激活:景物如故,言语如故,日常如故。无有新奇和惊艳,只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与释然。视仕途为“樊笼”而“田园”是“家”,所以陶诗无有“吴音”之专门拈出作重点来凸显。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陶渊明诗没有专门点到“吴音”,是因其本属吴音区域之人,对吴音不需要“著意”(《桃花源记》中亦没有对“语音”的特别书写,尽管“桃花源”中所居者是“秦时人”);而辛弃疾是北人,对异地口音是相当敏感的,尤其是地地道道的“村居”者极少与外界接触交流语言少受其他方音影响而“土味儿”更浓更醇更地道,当然也更不容易被听懂。身处“村”这个小小的封闭环境中,词人与原生“村居”者之间,就被“吴音”这道无形的屏障隔开成两个世界:一南一北。听不懂却不可能做“宅男”,出去走走游游,“老夫静处看”亦是日常生活常态,是消磨打发时光的方法。因为是旁观者,是看客,词中便有了物我之间的壁垒隔阂感,是“独”处“众”中的孤独感与寂寞感(辛词多用“独”“众”相对照,如《临江仙》“即席和韩南涧韵”之“今宵成独醉,却笑众人醒”)。如果“吴音”真被置换成陶诗的表达,《清平乐·村居》就丝毫不会再有“客”意的有意无意地流露与呈现,才可以被理解成一首真正意義上的体现萧散自然闲适淳朴的田园词或者农村词,这正好说明了“吴音”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它使得整首词看似平淡却山高水深,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书写效果。
辛弃疾作为旁观者去写“村居”,与李清照“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一样,在借旁人之乐消遣打发自己的无聊和愁闷,“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④。“笑语”是别人的,和自己无关,因为自己是来自“中州”的“北人”。基于“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经验,词人无论如何不会真正做到忘了何处是故乡,相反更是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痛会再次被凸显,“它将个人的感伤情怀融入了北方(词中的‘中州’)沦陷的悲痛中,并且将这有限的个人主观情感升华为全体南渡北人困境的缩影。这些北人将在南方度过他们的余生,他们对于王朝的衰灭特别地敏感,并且渴望着回到他们年轻时在北宋首都开封城里的光辉岁月”①。“帘儿”隔开了两个世界:“帘儿”内是“北人”李清照漂泊没有情感皈依和乡关认同感的孤冷;“帘儿”外是他乡众人的热闹;在《青玉案·元夕》中的“那人”即词人“自身人格的一种艺术化的外现”,“在‘一夜鱼龙舞’的元宵佳节,只在‘灯火阑珊处’旁观的‘那人’,必定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清醒冷静之人,也显然是一个不满意那些国难当头时,还一味沉浸于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人。她必定是一个高标独立、自甘寂寞,不肯、也不屑于随俗合众、趋炎附势之人。也必定是一个饱经忧患、内心有着深刻创伤的人,她不无感慨地远观着眼前的喧闹,这种举动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易安居士所深慨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悲哀”②。“饱经忧患、内心有着深刻创伤的人”,正是辛词中自我形象书写中的应有之义。《清平乐·村居》传达的“真意”正如《青玉案·元夕》中“那人”之“意”。用“吴音”隔开了两个世界:身处“吴音”区,操北音的词人自然就是个别的孤独存在。语言是日常生活中最寻常使用的媒介,时时处处都在提醒着词人“外来者”的身份,辛弃疾南归时已20多岁,“乡音”即北音自是难改,外在的语言带来的是主客身份的体认和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如南宋朱彧讲过一则连“鸟音”也会家乡味儿很浓的故事:“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译者盛称其能言。试听之,能蕃语耳,嘲唽正似鳥声,可惜枉费教习,一笑而还之。”③“鸟声”尚带“乡音”,况人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道出“乡音”之于“离家”者实不啻于一张终身“名片”和“身份证”,它时时提醒着“客者”来自何处的“乡关”,唤起“思归”的乡愁。对于辛弃疾而言,“吴音”对应着 “江南游子”的客者身份,而“西北”才关联着自己梦牵魂绕的故都和乡关。南渡初衷乃在于要做一个“补天者”,如在《满江红》“健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中的慨然自陈:“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补天”不成却只能闲散地“村居”,“西北”自然会成为辛弃疾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痛源,而“村居”在辛弃疾这里毫无疑问会转化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闲适”。明乎此,会明了辛词中“西北”何以在在皆是:《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之“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之“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之“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之“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等。只有北复中原,词人才能实现“归”家之梦,才能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归园田居”。所以可以说,《清平乐·村居》中的“吴音”,其实正是辛弃疾“西北”情结的另一种深有意味的表达。
三、《清平乐·村居》中的“北人情结”书写
宋室南渡,南渡者往往以“南”“北”对举以书写家国情怀,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为李清照,其诗词文等多时代伤痕,身为女子能写出“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④“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愁易水寒”⑤“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⑥等大气磅礴、忠爱淋漓的作品,使其获得了崇高的人格魅力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效易安体”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在男性的词体文学创作中,有一种‘效易安体’的风尚,即在词中仿效李清照的悲痛。如果没有更早证据的话,这个风气产生于李清照逝世后不久,并在南宋一直持续着”⑦。如刘辰翁《永遇乐》“效易安体”小序曰:“余自乙亥(1275)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①作为李清照的同乡,辛弃疾亦有“效易安体”之作,如《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明说“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更有直接用易安词语者,如《西江月·渔父词》之“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镕金”和《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之“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等。对易安词的接受当很大程度上有“同乡”的情感认同和同为漂泊者的生命体验在内:李清照“北人”身份的自我认定,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其词《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之“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声景书写,②毫无疑问对此辛弃疾是感同身受的。辛词中的自我形象书写更凸显着“北人”情结,故以“北人”身份视听感受眼前景物,疏离感、外在感会比较明显表现出来:一是对客居处司空见惯之景新奇。二是客居处出现的曾司空见惯之景会唤起回忆、伤感、念远等“归”情即“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之感,如《满江红·题冷泉亭》和《鹧鸪天·送元济之归豫章》中就分别对“客”中与故乡相似之景所唤起的“客”者身份体认而怅恨不已:“恨此中、风月本吾家,今为客。”“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三是对声音的敏感。口音是最能引发漂泊者乡关之思的媒介,独处于他乡异地,周围尽是他乡之音声,羁旅感可想而知。四是对客居地景观着意书写:或是用“吴”去标识自己非“吴”的他者身份,如《六么令·再用前韵》之“吴侬江上,吴侬问我,一一烦君说”、《江神子·和陈仁和韵》之“吴霜应点鬓云斑”和《贺新郎·柳暗清波路》之“行到东吴春已暮”等;或是对带江南地域特征的景物多著意呈现,如《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之“莼鲈”、《满江红·暮春》之“刺桐花”、《最高楼》之 “鹧鸪吟”、《鹧鸪天·败棋赋梅雨》之“钩辀”“稏”“黄梅”等自然景物,因与北方显然不同,故词人会“偏惊物候新”,从而不由自主和故乡进行比照。于是“稻花”“蛙声”“溪”“莲蓬”“吴音”等带有强烈地域特征即江南水乡之景被辛弃疾这个“江南游子”敏锐地感知到、从而会再次唤起自己自北而南“客”者身份的体认。“傍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献愁供恨,玉簪罗髻”等直接就把江南景物与“愁”“恨”相联系,表明词人南渡后始终在情感上无法改变的北人情结。
《清平乐·村居》以“吴音”表述着北人“客居”者身份,因之对所寄居地之名物标识极其敏感,这一点正如苏轼被贬黄州所写《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亦因“赤壁”之地名而敏感故起思古之情,“孙权破曹操于赤壁,今沔、鄂间皆有之。黄州徙治黄冈,俯大江,与武昌县相对。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后人往往以此为赤壁。武昌寒溪,正孙氏故宫,东坡词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矶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记尔”③。此言诚为确论。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还要以之为赤壁,其实就是为抒发自我情怀而已。是否赤壁之战之赤壁对苏轼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赤壁便可联想到周瑜,借周瑜实现与自我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从而可以“适意”地面对当下。辛弃疾自然深谙苏词个中滋味儿,从他一再沿袭苏轼来写赤壁便可了然。如,《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之“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水调歌头》“自湖北漕移湖南,总领王、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之“序兰亭,歌赤壁,绣衣香”等,更有《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一词:“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杰。堪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世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歌应伴残月。”此词再次印证辛弃疾同苏轼一样,是拿自己寄居“客地”之名物来做文章的。同样写于闲居带湖时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词可以作为解读《清平乐·村居》词真实情感的一把钥匙:“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吴音”区的一家五口,各得其所、忙闲自得。闲人在享受着眼前的生活,自得其乐;忙人在为眼前的生活忙碌,无暇去乐。该忙的忙,该闲的闲——这“村居”所见分明在清楚地提示作为旁观者的词人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说老不老、说小不小;官而落职、农而官身;欲忙而处闲地、身闲而心不甘、思北归不得且只能“苟且”于南方等诸多现实问题。作为旁观者的正当大有可为之年的英雄辛弃疾,真的会觉得很惬意很闲适吗?英雄不在沙场而在田园,诚如《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所言,“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故园有而难归、英雄却做了词人这一角色的错位、南渡初衷与当下境遇的反差等现实纠结,此当是文本不言而在的一种内在意蕴。
综而论之,《清平乐·村居》中“吴音”意味着词人所处之场域,既非事实上的故园亦非情感上的故乡,而是外在于故乡的他者之乡或者可以称之为异乡的一种存在。特特拈出,使得这看似寻常的“吴音”成为客居者自我处境体认的日常提示媒介,即“吴音”成为一种外在于词人一切非故乡境遇的具象的象征,故而会在某种即时场景下有意无意形成与“乡音”相对照的鲜明的异质存在,对于情感、精神等内在会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词人会不由自主对自身当下的处境与身份进行重新审视和考量,这会再度确认当下无论身和心俱出于漂泊的生存状态。正是基于对这种漂泊的生命存在的明确体认,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位之悲和“补天者”成了“村居者”的错位之郁,才会借对“吴音”的敏感呈现出来——“醉里”在此或可理解为词人自身的生命状态更为恰切。一个日常借酒浇愁的愁者形象尚且因情感的疏离而生发身在异乡的漂泊感,何况非醉状态下的日常?所以说,《清平乐·村居》从文本呈现看确实是一首颇为闲适的农村词,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文字呈现而已。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文本的外在呈现而忽略文本的深刻意蕴,一如我们不能把休闲款式打扮者判定为休闲人一样。事实上,《清平乐·村居》如一面两面皆可照人的宝镜:正面照出的是闲适安乐的村居者词人,在悠然自得地游走欣赏村居的日常;背面照出的则是如白居易般“不堪司马闲冷”①者的的失意英雄辛弃疾,正借“吴音”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沉重的一声叹息。因为词人瞬间被“吴音”唤醒的“江南游子”心理,当如公元前11世纪的泰伯之奔吴地,“和他曾生活过的周地相比,眼前这个不同的地貌,不同的气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还是构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在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泰伯这个外来者将承受着巨大的文化冲击。……接受和融入的过程,同时也正是经受着巨大的文化冲击的过程。他们毕竟是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当他们审视着江南的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时,他们眼光中闪烁着的判断系统却始终是以他们在周人部落中所受到的中原文化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和编排为标准的”②。这种身在异乡为异客者有意无意会把他乡故乡进行对比的心理和情感应该是异代而相通的。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堪称宋词中和田园题材相关的典范之作,它的文字在轻灵跳脱中弥散着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儿: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織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辛弃疾笔下的吴地田园和日常,是如此自然亲切、醇厚馨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首词化版的《桃花源记》。正是基于如此的文本呈现,我们可以理解在既有的研究中,此词何以被简单作为一首萧散自然的农村词来理解:“这首词通过一户农家生活的侧面,反映出当时江西上饶一带农村的和平宁静生活情景。……是一幅和平安定的欢乐场景。”①此词“带有乡村生活牧歌情调”②;“写农村生活的欢乐美好”③等。但“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④。还当考虑第三个着眼点即具体作品产生的整体文学场域。《清平乐·村居》作于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期间,至晚当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⑤因此,用以上观点解读此词者亦觉困惑,谓“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南宋,这样的‘农家乐’是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的本质的”⑥;“我们应看到这并不是‘国脉危如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严重的南宋农村的普遍现实”。⑦联系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对此词进行文本细读,可读出词人“如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苍凉无奈:以北复中原为志慨然南渡的英雄辛弃疾,“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自当驰骋沙场而今却只能“村居”做一闲人,怀失位之沉郁是必然的。以此心态观照“村居”之景时心境如何,词中以“吴音”①进行了暗点,即点出词人是一个“外来者”即“北人”做了“江南游子”的自我身份体认。所以词中的“吴音”最为关键,镜照出词人南渡初衷不得、却又不得不“乐居”当下“村”中的人生困局。考察此词真实的情感,需把它置入带湖期间辛弃疾的创作场域中进行整体观照:因为单独拈出此词考察即就词论词,视阈的有限正如在园林中透过一扇窗儿、一页门扉或者一丛花儿等去看外在的世界一样,所看到的是被一扇窗儿、一页门扉或者一丛花儿等限定或隔断的景观。框界中的景物相比于框界外的园林,毫无疑问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会导致片段性或局部性的误读、漏读和失读。这种片段阅读或局部阅读的效应,正如《红楼梦》中隔着“蔷薇花架”互看的宝玉和龄官:宝玉因不及看到事件的后续发展差点儿误判龄官的痴情为东施效颦;而龄官则因蔷薇花枝叶的遮挡竟把宝玉误认成一个“丫头”:
(宝玉)刚到了蔷薇花架……果然架下那边有人。如今五月之际,那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时,宝玉便悄悄的隔着篱笆洞儿一看,只见一个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一面悄悄地流泪。宝玉心中想道:“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特,且更可厌了。”想毕,便要叫那女子说:“你不用跟着林姑娘学了。”话未出口,幸而再看时……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划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致雨。忽一阵凉风过了,刷刷地落下一阵雨来。宝玉……因此禁不住便说道:“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湿了。”那女孩子听说,倒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只见花外一个人叫他不要写了,下大雨了。一则宝玉脸面俊秀;二则花叶繁茂,上下俱被枝叶隐住,刚露着半边脸:那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再不想是宝玉,因笑道:“多谢姐姐提醒了我。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遮雨的?”②
不惮赘引上文,乃在于揭示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果不考虑整体性的全域观照,一来宝玉会因仅截取场景之片段而误以为龄官画字是在东施效颦;二来宝玉因被花儿遮隐而被龄官局部误看成“姐姐”。宝玉和龄官的误读和互被误读,多多少少有点儿“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的意味。《清平乐·村居》长期以来被仅仅看成一首农村题材的词作,正当作如是观。所以考察这首词的情感倾向即《清平乐·村居》的本义,是需要把词作本身放置进整个“园林”即文本生成的历史场域进行整体观照的,如此方能还原出词作的彼时真义。辛弃疾同期所作《青玉案·元夕》③最为典型,如果考虑进“带湖”这个特定的文本生成场域,显然“嬉闹”“热闹”④的文本呈现场景,是为“别有寄托”⑤的局部场景呈现。赵仁珪先生谓“那人”,“一直是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站在一旁,冷眼地观看着这场人间的悲喜剧……正像梁令娴《艺蘅馆词选》所评:‘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⑥。正是把这首词置入文本生成场域解读出来的不易之论。
一、《清平乐·村居》中的“村景”书写
《清平乐·村居》毫无疑问是词人“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的心情呈现。它首先选取了一个限定性的静态视角,把视角限定在了“带湖的村居”:“村居”或为词人退隐处耳目可接之“村”,抑或是词人“闲”时游走置身其中之“村”。①如属前者则是词人司空见惯寻常“村居之景”;如属后者则是词人偶遇之村景,带有随意性和即时性特征,类似“记游”。当然,无论何种“村居之景”,都属“吴音”地域之景。因为是“村居”,“吴音”会更加醇厚也更难懂,“相对北方语言而言,吴语毕竟属不易听懂的南方方言。……郁达夫《出昱岭关,过三阳坑后,车道曲折,风景绝佳》诗有‘地传洙泗溪争出,俗近江淮语转蛮’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②。词人是操北音而身居“吴音”区者,故相对操“吴音”者而言是以他者身份而存在的,由此则可判定出作为“村居”书写者的词人和被书写者的“翁媪”“大儿”“中儿”“小儿”之间是互为他者的人物关系,这一点是以词人好似不经意间用到的一个“吴音”来作为明确标识的。③此关系的确立是理解该词中词人情感基调最为关键者,由此判定词人的视角是他者即作为一个旁观者去书写他者的日常村居生活——他者之于他者的关系,是“在一起”而又彼此疏离、“熟悉”却彼此陌生、生活在同一场域(时空)但彼此互不搭界的关系,故词中才会呈现“白发谁家翁媪”之平淡不经意且丝毫不须解答的语气。④不用“东家”“他家”“君家”⑤等具体标识语以确定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用有意无意的“谁家”来表示不确定亦无须确定的人物关系,这种心绪的书写与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中“人在何处”的表达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漂泊无依与身在何处的情感体认在淡淡的似问非问、根本无须作答的疑问中表露无遗,不确定的语气表示出对当下的不确定;无须作答的语气显示出的是一种对当下无可无不可的不在意和漫无目的的浮泛。故由“谁家”判定出“村居之景”当是词人“逛逛”时偶遇之“景”,是属于“村居”时的“记游”遣怀类词作。⑥
“记游”题材中“村居”类作品,最经典的是陶渊明作于71岁前后的《桃花源记》,⑦“桃花源”是相对于其外部世界的一个封闭、独立、纯朴的理想之“村”,只不过“游”者是“武陵捕鱼人”,陶渊明用全知视角代为“记游”而已;“桃花源”亦“武陵捕鱼人”无意间的發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①。这点出“桃花源”不是“武陵人”自觉“寻”得的,而是“捕鱼”时“忽逢”的结果。故“桃花源”带了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因素,正是捕鱼人无目的与无指向性“逛逛”的产物,这亦可用作理解《清平乐·村居》中“村居”之“景”的出现。陶渊明把渔人“无意”间“发现”的“桃花源”记下来,就化渔人的“无意”为书写者的“有意”,即“记录”者是有某种意旨或情感需要表达或诉求的,这才是“记游”的目的所在,也是文本义所在。自然,“桃花源”只是存在于作者理想中的“太虚幻境”,类似于“记梦游”。同属陶渊明的作品,如果说《桃花源记》是理想中“村居”景象的“记录”,那么《归园田居》②则是“现实”中“村居”生活“真实”的呈现:其中场景有“草屋八九间”、有“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带月荷锄归”、有“道狭草木长”、有“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有“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有“稚子候檐隙”等诸多场景呈现。与《清平乐·村居》对读可以发现,辛词中景物并非完全出自词人眼见实景,而多出于心中臆想,类似于“桃花源”。之所以如此断言,在于陶渊明是作为辛弃疾带湖期间“借”以“湔洗”胸中块垒的精神导师而频频见于笔端者,如他在《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中明讲:“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既然带湖期间陶渊明于辛弃疾的生命存在如此重要,故辛彼时“学陶”倾向特别突出,词中涉及“陶”者共计92首,占辛词629首的1/7多;诗中涉及“陶”者共计19首,占辛诗1/8多。③综合考察带湖期间辛的“学陶”词,不难发现《清平乐·村居》中隐见着对“陶醉”的效仿——“醉里”是最明显的标识,如《念奴娇·赋雨岩》之“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生查子》“谁倾沧海珠”之“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等在在有“醉”。
“茅檐低小”,显然指“村”中“草屋”,更是辛弃疾意念中“学陶”的“身心归处”,所以会一再出现:《洞仙歌》“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有“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有“平章了,待十分佳处,著个茅亭”等。“茅檐”与“庐”“茅亭”“草屋”当同一意指;“溪上青青草”之“溪水”和“草”,在陶诗中是“清且浅”的“涧水”和田中“狭道”上的“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在陶诗中是“墟里人”,他们“时复”“批草来往”“但道桑麻长”;“醉里吴音”在陶诗中则是被化整为零具体真切地消解在“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中,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辛词只不过是浓缩版的陶诗而已。陶渊明是江州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市西)人④,九江在春秋时属吴之西境、楚之东境,因而有“吴头楚尾”⑤(辛弃疾词中亦如此称谓)之称,自然以“吴音”相互“道桑麻长”。辛弃疾作为一名操北音来旁听“吴音”者,自不如懂“吴音”的陶潜听“吴音”而知所谈内容即“桑麻”的具体真切,故辛对“吴音”“媚”的特点因陌生而感觉鲜明。辛词突出的是对“吴音”听觉的大致浮泛印象,陶诗则重在说话的具体真切内容。如此区别的原因是辛根本听不懂“吴语”故只能对“音”有个整体的印象而已。这也是陶诗中“我”与“人”可以有对话交流有情感互动而更显亲切自然醇厚之因,因为“我”是作为“村”景之一部分而存在,是与“村”景交融浑然为一体的。而辛弃疾则不能,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听去看,是外在于“村居”之景的一个他者,只能作看客来“闲看”“村景”,故“景”与词人之间没有互动,只有词人看“景”、听“景”和对“景”的感觉或想象,如此则词中之“景”与书写者之间是纯粹的客与主的关系,对“景”是客观地书写①:从“低小”“青青”等客观存在状态修饰词的运用即可看出词人情感是淡出而非融入的。他者的自我身份体认使得辛词中此类题材之作中均凸显着一个“我”,且“我”与“物”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隔阂,如《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中“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依然可以读出词中“我”横亘其间、不能浑然融“我”于“物”中。外在于“物”,以“我”役“物”,是辛词写景类词作中自我形象书写的显著特点。因此,辛词不能如陶渊明一样消泯物我内外之分而做到身心圆融无间、真正让身心安适地“归园田居”。当然,退居园田时陶渊明55岁且是主动归隐,此年作《归园田居》;②而辛弃疾则正当大有为之中年被动“村居”;故心态上陶平和而辛郁闷:平和则温煦自然,郁闷则块垒巉嵒——虽极力消泯却终有不平之气。块垒感来自人生处境的严重错位即自我身份体认与现实所赋予身份之间的巨大偏差,其《水调歌头》“寄我五云字”曾托“雕弓”自喻:“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雕弓”“挂壁”非但“无用”,反有蛇影之嫌恶,这才是英雄辛弃疾对自我处境的一种悲剧性体认,也正是理解其写“村居”时心态的一把钥匙。
此心态下“游走”“村”中,自然是为消遣释闷,由此陶渊明及其诗文等构成了辛弃疾“村居”书写中隐约可见的一层意蕴背景:“大儿锄豆溪东”中“锄豆”场景,在陶诗中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中儿正织鸡笼”之“鸡”,在陶诗中是“雞鸣桑树巅”“双鸡招近局”;“亡赖”“卧剥莲蓬”之“小儿”,是陶诗中的“稚子”。“大儿”“中儿”“小儿”在陶渊明笔下,以“子侄辈”总称。在以上把辛词与陶诗对读后会发现:辛词中“景物”是借鉴、化用或者[檃] [急]栝陶诗相关题材所涉“景物”而成的结果,故是“记录”刹那间“心象”即心目中臆想“村居”图景的文字呈现,带有非常明显的自我告慰自我宽心自我和解的意味。或者可以直接说成是词人假装如陶渊明一样在“村居”以自欺欺人。如此断定的另一个依据是“大儿”“中儿”“小儿”的结构模式,不无借鉴乐府诗中频繁出现的“三妇艳”类书写模式。③
综合以上分析得出结论:辛弃疾“村居”仿效的是陶渊明的“园田居”;“村居”对“田园景观”的书写,又不无古乐府及南朝《三妇艳》的影响因素。可以看出,辛词从大的题材的选取、到具体的书写模式,都绝不是信手拈来眼前景的呈现(至多是由某点景物而勾起沉淀郁积于心的感、想或意念),是对其意念中“诗意栖居地”的书写:看似“实”写的“村”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意”中的存在而已。是把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和“园田居”题材、意境和“景观”等相浑融叠加后的艺术呈现:“桃花源”中的“太虚幻境”和“园田居”的“日常生活”书写,故给人的艺术感觉是“真”的“闲适”;但却绝非生活中的真实:蛟龙只能作池中物——如果真能心平气和,则恐怕就不是辛弃疾了,也就不会有辛词了。充其量也只能是如吉光片羽一般稍纵即逝、转眼便消的“会心一笑”而已。如沧海一粟,我们不能因为漂着“一粟”而断定“沧海”可生“粟”,但“粟”确实存在于“沧海”中。辛弃疾情绪心境等变化,亦当作如是观。
二、《清平乐·村居》中的 “吴音”书写
《清平乐·村居》如此亦真亦幻、虚虚实实地呈现“村居”日常生活,著意当然在“归”字:不仅仅是为求得身“归”可力田,词人更在追求一种心“归”,即彻底忘掉“村”外世界的喧嚣纷扰,不再纠结于对既往自我“补天者”身份的定位与“整顿乾坤”使命的执着,当然不无对自己“犹欠封侯万里”深深的怅恨。①正视、接受、享受当下“力田者”身份一如陶渊明主动弃“樊笼”而“归反”自然,不再“以心为身役”而身心俱“闲”。如此,方是“归”的真境界,此当为词人出游“村”中且“如实记录”“村居之游”写出《清平乐·村居》之初衷。
“记游”类题材在辛词中有很多,词人有很多“记游”之作会谈到出游的缘起、目的和游途所见景物等,此类词有较固定的结构模式:“独处无聊”→出游“闲看”→倦怠→抒无聊之怀。这刚好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模式:出游本为散心释闷、而出游又往往增“情怀恶”而还。“恶情怀”为此圆形结构的衔接点:起端衔接着“无聊”出游;终端衔接着还归。很显然,《清平乐·村居》属于此类词作结构模式中的“出游‘闲看’” 阶段,故纯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和游赏者的视角来客观书写。其中的景和人,都是作为“静景”被书写的,此乃被大多读者以为词人闲适自得情怀的主要原因。
只有“醉里吴音相媚好”处于“动态”中,是词人综合听觉、视觉(“白发”)、嗅觉(酒味儿)甚至感觉(“相媚好”)而得到的一个“景点”。如无此句,整首词完全可作为一幅静态“村居图”来解读。②但“吴音”的出现,表明这确实是词人“村居”生活的“现实书写”而不是一幅写意画,只有真实“听到”“白发翁媪”的“声音”,才可作出“吴音”的判断——是吴人而非如己一样南渡的北人或者其他方言区的移居者。这一点特别地被提及,是词中之眼,毫无疑问是被“著意”凸显的一处“声景”。围绕此“声景”的,则是词中其他全部出于视觉的“静物”——即便有“声”亦无甚特异的泛泛写来:“溪水声”“锄豆声”“织鸡笼声”“剥莲蓬声”等,这些“声”是无南北即“吴音”北音之区分的。在这些无区分的“声景”中,更显出“吴音”的个别与真切,它的出现暗示出此词情感的沉郁,提醒着词人自我角色的体认和由此所带来的不快,从而带上了浓郁的辛弃疾个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从这个意义上说,辛弃疾是一个高明的词人,是真正着眼于日常生活书写的妙手:他抓住最能体现生活原汁原味儿的声景进行书写,借声景把时代、家国、悲欣等大题材与日常生活打并糅合,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写出南北天涯的故国之思与英雄失志只能做“闲人”的悲哀。而这悲哀却是分散化解在对“村居”之景淡淡的书写中,丝毫不被人察觉——虽然“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但“雨”“风”却是客观存在着的。此词中的“雨”“风”就集中体现在“吴音”上,它明确提醒着词人“江南游子”的身份。在辛弃疾之前,杜甫就已用方言婉述心曲了,如其《夜宴左氏庄》:“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前六句写“夜宴左氏庄”之“赏心乐事”,在“诗酒”欢景中,诗人“闻吴咏”而起“扁舟意”。洪业考此诗作于735年,时杜甫对前途正踌躇满志。③因为“苏州、杭州和附近州郡的吴方言与首都以及其他北方地区的方言有很大不同。因为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换句话说,能确切地了解并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所打动”④。洪业此段分析即着眼于吴方言陌生化的效应而对北人杜甫心绪的影响,因听懂了“吴咏”,会起范蠡之思。辛词中的书写亦是听“吴音”而起“意”,只不过是听不懂地道的吴地村言而无形中更“著意”于自己“客”的身份罢了。如非基于“听吴音”而“客意不忘”,此句完全可以化用陶渊明诗中“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句式进行转换——“醉里杂言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醉里桑麻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置换后毫无疑问艺术效果更佳,因为谈话内容具体而更显出村居人家日常生活的细节与亲切。但辛弃疾却用了浮泛化的“相媚好”来传达一种听觉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吴音”不是自己的乡土之音,客观上的陌生化和主观上的疏离感,使得词人不可能对“声音”进行具体化和细微化地书写。如此,则“吴音”是突兀地被矗立在“村居”这幅看起来颇为静谧闲适的写意画中,打破了“村居图”本该有的和谐与“土味儿”,从而成了窥知辛弃疾“北人”心态的一个窗口。
在陶渊明笔下,所“归园田”之“居”是具体而实在的,诗中所叙“归园田”后一系列活动与景物都是真实可感的。作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主动向田园回归追求身心与自然契合、诗意栖居于“草屋”者,陶渊明是第一人。①他笔下的“田园”景物、人、事等,是亲切自然的,与诗人无隔阂而浑融为一,即诗人自身亦是“田园”中“风景”;“田园”同时也成就了陶渊明,故渊明“和那片风景已经融为一体”。②当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渊明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的“故乡”印记,③故园所有的一切自然而然在眼中是亲切的、温煦的,作为诗人生命一部分的记忆又被唤醒、激活:景物如故,言语如故,日常如故。无有新奇和惊艳,只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与释然。视仕途为“樊笼”而“田园”是“家”,所以陶诗无有“吴音”之专门拈出作重点来凸显。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陶渊明诗没有专门点到“吴音”,是因其本属吴音区域之人,对吴音不需要“著意”(《桃花源记》中亦没有对“语音”的特别书写,尽管“桃花源”中所居者是“秦时人”);而辛弃疾是北人,对异地口音是相当敏感的,尤其是地地道道的“村居”者极少与外界接触交流语言少受其他方音影响而“土味儿”更浓更醇更地道,当然也更不容易被听懂。身处“村”这个小小的封闭环境中,词人与原生“村居”者之间,就被“吴音”这道无形的屏障隔开成两个世界:一南一北。听不懂却不可能做“宅男”,出去走走游游,“老夫静处看”亦是日常生活常态,是消磨打发时光的方法。因为是旁观者,是看客,词中便有了物我之间的壁垒隔阂感,是“独”处“众”中的孤独感与寂寞感(辛词多用“独”“众”相对照,如《临江仙》“即席和韩南涧韵”之“今宵成独醉,却笑众人醒”)。如果“吴音”真被置换成陶诗的表达,《清平乐·村居》就丝毫不会再有“客”意的有意无意地流露与呈现,才可以被理解成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体现萧散自然闲适淳朴的田园词或者农村词,这正好说明了“吴音”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它使得整首词看似平淡却山高水深,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书写效果。
辛弃疾作为旁观者去写“村居”,与李清照“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一样,在借旁人之乐消遣打发自己的无聊和愁闷,“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④。“笑语”是别人的,和自己无关,因为自己是来自“中州”的“北人”。基于“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生命体验与人生经验,词人无论如何不会真正做到忘了何处是故乡,相反更是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的痛会再次被凸显,“它将个人的感伤情怀融入了北方(词中的‘中州’)沦陷的悲痛中,并且将这有限的个人主观情感升华为全体南渡北人困境的缩影。这些北人将在南方度过他们的余生,他们对于王朝的衰灭特别地敏感,并且渴望着回到他们年轻时在北宋首都开封城里的光辉岁月”①。“帘儿”隔开了两个世界:“帘儿”内是“北人”李清照漂泊没有情感皈依和乡关认同感的孤冷;“帘儿”外是他乡众人的热闹;在《青玉案·元夕》中的“那人”即词人“自身人格的一种艺术化的外现”,“在‘一夜鱼龙舞’的元宵佳节,只在‘灯火阑珊处’旁观的‘那人’,必定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清醒冷静之人,也显然是一个不满意那些国难当头时,还一味沉浸于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人。她必定是一个高标独立、自甘寂寞,不肯、也不屑于随俗合众、趋炎附势之人。也必定是一个饱经忧患、内心有着深刻创伤的人,她不无感慨地远观着眼前的喧闹,这种举动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易安居士所深慨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悲哀”②。“饱经忧患、内心有着深刻创伤的人”,正是辛词中自我形象书写中的应有之义。《清平乐·村居》传达的“真意”正如《青玉案·元夕》中“那人”之“意”。用“吴音”隔开了两个世界:身处“吴音”区,操北音的词人自然就是个别的孤独存在。语言是日常生活中最寻常使用的媒介,时时处处都在提醒着词人“外来者”的身份,辛弃疾南归时已20多岁,“乡音”即北音自是难改,外在的语言带来的是主客身份的体认和由此产生的疏离感,如南宋朱彧讲过一则连“鸟音”也会家乡味儿很浓的故事:“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译者盛称其能言。试听之,能蕃语耳,嘲唽正似鸟声,可惜枉费教习,一笑而还之。”③“鸟声”尚带“乡音”,况人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道出“乡音”之于“离家”者实不啻于一张终身“名片”和“身份证”,它时时提醒着“客者”来自何处的“乡关”,唤起“思归”的乡愁。对于辛弃疾而言,“吴音”对应着 “江南游子”的客者身份,而“西北”才关联着自己梦牵魂绕的故都和鄉关。南渡初衷乃在于要做一个“补天者”,如在《满江红》“健康史致道留守席上赋”中的慨然自陈:“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补天”不成却只能闲散地“村居”,“西北”自然会成为辛弃疾生命中难以承受之痛源,而“村居”在辛弃疾这里毫无疑问会转化为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闲适”。明乎此,会明了辛词中“西北”何以在在皆是:《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之“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之“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声声慢》“滁州旅次登楼作和李清宇韵”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之“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之“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等。只有北复中原,词人才能实现“归”家之梦,才能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归园田居”。所以可以说,《清平乐·村居》中的“吴音”,其实正是辛弃疾“西北”情结的另一种深有意味的表达。
三、《清平乐·村居》中的“北人情结”书写
宋室南渡,南渡者往往以“南”“北”对举以书写家国情怀,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当为李清照,其诗词文等多时代伤痕,身为女子能写出“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④“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愁易水寒”⑤“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⑥等大气磅礴、忠爱淋漓的作品,使其获得了崇高的人格魅力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共鸣。“效易安体”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在男性的词体文学创作中,有一种‘效易安体’的风尚,即在词中仿效李清照的悲痛。如果没有更早证据的话,这个风气产生于李清照逝世后不久,并在南宋一直持續着”⑦。如刘辰翁《永遇乐》“效易安体”小序曰:“余自乙亥(1275)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①作为李清照的同乡,辛弃疾亦有“效易安体”之作,如《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明说“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更有直接用易安词语者,如《西江月·渔父词》之“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镕金”和《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之“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等。对易安词的接受当很大程度上有“同乡”的情感认同和同为漂泊者的生命体验在内:李清照“北人”身份的自我认定,最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其词《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之“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的声景书写,②毫无疑问对此辛弃疾是感同身受的。辛词中的自我形象书写更凸显着“北人”情结,故以“北人”身份视听感受眼前景物,疏离感、外在感会比较明显表现出来:一是对客居处司空见惯之景新奇。二是客居处出现的曾司空见惯之景会唤起回忆、伤感、念远等“归”情即“异乡物态与人殊,惟有东风旧相识”之感,如《满江红·题冷泉亭》和《鹧鸪天·送元济之归豫章》中就分别对“客”中与故乡相似之景所唤起的“客”者身份体认而怅恨不已:“恨此中、风月本吾家,今为客。”“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三是对声音的敏感。口音是最能引发漂泊者乡关之思的媒介,独处于他乡异地,周围尽是他乡之音声,羁旅感可想而知。四是对客居地景观着意书写:或是用“吴”去标识自己非“吴”的他者身份,如《六么令·再用前韵》之“吴侬江上,吴侬问我,一一烦君说”、《江神子·和陈仁和韵》之“吴霜应点鬓云斑”和《贺新郎·柳暗清波路》之“行到东吴春已暮”等;或是对带江南地域特征的景物多著意呈现,如《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之“莼鲈”、《满江红·暮春》之“刺桐花”、《最高楼》之 “鹧鸪吟”、《鹧鸪天·败棋赋梅雨》之“钩辀”“稏”“黄梅”等自然景物,因与北方显然不同,故词人会“偏惊物候新”,从而不由自主和故乡进行比照。于是“稻花”“蛙声”“溪”“莲蓬”“吴音”等带有强烈地域特征即江南水乡之景被辛弃疾这个“江南游子”敏锐地感知到、从而会再次唤起自己自北而南“客”者身份的体认。“傍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献愁供恨,玉簪罗髻”等直接就把江南景物与“愁”“恨”相联系,表明词人南渡后始终在情感上无法改变的北人情结。
《清平乐·村居》以“吴音”表述着北人“客居”者身份,因之对所寄居地之名物标识极其敏感,这一点正如苏轼被贬黄州所写《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亦因“赤壁”之地名而敏感故起思古之情,“孙权破曹操于赤壁,今沔、鄂间皆有之。黄州徙治黄冈,俯大江,与武昌县相对。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后人往往以此为赤壁。武昌寒溪,正孙氏故宫,东坡词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矶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记尔”③。此言诚为确论。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还要以之为赤壁,其实就是为抒发自我情怀而已。是否赤壁之战之赤壁对苏轼而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赤壁便可联想到周瑜,借周瑜实现与自我某种程度上的和解,从而可以“适意”地面对当下。辛弃疾自然深谙苏词个中滋味儿,从他一再沿袭苏轼来写赤壁便可了然。如,《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之“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水调歌头》“自湖北漕移湖南,总领王、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之“序兰亭,歌赤壁,绣衣香”等,更有《念奴娇·用东坡赤壁韵》一词:“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之杰。堪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世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歌应伴残月。”此词再次印证辛弃疾同苏轼一样,是拿自己寄居“客地”之名物来做文章的。同样写于闲居带湖时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词可以作为解读《清平乐·村居》词真实情感的一把钥匙:“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吴音”区的一家五口,各得其所、忙闲自得。闲人在享受着眼前的生活,自得其乐;忙人在为眼前的生活忙碌,无暇去乐。该忙的忙,该闲的闲——这“村居”所见分明在清楚地提示作为旁观者的词人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说老不老、说小不小;官而落职、农而官身;欲忙而处闲地、身闲而心不甘、思北归不得且只能“苟且”于南方等诸多现实问题。作为旁观者的正当大有可为之年的英雄辛弃疾,真的会觉得很惬意很闲适吗?英雄不在沙场而在田园,诚如《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所言,“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故园有而难归、英雄却做了词人这一角色的错位、南渡初衷与当下境遇的反差等现实纠结,此当是文本不言而在的一种内在意蕴。
综而论之,《清平乐·村居》中“吴音”意味着词人所处之场域,既非事实上的故园亦非情感上的故乡,而是外在于故乡的他者之乡或者可以称之为异乡的一种存在。特特拈出,使得这看似寻常的“吴音”成为客居者自我处境体认的日常提示媒介,即“吴音”成为一种外在于词人一切非故乡境遇的具象的象征,故而会在某种即时场景下有意无意形成与“乡音”相对照的鲜明的异质存在,对于情感、精神等内在会自然而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词人会不由自主对自身当下的处境与身份进行重新审视和考量,这会再度确认当下无论身和心俱出于漂泊的生存状态。正是基于对这种漂泊的生命存在的明确体认,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位之悲和“补天者”成了“村居者”的错位之郁,才会借对“吴音”的敏感呈现出来——“醉里”在此或可理解为词人自身的生命状态更为恰切。一个日常借酒浇愁的愁者形象尚且因情感的疏离而生发身在异乡的漂泊感,何况非醉状态下的日常?所以说,《清平乐·村居》从文本呈现看确实是一首颇为闲适的农村词,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文字呈现而已。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文本的外在呈现而忽略文本的深刻意蕴,一如我们不能把休闲款式打扮者判定为休闲人一样。事实上,《清平乐·村居》如一面两面皆可照人的宝镜:正面照出的是闲适安乐的村居者词人,在悠然自得地游走欣赏村居的日常;背面照出的则是如白居易般“不堪司马闲冷”①者的的失意英雄辛弃疾,正借“吴音”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沉重的一声叹息。因为词人瞬间被“吴音”唤醒的“江南游子”心理,当如公元前11世纪的泰伯之奔吴地,“和他曾生活过的周地相比,眼前这个不同的地貌,不同的气候,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还是构成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空间。在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泰伯这个外来者将承受着巨大的文化冲击。……接受和融入的过程,同时也正是经受着巨大的文化冲击的过程。他们毕竟是在另一个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当他们审视着江南的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时,他们眼光中闪烁着的判断系统却始终是以他们在周人部落中所受到的中原文化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和编排为标准的”②。这种身在异乡为异客者有意无意会把他乡故乡进行对比的心理和情感应该是异代而相通的。
① 艾治平:《宋词的花朵——宋词名篇赏析》,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② 张毅主编:《词林观止》,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6页。
③ 郭彦全:《历代词今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④ 梁启超:《陶渊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编《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6页。
⑤ 详见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清平乐·村居》“编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1页。本文所引辛词均出自此书,为避繁琐,恕不一一出注。
⑥ 胡云翼选注:《唐宋词一百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第116页。
⑦ 艾治平:《宋词的花朵——宋词名篇赏析》,第305页。
① 汲古阁影宋钞本《稼轩词》甲集作“醉里蛮音相媚好”。“蛮音”相对于“吴音”来讲,在情感上的拒斥感更加强烈和明显。此词有浓郁的地域区别色彩,如《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武松刺配孟州寻衅蒋门神时,酒店的酒保道:“眼见得是个外乡来的蛮子”(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82页)。另,“蛮”在古代话语系统中亦自谦僻远之地,如《燕丹子》卷中太子丹对田光自谦道:“傅不以蛮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来降弊邑。今燕国僻在北陲,比于蛮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辛弃疾带湖期间词也多用到“蛮”字,如《满江红·送汤朝美司谏自便归金坛》之“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之“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等。详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第116页、第101页。
② 曹雪芹、高鹗著,俞平伯校,启功注:《红楼梦》第三十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324—325页。
③ 邓广铭笺注《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系此词作于带湖期间,第188-189页。
④ 赵仁珪:《互文的妙用——辛弃疾〈青玉案〉新解》,“经过一夜的嬉闹之后”“在元宵佳节这一天……在热闹了一夜之后”。《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⑤ 胡云翼选注:《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第285页。
⑥ 赵仁珪:《互文的妙用——辛弃疾〈青玉案〉新解》,《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① 词中的时、地、人等都是浮泛的,此或为难以考定此词写于何年的主要原因。
② 吴恩培:《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③ 文学中以语音标识情感的很多,如沈亚之《秦梦记》记作者“春时,昼梦入秦”,娶秦公主弄玉。后弄玉丧,亚之将东归,“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借“秦声”点亚之非“秦”人之意。见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197页。
④ 俞平伯先生慧眼独具,在其《唐宋词选释》中,《清平乐·村居》是——“白发谁家翁媪。”即句末标点用的是句号;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则用的是——“白发谁家翁媪?”标点用的是问号。见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
⑤ 如《水调歌头·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之“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之“只做个、五湖范蠡。是则是、一般弄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水调歌头·文字觑天巧》之“君家风月几许,白鸟去悠悠。”分别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之第128页、第118页、第115页。
⑥ 《红楼梦》五十八回“杏子阴假凤泣虚凰”可作为参照理解:宝玉病未大愈,“饭后发倦”,袭人因说:“天气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丢下粥碗就睡,存在心里。”“宝玉听说,只得拄了一拐杖,靸着鞋,步出院外。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歍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的,种藕的。湘云、香菱、宝琴与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们取乐。”以宝玉的视角写了大观园中的“繁忙热闹”——其中有湘云等在观“忙碌”者以“取乐”之“景”,“繁忙热闹”的人与事等“景”都是宝玉“逛逛”消遣时不经意所见者,宝玉“逛逛”的初衷、着装、神态、意绪等都透着懒、倦与病,故丝毫不关心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故可以说不是宝玉在“观景”,而是“景”“侵入”宝玉的视线、耳膜,正如温庭筠《织锦词》所写之“叮咚细漏侵琼瑟”。《清平乐·村居》之“村居”书写者心态意绪,亦当作如是解。详见《红楼梦》,上册,第632页。
⑦ 袁行霈:《陶渊明年谱简编》:“宋武帝永初三年壬戌(四二二)陶渊明七十一岁 渊明在家隐居。《桃花源记并诗》约作于是年。”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63页。
① 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卷第六,第479页。
② 《陶渊明作品系年一览》系此诗作年在“晋义熙二年,四〇六,五十五岁”;系《归去来兮辞》在“晋义熙一年,四〇五,五十四岁”,第868页。
③ 王雨婷:《论辛弃疾对陶渊明的接受》,该文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弃疾诗文笺注》统计得出数字,详见《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④ 袁行霈:《陶渊明年谱简编》,第845页。
⑤ 据吴恩培《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吴’之概念的地理内涵,三千年基本未有位移大变”“‘吴头楚尾’,其‘楚’字,则是指古豫章(今江西省)一带。春秋时,这里是吴、楚交界。因其地位于春秋吴的上游,楚的下游,如首尾相衔接,故有此称了。同样,南宋时曾撰有吴地史志《吴郡志》的诗人范成大,他的《题岳麓道乡台》诗:‘山外江水黄,江外满城绿……长烟贯楚尾,远势带吴蜀’句,这里的‘楚’,也是指的江西境内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第690页。)
① 俞平伯先生谓“本篇客观地写农村景象”,“客观”可谓的见。见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下卷,第193页。
② 袁行霈笺注:《陶渊明集笺注》, 第858页。
③ 俞平伯先生谓:“虽似用口语写实,但大儿、中儿、小儿云云,盖从汉乐府《相逢行》‘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化出,只易三女为三男耳。末句于剥莲蓬者一‘看’字,得乐府‘无所为’的神理。”见俞平伯《唐宋词选释》下卷,第193页。
① “是梦他松后追轩冕,是化为鹤后去山林。对西风,直怅望,到如今。”(《最高楼》“相思苦”)则直接道出对“归”的困惑。
② “这首词环境和人物的搭配是一幅极匀称自然的图画。老和小写得最生动。”见胡云翼选注《宋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285页;“轻笔淡墨,宛然一幅农家生活素描,令人赏心悦目。”见叶嘉莹主编《辛弃疾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6年版,第463页。
③ 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④ 洪业谓:“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暮春,它将变得极富意味。”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4—25页。
① 葛晓音论及陶渊明田园诗所达到的高度及其意义时认为,“陶渊明的山水诗创立了中国文人理想的田园模式,其性质与《诗经》中的田园题材迥然有别”。见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② 袁行霈:《陶渊明与魏晋风流》,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页。
③ 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渊明出生时浔阳县尚未划入柴桑县,柴桑又不为陶渊明本人及颜《诔》言及,则渊明之籍贯定为江州浔阳郡浔阳县为宜。浔阳县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柴桑县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至于其居处,则不止一处……其居处与田产是否均在浔阳县,抑或有在柴桑县乃至更远者,均未详。”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页。
④ 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① [美]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52页。
② 赵仁珪:《互文的妙用——辛弃疾〈青玉案〉新解》,《文史知识》1996年第4期。
③ 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州可谈》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7页。
④ 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卷二,第256页。
⑤ 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卷二,第258页。
⑥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其一,见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卷二,第220页。
⑦ [美]艾朗诺:《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第179页。
① 唐圭璋等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五册,第4087页。
② 李清照此词为其定居杭州后人生末年所作。如此论确,更可证“北人”是词人终其一生固守的自我身份界定。详参叶嘉莹主编《李清照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252页。
③ 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州可谈》卷二,第140页。
① 陆游谓:“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焕,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亦见其乐尔。可怜哉!”见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8页。
② 吴恩培著:《勾吴文化的现代阐释》,第41—42頁。
作者简介:郑慧霞,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国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