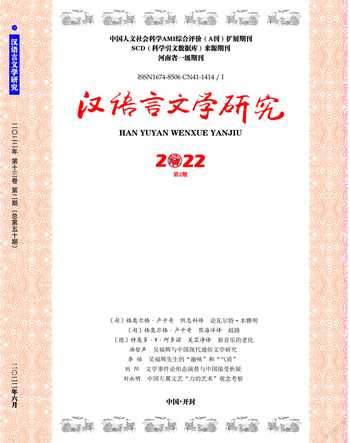张恩和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论的价值与启示
2022-07-11李斌
张恩和是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突出代表,他做过郭沫若、郁达夫、郭小川等作家研究,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协助过唐弢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书法方面造诣较深。在这些研究工作中,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鲁迅研究上,他的成名作是《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1963),晚年最看重的论文是《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1985)和《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2002),将其作为自选集《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的前两篇。
在《鲁迅——伟大的反封建主义的战士》中,张恩和认为:“鲁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这正是中国人民同压迫自己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作殊死搏斗的年代。封建主义以其特有的顽固性拼命挣扎,变换各种形式保护自己,对人民进行疯狂反扑。鲁迅始终坚定地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坚强的意志,通过深刻的道理和血淋淋的事实,揭穿封建主义的罪恶本质。可以说,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一生都没有停息,成为他十分重要的战斗业绩。”张恩和具体分析了鲁迅在留学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及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并归纳出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四个特点:深刻性、人民性、彻底性、灵活性。首先,“鲁迅着眼的是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它的思想体系。他不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枝一节,而是抓住根本。这表现出他斗争的深刻性”。其次,“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特别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妇孺等弱者,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他始终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再次,“鲁迅反对封建主义,具有坚定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最后,“鲁迅反对封建主义,十分注意斗争的方法和策略”①。在《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中,张恩和认为:“鲁迅自始至终对封建社会持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一生战斗最突出、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坚决彻底、锲而不舍的揭露和抨击封建主义。”他论证道,鲁迅对封建主义的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封建社会的核心是专制”“封建社会的命脉是等级制度”“封建社会的要害是家族制度”。②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张恩和再次表示:“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斗争;对封建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也是他最重要的功绩。”③
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课题,在学界算不上新鲜,张恩和先生孜孜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究竟何在呢?
一
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论述,瞿秋白、毛泽东早就提出来了。瞿秋白认为:“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①。但瞿秋白、毛泽东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论述,相当长时期内没有在学界得到系统的展开。
改革开放前,鲁迅研究界的主要代表是陈涌,其主要观点体现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1954)中。尽管陈涌也提到了鲁迅的反封建,但他主要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角度分析鲁迅的小说。他将鲁迅定位为“真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他把自己的全部创作活动都集中到找寻中国向前发展的道路这个中心点。人民被压迫的根源是什么?什么力量可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敌人,可以解脱人民的灾难和痛苦”。陈涌逐一分析了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关于资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几种社会力量的表现后提出:“鲁迅在‘五四’和以后一个时候以其深刻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力量真实地表现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的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农民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的真正动力,但其具有自身的弱点。而知识分子呢?他们许多人都是聪明、正直的,是每一个革命时期首先觉悟的分子,但当他们对现实还没有明确坚实的认识,当他们把自己‘孤独’起来的时候,他们是软弱无力,毫无作为的。很显然,鲁迅需要找寻一种比上面这几个阶级更加坚强的力量,能够把上面这一切力量都团聚起来,带动起来的力量,即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力量,鲁迅在整个写作《呐喊》与《彷徨》的时期,还没有找到,没有认识到。”②显然,陈涌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尤其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以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理论指导,带着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目的,展开了对鲁迅小说的讨论。陈涌的讨论有理论深度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代表了改革开放前鲁迅研究的最高成就。由于陈涌所处的时代要求的不同,他没有强调鲁迅的“反封建主义”的一面。
王富仁曾经指出:“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初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上取得的最高成果。”这实际上指的就是陈涌的鲁迅研究。王富仁对此是不满足的:“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和评定这个独立的个性。”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综论》(1986)一书中,王富仁区分了现代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相对于西方近代社会发展具有逆向性,西方社会是先有了資产阶级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然后才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中国社会是先有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但封建思想在社会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革命者对于封建思想的清除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视,因此鲁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王富仁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认为《呐喊》《彷徨》的“主要思想意义、它们的最有价值、最具特色的思想意义”在于“它们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必须有一个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它的重点应放在束缚人民群众思想最厉害、并给他们的思想发展带来极大损伤的封建等级观念和残酷、虚伪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上”③。
关于陈涌和王富仁在鲁迅研究上的主要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对鲁迅笔下的阿Q和知识分子的不同分析做一具体观察。陈涌虽然指出了阿Q的缺点,也强调阿Q的革命性,“农民,在鲁迅的实际表现里,证明是中国革命在农村的真正的动力”④,即分析作为农民的阿Q是否能够成为政治革命的动力。而王富仁强调的是阿Q身上所具有的封建思想尤其是封建等级观念,强调这些观念对于农民精神上的摧残,因为农民是需要启蒙的对象。关于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子君、涓生等知识分子,陈涌认为鲁迅以他的艺术表现证实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关于未与人民群众结合之前的知识分子的状态的分析,“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①。但王富仁认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力量,“鲁迅是把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当作当时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主要积极力量加以表现的”②。也就是说,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说,陈涌认为阿Q是积极力量,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说,王富仁认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才是积极的力量。
那么,同样是讨论鲁迅的“反封建”,王富仁和张恩和在学术观点上的联系和区别何在呢?
张恩和最初的论文《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关于狂人形象的问题,但也强调了《狂人日记》的“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③。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发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后,张恩和写作了《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作为呼应,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第一,王富仁讲鲁迅的反封建,重点只讲了鲁迅的《呐喊》《彷徨》,但张恩和明确将鲁迅的“反封建”作为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红线。他认为,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就“在思想上明确地向封建主义的总体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锐气不但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是愈战愈强”④。第二,王富仁讲的是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张恩和讲的是反“封建主义”。在张恩和笔下,“封建主义”的涵义要比“封建思想”广,既包括了“封建思想”,也包括经济剥削、等级制度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从这两点来看,张恩和不仅声援了王富仁,而且发展了王富仁的论述。这应该就是张恩和的鲁迅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毋庸讳言,张恩和在论述的深刻性、分析的细腻性上不及王富仁。客观地讲,关于鲁迅“反封建”的论述,王富仁的学术成果更有标杆意义。
二
鲁迅研究历来是时代思潮的晴雨表,是学术和时代紧密联系的枢纽。张恩和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研究,王富仁关于鲁迅“反封建思想”的论述,在陈涌之外另辟蹊径,开辟了鲁迅研究的另一个时代,这不仅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1977年之后,中国社会在反思“文革”十年时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文史哲领域在这次反思中充当了排头兵,《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批判封建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不懈》》(《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刘再复《封建主义在文艺领域里的复辟——论“四人帮”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的封建性》(《学术月刊》1979年第1期)、任继愈《封建主义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敌》(《山西日报》1979年10月22日)等文章是典型代表。在这些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⑤
邓小平和当时中国社会舆论中所谓的“封建主义”,显然既非西周的封邦建国中的“封建”,也不完全是西欧feudalism的汉译,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中的“封建”。1928年,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土地制度、半殖民地国家。192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28号》,认为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同时爆发社会史大论战,参与论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尽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止时间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经典论断,一致认为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并且在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一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看来,封建社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曾经历的,介于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其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关于封建主义和中国革命之关系的经典表述,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的。1939 年10月4日,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①不久,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②毛泽东的这些经典表述,历来是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动力论述的理论依据。40余年之后,邓小平根据此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变化了的现实和社会主要矛盾,对中国当时的时代任务做出了新判断:封建制度虽然被推翻了,但是封建思想还存在残余,肃清这一残余是当时的重要任务。邓小平这一判断得到学术界的衷心拥护,文史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将对“封建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学术课题。
尽管邓小平强调:“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③但学界集中火力研究和批判的却是“封建主义”。任继愈在邓小平讲话一个月后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正是这个封建历史残痕的大暴露。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在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后就心满意足了,对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这不是哪一个人认识不足,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广大群众,包括我们党内干部都对封建主义势力之大认识不足。这样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要对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敢于斗争,彻底决裂。这样我们中国才有希望,我们的‘四化’才有希望。”④1980年12月,天津史学会召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报道以《继续开展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为题发表。对“封建主义”的研究和批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热点,其中影响较大和比较典型的是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篇文章认为,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相得益彰的大好局面并未持久,从五卅运动到抗日战争,“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1949年之后,“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约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特别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①。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还是任继愈、李泽厚等著名学者,都将“文革”期间的一系列做法归结为“封建主义”的沉渣泛起,从而将“封建主义”作为改革开放的绊脚石和当时革命的头号对象,鲜明地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时代任务。
不再斗资批修,而是清除封建主义残余,为改革开放扫清障碍,这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转换。这一转换是一定程度的“倒退”,即重新退回到五四,重新开展启蒙,提倡个性解放,以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在半个多世纪前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一“倒退”从某种角度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因而得到了上下一致的拥护。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开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学术和政治高度默契的蜜月期。“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政治家发出的号召,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和积极响应,成为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界最为突出的时代主题,这正是学术和政治高度默契的重要表现。
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论述,在王富仁、张恩和之前,李希凡《“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封建的檄文——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小说“呐喊”的主题》(1978年)、平心收录在《人民文豪鲁迅》中的《论鲁迅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1981年)等文章都做了较有深度的讨论。这形成了鲁迅研究领域中较为集中的关于“反封建主义”的论述,这些论述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对此,张恩和是自觉的。他在《鲁迅——伟大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中明确提出:“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特别长,为世界所罕见;封建制度和它的思想体系发展得最为完备,十分顽固;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民族矛盾有时上升到主要地位,往往掩盖或冲淡了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致使封建主义得以避开斗争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这就使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十分艰巨,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这和任继愈、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张恩和处于当时的时代氛围之中,和时代主题保持了高度契合。在文章结尾,张恩和点出了这一研究的现实意义:“今天,全国人民正在全力以赴为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毒还是我们十分重要、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更需要认真学习和继承鲁迅反对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和斗争艺术,把它们化为我们的血肉,化作我们当前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伟大动力。”②这体现了张恩和的鲁迅研究和时代的密切关系以及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三
尽管王信认为王富仁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③,但在汪晖看来,王富仁的研究和陈涌的研究是相似的,都是“镜子”理论。“根据研究者对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矛盾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根据他们对鲁迅及新文化运动者观察社会的独特角度的各自认识,《呐喊》《彷徨》的史诗性质或整体意义经历了一个从‘中国革命的镜子’(主要指政治革命和阶级关系变动)到‘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的理解过程。”汪晖认为,他们的共同缺点在于“把鲁迅小说的整体性看作是文学反映对象的整体性,即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不是从内部世界的联系中寻找联结这些不同主题和题材小说的纽带”。所以,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中致力于探寻《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线索”和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①从而提出了鲁迅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自我意识,并开启了影响至今的关于鲁迅的内面、主体研究的新的鲁迅研究局面。当然,汪晖选择以《呐喊》《彷徨》去讨论鲁迅的内面和主体,有很多捉襟见肘之处,更适合讨论鲁迅内面和主体的文本是《野草》。此后,《野草》研究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一直延续至今,这实际上都是处于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延长线上。当然,这也不排除日本鲁迅研究尤其是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的影响。
《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所开启的关于鲁迅的主体和内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鲁迅“反封建主义”之后的题中之义。“反封建主义”本身是启蒙的话题,在启蒙之后,个体、内面当然就凸显出来了。问题不在于应不应该凸显,而在于在什么层面凸显。汪晖之后的许多学者,逐渐将这一研究固化,并倾注了鲜明的价值判断,从而形成了与陈涌、王富仁、张恩和的鲁迅研究的断裂,这是后话。对于《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所开启的鲁迅研究这一新趋势,张恩和并没有跟进,而是继续他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论述,这一观点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而作为鲁迅“反封建”论述的代表性学者王富仁,早已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结束而不再提及这一论述了。故而,张恩和的坚守,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张恩和处于以陈涌和王富仁为代表的鲁迅研究时代,那个时代的鲁迅研究和现在的鲁迅研究相比有三个特点:第一,其论述都建立在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经典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阶段、革命对象、革命任务的分析的基础之上,都自觉使用了“封建社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这样的话语体系。第二,在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上,他们都延续了瞿秋白等人的理论,认为鲁迅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而对鲁迅的评价,他们遵循毛泽东的经典论述。第三,都自觉和时代主题保持一致,甚至成为时代思潮的前沿,比如陈涌从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角度研究鲁迅,张恩和、王富仁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角度研究鲁迅,汪晖从“主观精神结构”的角度研究鲁迅,都是和当时的时代主题、解决当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高度契合的。有了这些特点,陈涌、张恩和、王富仁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于他们,当下很多鲁迅研究者刻意回避毛泽东、瞿秋白关于鲁迅的论述,刻意回避时代所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这些回避导致了很多研究成果割断历史、割断现实、自说自话,从而质量不高。这或许就是张恩和关于鲁迅“反封建主义”的研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① 张恩和:《鲁迅——伟大的反封建主义的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② 张恩和:《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③ 黄海飞:《鱼与熊掌 何妨兼得——张恩和教授访谈录》,《创作评谭》2019年第1期。
④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698頁。
② 陈涌:《鲁迅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7、72页。
③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④ 陈涌:《鲁迅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① 陈涌:《鲁迅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②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③ 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文学评论》1963年第5期。
④ 张恩和:《鲁迅——伟大的反封建主义的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⑤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人民日报》1983年7月2日。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③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人民日报》1983年7月2日。
④ 任继愈:《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1980年9月18日在陕西省哲学学会的讲话》,《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
①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8,29—30页。
② 张恩和:《鲁迅——伟大的反封建主义的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③ 许子东:《普通编辑王信》,《北京青年报》2021年2月21日。
①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125、126页。
作者简介: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