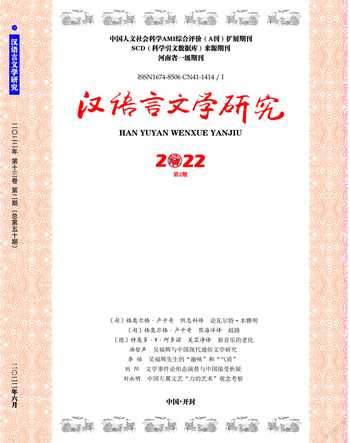主体生成的世界
2022-07-11孟庆澍
张恩和先生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包括鲁迅思想研究、鲁迅旧诗研究、郭沫若研究、郁达夫研究等领域,其中又以鲁迅研究的成绩最为突出。在我看来,其治学中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关注鲁迅反封建、鲁迅与辛亥革命等问题,并且总结出自己的基本原则。他的学术研究在在体现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术风气,体现出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与1980年代社会思想变化的共振性和同步性。在今天看来,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很值得重新检讨。
一
张恩和先生在研究中非常重视鲁迅的反封建主义。他认为,鲁迅到日本之后,认识到必须摧毁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封建社会的核心是专制,命脉是等级制度,要害是家族统治。他认为,鲁迅反对帝国主义,但更看到封建主义的流毒对我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是最大的障碍,也就是强调对专制主义传统思想的批判是最迫切的问题。张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这一观点,甚至提出,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斗争;对封建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也是鲁迅最重要的功绩。①这构成了其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面向。
应该承认,张先生的观点并不另类,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鲁迅研究的某种共识。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学者而言,封建主义这个术语已经“去学术化”,基本上已经属于失效的概念,很少有人再频繁使用。但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学术市场上的身价涨跌,既可能与其自身的阐释能力有关,也可能与这个学术市场的潮流、风向变化有关。这个概念本身在新时期之初是非常流行的、关键性的概念。今天的备受冷落,可能与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有关,反过来,也可能反映了学术界的某种势利和思维的受限。换言之,“封建主义”这个概念可能需要重新推敲和界定,但指出中国社会具有某种迥异于欧美社会的性质和文化,并且这种性质和文化仍在妨碍着中国的现代化、世界化的进程,这一判断可能仍有其价值。
举个例子。俞可平认为,“封建”一词在汉语中自古有之。柳宗元《封建论》所说的“封建”特指春秋以前各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秦朝以后这种封建就没了,中国长期的历史显然不是柳宗元所说的“封建”。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封建主义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地采邑制度,封建制度的实质是以领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显然,中国传统社会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所以,用“封建主義”作为主要框架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合适。俞可平本人提出,能够比较确切地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形态的概念是官本主义。②事实上,除了这两个概念之外,学术界还提出了“宗法地主专制社会”“郡县制社会”“选举社会”“帝制农民社会”“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形态”“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等各种观点。③这无疑说明,尽管“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框架并不一定完全适合于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性质,但中国传统社会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与欧美社会差别极大的特性是确实存在的。
因此,重新认识张恩和先生对鲁迅反对封建主义问题的关注,就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如上所言,封建主义概念自身的局限并不能取消或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质的追问。在中国与世界关系面临转型和重新结构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格外紧迫。其次,“封建主义”这一概念是从19世纪欧洲横向移植来的,是对19世纪欧洲状况的重复,“但每一次重复同时也是置换——不仅是背景差异的产物,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置换。这些概念重组了历史叙述,也打破了旧叙述的统治地位,从而为新政治的展开铺垫了道路。这并不是说这一时代的话语实践不存在概念或范畴的误植,而是说若无对这些概念或范畴的政治性展开过程的分析,我们根本不能理解它们的真正内涵、力量和局限,从而也就不能通过它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独特性”①。也就是说,封建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的兴衰成败,就是鲁迅研究史乃至新时期以来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三,张先生诚然是强调鲁迅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一面,但如果我们将封建主义替代为“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质”,那么鲁迅本人显然也是这一性质的基因携带者。那么,鲁迅是否也具有某种“封建性”,鲁迅的反封建与自身对封建性的超越是什么关系,就自然成为需要追问的问题。
二
值得思考的一个现象是,在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身上,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性,即他们在强调生命体验和主观投入的同时,又高度重视实证,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他们的“道”与“术”之间隐含着一种看起来矛盾紧张,但又奇特地彼此共存的关系,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催生了第二代现代文学学者富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兼具义理和考据,主体介入、现实批判和文献辨正共存的研究风格。这一点在张恩和先生身上也有体现。
例如,张恩和先生素以对作家深入妥帖的情理辨析和理论评价见长,但他并不拒绝进行严肃细致的史实考证。他的《鲁迅的初恋》和《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就是很典型、很有价值的考证文字,自成一家之言。他根据鲁迅旧诗的研究状况,借鉴古典学术传统,采用“集解”的方式研究鲁迅旧诗,并且提出这一工作其实可以当作“情报资料”来看,体现了他自觉的文献意识:
我可以和古人的集解、集释不同,不必将主要力量放在对诗句的研究上,逐字逐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尽量完全地把别人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自然,在此基础上,我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双百”方针,也谈点自己的看法,或者竟是提出问题。②
时至今日,他的《鲁迅旧诗集解》仍是鲁迅旧诗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著作。在现代文学发生“文献转向”的今天,强调张先生的考证功夫,似乎是有意溢美,以塑造张先生文献研究先驱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张恩和这一代学人的史料考证之所以值得重视,正在于其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特殊性,亦即“以考证为批判”。换言之,在他们的研究中,考证最初往往以方法论的面目出现,但最终却是具有根本的价值论的意味。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考证有时并不仅仅意味着历史事实的考订,而是具有意识形态的颠覆力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实证主义常常具有批判性的意味,常常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遣队和助产士。这既是文化传统的产物,也是鲁迅研究传统和现代史的产物,很值得注意和讨论。张恩和先生等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人,虽然多数也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但相对而言,20世纪中国壮阔激烈的革命历史才是他们最重要的课堂,他们更多是从家国的动荡和生命的颠沛中思考自我与研究对象。对他们而言,相较于思想,知识始终是第二位的。这就使他们的考证一定是服从于义理、史实,一定是服从于史识的。自然,这在今天很容易被诟病为不够学院化、规范化,但这种“不够学院化、规范化”自有它的优势。至少在他这一代学者身上,多有心忧家国的情怀和与现实肉搏的勇气,而少有饾饤腐儒的酸气与蝇营狗苟的铜臭。随着代际发展,学科逐渐正规化、体制化、专业化,不少青年学者受到更完整的学术训练,更加技术主义,其考据和论证也变得精致化,计算机技术的引入更使文学研究具有了数字化的一面,但学科草创期的某些内在能量也在衰减、消散。长此以往,令人不禁忧虑,在学术研究日益强调客观、实证、数据,日益排斥主观、情感的今天,现代文学研究离被人工智能彻底取代还有多远?数字人文是否最终会变得只有数字而无人文?
三
这其实涉及如何认识研究主体的问题。
张恩和先生并不讳言鲁迅研究的特殊性,在世纪之交,他提出鲁迅研究的三个基本原则:现实性、时代性和群众性。我认为,他没有明言但实际上坚持的还有一个主观性原则,这个原则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他在《我的鲁迅研究》中说:
我一向认为,研究鲁迅不应简单地将他当历史、当作一般作家研究,而应该把他当作一种精神上的对话者或引领者,以他为精神偶像。研究鲁迅不仅不同于研究自然科学,甚至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那些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保持客观冷静态度,研究者本身是不必要也不应该投入自己的热情和主观精神的。而在研究鲁迅时,则应该有主观精神的融入,用胡风的话说,简直是应该表现出不能抑止的热情,用全身心投入并拥抱他,并且应该表现出研究和学习相结合,即人们常的“知行合一”。对鲁迅要有一种以之为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情和态度。①
和当前“唯主观而欲去之”、追求“价值中立”的学术正确完全不同的是,张恩和毫不隐讳、毫无保留地提出鲁迅研究应该有主观精神的融入,应该以“研究和学习相结合”的态度对待鲁迅。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种观点对学术研究客观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张恩和先生偏偏就坚持着这种看起来不能成立、初学者也不会坚持的观点,毫不忧谗畏讥。
批评张先生是容易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理解和分析他对主观性的强调和坚持。他在文中所坚持的主观性,其实就是主体性的表现,是主体性的另一种表述形式,也就是强调在鲁迅研究中应该坚持主体性。张恩和先生把主体性表述为主观性,又表述为以研究对象为学习对象,这种看法是否恰当可以讨论,但其对研究者主体性的坚持是值得我们分析的。历史地看,主体性这个概念其含义异常丰富,但简单说就是“主体所潜在地具有并且能够发挥出来的属性”。②对我个人来说,张恩和先生对主体性的强调有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主体性思维要求以人为根本,反对将人视为工具。在研究作家时,就会将作家视为一个以人为基础的主体,而不是空洞的、非人格化的符号。例如,在回答鲁迅为何提前离开厦门这个具体的学术问题时,张恩和一方面承认原因的多元性,但另一方面又极为重视鲁迅作为人的情感性,看到鲁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进而提出鲁迅的私人感情生活是他选择提前离开厦门的主要因素:“种种原因,种种目的,都绕不开一个起主导作用(激化作用)的因素,就是希望尽快和许广平在一起。这是鲁迅作为普通人内心深处的主观愿望和情感需要,我们不但不应回避,相反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③张恩和先生自己解释,这是为了呼应“鲁迅是人不是神”、摆脱泛政治化的视角去观察鲁迅的学术思潮而作。将作家从政治幽灵的附体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其主体的意志、情感、实践,才能再现作家作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文学研究主体性思维的前提之一。
其次,主体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为我性。马克思曾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④。当然,我们不能狭隘地去理解这个“我”,它既可以是个体,也是指整个人类。但在学术研究这种主客体关系中,这个“我”显然是指研究者自身。所以,研究中的主体性思维,就要求以研究者为中心,研究不再是服务于客观对象,不再被客观对象所支配,而是从研究者自身需要出发,为研究者自身而服务,如此,研究者自身的存在价值才能得到确立,研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才有其意义。对鲁迅研究来说,从因果逻辑上看,当然是先有鲁迅才有鲁迅研究。但是从话语建构的角度看,鲁迅又是鲁迅研究所塑造的;从主体性角度看,鲁迅研究又是为研究主体服务的,是研究主体获得主体性的途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研究并不从属/依附于鲁迅,而是平等、独立于鲁迅的。鲁迅研究既是对客观对象的探索,也是研究主体自我实现的方式。那么,无论其研究结果的性质、状况如何,都应视为“这一个”研究主体的实践行动的成果,都是“这一个”研究主体生成的方式,都应加以严肃的对待和充分的尊重。从这一意义上看,鲁迅研究自身的历史与鲁迅文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最后,人的主体性不是单一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的,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社会历史中行动的人”所具有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从不同的思想、观点、方法去改造世界,表现出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主体性,这就是不同代际研究者同中有异的原因。这也启示我们,在鲁迅研究中,尽管以张恩和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學者的学术影响多被第一代和第三代学者所遮蔽,隐而不彰,但其研究主体性仍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开掘。同时,新一代的学者也应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坚持主体意识,在主体间的相互观照、交互和斗争中,追求并实现自身的主体性。也只有这样,研究包括张恩和先生在内的鲁迅学术史,才能不断地成为一代又一代研究者主体性的重要源泉,因此不同代际、彼此影响和共在的主体,最终参与并决定了意义世界的生成。
① 张恩和:《我的鲁迅研究》,《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② 俞可平:《官本主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学分析》,法治政府网,http://fzzfyjy.cupl.edu.cn/info/1223/4300.htm
③ 详见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① 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② 张恩和:《写在前面》,《鲁迅旧诗集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① 张恩和:《我的鲁迅研究》,《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② 魏小萍:《“主体性”涵义辨析》,《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③ 张恩和:《踏着鲁迅的脚印——鲁迅研究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作者简介: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新文化运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