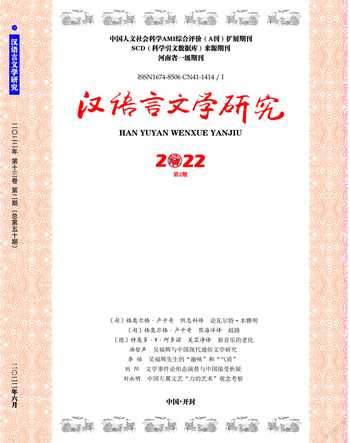曹操人格精神特征论
2022-07-11王艺雯王利锁
王艺雯 王利锁
摘 要:作为汉魏之际的历史风云人物,曹操的文化性格和人格精神结构相当复杂。结合曹操生活的时代和生平行实,从人格精神结构进行系统把握,曹操最突出的人格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六个层面,即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权者之术、智者之识、杂家之学和诗家之才,正是这六大人格精神要素的互融含化构成了曹操完整的人格精神结构。曹操的人格精神呈现出多面性、复杂性、交织性的特点。
关键词:曹操;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权者之术;智者之识;杂家之学;诗家之才
作为汉魏之际的历史风云人物,曹操的人格精神结构相当复杂,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汇做出定评。曹操在世之时即有对其各种褒贬不同的评论,历史上更是有多种说法,或以为曹操是一个英雄、豪雄、能臣、智计之士、超世之杰,或以为他是一名枭雄、奸雄、汉贼、乱世臣子、谲诈之人,等等。①尤其随着明代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对曹操的评价又往往历史与文学交织,事实与虚构难分,历史人物的曹操与文学形象的曹操交互错位,混淆不清,这都给准确认知真实的历史的曹操披上了迷雾,平添了困难。那么,到底该如何把握历史上的曹操?又该如何认知曹操的人格精神特征呢?笔者认为,对曹操人格结构特征的把握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个层面,应该结合曹操生活的时代和生平行实,从人格精神结构层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分析。具体来说,我们认为,曹操最突出的人格精神特征可以概括为六个层面:仁者之心、霸者之气、权者之术、智者之识、杂家之学和诗家之才。正是这六大人格精神要素的互融含化构成了曹操完整的人格精神结构。
一、仁者之心
以往对曹操的讨论,很少肯定曹操是有仁心的,似乎曹操天生即谲诈阴毒。我们首先必须肯定,作为一个深受儒家精神影响的时代风云人物,曹操是有仁心的,而非天性谲诈阴毒。尤其是早年的曹操,仁者之心的表现更加突出。曹操生逢汉末乱世,经历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等最惨烈的社会政治动荡,而动荡之后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下层的普通民众。可以想见,一场战争下来,会有多少人抛尸荒野,又有多少人背井离乡、骨肉离散。面对如此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曹操并非无动于衷,而是有深深的悯世情怀。如果无视曹操的仁者之心,就无法解释曹操那些力透纸背、慷慨悲凉、充满悲悯情怀的被锺惺《诗归》誉为“汉末实录”②的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初平元年(190),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关东州郡以讨伐董卓为名,举义旗、兴义兵,但很快这场义举就演变为军阀之间的混战厮杀。曹操经历了这场闹剧,他的《蒿里行》《薤露行》就是这一重大政治变故带来的沉重社会灾难的实录。《薤露行》描写董卓之乱引发的社会振荡和京师残破景象,“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①,字里行間透射出曹操对“贼臣”的愤慨和对现实之举的无奈与哀痛。《蒿里行》写军阀混战的恶果和造成的民生苦痛:“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②诗歌悲凉慷慨,真切表达了曹操忧念民生的仁爱之心。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在攻下袁绍大本营邺城之后,又发兵西征高幹,在行军途中作《苦寒行》。在这首诗中,作为军事统帅的曹操没有去昂扬奋发地激励士气、耀武扬威,而是对极度艰难严寒的行军环境进行铺陈渲染,通过“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③的艰苦生活书写,表达了他“念及征夫劳苦”的“悯劳恤下之意”和悠悠哀伤之心。④这些诗作没有丝毫的矫情与伪饰,都是曹操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悲天悯人之慨,哀民伤生之想,飘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苦寒行》的写作,对一个称霸一方的军事统帅而言,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的背后恰体现了曹操的仁者情怀,是曹操此时此境真实的心理情绪表达。
在曹操的行政公文中,也不时看到他的仁者情怀。建安七年(202),曹操南征路过家乡谯,看到家乡的残破不堪,发布了《军谯令》: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⑤
令文面对民生凋敝的现实处境凄怆伤怀,要求抚恤战死沙场的兵士家属,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言语朴质,真切感人,尤其对“生民”“将士”死亡的哀痛,是他悲悯之心自然而然的流露,并非沽名钓誉的伪装。建安十一年(206),在西征高幹攻下并州之后,针对山西境内百姓“寒食”的旧风俗,他下达《明罚令》,指出“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⑥。尽管移易风俗采用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但出发点则是为了保护老弱幼童,不使其因风俗而受到伤害。曹操的这些措施整饬的是恶俗,体现的是体恤,不能简单视为是对风俗的破坏,恰恰反映了他的人道精神。因为,只有亲临其境之人才能发现民众生活中的风俗病弊。
明代诗论家谭元春曾说曹操身上有“菩萨气”⑦;锺惺也指出曹操“惨刻处惨刻,厚道处厚道,各不相妨,各不相讳”,他作品中的悯世伤生情怀,都是“真心真话,不得概以奸之一字抹杀之”。⑧谭元春、锺惺所谓的“菩萨气”“厚道”,其实就是我们强调的体现在曹操身上的仁者之心、仁者情怀。清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评论得更直白:
从来真英雄,虽极刻薄,亦定有几分吉凶与民同患意;思其与天下贤才交游,一定有一段缱绻体恤情怀。观魏武《短歌行》此作及后《苦寒行》,何等深,何等真。所以当时豪杰,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今人但指魏武杀孔融、杨修辈,以为惨刻极矣,不知其有厚道在。⑨
诚如吴淇所言,如果曹操没有仁者之心,天生就是一个惨刻、谲诈、阴毒之人,“当时豪杰”怎能会“乐为之用,乐为之死”呢?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廿二史劄记》说,曹操初迎汉献帝都许时,“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①只是随着事态情势的变化,曹操个人欲望的膨胀,仁者之心被其他人格精神抑制和遮蔽,令人不易觉察罢了。如果仅仅强调他后期有篡逆之心,而不体察或忽视他前期的民生之爱,就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曹操复杂的人格精神结构特征。
二、霸者之气
自古以来评论曹操者皆认为曹操有霸气。《三国志》作者陈寿认为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乃“超世之杰”;②宋人敖陶孙说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③;明代谭元春认为曹操身上不但有“菩萨气”,更突出的还是“霸气”;④清代王夫之认为曹操时有“霸心”⑤;黄子云认为曹操有“强梁跋扈之气”⑥;沈德潜更明确指出曹操“沉雄俊爽,时露霸气”⑦。可见,霸气是历代评论家都认可的曹操显著的人格精神特征。
曹操的霸气,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心胸气势之霸。与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如袁绍、刘备、孙权等相比,曹操在心胸格局上要远远超过他们。这种霸气在他的诗作中有鲜明体现。如《观沧海》形象地描写了浩渺沧海的壮阔景象,给人以吞吐宇宙的壮美气势。沧海意象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生动描绘,也是曹操宏博胸襟的形象自喻,最能体现曹操的心胸格局。
二是理想目标之霸。在政治理想上,曹操是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宏志远图之人,他渴望建立一个“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的“太平”世界。⑧如此袒露自己的心迹,在军阀混战、私心暴露、野心膨胀、草菅人命、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的。曹操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自负的人,他不仅对人生充满自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⑨,而且也常常以古代圣人周公自况:“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⑩给人一种天命在我、舍我其谁的霸气。刘熙载说曹操“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11,揭示的正是其政治理想抱负的霸气。
三是政治魄力之霸。在行政处事上,曹操是一个典型的铁腕人物,决不容许他人忤逆自己。赤壁之战失败后,曹操深知完成统一已经无望,于是政治策略由对外征伐转向内政整饬,着手自身威权的巩固。建安十五年(210),当有人称曹操有“不逊之志”,希望他将“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时,曹操写了《让县自明本志令》,对此议论进行回应。在此文中,曹操虽不乏谦逊之辞,但真正表露的则是强硬之态。曹操告诫那些“谤毁”自己的人:天下之所以太平无事,正是由于他的存在,才使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不敢实现觊觎之心,“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因此,“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12表现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和斩钉截铁的霸气魄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观曹操一生,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集团领袖人物相比,可以说,曹操是一个典型的集霸心、霸气、霸道、霸权于一身的一代枭雄。
三、权者之术
曹操最为后人诟病且几乎成为其人格精神符号表征的无疑是他的权者之术。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谈到“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时即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①曹操確实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三国志》卷一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记载: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喎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②
曹操因厌恶叔叔在父亲面前告自己的状,就故意设计欺骗父亲,愚弄陷害叔叔。这说明曹操少时即机警善于权术。《曹瞒传》又记载:
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③
因军中缺粮,曹操先同意主事者以小斛的建议,后因士兵哗众,曹操就将责任推给主事者,还以盗官粮罪名处死主事者以此来稳定军心,这更是典型的欺诈权术。《曹瞒传》称曹操的这些行事风格是“酷虐变诈”④,概括相当准确。除此之外,《世说新语·假谲》中也记载有许多曹操生活中玩弄权术欺诈的故事,如: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⑤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此。”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⑥
这些故事都给人一种突出的印象,就是曹操是个极其善于玩弄权术的专家,谲诈成性。时人对曹操诟病最多的也是这些伎俩;《三国演义》无限夸大的也正是曹操人格精神的这一层面。不可否认,这的确是曹操为人行事和人格精神中最富有特征的个性表现。
如果结合曹操的生活时代设身处地地去想,少年曹操的顽劣淘气姑且不论,他后来的玩弄权术也是事出有因的。在那个他不杀别人、别人即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极限生存情境下,曹操玩弄权术欺诈说到底则是一种极端的自保方式,只是历史对他的行为记述比较显豁罢了。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又可发现,记载曹操玩弄欺诈权术且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故事,主要出自吴人的《曹瞒传》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假谲》。这就颇值得玩味和深思了。吴人所著《曹瞒传》很可能出于时代政治的考虑和需要,故自觉对曹操的为人性格进行丑化,里面不免有污黑曹操的成分。而《世说新语》的编纂已是时过境迁之后,编纂者如此突出和津津乐道曹操这些权术谲诈故事,其背后又是何种心态呢?对此,笔者在讨论《世说新语》的故事采录和编撰心态时曾进行过细致辨析,此不赘述。⑦
当然,具体到曹操的玩弄权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曹操毕竟是一个军事家,他一生戎马倥偬,作为一个军事统帅,凡排兵布阵、用兵行事,必然有谋略权术在。《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兵法本就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行有形于无形之中。如果把用兵谋略都一概视为权术,那所有的军事谋略家就都成了心术不正、玩弄权术的权术家了。如此认知显然是不公平的。据《曹瞒传》记载,官渡之战前夕,许攸自袁绍处投奔曹操,与曹操讨论军粮问题,曹操开始的回答不失为一种权术心理,但当许攸说透曹操心思处境时,曹操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了许攸实情。①这虚虚实实的背后不乏权术在,但其中也蕴含着作为军事家的曹操用兵行事的机智灵活。再如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韩遂,为了瓦解马、韩军事联盟,曹操进行了离间。《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
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于是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旧故,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②
曹操正是抓住了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和马超的猜疑心理,成功地使用了离间计,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这也应视为曹操对军事谋略手段的合理灵活运用,不能完全看作是曹操在玩弄权术伎俩。总之,曹操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人,但曹操的权术又往往与他的兵家“明略”浑融交织在一起,阴谋阳谋并用,彼此难分。所以,认知曹操的权术既不可无视其谲诈性格无限度地进行美化,亦不可忽视其军事家的身份简单地归结为天生成性而一味诋毁,应该放在曹操生活的复杂时代和极限情境下来进行具体认知。
四、智者之识
曹操是一个实践理性极强、非常善于审时度势的聪明人。曹操对时世的发展有非常清醒的理性认知和判断,他的许多治世行事策略都建立在他智者之识的基础上。如,他深知“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首先倡导大力“屯田”,设置屯田都尉,以解决大军乏粮之忧。③他深知“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④,身处乱世,统兵驭将,如果没有严明的军纪,就无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所以,他严明治军,赏罚明达,崇尚法术。他深知“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⑥所以,在用人政策上,他不沿袭东汉以来重德轻能的思想路线,而是“唯才是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均可提拔举用。⑦正是由于这些用人政策,曹操麾下集聚了众多才智武力之士,为日后曹氏的窃鼎取国储备了大批人才。曹操深知“多兵意盛”⑧的道理,所以,当有人要求他交出兵权时,他明确表示“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⑨,表现出异常清醒的居安思危的理性意识。
可以说,曹操的智者之识体现在他行政、治军、经济、法制、人事、文化政策的方方面面。正是曹操的这些明识之智,使他能够对现实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始终保持清醒理性的认知,也是他能够在军阀混战中冲出重围取得胜利的重要凭借。曹操具有人人皆知的篡汉之心,但他最终没有躬身实施,恐怕也与他对现实处境的理性认识有一定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身无尺寸之地的曹操能够从群雄争霸的汉末混乱政局中突围出来,并最终登峰造极于一时,与曹操本人的智者之识是分不开的。
对此,《三国志》作者陈寿还是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论,他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①陈寿说的“明略”,其最基本的内涵即是我们所说的智者之识。要之,曹操是三国时期一个头脑极清醒、认知极理性、富有智慧和远见卓识、又能够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五、杂家之学
在汉末争霸的群雄中,曹操的文化素养是最高的。曹操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文化素养,与他喜欢博览群书的文化性格有很大关系。曹丕《典论·自叙》描述曹操的读书生活时说:“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②王沈《魏书》也说:“(曹操)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③汉末群雄中不乏爱读书的人,如孙权,他自述自己的读书经历说:“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同时,他还劝吕蒙、蒋钦二人:“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④但能够达到曹操如此高的文化修养程度的则不多。
曹操对先代典籍相当熟悉,史实掌故,信手拈来,化为己用。据张振龙先生统计,曹操的阅读面相当广泛,除儒家的《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公羊传》《礼记》《论语》《孟子》等典籍外,其他如《老子》《墨子》《孙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司马法》《战国策》《楚辞》《史记》《汉书》《列女传》《盐铁论》《说苑》等均有涉猎。⑤这些经典意蕴内化为曹操的文化素养,使其知识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杂家之学的特点。这从曹操的思想表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如《对酒》描绘曹操心目中理想的太平社会图景: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戴。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⑥
其中既有儒家的仁政理想,也有墨家的兼爱思想;既有道家的小国寡民情怀,也有法家的礼法刑政意识;既有农家的重农观念,也有兵家的强兵理念。徐公持先生《魏晋文学史》即指出,曹操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杂家本色,儒、法、道、墨、刑名、兵、农诸家主张,应有尽有”,他描绘的“太平盛世的蓝图”,“颇具理想主义色彩”。⑦总之,从曹操社会政治理念的自我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曹操杂家之学的人格精神特质。曹操知识结构的杂学化倾向铸定了曹操人格精神特征的杂学化色彩。
六、诗家之才
曹操是个多才多艺之人,草书、音乐、围棋等才艺无所不能,但他最为后人称道的自然是他的诗家之才。关于曹操的诗家之才,各种文学史著作多有评价,此不展开论述。本文要强调的是,曹操的詩家之才与他的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曹操现存诗歌尽管只有20余首,但在形式体制上均富有创新意义。从体制看,曹操诗歌创作基本沿袭汉代以来的乐府旧题,但在创作时曹操却敢于进行大胆的革新。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汉代以来的挽歌,曹操却用来书写汉末社会时事。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①充分肯定了曹操诗歌的这一创新意识。徐公持先生也评价说:“曹操在继承发扬汉乐府的音乐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从现实创作需要出发,对乐府体制做了大胆革新,表现了他的尚实精神和通达作风。曹操的革新措施,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②从形式看,曹操的四言诗、五言诗也多有创获。他的四言诗是继《诗经》之后文学史上又一次大放光彩的创作,对魏晋四言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沈德潜说:“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③即肯定了他的四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汉魏之际是文人五言诗创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而曹操对五言形式却能够纯熟驾驭,以情运文,情自我出,辞以写心,语言朴质,气象苍然,慷慨悲凉,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审美风格。这充分体现了曹操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才情天分,是他诗家之才的鲜明表征。张溥《魏武帝集题辞》也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④这些评论背后实际都是对曹操诗家之才的高度肯定和赞扬。
以上我们概括了曹操人格精神的六大突出特征,即仁者之心、霸者之氣、权者之术、智者之识、杂家之学和诗家之才。需要说明的是,曹操上述六大人格精神特征并不是齐力并发、齐头并进、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生活情境和政治军事处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不同行事过程中,他的某一方面的人格精神会因现实的需要被唤醒而显得特别突出,而其他方面的人格精神则会自觉不自觉地被遮蔽和埋没。如曹操生活的前期与后期、军事生涯与日常生活、行政处世与饮酒赋诗等不同处境下,他的人格精神表现的隐显就不同,有时豪放爽朗,有时假谲诡诈,有时真情表露,有时虚张声势,有时多种精神杂糅迸发。因此,曹操的人格精神特征又呈现出鲜明的多面性、复杂性、交织性的特点。可以说,在曹操身上,理性与感性并存,奸雄与能臣兼备,明略与诡诈杂糅,仁心与刻薄浑融,霸气与权术互含,杂学与诗才交织。因此,认知曹操,既不能将其某一人格精神特征无限度地夸大固化,也不能仅据某一具体实例而过度诠释,应该结合时代情势进行系统观照,条分缕析,在全面把握曹操人生行实的基础上,充分认识曹操人格精神特征的复杂性、交织性、多变性,唯有如此,才能实事求是地对曹操的人格精神做出客观的评价,才能真正把握和复原曹操的历史真面目。
① 参阅张作耀:《曹操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河北师范学院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① 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② 《曹操集译注》,第14页。
③ 《曹操集译注》,第25页。
④ 刘履:《选诗补注》卷二,《三曹资料汇编》,第18页。
⑤ 《曹操集译注》,第80页。
⑥ 《曹操集译注》,第97页。
⑦ 锺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三曹资料汇编》,第17页。
⑧ 同上。
⑨ 《三曹资料汇编》,第22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②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5年版,第39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③ 敖陶孙:《诗评》,《三曹资料汇编》,第8页。
④ 锺惺、谭元春:《古诗归》卷七,《三曹资料汇编》,第17页。
⑤ 《船山古诗评选》卷一,《三曹资料汇编》,第25页。
⑥ 黄子云:《野鸿诗的》,《三曹资料汇编》,第31页。
⑦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
⑧ 《对酒》,《曹操集译注》,第15页。
⑨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曹操集译注》,第44页。
⑩ 《短歌行》,《曹操集译注》,第19页。
11 刘熙载:《诗概》,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2420页。
12 《曹操集译注》,第132~139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第122页。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2页。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9页。
④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9页。
⑤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52页。下引此书仅注页码。
⑥ 《世说新语笺疏》,第853页。
⑦ 参见拙文:《〈世说新语〉三曹故事辩议》,《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15页。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25页。
③ 《置屯田令》,《曹操集译注》,第66页。
④ 《以高柔为理曹掾令》,《曹操集译注》,第163页。
⑤ 《论吏士行能令》,《曹操集译注》,第87页。
⑥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曹操集译注》,第160页。
⑦ 《举贤勿拘品行令》,《曹操集译注》,第170页。
⑧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集译注》,第134页。
⑨ 《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集译注》,第138页。
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39页。
②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0页。
③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第38页。
④ 《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第942页。
⑤ 张振龙:《曹操散文中的语典和事典》,《中州学刊》2012年第1期。
⑥ 《曹操集译注》,第15页。
⑦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①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6页。
②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③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第105页。
④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4页。
作者简介:王艺雯,中原科技学院文传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王利锁,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唐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