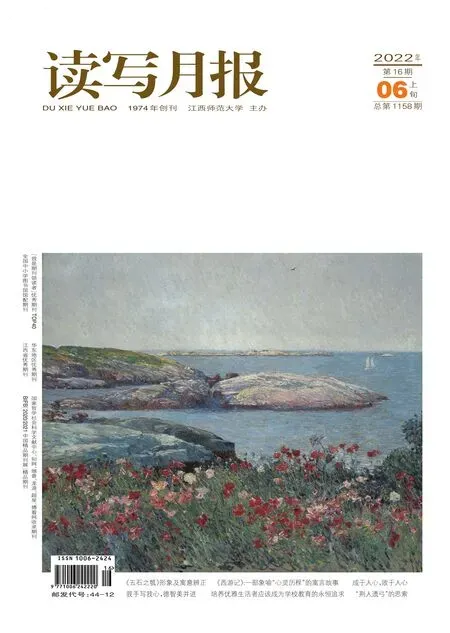追寻失落的人文精神
——《敦煌》导读
2022-07-06

【阅读导引】敦煌自古被誉为中西文化和文明交融的第一站。数千年间,因乌孙、大月氏和匈奴,吐蕃、鲜卑、西夏、突厥和蒙古等部族的轮番占领,中西文化、宗教和文明在此得到交融与演变,使得敦煌文化具有鲜明的多样性色彩。
1900 年6 月22 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资料。藏经洞内的“敦煌遗书”,与安阳殷墟、居延汉简并称为20 世纪初东方三大文明发现。而此时我国正处于清末的动荡时期,一批西方探险家得知消息后进入莫高窟,带走了大量的藏经洞文物,这些文物流散并分藏于英、法、日、俄等国的公私收藏机构。后来许多人把发掘文物的王道士视为千古罪人,把带走文物的探险家斯坦因等人视为“骗子、强盗”,认为他们造成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浩劫。
然而这样的评价无疑带有极大的偏见。事实是流落在外的文物虽然分散至各国,却完好无损地被收藏或展示,而那些没被运走的文物却遭到了破坏。国民党军队对文物乱挖乱凿、放任白俄军队对文物乱涂滥用、张大千等对壁画的破坏性临摹都是不可逆的。在那个癫狂的时代,仅仅因为对清朝不满,一些人就决定砸毁清朝期间的敦煌雕塑。当时志愿申请加入敦煌艺术保护行动的美术家高尔泰就目睹了这一悲剧。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热爱美与自由的理想主义者,高尔泰一直是孤苦的。二十岁的他挑战权威,提出“美是主观的”,与当时的主流背道而驰,遭到了无数的批判和打压,然而他一直保持着精神的坚韧和丰足。他的文字与他的美学观念一脉相承,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在描写回忆时,他对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叙述的角度无不体现他对历史、社会与人性的深度思考,其精练又富有美感的语言则展示了他对文字超高的驾驭能力。
选择去敦煌是特殊时期坚守个人精神的无奈之举,也是能够继续接触文化艺术的最好选择。在敦煌,他终于离开集体,获得了短暂的寂静,然而精神上的荒芜让他感受到无比的空虚。为了对抗虚无,高尔泰重新拿起了笔。通过写作,他找到了“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再次展现出人之为人的尊严与高贵,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异化。他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那一段历史的材料,更在于写出了普通人幽深而又复杂的心灵世界。高尔泰淡然又极富美感的文字启发我们不要遗忘苦难中的卑劣人性,更不要遗忘卑劣时空里依然存在真诚与高贵。
【作者简介】高尔泰(1935 年10 月15 日—),当代著名画家、美学家、教授。中国当代美学界称他与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等,为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他构建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曾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
【附文】
敦煌
高尔泰
面壁记
从1962 年到1972 年,我在敦煌十年,但只工作了四年。那时我常常被派去扫洞子。岩壁上落下的沙子,有时飘进洞里,久之积下或厚或薄的一层。我的任务就是把它扫出来,弄走。这是个没数的活儿,岩壁上上下下四五层四百九十多个洞子,谁知道哪里进了沙子?如果哪里我没扫,我可以说是刚刚扫过就又落了一层。
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在扫洞子。每天独个儿拄着扫帚,仰头向壁,与仙佛同游,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光暗看不清了,就到小道上望远,“更无人处一凭栏”,也是难得的体验。林海外,一片斜阳,万顷荒莽,有时恍惚里,真不知今夕何年。
这些洞窟壁画,以前都曾看过。但是拄着扫帚看到的,同拿着卡片或者画笔看到的又不相同。作为佛教艺术,在佛教教义给定的框架范围内,敦煌艺术所展现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作为经变(本生故事和感应故事)的背景,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耕种、蚕桑、纺织、建造、狩猎、畜牧、婚嫁、丧葬、教学、商旅、制陶、冶铁、驭车、炊事、战争、行乞、屠宰、练武、歌舞、百戏、宴会、帝王将相出巡、游猎、剃度、审讯等等场景都有。其间宫殿城池、亭台楼阁、桥梁水榭、舟车寺塔、学校店铺、驿亭酒肆、衣冠服饰、宗教仪式俱备。以致许多不同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在里面找到有用的东西。
对于卡片来说它们是资料。对于画笔来说它们是范本。对于以戴罪之身,手持箕帚,心无所求,依次从容不迫地看下去的我来说,它们成了心灵史,成了一个思维空间的广延量。
都说唐代艺术最好最美,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魏窟。十六国时期洞窟里的人物造型,一律矮壮质朴,唐代则一律丰圆壮肃。唯魏晋瘦削修长,意态生动潇洒。额广,颐窄,五官疏朗,眉毛与眼睛相距很远,恰如《世说新语》所说的“秀骨清像”,《历代名画记》所说的“变态有奇意”。也不以色貌色,绿马、蓝马、黑山、白山空无所依,蓝人、绿人、红人、黑人,都白眼白鼻,非人间所见。前呼后拥在黑色或土红色调子的背景上涌现出来,予人以一种奇幻神秘之感。
最使我流连的是西魏二八五窟,直以粉壁为天地,空灵透明。星汉奔流、云气飞扬,涵虚混太清。佛教诸天:日天、月天、纬纽天、鸠摩罗天,天龙八部等等,还有佛经中没有,来自中国古代神话的伏羲、女娲,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雷公雨师,东王公、西王母,以及《楚辞·天问》中提到的许多怪物,奔腾竞逐于天空。或乘雷电,或踏飞轮。灵幡飘渺,华盖悬空。旌旗舒卷,衣带流虹。潇潇飒飒,满壁生风。
所有这些,包括藻井、龛楣以及分布全窟的装饰纹样,都用线条勾勒组成。无数纤细强劲、金属丝一般富有弹性,而又修长柔软如游丝的线条,在幽邃诡谲、光怪陆离的色块之中穿行,互相跟随互相追逐,时而遇合,时而分离,轻悠下降,忽又陡然上升,徐缓伸展,忽又蓦地缩回。聚集、交错、相与旋转,以为要纠缠不清了,忽又各自飞散,飞散而又彼此呼应,相遇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像一组组流动的音乐,有笙笛的悠扬,但不柔弱。有鼓乐的喧闹,但不狂野。从容不迫,而又略带凄凉。凄凉中有一种自信,不是宿命的恐惧或悲剧性的崇高,也不是谦卑忍让或无所依归的彷徨。
唐代的洞窟,特别是贞观、开元之际的唐窟,以华严、瑰丽、气度恢弘为特点。色彩鲜艳丰富、金碧辉煌。线描技法亦更为多样。用笔仍是中锋,但有轻重、快慢、虚实、粗细的变化,抑扬顿挫。菩萨和供养人等,大都是周家样绮罗人物,曲眉丰颊,莹肌圆体,肩披长发,半裸上身,璎珞珠饰繁华缤纷。或静立,或歌舞,或飞天,或坐思,都妩媚生动,而又端庄从容。不是禁欲的官能压抑,也不是无所敬畏的张狂。佛国的庄严,都化作了人间的温馨。如此大气,又如此隽永。
唐窟中最使我倾心的,还是塑像,特别是二零二、一九四等几个洞子的塑像。同为佛教诸神,却又各有个性。阿难单纯质朴;迦叶饱经风霜;观音呢,圣洁而又仁慈。他们全都赤着脚,像是刚刚从风炙土灼的沙漠里走来,历尽千辛万苦,面对着来日大难,既没有畏惧,也没有抱怨,视未来如过去,不知不觉征服了苦难。
一三八窟的卧佛,是释迦牟尼临终时的造像,姿势单纯自然,面容恬淡安详,如睡梦觉,如莲花开,视终极如开端,不知不觉征服了死亡。
看到死亡的曲子,如此这般地被奏成了生命的凯歌,我想到西方艺术中那些以死亡为主题的雕像(如《拉奥孔》,米开朗琪罗的《死》,或者罗丹的《死》)都是悲剧性的。宽阔的胸脯隆起的肌肉,剧烈的动作,紧张的表情,都表征着恐惧与绝望的抗争。
相比之下,这些文弱沉静从容安详的塑像所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更加强大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阳刚阴柔之类现成的概念,或者十字架和太极图之类近似的比喻可以说明的差异。其中隐藏的消息,也为我打开了一个通向别样世界的门窗。
在那些小小的石头洞中面壁,我感觉到一种广阔。
寂寂三清宫
我是1962 年6 月2 日到的,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搬到下寺。
莫高窟原有三座寺庙。一座在狭长地带的最南端,原名雷音寺,简称为上寺。我去时,那里已成了所内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紧连着上寺的是中寺,原先是喇嘛庙,名“皇庆寺”,已经改建,成了研究所办公室、会议室、招待所、伙房、食堂等等的所在地。
庙里剩有两个喇嘛,一男一女。男的叫徐斯,女的叫宝乃。都搬到上寺住了。我初去时,徐斯七十多岁,瘦高一如插图中的堂·吉诃德。他给所里放羊,常在山中,经旬不归。宝乃八十多岁,仍穿着紫红色僧袍。人极瘦小,又是驼背,高不满一米,拄着拐杖行走,身体前倾,摇摇欲倒;语音嘶哑,但目光犀利,时或有一些强壮彪悍的彪形大汉,成群结队越过沙漠来拜望她,称她“老大”,敬畏有加。她那乌黑低矮的小屋门前,常系着雄健的矫马,喷着响鼻,前足刨地,俯仰之间,辔头哗啦啦直响。
下寺却是道观,原名“三清宫”,匾额犹存。位在狭长林带的北端,莫高窟山门之外。离上寺和中寺约一公里多路。据说很早以前,里面吊死过人。后来有个道士,在那儿被土匪打死。还有些狐仙鬼怪的传说。有几分神秘、几分恐怖,已久没人居住。廊柱油漆剥落,栋梁蛛网尘封,落叶堆庭,荒草芜径。出后门不远,就是著名的藏经洞,内有张大千题壁,字迹遒劲,略有板桥风。
我喜欢三清宫的宁静,要求住在那里,办公室同意了。我扫净一间厢房,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三年。所里四十九个人,编制分为研究部、石窟保护部和行政部。研究部为美术组、考古组和资料室。我所在的美术组,包括张大千留下的裱画师李复,共九个人。主要工作是研究和临摹壁画。按所里的年度计划,在年初把全年的任务分配落实到每个人头上,各自完成。七八个人加上考古组一共二十来个人,分散到近五百个洞子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我白天在洞里临摹,或在资料室翻书,下班后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回“家”。虽然工作并不乏味,我还是很爱回家——回下寺三清宫去。那是一个属于我个人的世界,离人群愈远,它愈开阔。
房间窗子朝东,窗外有几十棵合抱的大树,当地人叫它“鬼拍掌树”,疏疏落落占了很大一片地面。疏林外是河滩,川流不息。河那边隔着荒芜的丛莽,可以看见高坡上几个古代僧人留下的舍利塔。再过去就是三危山了。
傍晚回来,开门就可以看到,三危山精赤的碧岩映着落日,火焰般腾跃着一片金紫银红,烈烈煌煌。返照染红河水,还把蓝色的树影投射到房间里的东墙上。偶有鸟飞鱼跃,墙上就会漾起层层明亮的波纹。我常常凭窗站着,长久地一动不动,看山上的光焰渐渐暗淡,直到它变成深紫色,才点上那盏老式的煤油罩子灯,捣弄分配给我的专题。桌上一摞一摞,全是老得发黄的线装书。
我知道在敦煌研究敦煌学,条件难得。我知道我的安全和利益都在于利用这个条件,钻进故纸堆里,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是我想来敦煌的主要动机。想来而真能来,是一种幸运,我十分珍惜。我感激常书鸿先生帮助我来到这里,急于让他知道,他没有看错了我。
利益的考量加上急于求成,我在研究和临摹两方面都全力以赴。常常为了解决一个很小很小的问题,比方说某句佛经和变文的异同、某窟某条题记的确切年代这类,花上好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工夫。为临摹四六五窟元代密宗壁画,我在这个我所不喜欢的洞窟里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花落知多少
敦煌艺术的昌盛,以唐为最。唐以降,愈往后愈失掉昔年的高华与大气,一代不如一代。宋代的壁画都比唐代的草率粗糙。不但结构松散,笔墨缺乏功力和韵律,而且公式化、概念化,千人一面,走进去有种空落之感。好在色彩清旷萧散,还算是有自己的风格。元代除第三窟外,连风格都没了。剥皮抽筋(密宗内容)都入画,很不好看。清代几无壁画,少量彩塑皆鲜艳粗俗,更无美感可言。
纵观一千六百年敦煌艺术,唐代以后,确实是每况愈下。文艺风格的递嬗,包含着某种历史的信息。这个变化的曲线,值得研究。
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事,并不稀奇。中世纪欧洲艺术,落后于古希腊罗马时代;苏联文学的水平,远低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且不问什么原因,起码敦煌艺术的式微,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
奇怪的是,这条曲线运行的轨迹,会与内地(从中原到江左)的大致符合。例如魏窟粗犷略似建安风骨;唐窟华严正如盛唐之音;宋窟清空也像受了程朱理学的影响;元以降愈趋世俗化的倾向,也同内地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流行相呼应……
敦煌孤悬天末,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都比中原慢好几拍,为什么其艺术基调的变迁,却能与之同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962 年9 月,文化部一行人到莫高窟开专家会,策划石窟加固工程。参观洞子时,议论清代塑像,都说丑陋难看,竟在会上议决,把它们全部砸毁,从洞子里清除出去。我是跑腿的,没有发言权。只能看着雇来的农民抬着一件件砸下的断肢残躯往牛车上抛掷,然后拉到戈壁滩上丢弃,一任它雨打风吹一年年变成泥土。
这还不算什么问题。如果说,有些被劫掠的文物还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之类的地方,获得妥善保护和公开展览的话,那么当年在抢救过程中落入大小中国官员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抢救者据为己有的大量文物,后来连影子都没有了。即使那些抢救出来,终于收进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卷子,据陈垣《敦煌劫余录》记载,有许多都是撕裂了拼凑的。那缺失的精彩部分,早已经杳无踪迹。
民国十一年(1922 年),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每天提供食物,任他们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画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一条条的刮痕。后来(1939 年)国民党马步芳军队驻扎在莫高窟,乱挖乱掘,损失更无法统计。
抗战时期,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在莫高窟住了两年七个月,作摹本二百七十多件。期间给洞窟编了号,也曾呼吁政府筑围墙,禁炊煮,派人保管石窟。摹本在重庆展出,引起轰动。弘扬敦煌艺术,功不可没。但是张大千的临摹,是用透明薄纸在墙上直接拷贝,方法一如描红,不可能不对原作造成损伤。尤其对于那些粉化、起甲、漫漶、易剥落的壁画来说,损伤很可能是严重的。由于内行人挑选的临摹对象,大都是壁画中的精彩部分,问题就更大了。况且这不是张大千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画家、美术院校的师生来实习,都这样。
1962 年以后,所里的管理逐渐严格。八十年代后,莫高窟成了旅游热点,研究所改称研究院,按照商业化旅游区的要求,重建了窟前环境,加强了洞窟管理。卖门票开放参观,设专人带队讲解,基本上杜绝了上述种种情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人潮带来的空气污染,环境改变造成的生态失衡,反而大大地加快了壁画酥硷、起甲、大面积脱落的速度,要纠正已经很难。
所有这一切无心之失,都是一种历史中的自然。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不妨看得淡些。“六朝文物草连空”,听其自然比较好。要不,二十多年以来,整个中国在滚滚商潮中失落了那么多的人文精神,我们又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