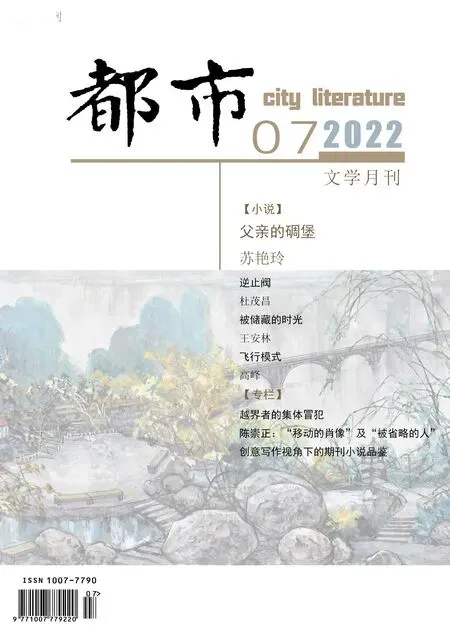你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
——评朱阅平小说《书包,书包》
2022-07-05钟小骏
○钟小骏
《书包,书包》发表于《黄河》2022年第三期,是当期短篇小说的头条。作者朱阅平。
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短篇小说,一个小学中两个孩子起了冲突,护子心切的两家家长把这个冲突从小孩子之间的吵闹变成了两家人之间的对抗,受到伤害的小女孩家长不要赔偿要求道歉,而要保护儿子自尊心的家长则只愿赔钱。于是故事开始了。
其实这个故事接下来讲述的内容很简单,女孩被迫转学后她的母亲想要个公道,男孩父母害怕受到对方的伤害,于是加强了防护,并因此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他们越来越紧张,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形,在一切接近崩塌时,女孩的家长消失了,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他们的生活究竟是否会恢复原样。
大部分创作者在遇到这个素材的时候会怎么处理?通常的方法是延展,在讲述家庭背景后提供充足的心理动力——注意,这里不是在说心理动机,那是给故事推动用的,而动力是建立人物形象的——不同的心理动力会建立不同的行为逻辑,而不同的逻辑彼此相遇时就会造成冲突,这样的冲突被事件化后我们就找到了矛盾,也就是核心事件。假如核心事件塑造得出色,那么在精准地描写了事件来临时人物各自的反应后,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小说的骨架,基于这个骨架,我们提供足够深刻的思考就可以得到主题,然后经过修改和润色,一篇小说的创作就完成了。
当然,也会有另外的创作方法,基于素材本身的事件,模拟着参与者各自有可能的行动和心理进行想象,方向没有限制,事件在此刻不指向任何特殊的预设,当灵感降临,故事的形状不再和素材产生因果关系,于是千人千面,这本就是创作这件事让人着迷的地方。
那么让朱阅平显著不同于其他创作者的地方肯定就不是所谓的“故事”本身了——因为故事本来就不会,也不应该相同——而是他的讲故事的方法。这里说的方法也并不是他的语言,尽管朱阅平在写作时很克制,但还称不上已经达到“风格”的评价。我所说的方法,是指创作者的形象不参与故事。
视角的讨论或者说研究已经近乎泛滥,无论是文学史,还是专业领域方面的研究,都可称得上汗牛充栋,但如果从专业培训写作能力的角度出发,大部分直接得到结果的学习者很容易陷入一种错觉,那就是在对人物进行描写时提供“他”的心理状态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方法有很大的益处,不但“全知”而且“逼真”,相比于曾经主流的“夹叙夹议”还避免了“创作者”进入读者视野从而让读者脱离“代入感”的弊端。但我要提醒学习者的是,心理状态的提供可以带来益处的前提,是行动描写和语言描写力不能及之后,而不是同时,假如你的作品不是特意去揭示“心理”的话。
《尤利西斯》的伟大在于剖析了灵魂,这样写不但成立而且成为必需,可《西西弗的神话》解释思想时使用的是直接的行动,由此再联想到《城堡》,“人”的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描写也可被展示,或者说,茨韦特科夫的困境在契诃夫的笔下只用对话和表情描写即可完成内心最细微、最阴暗的欲望呈现,那么对大部分的“素材”只是为了成为合格的“故事”的创作而言,心理描写确实是被滥用了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偷懒。
《书包,书包》全文1 万字,1 个核心事件,6 个情节,行动描写28 处,对话14 处,出场人物11 位,只有一处心理描写,那是男孩母亲担心儿子受到女孩母亲报复伤害时做的噩梦。它的作用巨大,让整个故事得以确实发生,也让最后的结局让人无措而悲伤!
看一个人,不要看他怎么说,而要看他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我不需要你说出来,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