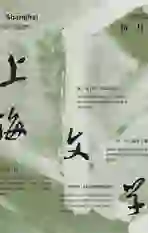耕堂聊天记往
2022-06-28谢大光
谢大光
偶然看到一本二○一七年的刊物,封底彩照为孙犁故居,说明文字:“作家孙犁故居,天津市南开区玉泉路学湖里小区十六号楼三门三层。一九八五年建成,为六层曲线型条式楼,天津人俗称‘蛇形楼’。孙犁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居住于此,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他一九九五年正式封笔。”
照片应该是对的,文字有出入。孙犁一九八八年八月才从多伦道搬到学湖里,按当时建制,学湖里属鞍山西道;地址也有误,准确说应是学湖里十六号楼二门三○一;说孙犁“晚年的大部分作品在此完成”,不准确,耕堂随笔十种,只有《如云集》《曲终集》两集,大致算在新居完成,因为《如云集》中不少篇章还是在老宅完成的。有人会觉得,我这样对着一幅老照片吹毛求疵,该不是没事找事闲得难受吧。实话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心里另有所属。
一九七九年第一次拜访孙犁,他住在多伦道二一六号,这是一处旧时的花园洋房,据说原为一政府要员的公馆,后来做了《天津日报》家属院,住进十几户人家。孙犁住大院南面一处平房,与李夫相邻,该是“公馆”前厅,门前有露台、回廊,室内高大轩敞,采光却不好,被一长溜书柜隔成两爿,里间卧室,靠南窗一边做书房兼会客室。这屋子中看不中用,冬天灌风,夏天漏雨、嘈杂,住着并不舒服,更不适于写作,孙犁曾以“空荡,破旧,清冷”形容,与友人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住的是间老朽的房,窗门地板都很破败了,到处通风。冬季室温只能高到九度,而低时只有两度”,“一到夏天下起雨来,每间屋子,几乎无处不漏”,“入夏以来,庭院大乱,我什么也干不了”这样的话。就是在这里,孙犁“闭门谢客,面壁南窗,展吐余丝,织补过往”,写出晚年大部分著作。一九七九年以后,我常到多伦道看望孙犁,开始是约稿、取稿、送校样,后来,有事没事也来聊天。有朋友曾提醒,这样的机遇难得,先生谈了什么,每次记下来,以后有用。我很享受与先生无拘无束地聊天,没在意,偶尔也会追记一点先生言谈,正式一些的留在本子上,更多是随手记在纸片上,时间长了,散在各处,忘记了。好在我有一个习惯,不随便丢弃写有字的纸,这两年准备写点回忆,彻底清点从单位拉回的旧物,才把散乱的追记归拢整理,就作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吧。
一九八○年二月十日上午,陪滕云拜访孙犁。滕云当时在社科院文学所,有意下功夫研究孙犁著作,很想当面向孙犁请教,又怕谈不拢,冷场,拉我作陪。滕云刚刚从湖南、广东考察回来,见到萧殷、黄秋耘,谈话从萧、黄二位与孙犁的交往开始,气氛融洽,时间也超出滕云预料。孙犁正在准备与《文艺报》吴泰昌的谈话,想得比较深,谈到政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也谈到艺术和政治还是有所区别。文艺评论是学术范畴,不能按照政治需要搞。“我赞成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像王国维那样,几句话都是站得住的,我很佩服。胡适之的小说考证也是扎实的学问。罗振玉是汉奸,可是搞了不少碑帖,都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那是硬挖出来的呀!”“今年过春节来人多,但并不觉得太累。接待人多了,有经验了,学滑了。来人我想法让他们自己说,或拿出作品来请他们看。这样我就省力了。”说到这里,孙犁哈哈大笑。说到文联作协恢复工作了,作家协会应该扶植创作,不要妨碍创作。“现在作协就是妨碍创作,起码妨碍我的创作。我坚决不干这些。我是很胆小的,很怕得罪人。写东西是要考虑这些。你们更为难一些。我完全能理解。河北作者写的一篇小说,传说我给韩映山寫信批得很厉害。其实我都没看过。大年初一收到信,马上回信说明情况。这样的事太不正常了。”
滕云说,现在希望开一个孙犁作品讨论会的呼声很高。孙犁说,这事我从不表态。花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新东西,就不好了。我那点东西,本来就浅,在浅的里边再评得更肤浅,实在没什么意思。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熟悉我那个时代的生活。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与同事李蒙英一起到孙犁家。孙犁谈到市里召开文艺座谈会,他头晕,又怕引人注目,这种人多的场合,最怕引人注意,坚持到市委领导同志讲完话,已经精疲力竭了。会后,袁静、王昌定等多人找他。他已书面提出,坚决不当作协主席。这些人来劝他当。孙犁说,他们还需要我做个幌子。实在无聊,把作协变成了权力角逐的官场。这是自古没有的。很气愤。坚决不当。后又谈及为刘绍棠《蒲柳人家》写的读后记(这篇读后记八月七日写出,发表时标题为《读作品记(一)》)。刘绍棠看后说,北京的一些老作家,都不像您这样直言。(《读作品记(一)》有这样的话:“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思考与发掘。”)孙犁说,这些人你们不要得罪。我老了,我不怕。对有成就的作者,只捧,会断送我们的事业。但现在多数人都不这样说。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绝不说违心的话。有看法就是有看法。当时拿去给《新港》发,表示还要写一篇读从维熙《泥泞》的。他没有妓院生活,而写妓院,漏洞百出。下等妓院哪还有什么大衣柜,有什么特殊房间。那样身份的人,也不会到下等妓院去。是哗众取宠,投一部分读者所好。这一部分和全书,没有什么有机联系。
一九八一年初,一天,北京宗璞打来电话,想专程来天津看望孙犁,听说孙犁住所门上贴了纸条谢绝来访,问我是否属实。我解释说,孙犁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不近人情,你来,他一定欢迎。宗璞说,那就请你陪我去吧。宗璞是个周四上午来的,我事先已和先生打了招呼。我们到时,先生已经在等候。彼此没有多少寒暄,直接谈起了文学。孙犁之前没有读过宗璞小说,知道她做外国文学研究,所谈围绕着近年读过的一些翻译作品。孙犁说在《儿童文学》上,重新读了安徒生的《丑小鸭》,心里好几天不能平静。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丑小鸭》好就好在声东击西,有弦外之音。这样的作品不多。又说到俄国作家库普林的两个短篇,发在《百花洲》上,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个行动,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这是很厉害的。还有普希金的《驿站长》《茨冈》。宗璞走后,孙犁对我感叹,不愧是名门之后,谈吐就不一样。没过几天,孙犁读到宗璞新作小说《鲁鲁》,写下《读作品记(四)》,“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里一天,去孙犁家。先生心情很好,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两张稿纸,是刚刚完成的《尺泽集·后记》,“你看看,提点意见。”文字不长,我很快看完,感慨地说,“写一篇序跋,您都这么动感情!”孙犁突然说,“嗨,我最动感情的文字,你还没看到呢。”我大感意外,忙问。孙犁有些卖关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动感情的是给张保真的信,有二百多封。后来分手她还给我,我一时气不过,投进炉子里,一把火烧了。”我连连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孙犁也说,“是呢。事后也有些后悔。那几年通信密,常常是她的回信还没到,我的信又寄出了。两个人的信在空中交汇。”(边说边做手势)我又问起,那您知道张保真现在的情况吗?孙犁说,“听说到国外去了。和前夫又在一起了。”我紧跟着打趣说,“看来您还是惦记人家。”孙犁不再说话。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友谊宾馆探访四川作家周克芹,周刚刚拜访过孙犁,忍不住谈起感受:很早就想来看看孙犁,去之前心情很紧张、激动,因为过去感到孙犁是个对青年人很严厉而爱护的老人。从文章看,由于上了年纪,可能爱生气。一见面,谈得很高兴。孙犁也很激动,说到,给《人民日报》写“小说杂谈”中,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批评(孙犁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写下《小说的抒情手法》,谈到“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坛,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今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点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有人说是吹毛求疵。我说,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感觉。孙犁说,我都是认为很好的作品才去讲的。一聊开了才知道,孙犁不仅看过我的长篇,还看了几年里发表的所有短篇,连在地区小报上发的答记者问都看过,真有心心相通之感。很感动。孙犁也说,和志趣相投的人相谈,是非常愉快的。我同意这种说法,就是繁荣的标准,是看塑造了多少感人的能保存下来的艺术典型。我写小说从不编故事,让人物活动起来,一活动就要和周围的人发生关系,就要有矛盾冲突,就有了情节。高晓声的陈奂生就是个典型。生活问题主要是个感情问题。深入生活就是要积累感情,感情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就会出来作品。有生活不一定写出好作品,要思考,要认识生活,提炼生活。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八日周三,上午到孙犁家。他拿出给《人民文学》谈散文的稿子(此稿发表时,题为《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让我看,并请我代他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我边读边发表议论。读到“文章要感人肺腑,只有出自自己的肺腑,才能够感人肺腑。读者都是具有良知良能的,不是阿斗,你言不由衷,人家就会看出你在骗人。有几分真诚,读者是看得很清楚的。”“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主要经验是:所见者大,取材者小(即以小见大),都取自日常生活的言谈、事件、与人的关系。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好的散文必须是真诚和朴实的。要敢于说出真心话,是不容易的。只有抛掉种种顾虑,才能写出好文章。”我深有感触。
后来谈到,现在学校里语文教学,讲什么段落大意、主题、结构,大多是老师自己的臆想,和实际创作很隔膜。我说,看女儿作业,老师讲的主题就是各段落大意合在一起。孙犁大笑。
孙犁说,上海一位老师来,问《山地回忆》是怎么构思的,我说没有什么构思。他不信,说,我就是要写谈你构思的文章。我说,你就为他写文章而“构思”吧。孙犁大笑起来。又说,一天河南、上海,两个编辑来约稿,河南是一写作杂志的,带一个大皮包。孙犁说是皮包编辑部,上海人忙说,我们不是,是教育出版社的。又谈到佛经翻译对中国散文的影响。谢灵运就曾参与其事。鲁迅也谈过。《红楼梦》里很明显,谈禅学。
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半到十一点半,和孙犁约好谈童年与家世。事先读了《我的童年》《在安国》《自传》《听说书》《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书的梦》《猴戏》等篇,拟定要提的问题:
和父亲的关系:期望过高吗?独子?父学徒到哪年,常回家吗?
是原始住户,还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
对母亲的印象。
最初的女性印象——安国的表姐?干姐?
第一次读《红楼梦》,看得懂吗?有什么印象?
《书的梦》中“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开始与书结缘?
《画的梦》中“赶年集和赶庙会,是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孤僻?
为什么说,“为衣食奔波,而不感到愁苦,只有童年”(《度春荒》)?
《木匠的女儿》中,对于村子的介绍,是否就是童年的生存环境?
《菜虎》中,“这种手推车的歌,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夸张成分吗?
开始,孙犁对这种聊天方式不太习惯,点颗烟,说得很慢,渐渐沉浸在回忆中,眼睛眯起来,似乎我这个提问者已不存在。孙犁出生时,父亲的情绪,既高兴又担心。上边五个孩子夭折,不知这一个能否活下来。当然,农户家死个孩子算不了什么,叫“干巴”扛出去埋了,就是了。这个村子很穷,逃荒的多,外出学手艺的多,有闯关东的,也有去上海的,但赌风颇盛。人们似乎要在赌场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要以此刺激填补空虚的灵魂。
事先命题的聊天仅此一次,我当场做了笔记,整理成《孙犁谈童年》《孙犁谈母亲》两篇文字。这种方式我也不习惯。我发现,在耕堂,和孙犁单独相处,最适于漫无目的的闲聊了。这个住着并不舒服的房子,倒是个聊天的绝佳所在。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去孙犁家拜早年。孫犁兴致很好,说得也多:今年春节我又忙了。帮忙的(玉珍)回乡下老家。我一人,要管两个炉子。每天六点起床生炉子,白天时时要注意,搞不好要灭掉。这样活动多了,反而胃口好了,能多吃些饭。中午孩子过来帮忙做点饭。我平常喝粥喝惯了,孩子来了,又赶上过年,当然要弄点肉。今天倒觉得肚子有点不太好。外孙女天天中午来,她爱吃鸡,我平常也不弄鸡,她来了,就弄鸡炖白菜。昨天我把鸡热上,盛好,中午她去奶奶家了,我只好自己吃掉。谁知一不小心,让一小块鸡骨头,把个牙硌掉了。牙已经糟朽了,就这么个小骨头。人老了,真不知会遇到什么事。
我说,你这样为炉子尽心忙活,炉子感觉得到,吃得多了,心情也好,因祸得福啊。可以写个《炉子》的续篇了。孙犁笑着说,写作真是可以锻炼人的好事。我有时有些不愉快,一钻进去写,就什么都无足轻重了,只有我这个文章最有分量了。勉励我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把精力用到写作上。对雪杉(诗人,我的百花社同事)也这样讲。我说,我这个年纪,还没有到宠辱皆忘的岁数。有些事,你不去找它,它来找你。总是不得安宁。我又联想到,上次和李蒙英来看孙犁,孙犁说起,每天晚上钻进被窝,总要披着上衣,点着一颗烟,坐半天。想的就是一件事:晚年怎么办?想来想去没办法。李蒙英说,找个老伴吧。孙犁说,早几年还可以。现在建立不起感情来。人不是一件东西,一盆花,可以随便搬进来搬出去。想想很是凄惶。
正聊着,沈金梅(评论家,《天津文学》副主编)敲门进来,说有个外语学院的日籍教师,临回国前,想访问孙犁。孙犁说,说我身体不好吧。婉言谢绝。我是下决心不见外国人了。要做很多准备,房子,衣服……前一天有人来给我照相,彩色的,还要拿到美国去洗。洗出来一看。我的裤子没系扣。真是没办法。有些外国学者要来,我都挡驾了(还是外文出版社社长,我们延安一起共过事,介绍的法国人)。有个青年作者,认识了一个英国女朋友,要我签名赠她书,我说不行。我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孙犁想起姜德明推荐《洪宪纪事诗注》,托沈金梅替他买。又说,老了,什么都想维持现状。不想搬家。不想来客人。不想过年。变化就可能带来事情,打乱正常生活。准备写些读书记。读《魏史》和梁启超的书。《饮冰室文集》太多,六十卷,看不过来。梁启超对推行新学是有功劳的,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投稿)对报刊的态度很敏感,稍有厌倦的表示,立即停止寄稿。《羊城晚报》关国栋不在,发稿就慢多了。现在对史籍感兴趣,对文学反而淡了。前几个月手抖得厉害,我真怕握不成笔,不能写作。那可该怎么办?现在好了。看来还是和心情有关。
说着话,孙犁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八行朱栏宣纸笺,北京许姬传来信。许是从姜德明给他的《天津日报》上,读到孙犁写关于王国维的文章,希望能看到全文。许在信中讲到其曾祖与王家的世交。孙犁说,现在能写这样信的人不多了。字好,写得好,规格要好,可以当个艺术品收藏起来。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去广州、深圳、上海月余,回津上班第一天,先去探望孙犁。《羊城晚报》万振环托我给孙犁带了一些广东土特产。已是下午五点多,小外孙女正在,十岁左右,长得很俊秀。孙犁对其十分疼爱。向我问起广州及沪上诸友。说肖关鸿来信,很热情,他感激。又说,我爱看熟人的作品,可以了解得更多;又问《解放日报》的吴芝麟,有一稿寄去一个多月,未见回信。我只有帮朋友打掩护,说他们太忙。忽然又说到中国作协让他去新加坡,和姚雪垠同行。有个写小说的,再找个写散文的,很难找,想到了孙犁,还考虑到新加坡是华语国家,生活习惯相差不多,很照顾了。马丁(天津作协秘书长)来问,孙犁说,我天津的活动都不参加,还去新加坡吗?又说到平生仅一次去苏联,人多,二十多人,好几个团长,不用他出面应付说话。他每次都是躲在人后边,弄得苏方接待人员都问翻译:这一位怎么总是一人向隅,郁郁不欢?也拿他没办法。打领带都要李季给他打。“我一辈子对这些,一点欲望都没有。”说到写作要甘于寂寞,我说,这些我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孙犁说,你们没有这个条件。我是几十年形成的,人家都知道,无形中批准了。连丁玲去厦门过八十大寿,原想让我去,后来自己就否定了:孙犁肯定不会来的。
我谈到对广州、深圳的看法,经济发展快,文化气息淡薄,难得出好作品。孙犁说,文化是要有闲的,要有时间,从容搞来,紧紧张张、分秒必争的空气下,无法搞艺术创作。
又说起出国的事,“这辈子不想出国了。”我说,“别说绝对了。要是给你诺贝尔奖呢?”孙犁哈哈大笑。我曾经写过孙犁的笑,这是毫无戒心的痛痛快快的笑,在这个空阔的房间里,这笑声填充每一个角落,震荡着屋宇。
我又问起那两首诗,《眼睛》和《甲虫》。孙犁说,寄给《诗刊》一个月,未见回音,给邹荻帆一明信片,邹回信说,《眼睛》不错,有哲理气息,把《甲虫》退回来了。孙犁笑着说,把我的“眼睛”留下,“甲虫”退回来了。我对人说,要不是大光说行,我这诗只有放在抽屉里,不敢寄出去。
我认真地说,“《眼睛》是你诗中最好的。”孙犁笑而不答,并说:“写诗就要灵机一动,计划好了就不行。《眼睛》就是偶然想到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和李华敏(百花社同事)去看孙犁。这个时间,孙犁不写作,来客亦少,适于聊天。果然,孙犁正闲坐吸烟。说到因文字引来的麻烦。孙犁说,李准写信,用“撞钟”来开导我。钟一敲就响,总有人敲;敲一下不响,就没人敲了。我说,这个道理我懂,但一遇到具体事,就沉不住了。我是一敲必响。还是修养不够啊!
我说在电视上看到吕正操打网球。孙犁说,学生时代,他也爱打网球,而且打得还不错,只是发球总不过关。现在还常常梦见练发球,将球高高抛起来,用力扣下去。又一再对小李说,编辑要写作。你写了拿来,我给看看。我现在只能给青年初学者看看、说说,有点名气的就不敢了。谌容昨天来,问我意见,我说,系统看看再说。我哪敢说什么呀。不只是她,就连铁凝,我现在也不敢说了。我说话常不注意。问谌容多大?答:四十八了。我说,正好。弄得她后来一头雾水,问柳溪:“嘛正好?”其实我的意思是正当写作的年龄。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周四),在耕堂,孙犁问到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们一家,父母一辈从山西来天津,乡土习俗重,到今天一家不吃鱼,勾起孙犁的回忆。他说,当年我们在晋西北,生活很苦,从河沟里捞上来些小鱼,房东不让用锅煮,只好拿茶缸子煮煮吃。当地人不只不吃鱼,连鸡都不吃。鸡死了,都埋上,不用说杀鸡了。养鸡只吃蛋。山西人我接触不少,老家县城里开染坊的,保定开钱庄、银号的,很能吃苦。从小出去,七八年不能回家(我谈我父亲在西安商铺学徒情况)。和山西作家接触不多。赵树理认真讲就见过一面。他来天津,当时我住后边小屋。他很有才华,在这辈作家里,底子厚。很可惜。(我说,赵写《三里湾》和孙写《铁木前传》时间差不多。孙没写完就病倒了,而赵以后写的也不行了。真正的文学生涯也是到《三里湾》就结束了。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孙犁说,他开始写《铁木前传》在一九五五年,后来一反胡风,写不下去了,拖到一九五六年。有人說,作家不受政治的干预不可能的,多么大的作家,也做不到。郭沫若、茅盾、曹禺,解放以后都没有写出什么。(我说,你晚年写了这么多好散文,是不容易的,出乎人家的预料。)孙犁说,其实都是些小文章,就是写得多了,才引起注意。写个一两篇,就不行。其实,写来写去,就是这么些东西。我不是不想看一些外国新作,下不了这个决心。你刚才说的三十多万字的《百年孤独》,我就下不了决心看。(我说,你是聪明的做法。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写散文。如果花几年时间,写《铁木后传》,就吃力不讨好。)孙犁说,我是写不出了。其实我是个懒人。没有情绪,写不出时,绝不去硬写。
我说,您的情绪倒是经常有。您还不是那种对一切都不感兴趣、都无所谓的老人心境。而是对很多事物还有兴趣,常有所感。否则,我就看不到这么些散文了。孙犁不吭声,笑。又问到我的家庭生活,住房情况。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周六。一早和李华敏去看孙犁,先生正在院里散步。昨天因邻居家做木工,没睡好,今天晚起一小时。说起做梦,我问:您写的梦特多,为什么?孙犁说,我好做梦,往往是一场梦醒来,才知道我确实睡着了。经常是噩梦。这是神经衰弱。(我说您睡眠质量不高。我经常是寻梦不着。您将来可以写一组芸斋梦谈。)
孙犁说,中国的哲学讲究将人的本性善诱发出来,本性恶压抑下去,重视道德的作用、后天的教育。粉碎“四人帮”之后,意识形态没有大的进展,总要有一个主导。什么能代替马克思?萨特恐怕不行。西方也没有一个主导的思想。我们也混乱。给《人民文学》王扶写的封二的话,三段,都是平常想到的,记在纸条上(来信裁下的白纸)。第一段讲艺术感觉来自艺术修养,修养不够,一遇时机,就易流入庸俗;第二段讲读者与作者关系的恶性循环,写书,读书,要有主导,否则就会导致恶性循环;第三段尤其厉害,写有些人迎合洋人口味,写中国人的落后面,实际是买办文学,等而下之。还有一段,写、出、吹捧坏书,都是为了钱。由阶级斗争为纲,一夜转为金钱为纲,是文学的悲哀。有一位姓韩的战友,想借《金瓶梅》,我不愿借,想办法给他买一本。写信给秦兆阳。结果说,拿到人文社出版部,一提孙犁的名字,没找秦兆阳,就卖给了。“想不到,我的名字还有这样的分量。今后可要珍重一点了。”说毕哈哈大笑。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一日,周五,由报社去孙犁家。孙犁正在整理书,准备搬家。旧书装纸箱,已装了八箱,新书装了五大木箱,还没完。见我来了,说正好休息休息。聊天谈及年轻时,在北京求职的情况。自年幼时体弱多病,农活干不了。父亲从商,伤了心,不愿儿子再从商。供上大学又不可能,只求一个安定的饭碗。高中毕业后,到了北京,原想卖稿为生,写了很多,投出去无消息,少数发表,稿费也很少,最多的一次三块,有的(如开明书店)只给几张购书券,实在太抠(看到叶圣陶回忆录也提及);什么都写,影剧评、明星演员介绍、杂文小说,大都未能留下来。记得沈从文编《大公报·副刊》,投稿寄去未用,退回的稿子上,有亲手改过的痕迹,很感动。无法谋生,父亲托人活动,在市政府某科任书记员,抄写文书。每月二十大洋,后来靠山调任,一朝天子一朝臣,遂被解聘,又活动到某中学任庶务,比看门的略高一些,每月十八元,实在不想干,这才由同乡荐至同口镇中学教学。那时对老师重视,心里很舒畅,受到尊重。在京期间,父亲来信让考邮电局的捡信员,英语口试未过关,淘汰。父亲和故乡邮局局长熟悉,从小希望他好好学英语,将来入邮局,铁饭碗。上学时英语水平可以,但口语不行,考试人又多,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等。其实就是一个捡信员的位置,英文也用不上几次的。北京终究是政治文化中心,流落求生的学生很多,大都带着一个梦,其实求职真不易。见识多了,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理论上的,鲁迅、普列汉诺夫。作品发表不了,不怨别人,是水平不行,达不到要求。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湮没的。写作的契机是抗战,各方面都需要人,队伍中有个高中文化,能讲出几个理论词儿和人名,就认为是了不起。有机会发挥了作用,才放开胆去写、去做。
孙犁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迁居到学湖里。新居比多伦道房间多,有暖气,生活方便,但屋子矮了,间量小了,没有院子,出门要上下楼。用孙犁致姜德明信中的话,“新地方有些新情况”,“就是安不下心来,从八月到今,已经四个月没有动笔,每天想定个题目,写点东西,就是定不下来”。孙犁新居离出版社远了,来往不如原来方便。第一次到新居看孙犁,老人穿了件新衣服,加上环境有陌生感,感到双方都有些拘束,聊起来不像原来那么放肆。去耕堂的次数少了。一九八八年十月,天津日报社首次召开孙犁作品学术研讨会,会后去看孙犁,还没落座,孙犁向我问起会议情况,并说,“听说你在会上发表了新论。”一听这话,我心里有些紧张。孙犁对文坛上的新思潮、新观点,历来有自己的判断,常说,“贩卖旧货,以为新奇,实今日文坛之特点。”我知道,有人提前向孙犁通报了会议发言,不知道如实,还是添油加醋。其实我在会上本不愿发言,听到太多的重复,才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孙犁所取得的文学成就,除了其他因素,还和一生中两场大病分不开,一是幼年患惊风,养成敏感、内敛、爱独处、怵交际的习性,加上喜欢读书,联想丰富,逐渐形成日后的艺术气质;二是一九五六年写《铁木前传》时,严重神经衰弱,导致匆匆搁笔,这一次患病使孙犁躲过了政治风浪,有从容读书、思考的机会。没有这两场病,就没有今天的孙犁。听我复述完毕,孙犁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上午,陪同万振环全家看望孙犁。老万在《羊城晚报》编“花地”副刊,从一九八五年始,经手孙犁来稿,由于编辑用心,处理及时,深得孙犁欣赏。那些年,我常到广东出差,每次回津,老万总要让我捎些广东小食品给孙犁,当时老万的儿子万志新还在上小学,也让我带一盒糖果给孙爷爷,还附上一封问候的信。孙犁特别看重小孩子的心意,说,小孩子的感情是最纯洁的。这一次,老万偕妻子、儿子专程来津看望,孙犁很高兴,望着个头快赶上他爸爸的万志新说,“这就是志新?长这么高。你送我的糖果、柚子,都好吃。谢谢你呀。”孙犁又对老万说,“你们发我的作品快。我也乐于为你们写稿。今年写新居的几篇短文,一次全见报了。挺难得。”又说,“我老了,写长篇没有精力,只能写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老万说,“您这些短文可不容易写。短小精悍,在我们报纸发出,很受读者欢迎。”话题扯到物价上,孙犁说,“现在什么都讲究经济效益。我喜欢用明信片,以前寄一張只要四分钱,现在涨到一毛五了。”临别时,孙犁与老万一家合影留念,还单独与万志新照了一张。
一九九五年四月的一天,去看孙犁。聊天时孙犁说,现在看,早年存一些线装书太对了。字大,纸白,书轻,看得很舒服。新书一打开,阳痿广告,错字连篇,印刷不匀。很堵气。说两件好笑的事吧。《新民晚报》严建民要我写字,一拿毛笔就紧张。我这人小气,怕浪费纸,怕写错字。寄稿子,用自己糊的信封,结果自己封上的一头打不开,成品的一头好打开,拿出稿子时,把一点连到了笔画里,“万”字成了“方”字。熟悉的编辑会把关。那也不容易。给《羊城晚报》的稿子,“到独单”,“独单”是方言,广东人不懂,疑为“单独”,给改成“单独到”。天气不好,就在阳台上活动,亲眼见邻居一老人,过马路时胆小,问着司机倒车吗?正巧司机在倒车,撞倒在水里了,后来再出来就坐上了轮椅,现在就见不到了。
我看先生这两年明显见老,问起身体,说是其他都还好,就是牙不行了,都磨平了,像老马一样,咀嚼的功能退化了。睡觉也不行,常睡一会儿就醒来,再也睡不着。每天早上还能出去转一下,警惕自己别摔跤。
没过多久,忽然传来先生生活失常的消息,不理发,不刮胡子,不思饮食,不愿见人。我知道,先生的精神又受到刺激了,以先生的脾性,这个时候最不愿意让熟人见到。只有默默祈祷先生能够康复。后来儿子晓达把先生接去了。一九九七年夏天,听郑法清说,孙犁住进了医院,在总医院高干病房。我和几位同事相约去探望。一间挺大的病房,孤零零放着一张病床,先生闭着眼平躺着,原来高挺的身材,瘦小了许多。我们几人排着队依次到床前,前面的人说着问候的话,先生始终合着眼,轮到我上前,我握住先生的手,刚要说话,先生突然睁开眼,问,“万振环有信来吗?”我心中一阵喜悦,孙犁还是原来的孙犁。我赶忙趋近一步双手紧握,连说,“有哇,有哇。老万来信,每次都要问到您。”先生又闭上了眼。这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