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译佳作:金斯作品的民国译介
2022-06-16余恒王洪鹏
余恒 王洪鹏
天文学作为最古老的自然学科之一,一直是科普图书的重要主题。在民国时期,我国的专业天文学工作者寥寥无几。市面上大部分天文科普作品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尤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金斯(J. Jeans)爵士的作品最多,达到了8本4种。其中,《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有两个译本,而《流转的星辰》(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甚至出现了4个不同书名的独立译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英国国力强盛,科技发达,是引进科普作品时的首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金斯的作品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广受欢迎。
金斯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科学家,在应用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他毕业于剑桥三一学院数学系,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应用数学系。起初,金斯的兴趣在粒子物理领域,曾修正英国物理学家瑞利(J. Strutt, 3rd Baron Rayleigh, 1842—1919)提出的黑体辐射公式中的错误,更新后的公式也因此被称为瑞利—金斯公式。1914年后,金斯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天文学领域,工作涉及旋涡星系、恒星能量来源、太阳系起源、巨星、矮星、双星等诸多领域。他和爱丁顿(A. S. Eddington, 1882—1944)同被誉为英国宇宙学的创始人。金斯所提出的物质云塌缩的临界质量(金斯质量)和临界尺度(金斯长度)至今仍是重要的天文学概念。因为工作出色,金斯在1925至1927年间当选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主席,于1928年受封爵士。但是金斯所坚持的稳恒态宇宙学理论没有获得学界认可。1929年之后,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公众讲座和科普。金斯撰写了多本科普书籍,以平易通俗的写作风格赢得了大量读者和赞誉[1]。其中最著名、最畅销的当属1930年出版的《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
《神秘的宇宙》来自金斯的一场高级讲座。1930年11月,剑桥大学副校长拉姆齐(A. Ramsay)邀请金斯在剑桥最高层次的“里德讲坛” (The Rede Lecture)上进行年度讲演,题目便是“神秘的宇宙”。金斯在报告中以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类比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时最新的科学理论以及它们所引起的哲学思考。在演讲的第二天,讲座内容的扩充版以《神秘的宇宙》为名出版。
《神秘的宇宙》一经问世就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短短几个月内就在英国卖出7萬册。该书在1931年仍保持很高的销量,前后重印8次,又推出了修订版[2]。它不仅是畅销书,更是常销书,直到1948年还在重印。这对于一本科普书来说非常罕见,只有半个世纪后霍金的《时间简史》差可比拟。
这本书还曾受到美国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S. Weinberg)的推崇。他在2015年将这本书与伏尔泰的《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等书一并列为“13本最适合普通读者的科学书籍”。
《神秘的宇宙》出版后,中国也有学者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本现象级的科普作品。1932年北平震亚书局出版了金斯“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一书的中译本,名为《宇宙及其进化》,书中“最近出版广告”部分还预告读者,该系列第二册将推出《神秘的宇宙》。这本书的策划和译者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张贻惠(1886—1946)是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进士,自己也在1898年考中秀才,科举废除后,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公费留日学生。1914年,张贻惠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物理系,随后回国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南京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等职务,曾作为首都高校代表出面营救李大钊。他还创建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积极推动全国度量衡统一工作[3]。在紧张的工作间隙,他仍不忘科学普及事业,策划编译科学丛书。张贻惠在《宇宙及其进化》一书的序言中写下自己对科普工作的看法:
“一个科学家主要的工作,自然是在实验室里,或著作室里,仔仔仡仡的,作那实验或理论的研究。但在科学落后的国家,像我们中国,把科学的思想,普及到社会,似乎也是很要紧的一件工作。……当然科学书本不易销行,在科学和经济都落后的中国,更不易出版和畅销。也是阻碍这些书,大批出现的原因。不过科学书,出现越少,正是表明他出现越重要,越需我们努力。”
第一本书译完出版后,张贻惠受委任成为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终日忙于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无暇顾及译著。后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西迁。译书之事就此搁置。日本投降后,国人终于有机会重整河山,年近花甲的张贻惠前往华北视察接收日本投降移交的机构设施情况,却因飞机发生事故致使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
于是《神秘的宇宙》直到1934年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周煦良。周煦良(1905—1984)毕业于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1928年,周煦良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学习文科,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1933年任职于福建省政府,在福建省政府抗日反蒋运动失败后,周煦良辗转回到上海家中闭门读书。为了解近代物理学对哲学的影响,周煦良找来《神秘的宇宙》边读边译,完成后由开明出版社的编辑顾均正列入“开明青年丛书”出版。
就在周煦良在上海开展翻译的同时,还有一位译者也在从事相同的工作。他叫邰光谟,在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工作。这位译者的生平不详,只知道他在 1916年毕业于陈仙樵担任校长的天津市武清县杨村小学。1929年,邰光谟于清华大学获土木工程学位,第二年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任文牍员,后来又进入天津北洋工学院。当时许多高校院系都有自己的出版组,负责编译教材,以供教学参考之用。邰光谟在1933年12月完成《神秘的宇宙》一书的翻译,1935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入选“万有文库”而广泛流传。

《神秘的宇宙》是周煦良翻译的第一本书,态度极其认真。出版社请他写序,他便“天天跑北京图书馆,连海森伯(W. K. Heisenberg)的书都借来看了。花了3个月时间,写了一篇8000字的序文”,占到了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周煦良父亲拿到样书后还是写信批评他说“有些句子简直像外国话”。不过,和后出的邰光谟译本相比,周煦良的版本还是更胜一筹。例如:第四章的标题是“Relativity and the Ether”,周煦良译为“相对论与以太”。这与今天的表述完全相同。邰光谟译为“相对理论与能媒”,虽然在当时的语境下并不算错,不过这两个术语在后来的使用中没有被广泛接受。第五章的标题“Into the Deep Waters”是个形象的说法。金斯在文中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比作沿着“知识的河流”去探索“真理的海洋”。周煦良把这个标题译为“知识的深渊”,如实地传递了原意。邰光谟将其总结为“神秘的宇宙概观”,有失喻体,未免过于笼统。
正文能够更好地体现两位译者的水平。金斯在全书最后这样总结人类对自然的认知:
“We have tried to discuss whether presentday science has anything to say on certain difficult questions, which are perhaps set for ever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understanding. We cannot claim to have discerned more than a very faint glimmer of light at the best; perhaps it was wholly illusory, for certainly we had to strain our eyes very hard to see anything at all.”
周煦良是这样翻译的:“我们不过试行讨论,今日科学对一些困难问题能回答些什么,这些问题也许永远非人类智力所能及。我们只能说,我们至多只能辨别一点黯淡的光,这也许完全是幻象,因为连要看见这点黯淡的光我们都得费去极大的目力。”
邰光谟的译文是:“我们曾经打算讨论科学对于某种困难问题,有什么主张可以发表,而这些问题也许原来就放在人类的知识范围以外。我们所辨识的,充其量也不能再多于一些极黯淡的光明,或许竟完全属于幻觉,因为我们必须努力使用我们的两眼,才能看见了什么。”
这段文字虽然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但也被金斯处理得简单明了。从译文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的文字水平无疑存在差距。邰光谟有一些明显的漏译和误译,汉语的表述也过于拘泥于英语句型。
如果说《神秘的宇宙》一书出现两个译本是个巧合。那么《流转的星辰》(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简称The Stars)一书出现4个独立译本就充分说明了金斯作品的魅力,以及民国学人对天文知识的强烈兴趣。
金斯在“里德讲坛”的讲演大获成功后,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邀请制作了为期6周的系列讲座“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向完全没有科学背景的普通听众介绍现代天文学概貌[2]。他在讲座的基础上扩充整理而来的同名科普书“The Stars”也很快出版。金斯从人们熟悉的日月星座讲起,由近及远地介绍了各类天体——日月行星、恒星、银河系、河外星系,以及宇宙的特征和演化。该书不仅文字通俗,描写生动,还采用大量真实的天文照片作为插图,对不了解天文学的读者也很有吸引力。因此,张贻惠选择这本书作为“科学丛书”系列的第一本,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本书)用极平凡的名词,富有趣味的文句,叙述深奥的科学原理,使读者忘倦。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周围的宇宙》的节本,扼要删繁,似乎更适合于偕俗的阅览。无论什么人,阅读一过,就可以得到近代天文学的一个大概观念。……本丛书的第一部,得采取这个兴趣广泛,关于天文学的本书,作为发轫,是编者所感到最荣幸的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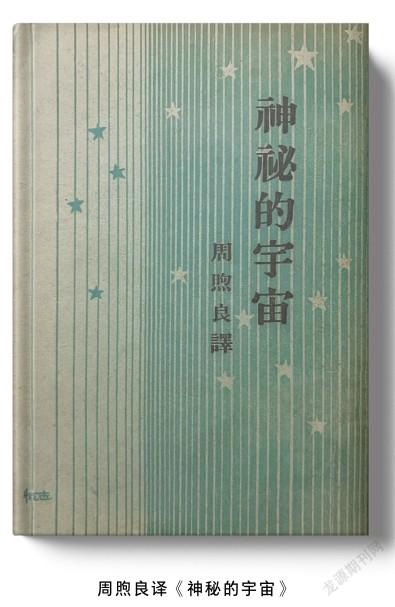
1931年,“The Stars”由英國剑桥出版社首次出版。张贻惠在拿到该书后便决定优先译出。其译本《宇宙及其进化》在1932年9月即告面世,可谓相当高效。不过可惜的是这个译本并没有流传开。出版该书的北平震亚书局销售渠道很窄,只有北平师范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武昌职业学校几处。书局在1933年后就销声匿迹,停止了出版活动。书上出版广告中提到的7本“不日出版”的图书最终都没有问世。
1935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清华学生侯硕之的新译本,名为《宇宙之大》。侯硕之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胞弟,1914年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1930年考入天津著名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读高中。由于成绩优异,学校以英文原版图书作为奖励。其中一本便是金斯的“The Stars”。侯硕之非常喜欢这本书,利用业余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又在侯仁之的导师顾颉刚的介绍下,由开明书店出版。由于侯硕之的英文成绩十分突出(他国文以外所有科目均以英文作答),新学书院的英国校长愿意保送他到英国深造。然而侯硕之一心想改善国人的生活,希望投身中国的水电建设。于是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理工科,虽然入学考试中数学交了白卷(补考也只得了2分),仍以加修数学一年的条件被清华大学电机系录取。
崭露头角的新诗诗人金克木(1912—2001)那时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他当时恰好也对天文很感兴趣。他仔细阅读了《宇宙之大》,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写信向译者指出。侯硕之非常感激,经朋友介绍约金克木在清华见面。两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一见如故,观星长谈直至深夜。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侯硕之随清华大学辗转南迁至昆明。由于时局纷乱,修筑水电站的抱负无从谈起。1942年,侯硕之来到临时迁至陕西宝鸡市蔡家坡镇的扶轮中学担任高中理化课教师[3]。那年冬季,他徒步前往凤翔县为侯仁之考察唐朝古迹。在投宿凤翔师范学校的夜间遇害,年仅28岁[4]。
其实,金克木在读到侯硕之的译作时,自己也在翻译这本書。同周煦良翻译的《神秘的宇宙》一样,这也是金克木翻译的第一本书。虽然他很早就完成了译稿,但因为不够自信,迟迟没有联系出版社,只是托人审读。后来,书稿被中华书局买下,他也因此得到了不少稿费(虽然这本书直到1941年才付梓面世)。由此,金克木产生了译书为生的念头,于是他辞掉北大图书馆的工作,翻译了第二本书——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 Newcolnb)的《通俗天文学》(Astronomy for Everybody),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就在他的科普翻译事业刚看到希望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金克木的人生走向也从此改变。他翻译的第三本天文书《时空旅行》交稿后未及问世便在战乱中遗失。为了谋生,他告别了天文,转而研习梵文、佛学。在1997年的回顾文章中,85岁高龄的金克木先生这样感慨:“从1937年起,做不成译匠,望不见星空,算来已有整整60年了。”[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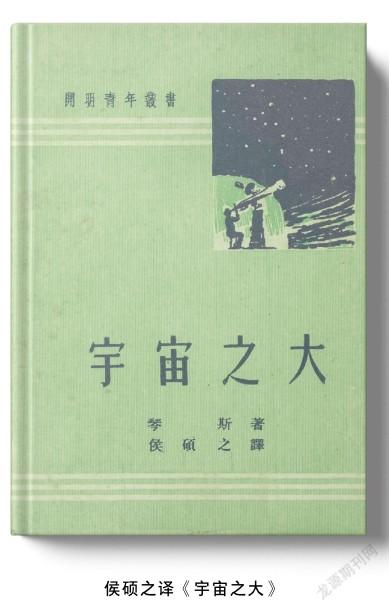
193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李光荫的译本《闲话星空》,作为自然科学小丛书中的一册。李光荫( 1903—1978)生于河北省怀安县。1925年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矿科,岂料才上了两年学,矿科就因缺乏经费停办,于是他只能转学至厦门大学数学系,遇到了刚从美国回到厦大任教的天文学家余青松。后来余青松出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李光荫便追随他来到南京从事天文研究[6]。李光荫在译序中提到,翻译金斯这本书是为了给中学提供天文学科的补充读物。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天文研究所内迁,李光荫前往北平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进修统计学,从此离开了天文界。不过,天文观测数据的处理经验让他认识到统计方法的重要性。李光荫在新中国成立后转而从事卫生统计的教育和研究,成为我国卫生统计学的奠基人。
于是,自“The Stars”一书1931年问世以来,国内一共出现了4个译本。分别是张贻惠译的《宇宙及其进化》(1932)、侯硕之译的《宇宙之大》(1935)、李光荫译的《闲话星空》(1936),以及金克木译的《流转的星辰》(1941)。在这4名译者中,张贻惠年龄最长,是晚清秀才,后来留学日本;李光荫其次,金克木和侯硕之年纪相仿,都是弱冠之年。几位译者的教育背景和语言功底本身就有很大差别,因此译文的风格也迥乎不同。
先说书名“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直译过来是“群星——在它们的道路上”。course一词语义双关,不仅指群星在空间中的轨迹,也包含了它们在时间上的演化历程。张贻惠的书名《宇宙及其进化》用“宇宙”代表群星组成的空间,用“进化”表示它们在时间中的演变,把握了整体的含义,但译名显得过于专业,无法令人联想到书中描绘日月星辰的具体章节。又因北平震亚书局影响有限,译作销量不佳,相关读者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个译本[7]。侯硕之觉得金斯这本书内容广博,便以“大”字概括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尺度,暗合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名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李光荫或许是考虑到原作语言浅易,仿佛作者对读者叙说一般,所以选了《闲话星空》这个非常符合畅销书模式的书名。但这种译法丢失了半个题目,从翻译的角度看来不够忠实。相比之下,金克木的《流转的星辰》堪称信达雅的典范。“星辰”二字对应单词stars,泛指宇宙中的各类天体,比笼统的“宇宙”更加写实;“流转”二字不仅刻画了众天体在天穹上转动的景象,也可以形容星体的演化历史,甚至还能品味出“逝者如斯夫”的感慨。这个书名完美传达了英文的意蕴,同时又富有中文的美感,充分体现出诗人金克木对语言文字的驾驭力和创造力。
在正文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几位译者的风格差异。例如,在解释地球自转引起星辰东升西落时,金斯用简单的语言形象而贴切地勾勒出地球自转的生动画面。原文是这样的:
“The motion of the stars over our heads is as much an illusion as that of the cows, trees and churches that flash past the windows of our train…We are like children on a ‘merry-go-round’ in a village fair. The whole fair seems to be going round them, but actually it is they who are going round inside the fair.”
“在我们上面星体的运动,不过像从火车里面,看见外面的田地树木,向我们后面运动的幻想一样。……我们好像小孩,骑在乡村游戏场里的,旋转木马上面一样,整个游戏场, 好像在绕小孩旋转, 但实在是小孩, 在游戏场内环绕游行。” (张贻惠译)
“我们头上的众星的运行实在是我们的错觉,如同我们在火车内所得车窗外飞逝过去的牛、树、教堂的错觉一样。……我们就像村市中玩旋转平台把戏(merry-goround)的小儿一样。由他们看,整个市集都在绕它们转动,实则是它们自己在市集中转动哩。” (侯硕之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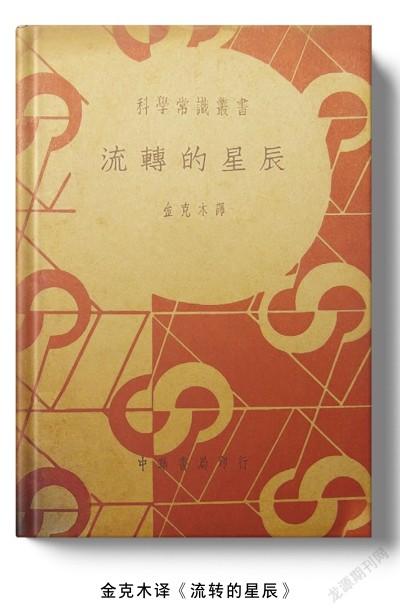
“天体之运动恰如吾人由火车窗口所见地上之牛,树,建筑物等似运动同。……吾人正如田庄中大转盘上之一伙儿童。儿童打转盘时所在田庄中物无一不围绕伊等转动。实乃伊等自身在田庄中转动也。”( 李光荫译)
“我们头顶上的星辰的运行跟火车窗外的牛群、树林、教堂的飞驰而过同样是一种错觉。……我们都好像小孩们在市集中的‘旋转玩具’上面,看起来全市集都绕着他们转,其实是他们自己在市集中间转罢了。”(金克木译)
可以看到,除李光荫是用通俗文言之外,其余3位译者都采用白话文。张贻惠译文的语句简短,大意把握准确,只是标点不太自然,仿佛句读。这可能和他所受的传统国文训练有关,毕竟他在翻译这本书时已经45岁了。李光荫虽然年纪稍轻,译文风格反倒更加古旧,没有顺应五四后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潮流。侯硕之和金克木的行文措辞已经很接近现代汉语的习惯。只不过侯硕之所用句式较为简短,偏向口语化,金克木的译文更加凝练优美。
金斯作品中也有许多富有哲学意味的隽永警句。这些相对抽象的表述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例如,他在本书的最后这样总结道:“In some way the material universe appears to be passing away like a tale that is told, dissolving into nothingness like a vision. The human race, whose intelligence dates back only a single tick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could hardly hope to understand so soon what it all means. Some day perhaps we shall know: at present we can only wonder.”
“物质宇宙可以说有些像讲说故事,过耳即逝,梦中幻象,转眼即空。人类文化的开始,只有天文学钟摆,一摆动之久,当然不能希冀,立刻了解这些事实的真意,将来有时我们或许能了解,现在却只能在观叹。”(张贻惠译)
“在某种意味上,物质宇宙的消逝就像一个故事,终要化为乌有如一场大梦。人类灵性的起源在天文学的时计上才只是一声滴答以前的事,人类怎能希望很快地就可理解了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呢?最后或者终有一天我们能够晓得的,然而现在我们只能惊奇而已。”(侯硕之译)
“物质之宇宙似说故事一般底逝去矣,一如看风景一般底化为无有矣。人类之智慧之由来仅天文钟一的答声间之久,实难了解其中之一切意义。将来或有以知之,惟目前吾人只有纳闷而已。”(李光荫译)
“不论怎么样,物质的宇宙看来总要飘逝过去像一个曾经传说的古老的故事,而且要化入乌有像一个幻象的。人类的智慧在过去所占的时间仅仅是天文学上时钟的一声滴搭,更难希望能这样快的了解所有其中的意义了,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明白的:现在我们却只能惊诧而已。”(金克木译)
客观地说,这段文字需要一定的人生阅历来共鸣。年长的张贻惠将wonder一词译为“观叹”,刻画出人们在看到宇宙奇观之后感慨赞叹的情态,比其他译者更准确地把握了金斯的想法。不过其他年轻的译者们无疑也在翻译的过程中得到了成长和锻炼。
这些不同的译本,既让我们看到金斯的科普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广泛影响,也让我们看到国人为了解世界和追求新知所作出的努力。在那个局势动荡、山河破碎的年代,我国译者学人出于各种因缘际会,将最新最好的科普作品译成中文,为国人同胞带来新鲜知识,给养心灵,激发热情。虽然他们自己由于各种原因没能继续仰望星空,不过薪尽火传,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1935年的北平崇德学堂里,一名中学生在图书馆拿起了一本《神秘的宇宙》。他被书中奇妙的宇宙和新奇的发现深深吸引,回家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拿诺贝尔奖!”。22年后,他如愿以偿。这位学生名叫杨振宁。那一年,他12岁。
[致谢:感谢北京天文馆王燕平、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晗对本文的修改和建议。]
[1]Smith R W. Sir James Hopwood Jeans, 1877-1946.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stronomical Association, 1977, 88(7-0297): 8-17.
[2]D Helsing. James Jeans and the mysterious universe. Physics Today, 2020, 73(11): 36-42.
[3]宋立志. 名校精英: 北京师范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远方出版社, 2005: 82-85.
[4]侯馥兴. 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 中华读书报, 2015-12-02[2021-10-39]. 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15-12/02/ nw.D110000zhdsb_20151202_1-18.htm?div=-1.
[5]金克木. 金克木散文: 人苦不自知.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162-166.
[6]陈展云. 中国近代天文事迹. 云南: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臺, 1985: 64.
[7]金涛. 林下书香:金涛书话.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3: 210-212.
关键词:天文学 科普图书 民国 译本比较 科技翻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