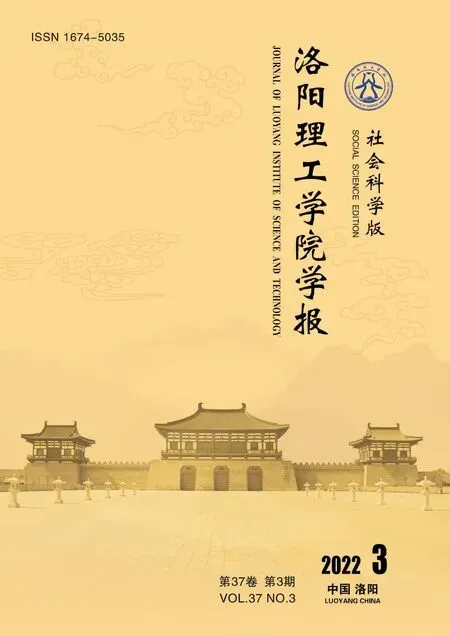杂史类考辨
——兼论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2022-06-14骆妍
骆 妍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6032)
“杂史”,今人对其的析解存在许多歧异。1981年版《辞海》将“杂史”归入《体裁》篇中,将其视作史学体裁之一[1]390。1979年版《辞源》“杂史”条则用广义的概念,将“杂史”作为“非正统史家所著”类典籍的统称[2]3313。然而,对“杂史”进行溯源,可知其最早是作为史部二级类目之名,出现在唐代官修史志目录《隋书·经籍志》(下文简称《隋志》)中,这应当是“杂史”的本义。作为被历代修史者常设的史部二级类目,杂史类在传统古籍四部分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著录的典籍有着极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20世纪末,李更旺的《古代杂史诸体概述——古文献学札记之一》[3]与彭久松的《简论别史、杂史》[4]开“杂史”专题研究的先例。到21世纪初,景新强以上述二文为参考,对杂史类的分类标准做了进一步的阐发[5]。笔者认为,“杂史”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指史部二级类目中的杂史类,广义泛指有别于正统史书的杂史文类。目前,学界以目录分类学为切入点的杂史类专题研究成果有限,对杂史类自肇始以来的历代演进历程与义界调整缺乏详备的梳理,需要更深入的考察。
一、《隋书·经籍志》杂史文类观的形成与拓展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6]460。《隋志》史部杂史类序文载:
自秦拨去古文,篇籍遗散。汉初,得《战国策》,盖战国游士记其策谋。其后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又有《越绝》,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谓之杂史。[7]962
这段序文没有对杂史类定出严格意义上的著录标准,却阐明了杂史类典籍的五个基本来源,与其著录的“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7]962先后顺序大致相应:一是“篇籍遗散”之后失而复得的先秦遗书;二是撰成于汉代的、“属辞比事”又明显不同于《史记》《汉书》等正史的史书;三是汉末乱世“博达之士”记载的时下“闻见”;四是后汉以来学者“钞撮旧史”改编而成的“体制不经”的书;五是其他关于帝王之事而内容“真虚莫测”的书。由此可知,《隋志》创设的杂史类兼包众体,不同于传统目录学按体裁立类的标准。相应地,“杂史”也就不能像“编年”“纪传”被视为史书体裁。
综观《隋志》杂史类典籍,随意性是其共有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著述者为非正统史官、编撰思想上“率尔而作”、体裁上“体制不经”、内容上“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等。司马朝军认为,图书类目包括辨义类目与辨体类目,即按照图书内容或体裁立类[8]166。杂史类自创设以来便属于前者。作为以义辨体的类目,杂史类有义界模糊的弊端。在《隋志》序文中,修史者没有设立较为明确的界限,这使修史者在典籍分类上有了主观裁决的机会,给历代书目留下许多可议之处。姚名达认为《隋志》分类不合理,“《隋志》之小类,则诚莫明其妙也”[9]77,“执一则不通,兼两则自紊其例”[9]78。《隋志》开创的这种以义立类的模棱两可的分类方法,致使后世典籍在类属上流变交错。
尽管拥有许多弊端,但《隋志》对杂史类有首创之功,为后世修史者提供了分类依据。首先,唐代史官创设杂史类是受制于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因此“非史策之正”也就成为辨识或指称杂史类典籍的首要标尺。具体表现为:典籍内容关系帝王之事,但由于著者与著体不是官方正统,真实性与权威性不及正史类典籍,而在史学地位上依附于正史类。其次,杂史类典籍之所以被史官“备而存之”而留存于世,是因为具有“资史”的功用,“通人君子”可以“博采广览,以酌其要”。
在《隋志》创设杂史类之后,“杂史”逐渐被史家征用。综观历代“杂史”的相关论述,学者对“杂史”的理解没有局限在《隋志》“史部二级类目名目”的狭义范畴之内,反而将“杂史”泛化为广义上的杂史文类。《隋志》所奠定的“非史策之正”和“资史”两种基调成为历代学者遵循的杂史文类观,影响他们对“杂史”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隋志》的编者之一李延寿,在修撰《南史》《北史》时除参考“八代正史”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10]3344。据胡宝国考证,李延寿所勘的“杂史”不仅有《隋志》杂史类典籍,还有杂传类的相关史料,李延寿所勘“杂史”的范围要宽于《隋志》[11]204。在《北史》自传中,李延寿指出其撰史宗旨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10]3345,可见其“杂史”的指称范围是正史的“遗逸”,具有“广异闻”的功用。李延寿遵循《隋志》“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文类观。
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也继承了杂史文类观。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下文简称《经籍考》)史部设置了正史、杂史、故事三大门类,其中杂史门类又细分杂史、杂传、伪史霸史、史评史钞等四类。两处“杂史”分别指代广义的文类和狭义的史部类目。关于狭义“杂史”,马端临认为:
杂史、杂传,皆野史之流,出于正史之外者。盖杂史,纪、志、编年之属也,所纪者一代或一时之事;杂传者,列传之属也,所纪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为一人之事,而实关系一代一时之事者,又有参错互见者。[12]5649
一方面,马端临认为杂史类与杂传类在记载主体上的不同,分别以时间范畴、人物范畴作为类属根据,不同于《隋志》将是否关系帝王之事作为两类的区分标准。另一方面,马端临认为杂史类与杂传类典籍“皆野史之流”,从内容的随意性和非正统性指出它们的相同之处,继承和拓展了杂史“非正史之策”的文类特点。这种观点被后人沿用,如明代学者焦竑就称“杂史、传记,皆野史之流”[13]309。也有学者强调杂史文类的“资史”功用,如明人钱棻的《萧林藏书记》载:“汲冢诸书,杂而伪者也;穆满诸传,杂而荒者也;西京诸纪,杂而碎者也;吴越、十六国诸春秋,杂而芜者也。然杂史之繁,亦正史之助。”[14]卷七16又如近代学者李更旺从文献价值出发,拓展了杂史文类的范围,其认为“从隋至清,……凡是正史、别史以外的史书,均可看作是杂史”[3]56。
综上,《隋志》没有对杂史类定出严格的著录标准,但奠定了“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不仅为修史者提供了杂史类的分类依据,而且影响了历代学者对杂史文类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凭借《隋志》指出的“资史”功用,杂史类典籍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二、杂史类历代著录范围的调整
自《隋志》设立杂史类以来,后世修史者皆有沿袭与模仿。然而,历代官私目录杂史类著录的典籍不尽相同,杂史类的著录范围多有变化与调整。
继《隋志》之后,唐代的目录以《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为代表。其中,《群书四部录》杂史类典籍“纪异体杂纪”[15]1963,符合《隋志》“体制不经”“非史策之正”的特点;《古今书录》杂史类的著录情况与《隋志》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唐代官修目录对《隋志》的沿袭。
宋代史官修撰本朝史时,相应撰有国史艺文志,其中《三朝国史艺文志》称杂史类典籍“体制不纯,事多异闻,言或过实。然籍以质正疑谬,补缉阙遗,后之为史者,有以取资”[12]5647,基本承袭《隋志》的杂史文类观。庆历元年(1041),史官在《三朝国史艺文志》的基础上撰成《崇文总目》,书中没有写明杂史类的著录标准,仅介绍了杂史类典籍的来源和功用[16]1886。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私修目录,有《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玉海·艺文》等,皆设有杂史类。据景新强考证,这些私修目录的杂史类著录情况出入较大,杂史类与其他类目存在纠葛[5]。可见,到了南宋时期,杂史类的界限仍然没有明晰。
尽管如此,宋代杂史类发展还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郡斋读书志》的撰者晁公武对杂史类典籍的评述。晁公武虽然认可了杂史类典籍“证史官之失”[12]5652的史料价值,但指出其中“亦有闻见单浅、记录失实、胸臆偏私、褒贬弗公以误后世者,在观者慎择之而已矣”[12]5652。晁公武是首位提倡对杂史类典籍“慎择”的学者,可见其不仅重视对典籍价值的“辨”,还强调对典籍内容的“用”。晁公武的观点被明代学者焦竑继承。焦竑在《国史经籍志》中同样强调了对杂史类典籍要“善择”。二是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下文简称《解题》)首次创立别史类。此后响应《解题》设置别史类的代表性目录有《宋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简称《总目》),但只有《总目》遵循了《解题》的分类格局。《宋史·艺文志》与《千顷堂书目》有别史类而无杂史类,其别史类的著录大多是原先类属杂史类的典籍,“就立类标准看,正是杂史之别称”[4]64。

清初官修目录《明史·艺文志》(下文简称《明志》)改变了传统目录通录古今书的做法,“去前代之陈编,纪一朝之著述”[20]7,相应地,《明志》杂史类只著录明一代的典籍。在此基础上,《明志》杂史类开创了著录官修典籍的先例,收录了嘉靖年间所撰的《大礼集议》《纂要》《明伦大典》《大狩龙飞录》等、天启年间所撰的《三朝要典》以及洪武年间所撰的《汉唐秘史》[21]2384-2387。其中,《大狩龙飞录》是“明世宗肃皇帝御撰”[6]474,记载明世宗南巡承天府的相关事迹,“资史”功用较为欠缺。《汉唐秘史》有许多“御撰”和“奉敕载入”的地方,但“择焉弗精,多取委巷之谈”[6]475,内容上较为随意。《大狩龙飞录》与《汉唐秘史》虽是官修性质,但都因为具有杂史文类的特点而被史官归入杂史类,体现了清代分类理念的进步。此外,《总目》将《大狩龙飞录》《汉唐秘史》归入杂史类存目,是对《明志》开创的“官修杂史”文类的沿袭。
综合以上考察,可见杂史类历代的著录范围呈扩大趋势,整体遵循《隋志》所奠定的“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但除《经籍考》和《国史经籍志》对杂史类有“纪一代或一时之事”的具体限定外,几乎没有修史者对杂史类的义界与著录标准进行明晰的规定。到清代修《总目》时,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三、《四库全书总目》杂史类著录特点
《总目》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总结性著作,实现了对四部分类法的合理化和完善化。《总目》杂史类序文载:
杂史之目,肇于《隋书》。盖载籍既繁,难于条析。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然既系史名,事殊小说,著书有体,焉可无分。今仍用旧文,立此一类。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6]460
由序文可知,“杂史”的“杂”,义为“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杂史”的立类目的是统摄“难以条析”的典籍。在归类原则上,《总目》强调了杂史类典籍的史书体例,认为“既系史名,事殊小说”,“凡所著录,则务示别裁”。在此基础上,《总目》制定了杂史类的著录标准:首先,典籍内容“事系庙堂,语关军国”,与《隋志》“大抵皆帝王之事”的标准一致;其次,内容形式“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不仅点明了杂史类体例的松散与记载的随意,更为杂史类拟出了较为科学明晰的著录标准。这也是为何《辞海》《辞源》等权威性辞书中的“杂史”条都参考《总目》的原因。此外,《总目》不仅规定了此类典籍须具有“存掌故,资考证”的“资史”功能,还指出“若夫语神怪,供诙啁,里巷琐言,稗官所述,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对典籍内容的真实性与史料来源的可靠性提出了比《隋志》更高的要求,相较于晁公武、焦竑对杂史类“慎择”“善择”的观点也更为严格。
对典籍史书体例与史料来源的高要求,是《总目》杂史类的突出变化与特点,这导致《总目》在分类上呈现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整,许多原先类属杂史类的典籍在《总目》中被分入小说家类、杂家类。这种变化体现了《总目》分类思想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发展。就学术层面而言,《总目》的贡献之一是“从前人收书范围相当驳杂的类目中,别出不该录入本类的书籍,使类目的内容更加趋于单纯、谨严而名符其实”[22]。在杂史类序文中,《总目》特别提及“杂家”与“小说家”,实际上暗示了分类工作中这两类典籍与杂史类相互混淆的普遍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总目》对杂史类的界限加以强化,凡是史书体例或史料来源不符合要求的典籍,都归入子部杂家类或小说家类。如杂家类《曲消旧闻》提要载:“其中间及诗话、文评及诸考证,不名一格,不可目以杂史。”[6]1039又如小说家类《大唐新语》提要载:“《唐志》列之杂史类中。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6]1183《总目》的归类调整,导致一些史料价值较高的典籍屈居子部。如长期被归入史部的《西京杂记》,《总目》称其“摭采繁富,取材不竭”[6]1182,却因内容“多为小说家言”[6]1182而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可见,《总目》杂史类对史书体例和史料来源的要求优先于“资史”的功用。
就政治层面而言,《总目》的分类特点体现了封建正统观在学术领域的强化。唐代《隋志》创设杂史类,是统治者对史学“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23]的正统观的要求;清代《总目》确立“正史体尊”[6]397,则是修史者对史学正统观的继承与强化。高路明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既然是集中国封建社会目录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其学术观点就必须以封建的正统观念为宗旨。”[24]218“与封建正统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封建的等级观念,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是把典籍划分为不同的等次”[24]221。可见,《总目》对“正史”与“杂史”乃至“史部”与“子部”的划分,是源于封建正统观的影响。此外,《总目》解释了强调史书体例的缘由:“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6]769既然《总目》将“史”的地位提高,修史者也就相应地对史书的体例和取材提出了可承其位的更高要求。
四、典籍类属变易的影响因素
综观历代曾被归入杂史类的典籍,“往往类属变易频仍”[4]65。典籍类属的出入,体现的不仅是杂史类著录范围的调整,还有背后的主客观因素。归纳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杂史类以义立类的局限性。杂史类以典籍内容特点作为依据的分类方法,使得修史者长期忽视对杂史类义界的规定,这是造成典籍类属变易的首要因素。事实上,类目义界的模糊是传统四部分类法的通弊,学者对此多有论述。最早有郑樵提出“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25]1816,后张之洞认为“别史、杂史,颇难分析”[26]334,甚至连《总目》的修撰者也称“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6]1204。可见,传统分类法即便发展到《总目》的成熟阶段,也依然存在义界不明的弊端。其原因是,《总目》的标准只解决了“史”的问题,却没对“杂”给出明确的指称与限定,序文中“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括殊名”泛化了杂史类的著录范围,使得杂史类成为容纳所有“难于条析”之典籍的渊薮。除了杂史类,《总目》中还设有许多带“杂”字的类目,它们的义界都不明晰[8]170。
第二,典籍内容的复杂性。“难于条析”是杂史类所收典籍的共同特点,这也是造成典籍类属变易的第二大因素。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南史》《北史》的修撰特点是“删烦补阙”[12]5582、掺杂许多“琐言碎事”[27]214,按照《隋志》的标准,应当被归入杂史类。但《南史》《北史》实际的归类情况是:在宋代目录中,它们出入于正史、别史、杂史类之间;明代以后的目录都将它们归入正史类。考察《南史》《北史》的相关述评,可见其“删烦补阙”的特点是史家的共识,也是修史者分类的重要依据。修史者对“删烦补阙”的重要性的不同判断,是造成《南史》《北史》类属变易的原因。如修史者认为“删烦补阙”是《南史》《北史》的优点,“过本史远甚”[12]5582。但《郡斋读书志》将《南史》《北史》归入杂史类,《直斋书录解题》将《南史》《北史》归入别史类,《玉海》将《南史》《北史》归入正史类。《总目》将掺杂“琐言碎事”的《南史》《北史》归入正史类,与其严辨史书体例的著录思想相悖,是《总目》自乱其例的体现。
第三,修史者的主观裁决与权宜心态。前文所述的两个因素,只有通过修史者的主观裁决,才能对典籍分类造成影响。因此,造成典籍的类属变易的根本因素,是修史者对杂史类义界的主观理解,以及对典籍内容的主观辨析。一方面,由于缺乏客观标准,修史者在分类时,容易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修史者自身的知识储备、社会的实际需要、统治者的政治要求等,这就导致典籍类属的流变交错。如《建康实录》曾被不同的修史者归入杂史类、实录类、起居注类、编年类等,而《总目》撰者仅据“所载惟吴为僭国”[6]447就将《建康实录》归入别史类。另一方面,主观裁决容易造成分类失当的情况。郑樵认为:“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25]1809马端临认为郑樵的观点“尤足以究其所失之源”,并指出考订分类工作的困难:“盖有前史仅存其名,晚学实未尝见其书者,则亦无由知其编类之得失。”[12]5651或是出于典籍散佚的客观局限,或是出于主观认知的不足,修史者在典籍分类时常有“姑仍其旧”[12]5651的做法,这便是修史者面对分类困境的权宜心态。如《总目》杂史类存目《马端肃三记》提要载:“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6]477面对典籍内容与体例之间存在的矛盾,修史者选择因袭旧例、权宜处置。但《马端肃三记》在明代《续文献通考》中被归入传记类[28]卷一七七7,《总目》因循的应是清修《续通志》[29]卷一五八10。由此可见,权益心态虽然不能直接造成典籍类属的变易,但在与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对典籍的分类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结 语
《隋志》首创杂史类,并奠定了“非史策之正”与“资史”的杂史文类观,不仅为后世修史者提供了杂史类的分类依据,而且影响了历代学者对杂史文类的指称范围和价值判断。由于修史者长期忽视对杂史类义界的规定,仅遵循《隋志》的杂史文类观来分类,导致杂史类的著录范围历代不断调整,整体有泛化为杂史文类的趋势。清修《总目》对杂史类拟出较为科学的著录标准,不仅明晰了杂史类的义界,对杂史类典籍的史书体例和史料来源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总目》在典籍归类上呈现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整。尽管修史者对杂史类的分类实践存在许多局限,但杂史类的概念与义界经过历代的发展逐渐走向规范化,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传统目录学乃至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