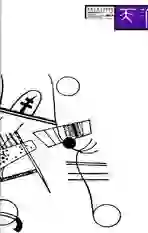看俑记
2022-06-09燕燕燕
在人间时,俑只是陶土或其他材质制成的小型人像,一入冥界,便会复活如人,供墓主人驱使。忠实的奴仆俑侍奉主人饮食起居,灵动的乐舞俑为宴饮助兴,兵俑和仪仗俑齐整威严,护卫安全。为了令主人黄泉下的生活与红尘中毫无二致,俑在具体而微的墓室里忙忙碌碌,各司其职。直至某天,头顶的地面忽然松动,俑被出土,又重新定格为小型人像。
作为陪葬物中一个重要的品类,几乎每座博物馆都存着数量极多的俑,然而千俑千面,鲜有重复,每个俑的样貌和姿态也都在显现着各不相同的内心世界。这是因为,俑虽是泥塑木雕,却并非全部凭空捏造,他们也有来处,也有前身。
我所在的博物馆里有一座复原的古墓,墓里陪葬六个陶俑。其中一个女仆俑,长着阔大的扁脸,两只眼睛距离很近,眼梢向上高高挑着,鼻子上不太能看出鼻梁,嘴巴小又歪。她头梳圆髻,双手环在胸前,上身穿窄袖右衽短衣,下身是上紧下宽的长裙,裙边装饰一圈波浪形纹样。在裙面上则有更令人意外的装饰:正面中间竖刻着一行字“女子姓季字阿多”,侧面刻的是“下邳任令明所作”,背面刻“元康九年所作有三日”。
大多数俑都是没名没姓的,她身上却携带着如此宝贵的信息。西晋元康九年,即公元299年,一个叫任令明的下邳陶工制造了她,可能对这件作品较为得意,他落了款识。至于季阿多这个名字,我不认为是他为方便墓主人使唤随意所取,而是墓主人家里确有一个叫季阿多的女仆。也许陶工先到府上走了一趟,记住了仆人们的长相,也许是听了订货者的描述,总之是依她的样子做的。季阿多如今被摆放在展柜里,我有时去看她,她不美,但不美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一个西晋年间当地小贵族家里的女仆,应当是这个模样。
古代权贵者在营造死后居所时,想把拥有的物品、妻妾、奴隸都带走,在另一世界继续享用。假如时间再往前移一两千年,主人去世,季阿多恐怕就要亲自陪葬了,她很幸运生得晚了些,只需造一个与她模样相仿的俑便保住了性命。活人殉葬制度盛行在殷周时期,我看过殉人墓的发掘现场,那是一处大型的东周贵族墓群,每个墓中至少有两个殉人,多则六七个,均是双手被绑,面目狰狞。从牙齿和骨骼看,他们都很年轻,有的是未成年人,并排躺在墓主人旁边。我蹲在墓沿上呆呆看着,想象他们死前的恐惧与愤怒。这类墓中通常还会放一只脖子上系着铜铃的殉狗,小狗的样子很安详。我还看过商代的车马坑,与后世车马坑不同的是,里面除了有杀死后放入的马,大部分还会有个殉人,俯着身子,被压在车厢下面或后面,像一个车祸现场。他们生前应是车上的驭手。
这种野蛮的葬制在春秋后期逐渐衰微,俑开始取代活人殉葬,除了人俑还有各类动物俑,也取代了活的动物。看上去,好像是人性很大的进化,但孔子犀利地指出“为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又说“始作俑者,岂无后乎”。刍灵是用茅草扎成的人,他认为以刍灵为陪葬品的人是善的,以俑为陪葬品的则不仁,因为俑是人形,用人俑陪葬,仍是变相的活人殉葬,两者在意识里没有区别,反倒又暴露出人的虚伪。孔子对事物总有超常的洞见,只不过无人理会他,俑之后被大规模使用,一直延续至清朝。
秦陵兵马俑便是以俑代人的有力实证,兵马俑也正是依照现实中将士的形象塑造的。秦始皇十三岁即位,不久开始建造陵墓。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在那座历时三十余年修成的大墓里,藏着众多奇器珍宝,墓顶有日月星辰,墓底有三山五岳,水银浇灌了百川江河大海,用人鱼膏做的蜡烛永久都不熄灭,照得整个地宫亮如白昼。这样一个神秘奇幻的所在,不知多少人渴望亲眼见到内中真景,比如研究者,比如盗墓者,这两类人都是墓的敌人。更何况,幽冥之界,充斥着各路妖魔鬼怪,要抵御它们的侵扰,还要防备死去的仇人们,他们或许正在下面等待复仇。为此,秦始皇太需要集结一支强悍的军队来守卫陵墓安全,他以横扫六合的精兵强士为蓝本,以在炉火中淬炼的陶土当血肉,铸就了几千个骁勇的阴兵。原以为,骊山脚下,渭水之滨,人马欢腾,封冢永固;谁料,两千多年后,地宫依旧安然,兵马俑却赫然面世。
想来略有遗憾,我游览过众多博物馆,也算阅俑无数,可一直没有机缘去看看秦王庞大的地下军团。只有一次,在山东省博物馆,遇上他们与秦陵博物院合办秦文化大展,才得以与几尊兵马俑照面。有一尊跪射俑,样子着实英武,引得我围着他看了好几圈。他国字脸,泥丸般的眼珠,丰厚的嘴唇,两撇柳叶状八字胡,典型的秦人相貌;左腿蹲曲,右膝跪地,上身笔直地挺着,双目凝视前方,两手放在右侧腰间,摆了一个紧握弓弩的姿势,工匠将他手心的掌纹也处理得清晰严谨;头顶挽一个发髻,后脑勺上又编了几股小辫子,头发丝皆是根根分明;脚穿方口齐头翘尖的鞋子,右脚直立起,露出鞋底密密的针线,亦是纤毫毕现。他虽已出土很久,战袍外的铠甲上还残留着点点红色颜料。那红色忽令我莫名感动和哀伤,这是一个人啊,那时,真的是有一个这模样的人啊,我这样想着,突然很想对他恸哭一场,而在他冷静如铁的脸上,似乎也隐藏着巨大的悲怆。所以尽管展厅墙上写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诗句,试图引导观者遥想秦军奋勇杀敌的场景,我想到的却是“行道迟迟,载饥载渴。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中踽踽独行的士兵。
秦俑是对秦国战士几近完美的复刻,但我后来在图录上再看他们的照片时,心境又有了不同。不由又想,虽然真的曾有过那样一个人,可是俑,你毕竟只是个俑啊,高度真实了,仿佛显得不可爱。自己想完也笑,人家的使命原本不是为了可爱,是为了威慑。不过,徐州狮子山出土的西汉微缩版兵马俑,那一个个的小兵人,身高只有三四十厘米,还要扮演很勇猛的角色,我乍看时真觉得非常可爱。尤其是弓弩俑,矮矮的个子,身后背着小小的箭匣,恰似背双肩包上学的幼童。待到再放眼细观时,这种感觉消失了,只见一条俑坑里密集地聚着上千个俑,摩肩接踵,挨挨挤挤,有的俑断了胳膊,有的俑发髻缺了一截,很多俑没有头,露着空空的腔子,有的俑头还在,可是从脖子处断开了,无力地抵在前面的俑的肩膀上,有的俑好像在哭泣,旁边同伴扭头愣愣地看着他。还有一个跽坐甲胄俑,摊开的双手在我看来正是在表达他的无奈——他的肚子破了个洞。
如果将俑视作真人,那么眼前的所见,非但与可爱无关,甚至称得上惊悚。俑坑旁另有一个奇怪的马坑,里面没有马,只分布着马的各个部位,一堆马身、一堆马头、一堆马腿、一堆马耳。狮子山出土的这些兵马俑,不合规制,疑云重重,曾令考古人员十分费解。后考证,俑的主人可能是西汉第三代楚王刘戊。刘戊因参与“七国之乱”,兵败后死去,叛臣没有资格以兵马俑陪葬,但之前已经预备了,不如大着胆子一埋了之。假若真相果然如此,便可以解释为何马俑没有组装,为何兵俑的阵形凌乱,为何发辫俑里混着发髻俑,发髻俑里混着头盔俑,跪坐式车兵俑中突兀地站了一个孤独的步兵俑。一切缘于当时形势紧迫,来不及整饬便匆匆下了葬。这位三十岁左右畏罪自杀的楚王,连死都是这般的仓促和漏洞百出。
刘戊自杀十三年后,他的堂兄汉景帝驾崩,葬于阳陵。景帝一生崇尚节俭,陪葬却并不节俭,阳陵里出土了十万余件文物,包括各式的陶俑。其中一种是着衣式,身上原先穿着丝麻衣物,肩上装的是可以转动的木头胳膊,出土时衣物和胳膊已腐朽,只剩下无臂的裸露陶躯。我在图录上看到有一个高颧骨武士,皮肤橙红色,形体逼真,凸起的胸肌和隐秘的性器官都塑造清晰。他大概也为自己裸体示人感到不好意思,微微垂着眼睛,脸上露出羞惭的笑。着衣裸身木俑源自楚地的习俗,制作的确奇巧,只是工匠们没有预想到他们日后的情形。
另一种塑衣式则不会有类似的尴尬,衣服直接泥塑在身上,再施以浓艳的彩绘,安全又美丽。姗姗是塑衣式陶俑里的一个女俑,名字是阳陵的工作人员为她取的,我很喜欢她,一度用其照片做微信头像。这位汉宫的侍女鹅蛋脸形,细眉长眼,削肩蜂腰,中分的长发拢到背部挽一个髻,发梢垂下,没有任何饰物,清丽极了。衣服是白色右衽交領曲裙深衣,领口、袖口、衣襟处都以红黄两色镶边。她席地跽坐,两手拱于宽袖中遮住一点面,模样含羞带怯,透着说不出的娴静娟秀。
姗姗名气很大,人称“汉代最美女俑”,只是没听说“汉代最丑女俑”是谁,若要评,我心里倒暗暗有个人选。曾见过徐州出土的一个汉女俑,眼睛形如蝌蚪,眉毛短粗,嘴过于小薄,脸上半部是方形,到了下面又尖起来,鼻子像一块两边斜中间高的屋脊,盖在了脸中央。偏偏她又蹙着眉,绷着脸,眼含怨愤,表情苦大仇深。不过,五官反正已是生得不妙,做什么表情也都于事无补了。
西汉的俑,我亲眼见过并深记于心的,还有两处。
一是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的彩绘木俑,出自马王堆辛追墓。这些俑以木块雕出人形和衣服轮廓,有男有女,均是通身施白粉,绘着墨色眉眼和朱红的唇。令我惊艳的是他们的着装:交领右衽曲裾长袍,色泽华丽,凡边缘处都以黑地红花镶边,白色袍面上则勾勒着黑红两色的长短云纹,流畅飘逸,密而不繁,虽是古典纹样,却勾出了强烈的现代感,看上去不像两千多年前的衣服,再加上穿着同款的细瘦木俑们排在一起,好似某个复古品牌的当季新品发布秀。看过他们,再看辛追的素纱禅衣和丝锦袍时,我也就不惊奇了,因为连她墓里等级很低的奴婢,尚且打扮得这般鲜亮高贵。
另一处是在青州市博物馆展出的香山汉墓陶俑。这些俑风格粗犷拙朴,笔法有些不周,面部描画略显轻率,有好几位都是斗鸡眼。如果是遵从了人物原型,何以这墓主专喜欢斗鸡眼的侍从呢?这批俑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丰富浓烈的色彩,陶工在他们身上分别使用了黑白色、紫褐色、粉红色、橙黄色,还尤为偏爱一种雪青色,不仅把它大量绘在男俑的衣和女俑的裙上,还绘在了动物俑上。有一匹马的身子是褐色的,配着雪青色的鞍,其他部位点染了橙色、白色,花里胡哨的,还算好看。后来可能也嫌搭配太费心思,没了耐心,于是有一只陶猪全身都被涂上了雪青色。我对西汉俑的记忆就终止在这魔幻的雪青色里。
东汉是热烈活泼的时代,东汉俑也更写实,充满生命力和烟火气。国家博物馆里有位著名的击鼓说唱俑,长了一颗圆硕的脑袋,袒胸露腹,笑口大开,眼睛眯着,眉毛扬起,额头上有几道滑稽的波浪抬头纹。正是他说到得意处的样子,左臂夹着鼓,右手举起了鼓槌,右脚板也欢乐地高高翘起。他人虽在展柜里,活灵活现的姿态,像即刻就要破柜而出。击鼓说唱俑是东汉俑的杰出代表,看了他的笑,我又注意到还有许多东汉俑也在笑。比如同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献食俑、舂杵俑、持帚箕俑和提壶俑,几位都是女子,头上一律梳三个并排高髻,中间簪一朵大花,两边簪几朵小花,眼睛、鼻子虽不太分明,唇边漾出的深深笑意却令观者悦目。尤其是献食俑,右手持杯,左手托盘,盘里摆了一圈年糕状的食物,众人里数她的发髻最齐整,簪的花最漂亮,笑容最耐看。
还有在定州市博物馆见到的东汉庖厨俑,红陶为身,外施绿釉,脸庞年轻俊秀,神态殷勤含笑,跽坐在一张砧板前,袖子高挽,左手按住一条鱼,右手拿个小板子刮鱼鳞。不久我在德州市博物馆又见到一位,长脸大耳,身上绿釉已斑驳,长得比定州的同行老相一些,同样的姿势,同样刮鱼鳞,同样含着笑。后来,我在网上看到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里也有一位,灰陶无釉,同样的姿势,相貌比不过前两位,面前的砧板比他们的要大,除了鱼,还摆着葱姜蒜等物,他的脸上也是笑的。俑从彼时来,带着彼时人的神采,由这三位快乐的厨师身上,或能一窥东汉之风貌。
汉代的陪葬俑灿若繁星,难以过多记录。往后的几个朝代里,零散记得一些俑的样子,其中也有几个在笑的。仍是在国家博物馆,有位东晋女俑,头发梳成我不懂的样式,紧凑的小眉眼,嘴角弯着,两只手拢在袖筒里,一副愉快的小模样。另有位北魏女俑,面部原先敷了白粉,现已多处脱落,露出黑底子,变成了小花脸,她也不在意,憨憨地笑着。旁边的北齐弹琵琶女俑,盘一个利落的高髻,脸上挂着艺术家端庄的微笑。
徐州市博物馆我去的次数多,最爱一个笑嘻嘻的北朝小丫头。她身材高挑,肤白唇红,凤眼高鼻,脑袋两边一边扎一个丸子髻,上穿宽松衣衫,下身是一条放在今天也非常时尚的阔腿裤。她手里拿着一枚笏板,这老气横秋的道具与她的年轻活泼太不相称,却添了几分身世的神秘感。她是谁?不得而知;但今生的身份显贵,乃国家一级文物。
南京的六朝博物馆我去过两三次,对那里的俑全无印象。同事再去时,带回一个树脂做的文创产品,原型是位东晋女俑,红上衣赭黄裙,头发乌密,容长脸形,高傲地眯着眼睛,嘴角轻笑,露出两个小涡。她被做成了U盘,使用时要从身子中间拔开,将她分为两段。对此设计我总以为有些不妥,没有用过她,摆在桌上观赏,以表尊重。
每个俑都是在考古史上有一席之地的人物,理当尊重。不止尊重美的,对丑的也应如是。有一回去固原,结识一位朋友,聊天时她提到某人,说那人“长得丑丑的”,她的当地口音说这句话时发音异常可爱。次日参观宁夏固原博物馆,看到多位北魏俑,发现他们恰巧也“长得丑丑的”。风帽俑没有脖子,头缩在肩膀上,文吏俑脸上坑洼不平,武士俑嘴唇肥厚,眼睛一大一小,还有几个只勉强有个人形罢了。我看得兴味盎然,因丑俑和丑人不同,俑的丑亲切有趣,一点也不讨厌,包括前面评选的汉代最丑女俑,我对他们都是没有丝毫恶意的。
何况到了隋唐,俑的形象愈加精妙,即使想看个丑丑的俑也难找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位唐三彩梳妆女坐俑,头顶高髻,面庞丰腴,身穿低胸褐色窄袖衫,外罩黄白绿花半臂,绿色高腰百褶裙上点缀褐色柿蒂形花朵。她左手作持镜状,右手伸出一根食指,脸上笑眯眯的,不知是要抹胭脂还是涂唇脂。她的衣服和她这个人,都同那梦一般的盛唐时代一样,俱是艳丽明快的调子。
唐朝的女俑们,纵然是侍女,也全然贵妇风度。慵懒的堕马髻,柳叶眉,樱桃口,揣着小手,腆着肚子,细长的眼睛似笑非笑,丰艳的脸蛋上,下巴已无迹可寻。她们珠圆玉润的立在那里,从容,稳定,坚信自己是美的,坚信自己全身上下无一处不对。
她们生活在社会风气自由的环境中,没有礼教束缚,可以郊游、射箭、逐猎、打球,与男子做同样的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位女射俑,梳着活泼的“丫”字形发髻,左手高举,右手在后,偏头仰脸,持弓射猎。她的姿势,像极了光阴流转的千年后,一手举手机,一手比剪刀,四十五度斜角自拍的女子。
她们常常骑马出行,有大量的骑马女俑为证。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一些彩绘女骑俑,其中一女装扮雅致,骑棕红色小马,身穿乳白与水绿相间的衣裙,头戴高顶宽边黑帽,帽檐处缀一圈网纱,遮住面部。此帽叫帷帽,武则天时期很流行。在此之前,女子出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要戴另一种名叫幂篱的连衣帽,就是在一个竹斗笠上缀一块筒状大布,由头顶倾泻下来,直至背部或脚部,只露一点面孔,穿着十分笨重,帷帽则轻便许多。这位女骑俑全身都是泥塑,帽上的面纱用的却是真正的网状纱。在当地另一座唐朝张雄夫妇墓中,出土的几个木身锦衣裙女舞俑,更是使用原材料做了全身的衣服,个个锦衣罗衫,明艳动人。最美的是一个头挽双环髻、面若粉桃花的姑娘,她额心贴花钿,颊上涂斜红,腮下画妆靥,双眉乌黑,鲜红小口,上身穿双面锦半臂衫,袖子是绿色的绢,下身一袭高腰红黄相间的条纹长裙,肩披姜黄帔帛。几个俑的身子为木质,胳膊是纸捻的,她们出土时,考古人员发现那纸上写满了密密难辨的文字,想来应是生者对死者的叮咛和祝愿。这里面的故事,连同彼此成为一世亲人的深情,细想是要落泪的。
女子的装扮,关乎民风,关乎国体,对此,唐朝的皇帝各自有不同的见解。唐高宗见女子戴着只能遮面部的帷帽时很生气,在诏书中大骂:“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唐玄宗是个开明的人,他下的诏书反倒要求“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遮蔽”,于是简洁的尖顶胡帽又流行起来。女子们靓妆露面,渐渐越发大胆,后来出行时彻底舍弃了帽子。唐皇室有一位公主安葬于开元年间,她墓中出土的骑马女俑里,已经有一些露着头发的了,不仅如此,她们还在马上弹琵琶、吹筚篥、弹箜篌,好不快活。还有一个英武的狩猎女子,骑跨马上,身后站一只猞猁,更增加了她的威风。她侧着身子,眼神机警,似乎已看到猎物。她没有戴帽,头上的髻又大又圆,她的脸蛋也是又大又圆。
唐朝的开放与繁荣,吸引外族人纷纷入境,唐俑里面也如实的混进了许多胡人俑。曾在洛阳博物馆遇见一个帅气的胡人男俑,深目高鼻,一身行头甚是惹眼。他上身小翻领紧身白色长衫,腰间系细黑腰带,下身是紧身豹纹裤,脚蹬棕色鞋拖。他两臂弯曲举至肩侧,一腿前倾,胯向后扭着,这姿势配上这妖娆的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跳什么热辣的舞步,其实人家是在牵骆驼。
唐俑是人俑艺术的高峰和典范,当朝代更替至五代十国时,造俑风格骤变,造型奇异的镇墓俑开始大行其道。2017年,我游南唐二陵,见李昪的钦陵中出土的仪鱼俑,是伏卧着的男美人鱼,头戴官帽,相貌端正,颈部以下为鱼身,鱼鳞和鱼鳍皆雕刻分明,看身形似乎是一条鲤鱼。两年后,我在福建博物院又见到一条鱼俑,仰面向上,双眼微闭,头上绑了个髻,身下有四爪,尾巴蜷曲,说是鱼,看上去更像壁虎。他是在五代闽国第三位皇帝的妻子刘华墓中出土的,此墓出了四十多个俑,除了一小部分正常的人俑,其余都是鬼面俑、独角羊嘴神兽俑、卷发尖咀神兽俑、十二时辰俑等。从名字能够得知其非人的面目,身子依然是人身,穿着广袖袍子,双手一本正经叠放在胸前,一副官员模样。非人的头和这样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极为怪诞,我不太喜欢。
五代十国以后的俑我见的就少了。也是因为宋朝兴起纸扎冥器,随葬俑的数量的确在减少,总之,宋辽金元的俑我没有特别记住的。明朝,俑有了一个复兴,王族常陪葬成套的出行仪仗俑。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朱檀,痴迷炼丹长生,十九岁时因丹药中毒死去,朱元璋恨其行径荒唐,赐谥号“荒”,后世称为“鲁荒王”。我去看过他的墓,也在山东博物馆看过他墓里出土的几百个木俑,有武士、官吏、内侍、乐手,场面宏大,俑的样子中规中矩,没有什么趣味。倒是在大理市博物馆见到的一批明陶俑,颇有异族风情,内有几位并脚站立的女俑,披着长发,椭圆形脸蛋,宽肩宽臀,低垂眉眼,低领裹身长裙,领口处露着结实的脖颈和胸脯。看到她们,总让我自然联想起西方油画里圣母玛利亚的风姿。
清朝是俑的终结期,迄今唯一出土的清俑,来自于吴六奇的墓,现收藏在广东省博物馆。吴六奇原是明朝总兵,后来反戈降清,死后得康熙御赐造墓。《鹿鼎记》中写到过他,然而小说与史实似有出入。他墓中出土了数十个陶俑,类别有侍女俑、庖厨俑、衙吏俑等,面目服饰都精心刻画加工过,制作极其精良。每人手中所捧道具,如宮扇、果盒、宝剑、文书等,以及身边摆放的陶桌、灯台、象棋、麻将、书、脸盆、椅、床、灶之类的物件,件件玲珑可爱。几百年前的东西,与现代相隔不太远,看起来也真也亲。只是我那年去时,对俑的历史尚且懵懂,不知这是古代墓俑最后的实证,糊涂地看了一回。事后忆起,非是专程而去,却能无意间遇见,无心时相识,让我在回顾自己看俑的历程时,得以圆满收尾,实属有幸。
郑玄注《礼记》时对俑有这样的描述:“俑,偶人也。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俑似人,又不是人,这种奇妙的特质,激发了古代文学家浪漫的想象力,编出了许多精彩的志怪故事。
明代有一篇《牡丹灯记》,说的是浙东某地,元夕灯会上,乔生邂逅美人符丽卿,丽卿身边有个挑着双头牡丹灯的丫鬟,名叫金莲。乔生与丽卿发生情事,夜夜相会。邻居老翁凿墙偷窥,看到的丽卿却是个粉骷髅。他告知乔生,让他去丽卿住处探访,结果乔生寻到了一处寺庙暗室,见一灵柩,上写“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灯下立着一个绢纸做的丫鬟俑,背上有二字:金莲。乔生忧怖交加,欲与丽卿断绝往来,她岂肯罢休,索性将他拉入棺材,一同做鬼快活去了。此后,每逢云阴之昼,月黑之宵,二人便携手出来散步,金莲挑着双头牡丹灯在前引路。如有人不幸遇到他们,回去就会生重病。众人请道士来捉妖,把三人擒了,堂前审讯。那二人认下了贪淫好色之罪,可金莲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她说:“我本是烘干的竹子为骨架,染色的白绢为皮囊,不知是谁把我做成俑来使用,尽管面目肤色头发都非常逼真,还为我取了名字,但我又没有妖术,我只是个俑啊,一个俑怎么能作妖害人呢?”
我看到这里,也觉金莲说的有道理,男女情爱,与俑何干?她着实是冤。
可道士不听,将她与那二人一同打入了地狱。金莲可怜。
同为丫鬟俑,另一故事中轻素和轻红的际遇则是一番柳暗花明。
唐朝人曹惠在寺院里看到两个女木偶,颜色有些剥落,雕刻甚是巧妙,便带回家给小孩玩。有天小孩正在吃饼,其中一个木偶忽然伸出手来,意思是也想要一块饼吃吃,小孩惊讶,跑去告诉大人。曹惠笑着说,你把那木偶拿来。木偶不悦,说,轻素我自有名字,为什么叫我木偶啊。原来轻素和轻红是南朝宣城太守谢朓的陪葬木俑,那天,她们正服侍谢朓的夫人洗脚,突然闯进一伙盗墓贼,夫人害怕,当场变成了白骷髅。贼人拿了墓里的财物,见两个木俑生得不坏,也顺手带走了,二人从此在世间流落。曹惠听了,知道不可轻慢,问她们有何打算,轻素说庐山山神想请她们去当舞女,她觉得甚好。曹惠于是找画工将二人重新描画,姿色更胜从前。轻素很满意,笑着说,看来不仅仅是舞女了。果然,庐山山神娶了她们为夫人。
写这故事的作者很有趣,把这等离奇的情节编排到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身上。难怪轻素俏皮机灵,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她的主人可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大文人小谢啊。文中还说谢与前夫人感情不和,到阴间另结了一门阴亲,与新夫人非常恩爱,可惜被盗墓贼坏了好事,他们还把谢的脸颊敲碎了,拿走了他的项圈。
作者说得绘声绘色,如亲眼所见,读的人也就权且当真。我喜欢轻素这个俑,她心思笃定,明白自己是异类,不可与人厮混,山神那里是最稳妥的去处。
相比之下,《太平广记》里记录的一位瓷妇人,就没有这样的见识,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白白丢了性命:卢生家里有一个瓷做的妇人,他的妻子偶尔调侃,说不如把这个瓷妇人与君为妾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瓷妇人竟因此动了痴念。后来卢生经常看到有个妇人躺在自己帐中,怀疑是瓷妇人在作怪,便把她送到寺里去供养。寺里的童子清晨看到殿内有一妇人,问她何人,她答是卢生的小妾,因为大老婆嫉妒,被赶出了家门。童子将此事告诉卢家,他描述那妇人的容貌服饰,正是瓷妇人的模样。
以前读胡兰成的自传,见他写曾经的同事沈启无时说:“……我乡下忌嫌木偶戏,因其对于人是冒渎,有一种鬼神的不吉感,木偶做毕戏到后台,要用手帕把它的脸盖好,否则它会走到台下人丛中买豆腐浆吃,启无亦如此对人气有惊讶与贪婪。”我问朋友,胡兰成用木偶的比喻是要说什么?朋友答:“不是人,硬充人。”
瓷妇人大概就属于“不是人,硬充人”的,只是有了人的模样,万万不该有想成为人的心思。她最后结局凄惨,众人将她击碎了,然后,发现她“心头有血,大如鸡子”。这个故事最动人处就在这八个字里,我读到时,心头一震。
俑最初由泥捏而成,在一些上古神话的记载中,人的起源亦是如此。天地初开,未有人类,女娲仿照自己的样子抟土造人——细想此举,女娲真是一位智慧伟大的女神。不料后面又说,造了几日,她累了,就用绳子蘸着泥水甩,甩出的泥点也能变成人。这样是轻省多了,只不过工艺和质量不同,出来的人的命运也不同,用土捏的成了富贵人,绳子甩出来的则成了贫贱的人。原来女神做事也难免虎头蛇尾,她一脸不耐烦甩着绳子的样子引人遐想。
造俑的工匠堪称另一种神,他们传承了女娲的手艺,仿照世间人的样子,企图造出另一世界的人。事实证明,他们造出的泥身,在时间的侵蚀中,比墓主人的肉身更有抵御的力量。当俑再次回到人间,后人从他们身上,得以看到没有摄影术的时代人的样子。
有时,在茫茫俑海中,我会邂逅似曾相识的面孔。一个东汉俑诡秘的神情和机灵的小眼睛,让我眼前瞬时浮现出某位友人的样子,而一个歪着脑袋背着手的唐朝女俑,怎么看都是我那个胖闺蜜的前世,还有一位憨厚刚毅的兄长,每次见他都会想起北魏的一个仪仗俑。我因而思忖,既然大多数俑都有人物原型,一个现代人和一个俑相像,其实是和古代的一个人相像,也许,这两人真有久远的血缘,他恰巧是他辗转留存在世间的后代。
可我没想到世上竟会有和涛涛一样的俑。涛涛患有唐氏综合征,我们认识时,他大约十岁,长着唐氏综合征患儿特有的面容,身高和智力与年龄不符。他家离我单位不远,他的爸妈都是淳朴的人,因为生了涛涛这个孩子,变成了淳朴又忧愁的人。两人在门前摆修自行车的小摊,每次见我经过,都连声说:“涛涛,快叫阿姨。”涛涛坐在小板凳上,抬起扁平的脸,斜着眼睛看我,咧嘴笑笑,说:“席。”
一旦离开爸爸妈妈身边,涛涛便会遭到闲人的恶意戏弄,或被脱衣裤,或让他跪下磕头,他毫不反抗,欣然接受。我碰见一回这样的场景,气愤又无计可施。后来他长大了,变得高胖了些,能帮爸爸给顾客的车打气了,继而又有了一份工作。每日,他慢悠悠地推着三轮车在附近运送垃圾桶,与我迎头遇上时,我大声叫“涛涛”,他仍咧嘴笑笑,叫我一声“席”。
若干年后,我在某个私人博物馆游览,忽见一石俑孤零零地站在展厅角落里,于是走过去,端详他的脸,心中不由惊异,那是一张与涛涛一模一样的脸。
他是个武士,身披甲胄,双手交握于腹部。我记得以前冬天时,涛涛将手揣在棉袄的袖筒里,也是这般样子。只是石俑手中还有一把竖握着的剑,扁平的脸上,没有涛涛神态中的障碍和迟滞,有的是风霜过后开悟式的平静。彼时展厅里没有别的游客,他平静地注视着我,仿佛早就在等我到来。
自单位搬迁,多年没有涛涛的音讯,与这石俑照面的瞬间,真如同故人重逢。我太想知道他的来历,但说明牌上只写着他是明朝人,其他一概不知。我为他拍了一张照,想着日后若是能再见到涛涛,拿给他看,告诉他,明朝也有个涛涛,明朝的涛涛很威武。
和石俑告别后,有所体悟。起初,我看俑单是看俑,看其意趣。之后,看俑是看人,看到古人也看到今人。再后,看俑是看史,因为俑是历史留下的插图,或者说,俑就是人形的历史书。而当我看俑看到極其用心时,从中更会生长出许多新奇深远的枝蔓。
这些年,每到达一个城市,行程中有一站一定是博物馆,博物馆里总有一些俑如明朝石俑那样,在我必经之处等候。面对他们,我惯常品头论足,指指点点,且笑且叹。俑们虽不语,心里想必对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每当我转身离去时,便能察觉到身后的异样,我猜,是俑们在冲着我的背影挤眉弄眼。我暗自笑了。
燕燕燕,作家,现居山东滕州。主要著作有《梦里燃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