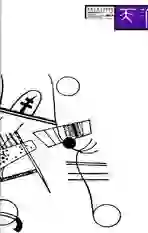废墟之上
2022-06-09孙郁
在旧都生活久的人,是很容易生出思古之情的。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日报社上班,办公大楼就在元大都南城墙的旧址,报社的老员工,偶尔念及于此,还说过不少的故事。身边有几位朋友,热心收藏古董,对于旧都是很有心得的。负责副刊工作的副总编辑是林浩基先生,也是嗜古很深的人,工作中常把自己的趣味也带了进来,影响了周围的人, 一时颇有些文气。
初次见到林浩基是什么时候,已经忘记了,大家都称他老林,印象中他慢条斯理,有点深不可测的样子。渐渐发现他是个可以深谈的人,与时风是保持一点距离的。他藏了许多古书,关注学界动向和艺术思潮,对于绘画尤有心得,多年前出版过《齐白石传》。在一向板着面孔的报社里,有这样的前辈在,氛围总还是不同于别处的。
那时候文艺部的副刊有《广场》《收藏》《流杯亭》几个版面,盛行着某些京派风格。老林很重视副刊的文章品位,看得出,在仕途与文途间,他倾向的是后者。他的点子很多,许多书斋气的栏目都与他的思路有关。我的那本《鲁迅藏画录》,就是我在他建议开设的专栏中所写的文章的结集,因此,我们也渐渐成了忘年交。
我离开报社不久后,老林就退休了。据说宣布退休那天,他就拎包离开报社,再也没有回来过。他或许去寻找别的什么,做自己喜爱的事了。总之,二十年间,消息全无。我和朋友偶尔谈及他,都很怀念那段难得的时光。
不料近日忽收到他新出版的《清明上河图前传》,才知道他这些年沉浸在古代文脉里。是否在报社时期他就酝酿了此书的写作,不得而知。这一本书将美术史中扑朔迷离的部分演绎得风生水起,雅俗共赏的韵律里,别有一番味道。一个人到了晚年倾力于一本关于古人的书,一定是有大的精神寄托。翻着这部满带古风的作品,好似又回到了当年的报社,楼道里传来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想起与他相处的日子,也有一丝往者不可追的感觉。
在这一本书的后记中,他说,所写的不是画家张择端的传记,而是历史小说。开宗明义,这是虚构的作品,借着远去旧迹,铺陈出北宋江湖的人文地图,也交织着诸多精神线条。原来老林有如此的情怀,先前的同事们,多半未能料到他的修炼之深。
对于今人而言,北宋的时光远矣,要弄清其间轨迹,需要做许多功课。《清明上河图前传》写的是画家张择端的故事,传奇与录异之调深埋于文中,主人公的生活,一波三折,光影缭乱。北宋的政治生态,士人之心,诗画品相,背后的存在都不简单。以张择端的爱情与艺术之路变化为主线,串联出官场风气、儒林积习和时代之音,时空是阔大的。艺术在中国从来不是高悬在空中之物,总纠葛着人间的冷暖阴晴。书中描述古人的精神生活,涉及诸多我们今人不太了解的东西,皇帝喜好,大臣心事,民众感觉,易代之苦,指示着一段血腥之迹。从作者的谋篇布局里,可以看出其历史观与审美观。老林在想象的世界里,流露的是他的人生哲学。
北宋年间,文坛出现了不少神奇人物,苏轼、米芾、周邦彦、黄庭坚的故事一直被后世不断叙述着。唯张择端史料阙如,行迹模糊。元代张著在其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卷帧上,留下几十个介绍性文字:“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这段介绍留下诸多想象的空间,许多人与事都语焉不详。不过从彼时社会形态与文化走向看,时聚时散的烟雨,不测的险境亦诡异万端。皇权之下的文化,要保持个性谈何容易,艺术家一旦出名,精神不被弯曲实则很难。要写好这段历史里的文化经纬,自然渗透了古人的各种经验,也多特别的学识。在大的变故里看人性的限度,体味生死之意,许多不尽的情思,都于此散开。
绘画史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六朝以后的人物画与山水画,已经颇有些风致。曾看见西川一篇文章——《在“伟大”的意义上,唐诗、宋画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能够感到作者对于宋代绘画的热心。说唐诗与宋画是一流的艺术,也是对的。林浩基钟情于北宋艺术,也是此类心情所致。他对于文化的流动性,有自己的心得,知道一切不凡的作品的产生,与时代精神有关系,而那些超俗的意象,都是远离台阁的一种顿悟,民间想象是滋润了诸多才子的。《清明上河图》的伟大,乃是因为心贴在土地上、河流间,在人间烟火里看出世间冷暖。张择端与周邦彦、米芾多有不同,因为他有着平民意味。他沉浸于百姓世界,又超于万象的慈悲。士大夫诗文中遗漏的社会史隐含,竟在他那里有了感性的表达。
记得有人说过,在绘画史上,倘若没有《清明上河图》的流传,我们对于古代艺术的理解就少了市井之风和民俗之韵。栩栩如生的日常生活,恰是士大夫文字里少见的东西。写张择端这个人,既要懂艺术生态,也要了解民俗史。因为历史留下的资料有限,小说家要靠想象与理解力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老林描写这段历史,一是有向艺术家致意的意思,二是从时光里寻觅人生的奥义。这两点乃是小说写作的重点脉络,后者所展示的隐含,引我们思考的地方甚多。古代小说常见的恩怨情仇,纠缠在雅意中。士大夫生活在俗世里,不免有烟火气,但倘若能超越于斯,有另类情怀在,会留下不同的行迹,那便是精神之光,会驱散士林的暗色。但在功利之徒那里,不会有类似的新径,多少年过去,人们不断礼赞张择端的笔下风光,乃是因为那里有主流文化所没有的闪光。
前人论及《清明上河图》,常参考《东京梦華录》一书。比较起来,二者给人的感受有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后者记载了汴梁的市井之风,北宋的各类形态引人思索者,都被学界深入研究过。曾经有人指出,《清明上河图》可以让后人对应某些形影,繁华之中,人的诸种形态也栩栩如生走入眼帘,真的是眼花缭乱。我们看彼时文人的诗词歌赋,享世的一面不免有沉落的气息,思想是灰色的时候居多。宋代诗人善写幽婉之句,大约与悠闲中的虚无感不无关系。有学者从城市文化层面论及其意,就看到了人间太平之景的背后,危机也深隐其间。
《清明上河图前传》提供了一个认识历史的角度,对于一向模糊的人与事,有了另一种演示。作者写艺林之事,丰富的感觉在人物的神色间飘动,于陈迹的缝隙间看见世相的诡异点。美丑之间,儒林的遮羞布也渐渐脱落。在中国,文化生态与政治生态是难解难分的。从普通的士大夫写到皇帝,百姓与皇权间的关系有复杂的纠葛。而奸人当道时,是非颠倒,万物蒙羞。这是旧小说间常有的主旨,我们于此也领略了文化中一个延续多年的主题。
历史小說,说起来是历史社会生活的缩影,感性画面的背后,也有认识论的支撑。这是这一题材所决定的。此书要表达的题旨有多重性的隐喻,诗意的存在乃社会形态隐曲的表达,只有在丰富的历史维度里,才能把握审美之趣。对于彼时的艺术品,老林多有崇仰,所涉话题繁多,事件离奇,全书有着浩淼的沧桑感。艺术与时代之关系,其实并不简单。
以往的士大夫者流,关心的是经学与科举之路。但真正的读书人,是不受时风影响的。苏轼、黄庭坚都有不俗之处,精神有别样的选择。到了张择端那里,趣味也在另一世界里,偏离了某些旧的审美情调。他的绘画受到六朝民风之趣的影响,也有唐人胡气的熏陶。跳出士人的窠臼,方有了敏锐的目光。在危机四伏的年月,他为时代绘下一幅长卷,实在是让人感叹。刻画这样的人,一需懂得笔墨之道,二要深解市井之风,三是有政治眼光。老林努力朝着这路径走,笔墨间留下探索的甘苦。于此三处可见社会的风貌,立体处理其间的风雨,时空就饱满了许多。老林的笔触不见暮气,从前人那里学来叙述的策略,又能在自设的危境里自如往返,娓娓道来之中,写出自己心中的镜像。
《清明上河图前传》要处理的难点很多,作者有两种笔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世态,二是侠者。前者有官场之浊流,蔡京、高俅、秦桧等奸臣嘴脸历历在目;后者则有民间爱意,汪家田、赵金明与张择端的友谊让人心生感慨。老林善写女性之美,爱情的表达带有士大夫的意味,在杨子清、杨子明、尚荷身上,不乏老中国读书人的心仪之影。看得出,传统的审美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染了老林,要跳出士大夫的惯性是很难的。不过这部小说也在不断挑战旧的模式,出奇的地方是对于战乱的描写,金人南下,北宋都城遭掠,靖康之耻中,艺术家也经历了生死考验。这小说不是耽于审美的醉意,根本的是写世相的无常与善心的苦涩。从宋徽宗到张择端,留下诸多历史的叹息,倘仅仅在艺术的世界里,不解外事,是不能解救生灵的。由此也能够体谅出一种苦味,在精神单一的社会,文明之光总还是脆弱的。野蛮常常摧残了天下,汴梁繁景,不过一瞬,转眼便消失在烟云之中。张择端的长卷,引得我们也只是在追忆里长长叹息。
说起来,中国的文化有光泽点的存在,都是在苦难里出来的。这部小说里要表达的,大概是这个观点。在叙述方法上,老林借用了通俗小说的笔调,而背后未尝没有现代悲剧意识,其精神的特指之处,我们还是明显感受到了。全书有花团锦簇之处,也多哀凉之笔,生命的价值如何才好,什么是人间最为值得驻足之所,文本里都有所暗示。我想,这一本书,是作者一生寻路的记录。在古人的身上,投射己身之内觉,给世间留下体味的空间。作者的士大夫心绪的矛盾、碰撞之处,也流露了探索中的甘苦。
通俗小说倘若一味耽于才子佳人的故事,易滑入平庸。老林深味悲剧的价值在哪,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得暗流涌动,凉风乍起,将古代小说的大团圆梦打破了。金人掠走《清明上河图》后,张择端曾冒死追画,但孱弱之躯岂能抵过兵匪。而心爱的人也在战乱里死去,暖意之光消失殆尽。后来在临安苦苦重画旧作,还残存着一丝希望,他天真地向南宋的皇上赵构献画,不料遭秦桧谗言,被轰出宫殿。拳拳之情,不得所认,落得孤苦之境。这是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忠而获罪,爱而得怨,屈原式的悲慨在此复现,历史在轮回里,上演的是同样的悲剧。
读《清明上河图前传》,一切都落入暗地,美的毁灭,爱的消失,已让先前的荣华成为碎梦。钟爱艺术、痴情于诗文的士大夫,在彼时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万难的。老林如此设计情节,看出内心无量之苦,对于华夏历史深层之痛是感触极深的。读书人的抱负,仅仅系于帝王一身的时候,易走进绝境。张择端荣于此,也哀于此,他的死,也说明了士大夫面临的是无路之途。在美的光泽下,是一片废墟。而废墟之上,也只生杂草,难见林木。荒原感才是进入历史的通道,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太懂得,经历了风雨的人,对于老林的苦心,当能解之一二。
取今念古,是近代许多小说家的一种审美趣味,每个人的兴奋点大为不同。施蛰存写《鸠摩罗什》,以弗洛伊德的观念为之,里面不乏幽默与戏谑,词语背后乃是现代意识。姚雪垠更聪明一些,从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那里借来经验,《李自成》就有现实主义的元素在,虽然讲述的是明末故事,但画面却经过了新文学理念的沐浴。历史小说怎么写,与作者的精神背景与知识背景有关。凌力的《少年天子》有清史习得的痕迹,多少受资料的限制,但于狭径里也能拓出新路。《清明上河图前传》里的北宋风云,带有《水浒传》与《神雕侠侣》的风韵,山高水长,野径生树,可以演绎的空间很多。老林为何不取写实之境,而走旧小说写意之途,其中有价值取舍也说不定。我觉得也许是受到宋代绘画风格影响,写意当能传神,笔端带有风情吧。
老林是个痴人,对于诗文与绘画,不乏沉醉其中的笔调。你会感觉他一直沉浸在远去的时光里,于灰暗里打捞着一线光明。这光明虽然弱小,但抚慰了读者的心。许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我们看他的自述,就能够感受几分苦意: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撰写《齐白石传》,三十多万字。白天上班,深夜十二时起床,写到第二天早上五时,之后,跑步到天安门,尔后坐公交回到东单二条的家。整整花去二十九个夜晚。而写这部书的“前传”时,近五十万字,我花了两年半时间。其间的艰辛、困顿,难以言说。真的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如此说来,在自我燃烧的时候,是可以与古人神遇的。这是老林的期盼,说他是寻梦之人,也不无道理。小说最难得的,是对于赤子之心的描摹,在张择端身上,有古代艺术家可贵的品格,寻找那神异的美,也无意中丰富了作者自己。我总觉得,写作之于老林,乃精神的游走。现实不能解决的难题,却在文字世界里得以克服。在张择端的影子里,有老林这代人的苦乐,古人的心事未必不是今人的心事,穿越古代的人,总能看到别人未遇见的光景。
孙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文字后的历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