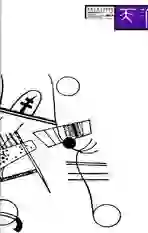去海南吧
2022-06-09贾梦玮
现代人去往某地,常常是受了旅游报刊和社交媒体的“蛊惑”,产生对某地的想象,因此而有了“动”意,成为某地的观光客。观光客与目的地之间很难形成深层次的关联,去过也就去过了,就此甚至产生“绝缘”关系:既已去过,不会再去,甚至不再想它。
有的地方因为自然条件优越,成为度假目的地,来了还会再来,比如海南。名字中含“南”者,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比如南方,比如海南。“海”本就具有一种魔力,海而南,南而海者,自然更是魅力的叠加与扩展。海南之所以吸引人,首先是它优越的自然条件:蓝天白云、洁净的空气、热带雨林、大海与沙滩。在中国,能把这几样东西汇聚到一起,也只有海南,没其他地方能和它竞争。这样的好地方有三多:度假者多、游客多、移民多。我第一次到海南三亚,印象特别深: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在公共場所听到最多的是东北口音——海南之南对东北之北吸引力太大了。
有些地方注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记忆中驻扎下来,成为意境、思念、玄想、牵挂等,因而不朽。比如苏轼之对于海南,就是一种相互锻造的关系。
在古代,特别是唐宋之前,海南是蛮荒、瘴毒的代名词,文明之地的人到此,一定是因为被贬官、发配,是严重的惩罚。如今的海南岛上建有五公祠,纪念唐宋以来被贬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纲、李光、赵鼎、胡铨。李德裕是晚唐“党争”领袖,另四位则是南宋时期因为主张抗金而被踢到此地。他们自然都不是被海南的风景吸引过来的。影响最大、流泽至今的是苏轼,在五公祠之外专祠供奉。苏轼无疑是来过海南岛的最具影响力的古代名人。
苏轼被贬海南之前,他已贬在惠州三年。那时的惠州,已是大陆最南端的南蛮之地。但苏轼到哪儿似乎都能享受生活,并且求田问舍,想着就此留在当地。苏轼在惠州所作诗歌描绘的“美好生活”,让读诗的人羡慕、嫉妒,“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苏轼的诗流传得快而广,哪怕他是戴罪之人。这些诗传到京城,他的政治对手章惇等人看了,心里老大不是滋味:哪能让你这么快活!于是,苏轼就被赶到了南而又南、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儋州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去世前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那时的海南,不是旅游目的地,不是度假胜地,而是流放目的地,但却是苏轼平生功业成就地之一,人生的骄傲。苦成蜜,涩酿甜。
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当时分为琼州、朱崖军、昌化军、万安军四个区。昌化军就是苏轼被发配居住的地方,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海南省儋州市、昌江县、东方市等地,那时尚是半开化的蛮荒之地。此时的苏轼已六十二岁,年岁不饶人。相伴朝夕的侍妾王朝云已病死惠州,唯一陪着他的就是小儿子苏过。苏轼的乐观中也掺杂了一丝悲观,正如他自己所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枢,此亦东坡之家风也。”首先做最坏的打算,然后视情况再说。想开了,人生也就开了;绝大多数人就是没能想开。
等着苏轼的是海南不宜人居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但他总能找到生活下去的理由。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九月十二日,他在《试笔自书》中写自己的坎坷: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
天际都是水,人不管在何处,其实都是在“岛”上,几块大陆也就是几个岛。既是如此,在哪儿不一样呢?苏轼还写道: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馀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甚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使折胶之寒,无所施其冽;流金之暑,无所措其毒。百馀岁岂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特如蚕鼠生于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温,一吸之凉,相续无有间断,虽长生可也。
知命乐天,苏轼总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而且总能感到让他庆幸,反正对他有利。即使什么也没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到荒地里挖野菜,苏轼也能把这些当成延年益寿的珍馐;抓老鼠逮蝙蝠,用此肉食补充蛋白质。苏轼本是微胖之人,此时终于伶仃体轻。他自嘲道:身轻如此,可以骑在鸟背上回家了。
苦成蜜,涩酿甜。海南锻造了苏轼,激发了苏轼,写于海南岛的诗词是他生命绚烂的表达。如立春日所作《减字木兰花·已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又如《千秋岁·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不抱怨,亦无悔意,这就是苏轼。
困境之中,亲情犹显温暖与珍贵。表达思念之情的诗词,如《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首写于中秋的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思念之情。此时,苏辙被贬在循州,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兄弟俩一起离蜀,中进士,享文名,或在朝,或为官一方,真是风光无限。但“月明多被云妨”,各自多次被贬,人生聚少离多,徒增想念。
秦少游曾这样评价苏轼:“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他认为,苏轼的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性命之理,也就是人生观;其次是担当与识见;再次是文章才华;最后是周旋世事、人事的能力。说他不合时宜,指的就是最后这一条。海南最好地证明了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道。
贬在儋州三年,苏轼劝农、讲学、制药。大量海南青年受教于苏轼,在他之后,海南才有了一定意义上的读书人,有了考中进士的士子。这是他所谓的“功业”。其实,苏轼无论身在何处,总有类似的功业,这次他是在荒蛮之地点起了文明的星星之火。
他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苏轼接到赦令,离开了海南时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在回京的半途去世,再也未能回去,但海南还是永远记住了这位“海南民”。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说不喜欢苏轼的,借他自嘲、自解、自炫、说事、说理的人不可胜数。我多次到过海南:去过海口、三亚、文昌、琼海博鳌……或者开会或者和家人一起来度假,但竟然从未去過儋州。倒是几次躺在三亚的沙滩上,想到苏轼,想望儋州。苏轼“深于性命自得”,特别是令身处逆境之人所向往;他能造福一方,给当地人留下念想;他的文章才华,是宝贵的遗产。但他不是忧国忧民、忍辱负重、折冲樽俎的大政治家。朱熹、钱穆甚至不太愿意承认苏轼是一个儒者。
在海南的沙滩上,面对大水,我还曾想起一位古人——张爱玲的堂叔张人骏。清末内忧外患之时,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人骏有着国人较为缺乏的海权意识,他两次派人到南海宣示主权,赶走盘踞在东沙岛的日本商人,给西沙诸岛命名并绘制地图,升起大清黄龙旗。为了纪念张人骏在南海宣示主权,1947年,国民政府将南沙群岛的一片海滩命名为“人骏滩”。张人骏后转任两江总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过不少革故鼎新的事。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由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打到了江宁(南京)城下。“战”已不可能胜,“降”又与他的道德理念相违背,他只好选择“跑”,最后张人骏是用箩筐从南京城墙上缒下去,逃到上海做了寓公,后流寓青岛,晚年在天津定居。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回忆说,她小时候在天津,张人骏(张爱玲称为“三大爷”)每次听张爱玲背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就流眼泪。亡国之臣的他,多情伤故国,掉眼泪是可以理解的。与苏轼相比,张人骏更显儒家精神。
我每次去海南,除了享受自然,吃海鲜、热带水果外,还有一件必做的事:见韩少功。他曾经是“寻根文学”的大将、文学湘军的主力;海南建省后,他去了海南,创办《海南纪实》,成为海南文化的积极参与者。这些是我从文学史上看来的,从别人嘴上听来的。《钟山》创刊三十周年,我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从他的文章中我才知道,他之所以落户海南,跟《钟山》1987年的南海笔会还有点关系:“那年《钟山》在海南组织笔会,有很多作家参加……海南岛地广人稀,林木丰茂,花异果奇,特别是东郊椰林的幽深和洁净一如童话,让我不知今夕何夕。说实话,一年后南迁海岛,我的念头就来自椰林里网床上星空摇动之时。”那时的海南虽仍是地广人稀,韩少功移居海南却是主动的选择。当然,不久那儿就成了一片热土了。
我认识韩少功时,他是名刊《天涯》的社长,海南作协的主席。记得一次海南作协组织青年作家改稿会,我作为《钟山》的编辑应邀参加。那次改稿会上,韩少功以海南文坛当家人的身份与会,对海南文学、海南作家如数家珍,毫不含糊,没有任何套话,说的都是海南青年文学创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我不是文学史家,无法界定韩少功对于海南文学的意义。但我能感觉到:在海南岛,韩少功是一杆文学的大旗,在海南的天空、海南的风中猎猎作响。还有,作为办刊人,我瞧得上眼的刊物不多,但对韩少功主编的《天涯》,我服气。我曾经这样评价他的作品:“有情感的思想,有思想的情感,是温暖的思想。”这也可以用来评价《天涯》。
“听听老韩怎么说。”认识韩少功的人,碰到问题,无论世事还是文坛之事,不少人特别重视他的看法,大概是因为他不仅态度公允,而且是很少见的作家中的思想家,能思常人所未思,见他人所未见。有一年春节前我带着儿子到三亚度假,本来计划从三亚直接飞回南京过年。想起这个季节韩少功应该在海口,联系好后,我改签了机票,挤上了春运的火车,从三亚到了海口。儿子年幼,被春运的人流挤得东倒西歪,对我改变行程颇不理解。我改经海口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想见见韩少功,就一些事情“听听老韩怎么说”。
我特地去看韩少功,却不是去海南,而是到他在汨罗的家。文坛的朋友都知道,他大致是秋冬在海南,春夏在汨罗。我有时想:他这是要沟通汨罗之水与南海之水吧。那次我先是坐飞机到了长沙,然后请作家宋元亲自驾车带着我前往汨罗。彼时长沙到汨罗的路况较差,也没有导航,我们只能不断地找人问路。好在离他家尚有几十公里时,被问路的人居然都知道这位“韩爹”——这是对这位甘愿与农民为伍的大作家最为敬重的称呼——否则我们真不知道如何寻过去。韩少功的家在一所乡村小学里边,周围都是农家,弥漫着一派乡野的气息。在很多时间里,他都在和乡民们一起抽烟聊天。我的印象中,韩少功是中国绝无仅有每年总有几个月时间真正与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名作家。他有资格思考中国问题。无论是在历史深邃、人文绚烂的汨罗,还是在天涯海角的海岛,韩少功都能系忧天下。
终于找到他家,韩少功正在地里忙活,伺候庄稼和蔬菜地。中午上桌的几乎都是自产菜。他的家中陈设极其简朴,家具用的是原木,连树皮都未处理。房后有一水库,一条小船自横于岸边。韩少功属龙,我开玩笑说:“你还是离不开水啊。”他不仅是汨罗水系的一条湘龙,而且是南海波涛中的一条中国龙。对于龙来说,往来南海与汨罗,也就是眨眼的工夫。我每次到海南,都会想一想:韩少功这时节在海南还是在汨罗?
每次到了节假日,总要和家里人商量去哪儿走走。犹豫、争论不决中,最后总有人跳出来说:
“那还是去海南吧。”
贾梦玮,作家、编辑,现居南京。主要著作有《南都》《往日庭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