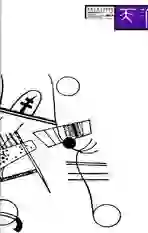母亲今年九十七
2022-06-09清风
在我住的宿舍小区里,母亲称得上是一位明星,不是因为有什么艺术特长,而是因为长寿且健康。母亲生于1926年3月10日(农历正月廿六),在小区属第一年长者。虽然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压弯了她的腰身,但她就像那傲风斗雨的椰树,依然那么苍劲,那么硬朗。母亲现在耳不聋,能听见悄悄话;眼不花,尚可穿针引线;步子稳,每天行走一两公里不用拐杖;头发少许花白,脑后部还都是青丝。邻居好奇地问我:“你母亲有八十岁了吧?”我笑着说:“今年虚岁九十七啦!”语气中流露着幸福、自豪!
都说海南空气好、阳光多,冬天温暖,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2014年底,我调到海南工作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将年近八十九岁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接到了海口。那一天,暖阳高照,白云舞蹈,看到脸上挂着笑的母亲缓缓走下飞机舷梯,我的心海翻腾起喜悦的浪花。自十六岁起,我一直在外地上学、工作。未能在操劳一生的母亲膝前尽孝,是常常在心头涌起的遗憾,盼望着能天天陪伴她老人家安享晚年。
但母亲哪里是来养老,分明是照顾我来了。尽管我早已年过半百,可在她的眼里,我好像仍在襁褓之中,仍是一个永远没有长大还需要她呵护的孩子。外面刮风时我出门,她总会叮嘱,多穿一件衣服啊,小心着凉。我回家常常光脚穿拖鞋,她总会提醒寒从脚起,让我马上穿袜子。她还会到我的房间,整理床上的被单,整理我的脏衣服。无论我下班多晚,她都会把饭菜摆好,等我回来。吃饭时,她总会先为我舀一碗汤,在钵里挑几块肉多的鸡块或排骨,全然不顾我坚拒,搁进汤碗里,令我吃下。她经常埋怨我吃米饭太少,总要把自己碗里的饭分拨给我一些,我说我想多吃菜,她瞟了我一眼,说:“吃饭吃饭,就是要多吃米饭。”她对我在跑步机上大汗淋漓地奔跑十分不解,说这样会伤身体。我解释这是减肥,她上下打量我,郑重地说:“就你这块头,我看还可长几斤。”她坚持在缺吃少喝的年代里形成的观念,以胖为健康和追求。我指着自己日渐增粗的腰围,搬出大专家的观点,讲肥胖对身体的害处,但她并不以为然,总是劝告我:“多吃點、多吃点。”
老实说,一开始我对母亲这般照顾不太适应,也担心她太辛苦太劳累,毕竟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了。后来我发现,母亲对自己尚能照顾忙忙碌碌的儿子、打理他的“单身汉”生活而感到宽慰、满足甚至是快乐,且越来越有劲头时,也就任其自然了。一次我和她坐在门口聊家常,突然她停下话头,盯着我的腿,一巴掌迅疾拍下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向我展示战果——手掌中一只已被拍扁的溅着血迹的蚊虫。母亲找来清凉油,一边轻轻涂抹我被蚊虫咬过的地方,一边重重地骂:“这个该死的坏家伙!”那一刻,我的眼睛潮湿了,身边很多同龄人都已经没有母亲可以去牵挂,而我不但母亲健在,她还如同守护神一般待在我身边,一双眼睛须臾没有离开过我。这是一份多真切多踏实的幸福。
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是愉悦的,但我们母子之间也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口角”。她坚持自己去菜市场买鱼,而我坚决反对:“冰箱里有鱼,不用到菜市场买。”她说:“你喜欢吃新鲜黄骨鱼,这只有在菜市场买得到。”我的住处离菜市场有两里多路,中间还隔了一条四十多米宽的马路。车来车往,母亲这么大年纪过马路,实在是危险之极。我说:“车多,把您撞了怎么办?”她却说:“海口司机很客气,见了我这老太太会自动停下来让路。”她的振振有词让我无言以对。就这样,她乐此不疲往菜市场跑了差不多三年。直到2019年8月间,一天上午,母亲又如常往菜市场买鱼。忽来狂风暴雨,路人纷纷涌进菜市场,一时水泄不通。人群愈来愈挤,母亲手足无措,差点被挤倒。幸亏一位好心的摊主扶着她进了摊位,还递上小板凳让她坐着休息。这场风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等我知道时,已有好心人把她送回了家。这场遭遇让我很是后怕。当天晚饭后,我与她进行谈话:“妈,我对您不听儿子的话,执意跑菜市场,很有意见。今天万一被挤倒了怎么办?海口风雨多,马路上车多,今后您绝不能往菜市场跑了,否则儿子与您‘翻脸’!”也许是她从未看见我如此神情严肃,也许是她也被上午的场景吓着了,自此,母亲不再去菜市场,但一点没少操心:每隔两天,就如闹钟一样准时提醒在家里帮忙的侄女到菜市场买黄骨鱼。
母亲随身带来了一个针线包,里面有大中小等型号的针,白黑红等颜色的线,还有两枚她用了多年、锃亮的顶针。衣服扣子掉了,她自己缝;扣眼错了,她自己改。一天上午,母亲又坐在椅子上,左手托着一件白色衣服,右手牵引着针线,正聚精会神地缝缝补补。我凑上去一看,是在补一件旧衬衣,便说:“妈,别费那个劲了,我给您买件新的!”母亲头也未抬地答道:“这衣服只破了一个地方,补补就可穿。别花冤枉钱。”
“别花冤枉钱”是母亲的口头禅。她常常交代子女晚辈,她的衣服、鞋子足够穿,千万不要为她花钱买新的。2019年9月,我到蒙古国访问时,心想,老人不能寒脚,蒙古羊毛制品质量好,便给母亲买了一双羊毛毡鞋。回到家,高兴地拿鞋给她试穿。哪知她不愿试穿,说有鞋穿,还连声责怪我花了冤枉钱。为了节省电费,白天,她不让开电灯;晚上,客厅里只让开一盏灯。看到侄女敞开水龙头直接放水洗菜、洗碗,她会说太费水,马上走过去制止。她自己洗漱、洗衣服,都是拧开水龙头接一盆水洗。一条毛巾用了几年,起了线坨坨也舍不得换。一张纸巾用了一面之后,还要折过来,再用另外一面。她还总抱怨海口菜价高,并与我算账,觉得在海口的各项开销都比老家多,增加了我的经济负担,甚至想还是回老家。
母亲自幼就经历了“没钱”过日子的太多艰难。不到十岁时,外公去世,她与外婆住在一间透风漏雨的茅草屋里相依为命。两个哥哥早已单立门户,勉强养家糊口,仅能时断时续地给外婆一点谷子作赡养。母亲同外婆的日子过得十分紧巴,找邻居借米下锅是常有的事。外婆因裹着小脚,下不了田地,母亲小小年纪就会喂猪养鸡、翻土种菜、纺纱染布,操持各种家务。她还起早贪黑给别人家插秧、割稻,挣一点工钱,贴补家用。现在回忆起来,母亲还感叹:“那个日子是‘南风打南浪,北风打北浪’(湖南省安乡县俗话,意为非常穷),我和你外婆真是遭孽!”母亲二十岁时与父亲结婚,单独立户时没有分得什么家产,倒是承接了一大堆债务。两人一起勤耕苦做,尽可能多收入一点;省吃俭用,把需求降到最低,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老家上年纪的人现在与我聊起往事,总唏嘘道:“你母亲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出了名的呢!”
我自记事起,就知道母亲是一位严管家,家里任何支出都由她说了算,父亲连抽什么烟喝什么酒,尽管已是最廉价的,也都要向母亲请示,更不用说涉及我们几个孩子的开销了。1978年,我考上大学,心想不能太土气,便给母亲提出买一个装行李的新皮箱。但母亲没有同意,而是请木工用旧家具材料做了一个又笨又糙的角箱。我觉得母亲实在太抠门了,闹了点情绪,有好几天闷闷不乐。离开家时,母亲拉着我的手,一双含泪的眼透着不舍和为难,许久才轻声说:“伢儿,我和你父亲当然很想让你体面一点到学校,但买了皮箱家里就拿不出钱让你买书了。角箱同皮箱一样能装东西。能省点就省点,用省出来的钱买书吧。”说完,她转头去擦拭泪花。大学期间,全班同学中就我一个人使用这种旧木材做的角箱,看着它,我会常常想起母亲送我时的目光,提醒自己来自农村、来自条件艰苦的家庭,父母亲正在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我上大学。后来,我曾写了一首《妈妈的目光我难忘》的歌,其中有几句是:“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眼前都闪耀妈妈的目光。在妈妈的目光里跋涉,山不再高水不再长……无论我身处什么时候,心上都流淌妈妈的目光。在妈妈的目光里打拼,无助时增添了力量。”1985年,我到北京工作,虽然派不上用场了,但几次搬家,我依然带着这个角箱,告诫自己像母亲那样节俭,也让女儿懂得节俭的道理。现在,它已成为我们家的一件“传家宝”。
每天上午九时,母亲就会像一个小学生,端端正正坐在桌子前写字。她小时候只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公学(政府出学费),认识不了几个字,没有断句作文的能力,人口普查时被归在“文盲”一列。严格意义上讲,她这种写字并不是真正的写字,而是“照葫芦画瓢”,属于“画字”。母亲会把侄女在当天报纸上挑出的大号字作“底字”,一笔一画地“画”在笔记本上,每行七个字,共八排。母亲“画字”时凝神聚气,心无他物,旁边有人说话,或者电话响了,仿佛没发生一样。由于她对“底字”大多不认识,既不知读音也不懂意思,所以得看一眼,才能动一笔,“画”完一个笔画较多的字,可能需要一两分钟,一页纸五十六个字“画”下来,需四十多分钟。她“画字”多“发倒笔”,笔画顺序大都不对,偶尔还有错字,但“画”出来的字横平竖直,整整齐齐,与“底字”模样基本一致。
母亲“画字”,让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看她临画的场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农家大都是自己请木工做床,最简单的是平头床,稍为复杂的称之为“一条街”,也就是架子床。这种床四根床腿上竖有固定的木架子,用于挂蚊帐,床架子的正面上方置有三个约5寸×9寸大小的画框,玻璃下镶嵌花鸟鱼虫之类的装饰画。那一年,我们家做了一张“一条街”的床,所用木材都来自父亲种的树。装饰画怎么办呢?母亲就从别人家借来几张旧的花鸟画,自己抽空用彩色蜡笔临摹。两只正在耳语的喜鹊,一朵盛开的牡丹花,临摹得很像,用透明薄膜蒙上,嵌入画框后,虽略显粗糙,但从远处看与买的画也差不了多少。我在旁边瞪大眼睛静静地看着,感到十分惊讶。母亲的手就像是一根神奇无比的魔术棒,画啥像啥,可是她从来没有学过画画啊!母亲真是聪明,真有才艺,我对母亲充满了崇拜。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风霜催老了母亲的容颜和双手,但她仍然还是那么心灵手巧。
看到母亲“画字”这个场面,我也会想起她多次回忆,小时候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没有读什么书,一生吃了许多缺文化的苦头。此时此刻,她是不是在弥补當年读书少写字少的遗憾呢?前年,她曾经念过公学的母校举办一百周年校庆,请她这位最年长的校友寄语,她就说了一句:“后生们要珍惜现在,好好读书,长大成材。”
我每天会检查一下母亲的作业,进行一番点评,当然都是夸奖。有客人来家里,我还会炫一下母亲的“画字”书法作品。客人无不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九十几岁的老人还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真了不起!”这时,母亲总会带些腼腆地问:“真的吗?”看得出来,她很有成就感。
2020年6月25日,是我一生中最难过也最自责的一天。这天母亲感冒引起肺炎,住进了医院。以前多次听专家说,肺炎是八十岁以上高龄老人的第一杀手。母亲来海口后,我一直小心翼翼,差不多每天给她讲,提防感冒。看着已经九十五岁、躺在病床上咳嗽不已、双腿浮肿的母亲,我如万箭穿心一般痛苦。参加会诊时,听到医生说母亲属于超高龄病人,风险比较大,我更是揪心不已,哽咽着请医生竭尽全力。母亲住院的第三个晚上,我悬着心出差在外,接到哥哥电话说“刚才母亲被痰噎住,差点不行了”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出差回来赶到医院,我守在母亲病床前,摸着她还在发烫的前额,一连串自责袭来:为什么没有对母亲那几天走路和吃饭速度慢了的异常现象引起足够的警觉?为什么简单相信她“没什么不舒服”的回答?为什么迁就她“过节不治病不吃药”的迷信观念(当天是端午节)而不是检查后当即住院治疗?母亲这次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懊悔将会伴随我的余生。多亏医生们医术高超,诊断准确,用药对症,仅四天时间就控制了炎症,七天后体温逐渐降至正常,二十天后母亲出院。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母亲与病魔抗争的顽强。医生让她咳出痰来送检,那是一个让五脏六腑震动的过程,她使劲配合。B超显示,她的胸腔里有近1500毫升的积液,需要尽快抽掉,她欣然接受。在住院头几天,医生使用了多种药物,每天输液长达六个小时,她强忍不适。为了补充营养,提高机能,哪怕胃口不好,她也坚持喝完鸡汤,吃一小碗稀饭。医生说:“这么高龄能这么快治愈,创造了奇迹!”
2021年9月的一个周日早上,侄女使劲敲我的房门,带着哭腔:“叔叔,不好了,奶奶跌倒了!”听到这喊声,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一直提防的母亲跌倒的事还是发生了。跌倒是高龄老人的另一个杀手。我奶奶九十三岁时还能生活自理,就是因为跌倒骨折,瘫痪在床,半年后去世的。为此,我常用奶奶的事提醒母亲引以为戒。但母亲还是摔了……我急忙冲到客厅,只见母亲仰面倒在地板上,脸色苍白,喘着粗气。平时遇事冷静的我此时也是慌了手脚,只敢半跪着,抱着母亲的头,声音颤抖地说:“妈,我们赶紧去医院。”母亲摇了摇头:“算了吧,送我回老家。不给你添麻烦了。”那会儿,她也可能认为过不了跌倒这一关,想落叶归根了。我强忍住眼泪,说:“妈,先别想那么多。到医院看看究竟摔到哪里,好吗?”医生给母亲做CT、核磁共振检查时,我在医院走廊上紧张地转来转去,觉得空气都是凝固的,深深的自责吞噬着我:怎么没有照顾好母亲?怎么还让她自己单独行动?怎么会这么大意?……大约一个小时后,医生走出来说:“左侧上肢肩膀、下肢大腿部韧带和膝关节有严重损伤,但没有骨折。”哎呀,谢天谢地!我紧紧握着医生的手,激动得一时语塞。母亲知道这个检查结果后也松了口气。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母亲虽然万幸没有骨折,但已属超高龄,且拉伤得不轻,因此,康复之路也颇为艰难。她先是忍着疼痛练习在床上侧身、坐立,然后练习下床站立,四天后开始借助助行器移动脚步,两周后到院里步行,一个月后就可独立行走几十米。医生说母亲又创造了奇迹!
母亲一生中遭遇过多次磨难,陷入过多次困境,但她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沟沟坎坎总能过去,以坚韧和要强支撑着这个家。婚后第二年,她顺心如意生育了一个男孩,也就是我从未见面的大哥。家里首添一个男丁是天大的喜事!大哥被视为全家珍宝,但长到一岁多时得了一场不知病因的急病,村里乡里那时也都没有医生,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紧紧抱着身体渐渐变冷的孩子,母亲撕心裂肺,眼泪都已哭干。第二个孩子是女孩,也就是我的大姐,已经长到五岁,十分聪明可爱,但不幸患上白喉,几天前还活蹦乱跳的宝贝女儿,就在眼皮底下慢慢地停止了呼吸,她哭肿了眼,痛不欲生。至今我都难以想象,一男一女头两个孩子的夭折,对年轻的母亲是多么沉重的打击,让她承受了何等的伤痛,她是怎样挺过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曾经进行过一场“四清运动”,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在我老家一带尤其过火。父亲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一个中国最基层的泥腿子“芝麻官”,在“四清”中也成了重点对象,隔三岔五被叫去开会挨批检讨,参加“集训”。母亲想不通,父亲那么忠厚老实,从早到晚忙碌生产队的事,从不占公家一丁点便宜,结果还挨整。她坚信父亲是清白的,多次在路上把下村来检查的各级领导拦下来申诉。最终,父亲勉强过了关,没有打成什么“坏分子”,但生产队队长一职被免掉了。父亲觉得十分委屈,母亲安慰道:“你当这几年队长,对得住各位乡亲,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当也罢,俺俩一起好好拉扯孩子,把自家日子过好!”恰在这时,父亲患上了急性胸膜炎,病情危急,这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几乎没有生的希望。但母亲毅然决然,连夜凑钱找人将父亲抬到不通公路且在十六公里之外的县医院抢救。医生说:“再晚来一个小时,人就没了。”为给父亲虚弱的身体补充营养,她冒着刺骨的寒冷,下到湖里摸鱼,凌晨熬成鱼汤,又马不停蹄赶到医院,这时太阳刚露脸,鱼汤还冒着热气。父亲终于捡回了一条命。第二年,厄运再次袭来,父亲又感染了急性肝炎。母亲又果敢地把父亲送进县医院治疗,几乎倾家荡产。她又一次把父亲从阎王殿那里拉了回来。这些往事,父亲在世时不知给我们四个子女深情地述说过多少遍。
汪曾祺曾写道:“人总是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母亲正是这样活着的。在痛失大哥大姐时,在父亲挨整又患重病时,在自己九十五岁和九十六岁超高龄患肺炎和跌伤时……她调动了自己全部的能量,“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应对各种磨难,活出勃勃的生机与希望,使极普通的人生让我们后辈景仰并有所感悟、有所效仿,磨砺心性,从而走向坚硬和强大。
书上说,为了健康,老年人要少吃糖、少吃肥肉,不吃糯米之类难消化的食品。但母亲恰恰喜欢吃甜食,菜里要放点糖;喜歡吃肥肉,每餐两三块湖南红烧肉;还喜欢吃糯米做的食品,早餐经常是一碗汤圆,或者一个糍粑。不过这些嗜好一点也没影响母亲的健康。除血压高需服药控制外,母亲其他指标都正常,医生听诊后也说,她的心脏跳动十分有力,像年轻人一样。她的长寿且健康的秘诀是什么呢?我想,除了乐观、豁达的心态外,恐怕与她坚持走路有很大关系。
小区院子里有一条环形道路,四百二十多米长。外侧,一排高高的椰树撑着洋溢清香的绿伞,里侧,几行叶片茂密的榕树、非洲楝洒下浓浓的荫凉。小鸟在树枝上欢快地鸣叫,似乎在传递什么喜讯,松鼠在草丛里奔来跑去,时而展示自己是爬树高手。几乎每天上午十时和下午四时,母亲都会准时下楼,沿环道走四圈,用时约五十分钟。走完路后,还会在道边的条凳上坐半个多小时,让太阳晒晒背。母亲走路时,会戴一顶黑色的太阳帽,架一副窄边的太阳镜,穿一双软底的胶鞋。她的步子不算大,体态平稳。邻居们见到她会热情地打招呼,她则马上招手,大声示谢。我只要有时间,就会陪她走路,同她聊天,聊她和父亲的从前,聊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小时候的事,有时聊天的内容可能重复多次,但丝毫不影响我们边聊天边走路的兴致。我还会经常用手机录她走路的视频,发给在湖南老家的姐姐、哥哥、妹妹和在外地的妻子、女儿,报告母亲的身体状态,尤其是在母亲经历这两次大病后,让他们及时了解母亲康复的情况,以免担忧。有时,我也会让她在视频上看看自己走路的样子。这时,她总会“扑哧”笑几声,对自己表示满意。
从前走路是为了生计,现在走路是为了健康。从农村走到城市,走路成了母亲的习惯,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渴望走路,享受走路,特别感叹海口的空气新鲜,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相伴,走路舒服。2020年住院期间,她举着氧气袋在病房廊道上走;出院后,就迫不及待要在小区里走。只要不刮风下雨,小区环道上必有母亲走路的身影。2021年9月后,担心她走路时再次跌倒,我想搀扶她,她毫不迟疑地推开我,说她能自己走。
看着母亲走路的背影,回忆总会像潮水一般涌来。幼时被她牵着走路,稍大一点后,跟着她走路,记得十来岁时曾“赶脚”,随母亲走到十六公里外的县城吃过一碗光头汤面。成年后陪她走路,在武汉大学校园里、在北京街道上、在贵阳宿舍小区……走着走着,母亲的背渐渐驼了,腰渐渐弯了,速度越来越慢了,里程越来越短了,但是母亲走路时的坚定和自信一点也没有变化。
母亲曾对我说:“你外公不到四十就去世了,外婆也不过七十。我没有想到活到现在这个年纪,心满意足了。”我说:“外公生活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旧时代,外婆又遭遇了天灾加人祸造成的饥饿年代,而您老人家所处的这个时代,病有所医,衣食无忧,国泰民安!您就安心养老吧。您坚持走路,我陪您,走到一百岁,再走到一百一十岁、一百二十岁,好好享受五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吧。”母亲脸上扬着笑,眼里泛起明亮……
清风,公务员,现居海口。已发表文章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