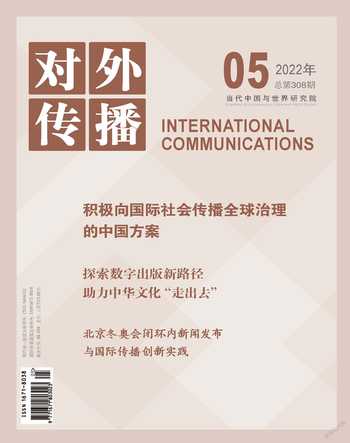中国扶贫故事对外精准传播的逻辑向度和策略进路
2022-06-09陈秋云刘爱章
陈秋云 刘爱章
【内容提要】贫困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具有世界意义。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做到对外精准传播,对于建构话语权、树立政党和国家良好形象、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重大。目前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在叙事逻辑、话语逻辑、对象逻辑和反馈逻辑方面存在不足,要善用共情策略,以小人物、小故事彰显大道理、大逻辑;要积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融通媒体的对外传播大格局;要建立科学评估和反馈体系,在传播中精进、在精进中传播。
【关键词】中国扶贫故事 国际传播 精准传播 文化符号
贫困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只有自身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事物,才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①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人类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对外传播始终伴随着中国扶贫脱贫的发展历程,而对外精准传播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做好新时代中国扶贫故事对外精准传播,中国有底气、有成绩,也面临挑战和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设定目标体系,健全策略体系,为对外精准传播的体系化建构积累经验,助力中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一、问题的识别和分析
(一)叙事逻辑:破除宏大叙事惯性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的特质包括“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②他认为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宏大叙事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细小叙事。其观点有待商榷,但也表明了宏大叙事在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互联网时代正遭遇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主流媒体惯于采用宏大叙事来构建主流价值观,在中国扶贫故事的选题上也常与“英雄人物”“大场面”“国家制度”有关。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以宏大叙事为主导的传播模式面临困境。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壮举,拥有世界上最精彩纷呈的扶贫脱贫故事。在对外传播中既要从中国扶贫的历史出发展开叙事,做到史论结合,同时也要避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惯性,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用细微叙事讲活中国扶贫故事。需要注意的是,“宏大叙事”和“细微叙事”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要努力实现两种叙事的平衡,做到“大题小做”。如上海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把脱贫攻坚主题和鲜活的百姓故事结合,赢得了外国观众的认同。
(二)話语逻辑:打破内宣逻辑主导对外传播程式
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认为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③在国际舆论场,西方话语仍然占据强势地位。“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窘境仍然存在。对外传播中国扶贫故事需厘清内宣和外宣的关系。内宣的对象是国内民众,外宣则主要是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由于宣传工作的任务、对象、语言、文化等存在差异,因此,必须打破以内宣的逻辑主导外宣的困境,避免导致资源浪费、传播不精准,从而丧失对国际共同议题的关联和搭载能力。
(三)对象逻辑:避免目标群体瞄不准
对于任何一种形态的传播,特别是国际传播来说,受众和效果应当成为传播启动的出发点。④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需要对海外受众进行解剖麻雀式的精准分析。以下从语言、文化和翻译三个方面择要论述。
其一,传播对象国的语言问题。“传播未动,语言先行。语言不通,一切皆空”。全球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极其丰富的语言。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面对的语言问题突出。如“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语言、使用人口超过400万的语言、各国的语言及地方上的大语种,整合起来大约有200种。⑤如能用他们的语言进行传播,就能取得比英语传播更好的效果。
其二,传播对象国的文化问题。对外传播是跨语言的传播,更是跨文化的传播。因此,需要深入到对象国文化圈,用我方的价值观去影响传播对象。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要做到“一国一策”,而不是“广撒胡椒面”。学术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硕果累累,但对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研究偏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讨论也集中于经贸领域,文化领域涉及较少。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面临文化盲区。
其三,对翻译话语的分析。翻译是连接传播主体和海外受众的桥梁,精准的翻译能极大地提升传播效果。中国扶贫故事极具中国特色,在翻译时会面临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扰。目前仍然存在翻译质量不高的问题,对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乱译、硬译的例子不少。这就需要译者对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及其背后的文化都有比较深入的把握,始终做到心中有受众,瞄准目标群体,使传播对象能看懂、能接受、能共情,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
(四)反馈逻辑:评估体系匮乏
完整的传播链条应该包括反馈环节。通过反馈,可以测量传播效果,为再次传播提供参考。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还未建立科学的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国内外对国际传播效果的评估关注较少,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有学者指出,构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⑥建立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评估体系更需要立足中国国情,用客观事实和相关理论分析,以实现对外传播的效果优化。
二、目标体系的设定
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需要精准定位目标,即争夺国家话语权、构建良好的政党和国家形象以及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三个目标相辅相成、逐步递进。
(一)国家话语权争夺
由于历史和现实双重因素的影响,西方中心论在国际舆论场仍然很有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所构建的强大的话语体系面前,所拥有的话语权偏弱。中国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方案,也为对外传播提供了争夺国家话语权的契机。创造美好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扶贫故事的对外传播可帮助中国提升话语权。需要认真提炼中国扶贫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同时用外国受众听得懂、能接受、易传播的语言来表达。E17C402C-20FD-4CC3-9473-A3F60C0F9D77
(二)政党和国家形象传播
其一,传播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是党的内在本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对党的建设和事业进步与否、合理与否、成功与否、水平高低与否的一种测度,它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复杂性和价值性。⑦中国脱贫攻坚成功的奥秘在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要利用好中国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客观真实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如何团结带领14亿中国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消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污蔑甚至攻击,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
其二,传播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开展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2020)显示,中国全球影响力持续增强。但需警惕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例如把中国扶贫与所谓“人权”联系起来,将中国扶贫置于负面语境。
政党形象和国家形象具有内在一致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是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需要伟大、光荣、正确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就此而言,离开中国共产党谈中国和离开中国谈中国共产党都是不成立的。中国扶贫故事的对外精准传播的重要目标,即建构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政党形象,建构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
(三)传播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具有世界意义。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制约着亚非拉等一些国家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贫困人口更是急剧增加。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极端贫困率自1998年出现了首次上升。⑧不仅如此,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也受贫困问题的困扰。“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⑨在此意义上,中国扶贫故事对外传播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减贫提供经验借鉴。
其二,构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贫困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各国独自发展也不是命运共同体。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说明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不等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的发展既造福中国人民,也为世界各国人民带去了福祉,展现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优越性。
三、策略的实践进路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立足叙事逻辑、话语逻辑、对象逻辑和反馈逻辑的改进,重点实施一系列战略策略,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内容,是做到对外精准传播的实践路径。
(一)叙事话语与共情手段:小人物、小故事彰显大道理、大逻辑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各种关心、兴趣、猜测和疑问并存,中国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主动地讲述中国的故事。⑩讲好中国扶贫故事,做到对外精准传播要善于叙事和学会共情。
其一,讲好脱贫人口的故事。2012年以来,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故事题材。从个人的角度去讲故事,可以实现共情,让受众入脑入心。中英合拍的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就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打动了无数外国受众。实践证明,往往是那些来自民间的、具体的、渐进式的交流效果较好,而自上而下的、抽象的、突兀式的宣传,效果常常大打折扣。11
其二,讲好帮扶群体的故事。2021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1981名同志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对1501个集体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千千万万个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志愿者等都参与其中。也有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友人对中国的减贫事业表达过关心,提供过帮助。要充分挖掘他们的事迹材料,用摆事实、讲道理、讲情感的方式,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把基层的扶贫故事讲述出来,运用同理心进行换位思考。这样既能讲好我们的故事,又能展示中国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
其三,创造可供广泛传播的文化符号。文化符号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20多年前,被称为“菌草之父”的林占熺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传授菌草技术,从此菌草成为了连接中国和外国百姓的“幸福草”。多年来,菌草在100多个国家推广,给当地创造了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使不少当地老百姓摆脱了贫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位“菌草之父”便可作为文化符号进行传播。
(二)构建对外传播大格局
要构建对外传播大格局,优化扶贫故事对外传播效果。对外传播大格局应是政府主导,媒体、企业和个人多主体参与构建的传播体系。
其一,政府层面。政府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权力机构,在对外传播過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从2003年到2016年就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情况共进行过8次独立调查,包括中央、省、县和乡镇政府,受访人数达31000多人。结果显示,多年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在90%以上,而且认为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更有效率。12政府拥有协调各方资源的能力、公信力,应主导统筹构建对外传播大格局。
其二,媒体层面。长期以来,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美联社、路透社、《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在全球传播体系中居于霸权地位。我国对外传播要突破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利用好国家梯队的媒体和民间媒体,利用好新兴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共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同时,可以“借船出海”,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如2019年由中美团队历时两年联合拍摄制作的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主要城市播出,引起了外国观众的高度关注,使更多观众看到了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
其三,企业层面。企业是中国对外传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世界第一,为当地缴纳税费445亿美元,拉动就业超过200万人,为东道国乃至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企业为对外传播对象国带来巨大的投资,是构建中国对外传播大格局中的一张靓丽名片。企业在对外传播活动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传播,讲好企业的扶贫故事。E17C402C-20FD-4CC3-9473-A3F60C0F9D77
其四,个人层面。个人也是对外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互联网时代,个人的传播力量不容小觑。要充分挖掘具有对外传播影响力的个人来讲好中国扶贫故事。中国的外国人是中国扶贫故事对外精准传播的一支新生力量,尝试以视频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脱贫攻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如《中国日报》高级记者聂子瑞(Erik Nilsson)来中国十余年间,见证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的著作《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三)科学评估与反馈:在传播中精进、在精进中传播
建立科学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是加强对外传播能力的必要步骤。可以说,没有科学的评估和反馈,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
第一,建立评估体系。在评估体系中可以分设不同层级的评价指标,包括传播内容、传播影响等。在每个层级再设具体的分项指标,如传播内容可以设内容竞争力和生产力,传播影响可设受众接触、受众态度和受众行为等。在建立评估体系时可参考国际上关于国际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设置方法及其效果评价,建立规范、易操作、受认可的评估和反馈机制。
第二,分类进行评估。由于对外传播的受众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有必要建立不同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语种、不同媒体、不同受众采取差异化的评估体系。如亚洲各国虽在有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在历史、政治、文化、民族、语言等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建立“一国一策”的评估和反馈机制才更具说服力。
第三,委托第三方开展传播效果评估。对外传播效果评估和反馈是一个规模大、范围广和主体多元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专业的评估机构来完成。需要注意的是,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保证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反映扶贫故事对外传播的效果,以便在传播中不断优化,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传播。
陈秋云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爱章系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①侯惠勤:《试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3页。
②王岳川、尚水:《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③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求是》2009年第9期,第43页。
④程曼丽:《中国的对外传播体系及其补充机制》,《对外传播》2009年第12期,第12页。
⑤杨宇明:《高峰之路:提升语言能力 助力国家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2月21日,第20版。
⑥刘燕南、刘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构:框架、方法与问题》,《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第9页。
⑦高晓林、谈思嘉:《深化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2期,第48页。
⑧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1, United Nations,https://www. un.org/en/desa/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dgs,July 6,2021.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7页。
⑩黄友义:《讲述好中国的故事》,《对外传播》2014年第1期,第27頁。
11徐占忱:《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困难与破解之策》,《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第24页。
12Edward Cunningham, Tony Saich & Jesse Turiel, “Understanding CCP Resilience: Surveying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im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July 2020,1-4,Harvard 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https://ash.harvard.edu/publications/understanding-ccp-resilience-surveyingchinese-public-opinion-through-time,July 4,2020.
责编:霍瑶E17C402C-20FD-4CC3-9473-A3F60C0F9D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