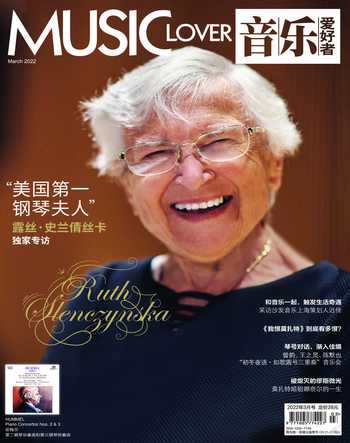“圆桌派”:寻找二十一世纪之声
2022-05-31朱则彦
朱则彦
2021年11月的上海,暖意渐退,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叶还未凋谢,一场名为“寻找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声音”的“圆桌派”活动在上海音乐学院如期举办。五位学者在这里进行思维的碰撞,一场与音乐有关的“圆桌派”对谈会由此展开。
“我们”是谁?何谓“我们”?
青年琵琶演奏家汤晓风时常演奏一些当代音乐作品,对他而言,这些作品中汇聚的大量新奇的音响、颠覆性的演奏法以及多元化的音乐风格都在吸引他拨动琴弦。结合自身的演奏体悟他指出:“若想探索二十一世纪的声音,演奏者不应只是关切技术层面问题与技巧练习,更需要透过技术,思考艺术背后的文化指向。”
诡谲、奇幻、飘逸、聒噪.....的二十一世纪之声在轻轻拨动演奏家心弦的同时,却也悄无声息地扰乱了创作者的思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李霓霞并不似汤晓风这般欣喜,她从创作的角度切入对谈,认为前人优秀的作品固然值得反复聆听、学习,但这些都不足以建构属于自己的音响世界,创作者所追寻的二十一世纪之声绝不是晦涩技法的简单堆砌。
一系列有趣的观点即刻让对谈会热闹非凡,洪丁副教授也随即表达了自身的困惑:如何增加对音乐的热爱?如何平衡差异化的审美标准?如何与当代音乐“和解”?在层层追问中终极问题——我们如何与音乐建立联系——逐渐浮出水面。那么,“我们”究竟是谁?仅仅局限于自己吗?

显然,答案不是唯一的。梁晴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一词蕴含多重含义,包含“小我”“中国人的我”“国际性的我”等。在这条道路上,许多作曲家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正如周文中、刘德海、朱践耳三位作曲家,他们逐步成为“中国人的我”,证明了中国人喜欢的作品属于中国。而瓦雷兹作为周文中的老师,教会了周文中应该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包容,并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坐标”。这已然不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我”,这个“我”更加深入,更独一无二,更不可替代。
此前,对谈会拟定的题目是“寻找属于我们的二十一世纪声音”,现在则删除了“属于”二字。洪丁副教授就此延伸提到:“音乐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声称拥有对一种声音的所有权?”简短的发问让大家再度陷入了深思。
二十一世纪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呢?不可否认,它是针对当下而言的。李霓霞最近创作的《百年瑰梦》(为唢呐与民族管弦乐队而作)就隶属于这一范畴。作品希望通过唢呐的音色质感传递乐器自身独特的声音表现力,以我们极为熟悉的“音乐、音色、素材”在不同音乐阶段的出现、消失、重叠、组合与分离,来表现乐器的角色功能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因此她设计了不同的樂器音色与各种音色的布局,明确唢呐的口部技巧与手部技巧,以此惟妙惟肖地刻画中国传统戏曲的神韵。开篇用唢呐模仿昆曲中的闺门旦(小旦),之后又采用口哨模仿韵白。“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这是邹彦教授听完作品后的第一感受。尽管这部作品可能不是那么“现代”,但却是经过现代音乐洗礼之后的又一次“回归”。作品中既有对于传统的认知,又有对于现代的理解,这与李霓霞长期学习竹笛演奏,再转学作曲专业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求新、求变的时代,创作与演奏均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代音乐创作虽丰富多彩,但只有深谙传统器乐演奏规律、对传承传统文化进行过思辨的作曲家,才能创作出既符合当下时代精神,又符合艺术审美规律的中国作品,而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公认的好作品。例如已故的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的当代琵琶音乐创作,也与他自身的学习经历紧密联系。




二十一世纪的声音包罗万象,所以它绝不仅仅是指作曲、音乐作品等,也包括音乐演奏、音乐理论研究。如何能够从音乐中感受到快乐、幸福,都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或许,当下的我们不仅没有自己的声音,甚至对于这种声音的存在之处都不甚清楚。这是洪丁副教授抛出的一个掷地有声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对声音充满未知和迷茫,是因为与过去各个时期的音乐相比,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是一个问号。梁晴教授觉得,正是因为它可以采用各种手段、风格、形式,打破一些概念、禁锢、羁绊、类别的边界,消解我们面对新与旧、传统与创新、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的刻板印象,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才能从有形逐渐趋向无形,这一发展趋势更加强调了蕴含于当代音乐中的精神性。
“寻找”是需要主体的,而我们正是这一语境中的审美主体。“寻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声音或音乐,而是找到自身与音乐之间的关系。
那么,处于二十一世纪的“寻找”应当如何进行呢?汤晓风副教授指出“寻找”应基于历史文脉,唯有建立在传统之上的当代音乐创作才能保持生命活力。梁晴教授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于感性的自觉,在这一层面上更多的是尝试;第二阶段需要不断的质疑、反思与理性的分析,但是要有目标地追求;第三阶段的核心是创造,这种创造需要个人的理解,毕竟只有自己找到的才是独一无二的坐标。她借用佛教中的“七辩八还”描述心中对“寻找”的理解:还不掉的即真、个性,它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这种“寻找”不再依靠民间曲调、作曲技术、西方思路、标题或是其他。不是拾人牙慧,也绝不重复自己。甚至可能不因它起、不凭借音乐进行表达……

寻找从未停止,也绝不会停止。对谈会临近结束时,邹彦教授指出:“我们过去在寻找,当下在寻找,未来依然要寻找。但在这个看似永无尽头的过程中,永恒不变且独一无二的坐标,是我们的内心。”正如阿诺尔德·勋伯格所言:“也许,在新的一天里,音乐中出现的阳光正是我乐于为这个世界所奉献的。”音乐需要我们的呵护。尽管直到此刻,我们仍无法对二十一世纪音乐的未来走向妄下断言,也无法给予在漫漫长路上摸索、前行、寻找的人们一个明确的终点,但我们始终应该对音乐抱有热爱和敬畏之心。因为终有一天,你会看见那缕阳光照亮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会在充满未知和一切可能的世界里真正找到自己的信仰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