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父母“双捐”救“双女”:一人一颗肾那爱的潮汐
2022-05-30戴志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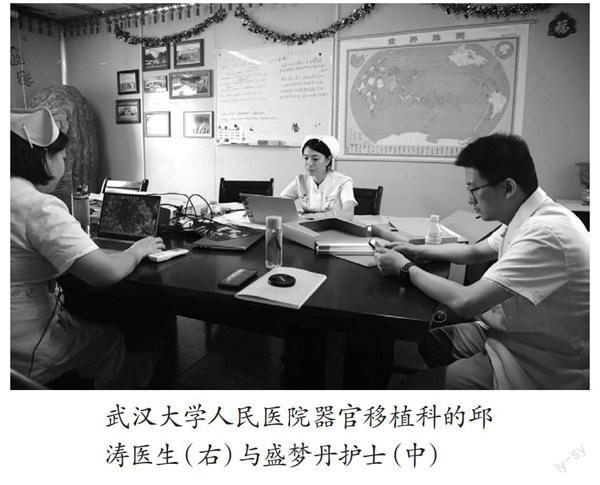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胡艳明多么希望回到2021年7月27日以前啊。
那時的她,还是江西省瑞金市一家酒店的普通员工,丈夫刘华平则开着电动三轮车为人送货。两个正值青春的双胞胎女儿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平凡的日子,简单而充实,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命运却偏偏在此时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吻”——两个女儿同时被确诊为尿毒症,生命告急,必须换肾。很快,夫妻俩便不约而同地做出决定:由他们自己给女儿捐肾,一人救一个!因为,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
生命告急:花季双胞胎女儿同患绝症
2021年7月27日,本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那天,在瑞景酒店上班的胡艳明下班后,像往常一样回到了家中,准备做饭。
17岁的小女儿晓怡皱着眉头,说:“脚痛。”“八成是生长痛吧?你们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胡艳明笑着打趣道,不以为意。谁知,晓怡委屈得眼泪汪汪:“妈妈,真的很痛,痛得受不了……”与此同时,大女儿晓茹也喊身体不舒服,头晕,头疼,咳嗽,浑身无力。晓茹这种症状已持续一个月了。一家人都当是普通感冒,给她买了点感冒药在服用。但晓怡的脚痛是怎么回事?晓怡说:“其实,我已痛了个把月,此前一直忍着,今天痛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胡艳明将手头的家务事放下,当天晚上,就带着晓怡前往附近的仁济医院就诊。
看到晓怡的常规检查报告后,医生告诉胡艳明:“孩子的血肌酐有点超标。”听说大女儿晓茹最近也一直不舒服后,医生建议她第二天早上带着两个女儿再来医院,进行更为细致全面的检查。
次日早晨,胡艳明带着两个女儿再次来到了医院。此时的她尚未意识到,病魔已向两个女儿张开血盆大口,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不期而至。
胡艳明甚至还计划着,待两个孩子检查完后,由医生开点药回家服用,她则继续回酒店打卡签到。毕竟,一家四口要吃饭,她和丈夫要挣钱。
孩子们的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看着报告单,医生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姐妹俩的血肌酐严重超标,正常上限值在110μmol/L左右,她们的高达560μmol/L左右。”医生说,“已经是慢性肾脏病5期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尿毒症。”
尿毒症?胡艳明感觉天旋地转,大脑出现了瞬时的空白。会不会是弄错了?医院八成是弄错了!
完全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结果的胡艳明,带着两个孩子,先后在瑞金人民医院、赣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了复查。不幸的是,两家医院的诊断结果与仁济医院完全一致。
来不及细想,胡艳明向酒店请了长假。8月2日,她和丈夫带上两个女儿和家中的全部积蓄前往广东省。她听在广州市打拼的同乡介绍,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的实力很强。只要能救孩子,别说去广州,让胡艳明上刀山下火海,她也义无反顾。
当天下午,他们就赶到了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室里,姐妹俩再次做了检查后,医生建议她们住院治疗,可短时间内没有床位。
病情汹汹,姐妹俩等不起啊!在医院旁边租房居住的她们,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头痛欲裂,吃什么吐什么;女儿们晚上疼痛难忍发出来的哀号,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悲切……
8月5日,等了3天的一家四口终于在住院部找到了床位。“尽快透析排毒,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医生的话一字一句敲打在胡艳明的心口上。
很快,晓茹和晓怡姐妹俩被送进了手术室,接受了腹膜透析置管手术。但因为姐妹俩体内的毒素积聚得太多太多,她们的身体犹如遭遇烈火灼烧的屋子,几只灭火器,只能延缓燃烧,却根本止不住狰狞的大火。
那段时间,胡艳明和丈夫每天除了帮女儿办各种手续之外,就是服侍她们打针、吃药、透析。孩子们睡不着,胡艳明也难以入眠。实在困极了,就趴在女儿病床边打个盹,或者坐在椅子上迷糊片刻。
精神的紧张与身体的疲惫让胡艳明暂时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她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连轴运转着,浑然不知身体和精神都已严重透支。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约20天。直到有一天,两个孩子痛苦的呻吟声渐渐地变小了、变短了,胡艳明才获得了喘息的时间。
那天,她难得地睡了一个囫囵觉。醒来后,医生对她说:“孩子们的病情控制住了,同时患病的原因也彻底查清楚了,是NPHP1基因突变,不过,要想根治,换肾才是最好的选择!”他告诉胡艳明,最重要的是找到两个能与姐妹俩匹配的肾源;另外,还得准备100多万元的医疗费。
胡艳明知道,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任何一个,于他们家而言,都是座难以逾越的大山。但为了女儿,再高的山,再多的坎,她也要去攀登,去跨越。
有人建议胡艳明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去,他们在肾移植方面的技术与经验,领先全国。但由于当时武汉有疫情,加上手术费用尚需时间筹集,一家人先回到了江西老家,晓茹和晓怡一直靠腹膜透析艰难维系着生命。
2021年12月,晓茹和晓怡的腹膜透析已渐渐难以为继,生命之火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加上武汉已经连续三四个月零风险,17日,一家四口打点行装,从瑞金来到了武汉。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姐妹俩能重启生命之门吗?
一人一颗:全国首例父母双双捐肾救女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的主任办公室里,周江桥教授告诉胡艳明,NPHP1又叫肾单位肾痨,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囊性肾脏病。由于肾衰竭前往往无明显临床表现,早期难以及时确诊,很多患者就医时已发展为慢性肾衰竭。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此前十几年的时间里,姐妹俩的身体一直好好的,一旦发病,就如此凶险。
肾源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胡艳明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完成了器官移植登记后,就开始和女儿们一起等待肾移植的机会。
因为医疗费还有巨大缺口,胡艳明和刘华平商量后,由她留在武汉照顾女儿,他则回江西老家继续挣钱。
等待肾源的过程是痛苦的。自从腹腔内置入透析管后,姐妹俩的身上就多了一个“零件”,做什么事都不方便,尤其是洗澡,更是成为奢望。实在需要洗浴的时候,只能由妈妈胡艳明用温水将毛巾浸湿,拧干后,再轻轻地给她们擦身体。
有几天,晓怡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头痛持续不断。器官移植科迅速为晓怡联系肾内科的专家诊治。经检查,晓怡的腹膜透析效果不好,水分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潴留,晓怡出现了心衰、胸水的症状。肾内科的专家团队一方面通过穿刺手术,紧急清除胸腔内的积水,另一方面连夜调整透析方案,将腹膜透析变为插管血透。
一套优质治疗手段的“组合拳”下来,危及晓怡生命的警报终于暂时解除,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经此一险后,胡艳明和刘华平一刻也不想等了。听说亲属间能够进行活体器官移植,胡艳明和刘华平当即决定:“我们自己来给女儿捐肾,一人救一个!”
医院对一家四口进行配型检查。结果显示,胡艳明是B型血,一对女儿则是A型血。胡艳明给女儿捐肾,需要跨越血型不同这道难关。
多年前,跨血型视为肾脏移植的禁区。但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已经拥有实施跨血型肾移植的成熟技术,完全可以开展ABO血型不相容亲属肾移植。
鉴于晓怡的体内有针对母亲的群体反应性抗体,移植肾容易受到攻击,在专家的建议下,夫妻俩商定:胡艳明的肾捐给大女儿晓茹,而刘华平的肾则移植给小女儿晓怡。
因为胡艳明与大女儿的血型不同,在捐肾之前,晓茹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脱敏”处理,即通过血浆置换手段,清除体内的血型抗体,让受体内抗体滴度标准降到可以接受供体的范围内。
2022年4月19日,胡艳明与晓茹之间的肾移植手术如期进行。为胡艳明主刀的医生叫邱涛,一位年轻但临床经验丰富的副教授。邱涛像往常一样与胡艳明聊着天,问她每天都吃些什么,觉睡得香不香。那感觉,就像和邻家大兄弟唠嗑,胡艳明本来有点紧张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待胡艳明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当天下午3时许。刘华平和晓怡守在她的病床边,眼神里饱满关切。胡艳明第一句话就是:“晓茹呢?”刘华平告诉妻子:“晓茹下午1点才被推进手术室,现在还在手術室里,没有出来。”
胡艳明还想问什么,却感觉一阵阵恶心,哇的一声,吐了起来。从当天下午3点多开始,她持续吐了三四天。吐得昏天黑地、天旋地转。因为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到后来,她没有什么可吐的,只有水,淡黄的、黏糊糊的水。
与此同时,麻醉过后,漫天的疼痛也席卷而来。稍微动一动,身体就犹如被千万把钝刀凌迟。
晓茹在19号当下下午1点被推进手术室后,下午5时左右被推出来。由周江桥教授亲自主刀,将胡艳明的肾置入晓茹体内。
接受了移植肾的晓茹,被安置在专有病房里,除了医生和一名由医院指定的护工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此病房。
见胡艳明担心,周江桥和邱涛两位教授告诉她,她的肾在大女儿体内存活得很好,晓茹恢复得不错。闻此,胡艳明突然觉得,什么呕吐啊,疼痛啊,全都不值一提了。
向阳而活:至暗时刻那爱的潮汐
眼见妻子和大女儿手术效果良好,刘华平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一颗肾脏捐献给病情更重的小女儿,“我一天也不想多等!”刘华平说。
然而,懂事的晓怡,尽管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仍强打精神,劝说爸爸:“爸,我们再多等几天。妈妈和姐姐才做完手术,需要恢复。这些天,您家里和医院两头跑,我怕您的身体吃不消。妈妈和姐姐康复出院后,我再进病房。”
听着小棉袄贴心的话儿,刘华平将头扭向一边,使劲地咬了咬嘴唇。他不想让女儿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他是家里唯一的男人,是顶梁柱、主心骨。
在这个家里,他如果脆弱,谁还会坚强?
一周后,胡艳明强忍着刀口的伤痛,坚持出院了。丈夫连续多日医院和租住地两头跑,体力已严重透支。他不能垮,小女儿还等着他去救,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他!
胡艳明出院两周后,晓茹也出院了,恢复得不错。她甚至告诉爸爸妈妈:“我还要去考大学!”胡艳明和刘华平喜不自禁地说:“只要你和妹妹有这上进心,爸爸妈妈就一定支持你们。”
母女俩出院后,刘华平更加急着要给小女儿晓怡捐肾。器官移植科也开始着手研究父女间移植的手术方案。
一般情况下,在供体左右肾GFR(肾小球滤过率)相当的情况下,由于左肾静脉较长、手术方便获取,后续操作难度也较小,应当优先考虑移植左肾。但是,考虑到小女儿晓怡体重较轻,刘华平GFR较低的右肾就能够满足女儿生命的需求,同时更能保证供体者父亲后期的健康状况。周江桥教授带领移植团队决定避易就难,选取右肾进行移植。
6月21日,父女间的肾移植手术正式开始了。
当天上午11时,刘华平被推进了手术室。为他取肾的大夫仍是邱涛医生。
因为右肾静脉较短,大约只有左肾静脉的三分之一,邱医生首先在腹腔镜下获取了刘华平的右肾,接着又延长了原本较短的供体右肾静脉,有效降低了后续操作的难度。
下午1时许,晓怡也被推进了手术室。刀法娴熟的周江桥教授,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而有序的忙碌,成功地将刘华平的肾植入到了她的体内。
父母两颗鲜活的肾脏,就这样在一对双胞胎女儿的体内“安营扎寨”。它们带着父母的爱与温度,重燃了两个孩子险些熄灭的生命之火。
一家四口,一人一颗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创造了全球第二(此前仅英国有一例)、中国首例父母双双捐肾救子的医学奇迹。
父女间的手术结束后,医院和租住地两头跑的人,换成了胡艳明。此时的她,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刀口还在隐隐作痛。但这一切,于她而言,都是毛毛雨。因为,遭遇了狂风巨浪袭击的他们,人还在,家也在,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的呢?
胡艳明的厨艺水平高,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她尽量为一家人安排好膳食。
早上,胡艳明为家人们准备的是稀饭和包子。午餐,有丝瓜炒蛋,有黄瓜炒肉,有番茄牛腩,还有黑鱼汤。医生说了,黑鱼汤含有丰富的脂肪,能够促进伤口的愈合。所以,这道菜,成为手术之后至今,一家四口每天的必备菜肴。
移植手术结束后,放在姐妹俩身上长达数月的透析管被取掉了,但她们暂时还不能冲凉。炎炎夏日,有火炉之称的武汉,热浪滚滚。两个女儿的洗浴问题,仍由妈妈胡艳明负责。不管怎么忙碌,她每天都会给两个孩子擦身子,让一向爱美的她们始终保持清清爽爽的样子。
恢复得较好的大女儿晓茹,也常常会给妈妈打下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把洗好的衣服晾上,把买来的新鲜蔬菜择出来,或者拿起拖把,把租住房打扫干净,再把屋内的东西摆放整齐。
本刊记者前往一家四口租住地采访时,尚未度过排斥期的晓怡因身体不舒服,在卧室里静养。
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租住屋,被一家人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面砖锃光瓦亮,桌椅上纖尘不染。一家人的穿着虽然朴素,但整洁得体,举手投足之间,彬彬有礼。即使身处生命中的至暗时刻,这一家人,仍抱着最虔诚的态度在生活;命运给了他们无比沉痛的一吻,但他们却报之以歌……
捐完肾的刘华平和胡艳明,看上去精神还不错。热情地为记者倒茶、让座。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们再三感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周江桥教授和邱涛副教授,以及包括盛梦丹护士在内的其他医护人员。他们不仅用自己高超的医术挽救了晓茹和晓怡的生命,而且在得知他们经济困难后,还积极组织员工捐款。同时,医院医务社工部也联合水滴筹发起筹款,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的确,自从两个女儿被确诊之后,夫妻俩就一直为钱的事情发愁。来武汉前,夫妻俩已花了10多万元。他们在老家住的是保障房,无房、无车。10万元里,有他们多年来的全部积蓄,还有亲友们大帮小凑的钱。
如今,手术虽已完成,但他们欠着医院30多万;两个孩子必须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方便定期复查,后续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还得在医院旁边租房居住……
为了挽救两个孩子的生命,胡艳明的父母、姐姐倾其所有地支持他们,刘华平的父亲拿出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几万元,如今他还和老伴一起每天起早贪黑地上街卖菜,为孙女攒钱治病。朴实的亲友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支援着他们,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人还在,家就在,希望就在!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愿爱心的涓涓细流一定能帮助他们荡涤伤痛。一家四口面对厄运时不服输,勇敢抗争,他们必定会走出至暗岁月,重燃生命之火!
编辑/戴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