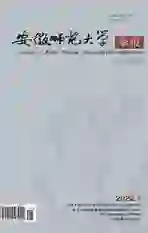语言选择与身份认同:辛西娅·欧芝克的民族共同体想象
2022-05-30赵娜
赵娜
關键词:语言选择;身份认同;语言策略;大屠杀;辛西娅·欧芝克
摘要:在《微光世界的继承人》《大披肩》和《普特梅瑟档案》中,辛西娅·欧芝克通过美国犹太人面临的英语、德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等诸多语言选择来洗涤人们的身份意识,勾勒了20世纪美国犹太人的生存史。欧芝克采用语言身份政治,以语言共同体的实施想象民族共同体,强调语言意识在能动的文化表演中产生自我信仰的身份。欧芝克在共享民族语言、文化、历史、情感的疆域中进行美国犹太共同体的想象,这些想象满足了散居美国犹太人的认同感,并且规划了一个希伯来语言景观,以实现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构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2)01-0062-06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Cynthia Ozick's Imagina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ZHAO Na( School of ForeignStudies,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2,China)
Key words:language choice;identity;language strategy;the Holocaust;Cynthia Ozick
Abstract:In Heir to theGlimmeringWorld,TheShawland ThePutermeserPapers,Cynthia Ozick awakens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identity through language choice of English,German,Polish,Yiddish,and Hebrew,faced by Ameri- can Jews,and outlines the living history of American Jews in the 20th century. Ozick adopts language-identity poli- tics to imagine the ethnic community wi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community,emphasizing that language consciousness creates a self-recognized identity in a dynamic cultural performance. Ozick's imaginations of the Amer- ican Jewish Community lie in the sharing territory of ethnic language,culture,history and emotion. These imagina- tions satisfy the diaspora American Jews' sense of identity,and a Hebrew language landscape is planned to realize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1928—)被誉为“美国文坛犹太文学复兴运动的领导人”①,得此名声不仅源于她以冷峻、幽默、犀利的笔触再现了犹太族群的生存境遇,提升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民族意识,而且她囊括了美国文学各项大奖②,有力推动了犹太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作为族裔作家,欧芝克在性别、种族遭遇与体验中品味着身份的复杂性与神秘性,身份认同是其小说反复表述的主题,评论者形成三类典型的观点:一类以文明冲突论,阐释人物恢复父辈民族与宗教身份的复杂性;①另一类以身份建构论,分析人物在寻找自我的历程中建构了个人与集体的身份,论证欧芝克复杂而多变的犹太身份理念;②还有从性别视角,论述女性身份是欧芝克架构美国犹太作家身份的主动力,③母亲身份是女性满足的身份角色④以及对痛苦的分离⑤。族裔、宗教、性别视角下的解读促进了身份主题的多元性争鸣,但忽略了语言与欧芝克身份书写的复杂关联。
为什么欧芝克对语言有着敏感的意识呢?多语言的成长环境揭示了其小说语言—身份主题探讨的原因。生于美国的欧芝克,5岁时在祖母的帮助下学习意第绪语,这成为她阅读、翻译意第绪语文学作品的重要基点。不过在基督教主导的学校,她被称为“弑耶稣”⑥的犹太人,她敏锐地意识到自我在他人眼中特殊的身份。不仅如此,欧芝克对语言的关注与犹太民族流散的历史亦息息相关。
公元2世纪犹太人从巴勒斯坦逃亡以来,散居世界各地,不得不适应寄居地的语言,从而引发流动中国族身份与民族身份连续性缺失的问题。欧芝克感慨:“自从我的奴隶先辈们停止金字塔的建造,流浪在西奈山的荒野后,他们使用过多种不为熟知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米语、12世纪的法语,以及使用了一千年的意第绪语……我是完全用英语思考、讲话与写作的第一代犹太人。”⑦欧芝克感慨犹太人的语言变迁历史,在文学空间讲述语言与犹太民族命运相连的故事。由此本文以欧芝克小说《微光世界的继承人》(2004)、《大披肩》(1989)和《普特梅瑟档案》(1998)中的语言选择现象为切入点,探究语言选择语境中的身份认同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本文认为,欧芝克通过对各类型美国犹太人物的语言选择及身份认同危机的描写,始终以大屠杀为显性和隐性语境,表达散居各地犹太人消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有意叙述大屠杀历史以形成犹太文化为根基的民族身份建构和民族共同体想象。
一、逃亡与身份迷失
从第一部小说《信任》(1966)到最近的《异体》(2010),大屠杀始终是欧芝克小说故事发生的重要语境。在《微光世界的继承人》中,欧芝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迁移为背景,描述这时期逃亡知识难民的“失语性”现象,以及现代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1933年4月7日,阿道夫·希特勒执政后立即颁布所谓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其中一条为:“凡属非雅利安血统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⑧这条法律直接将犹太人在内的非雅利安人排除在德国的义务范围外,完成了疏远犹太人的关键一步,为驱逐犹太人乃至其后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了道德催眠剂。在这场清洗运动中,德国犹太知识精英开始了影响终身的流亡生活。这时期美国知识界领导人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资助团体,联手美国高校接受了一批纳粹迫害的知识精英。尽管学界高度评价这批精英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在所有的流亡科学家中,人文科学家往往面临最为严重的‘失语性问题”⑨。即使得到美国的庇护,能否继续学术研究并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同是欧芝克半个世纪后的历史追问。
历史与小说中的时间差没有阻碍读者嵌入二战前后的背景进行互文性解读。密特威瑟与妻子埃尔莎一夜间皆被逐出德国学术界。密特威瑟受到美国哈德逊谷友谊学院的接纳,携家人历经艰险来到了美国。他禁止家人讲德语,家中只有妻子埃尔莎坚持与幼女讲德语。夫妇二人的语言选择表现了他们身份认知的差异。密特威瑟深知国家政策当然主要支持官方语言,毕竟“一个民族由其领土和语言所定义”①,其他语言总被看作外来者。密特威瑟克服了语言障碍,却面临知识话语权的“失语性”问题,他悲愤地感慨,“他们认为我的工作无价值。在那里曾经有价值,在这里却无价值。这儿他们缺乏欧洲人的思想”。②美国一贯以实用主义作为评价标尺,卡拉派宗教史研究既没有理论指导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可感觉到的应用效果。其实贵格会教徒之所以邀请密特威瑟是因为他们将卡拉斯迈派(Charismites)与卡拉派( Karaites)③混淆,没有受众的研究当然会归于沉寂。
不仅如此,从事犹太民族宗教研究的密特威瑟家庭没有犹太文化仪式,无独有偶,“弗洛伊德家族,与许多当时西方欧洲犹太家庭一样,抛弃了犹太传统”④。原因很复杂,比如“生存环境中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许多犹太人的自我仇恨意识,以及对犹太宗教仪式的厌恶”⑤等。这些家庭没有尊奉犹太文化礼仪,而礼仪的缺失会弱化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淡化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与集体认同,导致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消失殆尽的仪式中日益消散。密特威瑟从事与现实文化生活分割的研究,信仰的匮乏不仅影响研究意志,更降低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他茫然地发出本体性问题:“我在哪里?”“为什么我在这里”?⑥这一呼喊道出国族身份割裂之迷茫,然而战后还能返回德国重获失去的知识精英身份吗?
欧芝克不仅详细叙述了密特威瑟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而且始终贯穿与妻子埃尔莎的比照。战前埃尔莎是德国凯撒—威廉学院的一名研究员,来到美国,她的年龄、性别、精神创伤等都影响她的语言习得并阻碍她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主导语言的言说能力有时受到说话者之间权力关系的限制,而性别、种族、民族和阶级等结构性不平等可能会限制学习者对该语言的接触”。⑦面临语言与职业的双重“失语性”问题,她感慨改变语言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德国高级研究员是埃尔莎珍视的身份,科学家共同体身份有效保障了她对自我的定位。“害怕失去一个人的身份可能会产生对新环境规范的抵制”⑧,埃尔莎抵触英语而坚持讲德语的行为,也显示出国族身份认同的连续性以及流动的艰难性。
犹如许多德国犹太人所认为的,“他们国家经历的转变,即纳粹在1933年1月30日接管政府是短暂的事情,虽烦扰但却是暂时的”⑨。埃尔莎也怀揣返德的梦想,然而“身份是不稳固的,而是内在地处于变动中。它来自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规范的经验交流”⑩。当恢复旧身份的希望彻底破灭时,外界环境促使埃尔莎形成新的身份意识。小说结尾埃尔莎在丈夫颓废、女儿私奔、家庭陷入新的危机下,开始学习英语,谋划家庭共同体在美国的生存。学习语言是构筑新身份的直接途径,语言选择正是受难者在跨越边界中的艰难记忆历程,因此也必然经历固着于熟悉的语言与排斥新边界语言的转变矛盾。最终主体屈服于新的语言环境,向往未来的生活,激发出语言习得的内在驱动力。
欧芝克描述这一逃亡现象,有何意图呢?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关心,正如小说标题所示,是关于继承的问题,是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身份的连续性与流动性问题,而继承的主题反映了欧芝克对民族共同体的焦虑。密特威瑟夫妇因外孙女承袭了遗产,得以在美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我是谁”的问题不断侵袭他们焦灼的心灵。即使我们推崇自由选择的意志,然而一旦被标注为有形共同体中的成员,必将失去部分自由,这是获得安全共同体的代价。
二、大屠杀与身份遮蔽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欧芝克小说的主动力是为后大屠杀民族共同体记忆所支撑的历史书写,而《大披肩》①是一部直接描述大屠杀的文学作品,讲述了幸存者罗莎在集中营、美国及战前波兰的生活,尤为突出的是罗莎的语言选择所传达的抵制民族身份的立场。米丽亚姆·西文尖锐地指责罗莎“持有几乎歇斯底里、令人难以置信的拒绝承认归属犹太民族”②的身份立场;艾米丽·布迪克认为罗莎“就是纳粹定义的犹太人的原型缩影:怪异、自负、讨人厌、刻薄、极为有才智,专注融入鄙视她的文化,蔑视犹太同胞”③。读者在阅读这个所谓“负面”人物时,不禁思考:创作抵抗民族身份的人物有何意义呢?
二战后罗莎来到美国,新的国族身份迫使其面对新的语言,她的态度如何呢?她沉浸于女儿玛格达幽灵的折磨,采用精妙的波兰语给女儿写信,却用粗俗的英语向侄女斯特拉写求助信,至于意第绪语,她的否定态度令读者深感不安。大屠殺三十年后,罗莎与博斯基邂逅之时,罗莎以“不知道”“不会”回答了是否会讲意第绪语的问题,完全与博斯基的期待视野相左。然而罗莎在意第绪语环境中成长的事实以及她的口音,暴露了她的身份。毕竟“‘我认为我是谁融合在各种共同体中,所以‘我认为我是谁既建构也被‘我们认为我们是所建构”④。
欧芝克深谙“对于犹太人,意第绪语是认清我们是谁的最简洁方式”⑤,所以在语言层面考察罗莎对意第绪语的态度来反映其身份认同症候。二战中85%被屠杀的犹太人讲意第绪语,这造成战后该语言的急遽衰败。欧芝克忧虑的是意第绪语所代表的犹太民族共同体的消失,毕竟民族身份的瓦解体现在个体身上。欧芝克凸显家庭在培养和塑造个体身份意识方面的引导作用。“罗莎母亲是那么鄙视那些声音!”⑥“她父亲像她母亲一样,嘲笑意第绪语”。⑦父辈对族裔语言的态度直接影响后辈的语言选择,而这种语言观念架构着主体身份认同的走向。主体在去“民族性”过程中扭曲了自我与民族之间的历史关联,民族共同体在犹太家庭否定民族身份中日渐衰落。
欧芝克不仅厚描家庭原因,更关注大屠杀对个体身份认同的消极影响。简·斯特兰德观察到,“罗莎,与家中的其他成员一样,早就迷失了她的犹太身份与灵魂,甚至早在纳粹威胁她的犹太身体之前”⑧。集中营的伤痕在连接起罗莎过去和当下的同时,为她否认民族身份提供了亲历的事实依据,使她“将犹太身份视为一种悲剧命运”⑨。反之,身份认同也影响语言选择,大屠杀阻碍罗莎的语言适应能力,她的语言态度凸显了自我的选择意志,对她而言,语言就是身份。意第绪语是局外族群的标签;英语是生存的身份策略;唯有波兰语是她由衷认同的身份,然而已是回不去的白日梦。
由此观之,“罗莎弃绝讲意第绪语的犹太身份,却推崇一个被彻底消灭的世俗化的波兰语犹太社区”①。罗莎逃避与犹太人的身份联系,构筑了自我认同的身份,然而在博斯基等人的凝视中,社会认同罗莎的幸存者、难民、犹太裔身份。欧芝克强调自我选择的语言和认同的身份与社会认同的非同一性是困扰现代美国犹太人的身份困境,犹如大屠杀选择迫害的群体依据的是族群,而自我选择弃绝民族身份也无法避免迫害的后果。“有些人和群体过于急切地坚持自己独特的品质以及获得更好待遇的权利”,②其结果更加分化了族群的团结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崩溃,从而在整体上异化、排斥、隔离了这个族群。
罗莎沉沦于大屠杀的创伤中,反对被犹太身份所束缚的生活,但在美国不遗余力地讲述他们的悲惨遭遇,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更在事实上肯定了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促成了民族共同体新的想象。欧芝克发掘罗莎讲述大屠杀历史“作为犹太人共同体生活”③的意义,发现幸存者的力量。民族历史叙事是想象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手段,欧芝克视大屠杀讲述为重塑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方式,其小说普遍的大屠杀语境叙事编织了一张命运共同体之网,这正是“从大屠杀历史中得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结论”④。罗莎的叙述无意识中构筑了大屠杀后的民族共同体想象,这恰是欧芝克赋予这个人物的意义。
欧芝克以罗莎的语言选择为例,表明大屠杀创伤下民众对犹太民族身份的抗拒、弃绝心态以及割裂的身份现状,但更肯定讲述与传播大屠杀历史的意义。尽管我们认同“所有身份,包括族裔身份,都是可协商与可变化的,不存在语言与民族身份或国族身份的一一对应”⑤,但作为知识分子,忠诚于所属的犹太民族始终是她的书写立场。在《迈向一种新的意第绪语》一文中,欧芝克提出了建构语言的理想,“就像过去的意第绪语,新意第绪语将会是以犹太文化为核心和礼拜仪式为基质的语言”⑥。在建构新意第绪语的过程中,欧芝克试图恢复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意识,以实现重构犹太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抱负。
三、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语言策略
欧芝克的身份书写在进行美国犹太人局内与局外尴尬处境的厚描之时,力图在后大屠杀意识形态、知识分子话语与个体日常生活间寻找一个熔接点,而女性从来是她笔下历史景观中的核心人物。《普特梅瑟档案》中,普特梅瑟是一位拥有崇高抱负、强烈责任感的现代女性,她是如何解决自我身份困惑的呢?
生于美国的普特梅瑟讲着标准化的美语,这种语言管理有助于培养国族身份的认同意识,然而与白人的差异及距离激发了民族身份对话。欧芝克以身体描写展开个体身份在多民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西方凝视之间复杂关系的哲理探索。普特梅瑟,“她的眼睛小,睫毛短而看不到。她有平常蒙古人的眼睑——一张东方的犹太人脸庞”⑦。欧芝克以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强调“东方”的身份,这既是西方对东方凝视的刻板印象,也是东方在西方镜像中的自我审视。他者化的身体成为一种联系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方式。身体在自我与他人凝视中成为主体身份反省的催化剂,促使主体追问到底“我是谁”。主体难以达成一种满意的同化,毕竟“真正同化到主流文化的状态是不可能的”⑧。主体身体的他者意识正是民族身份觉醒的刺激物,为自我与本族群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依据。
曾经一度恐惧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的遭遇,父辈有意斩断了与犹太身份相关的各种联系,但伴随新一代的成长,犹太民族身份成为无法逃避的问题。“普特梅瑟必须要求一位祖先。她要求联系——当然一位犹太人必须拥有过去。可怜的普特梅瑟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没有过去的世界”。①欧芝克描述了当代美国犹太女性的困境,在身份形塑的各种因素中,语言对于形成我们是谁起着支柱性作用。欧芝克选择希伯来语作为民族身份的探寻,当然与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以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语言政策是犹太人在新时期建构国家身份、民族共同体的有效手段,成为引导美国犹太人民族身份建构的路标。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希伯来语被视为一种抵抗的语言,对于普特梅瑟来讲“神圣的希伯来语能够拯救流散中的犹太人”②。希伯来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重塑民族共同体的最直接方式。
学习希伯来语不仅是普特梅瑟自主认识犹太文化、历史的行动,更是建构自我理想身份的行为。她幻想金代尔叔叔教她希伯来语。“金代尔是一位熟知规范犹太教律法、惯例和传统的教师。就其本身而言,他不仅是抽象历史的提供者,也是过去的化身”。③金代尔的幻想是普特梅瑟对历史、祖先、乌托邦的渴望,是民族身份断裂的美国犹太人寻根意识的典型表现,反映了构筑民族共同体身份的内在需求。希伯来语作为维系民族身份的纽带在当下的美国得以承继,体现出欧芝克语言身份政治的策略。
欧芝克对民族身份的建构没有停留在语言层面,“语言选择不是言说者构建其社会身份的唯一手段,最终语言选择与交际性实践活动交织在一起形塑了身份”④。假人(golem)是犹太传说中有生命的泥人,假人传说作为民族文化遗产是想象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假人像一座犹太人受难史的纪念碑那样,标记犹太人自古以来的命运。“假人既是犹太人弱点的标志,因为边缘化的流亡者需要保护以免受迫害,也是犹太人的力量标志,实现了与上帝圣名相连的神秘创造力”。⑤普特梅瑟特意研习了伟大拉比勒夫制造假人的方法。在反犹主义危机中,勒夫的假人是为了拯救布拉格的犹太人而创造的,而普特梅瑟的假人具有多重功用,包括弥补她失去的情人,满足渴望女儿的需求,并帮助她成功当选纽约市市长。普特梅瑟把希伯来文化运用于城市政治的变革中,赋予语言的改革力量,希伯来语成为一种政治介入与权力变革的工具。尽管城市改革在假人欲望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最终功亏一篑,欧芝克让普特梅瑟充当拉比创造了女性假人,建构了女性民族身份的叙事史,在展演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普特梅瑟档案》中,欧芝克关心的是在族裔身份断裂的情况下以及寻根意识的推动下,如何继承他们的猶太身份。普特梅瑟对希伯来语的选择表明她并不把希伯来语看作是引发自我排斥的语言,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引以为傲的语言,因而这种语言选择是分享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联合象征,是避免丧失以及建构民族身份的直接途径。如果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⑥,普特梅瑟的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了安全感与认同感,建立起自我认同的民族共同体。
语言选择揭示了主体的生存困境,欧芝克通过美国犹太人面临的英语、德语、波兰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等诸多语言选择来洗涤人们的身份意识,建构了20世纪美国犹太人的生存史。欧芝克书写语言与身份的重要关系,采用语言身份政治,以语言共同体的实施来想象民族共同体,强调语言意识在能动的文化表演中产生自我信仰的身份。后大屠杀时代美国犹太人面临的棘手问题就是找寻能够安置自我的和谐身份,建造自我与社会相互认同的身份,而要抵达这个目标,必须能够正视自我的各种身份。欧芝克对美国犹太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是基于民族成员散居美国的想象,他们不能共享民族的居住地,只能在共享民族文化、语言、情感的疆域中进行共同体的想象,这些想象满足了散居美国犹太人的认同感,并且规划了一个希伯来语言景观,以实现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构筑。
责任编辑:荣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