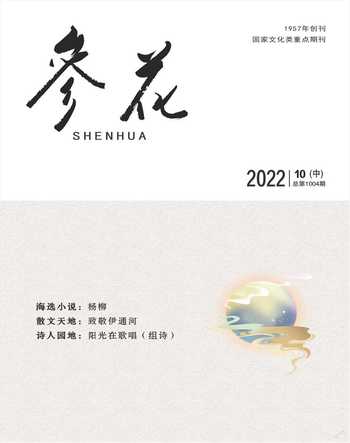冯晏诗歌《一百年以后》的创作艺术探究
2022-05-30杜家凤
一、引言
作为当代著名的诗人冯晏,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因其抒情优美的诗风,曾在国内诗坛引起一阵轰动和热议,其诗集《原野的秘密》在1998年获东北文学奖,其作品更是被国内外20多种版本的诗选选入诗作,获得不少读者与学者、批评家的掌声和赞誉。程光炜认为,“冯晏的作品具有清新的风格,以及隐含着东北地域景致的韵味,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而那时的她却带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和坚持在喧嚣热闹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悄然退场。近年,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淘洗,她一改初期的诗歌风格,以一种更为深入的哲学思想,在清晰的生命追问和思索中,以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哲思重扬了诗意的长帆。文学评论家张清华认为,阅读冯晏的诗歌,就像独自驾车于一场浩瀚如烟的大雾天气之中,让人有一种道不清说不明的无能为力之感。[2]
21世纪以来,冯晏诗歌转向更为深入和广阔的精神建构。姜涛认为,从近几年看,冯晏作品带有较强的思辨性、哲学与现象学色彩,具有鲜明的个人创作风格。[3]罗振亚曾评论道,冯晏将哲理思考、语言表达和情感诉求三方面融为一体的诗歌创作方式,是需要具备精深的写作水平才能达到的。尽管目前学界对冯晏诗歌的研究较多,但对于诗歌《一百年以后》,仍有待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实质上是以该诗为例,探寻诗人穿越时空的创作艺术,以超现实的方式,通过精确的选词和时空的交替转换,在现实与虚无之中,探寻诗人对于生命的哲思,以寻求现代诗歌的共同规律和美学本质。
二、精准的遣词造句
诗以言情,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以文字为媒介,通过表面的言辞展现内心生动而丰富的情感寓意。对于文字抒写和现实写照,词语使用和情感表达之间的艺术处理,是当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永恒话题。冯晏认为,“诗歌——是我用意念串起的词语的珠链,在写作中,选择词语其实是在选择表达自己情感时借以依附的物体”,可见,冯晏在创作中对于用词的用心和重视。她总是希望在通过对“词语”的巧妙运用和变化,充分展现诗意的同时,又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在情感,清醒而不热烈满溢,深刻而不张扬四射。
“一百年以后,冥想变成气流,低飞而聆听。写作是蛇脱掉的皮。如果幸运,词语可以穿过鳞。龙卷风袭来一只拖鞋……”
《一百年以后》
在冯晏的诗歌中,经常能看到很多日常生活中普通又常见的物品,表面上看,其词语之间的联系似乎较为散漫和随意,甚至带着诗人自己的喃喃自语,但内里却又承载丰富的寓意和深刻思考,看似深远,却又随处流散,还包含很多不确定性。在《一百年以后》这首诗中,如“月光曲和扭曲的梯子”“自尽的蝉”“蛇新生后蜕掉的皮”“龙卷风所夹带的拖鞋”“竖起的头发接收思考和月光曲的能量”,诗人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思维和想象,把写作过程中的状态隐喻成蛇新生成长后蜕掉的皮,寓意诗人写作过程中的进步和创新;以精准词语所达到的诗意效果的光芒,隐喻成穿透世间繁重物质的鳞片,这些看似毫无关联、不断跳跃的词组,在诗人不停地变换和重组之下,变得更加形象和通透,每一个意象都是如此准确和精妙,让人不得不惊叹其用词的微妙。
诗人冯晏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生活中的细节,又以创新性的词语组合,把蛇蜕皮的状态隐喻为创作的过程,生动且逼真。在描写过程中,既没有情绪化的倾泻,更没有概念化的堆砌,这种写作手法不仅丰富了诗歌的内涵,还给读者留下一种多维度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使藏匿于文字表面之下,诗作中蕴含的独特价值和深刻寓意以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得以展现。冯晏认为,语言在诗歌写作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含蓄且微妙地体现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在情感,“一位好诗人,应该会用不同的形式体现他的写作能力,但始终要伴随的是精雕细刻的结构和词语,语言的穿透力”。[4]
诗人冯晏在诗歌写作过程中对言语的高度重视和对词组的精准锤炼、理性而深刻的描述,使她的詩歌带有自身难以言说的复杂性。冯晏是从纯粹语言的角度理解和实践诗歌创作的,她的诗歌没有那些虚假情感和矫揉造作的情绪发泄,更克制住了情感化和人格化的冲动,在带有个人风格的理性睿智中,让诗歌在词语的不断创新和重组中富有穿透力,愈发显得深邃和透彻。这大概也是后期人们将她的创作称为“智性写作”的原因,诗人冯晏以其优雅的性情、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精准的遣词造句,挖掘人间万象之下深邃的精神力量,这是在她深刻地思考和追问下,对生命这一永恒话题的美学诠释。
三、时间和空间的交替转换
如果说小说中的时空叙述特点是连贯的,以情节推动叙事,那么诗歌就可以理解为是“片段式”的,通过对时空的错落排序,在转换和交替、打碎与重建之间,彰显诗歌蕴含的内在力量。诗人通过表象的文字符号,诗句内在蕴含的强大力量,在虚实变幻之间,时空转动之中,塑造出了诗歌中独特的时空意境。如巴赫金所言,“界定时空的一切概念相互间是不可分割”“时间仿佛注入了空间,并在空间上流动”。[5]诗人总是能够以天然的敏锐性一窥生活的细节和世界的本质,在时间和空间的交替转换中,营造氛围,构建属于诗人自己的一片天地,冯晏的诗是可以用来驻留和行走的。
“一百年以后,时间是扭曲的梯子/废弃了攀爬和触摸/是一个人播放月光曲时/头发竖起所接收到的能量。一百年以后……通过自尽的蝉。空门石阶上闪过一只猫,前世偶尔惊现……”
《一百年以后》
在《一百年以后》这首诗中,“一百年以后与前世”“空门石阶和不同医院”“蝉的自尽与人的咳嗽”等,这些词都在悄然之中传递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所带来的孤独气息。诗人将时间扭曲成废弃了的梯子,在梯子的一格一格之间,将看不见,摸不着、无形的时间空间化,把无限的时间具体化成有限的个体空间,将时间停顿,然后万物由虚实相加开始行动,构成空间的真容。如罗兰·巴尔特所言:“人类就是这样在空间中书写着自己,同时立即又使空间充满着亲近的举动、记忆、习惯和意愿”。[6]诗人冯晏就是这样,以诗歌的形式,通过在文字所建构的时空中,注入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留下自己的独特印记。在空间不断延展和时间反复重叠的过程中,时空在来回交替中环环相扣,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意世界。
《一百年以后》中包含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交替,这里的“历史”在于诗人以一百年以后为主题,写“前世偶尔惊现”“废弃了的梯子”,写出了时移世易、年代更替后,陈旧的事物已被废弃;“现实”是世人不论身处哪一时间段,“孤独的轰鸣”和“在医院咳嗽”不仅是人类面对的永恒话题,更是当下社会中所有人对生存、命运和时间状态的现实写照。有学者认为“前世”与“远望”,是汉语诗歌过去与未来的至高记忆,也是表达中国诗意至高的技艺。[7]这种观照方式和抒写方式是诗人对当下时代和现实的敏锐察觉和感触。也就是说,诗人既通过“现实感”写作描述当下,又回溯过去和预示百年以后,打通了历史脉络;既在饱含个人对过往情感的同时,理智地看清当下,又以超前的眼光和视角关注时代的发展趋势。
四、智性写作中的生命诗学
冯晏因具有不同于一般女性作家那种洋溢出的感性情感,加上理性思考、优秀的现实阐释能力和探究诗学的热情,被誉为当代的“智性作家”。她创作的关注点往往在于身体和心灵、人类与社会、时间与空间的生命诗学,以一双敏锐的眼睛去观察人间万象表面下的内部结构。有学者把冯晏的艺术创作比喻成拨开表面,打开表盘的后部,仔细看清内部的每个齿轮和构件是如何构建的。[8]她的诗歌是在历经万事后,建立于自身真实感受上,通过个人适度的想象力和对诗句选词的反复琢磨后的作品。她的此类诗歌,表面上看,只是些简短有力的文字,在意义层面上,却已经通过一些小的接触口,深深抵达了存在的时间以及社会结构的内部本相。
冯晏的这种智性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是其坚持多年阅读和思考后沉淀而成的宽厚精深的知识素养,二是历经生活和社会对她洗涤后的复杂的生活阅历。三是冯晏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和萨特等哲学家对她的思想启迪。冯晏曾直言,维特根斯坦是她最喜欢的哲学家,认为他的思想方法启发了她对于诗歌的创作灵感。正如在冯晏致敬维特根斯坦写的诗中所描述的那样,你思维轨迹上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密纹,思维逻辑的缜密和智慧,已足够我用一生的时间去破译解密,从中足以感受得到其对维特根斯坦哲学思维的喜爱和敬畏。诗人通过阅读学习哲人著作,产生了情感共鸣,这种精神召唤是诗人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苦楚后,对个人语言智慧的激发,由此迸发出的灵感再投入写作中,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世人眼前。这大概是诗人能够摆脱思考困境和个人局限,以更加理性的思维逻辑投入写作的原因。
“我在不同医院咳嗽/孤独的轰鸣声不时激活喉结和耳鼓……苦难在记忆里卷一根绳子/或者拉直一根铁丝,不停穿过……”
《一百年以后》
在《一百年以后》中,“不同医院” “咳嗽”“孤独的轰鸣声”“被激活的耳鼓,喉结和胸腔”,这些意象表明,人本身就是一个生老病死的有限生命體,晚年疾病缠身时的“咳嗽”、不断激活的喉结,胸腔和耳鼓发出的声音是个体生命对生命即将消逝时的抵抗和渴望生命存在的象征。诗人以百年之后,在这种循环反复中,感受生命的伟大与渺小,使诗歌中的诗学意蕴更加深邃。除了孤独和衰老病死,诗人还将人生命中历经的苦难隐喻成记忆中不断拉扯的绳子和被拉直的铁丝,纵使生命中曾历经的挫折与困苦已然随风而逝,但过往仍在记忆中放置储存,在闲暇或暮年时,不断被世人回忆和品味,这大概就是生命给人的切身体味。诗人这种趋向于在生活中抒写具有价值的生命诗学,是历经多年的人生实践体验和不断学习后的体悟,带有女性诗人情理交融下的知性与优雅、深沉和厚重,令读者回味悠长。更可贵的是,诗人冯晏不仅以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写出了对这个世界的真实体悟,还在她的诗歌中随处留下了一些具有诗意的碎片,供读者去想象和回味。
五、结语
在冯晏的《一百年以后》这首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在当下对哲学和生命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通过时空转换、虚实交替的创作手法,将这种哲思推向一个更加开阔的境界,在表面的文字之下,透露着诗人的现代性诉求。正如诗人所言,“……以往语言的轻柔已经无法让你抵达深处的灵魂……诗歌是在创新中靠突破时代来存在的”。[9]诗人以这种方式在时空的交替转换中,在觉察到生活细节的同时,摆脱了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以一种凝练、干净且明晰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时空的重塑和诗歌意境的构建,这种创作上的变化,不仅是诗人拒绝重复和人云亦云,渴望自我超越和创新的成果,更是对当下诗坛重新审视诗与时代关系的最好解答。
参考文献:
[1]程光炜,张清华,敬文东,姜涛,张桃洲,周瓒,夏可君,姚风,冯晏,苗霞,吴丹凤,宗仁发.词语无边界——冯晏诗歌创作研讨会[J].作家,2020(05):19.
[2]张清华.一条花蛇从梦中向外张望——关于冯晏的诗的一些断想[J].作家,2020(08):118-119.
[3]韩作荣.2000年的中国新诗[J].诗探索,2001
(Z1):75.
[4]张桃洲,冯晏.安静的内涵——关于《冯晏诗歌》的书面访谈[J].诗探索,2008(01):161-168.
[5][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6][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文集[M].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夏可君.冯晏的诗作:被灵魂所信赖所爱——或自我的缺席与语词的氧气[J].作家,2018(08):150-153.
[8]霍俊明.安静的“偏见”与知性的“钟摆”——读冯晏近期诗作[J].文艺评论,2015(01):106-108.
[9]陈爱中,冯晏.夜空下闪烁的思想之光——访诗人冯晏[J].雪莲,2015(06):92-97.
(作者简介:杜家凤,女,硕士研究生在读,石河子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