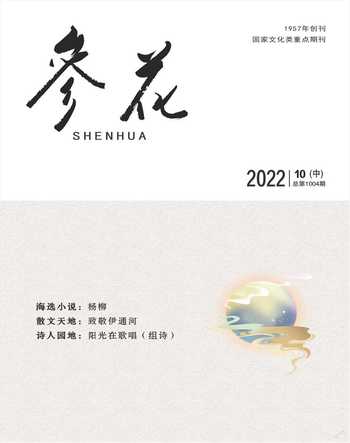论夏目漱石小说第一人称限制内聚焦式视角的独特审美价值
2022-05-30乔柏霖方香d
乔柏霖 方香d
在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之中,视点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叙述者与故事的距离由远及近,由全知全能到限制性视角,小說的艺术结构也相应地发生着变革,最终形成了叙事的三种视角:全聚焦式、内聚焦式、外聚焦式。夏目漱石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以第三人称的全聚焦式和第一人称的限制内聚焦式为主。本文以《我是猫》和《心》为例,分析夏目漱石小说中第一人称限制内聚焦式视角的独特性与审美性。
一、“狂欢下的涌动”:采用新奇的动物视角制造“陌生化”效果
狂欢化这一文化美学及诗学命题是由思想家和文论家巴赫金提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思维方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在文学体裁中的转化与渗透,他主张突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方式来颠覆理性化思维建构,正如夏目漱石《我是猫》中“猫”的叙述视角,“猫”可以跳脱出社会关系,站在社会的边缘,摆脱生活关系的制约,打乱正常的生活秩序和节奏,从而以更加冷峻的立场看待社会,从而制造出一种“陌生化效果”。
叙述视角大体可以分成“外视角”和“内视角”两种,其中,内视角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即“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又称“固定式内视角”或“固定式内聚焦”),在传统的全知叙述中,叙述者是指在叙述层面用于展示故事世界的人物感知,人物视角可以在叙事作品中短暂地出现。弗里德曼曾经将这一视角称为“选择性全知”,被不少叙述者采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选择性全知”显然不同于外聚焦下“选择性全知”中通过限制自己的观察范围,往往仅揭示一位主要人物的内心活动这一模式,这种视角的本质特征又与“全知”模式相违,即用故事内的人物的感知取代故事外全知叙述者的感知,读者直接通过人物的“有限”感知来观察故事世界。
在《我是猫》中,故事的叙述者是猫而不是人,这使猫摆脱不了猫的习性,难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同时,也因为有了猫的独立视角,多了更多的情趣和挥洒自如的笔致,猫也凭借这一点,在观察身边的事物时能够肆无忌惮、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想其所敢想,逞其所能为。这种边缘的地位赋予了猫双重性的视角,使猫在嬉笑怒骂间,狂欢地、随心所欲地揭露现实。这也是有别于第一人称内聚焦之中全聚焦叙事视角的部分。
这只猫站在超越人的立场上,不仅可以描写人的外观,也能描写人的心理,比如作者通过猫这一视角描写了苦沙弥的形象:
“……可他偏偏又是个饕餮客,撑饱肚子就吃胃肠消化药,吃完药就翻书,读两三页就打盹儿,口水流到书本上,这便是他夜夜雷同的课程表。”
猫站在一个超越社会关系的立场上,深入了苦沙弥的心里,肯定了“抗滔滔俗流”的精神,也把握到了他的反思倾向,得出了一定结论。同时,以猫的视角叙述人类的故事,起到了“陌生化”的效果。在传统作品中,大多是以人的视角叙事的,即使是最为客观的全知视角,读者也会以人的视角代入,会以人的视角去观察作品中的世界。而以猫的视角进行叙述,便为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通过另一个更加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书中的内容,通过另一种生物的视角,来展现明治时代的人物形象,许多在猫的视角看来,人的荒唐可笑的行为,以猫的口吻说出,更能让读者理解作者想表达的讽刺意味,也更容易令读者接受,达到比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更好的讽刺效果。人与人终究是同类,许多行为在情感上相近,但如果从其他物种的角度出发,这些行为会变得更加夸张,从而能够将其背后的含义,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猫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以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场景中而不显突兀,从而成为一个近似全知的视角。它可以看到主人的日记和信,可以听到人们的谈话。猫在观察时,可以有居高临下的视角,可以有从下到上的视角,也可以趴在人的身上去观察,同时,了解着不同人的内心与过去。并且其作为动物,还可以与动物交流情报。通过这种猫为主、人为辅的人猫互文叙述方式,丰富了叙事的角度,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使作品的叙事更加真实。同时,猫可以说是作为讽刺视角的最佳选择对象,小孩子同样对大人世界中的许多事情感到不解,但是他们没有成熟的思想;狗等其他动物在人的眼中是较为憨厚老实的,从它们嘴中说出的讽刺话语,缺少了一种真实感和自然感。因此,猫可以更加自然地传达出作者的思想。
二、“动态游移下的思考”:隐含作者与游移不定的叙述立场
在第一人称限制性内聚焦的叙述视角下,夏目漱石善于将叙事立场悬置在一个由不可靠向可靠游移的动态过程中,由此,将读者引入一个有意识、无意识的推断过程,此时就需要更多地介入读者本身的生活阅历与个人体验,而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我是猫》,作品中的“猫”作为游移不定的叙述立场,使读者能够审视与思考现实。
文学批评家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把叙述者分为“可靠的叙述者”和“不可靠的叙述者”:“可靠的叙述者”指隐含了作者个人经验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则指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隐含作者不一致的叙述者。《我是猫》却创造性地打破了传统的固有观念,“猫”很难被划定为“可靠的叙述者”或“不可靠的叙述者”。“猫”作为一个动物,很难拥有和人类相当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智力水平,在小说开头,“猫”甚至难以辨认“猫脸”和“人脸”,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发现,“猫”这一叙述者有时却成了真理真言的捍卫者,又成了可靠的叙述者,因此,“猫”作为叙述者是具有游移不定的特点的。
在《我是猫》中,“猫”尽管洞彻了世间百态,但始终没有丢弃自身“猫”的身份带来的特点,使整个小说趣味十足,因此,小说开头的“猫”更多的充当的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比如正是因为物种的不同,人类的行为和相貌通过猫的角度思考,就会变得尤为可笑。通过“咱家”近似高傲的语气可以感觉到,在猫的心中,人都是丑陋的,人的行为都是难以理解的,就像人类看待动物的心情一样。这样的反差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乐趣体验。同时,故事的叙述者——咱家,也是一只富有想法,又有些高傲自大的猫,它自己也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如在偷吃年糕的情节中,猫在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选择了偷吃,却没有想到年糕粘牙,心高气傲的它在人类面前“出尽洋相”,让人捧腹大笑。这一情节使“陌生化”更为突出,让一个看似全知的角色有了窘境,为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乐趣和新奇感。
但与此同时,在小说中又出现了与读者认知大相径庭的情节,甚至出现了让读者倍感震惊的情节变化。猫俯视日本明治时期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社会,对人们发出种种嘲弄与讥讽,对各种现象大加评判。这与其之前的胡言乱语有所区别,猫在嘲弄和评判中常常揭示出真理,不断发出饱含真知灼见的品评和鞭辟入里的言论。比如猫在品评金田小姐的婚事时提出的种种批判,作者借助猫的品评来表现自己对当时社会的反思。“猫”也会不定时地充当起“隐含作者”,以它那些独特而透彻的见解,不断撞击读者的心灵,敲打读者的思想,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对人物——叙述者究竟是可靠还是不可靠的立场产生怀疑,使读者不得不在阅读的过程中,投入自身的价值观念来对猫所叙述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和判断,去寻找“更深层的主观”。
三、“内聚焦下的透视”:非直接参与者与变换式的内聚焦
《心》也是夏目漱石采用内聚焦视角叙事的代表作品。其中的内聚焦视角也为小说的故事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故事分为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的叙述者是“我”,但“我”并不是故事的主角,也不是书中最主要故事的参与者。通过“我”与先生的不断接触,一点点地接近了真相,这属于非直接参与者的内聚焦视角。而在第三部分,通过先生的自白信,使故事的叙事视角发生了变化。这样的变换式内聚焦也为小说增加了十足的艺术效果,为读者带来了更清晰的阅读体验。
一是前两部分,“我”的非直接参与者的内聚焦视角。“我”是书中前两部分的叙述者、参与者。作品的高潮和最精华的部分,全在第三部分中先生的自白信里,而“我”与这一部分并无直接联系。但作者仍以“我”的视角去叙述前两部分的内容,起到了交代、铺垫和制造悬念的作用。在书的前两部分中,通过“我”的视角,在“我”和先生的交往中,先生的表现为读者和“我”抛出了许多谜题。为什么先生总是静静的,有时静得近乎凄寂?为什么他瞒着夫人,每月必去杂司谷墓地扫墓一次?为什么他和夫人十分恩爱,却又认为“爱情是罪恶的”?而他又为什么没有工作,待在家里?伴随着这些不断抛出的疑问,读者也一同随着“我”的视角,想要不断地接近先生,去了解先生的过去。而一切的答案,都在先生的自白信中揭开了。通过“我”的内聚焦视角去观察先生,不断地设置悬念,做铺垫,最终在第三部分解开所有谜题,使作品的内容更加完整,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读者在高潮部分感到震撼,也使先生的形象更加立体。
第三部分中的自白信是因,前两部分中“我”的视角中先生的形象是果,倘若作者仅以先生的视角,直接地去讲述他的故事,会显得十分突兀。如果没有前两部分,如果没有“我”的存在,先生根本没有必要去写这样一封自白信,而只会像他在前两部分中展现出的性格一样,带着这段故事,平静地死去。虽然全书的精华都在第三部分中先生的过去中,但是如果只以先生的内聚焦第一人称视角来没有缘故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不符合先生本应具有的性格——作品前两部分所描述的,被K的死亡深深影响的“静得近乎凄寂”的性格。因此,通过“我”这样一个人物,通过“我”的内聚焦视角,带领读者一同接近先生,一同因先生的秘密而费解,一同在了解先生的故事后恍然大悟,使全书的逻辑线索合理且清晰,不显突兀。以一个非主人公角色的非全知视角来观察,去了解主人公,通过打造神秘感,使读者渴望了解主人公,从而获得更专注的阅读体验。
二是前两部分到第三部分,由“我”的视角变换为先生视角的变换式内聚焦。小说都是以“我”的视角来叙述的,但“我”是不同的人。贯穿小说前两部分的“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小说一开始就把“我”和先生紧紧地拴在一起,“我”似乎在刻意接近先生,但是先生的言谈举止总是像谜团一样,让人难以捉摸,这成了小说的伏线,前两部分正是通过“我”眼中先生的行为素描进行透视的。而到了第三部分,则有所不同,“我”成为先生,并通过先生的遗书对谜底进行了揭示,让“我”将过去讲述给“我”的学生和读者,展示了“我”的经历和痛苦的内心世界。其实,主人公心理变化的伏线,早已设定,先生的悲剧结局可以让读者自然地会意于心。
小说在第三部分将“我”的叙述主体由“学生”转换为先生,其目的不仅是要在情节上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以更为真切的角度,从先生那毫不掩饰的心灵独白中,获取教训与表达对明治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无奈,渴望摒弃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封闭心态,以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好地迎接曙光,同时,表达出一个生于自由的新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如果一味地扩张自我,就不得不伤害他人,那么紧接着,也会将自己毁灭掉的观点。如果不变换视角,继续通过前两部分“我”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则无法深刻地展现出作者这样深层次的感情。变换视角后,在先生的自白信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有着日本文学特有的深沉感,具有独特的日式美感。
四、結语
夏目漱石作品中的部分人物都来自生活,也有他自己内心世界的影子,因此,通过冷冰冰的第三人称外聚焦视角,很难表现出所刻画的人物,以及作者本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深刻的思想。夏目漱石小说的精心构思使作品的叙述视角与故事相辅相成,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并极具特色与亮点。本文以《我是猫》和《心》为例,分析夏目漱石作品的内聚焦视角,发现独具特色的叙述视角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大大提升了艺术效果,并向读者展现了他的思想和明治时代的人间百态。
(作者简介:乔柏霖,男,本科,秦皇岛市海港区燕山大学,研究方向:日语;方香,女,本科,秦皇岛市海港区燕山大学,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