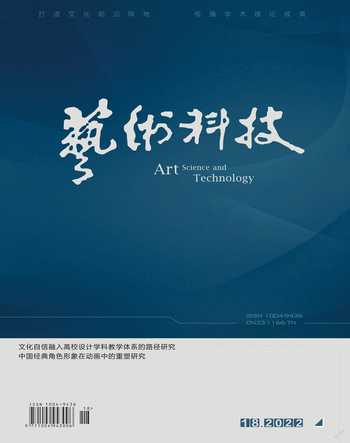从文化发展角度分析“抗日神剧”产生的原因
2022-05-30张靖崎
摘要:抗日剧是以我国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进行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优秀的抗日剧不仅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还有教育意义。然而,随着抗日剧的增多,许多带有离奇情节的“抗日神剧”出现。文章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抗日神剧”产生的原因。文化发展的过程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螺旋上升的,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不怕走弯路,而是怕没有纠正机制,对于错误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文化发展;抗日剧;“抗日神剧”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8-00-05
近年来,不少违背历史事实的抗日剧出现,由于情节过于离奇,被网友们调侃为“抗日神剧”。从2010年播出的《抗日奇侠》开始,诸多“抗日神剧”被官方和群众批评,有的已经下架,但2022年仍有《夜莺》这样的“抗日神剧”播出。
李安峰在《新时代抗日剧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反思与突围》中指出,“抗日神剧”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是对抗日战争的恶搞[1]。李一君在《“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传播效应及创作反思》中指出,“抗日神剧”将民族历史置于娱乐狂欢的情境之中,需影视制片方和监管部门共同提高历史认识水平,进而促进文化市场繁荣[2]。其他学者大多认为是历史虚无主义和监管不力导致“抗日神剧”的泛滥,他们的解释是自上而下的,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自上而下地加强监管。本文从自下而上的文化角度出发,分析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神化”文化,以及特殊群众也就是创作者的文化,再分析城市化带来的城市阶层受众,分析电视作为文化载体走进千家万户带来的娱乐性,最后分析人们心中存在的正义感带来的英雄主义。从这些文化的土壤出发,了解“抗日神剧”不断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从而对症下药,以更好的方式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祖国文化繁荣添砖加瓦。
1 抗日剧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众多爱国艺术家在艰苦条件下为宣传抗日努力,抗日电影就此诞生,但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因此电影只能使用隐喻或侧面描写来表达抗日救亡。例如,1932年上映的《野玫瑰》中有号召爱国青年加入义勇军的片段,1934年上映的《大路》中有与汉奸对抗、加紧修路以帮助军队的片段[3]。可惜此时的抗日电影还不能在明面表达上表达抗日救亡的爱国情怀。
1933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1936年初,中国电影界发起了国防电影运动,以宣传民族解放和抗日救亡为宗旨[4]。比如1936年费穆导演的《狼山喋血记》,讲述了北方某村的村民一开始不团结,狼群肆无忌惮,许多村民被咬死咬伤,最后村民团结起来打狼的故事。同年,吴永刚导演的《壮志凌云》讲述了东北两个村子有矛盾,但不計前嫌共同抵御强盗的故事。此时的抗日电影以呼吁全中国团结为主。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抗日电影的话题表现越来越明显。例如,1937年孙瑜导演的《春到人间》就直白地表现了中国军队的正面形象。1941年司徒惠敏导演的《游击进行曲》讲述了主人公王志强在家破人亡后,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最终歼灭日军部队的故事。此时的抗日电影旗帜鲜明,目标明确。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主要矛盾转变为国共内部矛盾,抗日题材电影变得比较冷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抗日电影作品,如《狼牙山五壮士》《地雷战》《地道战》等。这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娱乐生活,而且对教导人民打好游击战具有现实意义,能帮助人民牢记历史,激发其爱国热情与正义感。
1978年前,中国只有少数家庭拥有电视,到电影院看电影只是少数人的娱乐,且不具备拍摄电视剧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电视逐渐普及,中国家庭在晚饭后总有一段空闲时间看电视。港台电视剧率先发力,此时以武侠和言情剧居多,抗日题材比较冷门。在科技上,邹竞院士为我国彩色胶卷作出了巨大贡献,让我国成为第四个成功掌握彩色胶卷技术的国家,极大地降低了我国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的成本,为我国影视行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由于港台地区率先城市化,具有较大的先发优势,抗日题材电视剧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2005年播出的抗日剧《亮剑》,重新带火了抗日题材。此后,《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战长沙》等一系列优秀的抗日剧上线。2005年上映的新版《铁道游击队》,融入了武侠元素,主角将自行车用得出神入化,“抗日神剧”初见端倪。2010年播出的《抗日奇侠》,由于“手撕鬼子”的场面过于荒诞,引发了全网吐槽。之后,诸多的“抗日神剧”,如《箭在弦上》《黑狐》《敌后便衣队传奇》等都遭到网友吐槽和抵制。
2 “抗日神剧”产生的原因
从抗日剧的发展可以看出,抗日题材是中国历史的产物。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和科技稳步发展,为电视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抗日剧进而诞生,其中一些抗日剧因过于荒诞被称为“抗日神剧”。
2.1 以人为神
以人为神的农业传统为“抗日神剧”奠定了思想基础,把作出重大贡献或有卓越才能的祖先神化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例如印度的巴霍巴利王、古希腊的阿喀琉斯、乌鲁克的吉尔伽美什等。中国自周朝以来,确立了以人为神的文化,供奉祖先成为中国人民最重要的事情。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总喜欢为开国皇帝编撰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民间自然也会借用神秘主义证明反抗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人民也愿意将品德高尚和有巨大贡献者神化,最典型的当数关羽。关羽具有义薄云天的品格,人民一再将他神化,其从武将身份逐渐化为财神爷的象征。因此,人民群众尊敬的抗日英雄,自然也有神化的可能。但开展扫盲运动后,人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开始对旧时代的文艺作品抱有反感的态度。而且八路军深入群众,人民深知他们就是身边人,并没有过强的神秘感,因此普通人民群众神化八路军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我国没有开展扫盲运动,人民文化水平不高,那么其在茶余饭后神化八路军的概率不低,也会乐意看“抗日神剧”。
史书是古代知识分子为帝王所写,如果一些现代的编剧没有摆脱旧时文人的气质,还抱有以人为神的想法,便会自发神化当代的历史,认为这样有利于维护统治。因此,在一些“抗日神剧”中,主角无所不能,甚至出现了飞檐走壁、“手撕鬼子”的场面。另外,一些港台编剧沉醉于过去的辉煌,把玄幻、武侠、偶像和言情元素强加于抗日剧,想复制成功套路,不顾历史现实,这也是“抗日神剧”出现的原因。
还有一些家族过去站在错误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了下来,试图在政治上洗白自己的祖先,但是确实没有什么正面故事可写,于是就用历史虚无主义、用个人行为来掩盖自身阶级的错误。以最近下架的《人生若如初见》为例,主人公良乡的原型是良弼,本是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晚清贵族,但在剧中是一个圣人般的正面人物,革命党人反而像反派。
2.2 城市阶层
改革开放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城市,城市阶层形成。城市拥有比农村更好的基础设施,城市居民也拥有更高的收入,这使得城市在文化上有更大的话语权,抗日剧的受众从农民转向城市市民。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又是大城市,两种因素的叠加,使得以上海为背景的抗日剧逐渐增多。为表现出幻想中的城市小资生活,“抗日神剧”完全脱离了现实。例如,2022年播出的《夜莺》出现了在西餐厅里商量抗日计划,学习西方马术,在露天大阳台沐浴,甚至是走秀式战斗的场面。
小资产阶级总是认为生活会线性地变好,对生活中的损失十分厌恶,对革命道路的曲折不甚了解,所以他们属于中间派,在革命顺利时才会加入。由于长期居住在城市,他们对农村的革命不是很了解,因此,反映到“抗日神剧”中,便是八路军一边倒地打败日本鬼子,而且只有精英分子在主导革命,看不到普通人的身影。
2.3 娱乐时代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天然具有娱乐属性。电视本身乐意表现“抗日神剧”,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第十章中提出了电视的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这三条哲学如下:你不能有前提条件,你不能令人困惑,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5]。
人们用遥控器换台时,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某个节目上,因此抗日剧演员的服装一眼就要让人明白,以至于形象固化;大多数人不是军迷,如果费心讲解战前部署会让人感到非常困惑,不如直接展现枪炮轰鸣、刺刀拼杀的场面;如果为表现指战员部署充分,对作战指令进行分析阐述会显得说教感强,不如表现歼敌迅猛、横扫千军的情景。这就使得“抗日神剧”必须在剧情和杀敌手段上做文章,以尽快吸引观众。例如,2012年播出的《敌后便衣队》出现了“包子雷”炸敌的荒诞场面,2015年播出的《一起打鬼子》出现了“裤裆藏雷”的离奇情节,2018年播出的《特种兵之深入敌后》中消灭日军时甚至出现了现代装备。
隨着互联网的崛起,为博取流量,一些“抗日神剧”加入了网络游戏及流量明星等娱乐元素。例如,2013年播出的《向着炮火前进》的主角伴随不知道哪来的欧式沙发出现,还开着摩托用加特林横扫日军。再如,2020年播出的《雷霆战将》出现了战场上喝咖啡和走秀式战斗的情节,主角抹着厚厚的发蜡,“优雅”抗日。
2.4 英雄主义
英雄主义文化也对抗日剧产生了影响。英雄身上的优良品质受人崇拜,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可以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艺术虚构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无数革命先辈谱写了英雄般的史诗。例如,8次一等功获得者吕俊生,1938年7月在山东夏津战斗中,冲入日军阵列,杀敌27人。这些事迹应当被艺术作品全力塑造和宣扬。“抗日神剧”也通过塑造英雄人物来追求民族独立,但实际效果事与愿违。
严肃的抗日题材影视作品都将正面人物塑造成完人或是经历成长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抗日神剧”则使英雄人物的战斗叙述过于脱离现实,放弃我军强调的战术配合和战斗纪律,如三三制、迂回包抄、围点打援等。主角通常没有战术配合而是直冲敌阵,如2013年播出的《箭在弦上》,主角像拥有超能力一般,几人光凭射箭就可以对抗全副武装的日军。同年播出的《雅典娜女神》也出现了气功对打的离奇场面。“抗日神剧”只关注个人能力的强大,这些拥有超能力的奇侠更像是美国的超级英雄。
美国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排除一些创作者在学习好莱坞电影之后也想创造中国式的超级英雄。美国的创作制度固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电视剧在叙事和故事表现上需要符合中国国情。如今中国的影视业已有一定的实力,爆米花式的商业电影已经十分成熟,但在故事的叙述上仍然存在问题,部分影片甚至直接套用美国电影。例如,在电影《长津湖》中,中国志愿军像美国电影里描述的那样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而实际上我军采取的是三三制的分散阵型。
对我国英雄主义阐述较好的影视作品是2021年播出的《能文能武李延年》。李延年给张安东以及全连战士做思想工作的情节真正展现了这支军队的军魂——不惧敌人,为保卫人民而战。
3 “抗日神剧”产生的负面效果
3.1 歪曲历史
创作艺术作品不仅要追求艺术性,还要有社会担当。“抗日神剧”缺乏教育意义,政治宣传也背道而驰,一些作品甚至漏洞百出,进行了错误宣传。本该是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努力赶走了外来侵略者,赢得了抗战胜利。但在“抗日神剧”中,是一群拥有超能力的奇侠用娱乐化的方式赶走了日军,甚至对战斗乐此不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对不起革命先烈的牺牲,是对前人革命胜利果实的糟蹋。
在“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下,“抗日神剧”顶着“政治正确”的帽子可批量大规模廉价生产,使得观众对抗日剧产生不好的印象,即使有好的抗日剧也可能会被忽略。如果一些青少年接受了“抗日神剧”中错误的历史观念,那么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唯物主义教育是非常不利的。
3.2 反智主义
“抗日神剧”中反智的现象并不少见,最明显的就是不尊重历史。“抗日神剧”中超能力者左右民族命运的剧情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必须批判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结果,在“抗日神剧”中则被简化为某几个英雄的丰功伟业。
另一种反智现象是谁都可以打鬼子,忽略了其原本的阶级属性。哪怕他是恶贯满盈的土匪,只要他抗日,就能被洗白。如果土匪具有较高的觉悟,能接受马列主义的改造,就不会有《智取威虎山》了,更多的土匪勾结敌人,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在武器装备上也存在反智现象,主角拿着不合理的武器进行战斗。例如,2012年播出的《枪神传奇》中出现了子弹不合理拐弯的情况;2014年播出的《战神》中,八路军竟拥有数倍于日军的山炮、迫击炮和马克沁机枪;2021年播出的《雪豹2》中出现了竹筒做的迫击炮。我军确实诞生过不少狙神,如张桃芳,但他的成绩是靠不懈努力和顽强的革命精神取得的,他并不能违反物理规律让子弹拐弯,而是总结子弹发射的物理规律,从而成为一代狙神。对于武器的改进,如八路军神炮手赵章成在百团大战中,在炮弹中加入辣椒粉,炸得日军纷纷跑出碉堡,顺利完成任务,这是在合理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做法,而非凭空创造重火力取得胜利。
3.3 哗众取宠
如果抗日题材是个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就会冲淡其原本的文化意义。文化创作者首先要将主流的、通俗的历史意义表达出来,在文化上有争议的应当搁置,而不是对某段历史进行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的描写。有的人一意孤行地认为洗白某些人物或阶级是独立思考的表现,殊不知这只是哗众取宠的行为。例如,2013年播出的《青春烈火》加入了玛丽苏式的爱情戏,女主角涂着口红,穿着高跟鞋战斗。
哗众取宠也许一时能受到关注,产生流量,但这是不持久的,甚至是有害的,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底线,为了流量无恶不作,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影视作品的创作者要有职业操守,担起社会责任,不畏一时的困难,基于历史事实,创作出人民喜爱的抗日影视作品。
4 相关建议
4.1 创作者要加强学习
剧本创作者要加强自我学习,跳出熟悉的框架,实事求是地创作剧本,抛弃旧时文人迂腐的想法,认识到时代发生的改变,认识到剧本的创作不是“翻煎饼”,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思考而为某些历史人物翻案。历史是有评判标准的,而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学习的过程可能是艰苦的、枯燥的,若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笔下的人物就不会生动,故事情节就不会精彩。历史上那些革命前辈,仅仅是将他们的人生讲出来就足够精彩,如9次特等功获得者张英才,一生参加了上百次战斗,在鬼门关前游走无数次,传奇的一生令人不敢想象。
4.2 从多个方面创作抗日题材影视剧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本身具有娱乐属性,电视剧只为追求流量是不适合展现抗日题材的。抗日题材不必拘泥于一个方面,不一定要描写具体的战斗场面,也可以从侧面展现人民生活上的变化、思想上的变化。战争固然是抗日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战争之外,人民群众也会用实际行动帮助八路军做好侦察、运输、掩护等工作。例如,2007年播出的《地下交通站》讲述了发生在一家驴肉馆里的地下抗日故事;2011年播出的《巾帼英雄之义海豪情》展现了普通民众在日占时期的生活,其中角色“排骨”因没向长官脱帽被痛揍了一番,可见民众生活的艰难。
还应该鼓励创新形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从身边唾手可得的材料做起,不断传承革命先烈的优秀品质。
4.3 鼓励科普抗日战争的真实信息
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因为艺术加工的需要,会在不影响整体叙事的情况下,进行合理删改。因此,抗日剧兼具教育和欣赏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动群众,尤其是党史专业的学生,学习视频制作技巧,从辟谣电视剧中出现的错误开始,合理科普抗日战争的真实信息。例如,在电视剧《亮剑》中,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老百姓纷纷庆祝,就算是消息不够灵通,也不会延迟到屋顶还有积雪的冬天才传来。这是因为《亮剑》的拍摄时间是冬天,因剧组人员的疏忽,所以出现了时间上的错误。
在鼓励科普的同时,国家还要建设好党史资料的數字化图书馆,方便人民群众查找相关资料。一些枯燥的历史文献,经过有志之士的加工,更易于向公众传播,由于资料有出处,视频的可信度将大大提高。
4.4 鼓励群众网络监督和批评
好的影视作品即使有瑕疵也会深受人民喜爱,如上文提到的《亮剑》。优秀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需要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批评。网络监督和批评是有效联系群众的方式。影视作品的创作者不能闭门造车,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对人民不理解的情节作出合理解释,绝不能以“普通人欣赏不了艺术”的借口敷衍。孤芳自赏是精英主义的行为,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对人民群众的过激批评要给予宽容,情绪激动、表达不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伤。电视剧审查的过程和结果要按流程及时公开,从而博取人民群众的信任。
5 结语
“抗日神剧”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其淡化了抗日战争历史的真实性,是对革命先烈的不尊重,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反叛,同时影响了青少年正确历史观的形成和确立,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进入新时代,抗日剧的制作者应自觉加强学习,坚持唯物主义史观,而不是主观加入武侠、言情等无关元素;应坚持从多个方面展现抗日战争,而不是只追求刺激场面;应坚持联系群众,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并在此基础上,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为国家文化的繁荣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李安峰.新时代抗日剧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反思与突围[J].电影评介,2019(11):102-105.
[2] 李一君,史博公.“抗日神剧”的衍生逻辑、传播效应及创作反思[J].抗日战争研究,2020(3):146-152.
[3] 袁庆丰.左翼电影制作模式的硬化与知识分子视角的变更:从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大路》看1934年左翼电影的变化[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26-130.
[4]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社,1963:413-414.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70-171.
作者简介:张靖崎(1991—),男,江苏常州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数字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