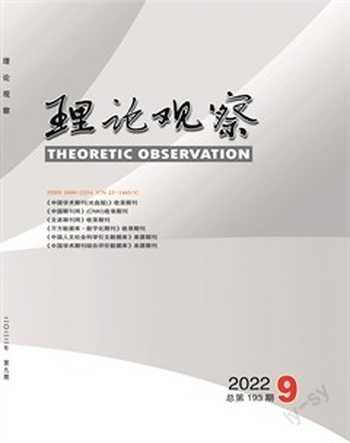低保户“污名化”形象:何以构建与如何解构
2022-05-30简荣玉
简荣玉
摘 要:低保制度長期在我国扶贫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关于低保户负面评价。低保户被认为是不思进取的“大懒人”、风评不纯的“关系户”、不被接纳的“边缘人”以及不愿退保的“钉子户”。对低保户形象的认知不仅影响其自我认知,还影响社会对低保制度认知图式的形成,最终导致对制度信任度和政策满意度的下降。本文从低保制度的理念、执行困境、福利泛化现状和文化后果等多方面探索低保户污名化形象的构建过程,并相应地从政治过程、执行技术、文化后果等三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试图解构低保户的污名化形象。
关键词:低保户;污名化;形象;构建与解构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9 — 0104 — 05
一、引言
最低生活保障是保障收入低于当地最低收入标准群体基本生活、补差式的重要政策,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7年,为缓冲大量城市工人下岗带来的影响,我国建立并推广了城市低保制度;2007年我国又进一步在农村实行低保制度。虽城乡低保在救助标准、基层管理等多方面存在差异,但在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增加福祉、维护稳定等方面均发挥了显著作用。通过与扶贫开发政策的良好衔接,低保在我国脱贫攻坚战中也继续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目前,我国进一步完善低保相关管理的政策,推动低保制度更好、更快实施。客观而言,低保制度整体上实现了改善贫困群体生活状况、增进社会福祉的目的,但陷入了资源不断投入、反贫效率没有同步提高的悖论中。
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的基础是政策对象的瞄准,即最低生活保障资源多大程度分配给了穷人。[1]低保资源真的是分配给穷人了吗?得到救助的人是真正的穷人吗?实际上,低保的瞄准偏差一直存在。李棉管(2017)认为受技术限制、政策基层复杂的执行环境和农村文化圈层的影响,农村低保的瞄准还是一个难题。[2]社会福利具有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功能,有基层人员变通性地将低保作为维护治理的手段。[3]地方权力关系嵌入低保资源分配过程,农村中的精英成为低保的获得者,即低保获得者并不完全是收入水平较低的人。[4]若说瞄准偏差是制度执行中长期出现且难以避免的问题,那低保群体的福利泛化、退保困难则引发了人们对低保制度的进一步思考。仇叶、贺雪峰(2019)认为福利泛化背离了低保制度“兜底保障”的目标,从而导致目标人群背离,引发福利倒挂、低保资源挤占和资源错配,低保政策效率降低,社会整体对低保制度满意度、对政府信任度降低。[5]而福利捆绑会引发边缘贫困户的被剥夺感,低保户出于理性选择则不愿意退出低保,进一步引发资源分配的矛盾。[6]瞄准偏差引发社会对低保制度实施和低保户获得救助的公正性的质疑;福利泛化不仅导致低保户退出低保意愿降低,还增加了社会对低保户行为的关注。于是,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关于低保户的负面评价,即出现了对低保户形象的“污名化”。
形象是人类社会交往互动的应用介质之一,正向良好的形象是“人”自我持存的一种内在精神需求,也是“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7]个体会顾虑自己的社会形象而放弃申请救助或隐瞒获得救助的事实,低保引发的福利污名不仅影响救助者的自我认知,还影响这一政策的救助效果。[8]贺璇(2020)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对农村低保的负面形象认知会传导为对政策“不合理不公平”的刻板效应,这一认知有极强的政策效应。[9]因此,探究低保户的污名化形象,分析其如何构建和如何解构,有利于增强低保户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低保政策的良性运转,改善社会对低保制度的认知。
二、农村低保户“污名化”形象的表现
(一)不求上进的“大懒汉”
近年来,我国大众媒体及社交平台上多次出现“低保养懒汉”的相关话题。以“低保懒汉”为关键词,在百度平台上搜得相关结果约983000条,结果中包含新闻、地方政策、互联网平台、视频应用等多种,时间跨度较长。许多正式新闻报道列举出低保户不求上进的表现,如好逸恶劳、不愿工作,虚报收入、不愿退保等。其中,一个以“农村低保户滋生了一群懒汉”为题的提问在百度提问上有37个回答,点赞数最高的回答认为有低保户四肢健全,但不愿意出去工作,只靠低保救助生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2010年就《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原则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中国福利过度导致养懒汉的担忧。2013 年 10 月末,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时表示,社会救助既要防止“漏助、错助、骗助”行为和救助不力的“冷漠病”,又要杜绝盲目攀比和“养懒汉”现象。[10]人民网近几年亦多次报道低保拒不养懒汉的主题。由此可见,不仅社会层面在关注低保户的懒惰行为,国家层面亦担忧“低保养懒汉”和福利依赖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风评不纯的“关系户”
“人情保”、“关系保”是低保制度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基层执行人员尤其农村官员利用职权便利,对低保名额进行违规操作。这一现象不仅导致低保资源的错误分配,又影响社会对制度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我国将纠正“关系保”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民政部多次发声要加强低保“关系保”“骗保”的责任追究。低保的福利泛化、低保边缘户的相对剥夺感与“人情保”“关系保”现象的频频出现,人们不免对一些低保户是否符合低保要求产生质疑。人们质疑低保分配的公正性,申请低保变为“吃低保”,低保户由贫困户变为有本领、有关系的“关系户”。低保救助者不愿主动对外透露自己获得救助的信息,除为维护个人形象外,更主要的原因是避免外界对自己获得救助公正性的质疑和举报。对于低保对象,人们往往忽略其经济条件而关注其与基层执行人员的关系,许多符合申请要求的低保对象被扣上“关系户”的帽子。如据媒体报道,覃燕梅大女儿读高中,小女儿患癫痫,全家收入仅靠丈夫跑滴滴,而前年底丈夫突发脑溢血去世,全家经济支柱倒塌。覃燕梅家有学生上学、有人患病、无经济来源,完全符合低保申请的要求,但同村人仍觉得覃燕梅是走了“关系”才吃上低保。[11]
(三)不被接纳的“边缘人”
低保户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缺少发展的资源和禀赋,容易在经济层面上遭遇排斥;大多数低保户受教育程度较低,公共参与能力不足、政策知晓途径单一,缺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和动机。许多农村低保户居住地偏远,交通极度不便、活动空间封闭,无法频繁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公共事务参与明显不足。人情支出占据低保户收入的较大比例,导致其人际交往难度大,人情交往关系受限;此外,学者发现低保救助者在申领低保后会减少与亲戚、朋友的互动,时常感觉自己在社区中不受重视、观点不被倾听和接纳。[12]社会将经济能力与低保户的道德品质、承担社会责任能力相联系并给予其负面评价,低保户成了不愿与外界互动的、对公共事务冷漠的、自我封闭的“边缘人”。
(四)不愿退出的“钉子户”
低保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争当低保户”的现象。部分人通过虚报收入、哭穷、夸大医疗费用、与父母分家、辞去工作等策略获得低保救助,即使仍有劳动能力依旧坐等政府救助。我国在扶贫中实行干部对口帮扶机制,有的贫困户在获得救助后产生了光荣感,认为评上贫困户是受到国家和政府关注的表现,因而洋洋自得,甚至自觉“高人一等”。此外,部分低保户在享受“两不愁三保障”的保障时,还要求更多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更多的低保名额。总之,部分低保户会采取各种策略获得低保并拒绝退出。我国对“钉子户”向来严厉,采取多了重监督、定期核查、清退等措施,以确保“应退尽退”,但依旧难以避免。学界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从制度设计、文化层面、生存策略、个人特质等路径进行解释。不管国家如何治理福利依赖,其学理形成机制如何,低保户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坐等靠要”、不愿退出的负面形象。
三、农村低保户形象污名化的构建机制
(一)“底线公平”政策导向与“非赋权式”救助理念的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13]“兜底性民生建设”意味着国家要保障每一个人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使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满足。最基本需求与我國低保制度的保障底线相契合。“底线公平”是低保制度运行的主要价值依据,这明确了保障对象是底线以下的群体,保障标准是保障其基本生活、维护其生存权。因此,低保的救助标准依据本地收入和生活水平进行划定。但选择性的救助与较低的底线性保障水平无法为贫困群体发展提供更多支撑,与我国兜底性制度应向适度、普惠的发展方向相矛盾。
公共资源配置从来都是一个充满政治的过程。[14]这一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救助的选择性。这意味着我国低保必须有明确的政策对象,否则救助资源则无法实现有效分配,导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的背离,而社会救助的目标群体越明确,招致政治反对的可能性就更大。由于制度的选择性,我国低保制度的理念和执行过程出现了偏差,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隐形引导,引发了福利污名。为降低行政成本,增加监督的有效性,低保制度设计了严密的家计调查和结果公示程序,将申请者的贫困情况“公之于众”,信息技术的引入更是扩大了低保户信息的影响范围和时长,对其权利保护更加不利。福利污名的出现不仅影响低保户的个人感受、降低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也影响社会对低保户的看法。社会救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而救助标准则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调整,这最终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基层执行过程中,“面对面”的居民期望基层执行者能够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实现个别化的福利满足,但基层执行雇员事实上只能依据政策所制定的普遍原则行事。[15]为方便管理,基层官员更愿意以划分类别、统一管理的方式将低保户进行身份划分,从而导致救助者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分裂。
总体而言,我国低保不是主动式、赋权式的救助,而是回应性、选择性的,在执行过程中带有一定社会管理和维护最低生活水平的特性。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需要关注执行的便利性和成本控制,忽视救助者的主观感受和需求。即更多的是追求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而不是微观层面上个人社会行动者之间以及个人行动者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融合。[16]
(二)“生活贫困”目标群体与“乡土社会”基层治理的冲突
低保制度的目标群体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收入标准的贫困群体,通常包括因灾致贫、因病致贫、无收入来源、因学致贫等群体,即只有当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达到最低生活标准,成为底线人群时才有享受社会救助的资格。[17]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低保救助水平不同,但无论标准如何变化,保障对象及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低保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符合要求但未纳入保障、不符合要求但被纳入保障的情况。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引发贫困群体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引发社会对“人情保”“关系保”的不满,从而导致对低保户关系不纯的猜测。
“人情保”“关系保”与我国低保的乡土治理逻辑有关,在农村中更加明显。作为一种先进转移支付手段,分配低保资格几乎等同于分配资源。基层执行官员通常将个人关系网络嵌入到低保资源分配过程中,将低保名额分配自己的亲戚、朋友,不管其是否符合低保申请规定。此外,社会福利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基层干部可以将低保资格作为条件,换取居民同意土地征收、配合选举。这种利益交换促进了基层官员与低保户之间相互庇佑关系的形成。在乡土社会中,出于“大家都是熟人”的观念,加上贫困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缺少公共参与的能力,形成了难以对基层官员进行有效监督的局面,从而导致“人情保”“关系保”不断出现。公平公正地选择低保户是低保制度目标实现的基础,这一现象不仅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还影响人们对政策公平性的评价,对低保制度的执行极为不利。
(三)“条件不足”融入困难与“贫困无能”社会排斥的冲突
低保户通常具有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较差等个人特征和缺少资产、支出大负担重、抗风险能力弱的家庭特征。这些特征直接限定了低保户的经济能力、活动空间和社会关系。经济上、公共事务上、人际关系上,低保户都存在融入困难的情况,这与社会对贫困的文化视角的态度有关。
人们通常对贫困群体的特定行为从道德方面进行评价,贫困经常与“愚昧”、“无能”、“懒惰”等负面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贫困不仅表现个人及其家庭的经济状态,还是个人能力水平、社会功能和发展意愿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贫困者通常被认为对其基本功能的实现和对社会角色的承担程度不足,而申请社会救助就相当于社会成员将自己的“贫困”状态暴露于大众视野,“社会救助接受者”的标签使项目申请者与社区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与互动失去了原有的平等性,导致其在接受救助后的生活陷入污名化。[18]低保救助带来的污名效应亦影响贫困群体做出与救助相关的决定,对于社会形象的考虑影响贫困者是否接受社会救助——接受社会救助和公共福利意味着承认自己缺乏能力,无法承担非贫困者能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人们的相互依赖,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形成对救助者的排斥,这种排斥经常发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基于日常生活的污名化会导致一种人格的羞耻感,显著阻碍人们特定行为的产出。
(四)“应退尽退”退出机制与“不断叠加”福利泛化的冲突
为实现低保对象“应退尽退”、公平保障,我国形成由县、乡镇、村三级联动的动态管理机制,对不符合申请规定、收入超过低保标准的对象进行清退。但仍出现瞒报收入、材料造假以继续“享受”低保的现象,甚至有人无端取闹、暴力抗拒,造成和基层执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救助者不愿意退出低保,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存在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信任断层[19]。居民普遍认可中央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肯定中央政策的目的,但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执行,且与居民接触过程中产生过不愉快经历导致其获得的制度信任较低。我国的差序格局也为低保退出困难提供了文化和社会基础。在关系圈层之内的人都是“自己人”,没有不帮的道理,这为公正清退低保户带来了困难。此外,低保对象个人的道德品质也是影响其退保决定的因素之一。不过,我国与低保挂钩的多种福利,亦是低保造成福利依赖、影响低保户形象的重要因素。
为在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实现对低保户的多重保障,我国将教育、医疗、住房、殡葬等多种优惠待遇与低保捆绑,低保证成了享受这些待遇的“准入证”。部分低保户在得到相应救助后开始心安理得并逐渐产生依赖思想,甚至要求更多的救助与帮扶。此外,基于这些救助,低保户的生活能得到有效改善,一旦退出低保就会失去诸多优惠,生活品质将受到较大影响,造成“福利断崖”。出于为获得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低保户选择隐瞒收入,继续获得低保救助。
四、农村低保户形象污名化的解构策略
低保户形象的污名化是一个复杂、多层次、多方面的过程,是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个体行为、社会文化结合而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对低保户形象的认知不仅影响低保户自身的自我认知,这一认知会转变为对低保政策的认知图式,最终影响对政策的评价。因此需要做出调整,解构农村低保的污名化形象。
(一)政治过程层面
低保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存在引发福利污名的可能。明确选择性的救济模式要求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资产审核,由此存在损害申请者自尊心的可能。救济而非赋权型的福利模式主要考虑政策执行的便利性而非政策效益和政策客体的感受,执行过程中主要注重执行的经济性而忽视政策客体的社会融入,由此造成低保对象的社会排斥。多种社会福利与低保相挂钩,进一步激发低保户延长享受低保时间的心理,同时增强了低保边缘户的相对剥夺感,社会对低保户的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
因此,我国需要转变低保制度的理念,发展积极型、发展型的社会救助,在救助的过程中培养救助者的个人能力,不让社会救助变为“嗟来之食”,在救助的同时避免造成对低保户的经济、制度排斥。此外,发展适度、健全、普遍的社会救助和福利,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发展方向,并逐渐由补缺性救助向普惠性救助转变,减少其他福利与低保资格的挂钩,避免福利依赖。其次要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之间救助标准和救助力度差距,以此减少地方与政府、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博弈。第三要注意基层雇佣执行的培训,提高其专业能力,减少贫困群体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以此减少由制度造成的对低保户的负面影响。
(二)技术过程层面
低保执行過程中的缺陷间接影响了人们对低保户的认知。技术过程层面的缺陷主要包括政策行政成本高昂、目标瞄准难度大、基层官员监督机制缺乏等三方面。为缩减行政成本,低保制度设置了结果公示这一环节,让社会多重主体展开对低保户的监督,以较低成本实现对不当低保行为的监督。而低保申请者收入核算难度大、资产信息易隐瞒、动态管理难度大等原因又为低保的不当操作提供了空间。基层群众公共意识缺乏,基层官员和低保户相互庇佑的关系造成对基层官员的监督困难为“关系保”“人情保”提供了土壤。
对于这些问题,首先要调整目标瞄准的方式,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准确跟踪贫困者的动态信息。使用“区域瞄准”、“整村推进”、“类型瞄准”和“个体瞄准”相结合的综合瞄准方式,做到应保尽保,及时清退。其次要在公示时保护救助者的隐私,不公示不必要的信息,充分保护低保户的个人自尊;同时也加强对基层腐败、寻租、人情保、关系保的监督和控制,削弱“张榜公示”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增加对基层官员的威慑。
(三)文化后果层面
从前期分析中可发现文化对低保户污名化形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文化不仅影响人们对贫困的观点,还影响低保制度基层执行的公正性。因此,实现政策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十分重要。
社会救助的政策调整、项目制定、瞄准方法均要考虑地方文化和风俗习惯,做到文化兼容和配适。可以通过短暂的教育和群体间的接触来减少群体外的敌意。充分运用媒体、现代网络平台,甚至包括教育和法律来应对福利污名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对低保户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其发展内生动力、增强脱贫意愿,促使其适当改变、约束个人行为,以实际行动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
五、结语
低保制度是我国现行社会救助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多面的,低保制度在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保户的形象,低保户长期与“贫困”、“关系户”、“懒惰”、“边缘人”等负面词汇相联系。除低保户个人特质外,低保制度在基层的执行、社会对低保户的固有印象、低保户资源禀赋的弱势地位也是造成其风评不佳的原因。针对以上原因,可以从政治过程、政策技术、文化等三个层面进行调整。客观对待低保户,正视其形象有利于维护低保户的尊严和心理健康,亦有利于改变社会对低保制度的认知、增加政策满意度,从而改善低保制度的扶贫效果,使其在新时代向积极型、发展型救助制度方向转变。
〔参 考 文 献〕
[1][9]贺璇.农村低保户形象的社会认知及其政策效应[J].人文杂志,2021(09):111-118.
[2][18]李棉管.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社会学研究,2017,32(01):217-241+246.
[3]徐步华.社会福利的社会控制功能与潜在控制机制——基于非正统经济学的解读[J].宁夏社会科学,2021(05):152-161.
[4]魏程琳,王木林.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5):110-119+196.
[5][17]仇叶,贺雪峰.泛福利化: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目标偏移及其解释[J].政治学研究,2017(03):63-74+127.
[6][19]张奇林,李鹏.政府信任、人际信任与制度依赖——一种城乡低保退出困境的解释框架[J].青海社会科学,2016(05):123-129.
[7]杨雪,杨进.乡村教师形象的问题审视及其重构[J].当代教育科学,2022(02):87-95.
[8]Jana Friedrichsen,Tobias K nig,Renke Sch-
macker. Social image concerns and welfare take-up[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8,168.
[10]新华社.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制度[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30/c70731-23379
928.html 2013-10-31.
[11]陈菊华.低保“关系户”(千家万户的事这样办)[N/OL].(2022-01-1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115/c1001-32331888.html
[12]程中培.農村低保制度“福利污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社会建设,2019(06):62-76.
[13]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央广网,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70101/t20170101_5
23423305.shtml
[14]Pierson, P.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World Politics 48.
[15]Lipsky, M.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New York: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6]王锦花.城市贫困救助中的福利污名问题探析——以对广州市的调研为基础[J].岭南学刊,2018(06):107-113.
〔责任编辑:孙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