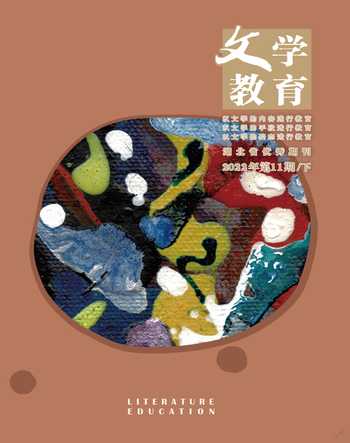泰戈尔与顾城诗歌比较研究
2022-05-30李雨竹
李雨竹
内容摘要:印度诗人泰戈尔与中国诗人顾城的诗歌主张与诗歌创作,在童话书写、死亡书写、现代主义书写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童真童心坚持着对童话理想世界的追寻,他们的人生体验赋予了死亡意识高级的美学价值和哲学意义,他们的现代主义创作特征与西方现代主义在认知观念上存在一定的同与异。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分别从童话想象的吟唱、死亡意识的叩问、现代主义的诉说三方面展开详细论述,着重对泰戈尔和顾城诗歌的内涵与意蕴进行阐释解读,走进诗人内心,领悟诗歌真谛。
关键词:泰戈尔 顾城 童话想象 死亡意识 现代主义
泰戈尔是印度伟大诗人,顾城是中国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两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诗人分别在诗歌中注入了童话想象、死亡意识和现代主义,用纯净真挚的笔触为我们开掘出一条通向诗歌盛宴的道路。
一.童话想象的吟唱
泰戈尔、顾城都是用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他们以天真无邪、纯真干净的儿童视角去书写世界的善美邪恶,这离不开诗人自身对儿童的关心和对童话的执著。因为拥有童心,他们义无反顾地相信童话世界的存在,义无反顾地坚持着对童话世界的追寻。
固守童心是泰戈尔的心愿,“我愿我能在我孩子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占一角清净地。”(《孩子的世界》)他的《新月集》以爱子和爱妻为基本形象,选取生活素材进行创作,天真且童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力量,能把我们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中去……”这是献给儿童的礼物,如童话般和谐美丽、温婉细腻。孩童般纯净的视野、朴素的语言、美妙的思维包容着外在的一切,没有善恶对错的评判标准。“墙壁是白色的银,屋顶是耀眼的黄。皇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宫苑里;她戴的一串珠宝,值得七个王国的全部财产”。(《新月集·仙人世界》)这流露着对童话世界的想象和珍视,但现实是,“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宫殿在哪里,它就会消失在空气中的”。现实没有童话,因为它无法存活。尽管如此,泰戈尔依然相信,坚持用一颗诚挚的心播种着对世界的爱,“我的歌将成为你的梦的翅翼,他将把你的心移送到不可知的岸边。”(《我的歌》)这种和谐博爱的审美价值观根植于他深厚的人文关怀。
顾城的诗作清新优美,充满对理想童话的渴望以及生命、自然、情感的自由抒发,既是对往逝岁月的怀旧眷念,也是对真善美归一的向往。《顾城的诗》中“幻影、梦、贝壳、夏蝉、桅绳……”等物象营造了理想诗意的心灵栖息地。《净土》中,“在秋天/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路上落满蓝莹莹的鸟……”是对童话世界的真切想象。《老猫悲喜录》中,“嘻嘻、老猫在海边捉鱼、捉了一万条、一条比一条美丽、老猫好不得意/晤——哇,大海哭了、哭呀,损失了这么多优秀儿女……”更是童趣十足。这些童话诗句同时是对人类命运的谶言。顾城企图在诗中建立一个“太虚幻境”般的童话王国,“我在世界上生活、带着自己的心、吆!心吆!自己的心、那枚鲜艳的果子、曾充满太阳的血液、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春天小夜曲》)他不仅想构建起超越现实的精神现实,还想用理想拯救现实。“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崇高又悲凉,圣洁而有力量,此时,孩童的稚语比成人的理论更震撼人心。顾城习惯沉溺于童年的单纯里,在童话城堡中漫游着、幻想着,又被禁锢着,被他自己禁锢着。对于纷繁的外在世界,他不断拒绝、不断对抗、不愿同流合污,“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生命幻想曲》),坚决固守孩童的纯净阵地,怀揣着涉世未深的童心感受成人世界,道德单纯,黑白分明。个体的存在状态与理想的追寻一直是他自我剖析、精神审视的重点,他自称“被妈妈宠坏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任凭用自己的想法去编织自己的梦和自己的城,这份倔强执著也正是一种魅力。
这份“童心”不仅是孩童的幼稚的心,也是未经污染的本心,是人类的财富。正因为人在现实中孤独、寂寞、游离,所以才需要通过童话对世界进行想象,构筑起超越现实的心之栖所。诗歌与童话本就贴近,诗歌创作需要强大的个性解放与心灵自由支撑,而童话中无边无界的想象驰骋以及现实与幻境的自然跨越也正符合诗歌创作的本质要求。泰戈尔和顾城的童话书写体现着童年经验的美好默契和童真个性的率性自然,不仅仅是对童年记忆和品格的直接表达,更承载着丰富自由的想象空间,形成一种诗意的呈现和童真童趣的自然流露。孩童视野的童话书写并不浅易、庸常,而是现实重荷下困窘不堪的人们缓解沉重压力、寻求精神宁静、获取人文关怀的一剂良方,这种自由想象和童真本心正成为理想的愿望和方向,使人们归省自身。由此,童话书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其内在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力量对当下社会语境更具有一种警醒与救赎的意义。
二.死亡意识的叩问
“死亡”是文学永恒的母题,是哲学难解的命题,是古今中外文人作家无法回避的問题。泰戈尔、顾城通过对死亡的深刻探究进行生命的叩问,可以说,死亡意识几乎贯穿他们的诗歌写作生涯。他们的人生体验和哲学认知赋予死亡意识高级的美学价值和哲学意义,使死亡意识完成了对生命限制的超越。
泰戈尔在诗歌中倾诉、思索着死亡。“我知道白昼即将结束,也知道总有一些剩余之物。情歌住在梦中,微弱的余音,在残夜消逝。”(《唢呐集·终结》)通句没有“死亡”字眼,但“残夜”显然与死亡相伴,人们可以不自觉地体会出其间意味。死神是重要的死亡意象,“无聊时日的光华,我知道有一天曾经,贷款给我的双眼,神王,如今你提出偿还的要求,债总是要还的,这,我很清楚,可你为何此刻就会夜晚蒙上黑影”。泰戈尔深知死亡的意义且以感恩的态度来歌颂。“啊,我这一生的,最后完满,死亡,我的死亡请对我讲”,这是《献歌集》对死亡的赞美,泰戈尔的灵魂在其中得到升华。
顾城在人生创作中经常提到死亡,逐步形成了鲜明的死亡意识。他13岁时写下“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虽没有“死亡”二字,但稚嫩的心灵早已洞悉到美的理想终将破灭;17岁时写下“让死/来麻醉/我翻滚的心灵”(《雨》);之后“死亡”不断涌现:“我将死去/将变成浮动的谜/未来学者的目光/将充满猜疑。”(《遗念》)他既悲叹固有一死的命运,也亲身感受着走向死亡的绝望与虚妄。他好像对自己的死亡早有预判,“是的/我不用走了/路已到尽头/虽然我的头发还很乌黑/生命的白昼还没开始。”(《就义》)他呼唤死亡、崇拜死亡。当理想遇到偏执、天真遇到绝对,现实外界的压抑与极端自毁的力量相互冲击,他没有办法解决生命的矛盾,没有办法对抗现实,没有办法改变世界,没有办法在现实中实现自己,“乌托邦”之梦自始至终无法到达,生的路彻底断裂,只能用肉体的死亡来拯救精神的生命,顾城用生命来写诗,最终以死亡完成了生命之诗。
泰戈尔、顾城的死亡意识源于他们人生情感体验和深层心理,生存环境、自身经历和哲学思想都是促使其死亡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童年经历对人的个性、思维影响重大,痛苦的体验作用更甚。泰戈尔13岁时就亲眼看着最亲的母亲离世,过早近距离地接触死亡给他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痕。顾城生长于文革,目睹了残暴与血腥,承受着打击与压抑,由此只想守护内心净土,躲避狰狞的纷争与喧嚣。童年痛苦经历难以忘怀、排遣,诗歌写作也难以摆脱其中影响。除此之外,泰戈尔和顾城的死亡意识都浸透着原始的自然观念。泰戈尔从小深受印度“梵我合一”的神学宗教思想支配,强调内在灵魂,忽视外在肉体,认为人之生命只是宏大宇宙的一瞬,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从容地面对死神,生命反映死亡,死亡不朽、通向神灵,主张超越死亡,使自然与人形成统一,使生命得以完整完美。顾城在创作之初就将自然作为创作源泉,他欣赏自然万物有灵,与自然交流对话,渴望融入“回归自然”的忘我境界,渴望拥抱“人之初”的自然状态,后又把自然上升到哲学高度并命名为“自然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生死自然”。由此,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在他们的自然哲学中实现了融通。
诗人对死亡的理解与认识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感悟与探索,泰戈尔、顾城的死亡意识蕴涵着对死的态度和生的思索,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意识,已经成为生命观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惧怕死亡到不畏惧死亡,从接受死亡到品味死亡,死亡逐渐变得与生命同等重要,并得到了平静、坦荡与超脱的对待。这种“否定——肯定——超越”是生命与死亡从矛盾对立到圆满统一的进化过程,死亡最终成为生命圆满的仪式和另一种价值的实现,也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三.现代主义的诉说
泰戈尔、顾城的诗歌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因素特征,其创作的思维倾向和表达方式都主动或被动地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在艺术表现上,其诗歌的象征、内向化等就有现代主义的审美意味,但是,他们所呈现的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在认知观念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对我们深入诗人内心、探索诗歌真谛具有一定价值。
象征是西方现代主义的重要艺术手法,泰戈尔和顾城诗歌的象征是经由自己选择的、带有个人色彩的、具有暗示性的象征。泰戈尔的诗歌通过寓言象征来表达难以言说的内容。其宗教抒情诗中的“神”就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本质上象征着真理、光明、自由、理想等,泰戈尔将其化为现实生活的人或物,比如父亲、情人、太阳、清风,这些日常事物都是对“神”的形象化表现,也使“神”有了具体而鲜活的形体和生命。朦胧诗通常被视为现代主义诗歌,顾城作为代表诗人自然离不开象征手法的运用。在《远和近》中,他用“我”、“你”、“云”的关系象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走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他在窗帘后面/被纯白的墙壁围绕/从黄昏迁来的野花/将要变成另一种颜色。”(《我们去寻找一盏灯》)这里的灯极富象征意义,暗示着黑暗的存在,顾城习惯用矛盾的、美丽的意象证实或证伪现实的黑暗与光明。
西方现代主义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向内转”,即由外在的客观模仿转向内在的主观表达。泰戈尔和顾城的诗歌都有现代主义的主观表达。泰戈尔十分重视对人内心世界的关注,“我的世界是我的,它的成分是我的心灵。”“心灵世界一直为表现自己而做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此,人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文学的创作。”这些都是其内倾性创作的理论主张。顾城在《感觉》中写道:“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这是典型的主观感觉;《眨眼》中,在喷泉游动的“彩虹”,在教堂栖息的“时钟”,在银幕绽开的“红花”,“一眨眼”瞬间,变成了“蛇影”“深井”“血腥”,这些都是诗人刹那间的幻觉,是错误年代里的错觉,实际反映了黑白颠倒的丑恶现实和被其扭曲的变态心理。
泰戈尔、顾城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有相通,但也有差异。现代主义通常把作家的主观感受抽象概括成一种类的特征,上升为一种本质哲学,如卡夫卡的“异化”、艾略特的“荒原”。顾城诗歌中对“童话世界”的追求就具有这种抽象的理念特征,它既是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诗人生存哲学的表征体现。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的是,顾城对“童话世界”是深信不疑且执着追求,而西方现代主义秉持的却是对理性与信念的怀疑,就此而言,顾城的感受不完全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感受,这种变异正是二者在认识世界上的不同。泰戈尔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其创作年代正是现代主义为主潮的时代,与时俱进的泰戈尔不自觉会受到影响,但其在思想理论上是拒斥的。泰戈尔始终站在“文学是人学”的人文主义立场,否定现代主义的非人性化、非理性化,并视之为病态的文学现象。他在《文学的道路》中说,“总有一天,心灵会康复,人的永恒的本性会复归,那时简朴的享受的良辰吉时又会到来,那时文学抛弃短暂的现代主义时髦东西,以真挚感情与永恒的文学相遇。”①真正的現代不是形式的玩味,而是心灵与自然的接近,泰戈尔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不无偏颇又不乏深刻。
泰戈尔、顾城的现代主义对诗歌形式主体和诗人本体具有重要意义,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泰戈尔作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诗人、泛爱主义者,借现代主义更真实地反映当时殖民残暴统治的国家忧患创伤,表达对民族、亲人、自然、儿童的爱。顾城借现代主义控诉着对中国五十至七十年代直白浅显诗风的不满,希望将诗歌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推动诗歌回归纯粹。他们笔下的现代主义有着内容与方法、动机和行为、思想与事物的和谐,这既是诗歌创作的境界,也是理念追求的目标。
泰戈尔与顾城是认真的,是天真的,也是真诚的。他们在诗中真正融进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写下了反抗与软弱、美丽与神奇、探求与徘徊、解脱与矛盾,记载了缕缕思绪、心灵历程与深厚慰藉。同时也证明,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诗歌话语,每一个时代的诗歌话语都随着时代不断流转,这个过程需要每一个诗人主体的融入、参与,才能使诗界保持鲜活的血液,才能使时代进程不至于走向精神匮乏。
参考文献
[1]刘安武,倪培耕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顾城.顾城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泰戈尔.泰戈尔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4]彼得.福克纳.现代主义[M].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5]许艳.顾城的死亡意识[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3).
注 释
①刘安武,倪培耕等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2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