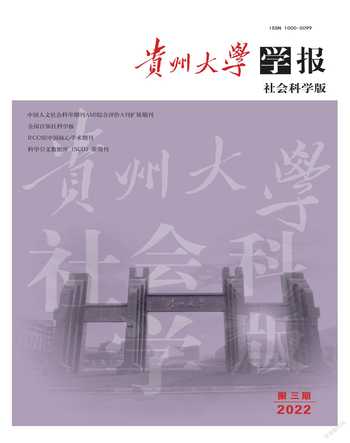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2022-05-25秦浩翔
摘要: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关键词:广西梧州;边疆重镇;国家整合;区域开发;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91/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3-0082-11
广西梧州地处南疆,历史悠久,素有“千年岭南重镇,百年两广商埠”之称,对华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梧州地区军事、社会、经济等问题已有诸多成果①,并且认识到梧州为明代军事重镇和清代商业重镇,然而对于梧州如何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业重镇”则缺乏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其实,这一演变过程不仅源于梧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同时也与明清时期西江流域的人群互动与国家整合等问题密切相关,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以秩序控制与经济开发为中心,对梧州地区②进行长时段考察,揭示其15-18世纪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
一、明代中期地方动乱与梧州军事地位的提升
明代中期,广西大藤峡“猺乱”③爆发,对梧州等周边地区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自宣德年间始,广西浔、梧等府“蛮寇作耗,攻劫乡村,官军不敷”[1]309。正统年间,“猺乱”日益严重,正统五年(1440)十月至次年二月,大藤峡“山贼时常出没”,流劫藤、容等县,“被其杀死及伤者多,又掳去男妇六十余人,牛畜近百,强占近山一带百姓纳粮田地耕种,抢劫不已”[2]52。除大藤峡地区“猺乱”频繁外,两广界邻地区同样爆发动乱。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广西总兵柳溥奏称:“岑溪及广东泷水二县,猺贼骆宗安等二百余人,劫杀岑溪县连城乡民,死伤者五十余人,复火其仓。”[1]1703广西动乱的不断加剧引发了明英宗的重视,他严敕地方官员必须“夙夜用心,以求安辑。”[2]52正是地方动乱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正统年间,明廷大量征调桂西狼兵进入梧州地区屯戍驻守,容县、兴业、北流、陆川“俱有狼总统领。”[3]卷28同时,梧州地区的城池得到大力整修。总兵柳溥充分认识到城池对于御寇的重要性,指出梧州等地“猺獞夷人叛服不时,所赖者,城池濠堑耳”,因此“每于农闲时,往来巡视,督工修筑,庶边鄙有备。”[1]2179正统五年(1440),因“怀集守御千户所逼近贼巢”,广西按察司胡智“请甓其土城”[1]1257,正统十四年(1449)又“请筑以砖”[1]3474。正统十年(1445),梧州府城毁于战乱,次年知府诸忠即加以重修[4]233。同样为了抵御动乱,正统十一年(1446)广西大量增设巡检司,其中梧州地区共计二十七所[1]2907。
正统末至景泰初的北虏南乱对两广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黄萧养叛乱使朝廷意识到两广地区军备松懈、事权不一的状况;土木堡之变则迫使朝廷召回各地资历较深的高级武将,以填补京营将领损耗的空缺,两广镇守工作,则由资历较浅的将领负责[5]。景泰年间,广西蛮寇行劫郡县,广东、广西总兵互相推托,拥兵自卫,致使寇乱蔓延广东。鉴于两广官员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景泰三年(1452),明廷遂命右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但此时总督属临时差遣,事毕即还朝[6]。王翱回京后两广官员之间的事权问题又再次显现。秦浩翔: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英宗复辟后召回各地督抚,两广随即动乱频传[5]。天顺年间,大藤峡及周边地区的动乱愈演愈烈,且波及甚广,梧州地區的城镇更是被多次攻破。天顺二年(1458),藤县地区蛮贼“不时出没,攻劫县治,杀掳人民,烧毁房屋”[1]6137。天顺三年(1459)四月,梧州、浔州等地“猺、獞、苗贼攻劫乡村、城市,杀虏军民共一千九百余口。”[1]6404同年五月,“广西流贼越过广东,攻围肇庆等处州县,劫掠乡村,为患不已”[1]6415,六月,“流贼攻破容县,屠杀居民,劫掠官库”[1]6424。天顺四年(1460)二月,“强贼攻梧州府,哨守指挥萧瑛逾江避之,贼遂攻破城池,杀虏官民及官库财物”[1]6544。天顺六年(1462),两广总督叶盛认为动乱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在于“两广将官,各无统摄”,且“谤毁日增,遂成嫌隙,尔我不顾”,因此奏称:今臣等看得广西梧州府是两广交界地方,北抵曾城,南抵交趾,程各半月,东抵广东省城,顺流而下,仅逾七日,最为紧关。中路控扼两广喉襟之地,流贼往来,必由梧州北南两江水面偷度。因无将官重兵总制其间,又因先年原守广西地方,贵州、湖广官军一万五千俱不赴调,旧守营堡,俱各废弃,以此不能守把,贼人肆志。
伏乞皇上特勅该部会议,合无于梧州立为帅府,挂印征蛮将军总兵官镇守,节制两省,会官专管军马盗贼事务……如此庶得耳目一新,号令丕变,将权归一,地方行事才得尔我相和,彼此相顾,实为经久便益。[7]然而,叶盛的提议并未被朝廷采纳,反而在不久后遭人弹劾而去职,但梧州的战略地位已初步显现。天顺七年(1463),梧州地方秩序再次遭到严重冲击。四月,“流贼攻破岑溪县及郁林州,戕杀官民,剽虏财畜”[1]7045,其后“破怀集县及守御千户所,烧毁公廨,劫去官民财物”[1]7171。十一月“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入府治,劫官库,放罪囚,杀死军民无数,大掠城中”[8]27。鉴于天顺末年,以侯大狗为首的大藤峡“猺乱”越发不可收拾,成化元年(1465)正月,明廷“以都督同知赵辅为征蛮将军,都督佥事和勇为游击将军,擢浙江左参政韩雍右佥都御史,赞理军务”,率兵进剿大藤峡,取得大胜,“斩首无算”[9]。大藤峡之役告捷后,韩雍留任两广,继续总理军务。考虑到“猺獞之性,喜纵而恶法,惊悸之后,易动而难安”,为巩固胜利,韩雍决定继续加强大藤峡周边地区的军事控制。成化二年(1466),韩雍奏请设立五屯屯田千户所,以千户李庆为之酋帅,以僮首覃仲瑛为之吏目,“筑城分哨”,加强梧州西北部的军事防御,借僮人之力抵御瑶人[10]。同时,韩雍还对梧州地区的城池进行大力整修。成化二年(1466),韩雍将郁林州城“重加筑砌”,“筑栏马垣,立瞭望楼十、鼓楼一”,并新修博白县城门楼,委知县谢铉用砖包砌藤县县城,委县丞孔舒修筑北流县城池。成化三年(1467),韩雍将府城“增高一丈,造串楼五百六十九间,城下设窝铺三十六间,宿守夜军士。浚濠深三丈,阔一丈,五尺内外皆树木栅”。成化四年(1468),又将怀集县城“砌以砖石”,并修建府城“东、南、北门瓮城,重建五门楼、钟鼓楼”[4]233-242。
通过韩雍征剿大藤峡的成功经验,两广地方官员已充分意识到事权统一对于秩序控制的重要性,纷纷奏请设立总督,开府常驻地方,而梧州则是最为理想的地点。成化四年(1468)三月,韩雍即奏称:“两广地方广阔,军民事繁,一人不能遍历,乞各增文职大臣一员,分理巡抚,仍命文武重臣各一员,专在两广接界梧州府驻扎,提督军务,总制军马”[8]1064。但未及朝廷回应,韩雍便于成化五年(1469)春,以丁忧去职,此后“贼势复张”[8]1414。是年冬,广东巡按监察御史龚晟、按察司佥事陶鲁、林锦再次提议:“两广事不协一,故盗日益炽,宜设大臣提督兼巡抚,而梧州界在两省之中,宜开府焉。”“于是起复(韩)雍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平江伯陈锐挂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与(陈)瑄开府于梧”[11]。成化六年(1470),总督衙署建成,两广总督常驻梧州[12]。开府之后,韩雍进一步加强梧州的军政建设,使其军事地位继续提升。成化六年(1470),韩雍在梧州地区“设营堡三十余处,府境道、府江道皆置哨守,调广东各卫所旗军一万员名,分戍各营堡江道,设坐营司统督之,并征派广、肇、韶三府属粮米五万石,解梧以备行粮。”[13]卷10此后,广东班军戍守梧州成为定制。同时为了扩充军饷来源,韩雍请立水关,“榷盐、木诸贷,以充军实”[13]卷4。
韩雍大征之后的数十年间,大藤峡地区的局势相对安定,然而至正德、嘉靖年间,动乱再起,梧州地区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再次加强。正德年间,明廷再度征调大量狼兵至梧州屯戍驻守,崇禎《梧州府志》载:“正德间流贼劫掠,调狼人征剿,乡民流徙,庐亩荒芜,遂使狼耕其地,一藉其输纳,一藉其戍守。”[4]128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平定瑶乱后指出,藤县五屯“正当风门、佛子诸夷巢穴,最为要害”,“宜设一镇,增筑高城,而设守备衙门,取回五百兵,分调哨守”[14]2200。此议为明廷采纳,梧州西北部防御再次得到加强。同时,王守仁奏请对桂西狼兵实行“更番戍守之法”,其中“戍梧者四千名”,来自左右江各土司,“一年一戍,周而复始”,“以其有头目管之,曰目兵”[4]689。此后,目兵戍守梧州成为定制。成化初年,明宪宗尚称梧州为“蕞尔小城”[8]27,及至嘉靖中期,梧州已是岭南军事重镇。嘉靖《广西通志》称:“(梧州)地总百粤,山连五岭,盖二广上游八桂门户也,故于此建节镇,则南援容邕,西顾桂柳,东应韶广,北可坐制阳峒诸夷,而安南无宿忧。”[15]卷2杨芳在《殿粤要纂》中写道:“梧踞五岭之中,囊九疑、三江之槩,为粤东西咽喉。西枕藤峡、八寨,诸酋出没无时。东接信宜、封川,鼠窃狼吞,窟穴其间。曩屡勤师出征,旋服旋叛。迄今百有余载。山防江哨,棋布星列,总一郡十属,所戍守军兵,凡一万有余。盖矻然称重镇矣。”[16]但同样指出:“第顷来帑藏浸耗,内地虚旷,岁登物产不供,或半需于邻,或半需于商,小大坐食,卒惰而将骄,客兵多不用命,识者谓此非细故也。”[16]嘉靖四十五年(1563),苍梧道佥事林大春亦称:“梧州为东南重镇,实两省冠裳之会,三军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鄙,非通都大郡。供俗尚简朴,无高堂华屋之观。”[17]
可见,此时的梧州已为“重镇”,但主要指“军事重镇”,其社会经济尚难称繁荣。原因在于连年用兵,使梧州财政匮乏。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即指出,自征剿思田叛乱以来,“所费银米各已数十余万”,“今梧州仓库所余银不满五万,米不满一万矣!兵连不息,而财匮粮绝!”[18]张瀚亦称,“招者履叛,兵连祸结,征调烦劳,财力匮竭”[19]。另外,府江、西江两大水路交通要道动乱频繁,严重制约了梧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蒋冕在《府江三城记》中说道:“自桂之梧,未有不经府江者。其江之流,洄洑湍激,乱石横波。两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为猺人所居,据险伺隙,以事剽劫。官舟商舶往来,为所患苦,盖非一日。”[20]苏濬在《两广郡县志》中亦指出:“(梧州)右枕藤峡、八寨,诸酋往往出没;左接粤东,犬牙相结,而狐穴狼窟,时跳梁其间,烽火相望,刈人如蓬藋然。于是闾里萧条,沃土为墟矣。”[21]
综上分析,明代中期两广地区动乱频繁,为了统一事权、协调资源,两广总督之设势在必行,梧州因其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开府的最佳地点,并在一系列军事政策的影响下逐步成为岭南军事重镇,发挥控扼两省的关键作用。然而连年战乱,军费浩繁,交通不畅,梧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二、明代后期梧州地区的秩序控制与社会转型
嘉靖中期至隆庆、万历年间,是梧州地域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随着大藤峡“猺乱”的逐渐平定,以及两广界邻地区社会秩序的日益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有所下降,行政事务的重心开始转向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
1.两广界邻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梧州军事地位的下降
王守仁大征之后,西江上游地区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梧州地区的军事任务也由征剿大藤峡转变为招抚两广界邻地区的“化外之民”。自嘉靖中期开始,明廷调动军队,增设兵营,对梧州山区的非汉人群进行征剿或招抚,将其编入户籍,并征收赋税。苍梧县罗峝、思马等处瑶人“先年纠合焚家、东安等猺流劫,嘉靖十年编立排甲,耕佃”,石砚瑶人居两广交界,“嘉靖年(间)愿来属苍梧,约八百余人”。万历初年,怀集县瑶户作乱,官府“大兵剿灭”,并将其抛荒田地“归官招种”,纳税征粮[13]卷8。岑溪县六十三山“与罗旁接壤,猺獞啸聚为患”,万历五年(1577),“贼首潘积善等畏威求抚,愿归地输粮”,总督凌云翼“设指挥千户五员,分兵屯守,以防芽摩。”[22]1509万历六年(1578),容县、苍梧县均有大量瑶人为明廷招抚。容县,三山、山心等“皆东瓜山所属,约五十余家,山巢崎险”,“万历六年,曾廷旺始愿输田赋,兴猺学”;山塘、党入等“皆横山所属,约三十余家,先年流劫,万历六年,刘德厚始愿编户入赋”;庆垌、柯木等“皆石羊山所属,几二百家”,“万历六年输赋”;都盘、六壬等“皆鸡笼山所属,约六十余家”,有酋目骆廷凤“倚山剽掠数年,万历六年始招服”[13]卷8。苍梧县,埇汉、员塘等处瑶人“叛服不常”,“万历六年设七山镇弹压猺峝”,老君峒、六寨等处瑶人“时与深源、焚家、北佗为害,后立大塘营弹压之”。万历八年(1580),岑溪县筑大峒城,“招獞目韦月统耕兵三百名,分十四营”,“屯耕把守”[23]卷2。万历九年(1581),岑溪县六十三山诸瑶“仍负固不服”,明廷筑城,“设连城、北科等大营”,“以浔梧参将握重兵弹压之”,并“招獞民百余人耕守”。万历十二年(1584),怀集县于城西八十里立金鹅营,设耕兵防守[13]卷10。万历二十三年(1595)冬,岑溪县再度发生动乱,粤东浪贼数百潜入七山,“诱诸猺劫掠”,“诸猺复仇,尽杀乾厢獞人,屠其村,复乘势剽掠”。督臣陈大科“大破之,而猺患乃熄”[13]卷8。其后,陈大科提议:扎信地以重弹压,将浔梧参将驻扎大峒;分割山界以便管辖,上七山专隶岑溪,下七山改隶藤、容二县;拓修城垣以资保障[22]5751-5752。梧州地区的社会控制进一步加强。
随着浔、梧地区社会秩序的不断加强,两广动乱的核心区域发生转移,梧州军事重镇的地位开始下降。嘉靖中后期,西江上游的“猺乱”虽基本平定,但东南沿海地区却屡遭倭寇侵扰,自嘉靖四十三年(1564)始,两广总督吴桂芳即频繁移巡肇庆总督行台。隆庆年间,广西桂林、柳州等地一批士大夫身居要职,极力倡议明廷大征古田,要求两广军门分割资源,解决桂东北地区长期存在的“獞乱”问题,结果朝廷在桂林专设广西巡抚,使其取代梧州成为广西军政中心[24]。两广总督移驻肇庆是梧州军事地位下降的重要标志,万历七年(1579)十一月,总督刘尧诲大规模重建肇庆总督行台,大概于万历八年(1580)春季完工,两广总督府址正式由梧州转至肇庆,两广防务重心亦随之东移[12]。
长期以来,梧州军队逃亡、耗饷过多等积弊一直未能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梧州班军及其军饷均来自广东,直接影响到广东地区的利益,因此随着梧州军事地位的下降,不少地方官员,尤其是广东官员开始主张裁撤梧州驻军。隆庆年间,广东巡按王同道已有裁撤梧州班军之议,指出“督府开镇于梧”,而广东“共拨官军二班,计一万余员名哨捕”,共派“本折粮五万石,起解梧州广备仓,以备行粮之用,度东资于广西甚侈”,因此提议从班军中“摘留二千名,赴督府输班,其余发回卫所,粮米扣留三万五千石,以济广东军饷之用”。时任两广总督张瀚等人反驳道:广东官军戍守悟州,非守梧州也,所以守广东之藩篱……守广西而后广东可固,守藩篱而后门庭可安。其势真有不可已者。不然广西猺獞千穴,土狼万族,山深箐密,境壤相错,设无梧州重镇控扼之,朝发巢而暮践郊矣!恐不止海寇之纵横已也。广东虽欲晏然,可得乎?此为广东计,亦有不得不然者。[25]张瀚的奏章送达朝廷后即离任,继任总督李迁考虑到“梧州地方虽属广西,实两广要害,故设立军门”,而“广东师旅繁兴,奏议撤兵减粮,殊非得已”,因此提出折衷办法,“请令戍兵如旧,其仓粮暂以三万石解梧州,余二万石留广东,俟二年以后,仍复原数”,此议为朝廷采纳[26]1427-1428。万历十五年(1587),免戍之议再起,时任总督吴文华复称,“两广相为唇齿,梧郡实为咽喉”,“东省兵防已密,无庸撤回,梧州所军虚弱,不得不籍东军,还以仍旧为便”[4]696。及至明末,班军俱“奉督院牌拔”,多寡不一,已无常额,“大略半守梧镇,半守江道”[4]699。万历年间,除班军外,目兵同样被裁减。万历十七年(1589),总督刘继文“题减一千名”,万历三十二年(1604),总督戴燿“题减一千名”,万历四十五年(1617),左江道“抽四百名,防守上思州地方”,万历四十八年(1620),总督许弘纲“议全撤,寻复议调”[4]689。
隆庆、万历年间裁撤班军、目兵之议,固然与两广地方官员的权力博弈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两广秩序的安定以及梧州军事地位的下降,班军、目兵等戍卫部队已无往昔的重要作用,只是徒耗军饷、徒劳无功。万历末年,同知陈煕韶即评论道:目兵以文成始,班军以襄毅始,当年作法虑自深,长年来习于承平,遂成枝骈……班军在国初其用足恃,沿至今日,市人等耳,其才不足于超距,其伍无禆于干城,计月而来,更番而去,徒縻官钱数万,苟欲简而练之,何似以官钱募市人,犹省往还之仆仆也。余谓班军则去之便然,要折冲樽俎,安危有备,毋徒纸上陈言,积弊日深,捉襟见肘,此其时也欤。[4]701-702崇祯《梧州府志》的作者谢君惠亦称:猺峝叛服无常,然其蠢动,必有奸人为响导焉,今咸就则壤矣。而七山、五屯、北科等营犹陈兵以戍,月费饷不赀,而半以虚伍冒也,一旦有急,保其不目逆送盗耶!汰冗为精,转弱为强,可以固圉,可以省饷,斯筹国一便画焉,斯今日之亟图也![4]128此外,明后期梧州卫所旗军的情况亦不乐观,万历年间总督吴文华即已注意到“梧州所军虚弱”的现象。崇祯《梧州府志》亦记载:梧州所原额一千五百七十四名,崇祯四年一百八十四名。
五屯所原额八百六十四名,万历间六百五十一名,今见在六百三十四名。
容县所原额一千二百六十三名,万历间一百五十八名,今见在一百三十八名。
怀集所原额一千三百四十名,万历间二百五十二名,今见在二百五十四名。
郁林所原额一千二百六十五名,万历间一百零二名,今见在八十七名。[4]667-668可见,万历年间梧州卫所旗军的额数已较原额大为减少,且存在大量兵士逃亡的情况。
2.梧州地区的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
嘉靖中后期开始,随着大藤峡及府江流域的动乱逐渐平息,梧州行政事务的重心由地方秩序控制转向社会经济发展。明代两广食盐贸易兴盛,以官营为主,梧州是广西食盐囤积之地,广东盐商先将盐溯西江运送梧州,然后散销各地,因此盐税是梧州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27]。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将原本行销广盐的湖广衡州、永州等地改行准盐。为确保梧州的财政收入,嘉靖四十四年(1565)两广总督吴桂芳上疏朝廷,请将湖广衡、永二府复行广盐,“庶军民便于得盐,商贾利于通济,而两广军饷亦赖之裨益”[28]。万历二年(1574),应两广总督殷正茂所请,“梧州府添设副提举二员,照例请给关防常轮一员,前往广东买盐运回梧州,候桂林船到转发,仍于桂林、梧州二府原设管粮通判,令其兼理盐法”[22]782。
梧州地区气候炎热,加之百姓习惯结竹为居,因此火灾频仍。然而嘉靖以前地方官员忙于军政事务,火灾问题并未得到足夠重视。嘉靖中后期,随着梧州城军事地位的弱化,社会经济发展成为施政重心,火灾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9]。嘉靖二十四年(1545)“梧城大火,二十五年又火,二十六年知府翁世经修火墙甃街道”。嘉靖四十四年(1565),“梧城外大火”,次年夏六月“又大火,民舍几尽”。总督吴桂芳等“合议添补火墙三道,共十三道,令通衢尽易陶瓦”[13]卷24。万历年间,地方官员开始重视仓储的建设。怀集县仓储得到大力整修,万历十年(1582),知县林春茂,创设义仓,次年新建预备仓二间,万历四十七年(1619),知县谢君惠重修预备仓“厅三间,东西厫四间,又添建一间”[30]卷2。万历末年,容县知县区龙祯建常平仓二十七间[3]卷10。万历四十八年(1620),梧州知府陈鉴“于阖属州县各发银平籴谷五百石,贮预备仓,以备赈济”[30]卷2。
同时,嘉靖末年至万历年间,明廷开始加强府江、西江水陆交通的疏治,为梧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容江“当梧郡西南孔道”,“诸滩舟行甚險,猺贼藏匿林菁”,“钩劫无已”,嘉靖三十九年(1560),兵巡佥事章熙“亲诣各洲,刊木掘根”,疏浚河道,“贼遂远遁,往来民商赖之”[13]卷24。万历十六年(1588)“从两广督臣吴善请”,“改平、梧二府清军同知各加江防职衔,府门等五驿为水马驿。”[22]3702万历二十二年(1594),“从抚按陈大科、涂宗濬请”,“开府江,桂林、苍梧水陆险阻,斩木划石,决淤疏湍,俾猺夷不得出没丛薄,江流无冲激之患。”[22]5170苏濬针对万历年间梧州地区的社会治理说道:“今上神武震于遐方,于是辟榛涂为周行,变丑夷为编户,管垒基置,材官星列,而梧人始获安枕以嬉。”[21]《明史》亦称:“自数经大征后,刊山通道,展为周行,而又增置楼船,缮修校垒,居民行旅皆帖席,猺獞亦骎骎驯习于文治云。”[31]
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水陆交通的畅达,使梧州逐渐向商业城镇发展,及至明末,梧州城已有不少外省商人,且多为富商,崇祯《梧州府志》载:“客民闽楚江浙俱有,惟东省接壤尤众,专事生息,什一而出,什九而归。中之人家,数十金之产,无不立折而尽……盐商、木客、列肆、当垆,多新(会)、顺(德)、南海人。”[4]133综上分析,明代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日益稳定,梧州社会开始转型,原有军事地位逐渐下降,而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得到重视,逐渐由“军事重镇”向“商业重镇”过渡。
三、清前中期梧州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清初,南明抗清战争与“三藩之乱”使广西再次陷入动乱,梧州因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焦点。至“三藩之乱”平定,广西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明清易代之际,梧州大量卫所军户借战乱之机,躲入两广交界的山区,以此逃避赋役,并时常引发地方动乱[32]。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皇帝即指出:“猺人所居之山,通连广东、广西、湖广三省,林木丛密,山势崇峻,向来持此险僻,顽梗不驯。近复突出抢夺村民,杀害官兵。”[33]卷207因此清前期,地方官员仍需动用军事力量将这些“化外之民”重新纳入国家权力体系。雍正年间,孔毓珣、金鉷等地方大员大举征剿“猺獞”,使梧州山区得到有力控制。乾隆《梧州府志》将《猺獞》附于《户赋》之后,并称:“猺人、獞人尽服畴食德之民矣,用并附载。”[13]卷首作者还在《猺獞》结尾感叹道:自是(雍正年间大征后),诸猺、獞莫不翕然怗服,革面洗心,土田尽隶版图,耕织无殊编户,愚者荷锄耒,秀者业诗书,泮宫芹藻之间,彬彬称弟子矣。遍历四境,衣服、室庐、饮食、礼节,其人俱同一色,为蛮为民无非族类,一道同风,于斯为盛,猗欤休哉!载笔至此,而不禁欷感叹于王化之及人者,深且远也![13]卷8也正是随着地方秩序的日益稳定,梧州地区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开发。梧州地区“俗尚简朴,务本者多,逐末者少”[13]卷3,且气候多变,温热多雨,适宜农业生产,加之百姓充分利用水资源,“甃砖以引之曰圳,架竹通之曰笕,树栅畚土以潴之曰陂”[13]卷8,“凡近溪涧之区,可设陂车以资灌溉者,不可胜纪”[23]卷1,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考虑到广西地处边疆,“土壤硗瘠,民生艰苦,与腹内舟车辐辏,得以广资生计者不同”,清廷亦对广西百姓予以特殊恩惠,将“康熙十六年通省钱粮、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钱粮”,“次第蠲豁”[33]卷160,使战乱后的广西社会得以尽快复苏。乾隆《梧州府志》称:“梧界高山,大川平原丛薄,间或数十里无烟户,地本旷也。近自久濡圣泽以来,井庐日增,生殖滋广……其乡一望,村墟熙皞成象。”[13]卷2乾隆《北流县志》亦“按”:“自康熙二年以来,生齿日蕃,恭遇圣明,爱养苍生,谆切劝垦,民皆踊跃开荒,昔为弃土,今则大半熟田矣。”[34]卷1反映出在清王朝的带动下,梧州地区的乡村和农业得到大力发展。
米粮是梧州地区的重要农产品,尤其是苍梧县,素为鱼米之乡,所属南五乡、东六乡,连城厢,共十二乡,物产丰富,尤其以谷米为最[35]40。加之清代广东严重缺粮,而梧州地处西江要道,与之界邻,成为供应广东谷米的主要地区[36]。苍梧戎圩每日有六七十万斤谷米销往广东佛山等地,“粜不尽戎圩谷,斩不尽长洲竹”的俗语在乾隆时期广为流传[35]39-40。也正因如此,清代梧州地方官员尤为重视仓储问题,较之崇祯《梧州府志》,乾隆《梧州府志》新增《积贮》条目,并引言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积贮者天下之大命,而在边土为尤要。两粤地相唇齿,东人之粟仰给于西,梧州则又比邻之挹注也。故常平、义仓、社仓而外,兼设备东一款。处漏巵之势,而谋备豫之藏,仓储重攸繁矣。”[13]卷9
明末至清中期,随着东南省区人地矛盾日益激化,大量外省移民向广西迁徙,梧州即是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37]。移民的大量迁入,推动了梧州地区的山林开发和经济作物的种植。岑溪县,大峝山颠种植茶叶,“叶粗味厚,故有峝茶之名”,漆山“各乡有之,干者入药”。[13]卷3藤县土人“沿江种甘蔗,冬初压汁作糖,以净器贮之”[38]卷5。容县物产尤为丰富,花生“去壳榨油,品在茶油、菜油之上”,苎麻“取皮如筋者,可绩布控线”,芝麻分黑白二种,“取油以白者为胜,服食以黑者为良”[3]卷5。木材成为梧州地区的重要物产,多用于筑室制器。藤县朔木、杉木、茶木各乡广植繁盛,“人稠用阁,起造多资于此焉”[38]卷5。容县,杉木“纹细条直”,“南人屋栋、船材及一切器物皆取资焉”,樟木“纹细质坚,可雕刻花鸟、造船、作联扁”[3]卷5。许多经济作物的种植呈现商品化趋势,推动了梧州商品经济的发展。藤县蓝靛“多在山种之,其利甚溥”[38]卷5。乾隆年间,岑溪“各乡近山处皆植”茶叶,“谢孟堡山场所植尤伙,远近贩鬻,民资以为利”[13]卷3。容县“土人挖甜竹、大头竹之嫩者,晒干为笋脯,贩卖出境”,黄杨木亦可“贩卖出境,颇食其利”,沙田柚“秋后金丸满树,获利颇厚”,铁力木“为南方美材”,“广州人多采之制几案等器”[3]卷5。容县外来移民以竹造纸,“火纸以丹竹为之,福纸以蒲竹为之”,“康熙间,闽潮来容,始创纸篷于山中”,乾隆年间“有篷百余间,工匠动以千计。”[13]卷3“郁林土产除五谷外,以蓝取靛、花生取油、甘蔗取糖三者为大宗,岁得厚利,茶次之”。郁林蓝靛“与北、陆、兴三县靛,俱从北流江贩运广东,苏杭人通谓为‘北流靛’”,郁林所产茶叶,因“土人不善制之”,故“有远商来收买,焙碾好,始运去”[39]卷4。
自明代开始,梧州即为两广食盐贸易的转运枢纽,清代中期这一地位继续保持并得到强化。乾隆年间,两广总督鄂弥达奏称:广西梧州为通省运盐总汇,盐道驻扎桂林,相距既遠,又因责任较繁,未能离省,一切转运盐包、给发水脚、稽查夹带,向俱委梧州府同知代办。然究非专管盐政之员,请照广东潮嘉汀赣分司之例,即于梧州府添设盐运分司一员,铸给关防,催征饷税,以专责成,仍归驿盐苍梧道管辖。[40]卷30正是考虑到梧州之于广西食盐运销的重要地位,地方大员奏请在梧州添设盐务官员,“以专责成”。梧州府苍梧、怀集等县有多处矿山,但清前期广西严行矿禁,一直未得到开发[41]。例如,苍梧县之芋荚山“界连怀集、贺二县,并广东肇庆府之开建、封川等处,山路险峻,出产矿砂”[42],雍正四年(1726),即有广东饥民同广西本地百姓潜往偷挖,地方官员担心其“蚁聚无常,贻害地方”,因此“严拿驱逐”[43]。雍正六年(1728),广西巡抚金鉷奏称:粵西一省,田少山多,其山可以布种者,杂粮竹木,罔不随地之宜以尽利。乃有一等不毛之山,顽石荦确,绵亘数十百里,既已农力之难施,复苦材产之有限,独其下出有矿砂,分金、银、铜、铁、铅、锡数种,实为天地自然之利,不尽之载。[44]同时,为了保证地方秩序的安定,“止用本地穷民刨挖、挑运”,“概不用外省流民”[44]。在金鉷的极力奏请下,广西矿禁解除,除梧州苍梧县芋荚山“地形四达,其砂产金”,“独宜官办”,“其余府州,凡有矿山者,俱令商人承办”[45]565-566。雍正、乾隆年间,梧州多所矿山由官府招募商人开采,并抽课收税。怀集县将军山“银、铅、铜并产,商人韩茂亨于雍正七年承认开采”,“照例抽收税课”[45]291。乾隆二年(1737),商人黄丹山“承认试采怀集县属银、铅并产之荔枝山矿厂”,获准开采,并由知县“就近督察煎炼,照例抽课具报”[45]366。同年,商人金在中承认开采“苍梧县之金盘岭金矿,抽收税课”[45]566。清代广西开发的矿产大多作为原料运至广东贸易,以满足广东手工业生产的需求[27]。
随着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梧州地区的墟市数量迅速增长。至清中期,梧州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戎圩是广西最为繁荣的商业圩镇,有“一戎二乌三江口”之称,高州、信宜、罗定、雷州、钦州、玉林、容县、陆川、博白、平南等地商人均到此经商[35]39。乾隆年间的《粤东会馆甲申年创造坝头碑记》称:(戎墟)袤延十里,烟火万家,西通浔贵、南宁,东接肇、高诸郡,故西粤一大都会也。富庶繁华,贸易辐辏,几与粤东之佛山等,故俗号□佛山。凡舟车之络绎往还,皆泊于此。[46]69外省商人会在梧州的繁华市镇修建会馆,“以贮百物,以敦梓谊”[46]69。苍梧戎圩“居货之商以粤东人为最盛”,康熙五十三年(1714),粤东商人捐资将本地关夫子祠更为会馆,“岁时习礼其中,展恭敬之情,序乡邻之谊”。其后会馆又于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五十三年(1788)、嘉庆四年(1790)三次重修。乾隆五十三年(1788)戎圩《重建粵东会馆碑记》称:“吾东人货于是者,禅镇扬帆,往返才数旦。盖虽客省,东人视之,不啻桑梓矣。”[46]71体现出粤东商人的本地化及其对梧州的地域认同。梧州地区河流众多,且气候多变、地形复杂,因此水旱灾害频仍,对商贾经营造成严重影响[47]。外省商人多会修建祠庙,祈求神灵消灾赐福,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当属龙母信仰。至乾隆时期,梧州地区已有多处龙母庙,府城附近即有两处,“一在城西北二里许桂江上”,“一在西南十里长洲尾”,“俱滨江商民虔祀,祈祷辄应”[13]卷7。雍正八年(1730),本地商民“共发诚心,乐为捐助”,对城北龙母庙“重为修葺”,知府甘湛泉亲自撰文加以纪念,并称赞龙母“凡有所求,靡不响应”,对其安定民心的作用予以肯定[13]卷21。
至18世纪,梧州已成为岭南商业重镇,“市中货物盛于他邑,邻封日用所需,皆取资焉”[48]卷32。雍正年间,广西巡抚李绂即称:“桂为省会,梧为通衢,皆商贾凑集”[49]。梧州知府甘湛泉亦称:“梧为西粤要衢,襟连三江,冠盖络绎,行商坐贾往来不绝,亦一大都会也。”[13]卷21广西巡抚陈辉祖在乾隆《梧州府志》序言写道:“梧州粤西一大都会也,居五岭之中,开八桂之户,三江襟带,众水湾环,百粤咽喉,通衢四达,间气凝结,人物繁兴,形胜实甲于他郡。”[13]序
清代以前,梧州地区的民风尤为淳朴,崇祯《梧州府志》称本地百姓“惟知力穑,罔事艺作”[4]131。雍正《广西通志》亦载,梧州“民之近山者樵,近水者渔,有陂池山泽之乐,鲜商贾经营之事,故俗颇淳古,而家少盖藏”[48]卷32。受外省移民的影响,梧州社会风气开始转变。府城附近“商贾辏集,类多东粤人,里民为其渐染,行事渐尚纷华”,“虽僻远乡落,久知以陋习为耻,彬彬日变矣”。[48]卷32梧州地区的语言也受到移民的影响,城郭街市“亦多东语”,乾隆《梧州府志》特意将本地方言与粤东音进行对比,可见粤东音已成为梧州主要语言之一[13]卷3。随着城镇不断发展,经济日益繁荣,民风渐趋奢华,社会教化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乾隆《梧州府志》之《风俗》结语道:志称里人质直好信,士大夫贵节尚气,坊厢之间彬彬称首善焉。奈何风之所移,君子积愒成废,小人积惰成窳。迄今,淳朴之气未散,而鸿钜之光亦未融,俚僿之习未开,而黠猾之风已渐长。夫移风易俗,存乎其人,则所以主持其风会,而齐一其教化者,士大夫之责欤,抑循良者之善治也,将于今日有厚望焉。[13]卷3这段按语不仅道出了梧州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时反映出地方官绅已对此深有感触,对“君子积愒成废”“小人积惰成窳”“黠猾之风渐长”等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后世官员善加教化。
四、结语
15-18世纪,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日益严重的地方动乱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地方官员大力整修城池,明廷大量增设巡检司,并不断征调班军狼兵等军事力量进入梧州屯戍驻守。景泰、天顺年间,大藤峡“猺乱”愈演愈烈,且波及广东,为了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明廷遂设两广总督总领军务,并于成化六年(1470)开府梧州。其后,在韩雍、王守仁等人的提议下,广东班军、桂西目兵(狼兵)戍守梧州成为定制,梧州地区的军政建设亦得到逐步加强。至嘉靖年间,梧州成为岭南军事重镇。嘉靖中后期至万历时期是梧州地域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随着两广秩序日益稳定、大量化外之民被纳入版图,梧州社会随之转型,原有军事地位逐渐下降,而财政、火政、仓储、交通等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由军事重镇向商业重镇过渡。明清易代之际,梧州作为军事要地,成为各方政权争夺的焦点,至“三藩之乱”平定后,地方秩序基本稳定,雍正年间的大征使两广交界的山区亦得到有力控制。明末清初,外省移民大量迁入梧州,推动了山林地区的开发,经济作物得到大力种植,并走向商品化生产,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雍正中期,清廷解除矿禁,招商开采,以尽地利。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梧州地区的墟市数量迅速增长,并形成了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外省商人,尤其是粤东商人,在本地悉心经营,积极修建会馆、神庙,呈现本地化趋势。及至清代中期,梧州已由军事重镇转型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由淳朴渐趋奢华。梧州的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明英宗.勅总兵等官抚安桂平等处地方[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3]易绍德.(光绪)容县志[M].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4]谢君惠.(崇祯)梧州府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5]杨景秀.博弈与平衡:明代两广总督的权力运作[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6]赵克生.经略西江[J].中国史研究,2014(3):23-28.
[7]叶盛.地方事疏[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12.
[8]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2015:571-575.
[10]韩雍.断藤峡疏[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13-114.
[11]应槚,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70:15-16.
[12]吴宏岐,韩虎泰.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3):50-61.
[13]吴九龄.(乾隆)梧州府志[M].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14]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5]林富,黄佐.(嘉靖)广西通志[M].明嘉靖十年刻本.
[16]杨芳,编纂,范宏贵,点校.殿粤要纂[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240.
[17]林大春.肇造全镇民居碑[M]//汪森.粤西文载:第三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89.
[18]王守仁.奏覆田州思恩平复疏[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43.
[19]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4.
[20]蒋冕.府江三城记[M]//汪森.粤西文载:第二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91.
[21]苏濬.两广郡县志[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76-277.
[22]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3]何梦瑶.(乾隆)岑溪县志[M].清乾隆九年刻本.
[24]任建敏.万历本《苍梧总督军门志》中的嘉靖史料考索——兼论明代两广总督地位的变迁与成书因由[J].文史,2021(1):187-205.
[25]张瀚.议复梧镇班军疏[M]//汪森.粤西文载:第一册.黄盛陆,校点.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206-207.
[26]明穆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27]黄启臣.明清时期两广的商业贸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31-38.
[28]吴桂芳.议复衡永行盐地方疏[M]//应槚,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70:282.
[29]麦思杰.“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J].社会,2018(1):81-103.
[30]顾旭明.(乾隆)怀集县志[M].清乾隆二十年刻本.
[31]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216.
[32]趙世瑜.“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明清易代的区域社会史解释[J].学术月刊,2010(7):130-140.
[33]清圣祖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34]张允观.(乾隆)北流县志[M].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35]饶任坤,陈仁华.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36]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史,2020:38-42.
[37]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406-407.
[38]边其晋.(同治)藤县志[M].清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39]冯德材.(光绪)郁林州志[M].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40]清高宗实录[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
[41]邓智成.清代广西矿产开发研究[D].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8.
[42]署广东总督阿克敦奏报拏获偷挖矿砂渠魁李亚展等情形折[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308.
[43]广西巡抚汪漋奏拿获狂徒情形折[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465.
[44]广西巡抚郭(金)鉷奏陈开采地方矿砂管见折[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252.
[45]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6]唐凌,熊昌锟.广西商业会馆系统碑刻资料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7]秦浩翔.明清时期广西梧州地区水旱灾害及其社会应对[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9(6):81-86.
[48]金鉷.(雍正)广西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9]广西巡抚李绂奏请九府分贮捐谷等事折[M]//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三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0:364.
(责任编辑:王勤美)
Order Contro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Wuzhou,Guangxi Province from 15th to 18th Century
QIN Haoxi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China,510257)
Abstract:From the 15th century to the 18th century,Wuzhou experienced a social change from “military stronghold” to “business hub”.During Zhengtong period,with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turbulence caused by Yao ethnic group in Datengxia area,the militarization process got started in Wuzhou.During Jingtai and Tianshun period,as the turmoil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e,in the sixth year of Chenghua period,in order to unify authority and coordinate resources,Guangdong and Guangxi governor established a permanent office in Wuzhou.Since then,Wuzhou’s military construction continued to be strengthened,and it became an important military area of Lingnan region.In the late Ming Dynasty,with the gradual stability of the local order,the military status of Wuzhou was declining day by day,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ame important,thus Wuzhou began the transition to a business hub.In the early and middle Qing Dynasty,as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Wuzhou was vigorously developed and traditional trade like grain and salt remained prosperous,a commercial trade network centered on Cangwu Rongxu was gradually formed.By the 18th century,Wuzhou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business area with a luxurious social atmosphere.The Wuzhou case show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border area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regional order control,infiltration of state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areas.
Key words:important border area; national integration; regional development; social change
收稿日期:2022-02-15
基金項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地方志纂修与国家认同、区域社会文化创造研究”(18AZS012)。
作者简介:秦浩翔,男,广西桂林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主要包括:覃延欢:《广西四大城市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上)》,《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侯宣杰:《西南边疆城市发展的区域研究——以清代广西城市为中心》,四川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吴宏岐、韩虎泰:《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吴庆洲:《“水都”的变迁——梧州城史及其适洪方式》,《建筑遗产》2017年第3期;麦思杰:《“以火为政”:明清时期梧州城火政与区域社会的变迁》,《社会》2018年第1期;孙将来:《梧州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变研究(汉-民国)》,广西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何俊宇:《明代梧州府军事地理研究》,《广西地方志》2020年第3期,等等。
②本文所指梧州地区以明代行政区划为准,包括梧州府城及其所属苍梧县、容县、岑溪县、藤县、怀集县、北流县、博白县、兴业县、陆川县、郁林州。
③“猺”“獞”等称呼包含歧视贬低之意,本文在行文论述时分别改为“瑶”“僮”,但在引用史料时为保留其原义,不做改动。而“狼”并非全为贬义,包含称赞狼兵骁勇善战之意,因此文中“狼”字一律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