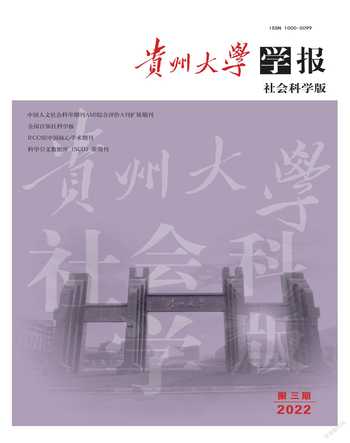论改土归流的复杂因素
——以鲁魁山之乱与清雍正改土归流为例
2022-10-24徐雯秀
罗 勇,徐雯秀
(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改土归流的原因是土司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关系来解释,认为改土归流是土官地区的经济基础从封建领主制发展到地主经济制度的需要,是消除落后、消极的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阻碍的需要。这些解释将土司当作一种落后现象,并受中原王朝正统论的影响,将土司置于与中央分权的对立面,甚至在史料方面也不自觉完全相信官方立场的史料,常建华进而呼吁从社会历史理论和民族政治理论的角度重新思考。如方铁从资源的角度解释改土归流,认为改土归流是土司与朝廷争夺资源并且阻挠外来移民的结果;常建华则将改土归流放置在雍正初年的新政改革的背景下讨论,认为改土归流与推行保甲、缉盗、设汛塘等有关,并通过贵州长寨改土归流的例子说明改土归流的起因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国家权力、皇帝意志对地方社会的干预,而不是地方社会自我变化的结果。方铁和常建华的研究通过对改土归流具体过程的分析,使改土归流的细节更为清晰,呈现出改土归流原因的复杂性。
学术界围绕云南改土归流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滇东北改土归流尤其是鄂尔泰与滇东北的改土归流成果最为丰富。实际上,清朝在顺治时已对滇西南的元江府进行了改土归流,随后雍正初年在高其倬的主导下对威远州进行了改土归流。这早于滇东北和贵州的改土归流,甚至鄂尔泰在滇东北、贵州等地的改土归流是对雍正初年高其倬滇西南改土归流政策的延续。可以说,滇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的开端,但学术界在滇西南改土归流的研究方面显得不系统,不充足。如曹相对滇西南改土归流的研究集中在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后开展的改土归流,没有讨论鄂尔泰之前高其倬的改土归流。周琼以高其倬为中心,叙述其在滇西南改土归流的过程,将鲁魁山之乱与威远州改土归流合而为一,将改土归流作为善后措施的前提。唐立讨论的则是雍正七年(1729)车里宣慰司的改土归流。这些研究对雍正时期滇西南改土归流进行了个案讨论,对进一步认识清雍正时期滇西南改土归流奠定了学术基础,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梳理雍正时期滇西南改土归流的缘起。本文即试图围绕滇西南鲁魁山的动乱与改土归流的关系来认识清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希望进一步认识清朝改土归流的复杂过程。
一、鲁魁山的自然人文状况
二、康熙时期鲁魁山的动乱与招抚
在康熙帝对土司的处置意见之下,范承勋通过招抚解决鲁魁山之乱。范承勋上疏《土夷归诚请授职疏》向康熙帝汇报其招抚过程。先是范承勋派遣官员持谕入山招抚,杨宗周等“遣目具呈,情愿倾心向化输诚,并籍所有把守口岸,目兵分晰造册赍投前来”。招抚初见成效后,范承勋派督标左营游击庄一虎、临安知府黄明,及临元镇臣马山会委中军游击郭玉明等至新平县招抚。杨宗周依“夷俗斫鸡,向天立誓,据译供称,情愿真心改恶从善,严戢土人,不许出没为非,及再取保头钱,并愿与朝廷出力拒守口岸”。在杨宗周等有接受招抚的意愿之后,范承勋建议授予杨宗周为新平县土县丞,普为善驻新平县了味,方从化驻元江府结白,李尚义驻新平县扬武坝,分别授与土巡检职务;建议“夷目土兵把守要隘,亦听自行开垦瘠薄山地,刀耕火种,以资养赡,免其开报税粮”;并按照清朝剃发令,“各土司一例剃发,验明取结具保后,据详称行府转行新平县,亲到宗周所辖地方转谕目民一齐剃发”。范承勋的建议基本被接纳。
三、鲁魁山之乱与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四、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改土归流原因的分析,主要是建立在较为宏观的视域下进行讨论,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为指导,认为改土归流是落后的土司制度与社会经济之间矛盾的结果,或以后知者明的视角认为改土归流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这些解释对从宏观上把握改土归流的原因起了积极作用,但从改土归流的具体实施过程来看,改土归流原因则更为复杂。如常建华认为清雍正初期对土司采取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将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作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认为雍正三年(1725)贵州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
从本文的讨论来看,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的开端始于滇西南威远州改土归流。威远州改土归流是因为威远州土官与鲁魁山残余势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威远州土官对土民的苛求索取。鲁魁山在明末清初已成为威胁周边社会稳定的区域,吸纳各种反清朝势力,包括大西军和南明的残余势力、吴三桂的残余势力、逃避赋税者和来自内地的游手好闲之人。在雍正之前,清朝已在鲁魁山西南设元江府,将产茶区域纳入清朝直接控制,但鲁魁山位于云南政治中心与元江之间,不仅对清朝与元江等地的政治造成威胁,还对往来的商人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对河西、通海等地进行抢劫,影响到周边地区的安定。清朝平定吴三桂之乱后,通海县知县范景陶曾提出“鲁魁宜剿”,被时任云贵总督蔡毓荣采纳,写入《筹滇十疏》,但由于康熙帝不同意而改为招抚,以至于鲁魁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直到雍正初年高其倬担任云贵总督,对诸土司、土目采取强硬政策。此背景下发生的鲁魁山之乱为高其倬推行强硬政策提供了机会,但高其倬起初未预计到鲁魁山与威远州之间的关系。直到鲁魁山残余势力逃入威远州,且被威远州土官藏匿,高其倬为了彻底解决鲁魁山的动乱而建议对威远州改土归流,进而将威远州改土归流列入鲁魁山善后措施中。鄂尔泰接任云贵总督后,延续了高其倬对土司的强硬措施,进一步推进改土归流。也就是说,清朝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从滇西南鲁魁山之乱开始的。鲁魁山之乱的残余势力被威远州土官藏匿是直接导火索。
综上所述,本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雍正朝宫中档案为主要史料,梳理雍正初年改土归流的过程,发现早在康熙时已有改土归流的想法,且改土归流与缉拿鲁魁山残余势力有密切关系。康熙时期蔡毓荣筹滇的意见影响了雍正初期的土司政策。从后知者明的角度来看,清朝在新改流地区设义学、编保甲、设汛塘是清朝改土归流的目的,改土归流促进了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制度一致,提高了边疆地区对清朝的认同度。实际上,改土归流只是使边疆地区与内地政治制度趋于一致,边疆地区对国家的认同还有赖于后续的讲圣谕、设义学、编保甲、设汛塘等保障措施。从清朝雍正时期滇西南改土归流来看,改土归流的初衷是根绝鲁魁山残余势力,改土归流与设义学、编连保甲、设汛塘等共同构成了鲁魁山之乱的善后措施。因此,对改土归流及其之后社会变化的研究应该将改土归流放置在一个社会治理体系中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