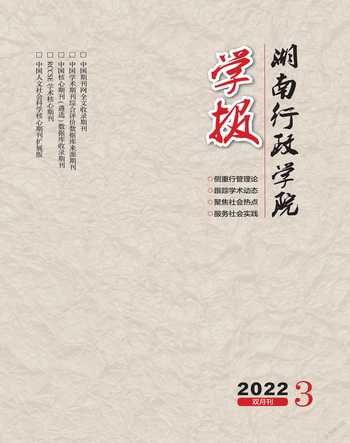现实困境与纯真救赎
2022-05-23盛紫薇
盛紫薇
摘要:郑小驴尤其关注底层儿童,在叩问现实的问题上始终保持严肃姿态。除一般的儿童视角之外,还透过特殊的病残儿童视角和犯罪儿童视角描绘新奇怪异的孩童世界。他似乎刻意关注孩童逻辑并以此反观成人秩序,两者不断交织表现出“消逝的儿童”物质世界、冷暖交织的精神世界以及泛灵的幻想世界。这不仅表现出作者的人文关怀,也进一步体现其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担忧与探索精神出路的尝试。
关键词:郑小驴;《西洲曲》;《天花乱坠》;孩童世界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05(2022)03-0138-07
郑小驴从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至今,呈现出一条从文本模仿探索到形成自我风格的创作轨迹,而他所钟爱的儿童叙事视角始终贯穿其中。早期的小说创作如《1921的童谣》《西洲曲》均带有莫言、苏童、余华等前辈作家的影子,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儿童视角呈现祖辈的历史,凸显了作者融入历史的愿望,虽强调在场感,但缺乏个人记忆,这是无可厚非的。在吸取经验的同时,他不断从现实土壤中汲取营养,表达对底层儿童的现实关怀。从长篇小说《西洲曲》开始,其个人的记忆色彩与社会参与意识愈来愈浓重,作家本人与时代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在时代的洪流下,采取一种童真的视角是郑小驴认知世界的独特窗口,透过这个窗口,黑暗、阴冷、暴力和血腥等皆为世界的底色,而在这底色之上的些许善意与光亮也是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一个唯有通过儿童纯净的双眼和心灵才可感受到的神秘世界在缓缓溢出,充当着底层人民表达的出口。
郑小驴无疑是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者,多数研究者关注到郑小驴作品中使用的儿童视角,将之与成长书写结合起来。杨钰璇认为《西洲曲》采用“水壶”的少年视角来讲述计划生育政策给几代人造成的伤痛,通过少年的成长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1]。刘阳扬将郑小驴的成长叙事置于城乡交融的过程之中,深入成长期少年的心灵,探查其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2]。也有研究者从郑小驴“病残儿童视角”与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长篇小说出发,分析这种独特视角的优势与局限[3]。这些研究集中在儿童的成长及其象征意义上,传达郑小驴的现实批判,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作家的“暖处理”,比如《西洲曲》中“水壶”对北妹、母亲等人的情感依恋和精神共鸣;新作《天花乱坠》里的“冬瓜”对细妹的淳朴暗恋;《蓝色脑膜炎》中少女黄秋对语文老师张弛的崇拜与情愫等等……这些多为生理不健全且常与死亡对话的少男少女们总是能传递世界的微弱阳光和暖意。这说明通过儿童表达的现实世界不都是黑暗与暴力的,在众多苦难青春体验中,浮现微微暖色的爱则是郑小驴对儿童世界的特殊关照。
本文选取郑小驴小说创作的几类孩童形象为研究主体,在此之上所形成的几重孩童世界则是笔者探讨的中心:“消逝的儿童”物质世界、冷暖交织的精神世界和泛灵的幻想世界。这些孩童世界可看作是作者对自我或群体青春时代的归纳与总结,亦是对人类发展初级阶段的精神反思与期盼。在这座孩童王国里,人性的混沌与纯粹似乎没有边界,他尽量不做判断,将人性的复杂性交予读者。带着问题意识思忖乡村的困境,将敏锐的触角深入到底层儿童身边,捕捉到儿童世界内部肉体的游离与反叛、精神的孤独与满足,挖掘这些“精神孤儿”的出路。这似乎成了郑小驴的创作源泉与动力,不断叩问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仍在继续与重复的生命形式。
一、“消逝的儿童”物质世界:困境与新质
孩童视角虽缺乏客观性,但主观的观察显得更为敏锐,与成人秩序不同的是,儿童们有一种自我的观察系统。郑小驴构建了以残酷挤压为物质外壳的孩童世界,这些孩童常被成人的空间秩序影响,不仅受到了同伴的挤压与捉弄,还会加入到挤压同类的行列中,演绎正在“消逝的儿童”现象,这样一来,孩童们所观察和体验到的外部的空间常常是非独立且受到挤压的、捉摸不透且缺少秩序的。一方面反映了成人社会对孩童世界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其中出现的细微新质也体现了郑小驴对孩童精神内部所持有的期盼姿态,力求建立一个属于孩童的独立表达方式。
《雨赌》讲述了三个放牛娃玩“炸金花”的打赌游戏时失了分寸,最终造成二墩子死亡悲剧的故事。“都重阳节了,他还光着脚,不仅光着脚,连件长袖都没穿,依旧套着夏天那件脏兮兮的破洞T恤,腆着个圆鼓鼓的肚皮。”[4]222与村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二墩子感受不到寒冷,也不知如何表达需求。他是个一直遭到歧视的孩子,没有亲妈,甚至还因为父亲攒钱买来的贵州女人被同伴嘲弄。但他却“长得很结实,像头小水牛,论力气,我和范范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4]222二墩子起初赢了几把,后面却一直输,输了的惩罚便是喝水。“我”虽有些害怕出意外,却被范范不断教唆着给二墩子灌水,最终二墩子躺在了地上,肚子鼓得出奇,再也没了动静。即使“二墩子”身体再结实,在面临占了上风的人性之恶时,也显得弱小无助。本应是放牛休憩期间的孩童游戏,却被范范和“我”演绎成没有流血的暴力杀人现场。赌博激发了人性浮躁与暴力的一面,作者在故事最后道出一个更深刻的原因,范范其实是在实施家庭间的纷争与报复——他从父母那里听来二墩子的爹才是偷了自家两万块钱的“元凶”。作者用二墩子的悲剧来审问作为边缘目击者的“我”与范范类群体以及孩童背后的成人群体,深沉叩问孩童人性狰狞的一面,进一步反映了成人社会的习性对孩童世界的侵蚀与挤压。
由此可看到,孩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界限正在消失。正如尼尔·波兹曼所提出的,“童年消逝的证据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出自不同的来源。人们可以看到,有证据显示儿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风格上越来越融合一气。相关的社会机构,如法律、学校和体育運动也在改变原来的看法。还有一种‘确凿’的证据,如有关酗酒、吸毒、性活动、犯罪等等的数据,这些都意味着童年和成年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5]169-170郑小驴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提及过成人群体的习性诸如赌博、看黄碟现象,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因孩子的参与而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如《天花乱坠》中“香茅鸡娘疯了……买六合彩买的,把小殷辛辛苦苦在湘潭打工挣来的钱都输光了呢。”[6]再如《枪毙》里的“光头李”因为六合彩欠债而抢劫杀人,“……最近手气背,买六合彩和打牌通通输……”[4]210这些在广东、澳门等大都市流行的金钱游戏传至农村,足以让每个人为之着迷,连放牧的孩童也无法幸免。除此之外,许多孩子会早早地接触到性,“火鸡不知道从哪里搞了台破电视回来,还有一台VCD,水车的男人都一窝蜂地跑到他家那破木屋里看毛片去了,小孩也去,大家看得口水长流,目瞪口呆,惊讶无比。”[6]孩童不可避免地依存于成人世界,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民过早加速了孩童的成长,孩童与成人互动的结果之一是对成人行为的模仿演绎。
在短篇小说《骑鹅的凛冬》中,立夏是个整天帮爷爷数鹅的孩子,被其他孩子认作是骑白鹅的“白痴”,他单纯中带着些愚笨,“二告指着地上一团暗绿的鸡屎,逗他,糖,甜的!立夏就蹲下去,抓了把,犹豫地望着他们,讪讪地笑,猛地往嘴里一塞……大家憋得脸红脖子粗,笑得肠疼,笑得脚软,笑得眼泪长流。”[4]51虽常受到欺侮,但正因为这样的特殊智力使其不同于正常孩子,反而不会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报复,他总以善良、弱小、边缘的品质待人。一次,他被牵扯进一起与“庆松叔叔”相关的性侵案里,成人社会的伦理报复,因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儿童“立夏”的偶然目击而获得合理性,由此可反观出成人社会的极大荒诞性。
以上的病残儿童是作为被挤压或被诉说的对象而出现的,但在《天花乱坠》里,郑小驴力图让此类儿童的代表“冬瓜”开口说话,表现出一定的生命新质。冬瓜因被父母抛弃而从小跟随二叔长大,成长过程中也被同伴火鸡捉弄,不仅嘲弄他那萎缩得像甘蔗的腿,还取笑他没有父亲的事实。“我身子往后缩了缩,畏畏缩缩地望了男人一眼,他似乎就等着我开口了。我于是怯怯地叫了声‘爸……爸……’,听见火鸡发出一阵爆笑,笑得他气都要断了。”[6]然而,即使被倾轧和捉弄,“冬瓜”还是一直保持乐观向上、越挫越勇的生活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倒立”这一行为的象征意义,身材矮小的他,力气却不小,都集中到了上半身。在倒立方面,他获得了先天的优势,还被同乡打趣说,“这瘸子手脚长反了!”在水车镇,倒立成了冬瓜的强项,他开始拥有了自我的表达权,要用这种能力躲避卫星的监视,引起喜欢的女生细妹的注意。即使这是一种被人耻笑和否认的荒诞行为,但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能力指向了对常人秩序的反拨:“我”虽发育残疾,却有“倒立”的一技之长,在与常人相反的世界里得心应手地走着。在揭示残酷现实的同时,也揭开残障人士的内心世界,隐现出作者对底层孩童的人文关怀。
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互动或表现为正向模仿,或是反向排斥,所呈现的相互倾轧的孩童物质世界,都指向了成人社会的荒诞可笑性。其一,通过病残儿童视角一瞥乡村社会的演变,反观“正常世界”秩序的荒诞,从而揭示乡村与都市互动间的巨大困境。其二,透过儿童群体的某些“犯罪”行为集中体现了人性的异化,并反思儿童畸变成长背后成因,揭示缺少资源的乡村少年群体精神虚无的本质。其三,挖掘孩童自我抒发新质的这一尝试,使得郑小驴的现实叩问抵达人性更深处。
二、冷暖交织的精神世界:反思与体悟
孩童不仅有敏锐的观察力,也有独特的情感抒发方式。除了反拨现实世界之外,郑小驴将孩童的精神世界展露出来,包括期待、孤独、反思与忏悔。为发掘人性的复杂面,在这个以困境和黑暗为基调的儿童物质世界里,也不乏有亲情、爱恋、友谊的光芒照射进来。在儿童与儿童的发现问题上,以约翰·洛克的“白板说”与卢梭的“儿童自然主义”理论皆为代表,“卢梭的第二个思想是,儿童的知识和情感生活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了解它,才能教育和培養儿童,而是因为童年是人类最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生阶段。”[5]85-86郑小驴在表现儿童成长时,接近卢梭的观点,阐发儿童的最接近自然的情绪与行为。
郑小驴早期许多中短篇作品都流露出家庭亲情的复杂性,《西洲曲》中的少年“水壶”(即罗成)生活在一个五口之家,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这样的身份赋予了他一双能自由观察万物的眼睛。按理来说,他是除哥哥和姐姐以外最受宠爱的孩子。但事实上,母亲一直沉浸在曾经因堕胎而早已逝去的“不存在的婴儿”的哥哥的回忆里,难以自拔。在罗成的眼里,母亲一直为隐蔽怀胎的北妹、姐姐左兰的婚事和帮助哥哥高考而到处奔波操劳,留给自己的关注却是最少的。对亲人的渴望在《我略知她一二》也有披露,正在读初中的少女青梨似乎患有精神分裂症,她跑到警局报案声称自己杀害了亲哥哥,要求警察局调查。而事实上,她的家中只有一个耳聋的老奶奶,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仅有的哥哥在四岁时就已溺水身亡。这一切都是她的幻想,为了抵抗孤独的侵蚀与获取被爱的可能性,她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想象了一个始终宠爱与陪伴自己的哥哥。
虽然,底层孩子的孤独属性贯穿许多文本,但这样的空间并非是封闭的,有时也会照进友谊、爱恋的情感光芒,抑或同类人的关怀与肯定。如《西洲曲》里水壶与罗圭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起上学、游泳和谈心,“那真是一个愉快的夏天,有稻花香,有永无休止的蝉鸣,有无处躲藏的烈日和火红的晚霞。很多年后,我依然怀念这种味道,这是夏天独有的,热烈饱满,像阳光灿烂的青春。”[7]27孤独使他们相遇,儿童直接的、最接近自然的联系使双方都逐渐变得快乐。这样的友谊不断感染和启发着“我”,逃离那个只有规章制度没有温情与爱的乡村牢笼。此外,作者的温情书写还体现在对孩童两性之间的朦胧爱恋意识和行为的捕捉上,《少儿不宜》中的游离是一个正面临高考的学生,他憎恶闯入村子的温泉度假村、开着豪车的有钱人和出卖肉体的小姐,但唯独对那位有着“大学生气质”的哑女产生好奇与依恋。《蓝色脑膜炎》里,那个被传染脑膜炎的少女黄秋,因在一次作文课上写到“我希望弟弟是蓝色的”而受到语文老师张弛的表扬,从此与老师之间有了某种默契的联系,她留意老师的一举一动,观察他的情绪。无独有偶,《天花乱坠》里冬瓜对于细妹的爱恋与《西洲曲》里罗成对北妹的暗恋形成了互文关系,即都是依恋母性般的暗恋。细妹貌美,是村中大伙儿争夺的对象,初中毕业后便去打工,当她再次回到家乡时,染了头发,打扮时髦,像是不属于水车镇的“细妹”,这些细微的变化已表明都市的现代文明对乡村人民的塑造与变形。即使她最后成了县长的情人,怀了孩子躲在家里,冬瓜对细妹的情感一直保持初心,还攒钱买下了价值一百元的手表去表达心意。再看《西洲曲》,罗成作为一个自闭少年,北妹是唯一能与他交谈的人,她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北妹的自杀给这位少年带来了更是沉重的打击,“我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凝视着她容颜的嬗变,一股莫大的悲凉朝我袭来。”[7]4考察几位残障儿童的暗恋史,可以看到这些深埋于心的暗恋情愫,属于儿童最真诚自然的情感状态,不含社会偏见和道德评价。与此同时,这些孩童爱恋的对象给他们的孩童世界添上了一抹亮色,带有母性或父性的光辉。
如果说孤独、暗恋是孩童精神世界的隐秘情感,那么自我忏悔与反思意识则是郑小驴挖掘的更深一极。短篇小说《枪毙》首次打开了犯罪少年的心灵,依次转换莫家孙子、光头李、光头李弟弟的视角,最后转为全知视角来审视这些怀着仇恨、忏悔和无奈的人物心灵之间的纠葛。作者将三位少年的内心活动放置同一空间,让读者去体悟这些底层乡村少年们的愤怒或忏悔。即使是犯过罪的少年,也能立马分辨出朝他伸来的“审判的目光”,最后“唯有大颗的泪珠从眼眶背叛似的滚出来”,说明良知意识是在人性深处根植的。
郑小驴不断梳理孩童的精神轨迹,不仅仅是发现底层社会的问题和痼疾,也在寻找散发人性光辉和良知的角落。对于现实不粉饰赞美,用一些黑暗丑陋的表象揭露现实,但又尽可能地发掘暖色,给人类的精神带来力量。归根到底,他想展露的是一个五彩斑斓多层次的世界,孩童的纯真情感是其精神内核,成为其创作的不竭动力。
三、泛灵幻想世界:自我救赎与主体表达
郑小驴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小说家,关注在荒蛮中野性成长的孩童现实外壳的同时,用不同孩童类型的口吻展露他们暗藏的心绪。除此之外,他也在不断探索孩童们冲破所处困境的审美出口——在一个超现实的神秘世界里,将孩童表达欲求的愿望公之于众。这也是孩童认识世界、观察生活与体认自我的方式。
从地域特征来看,郑小驴生来便与湖南这片巫楚大地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在某次大学讲座上,郑小驴表示,他笔下之所以有那么多儿童形象与神秘诡谲的历史,多源于身为“道士”的祖父在童年时期给自己讲故事的经历。西方哲学承认灵魂的存在,原始人在对象化与客观化的推演中,发展出“万物有灵论”。而在中国的文化里,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的南方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成为了一种传统,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研究者杨有楠专门探究过郑小驴的神秘书写,并指出郑小驴的经营耐心更源于一种主观写作动机:“即他想借神秘这一非理性文化表达对现代性的个人反思,有时甚至希图以神秘的传统之力延宕乡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8]笔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则补充性地认为,郑小驴试图构建一个鬼魅的幻想世界,为乡村儿童群体找寻一个纯真的自我救赎之路与实现主体表达的出口。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自我中心论是对前运算阶段儿童的物活论的反应,所谓物活论是指认为没有生命的物体具有类似生命的特征,如思维、期望、感觉和意图,就如同儿童自己。”[9]这就意味着,儿童具有独有的年龄物质基础与超凡的想象力。当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都失灵的情况下,郑小驴赋予孩童超现实的独特视角,通过梦境、通灵、古老预言等行为证实有那么一个隐秘的空间,是专属孩子的救赎空间。在《少儿不宜》中,游离常在小庙与菩萨对话,他祈求菩萨保佑自己考上大学和发财致富。在小庙里,他与一条无毒的菜花蛇成了同伴,“他想,蛇也是通人性的。晚霞从西方辉映了进来,庙里装满了金光。游离想起那个面壁九年的达摩祖师,心中异样的温暖。”[10]游离与菩萨、菜花蛇成了朋友。在外界,人人都被欲望诱惑着,只有在这样的神秘空间里,他才能自由表达对现代文明的愤恨与诅咒,道出真正的愿望。这样类似的神秘空间在《西洲曲》中也可找到,乱葬岗的婴儿墓地是许多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心灵寄托,而罗成因为自闭常常遭到家人的厌弃,所以他逃到离家很远的一片清朝民国间的墓地处,与死去的灵魂相依为伴,“我站在这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却出奇地平静,或许在那,世界上已经没有东西让我害怕了。”[7]10他常在这里度过精神孤独的日子,精神伴侣罗圭和北妹皆相继死去,“我”的内心更是孤立无援,隔着坟墓,似乎有一条隐秘的精神链条联系着他们。在这一诡谲的空间里,罗成不仅目睹了坟墓开了一处大洞,且有人钻进里头睡过的变化,还开始与不知身份的“神秘人”展开象棋间的博弈,似乎经过神秘的墓地洗涤之后,他能获得一些反抗世俗的力量。这些行径也足以表明孩童具备通往超现实空间的非理性能力,而且他们也需要一个隐秘的独立自处、表达和最终达到自我救赎的空间。
郑小驴表示过,“采用孩子的视角,的确给叙事带来便捷,但绝不是回避某些东西。如果不是借用孩童的视角,这种力量反而传达不出来。借用孩童的视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和宿离在小说中属于同一代人。”也就是说,孩童视角不仅能表达出成人无法表达的间离效果,更重要的缘由则是郑小驴也曾是那些孩子的一员。郑小驴虽做到了不直接介入文本,但透过对孩童群体的塑造,时时透露出自己对儿童群体的偏爱与思考。
郑小驴将儿童与鬼神崇拜结合起来并不是毫无指向性的,一方面,借用儿童想象與祖辈达成精神共鸣,获得暂时的庇护与慰藉;另一方面,通过民间信仰获得平静与豁然,找寻人类的心灵归所,人类之间所产生永恒的温情联结似乎才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
四、结语
郑小驴分别从物质和精神层面为读者呈现了三层不同的孩童叙事空间,聚焦于孩童的阴暗一隅,也窥探到物质与精神都处于底层的孩童们的挣扎路径,以引导人们不断地思考人类的困境。孩童的世界正在被瓦解,但也保留着其纯真的一面,与此同时,郑小驴借助泛灵的鬼魅叙事,将儿童置于独立自由的神秘空间,获取救赎慰藉与表达的出口。正如他所说的,“作家不是道德家,也不是人生规划师,他负责提出疑问,但不负责指出方向。”作为80后的作家,他的写作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他必须要记录与写作,使之与时代的文学接轨,我们仍能看到,90后的青春与80后青春有许多精神接续性,而这种写作在不断的历史打捞现场中获得认可。同时,体验过乡村伤痛的孩童即使在长大成人后也能从这些写作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在揭示伤痛的同时,也肯定伤痛对于人类灵魂的塑造。从孩童世界出发,他创造了一个不同于其他80后作家的青春伤痛写作。
参考文献:
[1]杨钰璇.“80后”作家的底层成长叙事——以毕亮、郑小驴、李傻傻为代表[J].文艺论坛,2018(3):82-87.
[2]刘阳扬.城乡交融下的成长书写——郑小驴乡土小说综论[J].当代作家评论, 2014(5):40-47.
[3]周银银.病残儿童视角与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J].文艺争鸣, 2016(3):109-117.
[4]郑小驴.消失的女儿[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5]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郑小驴.天花乱坠[J].清明,2020(6):29-62.
[7]郑小驴.西洲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8]杨有楠.论郑小驴小说的神秘书写[J].百家评论,2016(3):104-108.
[9]劳拉·E.贝克.儿童发展[M].5版.吴颖,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37.
[10]郑小驴.少儿不宜[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13.
责任编辑:袁建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