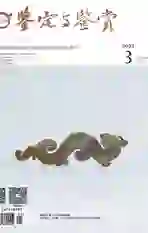邾叔彪簠器主名字新释
2022-05-18李游
李游

摘 要:邾国现存有铭青铜器数量不多,邾叔彪簠便是其中一件。该器铭文大体已无争议,但器主名字存在不同解释。当为一个字,而不应释为“某父”。与字形相类的金文和甲骨文进行对比分析,得知此字可释为“”。此外,金文中的“虢”字有多种字形,其中有一种字形从虎、攴,写作,与从虎、又的“”字字形极为相近,有学者将二种字形相混,但实为不同的两个字。将二者区分开来,期冀在今后的文字考释工作中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邾国;邾叔彪簠;铭文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5.007
1976年12月,山東省平邑县东阳公社蔡庄村发现一座古墓,出土了4件形制、花纹、大小一致的青铜簠(《殷周金文集成》①04592),1件现藏于平邑县文物管理站,另3件现藏于平邑博物馆。通高20厘米,口横30厘米,口纵22厘米,重3.5千克。直口,腹壁斜收,平底,两短壁有一对象鼻形耳,方圈足每面有长方形缺。口沿和圈足饰回纹,四壁饰窃曲纹。目前公布其中2件簠的铭文,另2件不知是否铸有铭文。为方便行文,暂将有铭文的两件簠编号为甲、乙。簠甲铭文铸于器底,簠乙盖、器对铭,两器铭文内容一致,字体略异(图1),一般释文为:“鼄(邾)弔(叔)彪乍(作)杞孟辝(姒)(簠),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亯(享)。”
关于邾叔彪簠的铭文,大部分已无讨论必要,有争议的部分主要是器主的名字,即“邾叔”和“乍”之间到底是什么字?本文要探讨的也是这个问题。
对于器主的名字,目前的考释结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名字有4字,如“□叔□□”③、“鼄叔豸父”④、“邾叔彪父”⑤、“□叔虎父”(《铭图》05926)、“□叔□子”⑥等;另一类是名字有3字,如“邾叔彪”(《铭图》三编0573)、“邾叔虢”(《全集》山东卷263)等。
“邾叔”与“乍”之间的、、字,字形上为虎形,下为手形,若释为“某父”恐不妥当。“父”为男子美称,冠于名后,金文习见。但在金文中,“父”字与名之间通常会有一定的距离,可以很明确地将名与“父”字区分开。簠乙的器、盖铭文均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下面手形与上面虎形的尾端是连在一起的,这在簠甲中尤为明显。《集录》会将其释为“□子”,便是这个原因。且“父”字通常作、、⑦等形,比手形多一小短竖,像一只手拿着工具。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曰:“父乃斧之初字。石器时代,男子持石斧(即石斧之象形)以事操作,故孳乳为父母之父。”而字下面的手形并无那一短竖,比起“父”字,更应当是个“又”字。故笔者认为“邾叔”与“乍”之间的字不能释为“某父”,且仅有一字。
“邾叔”与“乍”之间仅有一字的情况,学者多将其释为“彪”或“虢”。
《说文·虎部》:“彪,虎文也。从虎、彡。彡,象其文也。”彪在金文中一般写作、、⑧等形。与、不同的是,“彪”字的三撇与虎形是分开的,且较短,而、的三撇是与虎形连在一起的,且较长。故笔者认为、的三撇应当是虎形的一部分,因为“虎”字较原始的字形本身就是有“花纹”的,如、、⑨等。并且,若将、释为“彪”,既忽略了下面的手形,也无法与簠甲没有三撇的字相互印证。
《说文·虎部》:“虢,虎所攫画明文也。从虎,寽声。”林义光《文源》:“虢为虎攫,无他证,当为鞹之古文,去毛皮也。”《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虎部》:“虢,金文像两手上下张革之形。从虎,像张口露齿,有头及足尾的皮革,会意。”虢在金文中一般写作、、、⑩等形,像用手或以手持棍与老虎搏斗。简单概括来说,主要是双手持棍打虎(又+攵/攴+虎)、单手持棍打虎(攵/攴+虎)、双手搏虎(又+又+虎)三种字形。在金文中,以第一种字形最为常见。但在甲骨文中,又以第三种字形最为常见,写作、k等,这种字形也是最符合“虢”字的初义的,像用两只手去虎毛皮。第一种字形当是第三种字形的讹变(其中一个手形讹为“攴”),第二种字形或是第一种字形的省略体(详后)。“虢”字小篆作,左侧“寽”旁的上部为一手形,下部的“寸”是手形的讹变,很明显是继承了第三种字形。、、的字形为单手搏虎,与“虢”字的字形结构存在些许差异。此字能否作为“虢”字的又一变体形式,还需做进一步的讨论。
甲骨文中有一l字,从虎、又,与、、字形结构相类。《总表(修订版)》将其隶定作“”。《说文·又部》:“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过三也。”据此,“又”形作为部首时,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等同于“手(扌)”旁的,此种情况在金文中亦较为常见。如:,隶定作“扶”;,隶定作“择”;,隶定作“挛”等m。故“”应可与“”字等同。《玉篇·手部》:“,批也。”《集韵·陌韵》:“,打也。”《篇海类编·身体类·手部》:“,亦作掴。”
甲骨文中另有一、n字,从虎、攴,《总表(修订版)》将其隶定为“”。《玉篇·攴部》:“‘攵,同‘攴。”《广韵·屋韵》:“攴,凡从攴者作攵。”《九经字样》:“攵,音扑。《说文》作攴,隶省作攵。”故将、二字隶定作“”是没有问题的。另父癸爵(《集成》09024)中也有此字,写作。《集成》将其释为“(、)”,《铭图》《陕西金文汇编》等仅隶定作“”o,《古文字研究》则释为“虢”p,《金文总集》释为“虢”与“”q,《新金文编》隶定为“虣”,该书按曰:“从虎,从攴,即暴虎之暴。甲骨文从虎从戈,诅楚文从虎从,古书从虎从武。”r
将、、隶定作“()”是毋庸置疑的,那么这个字可以等同于文献中的哪个字呢?现分别对以上观点进行讨论。
《广韵·号韵》:“‘虣,同‘暴。”《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形教中,则民不虣。”《说文新附》:“,虐也;急也。从虎,从武。见《周礼》。”王玉树拈字:“通作暴,《周礼》多作,惟《秋官》‘禁暴氏尚作‘暴。”郑珍新附考:“,其形当左武右虎。”《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虎部》:“虣,甲骨文和《诅楚文》均像戈搏虎,应为‘暴虎冯河之‘暴的本字。”“虣”字不论是从虎、从戈,还是从虎、从,或是从虎、从武,其字形最基本的结构均是从虎、从戈,故从虎、从攴的字是不应该释为“虣”的。
在铜器铭文中,“又”形除可隶定为“手(扌)”“又”等偏旁外,还会讹变成“攴”“寸”等字形。下面列举一部分后世隶定为“扌”旁却在金文中有从“攴”旁现象的字:
(摹本,从“攴”,隶定作“扶”。作旅鼎,《集成》01979)。
(从“攴”,隶定作“措”。中山王厝方壶,《集成》09735)。
(从“攴”,隶定作“播”。师旂鼎,《集成》02809)。
(从“攴”,隶定作“擈”。应侯见工鼎,《铭图》02436)。
由此推断,“()”字还是有可能等同于“”字的。但事实上“手(扌)”旁和“攴(攵)”旁只是在部分字例中有替换现象,并不是一定的,所以还需做具体的分析。
前文中我们提到,在《新金文编》中释为“虢”字的第二种字形也是从虎、从攴的。那么,“()”字到底应该等同于“虢”,还是应该等同于“”呢?我们先回归相关器物的铭文进行讨论。
录伯簋盖(《集成》04302):“(贲)朱虢(鞹)靳。”此铭中“虢(鞹)”字作,从虎、攴。从其铭文内容来看,隶定为“虢(鞹)”无疑是正确的。《说文·革部》:“靳,当膺也。”靳表示的是服马当胸的皮革。“虢”在此处可引申为皮毛之意,正与“靳”的意义相对应。“朱虢(鞹)靳”即表示红色的皮毛、皮革。
“虢”字在金文中用其本义的例子不多,基本是用于姓氏和国名。周文王分封其弟虢仲与虢叔,二人分别建立西虢和东虢。周平王东迁时,西虢徙于上阳,称南虢。虢仲的后世又有被封于他地者,称北虢。故“虢”作为国名是由来已久的。国名转化为姓氏也是常见现象。而“”字在金文中本就少见,作为姓氏就更加罕见了。父癸爵的“”显然是作为姓氏而存在的,比起释作“”,更适合释作“虢”。
所以从虎、攴的“()”字并不能等同于从虎、又的“”字,而应该是“虢”字的多种字形之一。当然,由于二者字形相近,也不排除在古文字中有混用的现象,当根据辞例做具体分析。
综上,邾公彪簠中的、、应释为“”,此字与等同于“虢”的“()”并不是同一字。由此,邾叔彪簠应改为“邾叔簠”。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4.此书以下简称《集成》。
②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此书以下简称《铭图》;李伯谦.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山东卷)[M].北京:龙门书局,2018.此书以下简称《全集》。
③李常松.平邑蔡庄出土一批青铜器[J].考古,1986(4):366.
④在《集成》修订增补本中改为了“是叔虎父”.
⑤雅南.读《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琐记[EB/OL].(2019-10-25)[2021-10-11].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475#.
⑥劉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此书以下简称《集录》。
⑦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329-331.
⑧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587.
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527-528.
⑩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587-590.
k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528.
l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修订版)[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第1823号字.此书以下简称《总表(修订版)》。
m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1602-1611.
n见《总表(修订版)》第1825号字.
o《铭图》第08473器,《铭图》器名作“爵”。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第502号器.
p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古文字研究》(第七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5.
q严一萍.《金文总集》[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字在第3921号器中隶定作“虢”,在第4151号器中隶定作“”.
r董莲池.新金文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