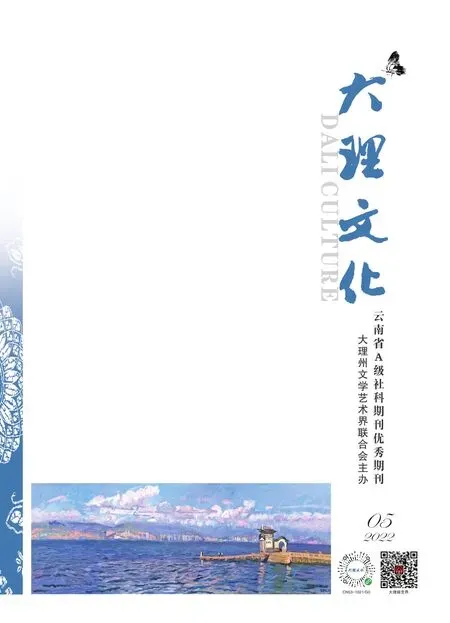徜徉密祉的悠长时光
2022-05-17郭玺芳
●郭玺芳
有时候,让人流连忘返的并不是誉满四海的名山大川,它可能是一处不起眼的清幽小径,或者是一方远离尘嚣的山野人家。随意地走进,不期地一瞥,很可能就是自己一直苦苦找寻的世外桃源。
春天,我同晨曦一起抵达密祉。
晨雾还未散尽,蚕豆的叶片上还泛着霜花,豆荚早已迫不及待地释放出清香来。四周的村落里炊烟渐渐升起。农家小院里的鸡鸭早已伸长脖子,一边大声叫唤,一边把放置在地上的餐具敲得叮叮当当乱响。主人怀抱一盆玉米,一边用它们才能听懂的语言召唤,一边将玉米粒儿撒在空地上。吃饱喝足的鸡鸭拍打着身上的羽毛,三三两两走出了院子。它们打算去村巷里散散步,或者在花前树下谈情说爱。
晨雾退去,阳光铺满古道,引马石泛着金光。文盛街上的居民打开板壁上方的雕花木格子窗户,让阳光满满地洒进屋来。石板路上,这些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马蹄印,在通透的阳光照耀下折射出一段段沧桑的历史。
沿着光滑的石板路缓缓前行,仿佛历史刚刚与我擦肩。一家过去的马店遗址还在。马厩、火塘和供赶马人歇息的房间,还完好地保留着。穿越似水的光阴,眼前的景致很容易让人浮想从前——夕阳里,古道边,南来北往的商旅和长长的马帮队伍一起行走的过往。
过去,具有互补性的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藏区产出的骡马、皮毛、药材和川滇以及内地生产的茶叶、布匹、盐等日用品,在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之间南来北往,川流不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便形成了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古道穿文盛街而过。不宽的街面,承接着寒来暑往的马帮,临街的小店,为马锅头提供着漫漫赶马路上所需的零碎物资。店家也不怎么吆喝,他们早已习惯了顺其自然,一切随缘。百抖茶和烧苞谷飘出了诱人的香味,让离家的远行人嗅得到家的味道。它们定格成一个永恒的等待,迎接着各地商旅。
小街最初不叫文盛街,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颇具个性的名字——马食铺。主街全长不足一千米,两旁店面林立,一道窄门进去,后面藏着一个可供数十人留宿的诺大院落,比如聂家马店、杨亮臣家的桂花店、张秀山家的张家店、李永康家的李家店、杨士俊家的杂货铺、张树藩家的张家店、赵育唐家的银匠铺……
这些店铺在当年的文盛街,全都赫赫有名,它们不仅为古驿道上马帮和过往商旅住宿、补给及货物运转提供了方便,也为那些长年累月行走在夷方路上的赶马人提供了温暖。
走走停停,无意中回头,眼见石家耕读大院的门口,老人们窝聚在阳光下,眯着双眼享受初春阳光的抚慰,仿佛在晾晒一本因藏在地窖发了霉的古书。马帮时代已经远去,古驿道上早已长满荒草杂树。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时代气息的摩托车和汽车。古朴的村落正在被周围众多城镇包围着。即使眼前这条街,也赶了时髦,古道两侧不远处渐次竖起的水泥楼房。还好,古道还在,马蹄印还在,引马石还在,那段繁华而沉重的驿站历史也还在。它们并不大声喧哗,静静地见证着随时光远去的那一段段鲜活的历史。
与密祉息息相关的,还有豆腐,此行便要去吃一次。它们不需要用文化包装,密祉街上大箩小筐的豆腐亘古不变地透露着原始的气息,很多时候几乎可以充当这座小镇的代言人。

文盛街 柴啟栋/摄
说到密祉豆腐,自然就会想到白伙食家的豆腐宴。每年春节之后,各地携家带口的游人大都会云集于此,放开紧缩了一年的肠胃大饱口福。实地来到这里,等待过后,眼前,满满一桌子的菜肴原材料全是豆腐,腌豆腐、炒豆腐、煮豆腐、臭豆腐、麻婆豆腐、豆腐圆子、豆花、豆浆……琳琅满目,让我不知道要先从哪里下手,照着以上菜品各来一碗,号称“八大碗”。
作为当地的美食,家家户户都会做多种豆腐菜肴,好客的密祉人就会端上色、香、味俱全的豆腐宴宴请远方的客人。传统的手工厨艺、纯粹的地道风味,物美价廉,食客赞不绝口。
密祉豆腐之所以味道纯正、质地优良,得益于一眼得天独厚的珍珠泉水和一门传统的制作工序,从淘洗、磨浆、滤浆、煮豆腐、点豆腐、压豆腐最后到捂豆腐,七道工序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水、这人、这厨艺,使得密祉豆腐香飘四方,深深烙在了食客们的记忆里。
吃完,继续行走。溪水依旧从尹宜公故居门前经过。它没有绕道,也没有枯竭。看护故居的石老爹每天将院里院外打理得干干净净。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院落,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阳光和灰尘似乎全都隐去了,小院里仿佛全都是小河淌水的声音。陈列室的桌子上,摆放着尹宜公生前手写的一份《小河淌水》词曲稿,满满的,全是梦幻般的天籁之音。那里似乎还残留着尹宜公先生的体温,我不敢贸然把沾满俗世尘埃的双手放上去。
尹宜公,这位弥川大地上妇孺皆知的早期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他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食粮。弥渡人每每唱起《小河淌水》,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尹宜公,更不会忘记他为家乡的革命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小河淌水》成为世界名曲之后,尹宜公向媒体表明:“《小河淌水》属于全世界,但我的家乡不能被忽略。我这是在为云南的荣誉作证。”……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弥渡与《小河淌水》之间宛若水乳一般,密不可分。
在这里,《小河淌水》诞生。在这里,《小河淌水》成为“东方小夜曲”走向世界。这样一首地方民歌,之所以能走出弥渡,走向世界,需要我们用心去倾听,用心去感悟。
走出文盛街时,远处似有人在低吟轻唱,那便是《小河淌水》了。一眼就看见了那棵老槐树,三五成群的文盛街居民围坐在老槐树底下的石桌旁聊天、“斗地主”,谈笑风生,享受着富足的生活。老槐树在这里站立了几百年,苍老得不成样子了,厚厚的树皮龟裂成一道一道长长短短的口子,经年的枝干默默地承接着每一季的花开花落,茂盛却不张扬。开花季节,清香四溢,把浓郁的树荫洒满周边,又把丰满的籽实奉献给那些需要它的村民。始终风雨无阻地守望在凤凰桥头,哪怕枯朽的枝干被岁月折磨成弯驼的软腰,亦风雨不惊,初心不改。
出了古道口,在凤凰桥上就看见一泉活水,这就是珍珠泉了。珍珠泉一年四季充盈饱和,溢出来的泉水汇入亚溪河又流向远方。泉的神秘在于,在泉边使劲跺脚,水里立即就会有大大小小的气泡冒出来,它们一个紧追一个,连成一串,像珍珠随着水波摇曳。在阳光照射下,大大小小的气泡五光十色,世间没有哪一颗珍珠能够与之媲美。
假如没有珍珠泉,亚溪河会失去它一半的妩媚。正值春天,微风轻柔地抚摸岸边的杨柳,嫩绿的枝条就婀娜地舞动起来,又给亚溪河增添了不少姿色。亚溪河水清澈见底,水流梳理着河床里的石头和青苔,并把蓝天白云搅成碎片,为这个繁忙的季节哗哗地歌唱。在密祉,水的情结,美妙得就像一首古老的歌谣。
在亚溪河边,水流过四季。从清晨抵达傍晚,又从傍晚流到清晨。就这样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欢快着、流淌着。循着潺潺的水声一路走去,眼见一棵老树把它的脚探进河里,青苔在它的脚上长了出来。连续不断的干旱也没有让桂花箐的水停流,它依然汩汩穿梭着,没有泥沙,没有杂质。我将手迫不及待地伸入溪流,溪不拒绝,它以水的胸襟,包容了一只突然闯入的陌生的手,那只手就悠然自得地在“绸缎”中滑行。
桂花树在溪畔静静地站立着,它始终没有开口说话。而且还将继续静默下去。深山里是否有过美丽动人的故事,桂花树下是否有人唱过情歌,无须去考证。你不问,它不说。你问,它也不肯说。桂花树只会对光阴流逝的秘密更加守口如瓶。
渐渐,游人络绎不绝。与桂花树合影,与溪水纠缠……说的说,笑的笑。满溪流水也跟着笑。总有一些传说与水有关,总有一些事物与水有缘,还有一些相思与水也有关。与生俱来,不离不弃。远处的田野在亚溪河水的滋养下生机勃勃,麦苗已经返青,几个身着蓝布碎花衣裳的女子,她们正在忙着施肥,身体一弯一曲之间,清脆的笑声就飘满田野。
密祉坝子里有一种带着拖腔的调子,好听极了,它在赶马人的路途中,在女人们插秧的节奏里,在放牧人的山坡上飘得漫山遍野。密祉盛产民歌小调,几乎所有生产生活的内容都可以入调。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八士村的女歌手李三姐,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编唱出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民歌。这位无所畏惧的民间女歌手,给密祉人民留下了许多积极向善的正能量。李三姐去世后,民间黎民百姓亲切地将她奉为歌神、灯神。
如今,在巍山县枫木林村的观音庙和大石碑密祉三姐庙中,还供奉着她的画像。李三姐的歌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密祉人民,人们将其视为传家宝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怪不得,在午后,密祉的田野里就充满了声音。
第二天,坐在中巴车上,我第一次在去往太极顶的公路上行进。目的很明确,登太极顶赏春日美景。随着中巴车一路向上,直至抵达哨所停车场。先不说一路上的风景,单是停车场周边的景色就足以让人流连,不忍匆匆离开。

田间密祉小调 柴啟栋/摄
四周树木葱郁,阳光温和,云南松根深蒂固,常年保持着它固有的姿态。杜鹃花开得正旺,红的火红,白的雪白。停车场外,农家小院的篱笆站得笔直,树头菜熬过寒霜,倔强地吐出新芽,在春风的撩拨里,它们若隐若现从篱笆缝里探出头来四处张望……花儿、草儿、风儿、水儿,它们全都成了春的忠实随从,争相展示着各自新鲜的姿态,人走近,春意就在心里荡漾开来。
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灌木丛,把我从山脚接引到山顶,我一路开心着,憧憬着。这样的场景,曾经在童年的梦境里出现过。不想就在这个春天,我已经惬意而真实地行走在了童年的渴望里。花香伴着鸟语,蝉虫尚在梦中。没有了蝉噪,鸟语便是林中世界的主宰。这些像青草一般等不及的小鸟,它们的啼鸣已经摇醒枝头的新叶。有的组成合唱团,一起合鸣,也有独自高歌的,旁若无人,这些免费娱人的林间歌手闷了一冬,早就想痛痛快快一展歌喉了。已有许久,未曾去林间听鸟鸣。这就是春的讯息,在城市里看不到,因为灰色的水泥掩盖了一切。要早起,要到山林里,还要细心听。
长长石阶两侧的灌木丛,枝叶绿得就要滴下来。藤蔓先是努力向上攀爬,与枝叶纠缠,再从半空荡下来,再走几步,卯足劲,又爬上另一株大树……它们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在春风里迎来送往。有好多次,我的脚误入草丛,草叶上的露水就明目张胆地浸湿我的布鞋。放轻脚步,屏住呼吸,静静聆听山中万物细语,我听到了春草拔节的声音,杜鹃吐蕊的声音……一两只麻雀在枝头嬉戏打闹,抖落三五片花瓣下来,树也不恼。时间推着节令一季一季轮回,大地上的花鸟虫鱼准时把每个春天弄醒。
风从山谷深处的灵山古庙吹来,吹过树梢,吹过浅草,吹过眼睛。此时,多么想让自己炽热的身体去紧贴太极山袒露的胸襟。当各地的名山大川被一拨拨游人搅动得躁动不安,人心也跟着浮躁,喧闹中再也难觅宁静的憩息。倒是这灵山景致,让人浸染其中,让一颗空虚的心获得饱满和宁静。
山林如此空灵静美,林中一切已然深深融入我的身体、我的血肉,让人感到尘世很远,又很近。仿佛听一曲生命的绝唱,周而复始。山林在,绿色在,我也在。
其实,此行我第一次登太极顶。还想看到那里落日的姿态。太极山顶,太阳不愿沉落,留恋地把燃得通红的脸贴在山头,向大地,向人类,也向立于转石阁边上的我,投来依依不舍的一瞥。
落日的余晖在空气中折射成仙女的嫁衣,洒向山林,洒向万物,人就恣意地沉浸在夕阳里。记不得平生看过多少次日落,但之前所见都感觉不生动,不具体,都不足以让我心醉。只有太极顶的落日,美得有骨气,谁也不依靠,独自表演。光凭这一点,即使它被淹没,我同样愿意为它曾有过的光彩而讴歌。
立于灵山之巅,伏地膜拜,虔诚地许下一个心愿——愿这景,从此美丽我的梦。“残阳如血,点点泪,几许忧愁几许疼。”难怪古人在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受落日美妙的同时,又生出了丝丝缕缕的失落和伤感。美好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正如所有的辉煌都会落幕一样,所有的沉醉都会在某一瞬间转为惆怅……
太阳沉下去了,潮动的晚霞向大地谢幕。群山挽着亚溪河唱起情歌: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
春去秋来,密祉小镇依旧生机勃勃又淡定自然,它不动声色地承接着那些风尘仆仆的脚步,给他们呈献热气腾腾的茶水和豆浆,宠辱不惊。我知道,密祉是一本古老而又厚重的书,仅用一次漫步根本无法深入。那么,就让我像一缕不得要领的轻风,能翻动几页就翻动几页吧,或者像一粒突然闯入茶马古道文化中的生字,亚溪河水也让我轻轻地读出如水的新鲜,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