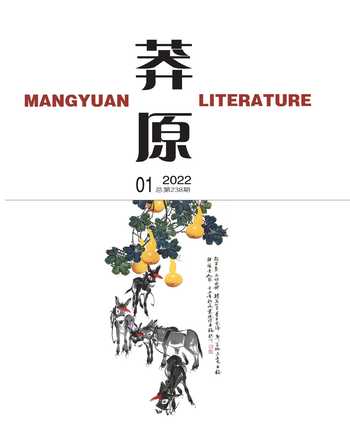年轻作家们的“现实”何在?(评点)
2022-04-29刘海燕
刘海燕
“重温经典”这个栏目,之前选的多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至少是90年代的,这期选的是年轻作家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这个中篇写于2014、于2018年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年轻作家的作品,时间距离较近,哪些能成为经典,还需要在岁月里沉淀。在这里的重读,我更倾向于,是寻找走向经典之路径及艺术精神。
当今时代,信息的快速传播,使所有的新闻瞬间成旧闻,天下难有新鲜事,文学几乎不可能再承载新生活经验的传播。评论家陈晓明早在2013年出版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他颇感无奈地谈到,文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50后作家李佩甫,几年前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曾幽默又朴素坦诚地给年轻作家讲,大意是说,和老一代作家相比,你们是不沾光的……我的理解是:老一代作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同步,个人身上可见时代风云,他们多是有戏剧般命运、有大故事的人;从农村走出来或经历了知青岁月的作家,他们多有自己的文学故乡。当然,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现实,可对于个体而言,时代大现实从来都是无法选择的。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正如狄更斯《双城记》开篇那悖论的断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年轻的作家,从外部看,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与众人无大异——日常平淡,老一代作家那种来自命运的第一手刻骨情感、第一手厚重现实,他们几乎不可能再有;在城乡一体化和网络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文學故乡。
那么,他们独创性的“现实”根基何在?他们的作品对于时代和读者,意义何在?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触动我再次思考这些问题。让我意外和心契的是,石一枫对“新文学”传统中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他在“获奖感言”中谈到:这篇小说的初衷“是想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了机会,在烈火烹油之后宿命地归于失败,但也有着令人唏嘘的悲剧意味和英雄色彩。他们和19世纪欧洲的于连、拉斯蒂涅,20世纪美国的盖茨比存在着某种呼应关系,而这种呼应关系本身似乎在从一个侧面说明着中国这片土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种种巨变……在诸多传统之中,我更希望自己有能力去继承的,是发祥于100年前被称为‘新文学的那个传统……”石一枫在鲁迅、老舍、茅盾等现代作家们的“新文学”传统中找到立足之地,来观察时代生活。对于没有文学故乡的年轻作家,在文学史中、在传统中找到自己的写作根系,也是让自己沉下来、不漂浮的可靠方式。
石一枫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就职于京城体制内的纯文学刊物。从庸常社会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生活在文化高地的幸运儿。论智力和学识,他更有炫技的资本,但他选择了现实主义叙事,而不是现代、后现代叙事。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现实主义”一词,似乎是一个很陈旧的词汇,我们不再好意思说出或承认它。青年时代,我本人也迎向新艺术形式,是岁月和现实让我意识到,艺术形式无高低,亦无新旧,首要的是它能否真实敏锐地表达我们的生活和精神处境。事实上,文学不面对现实,还能面对什么?人性、内心等等,都是现实里的。作家邵丽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今天比以往更需要现实主义”。(《青年作家》2021.11)今天的现实问题,包括全球生态失衡,恐怕更需19世纪以来世界文学里的那个“现实主义”,那种波澜壮阔像大海一样的气息,那种批判的力量,穿越一个世纪,并照耀到另一个世纪去……
石一枫写的多是小人物,但他选择的是能体现“大时代”、揭示“大问题”的小人物。这些“大”,不是老一代作家们普遍关注的政治权力,而是不同阶层的生存状况,时代的价值观和经济秩序对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等。同为底层“小人物”叙事,在老一代作家那里,多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叙事视角,直接经验的第一人称叙事,那些苦难人生中的“小人物”,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的精神自传,或有着命运牵连。石一枫的这篇小说,是城市人视角里的“小人物”。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城市人的视角,或者世界公民的视角,将更多地成为未来文学的一种叙事方向。
陈金芳初次出现在京城同学面前时,场面相当戏谑:站在外面不敢进来,老师喊道:“你进来呀。在外面哨着干吗?”这口气,“哨着”这词,进来的正配是下面这样一个发愣而寒碜的角色:个子很矮,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一看就知是从农村来的。这被乡野的寒风吹刻在脸颊上的“农村红”,是毫无防护下皮肤的损伤,是农村孩子贫寒的印记。这个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典型细节,让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如果在当年,我还会羡慕她,她还可以从农村转到京城的部队子弟学校借读。那是90年代的陈金芳。
城市里的“坐地虎”,对于这样一个转校生,仅仅视而不见也好——“我们咋咋呼呼地从她身边涌过,就像绕开了一张桌子或一条板凳。”在他们的经验里,像陈金芳这样的借读生,随时会从教室里消失,“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非我族类”。接下来,陈金芳就成为被哄笑的对象——“她手上攥着一只印有‘钾肥字样的尼龙口袋,跟在我身后几米开外。当我前行的时候,她便迈着小碎步跟上来,当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着肩膀,紧张地看着我。”这样一个“非我族类”的女生,在人性的势力和虚荣中,还被取笑,被嫌弃。但是,她好像浑然不觉,也许有觉,但只能如此隐忍,仍跟在“我”身后,并对气急败坏的“我”说:“我们家也住这里。”这个“农村红”女生,“面无表情地”接受着城市男生的戏谑与排斥,但你能感到她矮小的身体里有种闷劲,那是一种让你无可奈何的倔强力量。
陈金芳的姐姐姐夫,作为部队大院食堂的临时工,也是院内人的笑资,那玩笑里透露出他们生存的不易。
城市人视角讲述的农村人故事,充满好笑、滑稽。如果陈金芳是第一人称叙事者“我”,那应是另一种情感基调吧,我们从老一代作家的直接性叙述中,曾感受过人物最初“进入城市”时的恨意和苦难记忆。
接下来这个细节,见出石一枫不同凡响的表达——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在琴声中相遇。“我”这个从小拉小提琴、准备考音乐学院的幸运儿,夜晚练琴时发现:窗外一株杨树下的陈金芳,“那人背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她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从此,陈金芳成为“我”最执拗的听众,一个黑夜里的听者,她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她静立、倔强的身体语言,让我们感受到她内心的狂风暴雨。
对于陈金芳,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能像是天外来音,是和她的生活世界里完全不同的声音。她生活的世界里,是她姐姐“近乎凄厉的喊叫声”,是轮番来看病、找工作的七大姑八大姨,是班主任家访后感叹的话:“窗台上只有一只刷牙杯,里面插着七八柄牙刷”,但陈金芳一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是刷牙,而是吃饭……都是不堪面对的粗粝和苦难。因此,陈金芳和所有像陈金芳一样身份的人,都想让自己变得和城里人一样。在她还不知如何让自己变为城里人时,只能在外形上模仿,陈金芳偷穿姐姐还是姐夫的大西服,成为班上女生里第一个抹口红的,第一个打粉底的,穿或许是捡来的一只鞋跟高、一只鞋跟矮的高跟鞋……班上无论男生女生,都在集体排斥这个模样滑稽、“穷嘚瑟”、但并没有招惹过谁的女生。“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
在学校里这么被排斥孤立的陈金芳,在她父亲去世后、母亲要带她回乡下时,拼死也要留下来。在经历一番被打、骂和砸的折腾后,陈金芳终于留了下来。到底是什么让陈金芳们拼死也要留在城市里?这个话题是老一代作家们在写“进入城市”主题时,没有正面面对的。相对于农村,城市有属于它的文明。小说里的琴声,正是区别于粗粝日常的声音情境之一。这个话题暂且不表。
缺少家庭温情和保护的陈金芳,后来和周边的痞子们混在了一起。对于一个讨生活的底层女生,从食草动物一般的怯弱到泼辣与轻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后来,陈金芳和豁子一起同居、做生意。生意做得早,豁子有手段,如果沿着这个路数走,是可以有一份富裕生活的。但是陈金芳心里的音乐情结,使她像着了魔,“每逢北京有小剧场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死磨硬泡地让豁子给她买票”。“后来居然偷偷把店里所有的钱都拿出去,说是想买钢琴。”这件事使她和“痞子”心性的豁子彻底决裂,豁子当街暴打她,揪起她的头发,“令她像某种水鸟一样伸着脖子仰面朝天,同时用脚狠狠地踩向她的小腹与胯骨,发出了扑扑的声音,很像在踩一只暖水袋”。“在挨打的过程中,陈金芳始终是一言不发的,她只是尖叫,嗷一声,又嗷一声。我突然想起来,过去遭到班上同学欺负时,她也是这个反应。她就像个一捏就响的橡胶娃娃,当疼痛转瞬即逝,她便会归于平静。”
这场有观众围观的当街暴打,豁子是“寒了心”的狠。豁子认为,“没见过这么急吼吼地想要变成贵族的”;以至多年后,他也不明白陈金芳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陈金芳同样是寒了心的,她一定认为,这个豁子不可能明白她的心,这样打她,她也不辩解,表情淡漠,近乎凛然,就像个“橡胶娃娃”。她把更苦的痛苦闷在心里。“她曾经像孤魂野鬼一样站在我窗外听琴,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却又因为一架钢琴重新变成了孤魂野鬼。”
也许,即便陈金芳不着魔于音乐艺术,和豁子这样的人在一起也难以过好。分手多年后,豁子在回顾往事的言谈中,对她没有任何尊重,除了性,豁子对陈金芳其人基本否定。基于日常世俗的判断,陈金芳是不现实的,豁子也有他的委屈,但却带给人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
命运就这么不公,一个是匮乏,一个是厌倦。与陈金芳相反,“我”从小“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贵的小提琴”,“我”感叹的是“没有过选择爱好的权利”。陈金芳敢爱这样一个人吗?早年当豁子向“我”挑衅时,她淡定地上前解围。后来她劝说多年不再摸琴的“我”继续练琴,邀请“我”单独吃饭聊天,并在一个夜晚,精心设计了一场让往日重现的音乐会,请来名气很大的国外乐团为“我”当陪练。但“我”毫不领情地拒绝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咬牙切齿地说。“你说什么?”陈金芳瞪大眼睛,惶然又委屈。她如遭电击,不认识似的看着“我”。这个有些落魄的男人,此时依然没有把这个发迹的女人当成自己的同类,他觉得接受她的爱意比失去音乐更屈辱。陈金芳对这个中断音乐生涯的男人,是真心惋惜,这里有她的青春和梦想,与其说爱,不如说是珍爱。这时的陈金芳已名叫陈予倩,她无论怎样改头换面,在“我”的内心,她最终还是那个记忆中的陈金芳。陈金芳在任何一个时段,都得不到也找不到对应的真爱与尊重。
无论在城市人还是父老乡亲的眼睛里,陈金芳都是异类,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孤独者。她先是怀揣农业时代的梦想,想当个城里人;后又卷入商业时代的梦想,想一夜暴富。她的梦想,也是时代生活的浮华梦。
做生意失败的陈金芳,从南方回到京城,改名为陈予倩,混进了天花乱坠的艺术圈子,改行做“艺术品”。她本没想“诈骗”,本想挣了大钱回馈家乡父老,可是经济领域的困局,她“又搭上了b哥那样的专业投机客”,最终彻底崩盘。这对于陈金芳,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她用家乡父老卖地的钱奢侈消费,后全部押上去做风险投资。正如b哥说的:“别人拿出来的都是闲钱,只有她,很可能把什么都押上了……我们这样的买卖,本来就不是她能玩儿的。”
“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的陈金芳,最终也没活出人样来。她自杀伤残后,从医院里被抬进警车的后备厢,运回老家。来医院接她的姐姐姐夫,首先关心的不是她的死活,当发现“她坑的全是自己人”时,表情变得恶狠狠地,痛陈起陈金芳这些年的所为。金钱让亲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这样,快要死掉的陈金芳,生不如死的陈金芳,谁能给她一点人世间的温暖?而此时的他们——姐姐姐夫,穿着鼓鼓囊囊的棉大衣,在长椅上并排坐着,由于常年的体力活“脸上笼罩着脏兮兮的沧桑”,此刻又赔空了家财,精气神更损,像是“两团人”,这个“团”字,真是让人心酸。他们也是天下可怜人呢!作者的笔触充满了悲悯。
到底是什么毁了这些人的生活与命运?
从叙事人“我”的视角可以看出陈金芳们不幸的部分原因。“我”离婚后经济拮据,在陈金芳一掷千金,为感谢我帮她联络b哥,慷慨又得体地汇到我工资卡上一笔不小的款时,我没有犹豫就退给了她。“我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是活得身轻如燕,因而不愿与任何人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我不想因为这笔钱彻底改变我这个人”。他对自我和时代生活有认知,散淡、自我批判,也能清醒地看出他人的问题。这样一个人,不会被卷到想一夜暴富的时代漩涡里去。这是一种更为理性的视角。在这个视角里,可以看到陈金芳对生活、对艺术行业、对自我的非理性认知,尤其是不择手段想暴富的目标,最终毁了自己。
但是,对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社会生活和时代都有责任。陈金芳曾经那么想融入城市,那么执着地做着音乐梦,她遇到的人都在扭曲她的激情与梦想;她的渴望与痛苦,一直闷在心里,闷在她那忍辱无言的身体里,一直到死,她都是一个内心孤苦的人。这是一部充满痛感的作品!作者對陈金芳内心困境的关注,对城市人的势利与道德困境的有力表达,对时代生活问题的揭示,撼动人心,能够获得鲁奖,可谓实至名归。也许,陈金芳的同类和异类,读到这个作品,都会从中受益。
石一枫曾讲:“小说还有一个小小的功能,就是帮助人去想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在阅读中观照自己的生活,看出点收获来,这样甚至对中国人整体的生活,都可能有一种新的认识……人始终需要反思自己的生活和现实,这也是小说对人的意义所在。”(《作家石一枫眼中的“小说与中国现实”》,中国作家网,2020-11-19)这个时代,已不是仅靠生活经验就能写作的时代,作家更需有真正的思想力和判断力,需有深度反思现实生活的能力,对自我、社会、时代,以及整个世界,有相当理性、深度、全局的认知,才可能写出引领读者认识时代生活和个人命运的力作。
作者单位: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 申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