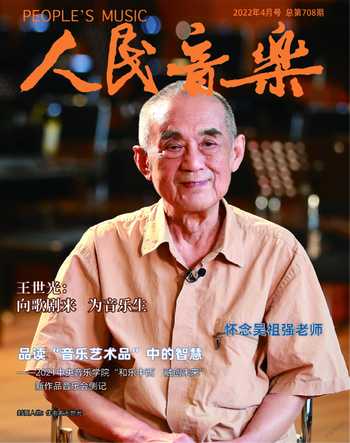品读“音乐艺术品”中的智慧
2022-04-27魏明
魏明
入新时代以来,作为全力弘扬、传播中国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先后创立了“三团一中心”,并多次赴美、欧,以高水准完成“原创作品音乐会”及多种形式的演出。作为该举措的延续,2021年岁末,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与“中国音乐创作中心”联合,分别于12月5日和10日,在该院歌剧厅成功举办了两场题为,“和乐中西·融创未来”的作曲系教师管弦乐和民族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需要说明的是,此次遴选“原创新作”时,虽依年龄按50、60、70和80四个代际向作曲家委约,但实际上则更多地向青年作曲家倾斜。一方面,给年轻作曲家提供一个高水准的创作实践舞台以展露头角;另一方面,通过新老作曲家同台的机会进一步积累创作经验,以“舞台上传承”的形式,内化中央音乐学院优良的创作传统。
应该说,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的“新作品音乐会”,因其在国内创作领域内的引领作用,历来都备受学界瞩目。此次两场“新作品音乐会”在海报发出后,便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12部新作品在指挥家杨力、林涛和陈冰(按出场顺序)的倾心诠释下,经由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和民族室内乐团的精致演绎,或熠熠生辉,或感心动耳,或发人深思。
笔者有幸亲历两场“新作品音乐会”的排练和演出。细细回味,12部作品虽然个性十足,但呈现于两场音乐会时,却似乎又折射出作曲家们在面对艺术创作时的某种共同性探索和艺术观,彰显出作曲家们的创作智慧。在“管弦乐新作品音乐会”中,尤为突出地展现出了他们把音乐作为“艺术品”来对待时的那种真情、精致和音响想象力;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中,则旨在传递出作曲家们自觉立身于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那种探索和抒怀。这些作品及存在于其中的智慧、想象力、音乐表达和组织思路等等,无疑会成为未来音乐创作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的路径参照。在此,笔者愿结合视听体会,分享些许所思所想,以飨读者。
一、管弦乐作品中的智慧——声音想象力及其控制力
“整场音乐会中不大能听到那种‘熟悉或动听的旋律,但同一个乐队,却演绎出六种不一样的精彩,传递出各不相同的音响观念、创作意图、表达手段……。这像极了学术会议时的‘头脑风暴,让人领悟到其中的精妙与智慧”,这一印象在“管弦乐新作品音乐会”观后,便盘旋于脑海,并再次使我深刻地理解到:由丰富多彩的乐器所构筑的管弦乐作品,就犹如艺术品一般,在聆听时,不必且不应仅关注其“歌唱”的一面,更应领悟其中所蕴含的真情、精致和智慧。因为,这其中包涵了作曲家把他对声音的想象物化成真实客观的音响,而后再将其“雕琢”成音乐艺术作品的全过程。当一部部个性十足而又精致的音乐艺术品呈现出来,在让人赞叹其智慧的同时,更丰富并拓展了人们的想象力,这便是创造力得以延续的关键所在。
音乐会以于梦石创作《长青马》开场。如此选题,显然是与作曲家出生成长于内蒙及其蒙古族的民族身份密切相关。
该作品用较为“传统”的笔法,在若干个场景转接中传递出作曲家在表达“草原母亲”这一主题时的真挚情怀。于聆听中,可明显捕捉到作品中有两个核心元素,即音高滑奏和具有蒙古族民间音乐性格的大二加纯五(纯四)度音高组合。作曲家便围绕这两个元素展开了音响想象。鉴于创作选题,作曲家在构建作品时,比较偏爱铜管及弦乐音色,并且在乐队中设置了四种“形象”,用于实现其创作意图。作品的头、尾部分以大提琴独奏来模拟马头琴音色,用于“吟唱”宽广悠远的蒙古族长调;在音乐进行中,以铜管组乐器的滑奏来“象征”蒙古族民间仪式音乐中的“大号”;在乐队全奏时,以弦乐组高音区长时值的线条来表达“赞扬”之情;通过对打击乐节奏和音色的设计传递出舞蹈性格。这四种“角色”交相配合,使整部作品在核心元素控制下,通过音响的张弛、薄厚,在悠远、欢快、赞扬和怀念等几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描写中表达出浓郁的民族情怀。
与《长青马》不同,代博在为小提琴与乐队而作的《追怀》(Saudade)中,则传达出一种理性的、均衡的、思辨式的音响观念。写作中,作曲家“尊重”每一件乐器的演奏习惯,几乎未使用乐器的非常规音色与演奏法。他将创作目光投向了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因此,如何以多种线条所制造出来的尖锐音响来传递思维抽象,便成为了作品的构思主旨。整部作品中,独奏小提琴陈述出的乐思与乐队的不协和音响,在构筑起音乐陈述逻辑的同时也牵引着笔者的想象,时而出乎意料、时而又似曾相识。例如,在独奏小提琴声部中,作曲家将象征着思绪持续的a1作为核心音高,围绕该音高,作曲家以跨音区的大跳或锯齿状旋律,使小提琴声部形成分层或对位,以此来实现旋律线条的衍展,并象征着思绪的展开。
第三首作品——贾国平的《琴况二则》(太和、清调),将思绪从“沉浸式的自我思辨”中带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里。应当说,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境”是贾国平音乐创作中重要的探索维度之一。为实现对这一探索的有效表达,作曲家改变了管弦乐队“传统的”功能分组式的音响观念,将整个乐队作为一个具有“调色意义”的音源,通过构建精致而考究的音效及其连接等手段,实现对“传统意境及其声音”的再创造,从而让管弦乐队“讲中国话”,传递中国声音。在《琴况二则》中,如何在对管弦乐队音效的“再创造”中来传递中国韵味和中国气质,自然就成为该作品的构思主旨。基于上述,作品中以极其精致和细腻的笔触,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古琴由其演奏法而带来的音效,并使听众清晰地捕捉到作曲家意欲传递出的意境。如《清调》中,作曲家通过对弦乐、铜管和打擊乐器音效的“再创造”来模拟古琴抹弦、进、退等音色。
第四部作品是史付红的《太阳下的风景》。作品传达出作曲家对于一种神秘、原始、幻想般的声音想象。这种想象源自于作曲家对“中国少数民族对大自然敬畏、崇拜等认知观念” 的感悟。因而,她使用了三管编乐队,运用了四组色彩性打击乐以及竖琴、钢琴和钢片琴。在表述时,隐退了那种较有具象性意义的旋律,突出乐器的色彩性。在组织作品时,作曲家以“渐强”或“渐强后渐弱”这样具有造型意义的几个的部分,使音乐呈现出一种“镜头式”的画面感。值得说明的是,与“镜头式”音效相配合,作曲家在实现音响想象时,使用了构建好“底色”,通过“添加点缀”布局音响薄厚来结构作品的思路。例如,在作品开始处,为了表现“天地玄黄”,作曲家通过用乐队的低音区(低音提琴、低音单簧管的低音区)和极高音区(色彩性乐器的泛音)以极度轻盈的方式来象征“天地之间”,而后用其他乐器的“点缀勾勒”逐渐“充实”乐队音响,并以渐强式的结构来实现音响的构建。
第五部作品是常平的钢琴协奏曲《未来之城》。其精彩之处在于,作曲家以“钢琴协奏曲”的形式,通过由远及近再走远式的“空间构想”,来设计作品的结构和“音响图景”。这使得作品结构紧凑、“既视感”极强,易于被听众捕捉并牵引思绪。基于上述,作曲家使用了三管乐队加钢琴的编制,在作品中设置了同音重复(开头木管中)、三度音型重复(开头木管中)、锯齿状音高造型(钢琴主题)、跨音区大跳的节奏性主题(59—60小节钢琴及乐队中)等几个具有贯穿意义的音乐材料,并赋予其一定的“形象意义”。构建乐队音响想象时,则以“音乐形象”并置的色彩性观念来安排乐器及其音色。引起笔者注意的是,作曲家虽然遵循了传统协奏曲独奏乐器与乐队之间的声部关系,但别出心裁地将钢琴与颤音琴和木琴一起,作为“乐队中的色彩性乐器”来构思,这使得钢琴的动态音高造型与整个乐队的音响色彩浑然一体。整部作品以7个“声响图景”,按由远及近、自然渐强后减弱,而后,由近及远,自然渐强,这种对称的音乐走势思路组织起来(见表2)。
第六部作品是秦文琛的舞蹈组曲《伶伦作乐图》。该作品作为“压轴之作”,将音乐会引至沸点。作曲家有感于大自然中天地万籁、自然及鸟鸣之声,有感于神话“伶伦造乐”之精神,在精致细腻的笔法下,以“音响拟态”思路,在五个乐章的连续中,传达出作曲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情怀的理解。作品中精彩之处在于:其一,作曲家极为精确地以动态音响材料,惟妙惟肖地模拟出体型、种类以及神态各异的鸟类,这尤为突出地体现在第二乐章中;其二,作曲家以强大的音响叙述逻辑,将五个乐章组织起来,使作品陈述时表述完整、没有跳跃感,并最终传递出作曲家热情、积极的人生态度(见表3)。
音乐会后,大家讨论着、评议着,久久难以平静。这其中,充满了对想象力的赞许、对音乐艺术品的尊重以及对于智慧的憧憬。或许,品读这种凝结于音乐艺术品中的智慧,是艺术家们攀登音乐高峰的有效途径。
二、民族室内乐队作品中的智慧——艺术化的“构思”与“表达”及二者之间的“自洽”
对于中国作曲家来说,在为民族室内乐队写作时,必然会“自觉地”思考及表达其所理解的“中国文化”,这无需强调。只是,相对于管弦乐队,因受编制,乐器性能、音量、音色,演出场地和表现力等因素制约,写作民族室内乐队时会显得“困难”一些。因为,作曲家难以像构思管弦乐队那样去实现声音想象,而是需要根据编制、乐器性能等条件限制,“换”一种写作思路。于是,如何“构思”与“表达”便成为创作中的关键之所在。这样,如何通过艺术化手法,使作品既不俗气、能准确地传达出意境,又能感染听众,则成为衡量“构思”与“表达”能否自洽的标准之一。此场“民族室内乐作品音乐会”所委约的6部作品,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路(按演出顺序)如表4所示:
第一首作品是龚晓婷的《山居竹春》。在作品演出之前的导读中作曲家介绍道:“该作品灵感来源于阅读唐诗……,题中的“竹春”是指农历八月。”? 因此,该作品实际上是想要表达她对于色彩斑斓般的秋天的感受。正如作曲家所言,该作品用调性化的音乐语言,以旋律性的线条和音高造型为载体,宛如一幅幅唯美画面的联展。二度加四五度大跳所构成的音高关系作为整部作品的核心材料,作曲家通过对该材料做出节奏、时值、音色、音区等变化生成形态各异的“同源性材料”,并用于主题陈述及织体写作中。而后,以不同形态出现的主题来描述一幅幅唯美的画面。整部作品由动静相交的四个部分构成,由此完成作曲家对于色彩变化的表达。第一个部分(第1—52小节)以静态方式展现出7个“唯美画面”,其中第五个画面(第31—36小节)因其换调而使音乐有升华之感;第二个部分(第53—138小节),则通过两种不同的动态描述,使音乐性格从“活跃”逐渐到“运动”,在第二个动态描写(第70—138小节)中将音乐推向高潮。第三个部分(第139—167小节),以从动到静的方式,“再现”了之前的唯美画面。所不同的是,这里的“再现”是一种情绪的升华。第四个部分(第168—195小节)作为尾声,则以动态方式总结了前面出现过的主题素材,使音乐在全奏中结束。应该说,作品中这种画面的瞬间变幻和结构之间的突然转换,与作曲家的表现意图是贴合的。
第二首作品《生生不息》则以一种“直抒胸臆”的方式,呈现出了萦绕于胡银岳心中的意念。该作品有感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譽?訛,作曲家将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的感悟转化为两个主题材料,即“觉姆主题”和对转经筒的动态描述。在表达时,作曲家并没有去刻画“场景”或“场面”,而是将一遍遍萦绕于心中的主题和印象,以变奏思路使之不断“轮转”,并通过音乐的发展来象征“生生不息”之寓意。这使得整个作品干净利索,一气呵成。在结构作品时,胡银岳将转经筒的“无穷动”作为结构基底,并发掘“觉姆主题”的动态化特征,由此构成音乐得以快速轮转中变奏、展开的主要因素。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在第三首作品《夜歌》中,陈泳钢则提供了一种如何围绕所引用的民歌素材?譾?訛及其表达内涵,通过对民歌素材的艺术化构思,使其为“我”所用,从而使作品实现表达清晰、具有感染力的思路。该作品以民歌《苏武牧羊》及其中所蕴含的思念之情为核心,采用调性化的音乐语汇,以具有三部性关系的五个部分,从抽象到具象逐步引导出“民歌原型”,使之得到情感升华,并被听众所理解。第一个部分(第1—82小节)以原民歌開头的五度大跳为核心素材,通过对该素材重构,以慢速、片段化方式,在呈递进关系的两种情景中,陈述出意境和思绪。在陈述时,作曲家频繁更换节拍,从而在不规则律动中实现“思绪”的自由衍展。在第二(第83—108小节)和第三部分(第109—163小节)中,作曲家将重构后的音高素材自由衍展,通过对片段化素材的音色配器,使其具有幻想色彩,并使之在第三个部分中得到展开。第三部分是整部作品中节拍变换最为频繁的部分,甚至会出现一小节一换节拍,从而实现音乐紧张度的递进。第四个部分(第164—201小节)虽然是第一个部分下四度的“再现”,但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出现了由重构素材演变出来具有抒情性的独奏线条,这为民歌原型的出现做好了铺垫。第五个部分(第202—216小节)中,民歌原型在经过之前的抽象后,在这里得到具体地陈述,且节拍不再频繁地变换。应该说,民歌原型经历过之前的抽象在这里出现时,不仅增强了它的表现力,还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颇具感染力。
第四首作品《寒山》是郭文景為了缅怀罗忠镕先生,并纪念勋伯格逝世70周年而创作。为此,郭文景在作品中使用了《一个华沙幸存者》的序列,但从写作技术和表达意图上则展现出作曲家个人的鲜明风格。第一,与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术不同的是,郭文景在这部作品中并不是探讨如何以十二音思维来构思和组织音高逻辑;第二,让十二音序列不必在设计之初便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第三,在上述前提下,能否用“十二音技术”来实现中国式的“意境表达”,并借此探讨十二音技术的表达边界。如此,作品中“用了什么材料”,反而不如“怎么表达”更为重要。
基于上述,作曲家采用民乐室内乐的形式(六重奏),使用了梆笛、曲笛、高音笙、次中音笙、大阮和管钟六件乐器,并对乐器做出了一定的“符号性”设置。如,用管钟来表现“寒山钟鸣”;从竹笛中还可领略到《竹枝词》中的意境,能听得到鸟的鸣叫,还能感受出“山风瑟瑟”。由此,作曲家实际上是通过曲调或音高及节奏造型,来塑造一种可被中国听众理解的“符号性”声音,从而通过营造“冬日氛围”中的写意性画面来实现表达意图。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是“冬日氛围”,显然与使用十二音序列音高材料的基调相关。在结构作品时,作曲家以“散引”(第1—5小节)—“慢”(第6—36小节)—“渐快”(第37—138小节)—“慢”(第139—156小节)—“散”(第157—161小节)—“尾”(第162—177小节),这样几个在速度上呈对称关系的部分安排结构。在结构内部及其之间,都会有“钟声”作为符号,象征着结构的开始或结束,以增强理解。
第五首作品《小组曲》是整场音乐会中唯一使用独奏乐器的作品。青年作曲家纪宇用三个乐章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情景和心境。整部作品意图清晰,音乐干净明亮。作曲家虽然为作品设置了一个五声性的短小主题(第1—3小节),并将此作为核心素材,从中剥离出一个短小的动机(三连音节奏下的二度加三度音高组合)贯穿于三个乐章中,但他在创作时却非刻意地追求五声性风格,而是追求如何将“这一乐思”在一点点地衍展铺陈中来表达心绪。由此,作曲家设置了慢—快—慢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主题在单簧管的高音区陈述,塑造出一种色彩明亮的思绪,乐队主要作为点缀与单簧管声部交相呼应,音乐以变奏思路一点点衍展铺陈。第二个乐章具有舞曲性格,音乐欢快,乐器组之间的“无准备换调”使音乐色彩鲜艳。在该乐章中,作曲家将民间吹打组合以及紧打慢唱的形式用于音乐中,尤其是作品的第59—65小节中,乐队的点状弹拨与单簧管的线条陈述,以“螺蛳结顶”的手法形成一种民间吹打的效果。第三个乐章回到慢板,音乐抒情甜美。在该乐章中,作曲家以琵琶声部衍生出的主题作为“固定旋律”,单簧管则以核心动机为基础做自由延展,从而使音乐在“固定旋律”贯穿下,其余声部展开自由变奏。
应该说,整部作品由同源性的主题控制,让乐思在一点点衍展变化中表达思绪的做法与作曲家的创作初衷是贴切的。
细听最后一部作品《倾杯乐》,自然、流畅、轻松,没有过多的灌输感,这反而可使人领略到其中的“潇洒”“随性”“快意人生”。陈欣若通过对多种风格音乐素材的运用,来象征和表达“兼容并蓄”,并由此展现了他音乐创作中“风格复合”的思路。首先,作曲家在每一个排练号的后面,都引用了一句唐宋时期不同诗人的诗句,诗句之间并无内容上的关联,仅仅是所引诗句均与“酒”相关。由此,其引用的目的并非是像标题音乐那样去表达诗句内涵,仅是借用诗句中的情绪或氛围,传达出一种酣畅淋漓、快意人生的心境。其次,作曲家在作品中设置了若干个具有清晰“风格符号意义”的音乐素材,通过将其音色化配置,以实现听觉的可理解性。如,对京剧和大鼓的风格,通过琵琶或竹笛的曲调来表达;文人风格则通过古琴音色和古曲风音调来配置;对民间吹打,使用打击乐和笙来实现;而异域风格则,则通过改变京剧风格音乐素材的音高关系,以管子和琵琶音色来实现,如此等等。再次,很讨巧的是,作曲家对民族室内乐乐队的运用思路做出改变,将其以“大协奏曲”的乐器和音色使用思路重新配置;将竹笛、管子、笙、琵琶、和古琴作为独奏音色,充分运用其音色象征意义;将古筝、扬琴阮族和二胡组用作乐队音色提供支撑。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不仅将打击乐器用于节奏性及风格性陈述,还将其用作“共鸣性”乐器来贯穿作品,以此服务于“风格复合”。应该说,将打击乐贯穿整部作品,是作品音乐风格不突兀的关键之一。
最后,在组织作品的结构时,作曲家以京剧风格素材贯穿始终,在内心听觉支配下,以六个“情景逻辑”相互关联的部分完成陈述,使思绪如同“图画展览会”一般,呈现出“内心—古境—市井(包括异域)—内心”的画面联觉,并由此在多种风格的音乐素材纵向叠置中,合理地实践了“风格复合”。
结 语
蕴含于“音乐艺术品”中的智慧是多样的、多维的,因而,发现它的角度也应当是多样的、多维的。同时,“音乐艺术品”之所以能够得以展示出来,也是与其背后的强大支撑密不可分。除了坚实的物质支撑之外,对于艺术创作的尊重、对于作曲家艺术追求的肯定,显然是此次新作品音乐会得以成功举办的关键之所在。
(责任编辑 李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