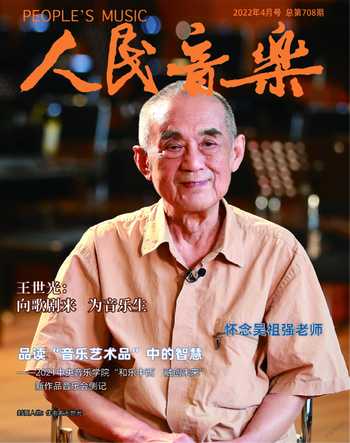托命于中国传统音乐理想
2022-04-27萧梅
们都叫他“老乔”,即便在他未老之时。
虽然在中国人的语境中,称“老”代表一种尊敬。不过在“左家庄·新源里”?譹?訛,楼上楼下直呼“老乔”的招呼里,却有着多样和复杂的内涵。老成、持重、亲厚,或是“老黄牛”……这个“老”,更多的是一种意象。说亲厚,我们可以不计师长,没大没小喊他“老乔”;但“老黄牛”却真可以牵引出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学者型“所长”的负累。
年轻人难以想象,在1988—2001老乔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大部分日子里,全所每年的拨款经费约四五十万,这些经费包括了八十余位在职和三十余位退休人员的薪酬、工作运转以及“新源里西一楼”的水电费。我曾经听老乔回忆音乐研究所当年经费困难的窘迫,其中有一个“水管漏了”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办公楼的水管漏了,检修工发现不了漏水处,看着楼里的水表哗哗哗地转圈,每转一圈都是扔出去的水费。老乔只能到处求人,乃至求到了北京市朝阳区里的领导,再通过领导层层找关系,最后找到朝阳区的自来水部门,总算是找到了原因。那个年代,年年打报告申请经费是老乔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居于“新源里西一楼”的音乐研究所,不仅储藏着全世界最为丰厚的音乐文化资料,包括乐书、乐谱、乐响、乐器等中国音乐研究资料的“黄金甲”。也凝聚着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学前辈们代际传承的心血和学统。要守住几代人艰辛立业开创的学科基础,要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继续“举步维艰的学术探索”,包括1985—1988年黄翔鹏先生任所长期间创办的、为中国音乐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再度起步意义深远、并充分体现音乐学术格局的“三刊”?譺?訛,老乔和所里的同仁们可谓劳心劳力。在《十年感言——贺〈音乐学术信息〉创刊10周年》一文中,他描述了该刊在草创的油印本阶段“每印好一期,音乐研究所的会议室就成了临时装订场,大家一边装订、一边装入信封”的情景。但面临“每年的费用由几千元上涨到上万元”“每年花销几乎都要所里自筹”等现实困难,因此“每至年终”“都要在‘办’与‘不办’之间作一抉择”。办下去的决心,不仅在那个年代成为“将百年来音乐学这一大文化中的小学科的某些历史踪迹以及世界各国音乐学家对诸子学科所作的探索思考,有选择地介绍给国内同行”,也反映着当年音乐研究所“学术情报研究室”同仁们“对学术的责任感的历史性认知”。
我入职音乐研究所较晚,有些事是听说,有些事是亲历。记得1996年所里承办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9届年会,老乔延续“开门办所”的方针,一如以往为办成每一件学术活动和学术出版所采用的办法,联合了曲阜师范大学以及山东省文化厅、山东师范大学等文化、学术机构共同承办。在筹备之时,我曾和“小韩”(锺恩君)、振涛与他共赴山东,并在济南见到了时任山东友谊出版社老总的徐世典先生。这位老乔的“老朋友”曾在《中国音乐年鉴》最困难的日子里以他工作服务的山东教育出版社无偿出版了1990—1992卷,并在自己调往山东友谊出版社后继续承担了1994卷的出版。1995年音乐研究所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后,老乔写下了《四十年淡泊寂寞、几代人艰辛立业》的文章,并为自己、也为音乐研究所做了一个“痴梦”:“终究有一天,音乐研究所会搬进一个极富中华民族特色,而又非常现代的大厦内。大厦的中心是我们几代人用心血积累起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同时大厦内有中国音乐研究中心;中国音乐陈列中心;中国音乐培训中心;中国音乐表演中心;中国音乐演讲中心……”因为他坚信,“沉寂了八千年的中国音乐一定会以它特殊的光彩触动某个‘上帝’,被触动的这个‘上帝’也一定会为它缔造一座与这个伟大民族文化相匹配的归宿之城”。
虽然在他离任之时,这个“上帝”并未出现,但那个年代还是有一些为音乐研究所内涵而感动的人,他(她)们以不同的方式伸出结缘之手。其中就有台湾地区原国民党主席的洪秀柱,在1990年代中期化缘60万台币,为音乐研究所购置了第一批286台式电脑。记得当时作为所长助理的学友“小韩”,就在这批办公用的电脑上,写下了《中国音乐年鉴》资料库计划,那个计划包括了音乐家档案、音乐学术档案,作曲家作品档案、音乐活动档案、音乐单位档案、音乐表演团体档案,音乐出版档案的集合——这也是一个至今亦未过时的“痴梦”。
同样作为四十年所庆活动高潮之一的“中国古琴名琴名曲国际鉴赏会”,应该是音乐研究所“文革”之后重为中国琴学复兴的一大举措。这一活动不仅留下了四张珍贵的唱片,也留下了一间由香港琴家资助的名琴展室“知音斋”。鉴赏会上,启功、周巍峙、黄胄、米南阳、高占祥、冯其庸、吕骥、李焕之、王世襄、蓝玉崧等都留下了墨宝。为鉴赏会提供活动经费资助的是“北京薪传文化顾问事务所”,这个事务所的背景是当年中国音乐学院的一拨中青年教师,它的实际领导人是李西安教授,我也是其中的参与者。
如果说音乐研究所建所之时的前辈们,为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和资料建设“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百废待兴的20世纪最后20年,音乐学界许多希望能有所作为的学者们,亦在各类尝试中“上上下下筹经费”。我不止一次地听老乔说,在有限的经费中,他要推进的工作是围绕中国传统音乐,一次次活动、一本本新书、一次次展演,有多少做多少。因此,他的精力大量花在申请资助、行政管理、学术规划、四方化缘和实施中,只能在“所事”“家事”的空隙中挤出时间,写出一篇篇“独行之文”。今天,当九卷《乔建中文集》付梓之时,这类“所史”“学史”“心史”的文论,真应当成为年轻学子的必读!
话说回头,“老黄牛”的辛勤中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事,那就是老乔对于全所各类往来经济账目的清晰。他从不借助工具,几十万、上百万的经费,每一笔都可以在大脑中细细算来。笔者亲历的1995年全国首届鼓吹乐研讨会,1998年的全国首届旋律学研讨会,1999年的香港艺术节“乐种——中国传统乐器的不同组合”以及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2000年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合作的“唐宋元明清百琴展”,2001年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中國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于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展”,2001年与常熟市政府合作的“全国第四届古琴打谱会暨国际琴学研讨会”,如此等等。甚至于在他2001年卸任前的审计中,他都能对不同渠道、不同使用、不同来历去向的每一笔经费“口头交代”,他的心算常常快过了财会的算盘,因此,我总在想,老乔真的是怀揣“一本账”。
人生在世,各寄其志,各显其能,各有所归。老乔说:“音乐研究所是一个环境,是一种氛围,也是一片安身立命的基地。”(《现代琴学论纲》)自1967年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又在中国京剧团、山东省艺术馆历练了传统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1978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郭乃安、简其华先生获硕士学位,1981年供职于音乐研究所。20年中汲汲于中国音乐学中心领地深厚的学养中,他的心里还有一笔账,这笔账,就是他反复咀嚼的20世纪中国音乐,尤其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当代历程。
曾经有一个学生问过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地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音乐及其研究在20世纪的经历呢?我告诉他,問学虽然没有捷径,但如果允许我们打开一张20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生态的索引之网,唯乔建中的“独行之文”集——《土地与歌》《国乐今说》《叹咏百年》《乐事文心》《乐人行旅》《乐论杂俎》。这六部先前已经出版的文集,所涉领域之广,包括了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歌舞五大体裁分类;包括了宫廷、文人、宗教、民间的四分类;以及学科及研究领域和方向分类的音乐地理、区域音乐研究、音乐教育、中西音乐比较、音乐学总论等等。表面上看,除了研究型论文之外,他所耕耘的写作文体可谓繁杂:序跋、乐评、综述、访谈乃至会议致辞,但这数百篇的“独行杂文”,皆无应景之作,仔细读来,那些围绕世纪之交的诸般乐态、乐作、乐事、乐论、乐人跃然纸上。记得我初入音乐研究所时,老乔就将几个全国性学术活动的综述任务交给了我。几篇综述之后,还曾有人戏谑我为“萧综述”。然而,个中收获,冷暖自知。数年之后,我也开始有了写序的邀约,下笔之际,深知其难。因此,翻阅老乔的六册文集,于“小巫见大巫”的慨然之际,更深地感受到此类“独行杂文”对于人的历练。老乔无论写事还是写人,有着他自己的思路风格,那就是除了艺术特征的分析评述之外,必将所论置于领域史、艺术史、人生史和社会语境之中。如此,见微知著,纲举目张。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老乔的“杂文”特点之所以如是,与他孜孜不倦地读人、读书、“临响”分不开。在他的许多文论中,你可以看到读书笔记的基础,并想象他在相当长的一段“厨房”写作和见缝插针于行政之余的勤勉。那都是围绕各类文献逐篇细读,边读边记,边记边思,感发思想,点点滴滴,聚沙为塔。正如他自己的剖白:他的那些评论都是“几十年实地考察教育传承和学术研究等多方面实践之后的点滴感悟,关注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不断发生之‘事’,用中国传统人文之‘心’作一己之叙说”。(《乐事文心·序》)就老乔所撰写的诸多音乐大家或者乐坛新秀的书序和唱片、音乐会评论,我不想多说什么,仅举一例,老乔近年来还曾为西安音乐学院陕北民歌班的毕业生撰写其音乐会的文案。在此文案中,每一首民歌的来龙去脉,他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这又是什么精神呢?故此,老乔之“老”,其亲厚,核心还是在“仁”。承上启下,有容乃大。
因此,就“老”之意象而言,老乔并非埋首拉车不看路的黄牛,而是识途的老马,不断在扎实的资料、严谨的学术、深厚的历史感中驰骋。一部全集如同一个人的历史,掩卷之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乔建中文集》充满了对20世纪的关注。那是一种对一个时代和一个人基于自我认知的自觉反省。
我们究竟为历史增添了多少新内容?在创作探索的路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我们曾面对何种挑战?还有什么应该向历史交待的地方?
——《中国民族音乐十年》
在中西之交、世纪之变中的中国20世纪音乐:对于成为历史的20世纪,作为一个音乐人,有哪些音乐之“事”我们不应该忘掉呢?又有哪些音乐之“事”应该成为我们的“师训”呢?
——(《世纪音乐感言》)
中国音乐有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要不要建立这样的体系,我们有没有能力建立这样的体系?
——《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
……
如此等等。他特别地强调要把20世纪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单元”来考察。当我读到他对于马达所撰《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序时,也不免想到在我写完《1900—1966中国大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后他一直再追问,何时能续写后34年,至少是续写1980年后的20年。他的催促和追问,他始终认为:“20世纪对我们有多么重要。我们生活在20世纪,20世纪不仅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而且,极大地改变整个人类社会。因此,重新认识20世纪,也就成为各人文社科领域直面新世纪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序》)
将自己嵌入一个特殊时代,并力图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部分,或许是我们研究定位的应有之义。也正是在对这一历史的反复沉思中,老乔的笔触也反复讨论着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关注着传统、新传统、后新传统的当代音乐现状。比如,在对二胡现代精神的讨论中,他虽然指出“这件乐器要进步,必须与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表现他们的精神境界”,但他也提出“在琴曲的创作上,古琴很少有什么突破,与二胡琵琶、古筝的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如果说现代琴学有什么特征的话,那么保护传统,尊重传统,整理传统,就是它的头一个特征。为了不断推进琴在新世纪的发展,20世纪琴学的这个特征完全值得今人当作一个重要课题加以总结”。(《20世纪琴学论纲》)这并不是矛盾,而是领悟和把握具体问题及其语境的深度。由此,20世纪的整体历史,20世纪有过的弯路、曲折、艰辛以及创造和奋进,20世纪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才成为一个“完整历史单元”,缺乏对其嬗变转型的深刻认知,又如何望向未来?
不过,老乔归根结底是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人。尽管在他的文论中,对传统音乐与当代音乐创作,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发展用墨颇浓,但他对于土地和歌的深情,还是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中国传统音乐上”(《中西音乐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即便偏颇,也如此选择。我们可以从他离任之后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看到他在21世纪的头20年里,对于传统的传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知灼见,看到他不断的历史一贯性的思考和实践作业。
说一千道一万,当阅读和学习“老乔”——乔老师文集,并再一次以晚生身份撰序,我内心其实是惶恐的,我更不想多说学术的“志业”或“理想”。也许,老师辈或说老乔这一辈学人的学术理想,并非有什么“想这样”或“想那样”的初心。他们只是在时代的动荡中起伏磨砺,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的背后,更多还是那些对人、对事、对乐;对土地、对家乡、对先辈“不辜负”的朴素情感。
独行之文无尽,老乔从不孤独。
2001年乔建中退休之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位于北京市左家庄新源里西一楼。
《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音乐学术信息》。
该事务所的工商登记者为张鸿懿教授的弟弟张鸿正,事务所中的骨干分子还有笛子演奏家张维良等。
萧梅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