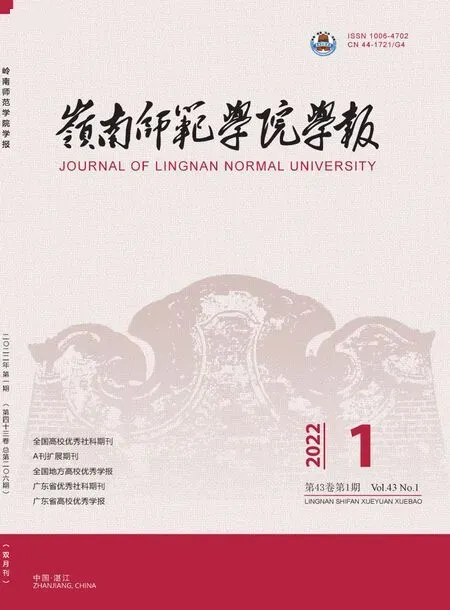公共阐释之三种理论走向反思
2022-04-26蓝国桥
蓝 国 桥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张江指出我们应开放地建构出自主性的中国文论,要不然我们不仅将如人所说严重“失语”,而且还会在理论上“失踪”。“公共阐释论”是旨在“阐释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1],是中国当代自主性文论建构的某种“自觉”。后来他还就该问题,与哈贝马斯、费瑟斯通、朱立元等中外名家,进行对话,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证,成果见于《哲学研究》《学术月刊》等刊物,是他创建中国阐释学派的重要举措,足见该问题的重要性。目击“公共阐释”论域,至少有三个问题走向难以回避,需引起我们的关注:由“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的深层机制何在;“公共阐释”的居间言说特点何是;及其理论资源的“中西融合”走向何如。
一、从“强制阐释”转向“公共阐释”
“强制阐释”是破中有立,更多偏重于破;而“公共阐释”则立中有破,更多偏向于立。可以说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是在破立结合中由破往立的有序推进。“阐释”方向由“强制”往“公共”的改弦更张,既有我们自身文论建设的实际需要,又有理论“强制阐释”本身的弊端促动。“强制阐释”因纠缠于“时间”的内感官而起,而“公共阐释”则围绕“空间”的外感官转动,因而其客观性、公共性更加显著。
首先是“强制阐释”的扭曲挤压,使得中国当代文论远离鲜活生动的文学场,进而容易把其推向险恶的异化深渊。中国当代文论实践所操持的话语,总体上带有双重“强制阐释”的特点,与具体的文学场相距甚远。当代学人群体阐释中国文学文本,大多喜好征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征用的结果是,迫使原已存在的中国文学经验,与所征用的西方理论相符合。本土文学经验只是注解西方理论观念的“正确性”,其所扮演的角色尴尬。如此“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213的“强制”做法,实是由来已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固然有“现代性”的开创之功,但却是“强制阐释”的始作俑者,不过后来有文化担当的王国维已幡然醒悟,他在《人间词话》中便以“本体阐释”置换了“强制阐释”。当代学界未能在王国维醒悟处起步,非常不幸地使“强制”之风气愈演愈烈。之所以说不幸,是因为中国学人所喜好征用的许多西方现代文论,原本就不是生成于文学场域,而是直接从哲学等领地粗暴地挪移过来。照此一来,西方现代学人进行文学批评,阐释的其实只是哲学等观念,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只能强迫文学文本与哲学等理论相契合。而各种文学文本,注解的也只是哲学等观念的“正确性”。西方语境中的哲学等理论与文学文本之间,显而易见已有点“隔”。伊格尔顿披露了当中的秘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皆远不止于是文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纯粹理论的情况,因为纯粹理论中实际上极少有什么是在文学竞技场中起源的。现象学、诠释学和后结构主义是哲学潮流,精神分析是治疗实践,符号学是有关符号的一般科学,而不仅只是有关文学符号的科学。新历史主义试图抹去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就像结构主义在它的年代里也曾做过的那样。”[3]5西方各种“主义”与“学说”等的“纯粹理论”,“极少有什么是在文学竞技场中起源的”,“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之间的区别”边界是模糊的,“强制阐释”已是昭然若揭。当我们再以西方林林总总的“强制阐释”理论,来批评中国文学文本,将会进一步加重“强制阐释”顽疾。历经双重的“强制阐释”,中国当代内敛“文学”的“理论”已渐行渐远,“理论”疏离了“文学”出现了异化。为了消除异化病痛使“理论”回归“文学”,恰当的选择只能是告别“强制阐释”。
其次则是由于“强制阐释”的主观论色彩,有意遮蔽了文学文本的本真面貌,致使批评沦落为呓语般的私人言说。“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核心因素和方法”[4],自然是“强制阐释”最突出的缺陷,因而“强制阐释”难以抹掉其主观论色彩。根据这样的理解,“阐释”之所以被定性为“强制”,主要是因为阐释者已事先生成某种先见、偏见、私见,而这些多是从文学场外有意征用的结果。阐释过程就是强制特定文学文本与某种先见、偏见、私见相一致。阐释结果于是就架空了文学文本,与文本实际没有多大联系,甚至背离了特定的文本,留下的只是批评者自己在言说,或者说是他借用的理论在言说。阐释活动的主观性、随意性、任意性就非常明显。导致的后果套用法朗士的话来说,就是“我阐释的就是我自己”,作品及其内容的完整性必招致肢解。如此这般的情形在阐释活动中较为常见。同是面对“青年马克思”,不同的“我”会看到不同的“马克思”,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家对象化了的“马克思”。“就是说,熟悉黑格尔的读者在读1841年的博士论文时,甚至在读《1844年手稿》时,‘将会想到黑格尔’。熟悉马克思的读者在读《法哲学批判》时,‘将会想到马克思’”如此等等[5]40-41。“我”就容易凭借先前就拥有的“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观念,在实际文本与思想上面覆盖了一张目的性很强的厚网。顺着这样的思路,伊格尔顿也指出,在批评者与作品之间横亘着现成的理论,这张厚网的存在与过滤作用,使得作品的少部分内容呈现出来,其他部分不是遭受扭曲,就是被无情掩盖,总之它不能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批评者贵族般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6]90-91。西方情况如此,中国也不例外。面对同一部《人间词话》,熟悉国学的从中看到国学,熟悉西学的从中则看到西学;了解词学的从中尽看到词学,了解佛学的则从中看到佛学;钻研叔本华的从中看到叔本华,认同柏拉图的从中则看到柏拉图,谙熟席勒的从中则看到席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同是批评《红楼梦》,喜好叔本华的王国维,从中看到了意志及其痛苦;而偏好存在主义的学者,会从中领悟到时间性焦虑;熟悉传统文化哲学的,从中则体会到儒、道、释等思想。每个人批评某个文本时,看到的只是他自己。文本的某一方面,只成为“我”的镜像倒映。批评者最需要做的就是从自我的房子里走出来。“公共阐释”已是呼之欲出。
最后是由私人言说的主观主义再往前推进,容易滋长理论上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弊病。相对主义的意思是指,阐释活动由于缺乏确定性,没有稳定的边界约束,因而可以做无边游动。因为怎样言说都行,阐释的主观主义往前再迈进,就容易走向相对主义。而虚无主义则是指,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一切坚固神圣的东西也已烟消云散,历史及其所谓的“意义”,都只源于人为的主观设定。阐释的主观主义对文本与现实的架空,再往前便会导致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是一对孪生姊妹。西方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理论,相当一部分受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牢笼的束缚。现象学突出意识的意向性,并强调其在意义产生上的主导作用。现象学虽模糊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边界,但它的“唯我论”色彩却已是相当浓厚。受现象学运动的深刻影响,有些理论家便指出,“我”(意向性、读者)存在的独特状况,便能直接赋予作品以意义。他们眼中“我”存在的流变性与作品意义的流变性之间,便跳起了和谐的双人舞,于是“我”的存在千变万化,作品的意义也千变万化。伽达默尔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存在主义的无穷体验等,都在高举着小写“我”的旗帜。分析哲学的理论言路,与现象学不甚相同,它们以语义的确定性为追求目标,但至少在后期的维特根斯坦那里,最终却以感觉与经验的变动性,取代了科学的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彻底捣毁了确定性的最后根基,它们消解一切、解构一切,虽在冲击、反抗僵化与固化方面有积极意义,但“什么都行”的价值论立场坚守,却使自身陷入相对主义泥淖。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影响也好,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罢,它们最终都是回归了生活之流,都企图以生活之青树对抗理论之灰色。竭力使理论决然回归生活之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旨趣。不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却对卢卡奇理论的整体性与乐观性,流露出强烈的不满,阿多尔诺与本雅明尤其如此。相比之下,他们两人对历史更感悲观、绝望,他们也更愿意相信碎片、痛苦的力量。新历史主义无暇顾及历史的苦难,它们模糊了想象与历史的边界,从而将真实的历史虚无掉。为消除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阐释弊病,更需推行“公共阐释”。“阐释”之所以能成为“公共”活动,至少还与它的中介品格有关。
二、“公共阐释”的中介特质厘定
“强制阐释”以“我”为出发点,很难保证阐释的公共性。阐释成为公共活动的有效办法是,使“我”向“你”“他”开放。阐释活动能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中介所起到的恰是桥梁的作用,它是连接两端的功能性力量。阐释活动能连接“我”与“你”“他”,其中介性便异常明显。或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江以“居间言说”[1]来指称这种特点。我们如果能进一步证实阐释活动的中介性,就可以指明阐释不是私人而是公共的活动。
阐释活动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内层。内层指的是阐释活动的主体,直接面对特定的文本,竭力将文本有效穿越,进而揭示其中意义。阐释者要求具有主体性,如此他便在阐释活动中,处于积极能动的地位。而阐释者所面对的文本,是意义的凝固定型样态,它是客观的存在,一般不可改变。由于文本是意义的凝聚,因此阐释活动需重新激活凝聚的意义,并展现活的意义世界。阐释者与文本、意义三位一体。根据贝蒂的意思,“阐释者”是“主动的、能动的精神”,说的便是阐释者的主体性;而作为主体性的阐释者,要穿越“富有意义形式的中介”,才能进入“客观化富有意义形式里的精神”世界[7]129。就内层而言,阐释活动是精神主体与精神主体之间,仰仗文本(形式、符号、语言)所进行的交流,朱立元说这也“是一种主体间性”[8]。其二则是外层。外层是指,阐释者将穿越文本之后所领会到的意义,毫无保留地传达给他者。阐释者向他者敞开自身。其三是中层。中层介于内层与外层之间。为更好地领会文本意义,阐释者尚需与作者联系起来。作者的“存在”可促进他的意义理解,他也要经受作者的拷问。另外阐释者向他者传达的文本意义,也一并将作者的“意图”传达,否则阐释将变得残缺不全。阐释活动由内层到外层扩展有中层连接着,中层在此便是中介性的“居间言说”。而每一层次本身,又都表现出中介性。
内层的基本图式是:阐释者—文本—意义。内层是阐释活动的核心,它的内容大致涵盖两个问题维度。第一是文本及意义的维度。文本及意义如何展现与如何生成,乃构成文本及意义理解的一体化格局。第二则是阐释者的维度。它要解决的问题是,阐释者如何“公正”地进入文本,然后领会文本意义。而阐释者应具备相应的“素质”,才能在文本意义的阐释上,做到“公正”不阿。阐释者“素质”的找寻与厘析,因而是要害所在。两个问题的澄清与应对,方能保证阐释的公共性。文本的存在千差万别,文本的意义各个不同。文本及意义的差异,并不是随意阐释的借口。事实上在文本及意义差异性的深处,我们还是能找到某些共通性。文本首先是言语的个性化铺排。它是指不同作家之间以及同一作家不同文本之间的文本言语差异。言语的背后是形象。形象是想象性的生成,因此带有直观性。形象并不空洞,而是连接着“生活”中的情思。文本的言语、形象与情思,往往是浑然无间,其根源于天才的创造活动。天才的创造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转动。想象力生出“审美理想”,但知性却无法穷尽对它的说明。天才在机能的和谐运转中,将“审美理想”通过言语传达出来,文本及意义便随此生成。文本是言语、形象与情思(“审美理想”)三者的共生,文本的意义因而是三者的共振。文本意义的阐释,只能在言语、形象与情思的共振处凿开缺口。意义便可在缺口处喷涌出来。喷涌的意义隶属于特定的文本,因此意义的阐释不能漫无边际。文本意义缺口的顺利开凿,取决于阐释者的存在状况。阐释者面对文本,需做到全身心投入。全身心投入,即是各机能的谐和转动。一言以蔽之,阐释者以审美判断为契机,使感性、知性与理性高度统一起来。感性是感觉的机能,它以身体感受作为转动的轴心[9]38,因此情感与想象等隶属于感性。知性是概念—逻辑的能力。理性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运用,它是把握整体—原则的机能。在文本阐释的过程中,阐释者先以知性撞开言语大门,转而在言语符号编织的迷宫中穿行;之后他需在符号迷宫的穿行中激活感性能力,让想象的翅膀随言语飞翔,并以身体感受为基础构建形象序列;最后是阐释者对形象序列感同身受,还原情感体验,领会思想内容。我们此处所标识者,只是意义理解的逻辑先后顺序,实际上在具体的阐释活动中,言语大门的撞开、形象序列的构筑与情思内容的领会,常常是同时进行的,因而感性、知性与理性诸机能在深层里相互交融。相互交融的前提除了需下审美判断,还要各机能在使用中消除掉个人主义的狂妄。而个人主义狂妄避开的关键,是感性、知性与理性机能及活动,需要接受他者的“公正”检验[10]5-7。文本及意义维度与阐释者的阐释活动,就因为有如此对应性的建立而使阐释变成公共活动。阐释者拥有的对象意识,也是保证阐释活动公共性的重要条件。
中层的大致图式则是:作者—阐释者—他者。作者是文本及意义的直接创造者,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现代以来理论家们一个极端的做法是,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剖析作者的内在世界,来透视文本的意义世界,因为他们认定在作者的内在世界与文本的意义世界之间,存在着重合性关系。两者之间是否真能建立重合性关系,倒是可以商榷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指明了作者与文本及意义联系密切,倒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之所以可以商榷是因为,假如是考虑到文本之间的差异,两者的重合性关系,在局部上当是可以建立。如果是写实性的抒情文本,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在两者之间,建立起若干的对应性联系。如此一来,我们一方面只要通过考量作者的“存在”,就能很好地理解文本表达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我们仅凭穿越特定文本,也能知晓作者特定的“存在”状况,如他的性情与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境界高低等。阐释者在阐释如此抒情性文本时,就得面对作者的审问。只要是这样,阐释者就不会对文本妄加揣测。如果是虚构性的叙事文本,如小说文本与戏剧文本等,作者与文本应是有联系,作者的“存在”状况也有助理解文本“意义”,但它们一般不会是镜子般的映射关系。作者的运思与文本的虚构,都会设置诸多理解上的障碍,因此要在虚构文本中,寻找作者的“真实意图”,大多是费力而不讨好。阐释者也就不应随虚构文本一味地虚构下去,对文本作随心所欲的阐释。其中的原因倒是不难明白,因为阐释者还需面对“他者”目光的严厉审视。这里的“他者”既指一般性的特定文本的“读者”,又指那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群体性“读者”。前者不受特定利益驱使,后者则受职业操守规约,他们都能对阐释活动“公正”与否做出裁定。中层图式的意思是,阐释者必将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向他者真实无妄地传达出去。
外层的基本图式是:文本—阐释者—他者。外层图式中的文本是复合型所指,它指围绕文本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文本的意义世界与作者的“存在”在文本中的意义、意图折射等。该图式所表达的意思是,阐释者将文本原意,完好无缺地传达给他者。所谓完好无缺是指,阐释者不篡改文本原意,他者亦能领会文本意义。而不篡改说的则是,阐释者不改变文本原义,连带将作者“意图”一起,毫无遮蔽地传达给他者。能领会则是说,阐释者将领会的文本意义,向不同的他人传输,在不改变文本意义的前提下,因人而异地陈述其意义,让不同的他人都能明白文本意义,这也是阐释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两者合起来,想表明的基本立场是,阐释活动的面貌,会因阐释者而会有差异性,但始终不会扭曲文本意义。外层涵盖了中层与内层,阐释活动“居间言说”的中介功能,在这里体现得最为充分。“中介”原是西方术语,用它来言说“公共阐释”的功能与特点,已涉及一部分理论资源的汲取问题。
三、理论资源的“中西融合”趋向
融合中西的习惯性做法,是将西方形式(观念)与中国材料(经验)融摄。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是用西方观念对中国材料,作出差强人意的“强制阐释”。避开尴尬最为妥当的办法,是使阐释形式(观念)从本土材料(经验)中来,达到中国形式(观念)与中国材料(经验)的亲和。国家与群体的强大,首先是观念上的强大,因而国家与群体之间的较量与竞争,归根到底是观念的较量与竞争。我们最后应提炼出中国的阐释学观念。不过目前顺着“公共阐释”的理论言路来看,建构中国的阐释学理论,完全抛弃西方合理的阐释观念似是不妥。当前最要紧的任务是,以中国经验为轴心寻找“公共”阐释观念的中西“通约”区域。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其社会经历了充分的商业化,随之个体分化趋势也异常强劲。然而西方社会中的知识精英,从未忘记为消除个体分化而努力。阐释活动公共性格的找寻,只不过是他们付出如此努力的表征。原因是在他们眼中,阐释活动是信息的传递活动,而信息传递原先是神的职责;而现实中的阐释活动沐浴着神的光芒,信息传递工作也随之变得神圣而光荣。神的信息传递是现实的榜样,它有两种相同的路径。路径之一是神与神之间的信息传递,神与神之间的信使是赫尔墨斯(Hermes)。赫尔墨斯负责在众神之间传达宙斯信息,宙斯自不允许他将信息随意篡改,他也没有违背宙斯意愿,被公认是宙斯最忠诚的信使。伊索以“赫尔墨斯与樵夫”的寓言故事,向凡俗世界传颂他的忠诚。路径之二是神与俗之间的信息传输,神与俗之间的信使是麦库理(Mercury)。Mercury是Hermes的罗马名字。名字的变化意味着他的功能已发生变化。麦库理负责将“土地法传给造反的佃农们”[11]379,他信息传递工作的出色完成,靠的也还是忠诚,即他不违背土地法的原意。神的信息传达无论采用哪种路径,都不允许擅自更改信息本意。Hermes(Mercury)的行为,为阐释提供了绝佳典范,阐释者应以其为标杆进行阐释活动。西方阐释学英文Hermeneutics的词根刚好是Hermes(赫尔墨斯),该事实足以挑明阐释学创建的初衷,是不可将文本原意改动。

第二个方面则体现在话语上。信息的发出、传达与接收,具体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话语转换,阐释活动的顺利完成,因而还表现在话语之间的成功转换。与本雅明、阿多尔诺相比,哈贝马斯相对乐观。哈氏始终相信话语活动,能建立起一种公共性联系。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哈贝马斯忠诚于语言,无论语言怎样被歪曲和操纵,始终交感或理解它的内在宗旨。我们为了得到理解而说话,即使我们的发音是傲慢的或唐突的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讲话了。无论怎样贬低,每一种讲话行动都含蓄地提出并且相互认识某种合理的要求:要求真理、可理解性、真挚,以及功能性的挪用”;因此“每一种说话的行动或者对话,无论怎样令人难受或者枯燥无味,都不禁产生出一种与理性、真理和价值的不言而喻的契约,建立起相互关系,无论多么恶劣的不公正,在说话的行动中它对我们开放,使我们得以瞥见人类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以及选择性社会的朦胧轮廓。”[12]401-402阐释当然是一种话语活动,随此阐释活动使分化了的不同个体,容易建立起交互性关系,哪怕是“强制”话语,在最低限度上也无不如此。海德格尔也指出,人的“此在本质上共在”[13]171。人靠有限体验的话语,而发生密切联系。海德格尔因而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阐释在海德格尔那里,是种归家的活动。足见话语也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了信息的顺利传达。
话语与机能密切相连,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捍卫着阐释的通约性。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学”,可以吸收西方如此的公共性观念。我们在理论归纳中能动地融入西方观念,不算归属于“强制阐释”阵营。事实上,我们在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中,都能找到有关阐释的公共性言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在解经的过程中,已经涉及阐释活动公共性的反思。孔子本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表现得很是谦虚。孔子似还相信“论可以群”,因此他对《诗经》做出了“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阐释,公共性意图昭然若揭。宋明儒是对经典儒学的创发。陆九渊对解“六经”有深刻的体会,他说要么是“六经注我”,要么是“我注六经”。其中的“我注六经”,就要求做到客观公正。朱熹说我们读书,不要执着于私见,不是以我观书,而是以书观书,正如在审美欣赏上,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14]181。以我观书,容易曲解文本意义;以书观书,才能忠实于文本原意。王国维承上启下。他将“我”的显现称为“有我之境”,而将“我”的隐没称为“无我之境”,且后者价值高于前者[15]461。与此相应我们可以说,“有我之境”是“强制阐释”,“无我之境”则是“公共阐释”。当代学人中,王元化与余英时对阐释的公共性倡导较为自觉。王元化“以为训解前人著作,应依原本揭其底蕴,得其旨要,而不可强古人以从己意,用引申义来代替”,他平生治学服膺并自觉践行“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信条[16]109。余英时秉承朱子意绪,坦言只要“虚心”读书,便可求得“客观的了解”,进而劝告年轻人说:“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17]416-418。此外刘再复立足中西倡导的“中道智慧”[18]40-44,也有助于公共阐释信念的确立。中国大小文化传统,都可筑牢“公共阐释论”的理论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