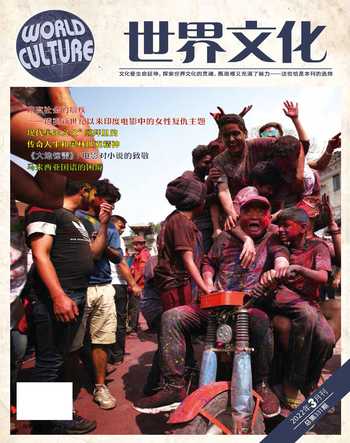“莎士比亚的我们”
2022-04-22冯梦珠
冯梦珠
歌德有言,“莎评无尽”,自莎剧诞生以来,对其评价研究从未间断,从早期对其褒贬不一,到如今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峰。莎剧艺术地位的确立不仅因为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也得益于绵绵无尽的莎评。伟大作品在于它拥有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的可能性,T·S. 艾略特谈到莎剧阐释说:“对于像莎土比亚这样伟大的人,很可能我们永远都不对;既然我们永远都不对,那么我们还是常常改变我们错误的方式为好。”犹太批评家菲德勒的莎评专著《莎士比亚笔下的陌生人》(以下简称《陌生人》)以神话原型批评对莎翁笔下陌生人做了详细阐述,菲德勒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洞见又新奇的观点,为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代评论家查尔斯·莫尔斯·沃思认为《陌生人》“可以被解读为作者最重要的批评声明,一本关于最大胆的艺术家的最大胆的书”。它是菲德勒批评工作的延伸和总结,对于菲德勒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将《陌生人》与菲德勒毕生的批评事业联系起来,探讨这本书对于菲德勒批评生涯的总结性作用,以期走近莎士比亚,走近20世纪的美国批评文化,也走近犹太批评家菲德勒。
纵观菲德勒的批评作品,离不开“种族与性别”的主题,菲德勒自称他是直面种族和性别神话的那些负面的、邪恶的东西:尤其是种族屠杀灭绝的噩梦以及深藏不露的厌女症。《莎士比亚笔下的陌生人》是他种族与性别主题的继续,作品分为四大部分,主要探讨了《亨利六世》中的女人,《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人,《奥赛罗》中的摩尔人,《暴风雨》中的卡利班。

第一部分论述女人作为陌生人,菲德勒分析了《亨利六世》《十四行诗》《辛白林》《麦克白》等莎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介绍之前菲德勒通过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总结了他的论点:“既然没有纯粹的男性原则,那么没有一个男性能够不受女性所代表的邪恶冲动的影响。”十四行诗叙述了“黑夫人”和青年男子的故事。菲德勒认为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神话是这些故事的原型,即女人具有邪恶本质,会给青年男子带来不幸甚至死亡。菲德勒指出在《亨利六世》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有三个女性角色:圣女贞德、奥弗涅伯爵夫人和玛格丽特,但她们从来没有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可以由一个演员扮演,换句话说,她们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她们善于说谎、挑拨离间,使正义的人蒙难甚至死亡,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就神话意义来说,琼就是玛格丽特就是伯爵夫人,他们都是被禁忌的女巫,这一神话不仅包括《亨利六世》中的女性也包括麦克白夫人,以及背叛父亲的鲍西亚和苔丝狄蒙娜。菲德勒认为由于莎翁隐秘的“厌女症”,使这些女性一般都拥有悲惨的结局。菲德勒指出在莎剧中“每一次婚姻都会让父亲哭泣,为那些眼泪付出的代价就是鲜血”。正因为这个原因《罗密欧与朱丽叶》结局是悲惨的,而背叛父亲嫁给摩尔人的苔丝狄蒙娜也悲惨地死去。当然,莎剧中也有一些女性拥有好的结局,菲德勒提出剧中女主人公要想得到好的结局总有一个变身男性的仪式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剧情中的女扮男装。
第二个陌生人形象是犹太人,菲德勒主要分析了《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形象,事实上,在菲德勒之前的莎評中有不少涉及夏洛克犹太身份的,而菲德勒作为犹太人敏锐地指出夏洛克的神话原型是《旧约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菲德勒认为亚伯拉罕拿刀杀子的形象一直困扰着欧洲人,使得亚伯拉罕在外邦人眼中成为邪恶父亲的原型,并在无数文学作品中不断复现,在菲德勒看来他们都是亚伯拉罕投下的阴影。菲德勒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他指出了夏洛克和他的女儿杰西卡的故事原型和其历史含义,菲德勒认为夏洛克和杰西卡符合食人魔故事类型,即:好女儿或被绑架的公主背叛抚养自己的恶魔或食人魔父亲,帮助王子杀死恶魔,并携带父亲的所有珍宝嫁给王子,简言之,就是善良女儿背叛邪恶父亲,这一故事模式在《李尔王》《奥赛罗》中也有出现。菲德勒指出,鲍西亚遵循父亲遗愿选匣结亲是这一神话的变体,三个匣子代表父亲的意愿,每个前来求亲者选匣失败的结果是终身不娶,表明这是父亲不想女儿被其他男人夺走而对青年男性施行的惩罚,而鲍西亚暗中帮助巴萨尼奥其实是在背叛父亲。而李尔王故事则是选匣故事的翻版,三个匣子不是外在的,而是实化在李尔王三个女儿身体中。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奥赛罗》中摩尔人如何被排斥为陌生人。菲德勒建议,从形式上来说,应该把《奥赛罗》看成两出戏——一出单幕喜剧,接着是一出四幕悲剧。喜剧的结尾是,年轻的新娘逃离了保护她的父亲,与她心爱的人私奔,与杰西卡的故事模式契合,后四幕则演绎了跨种族结合的悲剧,而且是一场近乎血腥的闹剧的悲剧。菲德勒认为在《奥赛罗》中黑人形象分裂为两个人,一个是摩尔人奥赛罗,他是外黑内白,另一个是伊阿古,他是外白内黑,菲德勒指出作为白人的伊阿古是作为黑人的奥赛罗的一部分,奥赛罗的嫉妒和暴躁易怒的性格成了邪恶敏感的伊阿古的帮凶,共同策划了这场悲剧。菲德勒指出黑人作为陌生人在人们心中一直都是邪恶野兽的化身,莎翁认同并迎合了这种想法,因此他认为《奥赛罗》的故事原型是美女与野兽,代表着人们普遍的对黑人强奸白人妇女的恐惧,白人男性将自己占有女性的欲望投射在黑人身上,又恐惧和排斥黑人。然而,菲德勒指出奥赛罗的黑人身份主要是象征性的,这并不是说他出身低贱,而是说他和他所爱的女孩儿以及爱他的人有着最大程度的文化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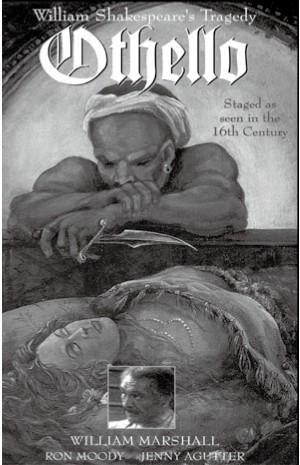
第四部分论述作为陌生人的新大陆的野蛮人,主要研究对象是《暴风雨》中的卡利班。早在18世纪,就有学者把《暴风雨》与美洲大陆联系起来,爱德蒙·马隆、西德尼·李,还有后来的李奥·马克思。莱斯利·菲尔德明确地认定卡利班是印第安人并指出《暴风雨》对美国历史的象征意义。菲德勒指出,人们倾向于认为在哥伦布发现西部之前,世界由三部分组成,而在那个世界西部边界之外的地区居住着威胁人类的非生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当第一批关于詹姆斯敦定居的报道到达英国时,莎士比亚写了他的“美国寓言”《暴风雨》。菲德勒认为,卡利班的形象代表了典型的欧洲人对所有美国人的看法。在他看来,在《暴风雨》中,卡利班只是莎士比亚对印第安人的噩梦般的想象——部分是摩尔人,部分是巴西—巴塔哥尼亚—百慕大印第安人,部分是鱼。他的名字是“食人者”的变形,而“食人者”来源于“加勒比人”,这是欧洲第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名字。此外,这种生物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吃人(非洲野人的行为),而是强奸欧洲白人妇女(如米兰达所代表)的欲望,卡利班代表着跨种族强奸的恐惧。
菲德勒对于莎剧中陌生人的研究,借用了很多以往莎评中新奇的观点,使这些观点得以传播,然而,正如马克·温切尔所说:“这本书告诉我们的菲德勒要比莎士比亚更多。”菲德勒的《陌生人》更多谈论的是他自己,是他“种族与性别”主题的延伸。陌生人和局外人一直是菲德勒关注的主题,正如他在1984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说的那样。“我先是写了局外人——黑人、印度人——然后写了被排斥的一代人和性别——青少年、女性——最后是生理异常的怪胎。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边缘定义什么是人类而不是通过核心定义。”他关注黑人、犹太人、野蛮人和女人这些陌生人在文学文化中的处境,这与他作为美国犹太人的身份敏感性与矛盾性分不开。菲德勒对于莎剧中陌生人的定义和解读,探索陌生人之所以成为陌生人的神话机制和社会心理,体现出他的犹太身份和他者意识,也是他进行身份探源的过程。
20世纪初“陌生人”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1908年,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西美尔(Georg Simmel)出版了《社会学》,其中专设“陌生人”一节。西美尔将“陌生人”理解为“外乡人”“异邦人”,他认为欧洲犹太人是陌生人的原型。因此,陌生人成为社会学概念之初主要指代犹太人,犹太知识分子大都认可这一概念并经常使用它指代犹太人。在菲德勒看来,陌生人是一个与我们非常相似的人,他们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但在其他重要的方面,他又显得与我们格格不入。菲德勒认为:“一个时代、一所学校、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在任何一部连续的作品的中心,总有一套关于人的本性的假设,尤其是关于人的限度的假设。……那个定义人类界限的边缘人物被称为‘影子’‘他者’‘异己’‘局外人’ ‘陌生人’。”在菲德勒看来,一个特定文化的人,每当他们在他们的世界的边界上遇到陌生人,也就是说,每当他们被迫面对那些在某些方面与自己相似得令人不安的生物时,这些生物却不完全符合(或者更糟,似乎已经拒绝了)他们对人类的定义时,似乎就不得不发明神话。这些生物被定义为超人或亚人类、神或恶魔,取决于定义群体是否征服或被他们征服。菲德勒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创造陌生人神话的过程是投射:投射到受人尊敬或鄙视的其他人身上。菲德勒认为人身上固有邪恶的一面,人们倾向于将这种邪恶的一面投射到他者身上。菲德勒指出:“邪恶的体现者夏洛克,他的贪婪、骄傲、对快乐的不信任,甚至毁坏他所讨厌的,某种程度上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心里——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或外邦人,而只是因为我们是人类。”他们邪恶不是因为他们有邪恶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是他者。
菲德勒对陌生人议题的讨论贯穿他整个学术批评生涯,他试图通过“他者”的眼睛看世界,菲德勒总是同情那些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的人。他同情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黑人——也同情美国以外的人包括巴勒斯坦人。他认同那些想要逃离种族、宗教和国家限制的文学人物。事实上,菲德勒对于陌生人的研究过程,也是他对犹太身份的认同过程。1975年,霍兰德的文章《统一性—身份认同—文本—自我》中提出“统一性之于文本”等于“身份之于自我”。他认为“解读是身份的一种功能”,阅读体验中“每个人都会找出与自己有关的特定主题。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方式使文本成为一种具有一致性和意义的体验……”每位读者都是根据自己的身份主题重新创作了这部作品,菲德勒是莎剧评论者,他的评论基于他作为阅读者对莎翁作品的阅读。菲德勒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写作,他曾说:“我发现不管我的新兴趣带我走了多远,不管愿意与否,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我还是继续作为一个犹太人写作。”菲德勒作为美国犹太人深切感受到基督教文化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和敌对。他敏锐地察觉到外邦人对于犹太人的敌视是存在于古老的文化基因中,存在于历代经典之中。菲德勒认为犹太人必须通过翻译和解释,将西方文学中通常归于犹太人的神话特质普遍化。犹太人可以是贪婪的,复仇心强的,可恨的,但并不比其他人多或少。他对陌生人的关注和解读,还原陌生人之所以成为陌生人的原因,旨在把犹太人形象或者与之相关的女人、黑人、印第安人,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者污名化或理想化的手中拯救出来,还原他们的真实面目,赋予他们作为正常人的权利,这个过程是解除附体的魑魅的过程,也是为他者正名的过程。
菲德勒无意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的封闭体系,而是把作品的文本看作是许许多多的“上下文”或“情境”的集合体,他认为,一部作品可以从各个角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和体裁学等角度去分析和评价,批评就是寻找作品与所有这些“上下文”之间的联系。菲德勒不把文本当作孤立现象,不仅将人物与人物、文本与文本连接起来,将文本与文化大背景连接,既关注自己民族,认同民族身份,为少数族裔立言,又不执着于种族主义,他的种族理想是连接孤独的个人,摆脱原子化世界,建立一个理想的整体的没有种族和他者的世界,体现出菲德勒文化拯救的终极希望。

菲德勒神话研究打通了所有作品,让不同剧作中的人物连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大的世界。他指出“所有真正的神话人物和事件都逃离了产生它们的作品并在公共领域生存。在那里,他们不属于任何人,只有彼此是同时代的”。因此,在他的莎评中人物与人物、文本与文本被神话原型串联起来。这些共同的神话和幻想,触及我们所有人,在那里,我们从未在精神上彼此分离。这些最深层的神话因素乃是人类自身欲望的历史积淀,因而能够引起普遍的久远的共鸣。首先,菲德勒将四类陌生人联系在一起,寻求他们的相似命运,菲德勒认为“被剥削的边缘人彼此之间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因此不仅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想象中,女人和犹太人都是一起堕落的”。他认为所有的女人“从神话的角度来说,她们是一体的,都是‘黑人’,都是法国人,都决心背叛英国的男性捍卫者”。菲德勒分析了莎剧中的陌生人,并指出在莎翁笔下女人=黑暗=犹太人=黑人。菲德勒在评论《奥赛罗》时暗示印第安人和犹太人在神话上是等同的,在对《暴风雨》的评述中甚至提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等同,菲德勒指出卡利班是个黑人,他的母亲来自“阿尔及尔”,“阿尔及尔是摩尔人世界的一部分,奥赛罗就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因此,从卡利班母亲的非洲根源来看待这一事实时,可以看出黑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神秘联系。其次,菲德勒将文本与历史联系起来,将文本神话与历史进行同构。在菲德勒看来,杰西卡和夏洛克分别代表犹太教和基督教,杰西卡“是圣母玛利亚的原型,通过完美的受孕和永远保持贞洁,她与犹太父权制没有任何联系,作为对天使报信的回应,她成为第一个基督徒”。菲德勒认为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徒对禁欲主义与违背人性的教条深恶痛绝,他们不敢否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而将这种憎恶感投射给这些教条的来源犹太教。在此,菲德勒将夏洛克与杰西卡的故事原型与犹太教和基督教进行类比,并试图给出外邦人反犹主义的原因。他将《暴风雨》论述为美国整个历史进程的寓言,一个关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叛乱的寓言,将欧洲、非洲和美国连接在罪恶和恐怖之中。菲德勒在《暴风雨》中看到了“殖民主义和种族的主题”,他不仅把卡列班视为美国印第安人,还认为他代表了非洲黑奴和中世纪欧洲野蛮人。在他看来,普洛斯佩罗对卡列班、斯丹法诺和特林坞罗密谋的镇压象征着“帝国主义美国的整个历史”。菲德勒认为《暴风雨》以预言的形式向我们预示了从最初通过战争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到建立印第安人保留地、从最初的黑奴制度到早期欧洲移民的整个历史。如果我们接受菲德勒的观点,即欧洲人本能地将美国视为卡利班文化,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普洛斯佩罗对卡列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个黑暗的东西我承认是我的。”它似乎“暂时完全把神秘的公爵和‘野蛮和畸形的奴隶’联系在一起,好像通过普洛斯佩罗,整个欧洲都在为当时被征服和奴役所造成的美国永远的邪恶承担责任”。菲德勒这段话是为了说明这些陌生人神话中所携带的普遍性,陌生人身上的“黑暗的东西”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正是通过陌生人神话,菲德勒试图将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人联系起来。

一个故事横向串联起所有类似的人物和故事,纵向串联起更早的神话来源或童话故事,或延伸到更广阔的现实历史文化。这个网由菲德勒推演而出,小到一枚戒指大到美洲新大陆都网罗其中,各个人物故事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推演,没有明确的逻辑因果关系,而是一个共时的整体。这与菲德勒学术理想和终极追求有关。布鲁克斯写道:“他们担心现代世界的解体,布什、菲德勒先生和许多其他学者和评论家都急于看到文学发挥作用来挽救这种局面。”布鲁克斯公开表示,菲德勒等学者的批评工作是在拯救我们支离破碎、脱离社会的文化。菲德勒的神话批评,以及他对陌生人形象背后机制的揭示,不是为了区分正常人和陌生人,显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不是仅仅为了批判这种歧视行为,从而为犹太人等陌生人正名,而是为了把人与人联系起来,他认为不管是白人、黑人、犹太人、女人、摩尔人、野蛮人,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之间,都没有本质的差别,有的只是神话上的差别,而他一生的文学批评都是致力于消除差别,建立联系。
现代美国学者马克指出:“由于莎士比亚是一个如此熟悉的人物,对他的戏剧和十四行诗的灵感误读往往比安全的和传统的分析更有启发性。”《陌生人》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启发性的书,菲德勒对莎剧的颠覆性解读,让读者耳目一新,他以独特的神话视角引起我们对莎剧中陌生人形象的深思。菲德勒说他讨论的不是“我们的莎士比亚”,而是“莎士比亚的我们”。他通过对莎士比亚的解读探索人性百态,也就是探索我们自己。他以“种族与性别”为枪矛,为少数人发声立言,试图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中异化疏离的个人之间搭建桥梁,建立联系。他进行了一场文学和神话的朝圣,为了在原子化的世界里,把日渐分离和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