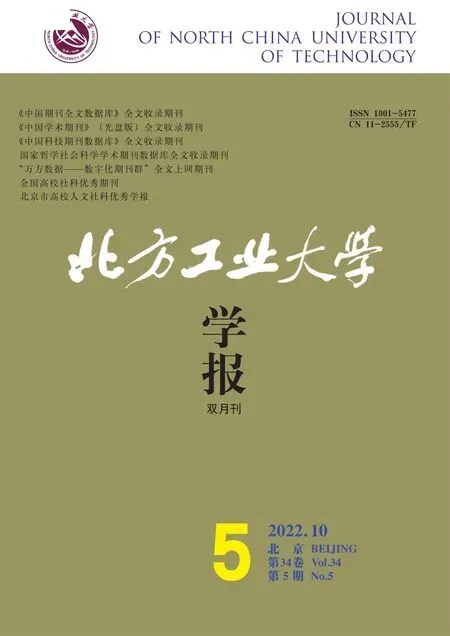印度现代印地语诗歌思潮的发展与流变*
2022-04-16王靖
王 靖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00871,北京)
现代印地语,即现代标准印地语(Modern Standard Hindi),是当今北印度文学文化、社会政经及人民生活等领域的通行语言,它的前身是印度克利方言(Khari Boli,一种北印度口语方言),是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的一种梵文化书写形式(Sanskritised form),自19 世纪发展至今。 印度独立后,现代印地语更是作为印度国语主导着整个北印度地区的文学语言。 它的形成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而印度现代印地语诗歌的出现则与印度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进程密切相关。 萌芽时期的现代印地语诗歌属于19 世纪印度启蒙运动和民族觉醒时期的产物,在诗歌语言和艺术创作手法上仍受17—18世纪印度旧体诗的影响。 进入20 世纪以后,现代印地语诗坛上相继涌现出了数股新浪潮,这些浪潮一方面主要受新时期活跃在印度社会上不同思想主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古老印度宗教哲学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焕发出的新的文化思潮的影响。 现代印地语诗歌在这种旧与新、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发展。 通过考察该发展进程,可以全面把握现代印地语诗歌思潮的流变过程,亦可对印度文学表现出的现代性转向和现代印地语诗歌的整体特征产生清晰的认识。
1 初期民族主义诗歌思潮的雏形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把19 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称为“帕勒登杜时期”,现代印地语诗歌由此开启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先河。 19 世纪下半叶,莫卧儿帝国灭亡,大英帝国建立统治。 自1857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失败后,英国殖民者进一步巩固了殖民统治的根基。 英语在印度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地位提升。 借助英语,印度知识分子精英接触到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价值。 19 世纪下半叶是革新的时代,旧的时代正走向终结,现代化时期渐渐开启。
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正是这一时期文学转折的代表。 在他的时代,作家们仍然效仿17—18 世纪印度法式时期(riti kal)的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用伯勒杰语(Brajbhasha)创作诗歌的作家自身不能完全脱离法式时期艳情诗歌的传统,帕勒登杜本人也创作这样的诗歌:
我若是笛多美妙,吸吮唇汁染他色。
他会把我持在手,或挂腰间贴唇边。
情郎林中吹竹笛,伯勒杰人身心迷。
向造物主求此郎,伯勒杰土幸运长。
赫利金德言,
莫亨情味盈入眼,永不分离意缱绻。[1]
在这首《女伴啊,为何我不是竹笛?》中,帕勒登杜使用北印度旧体诗的主流文学语言伯勒杰语,完全按照印度法式时期艳情诗歌的文学传统来创作唱诵大神黑天的诗歌。 诗歌继承了牧女与黑天艳情诗歌的叙事传统,使用“吸吮唇汁染他色”等诗句来表现牧女与黑天的艳情,同时,诗歌亦继承了15—16 世纪印度的虔诚文学传统,使用“情郎林中吹竹笛,伯勒杰人身心迷。 向造物主求此郎,伯勒杰土幸运长”表现出对大神黑天的赞颂和信爱。 此外在结构形式上,还使用“赫利金德言”这种印度旧体诗的印赞(chhap)形式。
虽然此时伯勒杰语仍然占据文学语言的主流,诗歌创作仍然延续旧体诗的文学传统,但作家们也开始寻求新的诗歌创作手法和新的语言形式,以广泛宣扬和增强印度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唤醒印度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 他们根据印度社会当时的形势,积极探索,将阐释民族主义和改造克利方言(创造现代印地语)视为国家发展进步的阶梯,致力于推广现代印地语成为国语。 他们希望通过对印度民族的塑造和描绘,燃起印度民族运动的星星之火。 我们可以从帕勒登杜的现代诗歌《英勇的印度》中窥知一二:
穿上战袍,披上铠甲,扎上番红花色的头巾,
束紧腰带,弯弓搭箭瞄准敌人。
为了民族长治久安,为了造福于民的理想,
印度不再恐惧。
你们从不让妻女失望,
从不背叛人民的信仰。
你们架桥修路,把天堑变通途,
为行路人传播幸福。
你们守护家乡,站岗放哨,
震慑了盗匪,让他们四散奔逃。
你们维护了家园、民族和国家的稳固,
你们视钱财和封地如同粪土。
你们依正法行事,保家卫国,
你们传授知识,无私奉献,修建了伟大的城埠。
你们因地制宜,从不顽固,
你们以无畏的肩膀庇护了人民所有的幸福。
你们保障了这个民族的繁荣和稳定,
你们在战场上谨遵誓言,尽忠职守。
敌人的铁蹄践踏我们的妻女,抢掠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安宁,
印度民族的英雄子孙为了尊严和荣誉不惜牺牲性命。
马纳·辛格与伯勒达波·辛格在孟加拉并肩奋战,
拉姆·辛格在阿萨姆大获全胜,热血沸腾。
恪守刹帝利武士之道的拉其普特王族子孙骁勇善战,
犹尤如婆罗多族神圣王者苏达萨的军队一样英勇。
为了印度民族,英雄们何不奋起,
手握宝剑冲向漫漫沙场,拼死战斗![2]
这首现代诗是帕勒登杜以印地语书写诗歌的早期尝试。 在语言上,他将日常口语克利方言的词汇引入诗中,代替旧体诗中所用的文学语言伯勒杰语,使得诗歌语言更加通俗易懂,更适合宣传推广,更符合平民大众的精神需求;在形式上,他摒弃了旧体诗中固有的格律、体式,开始了新诗律和自由体诗歌的大胆尝试;在内容上,他逐渐改变了旧体诗陈旧的艳情和信爱大神的题材,将民族觉醒、奋勇斗争的思想主题引入诗中。帕勒登杜对诗歌语言、形式和内容的改造使得北印度诗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这时期的诗歌并没有取得像散文、小说那样的革命性变化,传统的伯勒杰语诗仍在诗歌领域占据主流。 以帕勒登杜为代表的诗人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直接将克利方言口语词汇生搬硬套进诗歌之中,强行凑韵,诗歌语言的艺术性不够,此时的诗歌并非成熟的现代印地语诗歌创作。
尽管这一时期的现代印地语诗歌创作不够成熟,但却奠定了整个北印度文化民族主义的基调,即颇具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这点从《英勇的印度》中可以看到,诗人歌颂的是“扎着番红花色头巾”的印度教刹帝利武士,是对“婆罗多族王者苏达萨”一样英勇的印度教刹帝利王公的歌颂,这首诗出自帕勒登杜的戏剧《尼尔德维》,诗歌背景故事讲述的是印度教土邦领袖率领刹帝利武士英勇反抗异族穆斯林侵略者,整首诗歌充满了浓厚的印度教文化色彩。 以帕勒登杜为代表的作家们发起了文学和语言的创新,他们建立了宣传民族运动及爱国思想的主要阵地,塑造了北印度现代民族主义诗歌思潮的雏形。
2 初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潮
帕勒登杜之后,印地语文坛出现了另一位重要的领袖默哈维尔·伯勒萨德·德维威蒂。 他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农村,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推行印地语克利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对印度现代文学贡献巨大。 印地语文学界将20 世纪的前20年称为“德维威蒂时期”。 1903 年,德维威蒂成为印度著名文学杂志《文艺女神》(Saraswati)的主编,直到1920 年。 其间,他改变了印地语克利方言在文学语言中的模糊地位,修正了作为文学语言的印地语,成功地将其语言系统化、规范化,结束了文学语言使用中的混乱情况和无序状态。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文艺女神》这个文学阵地,培养和提携了整整一代印地语文学爱好者和著名作家。 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开始接受他制定的规范。 他确立了印地语作为现代印度文学语言的主导地位。
德维威蒂时期的诗歌思潮仍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主。 在甘地主义的影响下,超越了狭隘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以重塑国家、振兴民族为主,可以说该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对“帕勒登杜时期”民族主义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该时期的代表诗人有迈提里谢伦·古伯德,作为民族主义诗人,他主要受到甘地思想的影响,将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赋予诗歌创作。 他的诗歌多取材于印度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同时也描绘当时印度社会的种种惨状和现实,将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赋予了新的生命、使命和价值,以此来激励印度人民为建立共同的印度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
在古伯德的诗歌《印度之声》中,诗人描绘了印度社会的惨状:
犹如狂风吹散落叶飘零四方,
饥饿驱赶着千千万万的乞丐到处流浪,
烂布缠腰间,破碗举手上,
赤身裸体的幼儿哭哭啼啼跟在身旁。
树底是唯一可以栖身之所,
他们饱受折磨的身子瘦得不成人样,
寒来颤抖,热来发慌,
是谁让他们忍受这无尽的创伤。[3]
这首诗以叙事为主,注重表现当时印度社会的惨痛现实,以唤醒在苦难中“沉睡”的印度人民。 此时诗人已彻底摒弃了印度法式文学时期的骄奢与艳情的思想主题,受到民族觉醒思想的感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该时期诗人在诗歌取材上,以历史题材为主,依然运用传统梵语诗歌的格律进行创作,通过歌颂印度古老文明使印度国民产生自信心与自豪感,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勇担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的使命。 在古伯德的诗歌《耶输陀罗》中,诗人看似描绘的是佛陀释迦牟尼出家前的妻子耶输陀罗因被丈夫遗弃而内心充满痛苦和哀怨的故事,但实际上歌颂的是新时代女性义无反顾支持丈夫为国家建功立业的高尚品德:
女伴啊! 如果他离去时向我道声再见,
只是说声再见,难道我会把他阻拦?
他信任我,
却全然不知我的心念。
我一心追随,深悉他心中所愿。
女伴啊! 如果他离去时向我道声再见。
我会恪守刹帝利王后之道,
亲自为他收拾行囊,
将我这比生命更珍贵的爱人,送上前线。
女伴啊! 如果他离去时向我道声再见。
……
让他去吧,让他欢喜去把伟业建,
莫让我的忧伤使他徒生烦念。
我有何颜面衔恨抱怨? 这样的他才更让人眷恋!
女伴啊! 如果他离去时向我道声再见。[4]
在这首叙事诗中,诗人十分重视伦理道德,他着力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着重塑造那些为了国家的进步,为了推动社会改革和振兴民族文化而奋斗,能够体现民族大义和强烈责任感的新时代人物。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支持爱人远赴前线、去建功立业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耶输陀罗”。 在古伯德根据罗摩故事改编的“大诗”①《萨格德》中,诗人以特殊的视角刻意塑造了一个带有现代气息的独立女性形象——罗什曼那的妻子乌尔米拉,女主人公身上体现了甘地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宣扬甘地的坚持真理和非暴力的原则。
另一位民族主义诗人阿约特亚辛格·乌巴特亚耶·赫里奥特在取材“黑天离别罗陀”这一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大诗《情人远行》,诗人将罗陀塑造成理想的新时代典范:
这是我内心的渴求。
然而也存有另一个念头:
爱人啊,愿你为世界谋幸福,愿你长寿,
即使你一去不回头。[5]
该时期的民族主义诗人们受民族国家理想的影响,他们以诗歌文学为武器,投身于民族运动中,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现实,致力于树立道德理想典范,却忽略了文学丰富的情感性,因而该时期的诗歌缺乏对人类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和表达,同时也囿于旧有的传统诗歌创作手法,缺乏艺术创新和突破,他们没能超越印度复古主义的回声。 这一缺憾在其后的具有“印式浪漫”的阴影主义诗歌中得到了弥补。
3 具有“印式浪漫”的阴影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直贯穿于现代印地语诗歌的发展初期,在民族主义诗人的鼓舞下,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的爱国情绪不断发酵,然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无法摆脱英国殖民者的操纵和影响。 自19 世纪后半叶,英国殖民者就调整了其殖民政策,以资本输出和文化输出的新模式对印度进行压迫和剥削,这也在客观上对印度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对印度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启蒙以及对印度文学思潮的转向产生了促进和催化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国人的拖拽,印度深陷国际战争的泥潭,印度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痛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他们期盼的民族独立自主,仍然遭受着英殖民者的压迫和盘剥。 这种失望甚至绝望的痛苦情绪笼罩在文学界,弥漫进诗歌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20—1940 年前后,印地语诗歌思潮发生了转变,由之前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叙事转为内敛的人类自身苦闷情感的表达,由之前对西方理性和文学的推崇与模仿转为对印度传统文化意识的回归。 传入印度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文学在书写方式和艺术表达方面产生了影响,但印度诗人却从未忘记自身的民族传统和文学文化传统,正是在这样一种东西方文化意识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诞生了,这就是印度阴影主义(Chhayavaad)。
“阴影”(chhaya)一词借自孟加拉语,最初是反对者们对这类含蓄的和完全以个人幻想与感受为主的新诗的蔑称。 当时一些印地语文人反对这类诗歌,他们认为这类诗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逃跑主义,因为这些诗歌逃离现实世界的真实困苦,在幻境中自由驰骋,他们认为这类诗歌本质上来说是逃避现实主义的。 以德维威蒂为代表的一些文学评论家也反对阴影主义诗歌。 1928 年德维威蒂曾发文批判阴影主义:“我们已有像毗耶娑、迦梨陀娑、苏尔达斯、杜勒西达斯等伟大诗人创作的不朽诗篇,然而现在却有些诗人东施效颦,以‘诗人求名'‘杀死诗意'‘阴影主义少年'‘双生莲'‘莲花与大黑蜂'以及其他一些奇怪的笔名狗尾续貂,诗韵被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等标点符号破坏,有时一码长,有时两指宽,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没有停顿,缺少韵律,都是没有押韵的一行行黑色字体,虚无缥缈的诗歌令人费解,难以捉摸……”[6]德维威蒂的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那个时期评论家对阴影主义诗歌的偏见与谴责。 这些人认为这类诗歌的思想感情是模糊不清的,德维威蒂时代的读者熟悉以直义为主的诗体,新体诗以讽喻和隐喻为主及在幻想中表达个人感受的方式让他们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蔑称其为“阴影主义”。
阴影主义诗人苏米德拉南登·本德对这个名字并不满意,他认为“阴影主义”这一名称是德维威蒂时代的批评家对新体诗的嘲讽,因此他不赞成这种命名;但以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和默哈德维·沃尔马为代表的多数阴影主义诗人则乐于接受“阴影主义”这个称呼,他们认为用“阴影/影子”来称呼他们的新体诗恰如其分。 他们认为“阴影主义”的称呼契合了印度传统文化的表达,即“我”之中有“梵”的影子,如同黄昏时分的影子一样美丽朦胧却充满忧伤。 伯勒萨德曾说:“当诗歌开始在悲伤的基础上表达自我感受,而不是基于外部世界的描述时,这种印地语诗歌可被称为‘阴影主义'诗歌。 阴影在印度人看来更依赖个人感受的心理活动。 讽喻、隐喻、美好的象征以及曲折的情节再加上突出自我感受,这些便是阴影主义的特征。 从内心流出一股像珍珠般晶莹剔透的水流,这种激情澎湃的自我感受就是幻境美。”[7]之后“阴影主义”这个名字广为流传,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
阴影主义诗歌思潮是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具有一种新的文化意识。 这类诗歌以文学的形式开启了崭新的文化篇章,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它的精神灵感主要来自于仁爱与文明而非宗教,其出现与发展吻合了20 世纪科学和物质进步的历程。 古拉伯·拉易用更清晰的语言进行了阐释:“政府被卷入帝国主义的理论中,社会成为宗教教义的牺牲品,可怜的青年们对两方都感到绝望,他们只能栖身在美好的自然幻境和对广义至高存在的精神信仰之中,以对抗狭隘的教派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 由于受到政府和社会的谴责,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从阴影主义/神秘主义思想中诞生,独立意识觉醒,在激情澎湃的诗歌浪潮中遨游,将潜藏在外界冷酷生活中的美丽发掘出来,用生动、热情、甜蜜、优美的词语描绘出来,在这方面我们的青年诗人是先锋。”[8]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阴影主义包含了广泛的人道主义和宗教——世俗主义,或者说不带有印度传统教派主义的虔诚之情(虔爱)。②阴影主义诗歌中存在一种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之情,而所谓至高存在(the supreme being)也只是这种意识的一部分。 因此,阴影主义意识形态不包含任何狭隘的宗教理想,而是受到人道主义的影响,主要表达诗人个体的精神追求、诗人幻想中的自然风景、虔爱思想、道德观和社会观。 阴影主义诗歌或描写精神上的虔诚,或为个人的失败而落泪,或在饮酒中埋葬对生活的担忧,它引以为豪的人道主义是最响亮的声音,而这正是对旧体虔诚诗歌和法式艳情诗歌传统的真正意义上的打破与超越。 诗人们开始寻求人类自身的情感表达,诗歌内容从之前的旧体诗仿作和描述历史故事,塑造理想的道德人物,推进社会改革和努力创建新社会等宏大主题叙事转向了对个体情感的抒发和对自然及印度宗教、哲学的灵性回归。在一战阴影的笼罩之下,在英殖民主义的残酷压迫下,印度诗人除了从阴影主义的文化意识中寻求庇护之外别无他法。
文学批评家德沃拉吉认为阴影主义诗歌受到了孟加拉语和英语诗歌的影响,他写道:“阴影主义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受到罗宾德拉和英国诗人的诗歌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民主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快速成功地脱离德维威蒂时代的意识形态将印地语诗歌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新的审美观,新的爱情观和新的道德观。”[9]阴影主义开启了印地语诗歌的新篇章,该时期的艺术形式和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阴影主义诗人实现了幻境、理想和神秘的三位一体,将诗歌引向精神世界。 在精神领域进行艺术创作的方式是阴影主义诗人从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那里习得的。 泰戈尔的创作不仅受到了西方诗人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等的感染,而且还将印度觉醒作为自己诗歌的基调。 他探索吠陀知识,从深层次认识印度文明。 受到泰戈尔的影响,阴影主义诗人们坚守印度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质,并没有盲目照搬西方浪漫主义式的改良思想来书写人性解放。
印地语的阴影主义诗歌可以说是虚幻的,超现实的,但其中也包含了民族主义意识。 伯勒萨德的《我们美丽的红色王国》、尼拉腊的《为胜利而战吧,印度人》等作品中都含有具体的民族国家思想。 阴影主义诗人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来思考人类。 伯勒萨德在《迦马耶尼》中呈现了一个新的社会,这首长诗无疑是在构想一个新的国家面貌,它的独特之处一方面体现在从湿婆教派思想中找寻道路,另一方面体现在诗歌形式的创新上。 伯勒萨德的思想和情感是现代的,他的独白和诗歌中都体现了他的社会性,他心系整个国家。 对以伯勒萨德为代表的阴影主义诗人而言,殖民主义是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殖民者文明的挑战,他们致力于将民族文明以奇特唯美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此必须要说明的是,阴影主义同期还有其他诗歌倾向,有些与德维威蒂时期类似,有些将独立运动作为呐喊的口号。 事实上,民族主义思想存在于1947 年之前的所有诗歌主题中,因此不能将阴影主义诗歌与民族运动割裂开,它是在精神领域歌颂民族文明的诗歌。
阴影主义并不局限在神秘主义和民族主义范畴之内,“阴影主义”一词流传太广泛,以至于该时期其他形式的诗歌也被归为阴影主义流派。例如默哈德维·沃尔马的一些心灵诗和表达女性主义题材的诗歌也被归为阴影主义诗歌,还有伯金的类似“喝完就不渴了,/这样就会爱上酒”[10]的“饮酒”诗以及“不可接触者和婆罗门,/一同坐下举杯共饮。 /多少社会改革家们未竟的事业,/独独在酒馆中完成”[11]这类表达进步思想的“酒馆”系列诗歌也在阴影主义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说阴影主义是一个广泛的诗歌思潮。 该思潮孕育出了其后的多种文学思想流派,有些诗人将新的思想灌入带有浪漫色彩的民族和社会主题的阴影主义诗歌成分中,在摒弃个人幻想的情况下开始创作描述社会现实的进步性诗歌;而另外有些诗人开始在接受浪漫的个人幻想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精神层面的新诗创作实验和探索。
4 具有战斗性的进步主义思潮
尽管阴影主义诗歌之中不乏爱国和希冀民族独立、自治的思想,其对个人内心情感的抒写和艺术创作手法最为成熟,但这种“印式浪漫”并不适合当时寻求独立自主的印度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1930 年之后,除了阴影主义思潮之外,印度诗坛上同时出现了另外一种风格的诗歌,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下,出现的充满新的生气和战斗气息的“进步主义”(Paragativaad)诗歌。 1936 年印度进步作家协会的成立被认为是20 世纪现代印地语进步主义诗歌的发端,诗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进步主义主题。 这场会议由普列姆昌德领导,包括本德、耶谢巴尔、萨贾德在内的多位具有影响力的作家出席了本次会议。
早在1914 年苏联革命成功与共产主义成立之时,共产主义就开始对部分阴影主义诗人产生了影响。 这种平等主义的观点对于处在英殖民帝国的枷锁控制之下的印度人民而言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一些阴影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如本德和尼拉腊等人都受其影响,相继创作了一些进步主义诗歌。 他们追求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和特权,希冀结束印度的苦难,因此,为穷苦人民呼号和构建新社会的方案等进步主义思想也成为他们诗歌创作表达的主要内容。 早在1920 年代尼拉腊就曾创作了《芳香》(1923),《云咏》(1923)《乞讨》等具有进步主义思想的诗歌。 然而,进步主义能够在现代印地语诗坛上占据主流,形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思潮和规模,主要归因于印度进步作家协会成立的激发。 协会主席普列姆昌德本人支持共产主义,他通过《戈丹》指明了新的道路,他还在《觉醒》中写道:“谁反对让他人享受更多幸福的共产主义,就说明谁想奴役他人。”[12]
与描写自身情感和个体超验体验的阴影主义诗歌不同,进步主义诗歌描写的是印度社会的阶级情况。 诗人们意图以进步主义诗歌作为催发社会变革和实现独立自主的工具,他们意识到国大党仅仅是为了掌权而战斗,从现实层面看,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道路从社会底层根部进行变革,印度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和谋求幸福。 拉姆维拉斯·谢尔玛在讨论诗歌创作的目的时写道:“诗歌的目的是唤醒人民。 只愉悦小部分的人,这永远不可能是诗歌的目标。 诗歌能为在经济和政治状况中挣扎的人们提供帮助,并协助建立新的社会。”[13]
消除阶级压迫、剥削和破除旧宗教的桎梏是进步主义诗人的两大诉求,诗人盖达尔纳特·阿格尔瓦尔这样写道:“饥饿、干渴/虚弱、无力的大地将重现生机。 /时代的恒河/障碍将被消除/忠于一人的/用愉悦的心/去拥抱宇宙之海。”[14]德利罗金·夏斯德利这样攻击旧宗教:“在攻击,宗教的堡垒/我是诗人,新的人类或许会接受/他们的歌,歌唱自己的凯旋。”[15]在《形式之波》中,拉姆维拉斯·谢尔玛看到了没有剥削的社会到来的梦——“在曾经的封建文化的废墟上/将再次发出确信的声音/像恒河源源不断向前奔去/建设新时代的人民的脚步声不会中止。”[16]
印地语诗歌中像这样传达进步主义思想的声音迅速兴起,诗人们构想着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 进步主义诗歌从思想层面说是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艺术层面讲,则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进步主义诗歌与阴影主义诗歌同时存在于印地语诗坛,一些激进的进步主义诗人们反对阴影主义,认为阴影主义诗歌与社会利益相悖。 他们反对人道主义的、内省的、主观的、想象的、逃避主义的、消极的创作倾向,以帮助印度社会的底层人民和反对经济剥削为主要目标。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后,进步主义诗人们也通过诗歌宣传革命思想。 然而,无论是进步主义诗人还是阴影主义诗人,爱国思想和寻求民族的独立自主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1936—1942 年这一时期内,阴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诗歌潮流是并存的。 这一时期既是阴影主义诗歌的高峰时期,也是以纳迦尔琼、阿格尔瓦尔等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诗人积极创作、奋笔疾书、挥笔呼号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进步主义诗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奉行社会平等,主张要建立新兴和进步的社会。
在纳迦尔琼的这首诗《饥荒过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印度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不平等:
闹饥荒时,炉灶在哭泣,石磨也失落叹息
闹饥荒时,畸形丑陋的母狗蜷缩在角落昏睡
闹饥荒时,壁虎在墙上四处寻觅
闹饥荒时,老鼠也个个奄奄一息。[17]
广大劳动人民享受不到劳动的果实,而那些剥削者则在财富、生产和分配、社会经济结构中享有特权,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独立前的印度人民作为英殖民帝国的附庸,在忍受政治奴役的同时,也忍受着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剥削,进步主义的新视角为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之光。 进步主义诗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宣扬平等主义和社会公正,号召广大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特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进步主义诗人忽视了印度的古老传统文化,他们只做到了为劳动人民呐喊疾呼,却无法推动现实印度的社会改革运动。 进步主义思想无法被运用到现实社会改革中,而仅仅只成为一种文字表达,一种文学上构建的“主义”。 对于现实社会的变革来说,这种文字上的“主义”远未产生实际的推动效应,然而对于文学本身来说,进步主义诗歌开启了现代印地语诗歌文学的现实主义叙事,使得诗人们的视角不再囿于传统题材和浪漫的幻想,而是投射到印度社会和印度人民生活的本身。
5 多种思潮涌动缠绕的现代性新诗
印度独立前的印地语诗歌,无论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诗歌,还是具有印式浪漫的阴影主义和关注现实的激进的进步主义诗歌,都是在语言、韵律、内容、主题思想等层面对印度旧体诗的诗歌传统进行逐步解构和祛魅。 独立前的现代印地语诗人们都在努力尝试通过构建一种文学上的新主义来探索印地语诗歌文学的新路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诗人开启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表达,阴影主义诗人则凸显个人的感受,突出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而进步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得印地语诗歌开始注重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开始了对传统宗教的批判,理性主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盛在现代印地语诗歌中逐渐成为最强音。 在印度独立后,现代印地语诗歌中的这种现代性,表现为多元化的特征,诗人们开始涉及更为广泛的题材,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社会的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不公的社会现象、对小人物的书写、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感受和体验等主题都成为诗歌的表达。 独立后的印度社会多种文化思潮相继涌现,共生共融。诗人们或排斥或反对单一或特定的思想主义和诗歌思潮,而追求多元的文化思想和当时当下碎片化的创作方式。
印度独立后的印地语现代性新诗涵盖独立后印度所有诗歌形式的创新,它不仅指代狭义层面上由参与“新诗运动”(nayi kavita)的新诗派诗人创作的新诗,而且指代广义层面上从1940 年代开始出现的所有印度新时代的诗歌。 这些诗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和规则,虽然具备诗歌的基本要素,但却追求非同寻常、不拘一格的创作方式,追求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这些新诗契合印度社会的现代性转型,顺应了独立后印度社会、时代变迁及各阶层人民的不同需求。
印地语诗人深入探索多元化“现代性”诗歌创作的实验始于1940 年代。 1943 年,阿格叶耶主编的《七星》诗集出版,该诗集收录了七位创作风格迥异的诗人的诗作——阿格叶耶、内密金德尔·阇恩、穆克迪鲍德、吉尔伽库马尔·马图尔、拉姆维拉斯·谢尔玛、伯勒帕卡尔·马杰维和阿格尔瓦尔。 他们“以探索的视角面对诗歌”,用阿格叶耶的话来说,“他们(七星诗人)中没有统一的观点,所有人对于重要的主题都持有不同的论调。 关于人生、社会、宗教和政治,关于诗歌的对象、风格、格律与韵脚,关于诗人们书写的各个对象,他们都持有不同的观点”。[18]与之前的民族主义、阴影主义、进步主义不同,这种“实验主义”并非某种特定的思潮,而是指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受到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探索现代性新诗时所发起的不同实验性诗歌运动的总称。 它不是一种特定的诗歌流派,将七星诗人视作共同持有某一特定创作倾向的“实验主义”诗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实验”一词更多指称印地语诗人们对于多元化新诗的多路径探索,而非某种单一的“主义”或文学思想。
在探索新诗的实验运动中,阿格叶耶最为重要。 他赋予了诗歌许多艺术上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建立在诗歌技巧上的,其诗歌意象都变得“肮脏破败”,阴影主义时期诗歌中那种美妙的譬喻和美的意象消失了;第二个重要的创新在于引入了“不朽真理”的概念。 阿格叶耶认为:诗人应表达的是他灵魂的真理,这一真理不关乎个人的智慧,而是广袤无垠的存在。[19]他的诗歌包含了“对自我和人性的探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对人类和自然之美的热爱、对哲学思想的深刻体悟、对文艺创作的认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讽和对印度传统价值的珍视和忧虑等”。[20]他的代表作《疯狂的猎人》,通篇运用象征手法,使用大量的意象,展现了对自然、爱和自我的探索:
黎明时分疯狂的猎人
布下了万道光线织就的
洒满红色颗粒的罗网
当他收网之时
世间万物都被捆缚在那网中央:
宛如星群的小鸟
大大小小的鸽子
还有那体型巨大的飞机
展着硕大机翼
犹如展开一对翅膀
在空中翱翔
从那静谧神圣的寺庙高顶
到电报局那正在使用的
又粗又矮
圆滚滚又光秃秃的电线杆子
黄昏时分的吉祥的尘土
连同汽车排出的烟也一样被光网笼罩
公园道路两旁夹竹桃开满花朵
柔软的花瓣也镶上了金边,在尘世中熠熠闪亮
焚烧垃圾的烟囱
在远处骄傲地突兀而立
它喷吐着浓烟,仿佛凭此就可以把猎人打败!
疯狂的猎人啊
你毫不留情,要把一切事物一扫而光
请抹掉躲藏在我心深处的斑斑污迹
你不会不屑一顾吧?
来吧,我打开了所有的心门
请割破我这具残躯的所有血脉
用你那光束的利刃
把这座废墟全部捣毁
然后再建一个崭新的殿堂
请你擦净那所有失意日子留下的污点
请在我的眼圈上涂上油烟墨,让它发亮
这样我就能真切地看到你
请让我全身沐浴在你这金色的光亮——
看着你,感激之情在我内心充盈激荡
疯狂的猎人啊![21]
在他另一首代表诗作《与蛇说》中,蛇是堕落的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象征,阿格叶耶不无讽刺地写道:
蛇!
你蛮横无情,
就算居住在城市
你也是没教养的害人虫。
我问你——(你能回答吗?)
你怎么学会的噬咬——
又从哪里得来的毒药?[22]
在《我们的国家》一诗中,阿格叶耶亦是大力抨击了城市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对印度原有的和谐农业社会和乡村文明的破坏:
我们的国家
就建立在
这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
农村的茅屋、草房和竹棚之上
我们生活的情调
就流淌在
这充满锣鼓声、竹笛声的
喧嚣的湖沼当中
然而这种特质却被
隐藏在陌生城市中的
充满欲望和贪婪的毒蛇
一再噬咬
然而我们这些充满朝气的
质朴久远的文化却因贫困
而被现代文明的魔鬼
无情嘲笑。[23]
在1947 年印度独立之前,关于“独立”的诉求往往是“集体”的诉求,然而,在获得独立后,这种诉求演变成了“个人”的诉求。 独立后,印度人民的思想和心态发生了转变。 虽然印巴分治令人沮丧,但英国人从印度撤出后,他们获得的独立自主的幸福感也是真切的,他们期待能在这个国家构建美好的未来,能够在自由中分享未来。出于这一心态,印度诗歌的视角发生了变化,新诗运动应运而生。
关于印地语新诗,阿格叶耶写道:“新诗最初是一种新的心境的映射,与一种新的情绪、新的时代息息相关。”[24]穆克迪鲍德也将独立后的诗歌创作趋势称作新诗,“新诗中包含了许多潮流,而非仅仅一种。 在其中的某种潮流中甚至能找到进步主义的元素”;[25]同时他承认“新诗赋予了诗歌新的主题、新的喻体、新的标志和新的情绪表达的路径”,[26]他认为新诗是“现代情感的表达”。 这个“现代情感的表达”与阿格叶耶的“情感表达”有所不同,它不止包含了“小人物”的情感表达。 这就是阿格叶耶与穆克迪鲍德在新诗视角上存在的观点差异。 由此可见,关于新诗的界定和讨论充满了分歧,其创作视角也是丰富而多元的。 由新诗运动催生的诗歌流派难以计数,诗坛相继出现了“新诗派”“非诗”“破除迷惑”“新进步主义”等诗歌派别。 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思潮涌入印度,与此同时,古代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依然绵延不息,这些思想和思潮不断交融,并被印度知识分子接纳、吸收。 诗人们希望通过文学的书写来展现和满足不同人民群体的社会生活诉求,探索和表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 总的来说,从创作标识来看,独立后印度新诗属于现代主义与所谓后现代主义杂糅而成的综合性范畴。
6 结语
印度印地语现代诗歌思潮的流变轨迹是相对清晰的,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到阴影主义、进步主义再到独立后多元主义的实验性新诗,这是一个对传统旧体诗中宗教、艳情等主题逐步解构、祛魅和重构的过程,亦代表了印度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这其中体现了印度社会文化现代性的三个转向:一是从对神人世界(艳情、解脱)的关注到对现实世界和世俗社会的关注转向;二是从国家的宏大叙事到对人类个体叙事的转向;三是从对人类个体内在情感(意识)的关注到对日常生活、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社会顽疾以及人文关怀和文化交流的关注转向。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现代印地语诗歌不是直线、单向的发展,而是多线程、网状的移动。 新的诗歌潮流盛行时,旧有的诗歌和文学文化传统也并未消失,而是新继承旧,旧亦吸纳新,在融合中各自发展、并存。 整整一个世纪的不同诗歌思潮构成了现代印地语诗歌的多元主义灵魂,这些诗歌具有自身独特的形式和色彩,从各自特殊的视角传达自身的价值。
注释:
①“大诗”:印度文学传统术语,指结构复杂、情节曲折的长篇叙事诗。
②虔诚之情,即“虔爱,信爱”,原文为bhakti,在印度宗教中指对至高存在的纯粹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