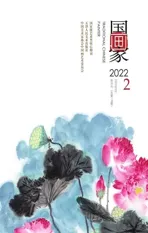映照、依存、对抗:江南美学
2022-04-13徐鑫桦
徐鑫桦

一、映照:地域与环境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典故人们耳熟能详。那么环境决定论是否适用解释艺术的产生?丹纳(H.A.Taine)特别强调环境因素对于艺术的影响,尤其是地理因素。他在《艺术哲学》中指出:河流、山地、气候等不同因素对于艺术作品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其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之“环境”是否可以转换理解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艺术?参展的三位艺术家井士剑、刘正、方利民,他们的作品可以权作驱赶丹纳意义上的环境说的迷思。
在“存在先于本质”的观念被普遍接受的时代背景下,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丹纳学说”已在艺术界式微。环境与人之间,并非是环境支配人的单向关系,人的生发也在塑造环境。参展艺术家井士剑深知这一点,他来自中国北端辽宁省黑山。国内艺评家夏可君谈到井士剑的画作时指出:一个北方艺术家在南方生活几十年后所体验到的一种差异,面对充满了文化象征的西湖,如何使之重新在绘画上醒来?既要复活明代末年的残梦,又要有着当下生命的反省与批判,面对时代的无根,个体生命的沉沦与无助,一个个飘浮着的生命如何进入那个古典的残梦时,还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想象?他的绘画充满视觉隐喻与符号密码,其绘画是画界少有能够指引现代性启蒙的通道。一般来讲,我并不喜欢艺术家使用《无题》作为其作品名,恰恰井士剑的参展作品就使用“无题”二字。也许他通过作品想说的是:理解的通道就是作品本身,而不在于题目的指引;或者,他通过画作的启蒙,是具有门槛的,只对具有灵性者开放。

丘挺 雪霁图 34cm×136cm 纸本水墨
《惊蛰》系列是艺术家刘正创作了二十余年的母题。其系列在媒材上跨越了水彩、彩墨、陶瓷雕塑、瓷上绘画、纸本线描。就其题目(“惊蛰”)的“所指”而言,唐人刘长卿的诗句已经道出:“忽闻天公霹雳声,禽兽虫豸倒乾坤。”其寓意为严冬过去,温度回升,冬季藏入土中冬眠的动物、虫子,开始慢慢复苏。就其题目“能指”而言,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是刘正对自身艺术前瞻性的自信,其二:作为美术学院陶瓷艺术学科带头人的他,是对“当代陶艺”即将在当代艺术生态中登场的预言。有必要指出,自1998年起,刘正与周武等人策划的“中国当代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已经成为业界的品牌展,对中国当代陶艺的推动意义非凡。回到环境这一话题,在同一个时代,每个人具有自身的小环境。艺术家刘正分身处理不同的公务之后,潜回画室,进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不停歇地创作。多年之后,他构建出了一种具有高度识别性的视觉语言、图式体系与观物逻辑。《惊蛰》的用笔与构成在自由与戒律的两极之间不断地拉扯。这种拉扯的张力不单使艺术家在多种媒材之间游刃有余地跳跃,更统摄出一种同一的艺术样貌。
疫情并未远去是我们当下的共同环境,艺术家方利民在表述传统饾版水印木刻时认为:“写不出,说不清的思绪,在版上刷上颜色,拉过宣纸,用马莲印一下,看着纸上的痕迹觉得有那么点意思。再刷、再印,再刷、再印……意识像雾中的小船,印痕是缆绳,我拽住了船缆,渐渐把船拉近,船的形状慢慢清晰起来。”他的作品《假日——湖山之四》创作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外界是不安与恐慌,而工作室中是水墨、印版、色彩、宣纸,素雅而平静。
二、依存:历史与记忆
在知识就是权力/力量(power)的共识下,我们对自然存有一种宰制的态度。科学技术使得我们从自然状态中抽离。当代人更加追随、崇拜数理逻辑,致使我们不再归属自然,也无法直接观照自然。我们知道,古人通过绘画来理解自然。而在今天,我们需要反观古人的笔墨重新认识自然。明末清初的画僧石涛一生历尽坎坷,在无限的矛盾和痛苦中,饱览名山大川,画出自己心中的世界,他笔下山川的氤氲气象,意境的苍莽新奇,为中国画的发展开创了一派新的意境,也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回到自然而然状态的路径:处理天、地、人的三重关系。端详本次展览的作品,我以为林海钟与丘挺偏向“人”,严善錞偏向“天”,刘文洁偏向“我”。
师古人成了学习传统山水画遵循的金玉良言。丘挺与林海钟是好友,也都是“师古人”的高手。通过《雪霁图》《春雨润万物》等作品,通过与古人的笔墨毫厘之间的交锋,使我们有了重新看到自然的可能。如将唐代画家张璪所提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换成哲学语言就是主体与客体、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林海钟是坚定的一元论者,在他看起来,外师造化与中得心源绝非单向的过程。既从内心感受出发,也能还原到外界的自然。林海钟私下闲聊时曾说,某年受他人之邀,创作有关太湖的画作。他并没有像一般艺术家那样,考察、拍摄、写生。而是在工作室借用笔墨“推衍”:水波、窟窿石、林荫、半岛,再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不断地推衍中,一张太湖画作即已完成。当他得到机会,亲身来到太湖边时,愕然地发现,真实的太湖与其在工作室中推衍的结果高度一致。
西湖作为客观存在。石涛曾经漫游浙江。顺治十四年(1657)春,石涛在西湖泠泉画有山水册,这也是他传世最早的画作。西湖也一直是严善錞创作的主题。当严善錞与石涛跨越时空,面对同一个西湖时,一种奇妙的联系就产生了。真正的“西湖”在哪里?“西湖”对于当下意味着什么?近十年来,严善錞创作了大量十分重要的铜版画。他通过拟李嵩、拟董源、拟董其昌、拟渐江、拟李唐、拟倪云林等古代文人,同时又结合西方艺术的严格造型,将中西绘画的高妙之处在其西湖主题的铜版画中融通,真切地表现了“历史西湖”的气质:清峻、遥深、温润、古雅。

林海钟 抱朴道院 70.5cm×34.2cm 纸本水墨

林海钟 春雨润万物 63.5cm×36cm 纸本水墨
刘文洁是当代中国学院山水画坛的异类。就像塞尚一生都在上唯理论(以普桑为代表的法国古典艺术)与经验论(追求视觉光影的印象派绘画)之间疑惑一样,艺术家刘文洁在以传统笔墨为基底构建的古典精神世界与眼之所见、身之所感的当代生活环境之间存在彷徨与焦虑。刘文洁的绘画创作不单单为了传达传统符号的“中国画”,也不为了彰显东方美学的为“中国”而画。刘文洁的绘画是通过艺术家个体的感知,折射了人类集体共有的情感。为此,刘文洁必须在传统笔墨与当代感知的双重夹击下,开创出山水绘画的第三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尽管回望是忐忑与不安,前路又充满荆棘,但刘文洁的每一个坚定的步伐都充满魅力。
三、对抗:当代与断裂
当代即为“同时代”。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指出:“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可见,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在我看起来,那些直面“当代”的艺术家,更为关注“个人”与“时代”的断裂关系,勇于不断地与其对抗。
在大众的心目中,陶瓷是用作把玩的工艺材料,而非如同油彩、水墨一般是纯艺术表达媒介。在二战前后,欧、美、日都刮起了现代(当代)陶艺的“泥土革命”。中国的当代陶艺起步较晚,究其原因,处理陶瓷艺术就是在转化传统艺术养分、调和中西艺术差异、综合材料属性与艺术家情感等多重的关系。敢于实践这些看似二律背反的问题,要么背上“胡闹”的骂名,要么开宗立派。艺术家陈淞贤是国内最早在陶艺中加入“当代”概念的人。早在1989年的《陶艺的当代风格》一文中,陈淞贤已经开始探寻与推广陶艺的当代表现形式。陈淞贤指出:“在陶艺创作中,材料个性的充分发挥,作者情感的真切注入,这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陈淞贤在提出现代陶艺概念之后,为了保持陶艺本体语言的纯粹性,他又发出了陶艺应该姓“陶”还是姓“雕”的追问。在展厅中,面对自己创作于数十年前的《柱》《碟》等作品,陈淞贤打趣道:“现在这些作品都没什么啦,都落伍啦,在当时还是有些争议的。”“中国现代陶艺之父”的尊位是空缺的。在我看起来,就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史意义而言,陈淞贤的贡献无疑配得上“中国现代陶艺之父”这一殊荣。

刘文洁 手稿 60cm×42cm 纸本水墨

刘文洁 易稿(之一)26cm×20cm 纸本水墨
花俊以特有的香灰书法(《灰书题壁》)曾在艺术界轰动一时。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致力于当代艺术的创作,就要跟当代人的生存处境、我们身边出现的问题以及社会现状发生直接关联,要把矛盾揭示出来,作品要反映对社会的深度认识。范迪安曾经如此评价花俊的作品:首先营造了丰富的视觉图景,这种感受来自当代都市生活,也表现出将人物画与山水意象相叠合的形式探索。他画中的芸芸众生通常消融在混沌的空间世界之中,突显了对当下社会生活节奏与韵律的整体感受。在笔墨语言上,他更是调动了既属于水墨领域又突破水墨界限的多种方式,从而在一种综合的笔墨形式中表现出精神的超越,推进了水墨艺术的开拓。
作品《对话》是梁绍基与梁铨跨越时空、跨越材质的艺术对话。两位艺术家在不同的媒介与风格中惺惺相惜、遥相呼应,以超越形式与观念的作品实现了生命与精神层面的碰撞。梁铨旅居美国之时,极简艺术、抽象表现主义依然大行其道。但他敏觉那种追求秩序的方格子、竖条纹跟他内心的感受和自身的文化领悟存在断裂。梁铨在新千年之后,发展出以直线和渍痕为特征的作品。他发现一张纸裁下来,上面的纹理和边缘,有天然的东西,又有秩序。正如他本人所言:“中国文人画讲究天趣;天趣和秩序都很重要。”在艺术创作的底层逻辑上而言,梁绍基掌握一种独家材料,这种材料不但代表他个人,还暗示了一个世界,甚至指代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文明——丝。梁绍基以三十年的光阴赢得了蚕丝对他的眷顾。精微的蚕丝是一种精神的物质化呈现,也是蚕的生命张力的显现、运动的轨迹、存在的证据、生命的余晖。更进一步,梁绍基的艺术并非其救赎式的造型,也非蚕丝的余晖,而是回归到蚕个体的生命。蚕的生、死、繁衍之“三合”。梁绍基正是通过一只小虫子,追问存在,体悟生命,妙悟宇宙的奥义。
四、结语
梁绍基喜欢在艺术札记中动用“此在”(Da-sein)这个哲学概念。“此在”语出海德格尔的巨著《存在与时间》,其同时具有“此时此地”(da)和“存有”(sein)的两重意涵。在当下,疫情削减了人们出行的空间,全球GDP的动线限制了对未来的非分之想。用“自然之形”与“艺术家意识”的相互映照、相互依存、相互对抗的关系所指引的“江南美学”,不但暗合“此在”,也可以成为超越历史、跨越地域,转为一种观照自然的方式,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