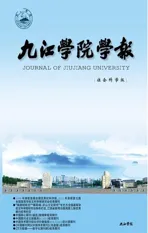世说人物形象在唐诗中的接受与重构
2022-04-07哈雪英
哈雪英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世说新语》分专题记叙品评了活跃在东汉末年到刘宋时期的人物,时至东晋,多有疏离政治、渐入玄远的人物涌现。笔者既欲讨论《世说新语》人物形象在唐代诗歌中的接受情况,则需要说明:唐人所接受与能重构的内容,既包含刘义庆描述的人物事迹,也涉及刘孝标注释中展现的人物风貌。因此,本文以《世说新语》中的阮籍和谢安为关照对象,选取“途穷恸哭”与“东山再起”两个故事典实,将其置于唐代不同时期的诗歌书写中,探究唐人如何将世说人物形象引入新的现实情境并进行重构。
一、泣于穷途:行路之难与宦游之思
“途穷恸哭”典出《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八》“阮步兵啸”条,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1]阮籍时常独自驾车外出,率意而行,无路可走时便会恸哭返回,这是一种困顿之中的焦虑甚至绝望。骆玉明评价“穷途恸哭”是“用一种固执的态度看待人和世界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感受到生命遭受外力压迫的紧张”[2],而这种紧张焦虑正与唐人漫游的生活经历相契,与唐人贬谪的仕途经验相合,由是,当唐代诗人生发四顾茫然的宦游体验之时,往往联想到泣于穷途的阮籍。
咸亨元年(670),王勃有诗《重别薛华》:
明月沉珠浦,秋风濯锦川。楼台临绝岸,洲渚亘长天。旅泊成千里,栖遑共百年。穷途唯有泪,还望独潸然。[3]
此时诗人因作《檄英王鸡文》得罪高宗、被迫离开沛王府客居蜀中,突遭政治打击,他与《世说新语》中“穷途恸哭”的阮籍产生了命运联结与情感共鸣。诗歌描绘了秀整泓净、浩荡开阔的剑南秋景。面对穷途逝川,诗人迎风洒泪,直抒“明月暗沉”的愤懑与凄苦。《唐诗分类绳尺》言其“平易实语,不须造作而露丰姿”[4]。作于此前的《别薛华》亦有句“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表达旅泊千里、栖遑百年之郁。然而,在接受《世说新语》中阮籍形象的同时,王勃亦为之增添大唐气象,其《送卢主簿》诗云:
穷途非所恨,虚室自相依。城阙居年满,琴尊俗事稀。开襟方未已,分袂忽多违。东岩富松竹,岁暮幸同归。[5]
诗虽以相送为题,但并未囿于离别之情,而是在歧路沾巾之外饱含穷且益坚的期待。诗人借“松竹”自况,希望能与卢主簿并肩前进,希冀着“岁暮幸同归”时刻的到来,为“穷途”注入昂扬奋发的感情,因为初唐时期,时代赋予文人的信心是“穷途之泣”的流淌出口。
至于中唐,刘禹锡有诗《赠眼医婆罗门僧》用“途穷恸哭”典故:
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6]
这首诗具体写于何时已岁月无可考,依颔联“中年似老翁”蠡测,作诗时刘禹锡应该已经经历了永贞革新的失败,被贬郎州,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中也有“据此诗之意,禹锡患眼在中年,当是在郎州时,后此未闻复有眼疾,盖得此医而竟愈矣”[7]的推论。我国东汉以后,称古印度为婆罗门,婆罗门僧的金篦之术医好了诗人的眼疾,使其不再怕风羞日、看朱成碧,故赠诗以表谢意。而联系大致写作时间,磋磨诗人、令之发出“三秋伤望远,终日泣途穷”悲慨的,不止是身体的痛苦,还有政治的失意,但是似乎眼疾的好转暂缓了穷途之感。究“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深意,还有亲近佛家以消磨世间无定忧喜的愿望,因为此时的唐王朝已渐式微,兼具朝官理智与诗人敏感的刘禹锡无法再发出王勃那样青春的呐喊,这也是唐人“穷途之泣”的另一个出口。
此外,唐代不同时期的文人亦多有诗作援引“穷途恸哭”之典。与王勃同时且政治命运相似的骆宾王《早发诸暨》有句“橘性行应化,蓬心去不安。独掩穷途泪,长歌行路难”[8],按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诸暨在县治南,即浦阳江,今吾邑人多由此行舟。”[9]诗歌写了早晨行舟诸暨的见闻,并将此行比作穷途,其《秋日送尹大赴京并序》有句“既切送归之情,弥轸穷途之感”[10]同作此喻,感叹行路之难。杜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中“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11]、《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中“衰颜偶一破,胜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12]、《敬赠郑谏议十韵》中“将期一诺重,欻使寸心倾。君见途穷哭,宜忧阮步兵”[13]等句皆以“穷途恸哭”自况羁旅困顿与人生艰难。中唐诗人元稹《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中“酩酊焉知极,羁离忽暂宁。鸡声催欲曙,蟾影照初醒。咽绝鹃啼竹,萧撩雁去汀。遥城传漏箭,乡寺响风铃。楚泽一为梗,尧阶屡变蓂。醉荒非独此,愁梦几曾经?每耻穷途哭,今那客泪零?感君澄醴酒,不遣渭和泾”[14],诗人醉酒之后长篇大论,吐露了羁旅离愁,虽言“每耻穷途哭”,却忍不住像阮籍一样恸哭。唐末诗人韦庄的七言排律《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郞中二十韵》有句“帝里无成久滞淹,别家三度见新蟾。郄诜丹桂无人指,阮籍青襟有泪沾”[15],按夏承焘《韦端己年谱》,此诗作于乾符六年(879)[16],此时韦庄四十四岁,落第后居长安,诗歌抒发了失志的苦闷。“帝里”即长安,“无成”即科场失意,“新蟾”代指月亮,“三度见新蟾”可知诗人离别家乡,滞留长安已过三载。古代常以“蟾宫折桂”喻科举得意,在此诗人自比郄诜、阮籍,因丹桂难摘而泪湿青衫。诗末言“如今正困风波力,更向人中问宋纤”,宋纤是东晋高士,隐居甘肃酒泉南山,诗人似有归隐意向。
在唐代诗歌创作的现实情境中,虽然出现多例使用“穷途恸哭”典故的作品,但整体上相较阮籍途穷的压迫感,唐人之途穷内涵的沉重性明显下降。《世说新语》言阮籍“常率意独驾”,一个“常”字、一个“独”字将读者带入绝望的漩涡,我们难以想象阮籍多少次率意而起却恸哭而返,并未实现逍遥与适意。这一典故所展现的不是魏晋名士的风流无羁,更多的是无可挽救的人生抱负。阮籍之途是无目的的,更像是一种抽象化的路,由于其表达范围更广,关照着每个读者的“行路难”,也引发了唐代文人的经验与情感共鸣。而与之不同的是,唐人之途是具象化的,诗歌中最常见的有旅途、别途、仕途。同时,阮籍的穷途之哭是绝望的、不得调和的,唐人的穷途之哭在抒发离别之感与行路之难之外,表现出了独特的困境心态,或因时代朝气驱散穷途风霜,或借佛家精神消解行路艰难。总之,唐代诗歌对《世说新语》阮籍形象的重构之处在于:阮籍在仕隐之间走向隐,唐人在仕隐之间偏重仕。
二、起于东山:栖心之所与托喻之辞
“东山再起”典出《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17]魏晋名士谢安隐逸之后再度出山,后世常用“东山再起”赞誉他为苍生而出的高情大义。明代李贽语评“高崧自谓极得意语,孰知只赢得谢公一笑”[18],后世文人羡慕谢安清醒、自如于仕隐之间,并将其当做从政典范。
盛唐诗人李白多次征引“东山再起”的典故,其《梁园吟》云:
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19]
安旗认为这首诗作于开元十九年(731)[20],按吕华明等《李太白年谱补正》,此诗当是开元二十一年(733)诗人离开长安,舟行抵达梁园时作[21],应为李白游历至梁宋之地所作。诗写当时的舞影歌声、豪奢的梁园宫阙、风流倜傥的枚乘与司马相如早已不复存在,空余汴水日夜东流到海不复回。吟到这里,诗人不由得泪洒衣襟,因为自己未能归得长安,只好以黄金买醉。呼白喊黑,一掷千金;分曹赌酒,以遣时日。诗人且歌且谣,暂以为隐士,但仍寄希望于将来。就像当年谢安东山高卧一样,一旦时机到来,再起来大济苍生,时犹未晚。
至德元年(756)十二月,李白隐居庐山屏风叠,作《赠韦秘书子春》:
谷口郑子真,躬耕在岩石。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斯人竟不起,云卧从所适。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惟君家世者,偃息逢休明。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秘书何寂寂,无乃羁豪英?且复归碧山,安能恋金阙?旧宅樵渔地,蓬蒿已应没。却顾女几峰,胡颜见云月?徒为风尘苦,一官已白发。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扪虱话良图。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22]
韦子春,曾官秘书省着作郎,韦为永王璘谋主之一。永王领四道节度使出镇江陵后,韦奉命来庐山说李白入幕。此诗当是李白应聘后赠韦之作[23]。诗以汉朝隐士郑子真起笔,写其隐居在谷口,耕读鱼樵于山涧,清高之风天下皆知。他坐卧松云,坚决不当官,过着悠闲自若的山中岁月。继而笔锋一转,反问若都像他一样独善其身,谁来救济世难呢?然后回到诗歌寄赠对象韦子春:曾经委身国子监秘书之职,后因官僚生活虚度生涯隐居故乡,现逢遇明主、滔滔谈论政治霸略,正如谢公在国有危难时毅然出山,拯救天下苍生。最后记叙与韦子春相会,安定天下的志气与“为君谈笑净胡沙”的豪情跃然纸上。但是之后永王兵败,李白的政治梦也成水月镜花。
李白《书情赠蔡舍人雄》写于天宝十二载,诗人被逐出长安后漫游大江南北,“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24]他为自己的遭谗被逐而愤懑,蔑视、鄙夷统治者的腐朽却又想做谢安那样的人,期望着再被任用,而这期望终将落空,不得不选择纵棹五湖闲居田亩的归隐之途。李白无疑仰慕接受了《世说新语》中的谢安形象,而其诗歌对这一形象的重构在于打破了“东山再起”的仕隐平衡,虽然以“起”为名,但是在这一故事中,是先藏后出、仕隐兼修的,事实上,写作这些诗歌时的李白处于浪游状态,并未隐过,甚至不曾做出归隐的模样,只是将自己建功立业的心灵栖息于“东山再起”之典,单方面凝视着“再起”,渴望着入仕。
孟浩然五言排律《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中“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25],借“东山再起”典故赞扬张九龄的仕途功业,以苍生之需劝慰丞相张九龄不要有退隐之意,并以此表明自己效仿谢安归隐,意欲为苍生而仕的渴望。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中“无数将军西第成,早作丞相东山起”[26],亦用谢安事抒发他对苏涣所寄予的厚望。刘禹锡多与曾入朝为相,政绩卓越的裴度、李德裕、令狐楚等人唱和往来,他也通过赞美谢安东山再起的担当,寄托对唱和对象的热切期望。其《奉和裴令公夜宴》云:
天下苍生望不休,东山虽有但时游。从来海上仙桃树,肯逐人间风露秋?[27]
这首诗作于开成元年秋至二年五月间,诗人时在洛阳。裴令公即宰相裴度,诗言天下苍生盼望着裴度隐居只不过是适时的游宴,因为他术来是海上的仙桃树,怎么肯随着人间的风露而调谢呢?用“东山再起”的典故希望裴度不要隐居。温庭筠《题裴晋公林亭》
谢傅林亭暑气微,山丘零落閟音徽。东山终为苍生起,南浦虚言白首归。池凤已传春水浴,渚禽犹带夕阳飞。悠然到此忘情处,一日何妨有万几?[28]
林亭即午桥别墅,是裴度晚年居所。诗人游历至此、有感而题。斯人已逝空留胜景,作者赞赏裴度深系苍生之望的不世功业,不离“东山终为苍生起”之主意。此外,刘禹锡《庙庭偃松诗》云:“势轧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见与扶持。忽从憔悴有生意,却为离披无俗姿。影入岩廊行乐处,韵含天籁宿斋时。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29]诗题中的“庙庭”指宰相官署的庭院,“偃松”是呈倒伏状的松树。按刘禹锡此诗以偃松自喻,感谢裴度对自己的“扶持”,当作于大和二、三年初入长安为官时[30],末句“谢公莫道东山去,待取阴成满凤池”称颂唱和对象虽有隐居之意,最终为天下苍生放弃归隐的慷慨大义。刘长卿作于大历十二年(777)秋的《题萧郎中开元寺新构幽寂亭》亦有句“康乐爱山水,赏心千载同。……独往应未遂,苍生思谢公”[31]。
这些诗歌中,谢安“东山再起”的故事感染了唐代积极向上的政治理想和精神风貌,谢安不再是清醒自如于仕隐之间的高士,而被唐代诗人建构为放弃归隐的救世主并将这一形象嵌套在当时与谢安地位相似的官员身上,唐人的入世之情与对苍生的殷殷系念可见一斑。
三、小结
管窥阮籍与谢安在唐诗典故中的运用特征,可以发现唐代文人因倾慕《世说新语》人物形象的个性情趣而接受之,更因感同《世说新语》人物形象执着世情的心理内涵而重构之。总的来说,促使世说人物形象多见于唐代诗歌的原因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崇尚用典的文坛风气。贞观时期,唐太宗及其身边的宫廷诗人多有应制奉和之作隶事用典,带起了诗坛追求典雅的风气,“世说入史”的编纂新识。唐代贞观年间修撰的《晋书》大量采用魏晋时期的小说、杂传等,其中包括《世说新语》。由于“在唐时刘孝标的《世说》注本最为盛行,刘注的详赡进一步增强了《世说》的史料价值。《晋书》的编撰者采用《世说》,基本上是把《世说》作为史料来看待和处理的”[32];建功立业的游宦经历:穷途之哭与东山之起多用于交往干谒的诗作,其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有官职,看似是两个相反的走向,实则都包含着隐仕之间对现实的体认与人生的感悟。而对典故中人物遭遇的亲切感,使唐代诗人在寻找精神的归属时与魏晋风度产生了契合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