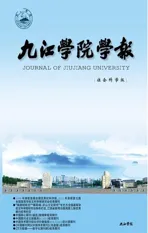贬途与心路*
——白居易被贬江州思想转折时间再考
2022-04-07周静敏
周静敏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学界历来认为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思想以及创作的转折点,思想由“兼济天下”变为“独善其身”,诗歌由讽喻变为闲适。但心态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应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白居易在赶赴江州的路途中,随着长安的逐渐远去和贬所的迫近,加之贬途环境的影响,其心态在贬途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思想转折在贬途就隐隐可以察觉。文章旨在从白居易贬途诗歌中探究其思想转变,即自白居易被贬的作品中分析其心态变化,从而探究其思想以及处世态度转变的动态过程。关于此次贬谪,白居易创作的散文并不多,但创作了一系列有明确地点标识的诗歌。据笔者统计,白居易此次贬途创作颇丰,除组诗《放言五首》外,还有44首诗歌,大大超越了同时代贬谪诗人。这些诗歌大多有明确地点,且都是吟咏环境。因此,本文通过白居易被贬江州途中所作的可考地点的诗歌,然后结合具体的自然环境分析,从而研究白居易心态转变的关键点。
一、贬谪路径再考
元和十年,白居易因“越职言事”和“伤名教”等罪行被贬江州,但其深层原因还是直言强谏而惹怒权臣。忠而被贬使得诗人内心产生了矛盾感和被弃感,进而导致其诗歌创作内容和风格发生改变。其贬所江州距长安数千里,唐代水陆交通发达,自长安通往江州的道路有数条。据《唐代交通图考》记载:“古代中国之疆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主体,而中隔秦岭、伏牛、桐柏、大别诸山脉,使南北交通局限于东西中三主线。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凌江入巴蜀。东线由河淮平原逾淮水至长江下游之吴越;汴河既开,即以汴河河道为主线。中线由关中东南行,由河洛西南行,皆至宛(南阳)邓,再循白水流域,南下襄阳,复南循汉水至长江中游之荆楚。此南北交通之自然形势也。”[1]但西道地势陡峭,水流湍急,运输量不大,所以其地位远不如东中两线。唐代水陆交通发达,馆驿制度也较为完善,东中两线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道,因此公私行旅出长安大都选择这两条道。东线前段即两都间驿道,自长安东行,经渭水,出潼关,至陕州,再南行至洛阳,沿运河南下。中线前段是蓝武驿道,亦称商山路,于长安灞桥始,经蓝田县,东南逾越秦岭至蓝田关,又越七盘岭,到商州商洛县,又东南行出武关。从地形上来看,商山路先缓后险,大部分路途位于陡峭的山中。而两都驿道是唐代国内第一驿道,平坦易行。
朱金城在《白居易年谱》中说到其“八月被贬,初出蓝田,到襄阳,乘舟经鄂州,冬初到江州”[2]。可知其走蓝田武关驿道。白居易为何舍弃平坦的大道而选蓝武驿道?有两个原因,其一,《唐会要》卷四一“左降官及流人”载:“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3]如此严苛的行程要求,显然并不允许贬官选择虽平坦但里程较远的两都驿道。其二,两都驿道中的汴河道时常发生河床淤塞问题,会严重耽误行程。除此之外,中唐以后,“汴河交通常为东方军阀所困扰,不如此道(蓝武驿道)之安全无阻,故此道之重要性益增,德宗时代更明令规定为仅次于两都间之大驿道。”[4]因此,唐代贬官迫于严苛的行程要求,往往会选择蓝武驿道。白居易经行蓝武驿道至襄阳改行水路,从襄阳水路至江州亦有两条道路。从地图上来看:自襄阳开始乘舟,沿汉水东南行,经郢州、复州、沔州,至鄂州转入长江,然后沿长江东南行至江州。但据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中的“我病方吟越,君行已过湖”[5],可知白居易此行经过某个湖,上述行程显然不对。据前文可知白居易走中道,而中道之总干线为荆襄驿道,荆州有洞庭湖,元稹诗中的“过湖”应是指此湖。所以白居易“是经襄州到荆州,再下经洞庭湖口,经鄂州至江州,非自襄州至鄂州直抵江州也”[6]。
白居易于元和十年八月被贬,冬初至江州。由于白居易被贬日期没有详细记载,在这里只做大致分析。白居易从长安出发,经商山路,至襄阳沿汉水南下,经鄂州,冬初到江州。冬初按十月,则白居易在路途中经行两个月左右。根据唐制,唐代馆驿每日传驿速度是四到六驿,平均每驿30里。那么正常行进速度为120里至180里,由于史书记载和所选参照都是根据唐代的“里”来记载,所以为方便描述,以下皆按唐代的“里”叙述,唐代一里约等于今天的454.2米。商山道山路崎岖难行,速度必然降低,笔者在《论韩愈贬潮系列诗歌中的贬谪之路》中曾考证,韩愈走陆路去往潮州的平均速度为日驰二驿或三驿,即每日行60-90里。从长安至襄阳的陆路约1130里,则白居易共走陆路12-18天,水路则走一个月左右。《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江州“西北至上都二千七百六十里”[7]。则水路共用一个月行1630里。水路行舟显然比陆路行走快,但舟行需风,如若遇到逆风则需等待,这也是白居易水路用时较长的原因之一。
水陆兼行使诗人看到更多往昔未见之景,而时空变化也使得诗人心态逐渐发生改变,所以贬途所作诗歌与以往皆不同,且不同的路途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倾向。因此将其贬途分为陆路、水路两个阶段,并从中探求其思想转折点。
二、陆路阶段白居易的纠结彷徨
陆路阶段是从长安至襄阳,白居易是经过蓝武驿道南下。据严耕望考证:“此道由长安东南行,经蓝田县,出蓝田关,经商州治所上洛县、商洛县,出武关,经邓州之内乡县、临湍县,至穰县。又由内乡经南阳县,亦至穰县。穰县南行经邓城至襄阳,凡一千一百余里。”[8]这条道路需越过多座山脉,险阻崎岖。《唐代交通图考》载曰:“自武关西北逾商山,七盘岭,秦岭,约四百里,皆行山中,至蓝田县,始出险就平,所谓商山道也。”[9]从蓝田至武关约有400里山路,但其地理位置险要,德宗时代更明令规定为仅次于两都间之大驿道,为唐代中线路程的必经之地。唐代由长安通往江淮岭南诸地的交通,“除物资运输及行李笨重之行旅者多取道汴河外,朝廷使臣及公私行旅远适东川、黔中、江淮、岭南者,皆利此道之径捷。”[10]因此此道有“名利道”之称。白居易《登商山最高顶》中说:“七年三往复,何得笑他人。”[11]仅白居易就曾在元和十年、元和十五年以及长庆二年七年间三次走此道。本文要考证的是其第一次经过此道时的具体情形。
出长安东南行,经长乐驿、灞桥驿,又东南行进入蓝田山区。《唐代交通图考》载:“蓝田北境,大道始入山区,上韩公坂,一名韩公堆。”[12]由此可知,诗人已进入山区,加之已至八月,天气转凉,诗人不免有悲秋之感,此时想到自己被贬通州的友人元稹,写下《韩公堆寄元九》,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把此诗列为元和十年作,且联系诗歌内容,元稹于元和十年三月被贬通州,因此可以确定这首诗作于此次贬途,诗歌的全文是:
韩公堆北涧西头,冷雨凉风拂面秋。努力南行少惆怅,江州犹似胜通州。[13]
韩公堆,严耕望据《长安志》及唐人诗句考证,其在蓝田县北二三十里处。而蓝田县距离长安八十里,此处应距长安五六十里,诗人应是刚出长安。元九指的是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元和十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面对着漫长的道路,想到了同被贬谪的好友,内心惆怅,写下了这首诗。首句点明时间地点,诗人沿路东南行,在经过韩公堆时,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冰凉的风夹杂着雨扑面而来,使其感觉到了秋天的气息,从而引发悲秋之感。加之从这里开始,道路变得崎岖,所以诗人在尾句勉励自己要努力前行,并自嘲地把江州和通州对比,从而起到宽慰自己的作用。整首诗弥漫着悲凉惆怅的氛围,充满对前路的怅然。从韩公堆出发,经蓝田驿,“又东南二十五里至蓝田县,去长安八十里。”[14]再由蓝田县“东南行二十五里至韩公驿,一名桓公驿。又十五里至蓝桥驿。”[15]在蓝桥驿,白居易见到元稹的题诗。元稹此前被贬江陵,元和十年正月自唐州奉诏还京,五年屈辱在此刻洗刷,在驿亭壁上写下《留呈梦得子厚致用》,谁知三月再次被贬通州。此处距长安有120里,白居易自此经过,看到好友昔日所写,不禁感慨万千,写下《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16]短短八个月的时间,朝堂变化如此诡谲,使得白居易感慨万千。这两首诗是诗人给自己与元稹的勉励之言,亦可看出其对世事无常的感慨。
除以上诗歌外,白居易在蓝武驿道还作有《初出蓝田路作》,此诗创作地存疑。诗中提到“朝经”和“夕次”显然已经过了一天,“韩公坡”即前文所提韩公堆,“蓝桥水”则指蓝桥驿,所以此诗必是创作于蓝桥驿之后。但下一句的“七十里”显然不符合事实,据上文可知,蓝桥驿距长安已有120里,因此做这样一个推测:诗中的里数指的是自韩公坡到蓝桥驿的距离。前文提到,韩公坡位于蓝田县北30里左右,而蓝桥驿位于县东南40里处,两者相加就是诗中提到的“七十里”。又据严耕望考证,这里的诗中提到的山指的是位于蓝田县城南的峣山。诗人此时应是位于峣山,下视群峰,方能看到此场景。因此本诗的创作地点为初出蓝桥驿之后的峣山。诗的全文是:
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去途从此始。绝顶忽上盘,众山皆下视。下视千万峰,峰头如浪起。朝经韩公坡,夕次蓝桥水。浔阳近四千,始行七十里。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17]
前两句表达了诗人因道路漫长而产生的迷茫,诗人此时位于峣山之上,看到山脉连绵不绝,千万山峰耸立。蓝田关因位于铙山之下亦称铙关,为关中平原通往南阳盆地的交通要隘,出关就意味着离开了长安。随着政治中心的远去,加之展望前途,看到的仍是连绵不断的山脉,所以后面三句诗人感叹旅途艰辛,行路劳苦。浔阳即今江西九江,是白居易的贬谪地,距长安2760里,即使把白居易所走里程相加,显然也不够“近四千”,因此,诗人是极言江州之远。尾句直接表达行路的艰辛,山路险阻,前路漫长,才走70里路程就已如此辛苦,郁闷以及悲凉之感油然而生。这首诗主要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前路的担忧,既担忧路途的险阻,也忧心自己的未来。与这首诗表达相同感情的还有《初贬官过望秦岭》,《商洛古诗文选注》中关于“望秦岭”一词的注释是:“秦岭经商州北面一段自唐以来人们习惯称之为望秦岭。”[18]唐代诗人欧阳詹《题秦岭》诗形容秦岭“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19],可以看出此道的分界特点。诗人在望秦岭上回首长安,伫立良久,却只有秋风无限,吹动诗人已渐白的须发。“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20]“草草”即可以看出诗人离京时的仓皇,根据唐制,官吏被贬要闻诏即行,因此白居易离开长安时家属未及跟随,只能自己孤身一人踏上贬途。而“忧后事”语含双关,既是说未及打点好家眷,也是在忧虑国家大事。所以才会“迟迟”,行路进程缓慢,表示出内心的依恋之情。“问前途”又是双关,既表示询问江州的路途,也表明诗人对政治的茫然。以上两首诗歌表明了白居易对前途的忧虑和对政治环境日趋险恶的担心。
从蓝桥驿出发,“东南逾秦岭,至蓝田关,去县九十里,去京师一百七十里,即今牧虎关。”[21]经蓝田关进入商州上洛县。上洛县有仙娥峰,在州西15里处,白居易经此作《仙娥峰下作》,诗大部分都在渲染仙娥峰的美好,最后一句“向无如此物,安足留四皓”[22]含蓄表达了诗人对归隐的向往。四皓指的是商山四皓。同样是在商州,诗人游四皓驿,写有《题四皓庙》:
卧逃秦乱起安刘,舒卷如云得自由。若有精灵应笑我,不成一事谪江州。[23]
秦朝末年,四位博士因不满秦始皇统治而隐居于商山,后来就用“商山四皓”泛指有名望的隐士。四皓庙,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四皓墓在(上洛)县西四里庙后。”[24]诗人一路东南行,“东南经北川驿,安山驿,麻涧,仙娥驿,至商州上洛县(今商县)。”[25]经仙娥峰后到达四皓庙,《仙娥峰下作》中含蓄的感情到此刻喷涌而出。诗歌首句的“安刘”是四皓的代称,是它们让刘邦下定决心不废太子刘盈,诗人羡慕他们做出丰功伟绩后归隐。功成身退是许多士大夫毕生追求的理想,如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26]欧阳修的“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27]名利与自由兼得,“四皓”也就得到他们的羡慕。尾句联系自身处境,借精灵之口表达自己未功成却被迫“归隐”的不甘与自嘲。与前文相比,这两首诗歌的感情发生了一定的转折。由忧心政治环境和自身前途变为对归隐、对自由的向往,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放弃政治,并为自己未作出一番事业而感到惋惜。
沿着山路继续东南行,到达商州。“商州去长安盖近三百里,去蓝田关约一百三十里,州有馆。”[28]诗人在商州驿馆里做了短暂停留,离开时写有《发商州》:“商州馆里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商州驿停留三日,等待与亲眷汇合。前文已经提到,唐代官员一旦被贬,需立即出发,且有严格的行程要求。白居易被贬,自己只身踏上贬途,亲人需筹措路费,收拾行李,所以未及跟随,到商州才终于成功汇合。“若比李三犹自胜,儿啼妇哭不闻声”李三指的是李顾言,卒于元和十年春,诗句的意思应该是自己尚活着,还可以见到妻儿,而李三却已听不到“儿啼妇哭”。这首诗主要是诗人对自己的开解与自嘲,也体现出白居易此行的艰辛与不易。也是行路的艰难使得白居易有了远离政治,保全自身的初步想法。
自商州出发,“由商洛又东南经桃花驿、层峰驿,亦九十里至武关(今关),有武关驿。此关北接高山,南邻绝涧,为春秋以来秦楚交通主道上之著名关隘,西去商州一百八九十里,去长安约近五百里。”[29]白居易又再次见到元稹的诗,并写下《武关南见元九题山石榴花见寄》,主要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和对长安的不舍之情。诗人此时已走完险阻的蓝武驿道,转入较为平坦的道路。出武关继续东南行,经青云岭、分水岭,至邓州内乡县(今县),此处距武关约350里左右。继续出发,沿“邓州南行一百四十里至故邓城,又二十里至安养县,……又南渡汉水二十里至襄州治所襄阳县(今县),凡一百八十里”[30]。以上可知,从长安至襄阳共计一千一百余里。诗人途经襄阳,写有《再到襄阳访问旧居》,诗写道:“昔到襄阳日,髯髯初有髭。今过襄阳日,髭鬓半成丝。”[31]《旧唐书》记载:贞元七年(791)其父季庚“历衢州、襄州别驾”[32]。这里的“昔”应是当年随父到襄阳,当时年方二十,嘴上刚刚长出了一点儿胡子。而这一次经过襄阳已经四十四岁,鬓边有了白发,连胡子都白了一些。前后对比表达时光飞逝之慨。“故知多零落,闾井亦迁移。独有秋江水,烟波似旧时。”[33]表明当年认识的人现在已不知去向,邻里也已搬迁,只有这深秋的襄江之水依旧烟波渺茫与往日一样。两句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襄阳距长安1100里,此时约已行12-18天。时间的变迁以及道路的行进,加之访问旧居勾起的往日情感,使得诗人产生逝者如斯,年华不再之感。自己汲汲于政治,得到的却是故知零落,年华不再和“儿啼妇哭”,这首诗与商州诗所表达的感情相似,都有着急流勇退的想法。
这是白居易此次贬途的前半段。陆路行程艰辛,时间上渐入深秋,加之刚被贬官,心理压力巨大,行程上也不敢懈怠,所以这些诗中多充满悲凉的氛围。并且随着时间和地点的推移,其心态逐渐发生改变,在蓝田和初至商州时,受畏祸心理的影响,只能隐晦表达对政治的关注。但也是从商州开始,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诗人已经不再那么执著于政治,初步萌生了保全自身的退隐想法,但这种退隐中还夹杂着未做出功绩的不甘。
三、白居易水路阶段矛盾表达和《与元九书》
白居易自襄阳转入水路,从此行舟前往江州需从汉江转入长江,前文已经论述,白居易走荆襄水道,然后至洞庭湖转入长江。这样比直接自汉水至鄂州,然后自鄂州转入长江里程更长。白居易选择绕路有其原因,汉江下游水位落差较大,且流速很快,可达到每秒四米,远不如前段平稳,行舟难度大大增加。而当时荆襄水道较为成熟且平稳,所以白居易选择进入荆州。自郢州沿荆襄水道继续南下,至扬口进入扬水西行至荆州。扬口即扬水运河,西晋初开辟,南连扬水,北连汉江。荆州即今湖北省荆州市,位于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腹地。是唐代通往江淮岭南等地区的交通枢纽。白居易自荆州入洞庭湖,自洞庭湖进入长江。这是水路的前半段,诗人沿荆襄水道行舟,中途时有停留。
(一)汉水段的《臼口阻风十日》再分析
白居易未直接沿汉水至鄂州,而是选择走荆襄线。荆襄路以陆上交通为主,但水运亦通。此道“由襄阳下汉水舟行至汉水折而东流处之扬口,改浮扬水折向西南行至江陵”[34]。此时诗人已行半月,秋天已过半,即将进入深秋,天气变得寒冷。
白居易自襄阳访问旧居后,由陆路转入水路时,写有《襄阳舟夜》:“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唐代交通图考》载曰:“襄阳有汉阴驿,盖在城西,汉水南岸,水陆兼用,甚宏大,故为一名驿,屡见文史。”[35]“本是多愁人,复此风波夕。”白居易自汉阴驿进入汉水,迎面来的“秋风”和“寒浪”表明此时已即将深秋。“风波夕”一语双关,既说明自己此刻面对的风浪,也隐喻当前如履薄冰的政治环境,而自己这个“多愁人”不免要愁上加愁。诗人此时刚入汉水,天气转寒以及风浪侵袭,诗人在诗中隐喻动荡的时局以及黑暗的政治,表达对自身处境的忧愁之情。沿汉水继续南下,绕过岘山,到达汉江中游,宜城北部时,写有《臼口阻风十日》,这首诗亦暗喻朝政:
洪涛白浪塞江津,处处邅回事事迍。世上方为失途客,江头又作阻风人。鱼虾遇雨腥盈鼻,蚊蚋和烟痒满身。老大光阴能几日,等闲臼口坐经旬。[36]
臼口位于湖北钟祥境内,现称旧口,位于汉水沿岸。白居易元和十五年自忠州召还以及长庆二年请求外任皆经汉水,但根据诗歌的思想情感以及此次心态背景等原因,可以判断这首诗是此次贬途所作。诗人行至此处,遇大风天气,逆水行舟,不仅行路缓慢,且易覆舟,所以诗人在此停舟十天。首句写途中受阻的原因为“洪涛白浪”和自己处处困顿、事事不顺境遇。第二句直抒胸臆,表示自己政治上是“失途客”,旅途中是“阻风人”。第三句描写阻风臼口的遭遇,因大雨死亡的鱼虾漂浮在江面发出阵阵腥臭,而蚊虫的叮咬和炊烟使得诗人混身发痒。这句诗也暗指官场的黑暗。尾句表明诗人等待的焦虑以及对光阴逝去的无奈。诗人借此诗暗暗表明了自己忠而被贬的愤懑以及对黑暗官场的痛斥,与白居易之前的讽喻诗有异曲同工之处。
沿汉水南下至荆州,首先要经过郢州。郢州今为武汉市武昌管辖,位于其治下的钟祥市(县级市)。其“西北至襄州三百一十里”[37],此处距长安已远,已在水上行驶约300里。诗人在此上岸,游白雪楼,写下《登郢州白雪楼》:
白雪楼中一望乡,青山蔟蔟水茫茫。朝来渡口逢京使,说道烟尘近洛阳。[38]
《太平寰宇记》载:“白雪楼基在州子城西。”[39]白居易行舟于汉水上,至郢州子城渡口靠岸,登白雪楼远眺写下了这首诗。首句写诗人在楼中望向家乡的方向,只看到一座座青山和茫茫的水面。《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郢州“西北至上都一千三百八十五里”[40]。此时距长安已远,路程已行多半,诗人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尾句诗人想起早上在渡口遇到京城的使者,说叛军已迫近洛阳。诗下小注:“时淮西寇未平。”淮西之乱是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叛乱,于元和九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最终在裴度等人的努力下平息。白居易被贬之时,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一年,因统帅非人,此时中央军队节节败退,甚至已迫近东都洛阳。通过这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担忧个人际遇之时,仍心系国家大事。
与陆路阶段不同,此段路程的诗歌中多处暗喻时局,政治比重增多。应是此时远离长安,没有了畏祸心理,同时江上波浪使得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加深。诗人称自己为“失途客”和“多愁人”,不单单是指道路险阻,也指自己的政治生涯不顺。而这些,是由水路的风浪所引发。
(二)长江段的《放言五首》再审视
至长江段大约已进入晚秋。自洞庭湖进入长江中游,然后沿长江东南行进入鄂州。鄂州即今湖北武汉鄂州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其:“西北至上都二千二百六十里。”[41]是江州的临州,是此次贬地的上一站。白居易在此停泊至鹦鹉州,写有《夜闻歌者》。这首诗是一首短篇叙事诗,通过描写歌女的悲惨状况,表达对她们的同情,也借此抒发了自己被贬偏远之地的凄凉心境。诗的构思与手法与《琵琶记》颇为相似。沿长江继续东行,至武昌靠岸,游黄鹤楼,写有《卢侍御与崔评事为予于黄鹤楼置宴,宴罢同望》。黄鹤楼是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位于蛇山之巅,濒临长江。诗人与友人相聚,宴罢,诗人伫立黄鹤楼头,无边美景勾起了诗人的感伤之情。“总是平生未行处,醉来堪赏醒堪愁。”[42]醉了还能欣赏,醒着恐怕只有被迫远离家乡的愁绪。同样创作于长江段的还有《岁晚旅望》:
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万物秋霜能坏色,四时冬日最凋年。烟波半露新沙地,鸟雀群飞欲雪天。向晚苍苍南北望,穷阴旅思两无边。[43]
此诗没有标明地点,但从其中的“岁晚”“秋霜”“冬日”可知此时位于秋末冬初,按白居易冬初到达江州来看,此时必是贬途的末尾。朝去暮来,季节变迁,转眼已经到了冬季,万物凋零,色彩消失,诗人隔着烟雾看到因植物枯萎而裸露出的“新沙地”和因快要下雪而导致的“鸟雀群飞”,一片苍凉之景。白居易站在船头,北望渐远的京都与所走的路,向南往贬所以及未走的路,激发了诗人的旅途愁思。
可以看出,因冬季渐至以及空间转换,诗人至长江段充满了无限忧愁,被贬的寂寞苍凉,因旅途遥远且艰辛产生的旅途愁思等使得诗人的忧愁已经到达极点。尚永亮在《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写道:“元和贬谪文学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力与阻力相碰撞、相抗衡并最终克服阻力的过程。”[44]面对自己的无边愁绪,白居易的选择与元和五大逐臣中的其它四位诗人不同,他选择参禅入道,企图用佛道来缓解内心无边的忧愁,这种思想也同时表现在诗中,如《岁暮道情二首》:
壮日苦曾惊岁月,长年都不惜光阴。为学空门平等法,先齐老少死生心。半故青衫半白头,雪风吹面上江楼。禅功自见无人觉,合是愁时亦不愁。[45]
首句感叹年华逝去,第二句则表明自己通过修习佛道而看淡生死。根据唐制,文官八品、九品着青衫,所以第三句的“青衫”暗指官阶,头发已半白却还是八九品小官的诗人,迎着风雪上江楼,如果是以前诗人肯定是无边忧愁。但由于诗人“禅功”的修炼,便不感觉忧愁,同时期的诗歌《晏坐闲吟》中也有“愿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46],鲜明地表达了借佛排忧的思想感情。这其实是古代失意的知识分子常用的手段,每当他们郁郁不得志或忠而被贬之后,内心怨愤无处发泄,又怕因言获罪,只能把方向转向佛道,悟道参禅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白居易亦是如此。其在《强酒》中就明确表示:“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47]
白居易不再沉潜于苦闷的心境,体现在他的组诗《放言五首》中。根据诗的小序“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48],这组诗通过辨伪和用典来表达自己不能言明的态度。因多含佛道哲理,且是在水路,所以推测是在其参禅悟道之后所作,即是在长江段,即将到达任所时所作。
贺贻孙在《诗笺》中评价道:“李颀七言古诗,佳者本多,其《杂兴》二句云:‘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亦偶然兴到语耳,而乐天独叹服此语,以为绝伦。”[49]白居易在小序中称赞此语,并不在于诗句的精彩绝妙,而是句中含义契合当下心境。通过济水与黄河的清浊对比,同时引用周公和接舆的典故,比喻兼议论,相反相成。程千帆认为此诗表达了诗人“善恶死生齐一贯,只应斗酒任苍苍”的道家思想。白居易此时受到道家影响,已经隐隐有看破名利与生死的想法,他的《放言五首》其一清晰地展示了这种倾向: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50]
这首诗告诫世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同时也兼及对自己政治生涯的反思。颈联运用了臧武仲和宁武子的典故。武仲凭借其防地来要挟鲁君,让世人认为他是圣人。而“宁子”,《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51]后来就以宁武子为君王有道则进用其智能,无道则佯愚以全身的政治家的典型。诗人把二者对比,讽刺权贵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宁武子处事方式的向往。而尾联则喻指自身微薄之力难以改变“朝真暮伪”的世道。而这首诗充满哲理,同时也是白居易对自己为官的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微弱之力难以扭转局势,产生了远离政治的想法。其三为善恶辨伪,亦表达了此种倾向,全文为: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52]
这首诗通过列举“三日烧玉”“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以及周公和王莽的例子,说明人的善恶不能通过表面来判断,而是要通过时间证明。尾句不只是对全诗的总结,亦是诗人真情实感的流露。也表明诗人对生死的看淡以及对政治的无力。其它三首诗亦是对政治、对世事的辨伪,其二为祸福辨伪;其四为贫富辨伪;其五为生死辨伪。白居易在诗中感叹世事无常,勉励自己将祸福、善恶、贫富、生死看淡,从而超脱于政治,体现出“退”的想法。这里的退与上文陆路后半段偶然的想法不同,而是摒弃各种情况影响后最真实的态度。
终于在这一年的冬天,白居易到达江州。江州即今江西省九江市,在唐代属江南西道,左倚庐山,右连长江、鄱阳湖,是一个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的江南水乡。白居易在即将达到浔阳时写有《望江州》:
江回望见双华表,知是浔阳西郭门。犹去孤舟三四里,水烟沙雨欲黄昏。[53]
白居易此时即将到达浔阳,其县治在长江之北,因浔水之阳而得名。诗人临州远眺,望见浔阳城门。此时距贬所还有三四里,轻烟缭绕,细雨绵绵,已是黄昏。此时距长安已远,被贬时日已长,加之白居易心态的转变,因此这首诗没有表现具体的感情倾向,只是对现下环境进行描述,表现出抛弃执念后的平静以及远离政治后的坦然,其之后的《初到江州》也表现出相似的倾向。
以上可知,与陆路阶段相比,水路所作诗歌中感伤之情加重。水路虽无行路之艰辛,但此阶段诗人更能敏锐感知日夜更替,时光流逝,加之偶尔因逆风需停留等待,光阴的虚掷使得诗人焦躁。而水上风浪以及秋日万物凋零,加重了诗人内心的愁绪。诗人未必想完全远离朝廷,从汉水段的诗歌可以看出,诗人很渴望建功立业,横遭贬谪使他感到自己虚度光阴,无法一展抱负,充满了无奈之感。而这些忧愁到达极点时,诗人只能借佛道排遣,直到他在《放言五首》中彻底醒悟,这种因政治而沉潜于内心的焦虑与忧愁才得以排解。在诗中,他表达出了对政治的无力,也是这种无力让他不再执着于政治与名利。因此可以看出,白居易在贬途思想就已发生转折。但白居易明确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以及对人生进行自我定位是在到达贬所之后的《与元九书》,他在书中说道: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而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54]
白居易此书虽主要论述创作方法,但从以上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其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处世态度,当君王有道,政治清明,他会大展身手;但当时局动荡,权奸擅权时,他会急流勇退。这是经历了忠而被贬的不甘以及贬途的身心磨损后保全自身的一种方式,亦是白居易人生态度的一大转折。同样创作于贬所的《与杨虞卿书》也表现出这种倾向:“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55]以上可知,这种“隐”与“退”的思想,以及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写作态度,同过去的刚直态度,和“不惧权家怒,亦任亲朋讥”[56]的反抗精神,已判若两人。
四、结论
学界历来把《与元九书》看作是白居易创作的转折点,把江州之贬认作是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关键点。但通过上述对其贬途诗歌的分析,可以看出白居易的退隐想法是在贬途中逐渐产生,逐渐坚定的。陆路阶段由于畏祸心态,使他不敢在诗歌中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且受特定环境的影响,初步产生远离政治,保全自身的想法,但同时还有被贬的不甘。至汉水段,畏祸心态减弱,政治在诗歌中的比重增多,多处隐喻官场黑暗,前文的不甘亦在此刻表现出来,也表明了白居易对时局的关注。时局动荡而对自己未来感到忧虑,道路艰险以及距长安遥远而产生的旅途愁思等,使得诗人把参禅作为排解之法,而在《放言五首》其一中更是表达了对宁武子做法的向往,初步表露了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从而使得白居易思想转变实现由《与元九书》的“点”,到贬途逐渐转变的“线”的延长,证明其人生态度并不是骤然转变,而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