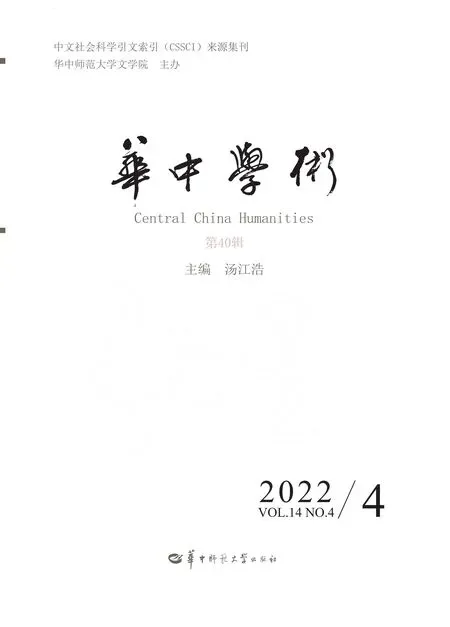“汉无礼乐”、两汉礼议及其经学典据
2022-04-07曾军
曾 军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黄州,438000)
汉代是经学时代的开始,也是传统礼治思想的形成期。“宏观地看,整个两汉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礼治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逐步形成的过程。”[1]礼学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必然需要国家层面的礼制设计。从这个意义出发,应如何理解清儒王鸣盛“汉无礼乐”的论断?两汉制礼的重点是什么?两汉就哪些问题展开礼议?如何整合经学典据进行礼制建构?
一、汉代制礼重于郊庙朝廷
清儒王鸣盛以为“汉无礼乐”:“子长《礼》《乐》二书亦空论其理,但子长述黄帝及太初,若欲实叙,实难隐括,孟坚述西汉二百年,何难实叙,只因汉未尝制礼,乐府俱是郑声,本无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论了之。”[2]推断汉未尝制礼,二史无礼可志。
王氏所据为《史记·礼书》《汉书·礼乐志》。然《汉书》记事下限在王莽地皇四年。又《后汉书》有《礼仪志》,包括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高禖、养老、先蚕、祓禊;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貙刘、案户、祠星、立冬、冬至、腊、大傩、土牛、遣卫士、朝会;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等;有《祭祀志》,包括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北郊、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等。可知东汉礼仪礼制已初具规模,故王氏论断的时间断限可能指西汉一朝。
如言“西汉无礼乐”,仍不免失之偏颇,东汉礼制不可能凭空而来。《史记·礼书》取荀子《礼论》《议兵》专论礼制之重要而未叙实礼,然有《封禅书》记黄帝至武帝太初间封禅祭祀事。《汉书·礼乐志》从礼乐治国立论,列叙汉高祖时叔孙通、文帝时贾谊、武帝时董仲舒、宣帝时王吉、成帝时刘向提议制礼均不了了之,后大言乐教。然有《郊祀志》全取《封禅书》,并增补宣帝至王莽篡位二年之间郊祀诸事。又《汉书·韦玄成传》详载西汉郡国庙罢废与宗庙迭毁等礼议,可知西汉既多制礼之倡,又多议礼之事,都重在治国礼制。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自汉以来史官所记礼制止用于郊庙朝廷,皆有司之事。”[3]
叔孙通制礼重在宗庙朝仪。《汉书·礼乐志》载“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本传载汉高祖时叔孙通“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惠帝即位后“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4]。《后汉书·曹褒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5]可知叔孙通制作的《汉仪》内容偏重朝仪和宗庙仪法,班固见过,至少东汉章帝时尚存。又郑玄注《周礼》提及《汉礼器制度》,贾公彦曰:“云《汉礼器制度》云云者,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郑君依而用之也。”[6]叔孙通所制朝仪使高祖“知为皇帝之贵”,制宗庙仪法、礼器制度有草创之功,足证西汉有制礼订仪的举措。
班固引其父班彪言:“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纷不定。”[7]元帝时贡禹发起宗庙迭毁之议,成帝时匡衡改郊兆之议,皆成定制,但废而又复、反复不定。《晋书·礼志上》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余年,故往往改变”。陈戍国先生认为汉代有礼、汉礼多无定制[8],都指出了西汉制礼具有反复不定的特点。
汉礼无定制致使汉礼的记载流传成为问题。《南齐书·礼志上》:“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9]说明西汉有所创制却立而又废,反复不定;东汉有个体创制而史官不取,导致汉礼无传。这可能就是王氏以为“汉无礼乐”的原因。
西汉郊庙朝廷制礼反复不定,有现实政治和经学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秦汉祭祀之风极盛,名目繁多。西汉制礼多杂采秦仪,秦时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祀众多。
于是自崤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霸、产、丰、涝、泾、渭、长水,皆不在大山川数,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壻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逐之属,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丰、镐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也。各以岁时奉祠。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10]
名山大川与京师周边的小山小川都有庙祠。最尊贵者为祭祀天地上帝的雍四畤。秦之君王多建畤祀天,如秦襄公建西畤祀白帝,秦文公建鄜畤郊祭白帝、建陈宝畤,秦德公作伏祠,秦宣公建密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建畦畤栎阳祀白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至泰山封禅祭天地。
汉沿秦制,高祖增建北畤,其后渐增。帝王迷信鬼神,各地方术士趁势而起。文帝时有鲁人公孙臣谈五德终始,赵人新垣平讲望气。武帝更是沉迷鬼神之祭,如李少君祠灶、谷道、却老方,亳人谬忌献泰一方,齐人少翁言方,栾大言方,汾阴巫锦发鼎,齐人公孙卿言宝鼎神策,王朔望气,粤人勇之鼓吹粤祠鸡卜,济南人公玉带献黄帝时明堂图等[11]。《隋书·礼仪志》讽“武帝兴典制而爱方术,至于鬼神之祭流宕不归”,丝毫不诬。至汉哀帝,“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12]。数字十分惊人。其时各种思想如阴阳五行、黄老道学、易学、谶纬、地方宗教与儒术混杂融合,呈现凡祠即祀的祭祀之风。如此庞大而频繁的祭祀活动给汉王朝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混乱的祭祀对象也不利于统一王朝的思想统一,需要从礼制上进行全面清理。
其二,汉高堂生所传《礼经》为士礼,没有天子之礼。“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13]“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14]天子祭祀上帝、祖宗等礼仪无经可据,汉王朝只能由士礼推及天子之礼,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论定的过程。汉代两次皇帝亲自参与的重大经学讨论,集举国之大儒,论经学之是非,皆可谓从经学典据中寻求“推及”之法。
一次是西汉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15]。刘向以《穀梁》,薛广德以《鲁诗》,施雠、梁丘临以《易》,欧阳地余、林尊、周堪、张山拊、假仓以《尚书》,韦玄成、戴圣、闻人通汉以《礼》,于长安未央宫北石渠阁杂论《五经》同异。当时礼有庆普、戴德、戴圣三家,《小戴礼记》的编撰者戴圣参加了此次会议。现存《石渠礼论》10余条,涉及祭祀、宗庙、继嗣、丧服、谥法、乡射、大射等。此次会议为元帝、成帝时专题礼议开启了先河。
一次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16]。鲁恭以《鲁诗》,丁鸿以《尚书》,贾逵以《左氏传》,杨终以《春秋》,李育以《公羊》,魏应负责问难,班固撰集其事,成《白虎通义》。所论如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乡射、封禅、耕桑、封禅、瑞贽、三正、嫁娶、绋冕、丧服、郊祀、宗庙之类等,与郊庙朝廷礼制紧密相关,既明确了礼制中重要概念的含义,又对朝廷相关重要名号、仪制作出清晰的规定,说明礼治思想已确立并逐渐成熟。
郊庙礼制既衔接着古代社会的思想信仰,又连通着当世王朝的治术框架。在天下已定、各种思想混合交融之际,汉王朝以郊庙祭祀之礼等国家典制的设立为重点来建构礼治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寻找传统来源、经典依据,也要符合现实的需要,接受政治的检验。
二、两汉礼议:缘经学以饰政治
西汉礼制创制之初,朝廷大员激烈论议,皇帝态度反复不定,礼议频繁。元帝时郡国庙罢废和宗庙迭毁之议,成帝、平帝时徙置长安南北郊等重大礼议,反映了汉王朝以郊庙朝廷礼制稳固皇权,以经学缘饰政治的多方努力。
(一)郡国庙罢废之议
郡国庙是指奉皇帝命令设立在各郡国都城内、由诸侯王主持祭祀的专祀汉帝及其先祖的宗庙。起于高祖十年,令诸侯在王都皆立太上皇庙,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文、景、武、昭、宣帝逐渐增加,元帝永元四年罢废。西汉元帝时丞相贡禹发起关于罢废郡国庙的礼议,《汉书·韦玄成传》详细记载了该礼议的始末[17]。
对郡国庙的质疑并非到元帝之时才出现,只是前期禁止群臣讨论。“初,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元帝之所以要废止这道禁令,与宗庙越来越多,祭祀耗费越来越多,朝廷财政无力支撑有很大关系。“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每年约24455祠,用卫士45129人,祝宰乐12147人,再加上牺牲玉帛等巨额配套物资,无疑已成为汉朝财政一笔沉重的负担。贡禹动议“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元帝诏议罢废,要朝臣在礼学上找依据,对礼学而言,是一次清理整合先秦经学礼据、发展礼学的机会。
元帝诏书曰,打天下时在郡国建宗庙是出于“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的政治目的,沿袭至今,一是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二是不能亲祭如不祭。韦玄成等70人顺应元帝之意,立足于尊卑等差申论:从肯定“祭繇中出,生于心”提出“圣人飨帝/孝子飨亲”,推论皇家宗庙只能建在京师,只有天子才能亲祭,诸侯只能助祭。建在郡国的皇家宗庙必须罢废,才能确立天子、诸侯的尊卑分界,从礼制上确保天子在庙祭中的至高地位,凸显尊尊之义。其后元帝因梦祖宗谴告欲复郡国庙,诏继任丞相匡衡商议。匡衡指出郡国庙的设立“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祭祀之义以民为本”,说服元帝坚持罢废。
该礼议经学典据有四:一是古礼,先秦礼制中无郡国庙。《春秋》载鲁国立有文王庙,鲁国仲孙、叔孙、季孙都立有桓公庙,其设立似有先例。《礼记·郊特牲》曰:“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18]私家立公庙,混乱尊卑秩序,是为僭礼。
二是《诗经》“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出自《诗经·周颂·雍》。郑玄注:“有是来时雍雍然,既至止而肃肃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与诸侯也。天子是时则穆穆然。于进大牡之牲,百辟与诸侯又助我陈祭祀之馔,言得天下之欢心。”[19]描绘的是周公、成王在太祖庙禘祭文王,诸侯纷纷前来助祭的场景,说明虽无礼制明文,但天子主祭、四海之内诸侯助祭的周礼仪制客观存在。
三是《春秋》“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原文不见于《春秋》三传,但合乎《春秋》微言大义,严嫡庶、君臣、天子诸侯之别。
四是《论语·八佾》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皇侃说:“既并须如在,故说者引孔子语证成己义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摄之,而于我心不尽,是与不祭同也。”[20]祭祀最重要的是尽心,汉帝先祖庙只能由天子亲祭,天子不能去郡国亲祭,请诸侯主祭为不尽心、不诚,所以郡国庙已失去存在的价值。
罢废郡国庙之议,通过罢废郡国汉帝先祖庙、保留京师宗庙的举措,确立天子独尊的地位,体现了礼以别异的功能,以礼制有效地区别天子诸侯尊卑等差来稳固皇权。
(二)宗庙迭毁之礼
宗庙迭毁涉及天子庙数、昭穆排列,是礼学上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宗庙迭毁制度,就是根据祭祀者与被祭祀者血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而制定的宗庙逐级闲置的制度……最根本的目的,是保证作为奉祀人的当代君王能够与祭祀对象之间具有最明确、最亲近的血缘关系和世位继承关系。”[21]这个定义强调宗庙迭毁与血缘、世位继承的关系。宗庙迭毁的依据是五服制度,五服制度又以血缘亲疏远近为基础。只是世位继承有时与血缘关系并不一致,由此衍生出一些具体问题。
汉帝多自立庙又增加了宗庙迭毁的难度。清儒赵翼曰:“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汉书》本纪,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可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22]这必然导致“宗庙异处,昭穆不序”的局面。
宗庙迭毁之议也由贡禹发起。贡禹卒后,永光四年罢郡国庙之后一个多月,元帝下诏讨论京师帝王祖先宗庙迭毁问题。此次礼议是真正意义上的礼学交锋,直至平帝元始中还在讨论,“此事在西汉庙制转变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3]。《汉书·韦玄成传》详细记载了这次旷日持久的礼议[24]。文繁不载,下简述该礼议过程、各方主要观点及主要典据。
贡禹认为“古者天子七庙”,主张“亲尽宜毁”。元帝诏书称“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二者都主张“亲尽宜毁”,但在庙数上有七庙和五庙的不同。
韦玄成等44人的观点是,设五庙,始祖祭天配祀,太祖(始受命、始封君,即高祖刘邦)因功绩卓越世世不毁,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其依据为:一是《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世世不毁;二是《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祭天以其始祖配;三是周加设文、武至七庙是为特例。七庙有《礼记·王制》“一始祖,三昭三穆”与《礼记·祭法》“一始祖,二祧庙,四亲庙”的不同,周为后者。
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29人认为孝文皇帝有大功绩宜为太宗之庙。廷尉尹忠以为孝武皇帝有大功绩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18人认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昭穆制是在祭祀先王时安放先王神位时的一种排列顺序,前提是必须即位为王。根据昭穆制度,元帝的皇考曾祖父戾太子刘据未尝即位,不能列入昭穆序列。
元帝犹豫不能决,一年后又下诏,明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的基本原则,以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韦玄成等调整为“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的方案: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与元帝不同的是,韦玄成依然认为“皇考庙亲未尽”。
一祖一宗、五庙迭毁的方案施行之后,元帝因疾又欲复诸庙。匡衡撰《告谢毁庙文》尽力劝止,元帝依然“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成帝继位,按匡衡提议,保留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悉罢孝惠、孝景庙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河平元年复立如故,甚至恢复吕后“擅议宗庙之命”,禁止论议宗庙问题。
哀帝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以为“迭毁之次,当以时定”,重启迭毁之议。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53人坚持“亲尽则毁”的血缘关系原则,反对功烈论定原则,提出武帝亲尽宜毁。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在《礼记》诸篇和《春秋》传中发现庙数、丧期体现“尊卑之序”,宗庙常数和变数的依据;在《诗经》中找到历史先例,在《礼记·祭法》中发现了尊德贵功的合理性,提出“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赞成功烈论定原则,认为武帝不宜毁。哀帝从之。
究其根本,宗庙庙数来源于五服制度,如果天子庙数完全按照五服来排列,就无法与诸侯、大夫、士相区分,无法体现尊卑之序,所以五庙制很快被舍弃。故宗庙迭毁之议的争论,归根结底是“亲尽宜毁”的血缘亲疏论定原则与“祖有功而宗有德”的功烈论定原则的博弈,也可谓是宗法与政治的博弈。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也都能找到经学典据的支持。钱杭先生肯定调和帝王文治武功追求与宗法礼制的做法,“王舜、刘歆试图将外在的礼制‘内化’为帝王对自身的功德和道德要求,这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基本方法”[25]。曾亦先生认为汉初遍祀群庙的做法以及元帝以后“亲尽宜毁”共识的贯彻,体现了亲亲的原则;儒臣普遍赞同礼家“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说法基于尊尊的原则,儒家礼乐制度的建构常兼顾亲亲与尊尊的原则[26]。
宗庙迭毁之议主要处理宗庙中帝王祖先的排列位次问题,既要尊重血缘关系敬宗收族,又要清理世系利于继统。既要团结五服宗亲以维护皇权,又要让帝王统系区别于普通宗法。因此,兼顾亲缘和功烈、兼顾亲亲与尊尊的宗庙迭毁制度是最好的选择。至于这样的制度设计会不会突破经学理论的基本构想,则是经学家们难以掌控的。
(三)徙置长安南北郊之议
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天。只有天子才能祭天,所以郊外祭天之礼,是汉王朝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制度设计。成帝以前关于郊祀讨论过天子亲临、郊拜泰一、郊祠配乐、以木禺马代驹等问题,成帝时开始讨论郊祀地点是否由京师以外移至京师之中。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发起了将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徙置长安南北郊的礼议,成帝崩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等67人议复长安南北郊。
考察《汉书》诸本纪及《郊祀志》王莽等人的奏议,可梳理出西汉以来郊祀的历史沿革。西汉高祖沿用秦雍州四畤增北畤,祀五帝。文帝十五年始幸雍郊见五畤。武帝元朔五年立泰一祠于长安城东南郊,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阴,元鼎五年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确立天子祭天之制。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于长安南北郊。第二年成帝始祀南郊,完成了从雍五畤到南北郊祀的重大礼制转变,此变革始于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发起的礼议。
汉成帝建始元年,匡衡、张谭奏议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应徙置长安南北郊,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8人主张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支持匡衡、张谭的观点。最终赞成徙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于长安南北郊的意见取得胜利。
匡、张二人的主要观点是“承天之序、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此说法与“唯圣人为能飨帝”极其相似,显然是顺承郡国庙罢废礼议而来。即天子为受命帝王、天之子,惟天子可以祀天,祀天地点应该设在天子所居都城的近郊,以便于天子亲祭。
徙置理由有二:一是方位不合。古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武帝住在甘泉宫,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而成帝住在长安,却到长安的北边祭天,到长安的东边祭地,不合适。二是亲祭困难。“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吏民困苦,百官烦费”,无地利之便,反有劳民伤财之虞,不合“承天子民之意”。他们的支持者找到《礼记·祭法》和《尚书·召诰》予以佐证:
《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薶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27]
厘析其意,其一,方位的礼学含义。从尊卑言,南郊可定天位;从阴阳论,南郊、北郊应当置于正阳、大阴之处。又《礼记》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祭统》:“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皆说明南、北郊方位的特殊意义。其二,经书载周公徙都洛邑、定郊礼于洛,足以说明改变郊祀地点有圣王成例。其三,尊卑贵贱等差的要求。“天地以王者为主,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
匡、张又以“广谋从众合于天心”劝说成帝,天子从之。又议雍、鄜、密、上、下、北畤、陈宝祠皆不宜复修,天子一一听从。第二年匡衡坐事免官,成帝无继嗣,认为是罢废郡国庙和徙南北郊的后果,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史书未具载许嘉等人“所以从来久远宜如故”的奏议理由,大体上应该相当于刘向“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之类。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等67人议,历数西汉郊礼的历史沿革,列举复甘泉、汾阴祠依旧无福的实证,主张复长安南北郊如故,但该奏议的核心要义已经从方位、尊卑转到配祀问题。
西汉罢废郡国庙之议,通过罢废京师外的郡国庙区分天子与诸侯宗亲的尊卑等级。京师宗庙迭毁之议,通过调和血缘亲疏与世位继统的矛盾安排天子祖先的排列次序,确定超越普通宗法制的帝王宗庙迭毁机制。徙置长安南北郊之议,确定皇帝承天之序的天人秩序。这些礼议配合王朝政治调整郊庙制度,从礼制上妥善安排天子与诸侯宗亲、与祖先、与天地的关系,逐步完成了汉王朝宏大的礼治架构。尽管其间制度多有反复,但是关于郊庙朝廷的礼制设计在礼议中不断调整,实际上取得了共识,这是礼学发展的重要成果。
三、元始仪:礼治架构的完成
西汉王朝郊庙祭祀的制度框架,最终是由王莽借助《周礼》完成的,这就是平帝元始五年提出的元始仪。王莽议曰:
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穀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28]
奏议所引孔子之言及“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皆出自《孝经·圣治章》。王氏据《孝经》《礼记》《穀梁传》将尊祖与祀天用孝道联系起来,从人伦尊祖严父推及天子父事天,由此建立高祖配祀制度。
王莽设计了包括天神、地祇、四望、山川与祖妣的一整套祭祀方案。首先是郊祀中天地与先祖先妣的配祀:“《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通过配祀,帝王宗庙与南北郊祭天地从礼制上关联起来。
其次是郊祀中常祀,孟春正月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冬至南郊地上之圜丘祭天,高帝配;夏至北郊泽中之方丘祭地,高后配。从此,南郊地上之圜丘祭天,北郊泽中之方丘祭地,高帝、高后配祀成为定制。
再次是设立五郊兆。王莽根据“《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认为“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提出“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将原五帝兆变为五郊兆,环绕在长安城周围,分别为未地兆、东郊兆、南郊兆、西郊兆、北郊兆,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各方山川于其中。至此,王莽整合了自先秦以来的阴阳五行及经学纬书中的天道系统,将五方帝、五色帝、五人帝结合起来,建立起包含南北郊、五郊兆和四望等较为完整的祭祀体系,史称“元始仪”。
元始仪的经学依据从《春秋》《礼记》转向了《周官》。当王莽试图彻底清理祭祀体系、整合秦汉以来的祭祀传统、建构新的祭祀礼制框架的时候,《春秋》《礼记》中零散的关于礼制的碎片化记录或言论就无法满足其理论需求,而《周礼·春官》对于祭祀活动中职官职责的描述给了他巨大启发,促使他对祭祀制度作体系化建构。王莽依托《周礼·春官》,结合《孝经》《礼记》等经学典据所制定的元始仪,也使得西汉末横空出世的《周礼》一跃成为“三礼”之首,直至北宋王安石还以其为改革财政的经学依傍。
总之,宗庙与郊祀制度的改革,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章学诚曰:“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29]武帝对董仲舒的策问:“前王为何覆灭?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30]成帝白虎殿对策问:“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31]可知证明刘汉政权承天之序是两汉郊庙制礼的核心问题,也是两汉郊庙制礼的根本。如何依经立义运用经传典籍解释政治问题,如何有效处理法古与变古、尊祖敬宗与皇权独尊的关系,是汉王朝要求经学努力的方向。
郊庙礼制的论议和制订,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学问题,而是对经典的重新发现与诠释,又须与现实政治相糅合相调谐。贡禹、韦玄成、匡衡、王莽等人提出的礼制方案,同时也是礼治方案。他们通过诠释《礼记》《周礼》《春秋》《孝经》等经学典据,将经学郊庙祭祀理论与秦汉传统祭祀实践相结合,从人伦关系到天人之际,尽力安顿天子与天地、天子与祖先、天子与诸侯宗亲的关系,建构出一套大体完整、包含天地秩序的祭祀系统并付诸实践,既发挥着维护大一统、稳固皇权的作用,又意味着汉代礼治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
注释:
[1] 李宗桂:《汉代礼治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林中坚:《中国传统礼治》,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 (清)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77~78页。
[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页。
[4] (汉)班固:《汉书·叔孙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26、2129页。
[5]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3页。
[6]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
[7] (汉)班固:《汉书·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30页。
[8]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83~88页。
[9]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7页。
[10]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6~1209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03页。
[12]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4页。
[13] (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03页。
[14] (汉)班固:《汉书·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5页。
[15] (汉)班固:《汉书·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2页。
[1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丁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4页。
[17] (汉)班固:《汉书·韦玄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5~3125页。本节礼议各方观点皆引自此处,下不出注。
[18]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43页。
[19] 李学勤主编,龚抗云等点校:《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3页。
[20] (梁)皇侃著,高尚榘点校:《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3页。
[21] 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2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页。
[23] 顾涛:《汉唐礼制因革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24] (汉)班固:《汉书·韦玄成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18~3127页。本节礼议各方观点皆引自此处,下不出注。
[25] 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1页。
[26] 曾亦:《“亲尽宜毁”与“宗不复毁”——论汉儒关于宗庙迭毁争论中的亲亲与尊尊问题》,《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第79~89页。
[27]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54页。
[28] (汉)班固:《汉书·郊祀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64~1268页。本节王莽语皆引自此处,下不出注。
[29]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诗教下》,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8页。
[30] (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6页。
[31] (汉)班固:《汉书·杜周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