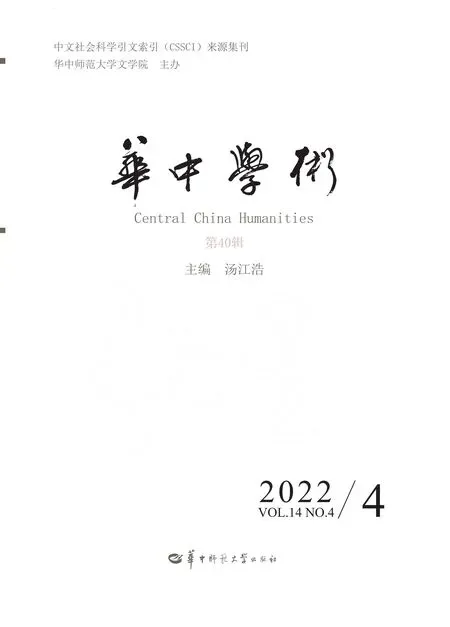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融合的文化认同
——以杨家埠木版年画实践为中心
2022-04-07张倩倩
张倩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以图像叙事为媒介的民间美术和以口头叙事为媒介的民间文学分属不同的文本体裁,这两种看似泾渭分明的文体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壁画就与民间文学产生了密切联系,民间画工借鉴口头文学的神话、传说、故事等资源,丰富了民间壁画的创作内容,而口头文学也在民间壁画的基础上通过图像的形式加以记录与传播。近几年,学界对跨媒介叙事的关注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二者之间的学科壁垒,使跨媒介叙事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代表成果中,有从“文本化:书面文字媒介对民间故事的呈现,影像化:电子视听媒介对民间故事的延展,展演化:媒介互动融合对民间故事的再造”[1]三个层面,探讨民间故事在不同媒介中的应用与转化;也有从“语言文字叙事、仪式行为叙事,以及景观图像叙事”[2]三种基本叙事形式中,探讨神话在当代社会的转化问题;还有的学者“从神话学研究出发,对此类神话叙事所属的神话图像叙事进行述评,进而探讨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特点、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对此类手工艺中所蕴含的神话叙事进行研究的可能框架”[3],在“万物有灵的创作动机、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核、境由心造的展演语境”[4]中探讨民间祀神活动这一民俗文化展演中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互融共生关系。可见,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在学界已成为学术焦点,但对于跨媒介叙事中的融合生成机制问题,学界却较少触及,成果并不显著。笔者将立足于潍坊地区的特有民间艺术形式——杨家埠木版年画,探讨民间文学的图像化与民间美术的文学化之间融合的生成机制,进而深入讨论年画中的文化符号,以期思考年画融合表达对于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重大意义。
一、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融合形态
自古以来,民间文学和民间美术分属不同的叙事媒介,在历史的发展与演变中,彼此交织,彼此借鉴,彼此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这两种看似彼此独立的叙事媒介缘何能够打破文本的形态壁垒实现交融呢?一方面,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根植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服务于民间,其深刻地反映了民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体现出一种不同于政治化与精英化的民间意趣。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份体征和审美品格为二者之间的融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另一方面,叙事作为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文本中介,为二者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与传播路径。以口头叙事为媒介的民间文学,为超越狭隘的口语叙事媒介的时空限制,促进民间文学的跨域传播,口头叙事开始向更为稳定的书面文本与图像文本输出。而民间美术则借助民间文学的叙事文本,丰富并拓展了民间美术的创作内容与审美意蕴,有效提升了民间美术的艺术品质与审美格调。作为叙事图像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便是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融合的典型范例。
杨家埠木版年画是民间艺人根据民众的生活环境、民间信仰、思想追求、审美意趣创作出的民间艺术珍品,其中既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戏曲、小说典籍,又包含祥禽瑞兽、辟邪纳福、风景花卉、政治时事、民俗风情、生活娱乐等内容。其中,数量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与民间文学融合最为紧密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本文试图以神话中的“门神”形象为例,考察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融合形态,进而理解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融合生成机制。
“门神”一词的文献出处始见于汉代,在《礼记·丧服大记》中记载:“大夫之丧……君至,主人迎,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君释菜。”[5]郑玄注:“释菜,礼门神也。”[6]。最初记载的“门神”只具有抽象的象征意义,没有具体形象指涉,随着“门神”信仰的传播与演变,逐渐被文学化为真正的“门神”形象。而“门神”的艺术图像在汉代也已初具雏形,在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代墓葬群发掘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依稀再现了那历尽沧桑的门神:“神荼”“郁垒”的艺术图像。由此可见,“门神”早在汉代就被纳入民间文学典籍与民间美术作品中,成为重要的文学、艺术形象。
“门神”的产生反映了原始先民的鬼神观念,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落后,思维原始,先民往往将生活中的不如意归罪于鬼魅作祟,而“门”是鬼秽、邪魅入侵人身的重要通道,民众遂将门神画贴于大门之上,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随着科学文化的进步,鬼神观念逐渐淡化,用以驱邪的门神逐渐演化为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与期盼的世俗化象征,民众依托“门神”这一符号化的神秘象征意义实现平安吉祥的心灵满足和情感慰藉。在杨家埠木版年画中,门神主要分为三大类:武门神,主要张贴在院外大门;文门神,张贴在院内屋门;吉祥门神画,张贴在室内房门。
1.武门神
最为常见的有“神荼、郁垒”“秦琼、敬德”“关羽、关胜”“赵公明、燃灯道人”“钟馗”五种。“神荼、郁垒”源自汉代王充的《论衡》所引《山海经》:“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藩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阅领万鬼……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7]除此之外,在《荆楚岁时记》《历代神仙通鉴》等书中,对“神荼、郁垒”所承担的门神形象也有详细记载。“赵公明、燃灯道人”因其所乘坐骑也被称为“虎鹿门神”,此形象取材于中国神怪小说《封神演义》赵公明与燃灯道人斗法的故事,因二人具有禳灾驱疫、护佑众生的本领,后被奉为门神。“秦琼、敬德”“关羽、关胜”则来源于民间传说,因勇猛善战、战功卓著、忠信仁义等优良品质在民间备受赞誉,受到民众的顶礼膜拜,故将此四人列入门神行列,成为镇宅护院的保护神。除以上所述的四对双座门神外,在杨家埠木版年画中还有一类单座门神,即钟馗。他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捉鬼、吃鬼之神,在《历代神仙通鉴》及《东京梦华录》中有关于钟馗的记载:“近节岁,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8]武门神借助民间文学中的神灵形象与英雄形象,实现了从神灵信仰向英雄崇拜的跨越,“神”不再深居庙堂高不可攀,仅供信徒瞻仰祭拜,而是走下神坛,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替百姓镇宅护院的“家神”。
2.文门神
最为常见的有:“五子门神”“三星门神”“状元门神”。所谓“五子门神”,是指“以赐福天官为主体形象,怀抱以及围绕五子,五子手中分别有牡丹、花灯、宝瓶等物,表现出富贵连登、平安喜庆等内容的门神画”[9]。其神话形象源自窦燕山教子故事,在《三字经》中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10]的记载,其后被神话化。“三星门神”则是由中国民间信仰中具有美好祝愿的福星、禄星、寿星集合而成,福星、禄星、寿星由星辰演化而来,体现了原始初民的自然崇拜,后被人格化。福星赐福天下,禄星掌管功名利禄,寿星则是中国神话中的长寿之神,后被纳入道教神仙谱系,在明代的道教典籍《金箓斋玄灵转经早朝行道仪》中详细记载了福、禄、寿三星之说。“状元门神”是杨家埠木版年画中的一种祈福门神,分左右两座,画面中状元喜骑高头大马,一手持兵符,一手持将印、相印,上有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字样,表达了民众对于获取功名利禄的美好希冀。此时的文门神不再承担镇宅护院的功能,而是将民间文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话原型纳入其中,与宗教画进一步拉开距离,展现了民众祈福的吉祥文化心理。
3.吉祥门神画
主要有“麒麟送子”“刘海戏金蟾”“连年有余”等。“麒麟送子”源自晋王嘉《拾遗记》:“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周绕室,五星降庭。”[11]“刘海戏金蟾”为道教神话故事,刘海相传为五代宋初的道士,本名刘操,字昭远,因劝谏燕帝不从,后托疾挂印而去,改名为刘玄英,道号“海蟾子”,民间将其称为刘海蟾。随着名望的扩大,民间流传的故事甚广。其后由于民众望文生义,刘海蟾被拆分与“刘海”与“蟾”,在民间有“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之说。“连年有余”运用谐音的表现手法,将“连”谐音为“莲”,“余”谐音为“鱼”,根据民间流传的吉祥动植物典故,灵活地运用到年画创作中,表达了民众朴素的生活愿望。吉祥门神画与传统门神进一步拉开距离,如果说传统门神画是一种神圣灵验的显现,那么吉祥门神画则更具生活气息。民众借助民间文学中的吉祥物、吉祥语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将潜藏在民众内心的吉祥文化心理展现出来。
二、图像叙事与文学想象的互动
民间文学的图像叙事与民间美术的文学想象从来不是独立、分离、隔绝的关系。民间文学通过图像叙事不仅丰富和延伸了传播的媒介和渠道,而且利用民间美术的直观表达,鲜明地突出了民间文学的叙事特征;民间美术借助民间文学的叙事功能,经过民间艺人的文学想象与加工,突破了民间文学口头叙事的结构框架,在解构传统民间叙事的基础上,融入劳动人民对民间叙事的审美感悟与审美体验,重新建构出一种符合大众审美特征的艺术图像。在这个基础上,杨家埠木版年画不再囿于传统民间绘画中对制作技艺、图示语言、表现手法等艺术本体的依赖,而是上升为跨媒介、跨视域、跨学科的图像叙事。因此,在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交织中,在图像叙事与文学想象的互动融合中,杨家埠木版年画超越传统绘画的艺术范式,成为一种“文学化的图像”或“图像化的文学”。
1.造型
造型主要是指对年画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设定,主要包括外形、神态、结构等方面的塑造。杨家埠木版年画不是自然主义的真实写照,也非缥缈虚幻的主观臆想,而是在遵循民间叙事的语言和文字表述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通过象征、夸张、概括等表现手法进行艺术再建构。乌格里诺维奇指出:“神的象征是对神的一种‘不似的临摹’,跟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不同,象征与所象征的对象没有直接相似之处,象征‘标示’对象但不反映对象。”[12]与中世纪宗教画对神的形塑类似,年画艺人对待非自然存在的门神,同样采用象征的表现手法。在这种情况下,门神的形象是否真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门神是否符合民众对门神形象的心理设定,也就是说,门神是否为“门神”全然由民众决定。当然,民众的决定权不是对门神定义的肆意妄为,而是基于文学作品中门神形象地再建构。于是,威严肃穆的英雄门神,和蔼安详的文官门神,赐福纳祥的吉祥门神便成为民众对门神的理想主义诠释。这时的神不在虚无中遥不可及,而是释放出人性光辉,成为抵御凶魅的守护者。既然门神要护佑人类,那么人神必须生活在一起。这时,天地之间、人神之间、虚无与现实之间、神圣与世俗之间通过艺术图像和文学感应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年画实践中,文学想象不能超越年画艺术的美学范畴而忽视年画的本质属性,同时,艺术创作也不能脱离文学想象流于扁平化的形式而无据可依,二者在互动与交流中实现图像叙事与文学想象的融合与统一。例如,在武门神中,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将虚幻的实体加以形象化构拟,塑造成身材魁伟、威风凛凛的英雄形象,为突出英雄主义般的气质,在艺术传达中,利用夸张的表现手法,将门神的头部与眼部比例合理放大,突出了武门神威风赫赫的英雄气势。而在文门神中,年画艺人充分利用文学的想象空间,根据百姓对神灵的理解与体悟,将现实中不存在的客观意象,赋予神灵以人类的基本特性,文官笑容可掬、童子灵动率真。此时的神脱下了神秘、虚无的宗教外衣,成为人类对神灵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想象的最高诠释。吉祥门神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再具备看家护院的职能,而是专门满足民众祈求多子多福、发财致富、福寿延绵的愿望和心理。麒麟,作为一种瑞兽,世间本无此物,但在年画中,把现实中狼头、麋身、马足、牛尾等进行拼接,塑造成为神形兼备、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对于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植物,如金蟾、鱼、蝙蝠、莲花、寿桃等并不进行客观描摹,而是经过文学想象与艺术加工,从形象、色彩等方面赋予人的情感,使各类动植物更显活泼、灵动。由此来看,年画艺术的文学想象并非无所依,他们依据自然界的实体但又不受实体的限制,这些灵兽为神所驱使,为百姓带来福祉,成为尘世与神灵的中介,加强了神人之间的联系。
2.色彩
色彩即赋色,年画艺人将孕育的艺术形象加以赋色,使年画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的视觉效果。杨家埠木版年画色彩鲜艳、饱满、富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同时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又使民众获得了丰富的视觉情感,不仅满足了春节的装饰需要,又给春节增添了一丝喜庆、祥和、欢乐的气氛。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色彩主要有红、黄、绿、紫、黑五种,五种颜色均就地取材,由当地的植物萃取而成,色彩较为纯净、透明。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色彩运用不以反映客观物象取胜,而是巧妙地经营色彩的位置、布局、结构,通过主观化的色彩营造,赋予年画强烈的视觉对比,从而产生丰富的情感体验。
在年画实践中,年画讲究“随类赋彩”,年画艺人依据不同的文学人物形象选择不同的设色方式,彰显不同的色彩情感。如武门神主要有大红、蓝绿、紫、嫩黄四种颜色,面部以大红色为基底,突出勇猛、威风的英雄个性,四种颜色借助于服饰、铠甲进行色彩的均衡搭配,紫、绿交错布满画面,构成人物的骨架结构,红黄镶嵌于骨架之上,形成一种庄重、威仪之感,鲜明地突出了门神的性格特征。而钟馗的面部则为紫色,再搭配狰狞可怖的面部表情,形成一种肃杀之气。“刘海戏金蟾”通过服饰变化分为黄、绿、紫、金等若干色块,增添了画面的律动感与节奏感,从而契合了“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故事情节。而对于仕女和娃娃则以白色为基调,搭配粉红的腮红和服饰,使人物形象更显秀丽与可爱。杨家埠木版年画的设色极为考究,不仅要满足传统绘画中“随类赋彩”的色彩规范,还要满足春节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和房屋内部的装饰要求。
三、年画实践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
杨家埠木版年画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记录了特定区域不同朝代和社会制度下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时代风貌;存储了老百姓为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工具、提升制作工艺的生活智慧;见证了不同时空语境下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文化的变迁。年画实践为人们提供了以直观和生动的活态形式认识民族文化的有利条件,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集体生活、民族精神遗存、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痕迹,从而更全面、更真实、更完整地还原已逝的历史面貌及文化传统。年画作为凝结劳动人民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艺术载体,体现了老百姓长期以来孜孜以求追逐美好生活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无论从年画的物质载体本身抑或是内部所潜在的精神蕴藏,无不充盈着丰富的人文讯息。年画是年俗的特定产物,是民俗生活的真实再现,尤其内部所蕴含的精神民俗——民间信仰,是老百姓长期以来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经验,是民众集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民间信仰日益决堤的当下,年画实践无疑是对当下民俗文化淡漠和精神缺失的一种适时修复与弥补,对重塑民族文化认同和推进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吉祥符号的文化透视
吉祥符号是指传达一种吉祥寓意、吉祥心理、吉祥感受的图案、纹样或文字,是劳动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对趋吉避凶、趋利避害的心理暗示。
1.吉祥符号的文化心理
杨家埠木版年画作为民众精神信仰的艺术载体,它经历了从古人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整个过程,尤其在春节年俗的映照下,通过神圣的仪式展演、行为规范、年俗禁忌、吉祥符号等为我们还原了民间百姓的信仰体系与价值系统。然而,这一系列神圣民间信仰形式的背后却直指一个中心,即:满足民众世俗化的吉祥文化心理。
吉祥文化心理是指,民众在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对平安喜乐、长寿安康、万事顺遂等吉祥文化的尊崇与信仰。在古代社会,民众往往将生活中的不如意怪罪鬼魅邪祟的为非作歹,并试图通过一系列的神灵信仰、仪式展演、吉祥符号等方式来实现趋吉避凶的世俗化诉求。于是,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如动植物、文字、器物、图案等赋予一种神秘的光环,并加以利用,而且坚信这种吉祥符号会为自己带来平安好运、吉祥止止。“你可以把吉祥当成祝颂,也可以将吉利祥和视为一种文化实体。总之,它是最美好的精神滋养,可以使人修养升华,灵魂得以净化。”[13]长久以来,民众从未停下对美好生活探寻的脚步,这种探寻无论是出于对现实苦难生活的救赎还是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憧憬,在他们的言语、行为、思想中处处洋溢着对吉祥的期盼。既然追求幸福的生活、寄托美好的祝愿是民众共同的心理诉求。那么,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必将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渗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道德、伦理还是民俗、艺术。总之,民众的吉祥文化心理的表现是具体的、是现世的、是世俗的,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满足一切向“好”的心理。但究竟什么是好,好的标准是什么?在笔者看来,民众并没有奢望能够过上骄奢淫逸的奢靡生活,而仅仅是希望能够超越原有的生活状态,实现丰衣足食、平安无虞的朴素愿望罢了。
2.吉祥符号的精神意蕴
《说文解字》中记载:“吉,善也。”[14]“祥,福也,一云善。”[15]可见,吉祥自古以来就被解释为美好之意,也就是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可以被理解为吉祥。透过年画,我们读懂了古人为追求理想的幸福生活,祈求富贵平安的吉祥意识。年画中,无论是寓意吉祥的动物、植物、器物还是保境安民的门神,都是传递吉祥文化的符号形态。吉祥符号题材丰富,通常借由人物、花卉、祥禽、瑞兽、器具、文字等形象,通过谐音、象征、借喻等表现手法赋予年画吉祥的意蕴,从而形成了色彩斑斓、喜庆祥和的吉祥画面。如“鱼”同“余”象征财富,“连”同“莲”象征多子多福,“蝠”同“福”象征福气,“寿桃”象征长寿。在构成吉祥意蕴时,各类题材交叉融合,或通过人物与祥禽瑞兽组合,或神祇与花果器物组合,分别传达不同的吉祥寓意。如童子与莲、鱼组合反映了民众对多子多福、富贵荣华的渴求;寿星与寿桃、蝙蝠组合传达了民众对健康长寿、福星高照的希冀。总之,在年画中,无论是鱼、莲、寿桃、蝙蝠还是各类神祇、童子、文官、武士等都被符号化为吉祥的寓意。在春节来临之际,吉祥年画的出现为辞旧迎新的年俗时空增添了喜庆祥和的欢乐气氛,同时也消解了老百姓对未来不确定的担忧与焦虑。
(二)吉祥年画的文化认同
年画与年俗作为中华民众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既非个人的创造,也非个体的产物,而是文化群体各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惯例和民俗通则。年画的产生、传播、演变发生在人民群众所塑造的年俗语境中,无论是年画的精神信仰抑或吉祥文化都是老百姓长期以来探求美好生活的情感反应与价值判断,内部蕴含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和共同的民族情感。
1.吉祥年画的家园意识
年画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在家家不得温饱的封建社会里,“连年有余”这点可怜的理想却为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救赎的福音。杨庆堃先生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宗教的神坛,保留着祖宗的神位、家庭供奉神明的画像或偶像。”[16]这里所提及的“神明的画像或偶像”,在家庭中最为广泛的代表自然为年画。脱胎于“宗教”信仰的年画无疑是对家园的呵护与捍卫、对家庭生活氛围的营造与建构、对家庭内部成员的护佑和庇护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核心要素,它昭示着中国人内心深层的家园意识。
门神的首要职责是对家园的守卫,防范、阻挡、抵御鬼魅邪祟对安定、祥和家园的侵犯与攻击。基于万物有灵观念,对那些无法预见和洞察的异灵、鬼魂、瘟疫等则采取巫术的手段来防范。于是,吃鬼捉鬼的钟馗、威风赫赫的将军、辟邪驱疫的猛虎则被请来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而对于家庭内部生活空间,五彩斑斓、题材各异的年画,如童子佳人、祥禽瑞兽、瓜果鱼蝶、吉祥寓意、民间故事、民俗风情、文娱劳作、道德训诫等,成为装点居家环境、规范言语行为、塑造优良品质、调剂日常生活、传承文化精神的理想媒介,不仅拓展了家庭的生活场所、丰富了家庭的生活意蕴,而且使民众以热情的姿态直面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不仅如此,年画中的各界神灵,从门神到财神,从灶神到喜神,从生育神到婚姻保护神等营造出一个神灵信仰的世界,每位神灵各自担负着自己的职责,维持着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维护着价值规范的有效运作,维系着精神家园的有序建构。
年画在为家庭环境提供了色彩的同时,也为劳动人民建构了一个多元化的精神家园,“在这个精神家园里面,有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精神世界,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形象图式,不同的俗信范围,人们的家居生活在年画的视觉包围下,获得多向度的满足、多样性的安宁、多元化的自洽”[17]。这个精神家园不是个人的主观臆造,而是现实生活的影响下,在年俗时空的感召下,在心理结构的共同作用下的达成对理想生活的满足感与归属感、家园感与幸福感。
2.吉祥年画的民族情感
年俗与春节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而年画作为春节期间的民俗事象是彰显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的艺术纽带,“这些色彩艳丽,快乐喜庆的吉祥年画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成为民间百姓的苦难慰藉,折射出民族的精神风貌”[18]。“二十四孝图”并未因时过境迁而丧失生存的语境,其中所蕴含的儒家“仁孝”思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情感,映射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族群之间的伦理关系。“寿星”“仙翁”“鹿”“鹤”“龟”“松”“桃”等寓意长寿的吉祥符号反映了中国人对待生命的理性态度。年画作为流传于中国广袤大地上的民间艺术形式,经久不衰,反映了东方文化独特的审美观与审美趣味。另外,年画中所隐含的民间信仰形式,如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动植物崇拜、吉祥文化崇拜等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信仰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年画不再是单一的艺术图像形式,而是凝聚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记忆与传统文化观念,在春节习俗的映照下,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
结语
民间文化与民间美术从来不是孤立的文化个体,年画艺人灵活运用图像叙事与文学想象的互动生成机制,实现了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跨媒介融合:民间文学通过民间美术的图像叙事功能实现了民间文学的跨域传播,民间美术通过民间文学的叙事资源,丰富并拓展了民间美术的创作题材与审美意蕴。后现代语境下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遇了难以预见的信任危机与认同危机,而以春节为背景的年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滋养了中国人最基本的家园感和幸福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注释:
[1] 徐金龙:《跨媒介叙事:民间故事资源的转化策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108~116页。
[2] 田兆元:《神话的三种叙事形态与神话资源转化》,《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11页。
[3] 王均霞:《朝向普通人日常生活实践的神话图像叙事研究——以手工艺为中心的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93~99页。
[4] 刘吉平:《意识·仪式:民间文学与民间美术的共生互融——以陕甘川毗邻区域民间祀神活动为例》,《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06~114页。
[5] (汉)戴圣主编:《礼记·丧服大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63页。
[7]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83页。
[8]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0页。
[9] 王巨山、王永海编著:《中国杨家埠木板年画研究故事·传说》,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0] (宋)王应麟编,(清)贺兴思注,子静补释:《三字经》,见《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1] (前秦)王嘉,等撰,王根林,等校点:《拾遗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12] [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2-123页。
[13] 张道一:《吉祥文化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14]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84页。
[15]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5页。
[16] [美]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17] 向云驹:《年画:作为一种视觉包围的层次与感性意义》,《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79~83页。
[18] 张瑞民,等著:《年画民俗文化及其传承与保护创新机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