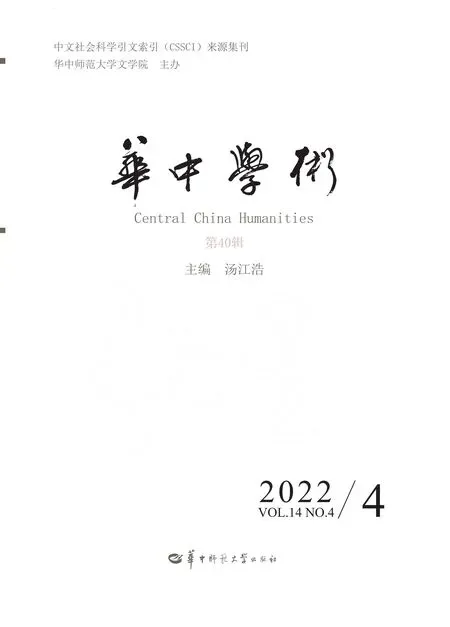朝向整体:金荣华先生民间文学思想研究
2022-04-07马培红
马培红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在刘魁立、刘守华、刘锡诚等学者推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中国民间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民间文学成果丰硕、不容忽视。要理解台湾民间文学,金荣华至关重要。从民间文学采录整理到建构资料体系,他深耕民间文学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1],是“民俗学家”[2],“壮丽的故事山”[3]的塑造者,“台湾民间文学的耕耘者”[4],“资深学者”[5],此项“学术领域中最杰出之学者”[6]。自1987年出版《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以来,金荣华正式踏入民间文学领域,以学贯中西的眼光和汇古通今的学识,在田野与文献的综合研究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理解,并与普罗普“故事作为一个整体”[7]、刘锡诚以“原始艺术现象、民间口头创作作品和民间艺术作品”[8]为研究对象的整体研究形成了对比。他对台湾民间文学生存环境的关注,对知识体系的建构,重在将中国纳入世界民间文学体系,具有聚焦台湾、面向世界的整体研究取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深入理解金荣华的民间文学思想,是对台湾民间文学的深入认识,是对中国民间文学的阐释,更是对世界民间文学体系“中国特色”的观照。
一、思想基础:金荣华民间文学的科学实践
民间文学研究离不开资料占有,要对民间文学的整体性进行阐述,就要先理解其采录整理民间文学资料的科学实践。20世纪80年代,为摸清中国民间文学现状,中国文化部(现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协作、组织搜集整理并编撰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庞大而鲜活的资料彰显了民间文学的地方性、文艺性和多样性,具有社会记忆、文化认同和学术研究等多重价值,为民间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期,金荣华深深扎根于台湾民间文学的采录整理工作,虽然他并未受到当时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影响,但在无形之中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国家话语。
金荣华民间文学采录整理秉持科学、客观的学术品质,力图呈现民间文学完整的讲述环境和讲述内容。1987年,金荣华组织当时就读于中国文化大学的学生采录民间文学作品,正如他所说的,“以民间文学的角度来开始搜集大概是从我开始的”[9],从此他开启了台湾民间文学采录的先河。在采录中,他注重呈现完整的讲述环境,摸清采录区域或民族的基本情况如人口、居住区域、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简史等,甚至画出采录地点示意图,了解该区域的文化环境,如在《澎湖县民间故事》《金门民间故事集》和《台湾鲁凯族民间故事》(1)此处鲁凯族应为鲁凯人。后同。——编者注中都有民俗、寺庙、名胜古迹等照片,直观地反映出采录地的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等状况。以《台湾排湾族民间故事》(2)此处排湾族应为排湾人。后同。——编者注为例,他不仅列出了排湾人的基本概况如人口、居住区域、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文化特色,还画出排湾人的居住区域图以及该人群在台湾的分布情况。对民间文学内容而言,金荣华认为民间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民间文学作品共生共荣,因此他在专注于采录地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歌谣等的同时,也不放过风俗习惯和信仰如瞭望台和笛子、彩虹的禁忌、秋雨等。为保证采录资料的学术价值,他在每则民间文学作品之后附有讲述者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口译者、采录时间、地点、采录者、初稿整理者等相关信息,还附上故事讲述人简介、近照、口译者简介。如《排湾族的源起》[10]中,他将资料整理为讲述:陈归名(女,75岁,排湾人,日本教育四年,家管);口译:吴水华(女,38岁,排湾人,中学毕业,船身清洁工)、张惠妹(女,35岁,鲁凯人,中学毕业,家管);时间:1996年11月26日;地点:高雄县凤山市(今为高雄市凤山区);采录:张百蓉,并将陈归名的图片等信息放置在书中。有的民间文学作品甚至记录故事的来源,如《我们为什么要种桂竹》是讲述人蔡马信“小时候听曾祖母说”[11]的。
民间文学作品是“讲唱、采录和整理三者的结合”[12],现场采录之后需大量规范化的后期整理,才能转化为可供研究的书面材料。民间文学整理是复杂的,基本流程是访问录音——转录文字——整理分析。口头叙述的民间文学与书面的民间文学在口语与文字的表达上不同,“其间差异,在转换过程中,是要有所拿捏的”[13]。金荣华认为,
口头传述的故事,若是照话直录,必然有一些芜词冗句要梳理,但这种梳理工作以不影响原有的语言风格为基本原则。其次,故事几经传述,或许有漏脱疏略之处,如语句意义不完整、情节单元残缺、关键性之说明遗漏……但是,这一类的故事有些可以揣摩出词句的本意,有些可以推求出脱略处的原貌,在有所依据的状况下应当酌予补足,只要不涉及情节变动而丧失忠实纪录的原则。[14]
民间文学来自民间讲述者的口头叙述,他们在讲述过程中可能因为赶时间或忘记或被打断等,就需要研究者在整理时进行人物角色、故事情节等的补充或完善,有些“只是梳理冗杳的词句及作填缝式的补述,并不改动任何原有的情节单元”,而“刷洗填缝式的整理……是民间文学工作者所必须做的基本工作”[15]。金荣华还注重对讲述中出现的生词或地名等进行注解,如在《老鼠怎么在生肖排行中拿了第一》中提到,“啊?其他呢?其他就是在这样排的啦,鸭就排不上啦”,金荣华对“啊”字注释,“‘啊’在闽南语中与‘鸭’同音,讲述者故谐其音”[16],这种解释能够让读者清晰领会民间文学作品的有趣之处。当然,民间文学整理中还要保留原有的语言风格和讲述人的特点,金荣华认为较早定居本地的居民的语言最能够表达作品的原汁原味,因此在采录时应多请讲述者用较早定居本地的居民的语言讲述,以保留讲述者原意和讲述风格。除此之外,金荣华在民间文学整理中更看重情节和结构的完整性,他会将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人的讲述内容进行对比分析并找出最佳版本列于书中,其他版本则作注。如《傻丈夫》的正文采用汪素玉版本,而在注解中标明:“1987年8月17日知本村林双妹女士讲过一则情节单元大致与此相同的故事,但主角是妻子不是丈夫……整个故事的结构和情节秩序以汪素玉女士所述较胜。”[17]
金荣华在田野作业中还注重伦理性。讲述者是文化的主人,而作为采录的学者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因此,一定要尊重讲述者,在采录故事时要讲明来意,取得同意。当时进行资料采录的方式主要是录音,他认为“采录第一,你不要打岔,老是打岔不行,不要老是问为什么,讲述人可能一问就被你问倒了……做一个很好的听众”[18],让讲述人能够以自己的风格把作品讲完。当然,还要尊重讲述人的讲述内容,谨遵整理原则进行细致爬梳增补。金荣华的田野经验与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在广泛的资料采录过程中,金荣华对民间文学面貌的科学整理和全面理解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资料脉络和思想基础。
二、整体思维:金荣华民间文学的思想体系建构
金荣华通过理论研究与田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剖析民间文学中的神话、史诗、传说、谚语、谜语、故事等,提炼出民间文学的差异性与共同性,进而勾连民间文学的流传区域和流传脉络,建构了民间文学有关联、有层次的知识体系。
(一)金荣华民间文学研究脉络
如果说采录整理促使金荣华形成了对民间文学生存环境的整体认识,那么丁乃通则促使他将中国民间文学置于世界民间文学体系之中,从国际层面理解中国民间文学。金荣华最早开始研究敦煌史、中外交通史,虽没有直接研究民间文学,但在《真腊风土记校注》[19]里的服饰、语言、正朔时序部分已有不少对民间文学的碎片化认识。他真正介入民间文学研究始于丁乃通。丁乃通从金荣华的《十洲记扶桑条试探》中看到了他的学术潜力,认为以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方法是可以接力自己进行民间文学研究的,之后“阅读笔记小说和各种故事,对我便不再只是欣赏和消遣,也是资料的存储和检索了”[20]。随后,金荣华在丁乃通借用芬兰学派AT分类法编制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21]中发现其分类框架并不完全适合扎根于独特历史文化土壤的中国民间故事。于是他在沿用丁乃通民间故事类型基本框架的基础上编制了《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一、二)《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第一、二、三、四册),为民间故事研究增添了新鲜的研究资料,增强了类型索引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为了更全面搜集资料,金荣华认为“目录学很重要,一个学科没有目录学,你就根本不知道该学科都有哪些资料”[22]。为了对民间文学资料有更为全面的把握,他倡导对新增材料进行持续性关注,这也是金荣华民间文学整体性思想的进一步科学追求。
当然,民间文学的整体性认识离不开金荣华多元的知识结构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从中外交通史到敦煌学,从古典文学、通俗文学到民俗学都是他的研究范围,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半路转向,不过“主力放在民间文学”[23],并在该领域独树一帜。他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古典文学及比较文学专业,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修习图书馆学专业,多学科的知识学习使金荣华接触到了中国古典文学,了解了比较文学,熟悉了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合并归类方法,出版了《比较文学》《敦煌俗字索引》《元明杂剧异体字索引》等著作。多学科的知识积淀让他能够迅速切入民间文学领域并熟练地将多元知识融入民间文学研究之中,奠定了金荣华民间文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另外,在美国、墨西哥、韩国的学术研究经历使金荣华深受多国文化影响,让他能够立足国际平台对文化的交流性与共享性有更深刻的体悟。
金荣华从实践中汲取经验,继承了国际通用的AT分类法和丁乃通的学术传统,汇通中西古今,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对民间文学深入而系统的理解,逐渐丰富了民间文学的整体性思想。
(二)金荣华民间文学研究路径
金荣华民间文学的整体思维源于对田野与文献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的科学把握。其中,田野与文献的综合研究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金荣华尤其如此。他一方面从田野中理解民间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地域流变,比如他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人物讲述的《七尺无露水》五则传说要点的罗列,发现该传说是同一人同一事,只是在传述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或省略。另一方面,他通过文献理清民间文学的历史脉络。而这得益于他扎实的文献研究能力,金荣华在文献研究中精耕细作,出版了《王绩诗校注》《中国文学史初稿》(宋代文学部分)《中暹交通史论丛》《中韩交通史事论丛》《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敦煌吐鲁番论集》《禅宗六祖求法事迹考》等著作,形成了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田野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为他提供了更丰富的研究材料和更广阔的研究空间,使他能够发现并解决社会生活中的民间文学问题。比如,金荣华在韩国参观关庙时发现汉城关公的关庙[24]中有一些中国关庙没有的特色,他结合文献及实地调研情况,认为关公作为一名被神化了的人物,由于显灵助战的传说而久受朝鲜君臣的尊崇,进而判断关公信仰已经深入韩国民间。
民间文学研究离不开跨地域、跨国家、跨民族的比较分析,从比较中可以发现事物本质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金荣华的比较思想与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进行的比较文学研究密不可分,他认为,“透过比较的方法,从二者的相同之处,探求其源流,从二者相异之处探求其意义”[25]。不管是对地理流布的分析还是追根溯源的探讨,都是在从不同地方所得的口传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综合比较中逐步实现的。金荣华将在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搜集的《台湾陈办歌》[26]与以往研究进行对比后否定了向达所认为的该书是道光初年刊本的观点,认为此书是道光中叶刻本。《定婚店》[27]是一个世界性故事,金荣华通过比较不同地方不同身份的男主角,并与中国最早记载的《定婚店》《灌园女婴》对比,推断该类型故事的源头是印度。有些故事是多个故事的综合体,需要抽丝剥茧、由表及里才能看清楚其真面目。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28]的情节单元分别对应德国、印度、小亚细亚等地的三则民间故事,也就是说,该故事是中国民间说话人和冯梦龙捏合上述三则民间故事而成,它们可能都是其故事源头。除了对民间文学作品源流的探索,他还通过对比寻找作品之间的差异性。民间文学是流动的,活态地存在于民众口头,民众会结合地理、生态、人文等对其进行加工,如《拿捏石头比力气》在欧洲是巨魔和人比力气,人用干酪冒充,在有些说法中就将干酪替换成鸡蛋、石灰等,这都是民间文学结合地方文化进行的本地加工,也是民间文学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流传时产生的“瑕疵”。
(三)金荣华民间文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整体性是在事物联系中对其外在特征和内在本质的系统把握。金荣华的整体性思想建立在对民间文学资料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中国古代的史书、方志、通俗小说如《搜神记》《清平山堂话本》《月令广义》等,现代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十六册)》《台湾排湾族民间故事》等,当代民间故事家如刘德培、谭振山、金德顺等人的故事集以及各地少数民族故事集,国外如英国的《坎特伯利故事集》、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印度的《五卷书》等都是金荣华民间文学研究的主要资料。当然,这种整体性也源于对AT分类的认识,“AT的世界性,就是大家会觉得每一个故事视野也可以放宽一点,并不是说每一个故事都要研究全世界的,但你要了解每一个故事的世界性”[29]。金荣华不断完善民间文学资料之间关联的、层次的知识体系在民间故事研究中表现得尤为耀眼。
为了让民间故事整体性更为完善,金荣华结合中国民间故事实际情况,针对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存在的如归类不妥、排列不妥、中国故事等问题对原有故事类型索引进行增补修订。他将古印度故事《弃老国》《旧毯》、日本故事《弃老山》、尼泊尔故事《铃铛》、中国故事《破碗》等进行比较后,认为这些故事在AT分类中应属981“躲藏的老人智救王国”、980A“半条毯子御寒”、980B“劣器恶食养老父”等类型[30]。据统计,他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增订本)中,新增类型有编号105A猫的看家本领没有教、159A.2老虎误含了火枪管[31]等百余个;在《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32]中,新增类型也有十余个,这些修订增补是金荣华结合田野与文献资料对已有学术成果的有效补充,也是对民间故事分类体系的完善。
民间文学资料在地域、时间、民族上的关联,有助于摸清民间文学作品的源头以及发生的变异。民间故事一直处于民众的生活传统中,历时性的流变和共时性的扩展是同时进行的。金荣华借助飞头传说[33],认为晋人的飞头传说流行于交趾,唐代除交趾外,还流行于占城,元、明时期除占城外,还有越南中南部的宝童龙国,显示了民间文学历史的、跨国的、多地域的知识网络。当然,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间的关联也可以透过民间故事表现出来。如编号为543的“蜘蛛鸟雀掩逃亡”情节流传在回族的《蜘蛛救穆圣》、东乡族的《上马杀土狗》、藏族的《英雄拉龙·博吉都杰》、壮族的《农智高成神》等民族,体现了多民族彼此交往、共同发展的局面。如果上述只是部分地建构了民间故事之间的时间、地域和民族的关联,那么金荣华的《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和《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增订本)则将民间故事的时间、地域与民族维度的故事流变清晰且全面地显露出来。如索引编号为400的“凡夫寻仙妻(牛郎织女)”,从时间上能看到该故事从晋代的“汉董永千乘人”到清代的“牵牛织女”的演变,从地域上可以看出该故事在四川、浙江、广西、云南、台湾等不同区域的具体形态如北京的“张二遇蛇仙”、贵州的“侗笛声声”等,从民族上可以看到该故事在土家族、彝族、苗族、侗族等民族中的流传,建构了同类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网络关系。
不管是民间故事的情节单元索引还是类型索引都呈现相互关联的层次性,金荣华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与《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就凸显了这一点。如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金荣华将“神奇的兄弟姐妹”的层级分布为:第一层级的“一般民间故事(300—1199)”,第二层级的甲“幻想故事(神奇故事)(300—749)”,第三层级第2的“神奇的亲属”,第四层级的“450姐弟俩;451公主沉默救兄长;451A小妹寻兄长”,其中450姐弟俩之下还有新疆的《姑尔娜和迪尔达》《三个孤儿》《姐姐和弟弟》,俄罗斯的《俄罗斯故事》、德国的《格林童话》、荷兰的《荷兰童话》、法国的《魔境和牧羊女》、希腊的《希腊童话》、意大利的《意大利童话》,这种层层细分的分类体系展现了民间故事的整体框架,不仅确立了每一类型故事在整个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而且建构了整个民间故事的知识体系。金荣华认为,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与他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增订本)《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合在一起,构成了民间文学资料之间的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的有层次的整体性,既从宏观上建立了层层细分的金字塔式的民间故事知识谱系,又从微观上揭示了民间故事的内在关联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
虽然上述体系只是有书面记录的金荣华见到的民间故事,“并不能够概括整个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和情节单元”[34],AT分类也并不是金荣华的独特创造,但是依然可以从他填充大量的资料并增订修补民间故事分类体系中看出其力图建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世界民间故事资料体系整体性的学术旨趣。
三、多维表达:基于整体性的金荣华民间文学思想的深层意蕴
民间文学源于民众的生活实践,承载着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表达着朴素的道德认知、文化知识和家国情怀。民间文学可以超越民族和地域成为多民族、多地区交流交往的媒介,也可以跨越历史见证前后相继的生活变化。从国家、民族、生活的维度挖掘金荣华基于整体性的民间文学思想的深层意蕴,可以洞悉其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深刻思考与情感表达。
(一)国家观念与中国特色
金荣华一直将台湾民间文学研究置于中国民间文学的框架中,努力建立台湾与大陆民间文学的联系。在采录方面,他虽然以台湾民间文学为主,但是不断奔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从河北耿村的“在大陆第一次和说故事的农民在他们耕作的田地上交谈”[35]到广西罗城采录的情歌《山上树多树林林》,从青海、陕西、广西到贵州、云南等地都有他的身影,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通过采录中国多地的民间文学资料形成对中国民间文学的整体认知。在交流方面,为了加强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联系,“跨越海峡道不孤”[36],他参与多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并以整理、研究、推广民间文学为宗旨创办中国口传文学学会,陆续出版《汉译外国民间故事书目》《火神眷顾的光明未来——撒奇莱雅族口传故事》(3)此处撒奇莱雅族应为撒奇莱雅人。后同。——编者注《台湾花莲赛德克族民间故事》(4)此处赛德克族应为赛德克人。后同。——编者注等著作。在资料使用方面,金荣华始终站在国家立场研究民间文学,在研究中他发现台湾望安岛上陈秀女士讲“父子题诗”与“山西大同及河北涉县一带流传的父子题诗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37];故事类型编号210“弱小联合克强敌”出现在四川《母鸡与野猫》、陕西《神锅》、广东《熊人婆》和台湾《台北乌来民间故事》中,也体现了两岸故事的内在联系。两岸民间信仰的联系也很密切,金荣华深挖澎湖鸟屿[38]的岳飞传说,认为由于岳飞字鹏举,民间传说他是金翅大鹏鸟转世,因此岳飞信仰和台湾澎湖鸟屿透过民间传说联系了起来。
金荣华在探究两岸民间文学关系的同时也在挖掘民间文学的中国特色。他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不断新增中国独有的故事类型强化民间文学的中国特色。如只在中国出现的《人若有理神也服》[39],主要表达了人承认神的超自然能力,但当人神发生冲突时人可以据理力争,显示了人神的基础性平等,而这正是深层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现。事实上,各地语言差异也会形成中国民间文学的独特韵味。故事《不怕老虎只怕漏》主要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流传,金荣华比较了梵文、北印度语、孟加拉国语、日语、西班牙语和中国汉族北方语系、潮州方言、闽南方言里的“虎”和“雨”的读音,只有粤东的潮州方言“虎”和“雨”的语言和声调完全相同,都音ho,上声,闽南方言这两个字都音ho,只是声调稍异,也就造成了故事中人不怕虎而怕漏的特殊现象。金荣华从国家视角出发,积极以民间文学为桥梁建立两岸的交往交流平台,探索两岸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发掘中国民间文学的独特价值观念和地方特色,而这正是对国家认同的生动阐释。
(二)民族特色与多民族关系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互交织的历史关系让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整体且有层次的多民族民间文学结构体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按照自己民族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艺术传统等对民间文学进行改变或再创造,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金荣华自对台湾民间文学进行采录以来,就开始有计划地对不同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整理,他以卑南人为起点,先后以鲁凯人、排湾人、赛夏人、阿美人等为调查对象,有计划、系统性地整理了《台湾卑南族民间故事》(5)此处卑南族应为卑南人。——编者注《台湾鲁凯族民间故事》(6)此处鲁凯族应为鲁凯人。——编者注《台北县乌来乡泰雅族民间故事》(7)此处泰雅族应为泰雅人。——编者注《台湾赛夏族民间故事》(8)此处赛夏族应为赛夏人。——编者注《台湾花莲阿美族民间故事》(9)此处阿美族应为阿美人。——编者注等故事集,实现了从一到多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目标,彰显了中国不同民族民间文学的特色。金荣华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它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每个民间故事都承递本民族的某些传统”[40]。鲁凯人的《蛇郎君》[41]中,鲁凯人老人所采的花为象征女子贞节的百合花;故事中的蛇为鲁凯人敬重的图腾——百步蛇,这些细节都体现了鲁凯人的民族传统与特色。而要论卑南人民间文学特色的话,则在于其强烈的教育意义。不管是故事本身的教育意义,或是口述者增添的教育意义,或是在其他民族不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卑南人都发展为具有明显教育意义的故事如《人变山羊》等,在十二岁以下孩子的教育上担任了重要角色。
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中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形成了与中华民族密不可分的关联,凝聚了一种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金荣华认为上古神话在后世都有与之相应的民间故事,也有与之相应的真实事件,与精卫填海相应的愚公移山体现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相应的真实事件如张巡、史可法的守城行为仍是中学教材,与“夸父追日”相应的“夸父山和桃林塞”则是附会于夸父追日而形成的地方性传说,对应的是王阳明的“格竹”。金荣华认为一则简单的上古神话,能在本民族长期流传,在后世有与之相应的故事还有真实的历史事件被人们相信,那么这则神话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与意义,“已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其行为价值观的一部分了”[42]。他通过历史、神话、故事的综合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会随时代发展附着于不同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但是体现的价值认同是不容置疑的。
(三)生活传统与民间文学形塑
各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塑造了五彩斑斓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那些“有足够的听众认同,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43]的作品,所呈现的是民众的生活传统。因此,透过民间文学可以挖掘当地民众的精神风貌、生活态度,展示民间文学的生活相。
民间文学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作品角色、情节等细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民间文学流传地区的文化背景或社会习俗。金荣华通过搜集《拾金者故事》历代典籍的多篇异本,和中国、西班牙、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拉伯等地的同类型故事,从钱的类型与重量,在古籍中出现时间推断该故事应与中国14世纪中叶的社会环境相关。民间文学也与民俗观念密切相关,民众会据此对民间文学进行种种情节内容编排。金荣华在整理水鬼与渔夫的47则故事之后,认为“投胎转世的观念,阎王、土地和城隍的信仰等等”[44]交织形成了这一故事的民俗基础,故事中的神鬼形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神鬼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45],进一步来说,故事的世界也就是人的生活世界。
民间文学吸收宗教思想的养料,将不少高深莫测的宗教观念通过民间文学表达出来,成为人们易于接受的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因果报应等思想在民间文学中流传广泛。在佛经《众经撰杂譬喻经》的《人在险境》故事中,险境就是绝境,在欧洲这种险境通过增加情节、人物行为的后果等得以解释,而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对险境的处理是不入境,中外的相同之处都是教人不被无畏的困境困住,差别在于欧洲的处理方式是入而求解,中国的处理方式是悟而无须解。两相对比,揭示了中国民众面对困境的生活态度,也将佛教难以为普通人所理解的“悟”通过民间文学变得通俗化。禅宗扎根于社会底层,对民间文学影响巨大。就拿“民间的反唱歌与禅宗颠倒偈”[46]来说,“颠倒偈”需要佛僧领悟禅宗真谛,不免要反复吟诵,久而久之就流传到禅门之外,而民众因其新奇有趣又不以常理的叙述,从生活中取材,进行颠倒唱述,二者自然就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金荣华认为宗教与民间文学的结合一方面将高深的禅宗思想进行了通俗化的演绎,扩大了宗教文化的传播范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增加了民间文学的趣味。民间文学与生活、宗教紧密相连的背后是对民间文学所处生活世界的立体把握和深刻理解。
结语
金荣华扎根于田野,从民间文学资料采录出发,在完善中国民间文学的台湾资料的同时,将台湾乃至中国民间文学资料置于世界民间文学资料体系,构筑不同国家、地域、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之间的知识谱系,使世界民间文学的中国特色熠熠生辉。
金荣华民间文学的整体性是由故事文本、讲述者、讲述时空所构成的资料的整体性;是超越时空的知识体系的全面性;是包含不同故事内在的共同观念的价值的联系性。他从国家观念、民族特色和地方生活维度透析中国民间文学,是对其蕴含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以及对民众生活实践与民间文学关系的整体把握,更是对中国民间文学之特色的有力诠释。
注释:
[1] 陈丽娜:《因应无碍——论金荣华教授之民间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37期,第79~100页。
[2] 陈劲榛:《民俗学家金荣华教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1页。
[3] 鹿忆鹿、陈丽娜:《一座壮丽的故事山——金荣华先生访谈》,《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第51~60页。
[4] 应裕康:《金荣华:台湾民间文学的耕耘者》,《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61~63页。
[5] 王甲辉、过伟:《台湾民间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217页。
[6]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等编:《金荣华教授七秩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2007年,刘兆祐序第1页。
[7] [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7页。
[8] 刘锡诚:《整体研究要义》,《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1期,第16~21页。
[9]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7日14点至16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10] 金荣华:《台湾排湾族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7年,第11页。
[11] 金荣华:《台北县乌来乡泰雅族民间故事》,台北:中华民国民间文学学会,1998年,第38页。
[12] 金荣华:《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前言第1页。
[13] 金荣华:《金门民间故事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7年,金序第5页。
[14] 金荣华:《台湾卑南族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2年,第4页。
[15] 金荣华:《台湾卑南族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2年,第11~12页。
[16] 金荣华:《澎湖县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年,第150页。
[17] 金荣华:《台湾卑南族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2年,第75~76页。
[18]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7日14点至16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19]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金荣华校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2015年。
[20] 金荣华:《治学因缘》,《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9~80页。
[21] [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郑建成,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22]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7日14点至16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23] 访谈时间:2017年5月12日13点至15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24] 金荣华:《汉城关庙的传说和特色》,《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57~60页。
[25] 金荣华:《比较文学》,台北: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第3页。
[26] 金荣华:《文学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2018年,第221页。
[27] 金荣华:《〈定婚店〉故事试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82~85页。
[28] 金荣华:《冯梦龙〈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故事试探》,《黄淮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51~53页。
[29]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7日14点至16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30] 金荣华:《谈孝——就所知民间故事印证其演进,并论AT980、980A和980B三型故事之分类》,《民间故事论集》,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67页。
[31] 金荣华:《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增订本)第四册,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4年,第1251页。
[32] 金荣华:《中国历代笔记故事类型索引》,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9年。
[33] 金荣华:《从汉文资料看飞头传说之发展及其流行区域》,《民间故事论集》,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37页。
[34] 访谈时间:2017年4月27日14点至16点;访谈地点: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金荣华老师办公室;访谈对象:金荣华;访谈人员:杨之海、马焓予;整理人:杨之海。
[35] 金荣华:《记第一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学研讨会缘起——寿贾芝先生百岁华诞》,《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第24页。
[36] 金荣华:《跨越海峡道不孤》,《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349页。
[37] 金荣华:《澎湖县民间故事》,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年,前言第2页。
[38] 金荣华:《澎湖鸟屿之岳飞传说及其信仰试探》,《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15年第31期,第55~64页。
[39] 金荣华:《人若有理神也服——从民间故事看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38-39期合刊,第1~8页。
[40] 金荣华:《鲁凯族民间故事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2期,第33~34页。
[41] 金荣华:《鲁凯族口传故事试探》,《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223页。
[42] 金荣华:《神话省思三则》,《民间故事论集》,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13页。
[43] 金荣华:《民间文学概说》,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15年,第5页。
[44] 金荣华:《〈落水鬼仁念放替身〉故事之衍变及其型号之设定》,《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166页。
[45] 金荣华:《从六朝志怪小说看当时传统的神鬼世界》,《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296页。
[46] 金荣华:《禅门偈语与民间反唱》,《禅宗公案与民间故事——民间文学论集》,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7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