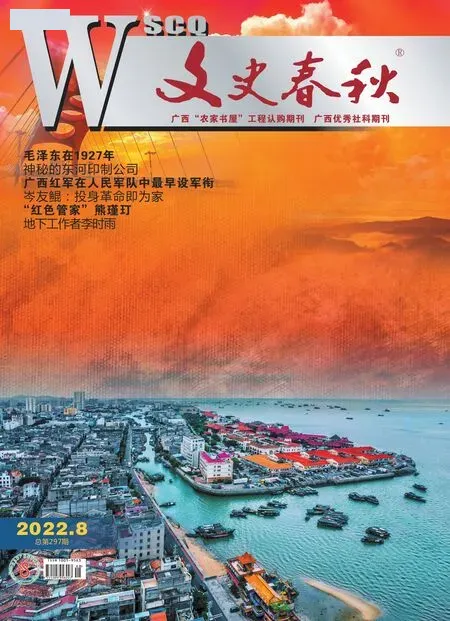广西红军在人民军队中最早设军衔
2022-04-06韦英思
● 韦英思
一般认为,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之初,并没有设立军衔。据《军事史林》杂志2010年第1期刊发的《人民解放军首次军衔制度实行始末》等资料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改编为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中央军委(以下简称“军委”)曾于1938年通知准备实行军衔制,以符合全国抗日军队总体制度,并利于正规化指挥;当时八路军、新四军一些负责对外交往的干部,也被临时授予军衔。但军委随即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正在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不具备正规战的条件,而且强调等级制不利于密切官兵和军民关系,因而,全军部队并未真正和全面授衔。
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环境原因,局部范围内有一支英勇的红军部队在创建之初就设立了军衔,实行军衔制,这就是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是人民军队中最早实行军衔制度的革命队伍。
人证、物证、文证:广西红军有军衔
广西红军实行军衔制的情况,在当事人的回忆及有关文献的记载中,虽断断续续零星出现,但确切、多角度佐证了广西红军有军衔这一史实。
袁任远(1898—1986),原名袁明濂,参加过五四运动。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事部派袁任远到南宁,在张云逸领导的广西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同年10月,袁任远随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赶赴百色,参加百色起义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在百色起义大会担任司仪;百色起义后,先后任红七军政治部总务科科长、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11月红七军集中河池整编时,任军教导队政委;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途中,任团政委;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任军前委委员、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中共湘赣省委秘书长、湘鄂川黔军区大庸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他在1981年《星火燎原》丛刊第6辑发表的文章《从百色到湘赣》回忆到:起义前夕,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准备军旗、刻制各种印章、胸章、臂章。胸章是分等级的,将级军官的是红边,校级军官的是黄边,尉级军官的是蓝边。这些具体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大约在起义前的一两周,就广泛开展起义的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并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思想教育。
开国中将莫文骅(1910—2000)多次在回忆录中讲到自己被授予尉校军衔的亲身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二十年打个来回》(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中,莫文骅回忆说,他1929年7月考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10月在部队开往百色之际,张云逸任命他为第四警备大队副官处中尉副官。“百色起义不久,组织上分配我到红七军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机要参谋,管行军、作战、电报(有线电报)和其他机要工作。”在《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中他又提及,1930年4月、5月,红七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黔桂边打游击,6月又回师百色,“入百色不几天,我的工作又有所变动。因第一纵队要成立辎重队,军部同意李谦的推荐,要我去任少校辎重队长,我即离开军部,到一纵队报到,负责纵队的后勤保障。”在另一本回忆录《百色风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里,他更明确说道:“我担任过二十师少校辎重队长(红七军开始是有军衔的,后来取消了)。”
莫文骅在《二十年打个来回》还提到自己的中学和军校同学、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黄奇彦也有军衔:“1929年12月11日起义成立红七军,我当中尉参谋,黄奇彦当中尉监印官,我管作战,他管关防。”黄奇彦在红七军军部任参谋,是红军中的漫画家、诗人,随部队转战江西,1934年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光荣牺牲。
《百色起义人物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记载,莫文骅1929年“12月11日,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军部中尉机要参谋”。
开国少将黄一平(1903—1980),原名黄启滔,广西贺县黄田镇(今属贺州市平桂区)新村人。1925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回到广西。1927年5月,中共广西地委成立,黄一平当选为委员,负责农运工作。1929年10月,黄一平赴百色参加起义,任红七军政治部社会股股长,并当选为百色县苏维埃委员,负责肃反、财政工作;1930年1月,兼任警卫总指挥李明瑞的特务队政治指导员,不久调任营政治指导员,在河池当选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兼团政治委员。红七军北上途中,他被安排到桂林做地下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2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刊登了黄一平的自传,黄一平在自传中提到自己被授予军衔的情况。他于1930年10月在红七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红七军前委委员,任团政治指导员(政治委员),在河池“整编部队,全军编为3个师,每个师辖2个团,我被提升为团政治指导员。红七军有等级制,我当营指导员是少校,团指导员是上校,因为不能越级提拔,讲究形式,在任团政指前,还调我任总政治部中校秘书几天。跟着向江西前进”。也就是说,红七军在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初,仍实行军衔制。此时距红七军成立已有10个多月。
关于广西红军设立军衔的情况,相关史志资料也有明确记载。《广西通志(1979—2005)》记载,许凤翔“1929年夏到南宁参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十九师部少尉副官”;《平乐县志·人物传》提到,许凤翔参加百色起义后,“任红七军十九师上尉副官、会计股长”。两处衔级似乎并不一致,但细究可发现,少尉是他当副官时的军衔,上尉则是他任副官并作为会计股长时的军衔。
许凤翔(1908—1991),广西桂林平乐县桥亭乡人,1925年,考入平乐团练讲习所,后到广西农民运动讲学所学习,结业后投身农民运动。1928年,他与同村10多人前往广东乐昌县当兵,次年春转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上士文书,部队开到南宁时升准尉司书;参加百色起义,转战到江西后,任师参谋处科长。他在1983年8月1日撰写《攻占榕江前后》一文,文末署名为“原红七军司令部副官处少尉副官”。在另外一篇文章《回忆红七军转战途中的筹粮工作》中他写道:“1930年9月,红七军在广西河池整编,我从军部调到十九师师部经理处当上尉会计股长。”这与黄一平自传中记录的红七军整编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时,仍实行军衔制是一致的。
《红七军红八军英烈传》(解放军出版社,1991)也提及:百色起义后,杨英“在红七军特务连当少尉司务长”。土匪武装趁红七军主力分兵游击右江各县、百色城防空虚之机,偷袭百色城,杨英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且出身好,又是党员,得到军部领导的重用,“很快提为特务营的中尉副官”。
杨英(1911—1934),湖南省邵阳人,14岁在长沙加入桂军,在李明瑞的师部当警务兵。1929年,杨英加入中国共产党,随部来到南宁,任第四警备大队会计;百色起义后任军特务营副官、军前委委员、第二纵队营政治指导员;红七军远征时任团政治委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先后任红十九军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独立第二十四师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3月在一次突围战斗中牺牲。他与莫文骅有很深的革命情谊,在百色并肩战斗时,曾送给莫文骅一枚金戒指,该戒指现珍藏于百色起义纪念馆。
1985年1月24日,河池市为7位老同志隆重举行追悼会,在红七军老干部卢继馨的生平简介中,提到他“1930年10月参加红七军,在政治部社会股任少尉干事”。卢继馨的同村亲戚,曾担任其通讯员、警卫员的卢福泰回忆,卢继馨在河池整编时参加红军,因有文化,会做群众工作,表现积极,被分配在二十师政治部社会股任少尉干事,后因工作出色,被军政治部主任兼二十师政委陈豪人调到身边工作。
卢继馨(1901—1966),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河池镇人,河池地下党的开拓者、组织者和游击队的创始人之一。红七军北上到广东乐昌时,部队被敌人包围,队伍冲散,卢继馨被俘。敌人押解他回广西到达南宁时,他趁人来人往混乱之际,巧妙逃脱,后曾到小学任教;1939年,考入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毕业后以乡长等各种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他任中共河池特支委员,曾把当地的打猎队改编为抗日自卫队,发动胞弟、妹夫参加抗日活动;1946年,任中共河池特支书记,组织武装游击斗争,后任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潘敏文在其文章《我的祖父辈们》中介绍,自己的家乡是田阳县被称为“红军屯”的百育镇新民村花茶屯。1926年,上级党组织派到百色工作的第一位地下党员余少杰当时经常到花茶屯,就住在潘敏文家里,并在他家召开了奉仪县(今田阳县)第一次农民运动骨干会议。他的曾祖父潘仲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财政委员,后在掩护群众转移时,因子弹打尽,被敌人杀害。他的祖父潘尚书踏着父亲的足迹参加了百色起义,“担任红七军第二纵队第三营营部上尉副官即党支部书记兼第十一连指导员,从此过上军旅生活”。
红八军实行军衔制也有史料可循。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后,红八军成立,同样实行军衔制。红八军虽因当年3月被敌人袭击,战斗失利,幸存的骨干人员不多,但军衔制也有迹可循。1985年中共南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的《左江革命根据地史实(1926—1930)》记载:黄履中“原是红八军二纵队少尉副官”。1930年3月20日龙州县城战斗失利后,红八军军部率余部撤离,3月28日部队整编为1个团,下属3个营,黄履中为三营副官,而且从“少尉提为上尉”,其回忆录原件,现存于南宁市邕宁区党史办。
另据现存于河池市档案馆,老红军潘兆昌1950年4月亲手填写的《行政人员登记表》,他“1929年10月—1930年8月 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第一纵队任上校政治部主任”。在1956年的《干部自传》中,他又写道:“1930年春,党指示我在红八军第一纵队负责上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兵运条件成熟,党成立红八军,并任命俞作豫同志为军长,任命潘兆昌为该军第一纵队上校政治部主任。
潘兆昌(1907—1974),广西玉林市北流县人。1927年1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国民党清党时被迫出走广东,后参加广州起义。俞作柏、李明瑞执掌广西军政后,潘兆昌回到俞作柏任大队长的广西第五警备大队,参加兵运工作。龙州起义时,潘兆昌任红八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在一纵转战桂滇越边,与红七军会合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在凌云县彩架村与敌人激战中身负重伤,潘兆昌被敌人俘虏。不久红军再次攻占百色,将他从监狱救出,送往东兰及广州医治。因伤病无法快步行走,红七军远征时,潘兆昌便留下从事地下工作。
时情、地情、兵情:广西红军实行军衔制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广西红军实行军衔制,并非为了给军官以特权,部队仍是实行真正的官兵平等。河池整编时,普通士兵李朝纲入选作为领导核心的前委成员,而军参谋长仅是候补委员;起义后全军首次发饷,无论官兵,无论军衔大小,每人都是20元。
综合当时的情况,这支革命队伍实行军衔制,是基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客观条件。
其一,广西红军基础干部因兵变而来,最初大都脱胎于李明瑞指挥的国民党桂系部队一部。国民党军队是实行军衔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仅在其部队开展工作三四个月的情况下起义,为保持和加强对起义部队的领导,也实行军衔制度。
其二,广西红军广大基层指战员主要来自桂西地区,而百色、河池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仅百色就有壮、汉、瑶、回等20多个民族,语言上多语并存,方言土语差异不小。1930年1月,军委在香港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讨论会上,报告人汇报广西军事工作进展情况时说,第一个时期,军委还未建立,士兵运动还不能有计划地开展,且好多派去的同志都因不耐其苦而离开;第二个时期,贺昌同志成立了军委,这才开始有计划地注意士兵运动,但依然是进展较慢,虽然又有计划地派了些人到军队中去,可惜都因语言不通而未取得有效成果。红七军老战士黄征在文章《回忆右江赤卫军第十二连》中写道:“队伍的语言很杂,有土话、壮话、白话、客家话,在湖南,人们都称我们‘蛮子兵’。”从红七军成长起来的开国少将欧致富到井冈山任指导员时,首次在全连用白话做指示,壮族战士听了心领神会;汉族战士听了一愣一愣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即使在远离战场的医院也是如此,红七军军医处处长吴清培是福建人,部队里壮族人多,而他不懂壮话和广西白话,便找到红七军护理兵李华清做自己的翻译。同样做医护工作的老红军谢新亭提到,红七军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调来部队工作的反“围剿”中俘获的几个军医听不懂广西官兵的白话,工作起来既困难又常弄得哭笑不得。开国中将冼恒汉在《难忘的记忆——兼述我参加红七军的经过》中写到,他刚参军时,多少懂一些普通话,“但是说白话和普通话开始不流利,人家还笑我们说偏了。时间长了,壮话、白话、普通话我可以讲了,工作起来方便多了”。这种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设立军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跨越和克服语言障碍,区别军人等级。
其三,在广西红军成立和北上转战江西途中,受到地方军阀、民团、国民党嫡系的围追堵截,大小战斗接连不断,各级干部身先士卒,伤亡很大,替换频繁,出发时的两位师长,一位英勇牺牲,一位身负重伤,第十九师的两位团长都已牺牲。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右江约有3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及,红七军自第二次右江出来游击,受了数次打击,干部死伤颇大,老兵余下不及十分之一。彼时设立军衔,明确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责任,便于指挥和管理,是应对战时残酷环境的需要。